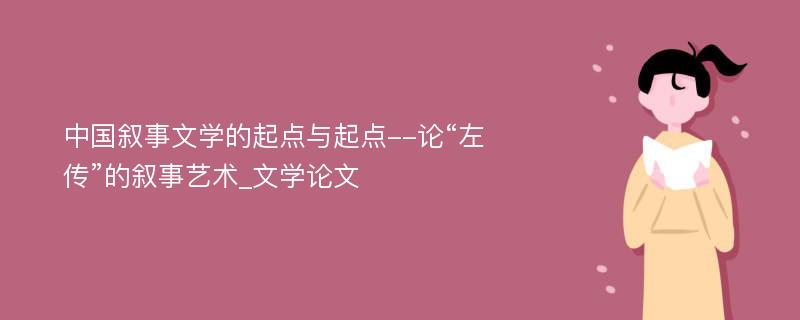
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开篇论文,中国论文,起点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6)05-0043-06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有多个源头。有人说古代的神话传说是源头,有人以为《诗经》中的叙事诗是源头,有人指出《庄子》、《韩非子》、《列子》里面的寓言是源头,还有人说志怪小说才算得上是源头,更多的人则认为千古叙事文学之源头当推《史记》。看来,中国古代的子书、史书,记录神话的书,再加上口头传说,都可以看作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中国叙事文学的产生应该是多源头,而不是单源头。但源头与起点不同。《左传》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与开篇。在《左传》之前的《春秋经》虽记事,但没有“情节”;《诗经》中也有叙事的篇章,但那是在“歌唱”故事,重点在抒情,是抒情文学的一种,不能算叙事文学。寓言则注重背后的理,很难称为叙事文学。真正具有叙事文学要素的是《左传》。
关于叙事文学的要素,西方的叙事学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里我只想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实际情况做点考察。我的考察是这样: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要素有三点:即情节(讲什么)——演进(怎么讲)——视角(谁讲)。第一是情节,情节是叙事文学的内容,即讲什么。诚然,叙事文学就是通过事件的展开来讲故事,但所讲的故事能不能成为叙事文学的一个要素呢?这就要看故事所展开的事件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即故事的情节化。如果讲一些看不出联系的孤立事件,那么这故事还不能构成情节。20世纪英国作家福斯特曾把“故事”和“情节”作了比较,说:“‘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便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因伤心而死’则是情节。”[1] (P75)“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了”,这不过是两个偶然事件排列在一起,本身不包含文学意义。但“国王死了,王后因伤心而死”,就把两个事件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就获得了文学意义。因此,对于叙事文学来说,情节比偶然的故事排列更具有文学意义。难怪亚里士多德不但指出悲剧的六要素(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歌曲),而且认为六要素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2] (P21,23)。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注重整体的观念反映到叙事文学上面,就必然重视故事中事件的联系,这样才能使读者知道“前因后果”,才会获得意义的启迪。第二是演进,情节在文本中如何发展,如何把在某个空间里面发生的事件,放到一定的时间秩序中来叙述,这对叙事文学来说也是一个基本要素。中国文化使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演进带有明显的中华民族特色。第三是视角,即这情节由谁来讲,采用一个怎样的视点来讲,这也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一、《左传》的“故事情节化”
为什么说《春秋经》不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起点,而说《左传》才是起点?道理就在于《春秋经》只是单纯的事件排列,没有或基本没有揭示事件之间或事件内部的因果关系,即没有情节化。例如按照《春秋经》隐公元年,作者排列了“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3] (P5—8)。这是鲁国的史官对于鲁隐公元年的记事。这里有事件,但无论是事件之间还是事件内部,都没有揭示其因果关系。这样从文学角度说,就是没有意义的。《春秋经》虽然叙事但不是叙事文学,原因是没有情节。但解释《春秋经》的《左传》就不同了。它不但把事件的具体情况加以展开,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事件之间或事件内部的因果关系。如以《春秋经》鲁隐公元年的一个事件“郑伯克段于鄢”为纲,《左传》所写“郑伯克段于鄢”,不但把这个事件具体化,更重要的通过揭示因果关系而情节化。如姜氏生了庄公和共叔段两个儿子,可为什么不喜欢庄公而喜欢共叔段,多次要武公立共叔段?《左传》作者回答说,这是因为“庄公寤生,惊姜氏”之故。共叔段是庄公的亲弟弟,庄公不为他的兄弟着想,一味放纵他,闹到共叔段一再违制,最终要造反,这时候竟然下狠手把他的弟弟收拾了,这是为什么?《左传》写道:“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3] (P14)这种对于《春秋经》“郑伯克段于鄢”写法的解释,从文学上,并不是很高明的,但其用意在于回答上面的问题,使事件内部的因果关系昭示出来,使故事情节化。就是说,哥哥攻打亲兄弟,是因为弟弟太放肆,哥哥又太阴险,终于闹成兄弟骨肉之间自相残杀。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强调“故事情节化”,最早就是从《左传》开始的。可以说《左传》把通过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使故事情节化,不论从大处的宏观的角度,还是从细处的微观的角度,都十分重视因果关系的揭示。
如晋文公的兴起和称霸的故事,这是《左传》中的重大事件。作者写他在流亡各国中所受到的礼遇和非礼之遇,接着写“晋楚城濮之战”。那么,晋文公重耳为何能获得城濮之战的胜利,成为五霸中势力较强的一霸?《左传》在描写晋楚城濮之战之前,就先讲战事是由楚国围宋、宋求救于晋开始的。这时候作者通过回叙,说晋公子重耳经过19年的流亡,回国获得君位。仅过了两年,就想用兵。子犯晓之以理,提出先要教导民要“知义”、“知信”、“知理”,然后才能获得民心,形成力量,最后才可用兵。晋文公重耳一一照办,终于富国强兵,这才能在晋楚城濮之战中获得胜利,奠定了称霸的基业。这就给整个城濮之战晋国用兵取胜从原因上作出了一个整体的解说。或者说,就是给城濮之战这个关系到战国新局面形成的故事注入了情节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左传》为了强调晋文公重耳终成霸业的原因,还两次借对手楚成王之嘴作出解释。第一次是在“重耳出亡始末”中,重耳到了楚国,楚臣子玉要杀重耳。楚成王不同意,说:“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理。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3] (P409)第二次是在城濮之战进行过程中,楚成王在晋文公退避三舍之后,感到了晋国军队的压力,他退入自己管辖之地,又命令申叔离开穀,子玉离开宋,并说:“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3] (P456)楚成王的这两次分析,似乎是在关键时刻,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实际上是作者有意用对手的分析从宏观上说明晋文公兴起和称霸的大背景和根本原因,这里的因果关系是作者着力之笔,不可不察。
不仅如此,从僖公二十四年、僖公二十七年、僖公二十八年,从“重耳流亡始末”到“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兴起整个过程的描写,又从微观的角度,用许多看似游离故事主干的细节描写,来解释晋文公终成霸业的原因。如描写重耳逃亡进入卫国,卫文公对他无礼,连吃的东西也没给,他向农民讨饭,农民不但不给,还故意扔土块给他,他愤怒了,要鞭打这些农民。但子犯解释说:这是天赐啊,为什么不要?于是行稽首大礼,载着这些土块走了。这种“突转”的描写,以象征性的解释来说明重耳日后的成功。又如,城濮之战开始前不久,郤縠被委以中军将。为什么单单委任他,赵衰有一套说法;不久郤縠去世,由原来任下军佐的原轸越级升为中军将,也解释说,原轸“上德”。事件中人物角色的变化,也一一说明其原因。在城濮之战即将开始的时候,晋文公作了一个梦,梦中与楚王扭打在一起,发现楚王伏在自己身上,吸吮自己的脑子,自己反倒仰面朝天。为此晋文公感到害怕。又是子犯为他解释说:好梦啊,我得天,而楚王则伏其罪,楚国将归顺我们。这些细节,都可以说是“闲笔”,无关宏旨。其实不然。作者正是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说明晋文公得到上天的帮助,力图为晋文公的称霸寻找原因。又,重耳返国取得君位之后,和城濮之战后,都有一些看似无用的细节描写,如重耳的小跟班叫头须的求见的故事等,都可以说是“闲笔”,但“闲笔不闲”,说明晋文公知错必改。
故事情节化,看重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的描写,可以说是《左传》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一大特色。西方小说也注意事件因果关系的描写,但比较之下,除了那些专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外,其因果关系的描写并不十分细密,而其追求也主要在艺术情趣方面。《左传》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与后续中国叙事文学一样,它们注重事件发展中的因果关系的描写,这与中国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文学传统之一是重“道”。儒家、道家等都有自己的“道”。“道”是什么?道的本意是道路,后引申为道义、道理、规律、学说等,如《论语·里仁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4] (P232)“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4] (P244)《论语·里仁下》:“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4] (P257)《孟子·滕文公上》:“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5] (P319)“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5] (P393)。这是儒家之道。儒家之道以人与人之间的“仁”的关系为核心。道家则把“道”理解为自然万物的源头。《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 (P174)因此古代的“道”不论儒家重在人伦之道,还是道家重在自然之道,都有原初的整体的道理和根据的意思。叙事文学在中国古代的开篇是“史”,所谓“叙事实出史学”(章学诚)。所以文学叙事也必须讲“道”,即要说明事件发展过程的来龙去脉、因果根由。事件发展过程中的“突转”还是“发现”等,都要有“道理”贯穿其间,都要有因果关系使其联系起来,才能成为一个由主旨贯穿的整体性情节。对于读者来说,也才能很好地理解它,并明白其意思所在。正是由于受“道”的影响,中国叙事文学作者要使一篇作品有一个明确的意思,读者也一定要读出一个明确的意思来,决不能像某些西方的小说那样意义朦胧或含混。兄弟不能自相残杀,要兄友弟恭,这是“郑伯克段于鄢”这一章的意思所在。要经过长期的磨难和曲折,在许多人的帮助下,一个人才能获得成功,这是“重耳流亡始末”这一章的意思所在。要自己和自己属下的人民都“知义”、“知信”、“知礼”,这才是富国强兵之路,这是“晋楚城濮之战”这一章的意思所在。这些意思怎么才能被发现,这就要在事件发展中强化因果关系的描写,因为在因果关系中,意思才会自然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左传》为开篇的中国叙事文学,表层是在讲“故事”,可更深层则在讲“意思”。
二、《左传》叙事的“演进”
“怎么讲”的问题主要关系到一个故事展开的时间演进问题。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这是普通常识。但在文学叙事中,就出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一个是讲故事人讲的时间。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可以称为“故事时间”;讲故事人的时间,可以根据讲故事人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前面讲,或把前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后面讲,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时间”。文本时间的顺序与故事时间的顺序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这些都是叙事学的一般道理。问题是中国的叙事文学的时间演进与西方国家叙事文学的时间演进是否各有特点呢?表面看是没有什么不同,如中外小说都有顺叙(顺时序)、插叙和倒叙(逆时序),实际上因文化的差异各有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的叙事按自然时间演进的占了绝对多数,逆时间的演进,如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就拿前面我们谈到的“晋公子流亡始末”和“晋楚城濮之战”来说,多是按照事件的自然时间顺叙,个别地方虽有插叙,其作用也很有限。《左传》中所谓“几大战役”(“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的描写莫不按自然时间演进。可能受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左传》影响,像后来的《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莫不如此。那么为何《左传》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多按自然时间顺叙呢?这里有深层的文化原因。这主要是中国古代“上农”,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看重耕田种地,而耕田种地当然要对四时的更替特别敏感。因为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守时,顺时,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不误农时”。就是对于那些在精神领域活动的人来说,也明白“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7] (P693)的道理。这种从农业文明所滋长出来的文化观念,都不能不影响叙事文学对于事件演进时间的把握与运用。即从守时到顺时,折射到文学叙事上则是更重视顺叙,认为顺叙最为自然,也最能为大家所接受。
其次,《左传》和其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即使有倒叙的逆时间演进,也与西方神话、小说的那种倒叙的功能有所不同。西方叙事作品擅长逆时的倒叙演进,其功能往往更多是为了制造惊人的悬念。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是一种逆时的倒叙的典型,故事一开始就叙述忒拜城遭受天疫,神谕告诉大家,是有人犯了乱伦的罪孽。于是俄狄浦斯开始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过去的事情一件一件被揭示出来。这种逆时的倒叙打乱了原本事件正常的次序,一下子把人带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出人意料的状态中,由此造成强烈的悬念,出现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就让人联想到西方人在大海上坐船来往做生意,此时还是风平浪静,一切如常,突然风暴兴起,巨浪滔天,船只摇荡,甚至不幸沉没。因此西方小说的倒叙往往留下了海洋文明的印痕。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也有逆时的倒叙演进,但往往是激烈冲突过后的一种绵长的回忆,一般很少那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以“初”开始叙述,就是一个倒叙演进。所有的矛盾都已经结束,郑庄公已经打败了向他挑战的亲弟弟,他在颍考叔的帮助下,得以在“黄泉”下与母亲姜氏相见,挽回些许与母亲的感情。《左传》的这种逆时倒叙演进,决无惊心动魄的效果,也没有让读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这就像秋天过后,一位获得了丰收的农民在一个休息日,一边饮着茶,一边向他的朋友平静地叙述一年的经过,尽管遭灾,备尝艰辛,最后一切都很完满。这种节奏舒缓的逆时倒叙演进,是否可以说折射出中华古代农业文明的特征呢!
再次,《左传》作为对《春秋经》的解释,在标示时间的时候,与西方的计时方法,按照日、月、年的顺序来标示不同,是按照年、季、月、日的顺序进行的。如僖公二十七年,按照“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夏,齐孝公卒”,“秋,入杞,责无礼也。”“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3] (P442—443)。从年,到某季,到某月,到某日,这种由大而小的时序安排,与《左传》的史书性质相关,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西方重个案分析,从细部切入到整体把握,哲学上重个别到一般,折射到文学叙事上面,首先想到的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天,然后才是到月,最后才是年,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的时间排列。中国的年、季、月、日的时间排列则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密切相关。整体性的传统文化特点体现在叙事艺术上,就是所谓的“以大观小”的笔法。“以大观小”的说法可能最初是从中国绘画笔法上提出来的。沈括说:“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却)[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8] (P170)沈括谈的是绘画的空间问题,他所批评李成的画法恰好就是西方的“透视法”,而他主张的恰好就是中国传统的“散点法”。其实,不但中国古代绘画与西方绘画有此差异,从《左传》开始的叙事文学也有此差异,不过此种差异从空间透视变成为时间演进问题。中国叙事文学年、季、月、日的“以大观小”的时间演进与西方叙事文学日、月、年的“由小到大”的时间演进有很大不同。《左传》等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总是先要从一个时间大框架中说起,然后再一步步沉落到更具体的时间。如《左传》就首先要纪年,然后是这年的春或夏或秋或冬,然后才是月,然后才是日。后来的《三国演义》第一回是这样开始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纷争,又并入于汉;汉末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建宁二年四月癸巳,帝御温德殿……”[9] (P2)三国的纷争,却从周末七国争雄开始讲。这样就看出了一个历史的“走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同观山,从山顶上往下望,山下的一丘一壑都历历在目,山的走势也一目了然,这就是“以大观小”,这是中国叙事文学时间演进的特点。它的意义就是关注故事演进的整体性,把部分看成是整体的部分。西方叙事文学的“由小到大”的时间演进,则让读者从下往上望,先看到眼前的一重山,山上的丘壑,山的走势,开始的时候都还看不到,要一步步往上走,才能逐渐领略到。西方叙事文学时间演进的特点,是分析型的,看完一景,再看一景,现实性很强。
以上分析说明,在怎样讲的问题上,主要在叙事时间的演进上,从《左传》始,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三、《左传》叙事的“视角”
故事的内容即情节有了,怎样讲也确定了,就产生一个由谁来讲的问题,一个故事由不同的人来讲,关系到看这个故事的视角,视角不同,所见的也就不同。视角的叙事特征通常是由人称来决定的。《左传》的叙事视角有什么特点呢?
当然,按照一般的叙事学理论,立刻就会说《左传》是按照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叙述的。这当然没有错。问题是《左传》的第三人称视角与别的叙事文学的第三人称视角又有何不同。《左传》叙述人是史官,其叙述视角是史官的视角。《左传》的作者是不是孔子提到过的左丘明,众说纷纭。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史官,编写历史就是这些史官的任务。《左传》是根据《春秋经》编写的,肯定是当时鲁国的史官的作品。在《左传》中经常出现“不书,不以告也”。原来,鲁国史官所写的历史,是由各诸侯国通报而来,如果事情发生了,别的诸侯国没有通报,并不了解情况,就只能“不书”了。这些地方明显地说明《左传》作者是鲁国史官。
史官的叙述视角有什么特点呢?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史官的口吻问题。这种口吻使叙述处于“真”与“幻”之间。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史书虽然力图给我们造成一种客观记载的感觉,但实际上不外乎一种美学上的幻觉,是用各种人为的方法和手段造成的‘拟客观’效果。”[10] (P15)《左传》的叙事人是史官,用史官的口吻来叙述,中间又有如“不书,不以告也”的声明,所以读者误以为这是完全真的。实际上《左传》只能做到大体的真实,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真实。《左传》所写的许多对话是在密室和睡房中进行的,史官并不在场,他何以能知道,而且还知道得那么详细,这是不可能的,完全是推测出来的虚构之词。不过,《左传》这种在“真”与“幻”之间的状态,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内容,也因此它才有文学价值。
第二,史官写史的价值取向问题。中国的史官与他所服务的君主是什么关系呢?是否可以说史官都是君主的附庸,完全没有独立的观察和客观的写作态度呢?或者反过来,是否可以说史官书写历史完全是秉笔直书,对于当权者完全没有阿谀奉承的可能?根据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考察,中国古代的史官多数在“隐幽”与“直笔”之间。一方面,史官不能不顺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管理,看当时帝王将相的脸色是常有的事情,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说明了这一点。孔子是鲁国人,在《春秋》所记的两百四十年中,鲁国先后有五个君主被杀,一个被赶跑,这在当时是很不成体统的大事,但孔子删改过的《春秋经》,竟然全部隐去,一字不提。为什么孔子要这样做,因为他不能不照顾鲁国君臣的意见和面子,不能不笔下留情。另一方面史官又有“贵信史”的职业意识,不但不能事事皆隐,有时候还要有独立精神,秉笔直书,“按实而书”,以求揭露事实真相;在“直笔”不可能的情况下,也要用“曲笔”委婉地透露出事实的真相来,与当权的君臣拉开一定的距离。概而言之,中国古代史官的叙述视角处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左传》作者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首先,作者在叙述的时候,力图与当权者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尊重事实真相,确有“贵信史”的一面。如宣公二年,有“晋灵公不君”一章,其中写到晋国史官董狐在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晋灵公之后,就直笔书写:“赵盾弑其君”。赵盾找董狐去评理,认为他自己没有杀君,是他的弟弟赵穿干的。但董狐回答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11] (P663)《左传》还引孔子的话赞美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1] (P663)由此可见《左传》作者赞赏“实录无隐”的态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又写了齐国史官直笔书写“崔杼弑其君”,结果被杀;史官弟弟照样续写,结果还是被杀。第二个弟弟又照样书写。其中谈到“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12] (P1099)可见,《左传》作者是赞扬和向往史官的秉笔直书精神的。或者说《左传》作者是持史官实录“信史”观的。在对具体事件的描写中,尽管《左传》作者是鲁国的史官,但也并非一味吹捧鲁国君臣。如在《晋楚城濮之战》中,对于鲁君在这一过程中的暧昧态度,采取客观的态度,其中写道:“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指鲁僖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3] (P452)明明是鲁僖公派公子买去保护卫国,但在楚国打不过晋国的情况下,为了取悦于晋国竟然把公子买杀了,骗楚国人说,他驻守时间未满就想走,所以杀了他。作者不顾自己是鲁国的史官,不顾鲁僖公的面子,把他想两头讨好的态度如实写出来,这里不无讥讽嘲笑。其次,又不能不看到,《左传》作者写史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与当权君臣相一致的,他评价历史的标准主要是以天道、礼乐和仁义为政教标准,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规范,甚至还有“尊王攘夷”的正统观念,而这些标准、规范和观念又不能不影响他对事件的增饰夸张,对人物的“刺讥褒贬”。特别在那些细节虚构的部分,作者的标准、规范和观念作为一种视点所起的作用可能就更大一些。
《左传》是一部不朽的历史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开篇,它对中国文学叙事发展的影响很大,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左传》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