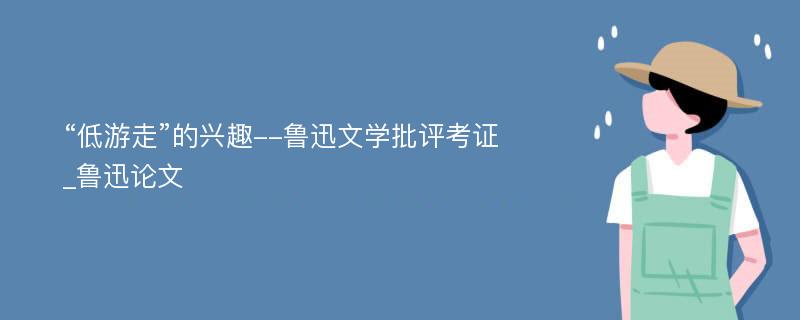
“低徊”的趣味——关于鲁迅一个文学批评的笺疏与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文学批评论文,趣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对废名从《竹林的故事》到《桥》、《莫须有先生传》的小说创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揭示其创作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的一段话: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①
鲁迅显然是批评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不过鲁迅这里用的是史的笔法,即所谓的“春秋笔法”,没有直接提出批评,而是说“从率直的读者看来”,似乎不完全是自己的意见,语调颇为客观,有效地缓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之意。其实,这恰恰也是——或者说也包括——鲁迅自己的意见,因为据作者自注,这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写讫”,而在此几乎同时,鲁迅在《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的开头,就这样批评废名说:
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②
这里的“顾影自怜”,显然与《〈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的“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是互文关系,甚至可以看作后者的最直接的出处。而就此时着力写作杂文的鲁迅来说,自然也可以说是一个“率直的读者”。按,《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鲁迅生前没有公开发表,收入后来的《集外集拾遗补编》中。这并不是说鲁迅有所顾忌而故意使用“春秋笔法”来回避直接的批评,合理的解释也许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那样措辞是史论的文体原因之使然。史论当然有作者的史识,但史识必须出诸客观化的“公意”而尽量避免过于个人化的“私意”形式。鲁迅深于史学,自然长于此道,有《中国小说史略》在前,他对这种文体当然是得心应手。此似小节,实属大端,历来论述鲁迅文学创作之“艺术”者众,而于《中国小说史略》等孜孜以求证其“史识”者亦众,其实领略其史著的“笔法”,未尝不是推敲其“史识”的正途,抑或有助于深于认识其文学作品的“艺术”。这当然不是本文的论题,不贤识小,敝帚自珍,姑且附识于此,权当“入话”。
“有意低徊,顾影自怜”,语意明了;“低徊”可与“顾影自怜”互训。从具体语境来看,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废名作品的思想内涵的特征:“哀愁”是内核,却“以冲淡为衣”。二是指废名作品的艺术形式的特征:“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也就成了所谓的“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一体的,“哀愁”的思想却艺术地表现为“以冲淡为衣”,自然是不直接“闪露”其“哀愁”之思想主旨。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下文从两个方面进行笺疏和考释。
一
鲁迅所谓的废名创作自《竹林的故事》之后“不久”发生的变化,自然是指从《桃园》开始的,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符合废名创作的实际。周作人在给废名这第二部作品集《桃园》所写的“跋”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废名君的小说里的人物也是颇可爱的。这里边常出现的是老人,少女与小孩。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这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像,特别是长篇《无题》中的小儿女,似乎尤其是著者所心爱,那样慈爱地写出来,仍然充满人情,却几乎有点神光了。……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在这一点上废名君的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③
周作人把“隐逸性”解释为废名创作变化的重要原因,而所谓的“隐逸性”即他在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从意见的异同上说,废名君似很赞同我所引的说蔼理斯是叛徒与隐逸合一的话”。这实际上是含蓄地说明了废名创作的变化与周作人自己从“叛徒”到“隐士”思想变化的关系。在这篇“跋”文写作的同时,周作人在给另外一个弟子——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所写的“跋”中,周作人这样解释了他们师徒们走向“隐士”的原因:
……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④
所以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说:
周先生在文体风格独特以外,还有所注意的是他那普遍趣味。在路旁小小池沼负手闲行,对萤火出神,为小孩子哭闹感到生命悦乐与纠纷,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在中国新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无一个人有与周先生相似处。
并且进一步指出“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
作者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那样活到那片土地上。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
也就是说,废名创作的变化,来自周作人的思想“趣味”的影响。沈从文还说:
冯文炳君所显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细微雕刻,给农村写照,其基础,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有一点忧郁,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对宇宙光色的眩目,有爱,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作者是诗人(诚如周作人所说),在作者笔下,一切皆由最纯粹农村散文诗形式下出现。作者文章所表现的性格,与作者所表现的人物性格,皆柔和具母性,作者特点在此。⑤
这个分析和周作人的说法相近,而“有一点忧郁”云云,却又可以用来解释鲁迅所谓的“有限的‘哀愁’”——这种“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那“一点忧郁”,当然诚如鲁迅所说的不过是十分“有限”的。
被周作人称为“几乎有点神光了”的《无题》就是出版单行本时的《桥》。朱光潜对《桥》的分析,比沈从文更为深入地说明了废名是如何“以冲淡为衣”来表现其“哀愁”的艺术特征:
《桥》颇易使人联想到梅特林的名剧本《Peleas et Melisand》,所写的好像也是一种三角恋爱,而氛围气息却没有一点人间烟火气。其中的主角虽都是青年,而每人身上却都像背有百岁老人的悲哀的重负与老于世故者的彻悟。……在《树》的那一章里小林赞赏细竹的谈话说:“厌世者做的文章总美丽的”。《桥》的基本情调虽不是厌世的而却是很悲观的。我们看见它的美丽而喜悦,容易忘记它后面的悲观色彩。也许正因为作者内心悲观,需要这种美丽来掩饰,或者说,来表现。废名除李义山诗之外,极爱好六朝人的诗文和莎士比亚的悲剧,而他在这些作品里所见到的恰是“愁苦之音以华贵出之”。《桥》就这一点说,是与它们通消息的。⑥
这种“没有一点人间烟火气”的“百岁老人的悲哀的重负与老于世故者的彻悟”,自然要被鲁迅视为“有限的‘哀愁’”并且大不以为然了。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批评的意义了。作为“战士”的鲁迅,坚持的“绝望的反抗”,自然对这种从“叛徒”到“隐士”思想变化,会大不以为然。因此,鲁迅对废名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周作人的含蓄批评。鲁迅显然比沈从文更清楚地知道废名和周作人的关系。本文开头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和同时写作的《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是互文关系,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鲁迅不仅批评了废名的“文学不是宣传”观点,而且进而以不指名地批评周作人结束文章的:
但文人又不愿意做这样的文人,于是他只好说现在已经下掉了文人的招牌。然而,招牌一下,文学观也就没有了根据,失去了靠山。
但文人又不愿意没有靠山,于是他只好说要“弃文就武”了。⑦
这里所谓的“他只好说现在已经下掉了文人的招牌”、“他只好说要‘弃文就武’”云云,是有出处的,是暗用了“今典”的:两个“他”即周作人。周作人在1934年12月写的《弃文就武》一文中说:“我自己有过一个时候想弄文学,不但喜读而且还喜谈,差不多开了一间稻香村的文学小铺,一混几年,不惑之年倏焉已至,忽然觉得不懂文学,赶快下匾歇业,预备弃文就武。”⑧废名的“文学不是宣传”说,显然直接来自周作人的“言志”说,这也是鲁迅这篇《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最后归结到对周作人的不点名批评的原因。
对废名的这种“有限的‘哀愁’”尚且大不以为然,而这种“有限的‘哀愁’”却又要“以冲淡为衣”,自然更是大不以为然,但鲁迅所谓的“以冲淡为衣”,恐怕更主要是对周作人的批评,只是这个批评的意旨比《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表述的更加隐晦。废名并没有说过“以冲淡为衣”这样的话,这其实是周作人文章中一再出现的“关键词”。早在1925年,周作人就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⑨,后来还自我解说是“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⑩,等等;而其30年代初一再以“苦”字命名他的散文集,如《苦茶随笔》、《苦竹杂记》,甚至有斋名曰“苦雨斋”,等等。这才真正是“以冲淡为衣”文饰其“苦味”。而在鲁迅看来,这“苦味”自然也不过是“有限的‘哀愁’”而已。这样看来,“以冲淡为衣”一语,就是出典于周作人的话语。再从鲁迅这篇文章写作的具体语境来看,更为直接的原因恐怕有两个。其一,从1933年到1935年鲁迅写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篇文章为止,鲁迅发表了《小品文的危机》(1933年10月)、《小品文的生机》(1934年4月)和《“京派”与“海派”》(1934年2月)、《隐士》(1935年2月)等著名文章,批评的矛头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周作人,至少都与周作人有关。其二,还与周作人1934年在《人间世》发表《五十自寿诗》并引起轰动性事件有关。诗中所谓“吃苦茶”、“玩古董”云云,诚为反讽,真正是“以冲淡为衣”来表达为鲁迅一语道破的“讽世之意”(11)。因此,“以冲淡为衣”一语,既隐含而又明显表露了鲁迅这篇文章在批评废名的同时对周作人的批评。就“笔法”而言,是鲁迅将杂文“笔法”用于“史笔”的佳例。
换一种角度来看,注重《〈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作者的小说家身份,鲁迅对废名的批评也是意味深长的。作为《呐喊》《彷徨》的作者,鲁迅的创作主旨如其自述是:“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2);“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13)。这和废名的那种周作人所谓的“小说里的人物也是颇可爱的”、甚至“几乎有点神光了”的写法,创作思想显然有截然的区别:说到底,鲁迅进行的是文化批判,而废名却别出心裁地书写文化牧歌与挽歌。对此,卞之琳的比较分析很有见地:
鲁迅早期写乡土小说,笔墨凝练,好像进行铀浓缩,早有火药味;废名早期以至到更炉火纯青时期,写小说却像蒸馏诗意,清甚于水。他同鲁迅早期的一些小说一样,以南中水乡为背景(他以内地的湖北,不像鲁迅以近海的浙东,历史环境也有发展先后不同的因素),却写成了田园诗。他的小说里总常见树荫,常写树荫下歇脚,所以正中由厌恶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军阀统治,到厌恶政治以至最后不免“下水”的周作人的下怀——他不是早已老爱捧苦茶在树荫下坐坐吗?周作人说废名写小说并不逃避现实,废名晚年自己忏悔逃避现实,客观事实恐怕却证明他的小说创作也还是反映现实的,只是反映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他在小说里(诗里也一样)常无端插入以点概“宇宙”、“世界”、“天下”之类话,好像(实也真是,不过从自我出发)以天下为怀了,认识不深,难于捉摸,有“哀愁”倒是可称“无限”,像西方十九世纪末一些探索无门的诗人爱用这个夸大的形容词一样。所以经过“呐喊”、“彷徨”,视域扩大,认识深化,发展到三十年代的战斗者鲁迅,就说废名“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满他“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有意低徊”等等了。(14)
卞之琳虽然是“京派”中人,虽然也并不讳言自己曾经从废名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15),但他从不同的创作思想和风格的角度来分析鲁迅对废名小说的批评,说得十分到位。而在创作上更直接受到废名小说影响的沈从文,则因为创作思想的相近,反倒更欣赏废名的小说,对废名小说的文化意义曾有这样出人意外的论述:
时代的演变,国内混战的继续,维持在旧有生产关系下而存在的使人憧憬的世界,皆在为新的日子所消灭。农村所保持的和平静穆,在天灾人祸贫穷变乱中慢慢的也全毁去了。使文学,在一个新的希望上努力,向健康发展,在不可知的完全中,各人创作,皆应成为未来光明的颂歌之一页,这是新兴文学所提出的一点主张。……在这地方,冯文炳君过去的一些作品,以及作品中所写及的一切,算起来,一定将比鲁迅先生所有一部分作品,更要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作品,这种事实在是当然的。(16)
显然在沈从文看来,“维持在旧有生产关系下而存在的”中国农村,有如鲁迅小说所表现的那样一个黑暗的“吃人”的世界的一面,同时也有如废名小说所表现的那种“农村所保持的和平静穆”的一面,那是“使人憧憬的世界”,甚至更是“中国典型生活”;一方面鲁迅小说以及受其影响的20年代乡土小说已经成为对中国农村叙事的主流叙事模式,从而遮蔽了中国农村面貌的一个方面,使得废名小说所表现的中国农村已经“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另一方面则由于这个世界“在天灾人祸贫穷变乱中慢慢的也全毁去了”,虽然这是“时代的演变”的必然,但却是“民族复兴大业”的文化资源(17),因而不免使人“低徊”,令人“哀愁”。——这里也不妨再补充一个我们历来忽略的历史细节:沈从文这样高度肯定废名作品的思想价值的论述,鲁迅是否看到过,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收入《论冯文炳》的《沫沫集》却是在鲁迅写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之前的1934年4月出版于上海;而鲁迅写作此文并编定这部小说选集时,沈从文已经是著名的作家了,然而鲁迅不仅在文章中只字未提,而且小说集中也没有选一篇沈从文的作品,实在令人意外了。
二
鲁迅所谓“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的“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这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是指废名“低徊”的趣味在艺术上的表现形式,或曰文体特征。对此,我们不妨先看对废名其人其文知之甚深的朱光潜和周作人的论述。
朱光潜在分析《桥》时,首先指出“《桥》几乎没有故事”的艺术特征,并且有这样精到的细致分析:
我们毕竟离不开戏剧的动作,离不开站在第三者地位的心理分析,废名所给我们的却是许多幅静物写生。“一幅自然风景”,像亚弥儿所说的,“就是一种心境”。他渲染了自然风景,同时也就烘托出人物的心境,到写人物对风景的反应时,他只略一点染,用不着过于铺张的分析。自然,《桥》里也还有人物动作,不过它的人物动作大半静到成为自然风景中的片断,这种动作不是戏台上的而是画框中的。因为这个缘故,《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它容易使人感觉到“章与章之间无显然的联络贯串”。全书是一种风景画簿,翻开一页又是一页,前后的景与色调都大同小异,所以它也容易使人生单调之感,虽然它的内容实在是极丰富。(18)
我们所要补充的是,《桥》“写人物对风景的反应”,“风景”不仅是“自然风景”,人与事往往也是人物注目的“风景”,特别是写小林对琴子和细竹的欣赏。这样《桥》的叙事重点不在于讲故事,更没有将故事情节化,而是着力写人物对自然风景、对人与事的心里反应、情绪波动或人生领悟,确实如朱光潜所说,每一章都“是诗境,是画境”,并且“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因此《桥》不仅写人物(主要是主人公小林)流连光景、低徊不已的人生态度与姿态,同时也表现出流连光景、低徊不已的叙述特征。
而周作人对《莫须有先生传》的“文章的好处”的分析,和朱光潜对《桥》的艺术分析,看法十分相近,却是对废名小说文体特征的更为形象、生动的说明:
《莫须有先生》的文章的好处,似乎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情生文,文生情。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几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19)
也正如陈言所谓的“结果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过程”,这就更是流连光景的低徊趣味了。
朱光潜的评论和周作人相近之处就在于他们均欣赏废名的“文章的好处”,差异则在于朱光潜立足于小说本体而有所批评,周作人却是将小说当作散文阅读而欣赏其“文章的好处”。他们共同欣赏的“文章的好处”,恰如上文引述的那样,是欣赏废名文章流连光景的低徊趣味,也就是鲁迅批评的“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行文不惜篇幅地恣意枝蔓,流连忘返于一枝一蔓、一花一叶,这样的文章“从率直的读者看来”自然也就是“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了。
自废名的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到最后一本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周作人均写有序跋,一再表彰废名作品的“文章之美”、“文章的好处”。这些也都是鲁迅这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写作之前的事,鲁迅自然十分清楚周作人对废名作品的这种表彰,因而他对废名作品的价值判断和周作人截然相反的批评,显然是对周作人之废名论的批评。
这里我们尚需作进一步的探讨,因为问题可能不仅仅是这样的简单。
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还这样说过:
但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由于对周先生的嗜好,因而受影响,文体有相近处,原是极平常的事。用同样的眼,同样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支笔,把这境界纤细的画出,成为创作了。(20)
也就是说,周作人所欣赏的废名“文章的好处”,恰恰来自周作人的艺术影响,他们的作品“文体有相近处”。沈从文的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也为后来的研究所证实。舒芜《两个鬼的文章——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中说:
孟子形容有本源的泉水,滚滚地往下流,昼夜不停,把洼下之处注满,又继续向前奔流,这叫做“盈科而后进”。周作人散文最有这种“盈科而后进”之美。他评论废名的文章:“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这些话用来说他自己的文章更为适合。
接着舒芜连举三例,十分细致、详尽地分析了周作人的这种艺术特征,这里不妨节引其对周作人著名的《喝茶》一文的分析:
例如早期的名篇《喝茶》,由喝茶说到茶食,说到江南茶馆中的“干丝”,于是详叙其制法与味道而外,并详叙茶馆中吃“干丝”的情形:(按,引文引略)穷学生的小盘算,小堂倌的小喜怒,这些平凡有情的世象,用了幽默的调料调和起来,与清茶及干丝的质朴素雅的味道正好相称。以下更详细地写到他故乡绍兴的三脚桥,桥的名与实,其地的名产周德和茶干,以及已经不是茶食的油煤豆腐干之类,似乎岔得很远了;但是说,豆腐这样佳妙的食品,“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正如茶一般”,一句便收了回来。此文的主要意思是提倡“茶道”,即以“片刻的优游”,“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吃“干丝”如何应付堂倌,油豆腐干如何制法之类,似乎与此关系不大,不必写得这样多,这样详尽。但是这样写了,本身就表明作者的“优游”态度,不是急匆匆地赶着把主意说出来便完事。(21)
这里所谓的“‘优游’的态度”,不正是鲁迅批评废名的“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吗?而所谓的“不是急匆匆地赶着把主意说出来便完事”,自然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是“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了。
所以,鲁迅对废名小说的文体特征的批评,更是包含了对周作人的批评。只不过在周作人那里,这种“低徊”的趣味表现在具体的创作中,诚如舒芜所分析的那样,有各式各样的具体的艺术技巧,变化多端,相对而言,在废名那里则有些单一,远不及乃师周作人的炉火纯青,所以朱光潜也不免惋惜其“容易使人生单调之感”,而有“大同小异”之叹,然而也正因为是这样,废名的文章更如鲁迅所批评的那样,“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是“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了。
三
问题似乎尚有出乎意外之处。
鲁迅对废名的批评中所用的“低徊”这个词,在鲁迅乃至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也是比较罕见的。考查其来历,原来别有出处。在鲁迅、周作人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的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中,有这样的关于夏目漱石的文字:
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1867-1917)名金之助,初为东京大学教授,后辞去入朝日新闻社,专从事于著述。他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一九○八年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头》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说明他们一派的态度:
“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谓触着不触着之中,不触着的这一种小说。……或人以为不触着者即非小说,但我主张不触着的小说不特与触着的小说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间很是广阔,在这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挂幅》(Kakemono)与《克莱喀先生》(Craig Sensei)并见《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系《永日小品》的两篇。(22)
这篇文字出诸鲁迅之手,据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研究,鲁迅这里节略引用了的夏目漱石为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头》所作的序,“曾因成为自然主义派攻击的目标而特别有名”;“由于自然主义派在文学活动中一味狭窄地执着‘对人生切实的紧迫的问题’,因此觉得漱石无论如何是难以理解的存在”(23)。再据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夏目漱石是鲁迅十分喜爱的寥寥两个日本作家之一(24)。又据周作人回忆:
(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至于岛崎藤村等的作品则始终未尝过问。自然主义盛行时亦只取田山花袋的小说《棉被》,佐藤红绿的《鸭》一读,似不甚感兴味。(25)
综合这三条材料,可以看出,鲁迅在日本时期十分欣赏的是主张“低徊趣味”、“有余裕的文学”的夏目漱石的作品,而对执着于“对人生切实的紧迫的问题”的自然主义文学则“不甚感兴味”。鲁迅在上面那种简短的作家介绍文字中,竟然用了超过一半的篇幅节略引用夏目漱石为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头》所作的序文,可见他对夏目漱石主张“低徊趣味”、“有余裕的文学”的文学观的异乎寻常的重视和兴趣。这和我们历来的所理解的鲁迅形象,似乎有相当的距离,因为我们更熟悉的鲁迅似乎应该反对夏目漱石主张“低徊趣味”、“有余裕的文学”的文学观,而赞同执着于“对人生切实的紧迫的问题”的自然主义文学。然而事实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对此,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对鲁迅赞同夏目漱石主张“低徊趣味”、“有余裕的文学”的文学观,有这样令人信服的解释:
清末革命思想史发展的结果,鲁迅发现了自我;与此相同,漱石也从“当前文艺应该帮助日本进步”的追求中,最后找到了自我。(26)
这和鲁迅当时《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主张“独立”于“庸众”的“立人”思想的精神实质是内在一致的,也使我们联想到鲁迅论魏晋文学时所谓的“文学的自觉”说。藤井省三进而指出,这样“发现了自我”之后,“在《域外小说集》后十年的文学沉默期间,鲁迅为超越封闭的自我而一直苦斗着”,而夏目漱石在主张“低徊趣味”、“有余裕的文学”的文学观之后,也“打破了自己封闭的自我”:
1915年写了《路边草》的漱石,在书中摆脱了三角关系,把笔触伸向对家族及夫妇的幻想的解剖。第二年的《明暗》转而专心描写社会,我以为这时的漱石恐怕与写《狂人日记》的鲁迅一样站在一个出发点上。(27)
也就是说,鲁迅和夏目漱石一样经历了从“发现了自我”到“超越封闭的自我”的思想变化的历程。
经过这样的梳理,我们可以先下这样一个初步的结论:鲁迅批评废名小说时所使用的“低徊”一词,正是出典于他曾经喜爱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所主张的“低徊趣味”、“有余裕的文学”的文学观;他对废名的批评,并不与他自己当时的文学观自相矛盾,因为他已经经历了从“发现了自我”到“超越封闭的自我”的思想变化的历程。
然而进一步分析,就鲁迅1935年对废名的批评并且包含了对周作人的批评而言,其意义却在于废名、周作人的“低徊”的趣味,不是“发现了自我”,而是陷入了“封闭的自我”。而在周作人那里,却颇为自得其思想的转变,自诩为所谓的从“叛徒”到“隐士”的人生选择。我们上文曾经引述的周作人的“从意见的异同上说,废名君似很赞同我所引的说蔼理斯是叛徒与隐逸合一的话”,其实是一语道破了他和废名的思想玄机。
之所以说鲁迅对废名的“低徊”趣味的批评包含了对周作人的批评,还因为对鲁迅与夏目漱石的关系的分析,我们进而发现新的证据。《现代日本小说集》是鲁迅和周作人合作编选、翻译的,夏目漱石的作品虽然是鲁迅翻译的,但周作人也曾明确表示过他对夏目漱石作品的欣赏,并且恰恰是称道其“低徊趣味”,见他的文章《森鸥外博士》一文:
(森鸥外)这种态度与夏目漱石的所谓低徊趣味可以相比,两家文章的清淡而腴润,也正是一样的超绝……(28)
此文写于1922年。鲁迅显然知道周作人也曾这样欣赏夏目漱石的“低徊趣味”。问题是远在1922年时的周作人这样欣赏“低徊趣味”,尚未如后来那样陷入“封闭的自我”,但自从他标榜并自诩他的所谓从“叛徒”到“隐士”的人生选择之后,“低徊趣味”不仅成为他“生活的艺术”的思想主旨,而且也是他小品文创作所追求并实现了的审美趣味,甚至用来倡导“言志”的文学、批判“载道”的文学;影响所及,乃至于废名、俞平伯、沈启无等弟子,还有朱光潜等人。此乃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必论述,且引述几条材料,以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考释。一是舒芜的分析:
周作人赞美日本作家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两家之文“清淡而腴润”,有“低徊趣味”,这也是他在艺术上极力追求的。周作人最短的一篇文章是《知堂说》,(收入《知堂文集》)全文云:(按,引略)全文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一百四十字,主意正文只是自开头至“以名吾堂”这三句,在全文中只占八分之三;自“昔杨伯起”以下至末尾,八分之五的篇幅,全是游词余韵,空际翻腾,几乎一句一个转折,这就是低徊趣味,这就是简短而不窘局,平淡而不枯搞。周作人自己特别看重这篇文章,不是没有道理的。(29)
二是苏雪林30年代的分析:
(丰子恺)其作风虽不能强说与俞平伯一路,但趣味则相似。所谓趣味即周作人之“隐逸风”及俞平伯“明末名士的情调”,我们又不妨合此二者以日本夏目漱石的东方人“有余裕”、“非迫切人生”、“低徊趣味”来解释。(30)
苏雪林30年代的这个分析,独具眼光,很有见地。至于朱光潜,且看他30年代在《谈美》一书最后一篇论述“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时的一段话: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31)
朱光潜所谓的“人生的艺术化”的说法,就是来自周作人,而他这里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就是一种“流连风景”的人生趣味与艺术趣味,也就是周作人所欣赏的“低徊趣味”。朱光潜曾对周作人的散文集《雨天的书》写有书评,对其作品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慢慢欣赏,细细品味,低徊不已。(32)
注释:
① 参见《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
② 参见《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0页。鲁迅此文在《鲁迅全集》中被系年于1934年底,大概是根据这篇文章的注释3所谓的周作人《弃文就武》写于1934年12月22日,但是,周作人此文发表于1935年1月的《独立评论》,因而鲁迅的文章只能是看到周作人此文发表之后写的,绝不可能写于1934年。
③ 周作人:《〈桃园〉跋》,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507页。
④ 周作人:《〈燕知草〉跋》,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⑤ 参见沈从文:《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1-12页。
⑥ 朱光潜:《桥》,《文学杂志》,1937年7月,第1卷第3期。
⑦ 《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0页。
⑧ 参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1页。
⑨ 周作人:《〈雨天的书〉序二》,《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5-346页。
⑩ 周作人:《〈药味集〉序》,《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7页。
(11) 参见《鲁迅致曹聚仁》,1934年4月30日,《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页。
(12)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13)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14) 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引自《人与诗:忆旧说新》,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9-50页。
(15) 同上,第51页。
(16) 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11-12页。
(17) 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9页。
(18) 朱光潜:《〈桥〉》,《文学杂志》,1937年7月,第1卷第3期。
(19) 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20) 沈从文:《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3页。
(21)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256页。
(22) 参见《现代日本小说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23) 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陈福康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24) 《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25)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452页。
(26) 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陈福康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27) 同上。
(28) 参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0页。
(29)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39页。
(30) 苏雪林:《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青年界》,1935年第7卷第1号。
(31) 参见《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32) 朱光潜:《〈雨天的书〉》,《一般》,1926年第1卷第3期。又,关于朱光潜与周作人的关系,参见拙文《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批评的意义及其反响》,《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1期。
标签:鲁迅论文; 周作人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竹林的故事论文; 莫须有先生传论文; 读书论文; 夏目漱石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人物分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