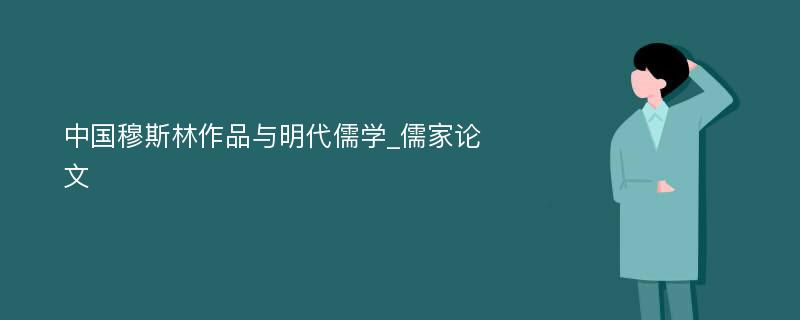
明代穆斯林的汉文著述与儒家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斯林论文,著述论文,汉文论文,明代论文,儒家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对话与文化自觉——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6)02-0005-06
文明冲突论与明代的文化多元
自从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提出文明冲突理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既非意识形态也非经济,而是以文明为主导,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遂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课题。
民族特性与宗教信仰差异所带来的文化现象,是否足以导致文明的矛盾对立,甚至冲突,是目前研究文化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学者们所最关注的问题。许多人曾对亨廷顿的说法提出反驳,如羊涤生便认为他“不适当地夸大了文化冲突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不同文化之间还有共性、互补性和互相渗透融合的一面”。羊氏并强调从历史长河来看,文明互动往往是主流,是基本的,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冲突则往往是暂时的,占次要地位的。人类文化的总的趋势是走向全球化、一体化[1]。
这里其实牵涉两种不同的文化理论假设,而其立场不但影响我们对国际间关系的提法,甚至管理学上的跨文化理论,都受到这两种假设的影响而有截然不同的应变对策。这两种看法,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分歧假设”(Divergence Hypothesis),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接触虽然越来越多,资讯发达使距离越来越近,但却加深了文化的对立,甚至带来冲突,并否定了文化及社会将趋于一致的可能性。另一种看法,我们可以称之为“聚合假设”(Convergence Hypothesis),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将逐渐缩减,文化的差异亦日见减少,终至消失。
文明的接触是否一定会带来冲突?这是非常值得去探讨的问题。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东方文明曾经多次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传统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立场是怎样?究竟是和谐的聚合还是矛盾的分歧?这篇文章希望通过对早期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及明代文化多元的背景,探讨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接触时所产生的“化学反应”,从而分析文化理论背后的客观性和局限性。
文明接触——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伊斯兰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中国文献中有提及伊斯兰教在隋朝时已传入中国,如唐代王珙所撰《建筑清真寺碑文》说:“西域圣人,生而神灵,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生死之学。隋开皇中,其教遂入中华。”明朝郎瑛《七修类稿》亦云:“清真教入中国,乃隋时,其法有数种,吾儒亦有不如。”[2] 但此说法尚嫌证据不足,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应在唐代(618—907年)传入中国。
唐代时中国和阿拉伯的交通往来已具相当规模,通道主要有两条:一为陆路,经波斯及阿富汗到达新疆天山南北,后经青海、甘肃直至长安,历史上称为“丝绸之路”;另一条为海路,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至南海到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历史上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香料之路”。因为当时商业贸易发达,外国商人往来频密,其中又以阿拉伯(唐代称为“大食”)、波斯和中亚各国商人居多。有些外商甚至客居长安和沿海各通商口岸,唐代称外族为“胡”或“蕃”,外国客商有被称为“蕃客”。外族在中国客居,唐朝政府有指定的范围,其聚居地称为“蕃坊”或“蕃市”。当时唐代的长安俨如一座国际都市,根据记载,在100万城市居民中,约有2%是外籍侨民和客居的“蕃客”[3]。伊斯兰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传入中国的。
胡商客居中国,因为有自己的聚居地方,所以能够保存和延续他们所带来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4]。他们也保留了自己的名字和服饰,仍然以阿拉伯或波斯语作为他们族群之间的沟通语言[5]。一些研究认为当时在广州、泉州、扬州、长安、南京、杭州、开封、北京、福州、大同、太原、昆明、桂林,甚至海南岛都有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建立[6]。但这说法并不可靠,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文献证据或考古发现去证明当时中国全国各地都有清真寺。一般相信当时最多胡商聚居的广州、泉州、杭州和长安,应该是最早有清真寺的城市。
随着接触的增加和了解的加深,一些定居在中国的伊斯兰教商人开始与中国妇女通婚,有些则收养中国孩子,这不但增加了伊斯兰教社团的人数,也增进了早期中国与伊斯兰教国家的民族与文化交流。当时长安西域风尚盛行,连唐代帝王皆嗜好源于波斯的马上球戏(击鞠)和乐道大食及中亚传来的棋弈(双陆)。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便列举了西域艺术和习俗在唐代流行的情况,并指出唐代长安有“胡化”的现象[7]。然而,这只局限在社会上一些外在的层面,伊斯兰教教义与价值观并未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任何深刻的影响和冲击,与代表中国思想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便更谈不上有什么沟通了。
宋元两代,随着沿海贸易的发达,外国胡商到中国定居的人数相应增加,中国的穆斯林人数也因此而有显著的增长。宋代在杭州、泉州、宁波和广州设有市舶司,处理外商船只在沿海港口进行贸易事宜。白寿彝的研究指出当时在民间可见的外来货物便超过100种[8]。元代西域民族在元朝廷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又因为蒙古的多次西征,大量回回人(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民族及西亚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东迁,使居住中国的穆斯林人数大增,而他们的社会地位亦日见提高。《明史·西域传》记载:“元时回回遍天下”、“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可见穆斯林情况的一斑。但蒙古人对汉文化排斥最力,民族的四等划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妨碍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与思想交流。这种情况到了明代(1368—1644年)才得到改善。
明代的建立标志着汉人政权的光复和汉文化的复兴。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消灭蒙古风俗在中国的影响,采取了强硬的政策。《大明律》记载:
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族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宫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9]
明廷的强制性种族通婚政策,反映了明太祖意图同化蒙古人的野心。这也许是过分苛刻,但根据文献记载,元朝灭亡后,留居中国的蒙古人为数众多,单是北京就有10万之众,如何解决境内蒙古人问题,确实是燃眉之急。虽然通婚律令并不影响回回人,但明代整个社会环境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同化和文化的了解。明代的汉化政策也并未禁止穆斯林的宗教生活,而其对伊斯兰教颇为尊重。况且,明初建国,许多开国功臣如常遇春、胡大海、沐英、冯胜、蓝玉等都是穆斯林,民间更有“十大回回保国”的逸话,助长了伊斯兰教在明代的发展。洪武元年(1368年),明廷建礼拜寺于金陵,明太祖敕书《至圣百字赞》,称颂伊斯兰教与穆罕默德:
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接受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祐,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贯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10]
其次,在中国定居的穆斯林与汉人通婚后所生的第二或第三代,也为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沟通扮演重要的角色。明代时许多回回人已采用汉人名字,并且说流利的中文,在外表上已经与汉人没有分别。Donald Leslie指出当时有些回回人能够写出优美的诗句,并且体现士人风范。他说:
他们的作品是特别的,又能够与广大的中国文学混为一体。它们不可能是伊斯兰的,我也差不多或完全没可能从这些作家和作品中找出穆斯林来源的痕迹。然而,这些作品明显看出回教徒穆斯林在儒家中国被汉化和同化的情形。[11]
明代的穆斯林在言行举止方面,已经与汉人没有任何分别,他们本身的中文修养使他们成为儒家思想与伊斯兰教思想会通的最理想人选。在中国的伊斯兰教史上,明代开始出现“土生土长”的穆斯林。正如Raphael Israeli所说,至此人们可以称他们为“中国穆斯林”(Chinese Muslims)而不再是“在中国的穆斯林”(Muslims in China)[12]。这样的背景,给儒家思想与伊斯兰教价值观的接触和沟通,提供了最理想的历史条件。
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
敘述伊斯兰教教义及价值观的汉文典籍的出版,始于明代,至清代而达高峰。有些学者称这段时间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13] (P584-588)。同时,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学者的著作中,也开始出现对伊斯兰教的描述。虽然这些记载都比较浮面,但已足以说明该宗教已经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如明嘉靖期间的郎瑛(1487—1566年)在其《七修类稿》中便特别谈到“回回”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14]。
从明人的记载中所见,当时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教的印象基本上是颇有好感的。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尚书王鏊为南京重修的礼拜寺撰碑,认为伊斯兰教的创教人穆罕默德虽然生在孔子之后,又与中国异地而处,但“其心一,故道同也”。他并指出伊斯兰教中“如沐浴以洁身,如寡欲以养心,如斋戒以忍性,如去恶迁善,为修己之要,如至诚不显,为格物之本”,体现了“千圣一心,万古一理”的道理[15]。王鏊、郎瑛等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主要是根据个人的接触或中文文献。这与大量汉译伊斯兰教教义的著作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
对伊斯兰教而言,最主要的文献自然为《古兰经》,其地位有如基督教中的《圣经》。虽然《古兰经》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有1000多年的历史,《古兰经》的中文译本却是近代才出现。《古兰经》全文的中文译本,最早的是铁铮所译的《可兰经》(1927年出版于北京),其次是姬觉弥等人所译的《汉译古兰经》(1931年出版于上海)。其后教内人士陆续有重译,较早期的计有:
王文清 《古兰经译解》 1932年北京版
刘锦标 《可兰经汉译附传》 1943年北京版
王静斋 《古兰经译解》 1946年上海版
杨仲明 《古兰经大义》 1947年北京版
马坚《古兰经》 1949年北京版
既然《古兰经》的汉译是较后的事,可知《古兰经》在过去是没有中文本的,一般人必须学会阿拉伯文才能读通和了解《古兰经》中的知识,这对非穆斯林而言,要了解其宗教之一二,实属难事。明代以前,穆斯林的著作多为医药、天文历法等主题。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期间,出现了一批精通汉文而又对儒家思想认识深厚的穆斯林,以南京、苏州为中心,他们用中文编译书籍,引用《古兰经》原文阐扬伊斯兰教。他们的著作对回儒的交流互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这些作品的出现有特殊的背景因素:17、18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运动、明代中央政府的汉化政策、明末清初穆斯林的社会地位状况、教外人士对伊斯兰的误解、以及传统儒家环境的影响,都可能有刺激的作用[16]。日本学者桑田六郎称这批作者为“回儒”,他并指出:
中国本部之回回,则迄明末尚颇沉默,不见活动。直至明清鼎革之际以及康熙年间,彼等间乃起一种自觉。于是多数回回学者辈出,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及仪律之举甚盛。此确为中国回回史之一划时代的时期,余算此时期为中国回回史上之文艺复兴时期。盖鼎革之事极有影响于人心之变动,而明末耶稣教在中国传道之态度与方法,及清朝以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后之尊重文化,奖学术,一志明代因循固陋之风习,皆与此复兴时期之现有莫大关系。[13] (P786)
汉译伊斯兰教著作的涌现是否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是可以商榷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汉译著作的出现只是时机的问题。当时“回儒”的主要著作有:
王岱舆《正教真诠》2卷1642年
《清真大学》1卷?
《希真正答》1卷1658年
张中 《归真总义》1卷1661年
《四篇要道》4卷1653年
马明龙《认己醒悟》1卷1661年
马伯良《教款捷要》1卷1678年
马君实《卫真要略》1卷1661年
伍子先《修真蒙引》1卷1672年
《归真要道》4卷1678年
孙可庵《清真教考》4卷1720年
马注 《清真指南》
10卷1683年
刘智 《天方性理》5卷1704年
《天方典礼择要解》 20卷1708年
《天方至圣实录》
20卷1721年
《五功释义》1卷1710年
《天方字母解义》 卷1710年
《天方三字经》 1卷?
金天柱《清真释疑》1卷1783年
马复初《四典要会》4卷1859年
《宝命真经直解》5卷?
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所兴起的“以儒诠经”的伊斯兰文化运动,与当时南京地区的文化多元及流行的三教合一背景有一定的关系。从明末清初的伊斯兰学者可见,他们既精通汉文,又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同时精通伊斯兰教义和儒、佛、道思想。这是“以儒诠经”的必要条件,也为回儒会通提供了有利的背景。但目前我们对这场在明末展开的宗教运动的了解非常贫乏,除了王岱舆以外还有什么人?有没有其他重要著作?整个背景是怎样?因留下来的材料不多,我们的认识其实还是很有限的。
澳大利亚学者Donald Leslie曾经统计明末清初出版的伊斯兰教汉籍,胪列出著作59种,并指出大部分都有再版和重印[17]。在明清之际新兴的译著伊斯兰教经典的活动中,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复初等人成为回族中最负盛名的四大宗教著作家,其中王岱舆又被推为四人之首,因为他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学者中第一位系统地论述伊斯兰教哲理并付之刊行的人。他的著作对回儒的交流和沟通有深远的意义。
王岱舆与明末的“以儒诠经”运动
王岱舆别号“真回老人”,确实生卒年不详,约生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死于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享年应在60岁以上。他生于南京,晚年北上北京,于正阳门外讲学,死后葬于北京三里河清真寺附属墓地。白寿彝《回族人物志》认为“岱舆的先世原是西域人。所谓西域,不知是指现在的新疆还是葱岭以西的地区”[18]。但这说法并不准确。王岱舆在《正教真诠》的《自敘》中说:“予祖属籍天房,缘入贡高皇帝,订天文之精微,改历法之谬误。”[19] (P16)“天房”与“天方”通,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可见王岱舆的先祖应不是来自西域而是阿拉伯,因“朝贡”关系在明初太祖时来到南京,后来在钦天监做官,遂定居南京。到王岱舆时,其家族已在南京居住了200多年。王岱舆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大概完全是宗教教育,沟通的语言则是阿拉伯语。在20岁时,他才开始学习汉字,并以中文写信记事。30岁以后,因感觉自己的学问不足,又大量阅读子史和性理书籍,梁以浚称他“四教博通”[19] (P3),即回、儒、佛、道兼通的意思。因为这样的缘故,当他讨论伊斯兰教的道理时,往往能够与儒、道、佛思想互相对比,旁征博引,间接促成了伊斯兰教价值观与儒家思想的沟通和调和。这在他的著作《正教真诠》中最为明显,我们可以以此作为例子来进一步说明。
《正教真诠》分上下卷,共40篇。上卷10篇讲归真明心之学,下卷20篇谈修身行道之法。其40篇的目录是:
真一元始前定普慈真赐
真圣似真易真昧真迥异
性命真心生死人品夫妇
仙神正教正学回回作证
五常真忠至孝听命首领
友道取舍预备察理参悟
利名较量宰牲荤素博饮
利谷风水正命今世后世
本书主要是王岱舆与门生和教外人士谈论时的记录,成书刻版大约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是书的宗教意义,粵东城南重刻本的《序》说:
惟是经文与汉字不相符合,识经典者必不能通汉文,习汉文者又不能知经典。自《正教真诠》出,遂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奧义,故开卷了然,瀹我心源,发人聋聩。[19] (P1)
《正教真诠》以“中土”的汉文,阐明“天方”的奧义,但在阐释的过程中往往牵涉儒、佛、道的观点,尤以对回儒关系有较明显的论述。教中人士梁以浚在崇祯版的《序》中便指出:
是以孔子之对太宰曰:“西方有大圣人焉,不教而治,不言而化。”夫孔子为东土儒者之宗,一言而为天下法,此言宜可信也。然则儒者之道非乎?曰:“否!”宇宙间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理尽义极,无复遗漏,至正大中,绝去偏颇,非此则人道不全,治法不备,此儒者之道之所以不易也。[19] (P3)
文中所引孔子的话,在《论语》未见,但明显可见梁以浚是希望借孔子的口来肯定伊斯兰教的地位。其实明清的知识分子在谈到伊斯兰教时,时常回儒并举,并认为回儒不谋而合,不相违背。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何汉敬的《正教真诠》敘便明显地说:“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昌黎曰:近乎儒者则进之。是可悉其始末而昌明之也。”他进一步以伊斯兰教与儒家相比:
其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且立说平易,不事玄诞,与道释两家,绝为霄壤,较之吾儒性理一书,同而异,异而同,亦在所不讳。[19] (P5)
这类观点,大抵可以说代表当时一般穆斯林和对伊斯兰教有好感的知识分子的立场。类似的观点在《正教真诠》中摭拾皆是。从篇章中可见,王岱舆在阐述伊斯兰教理时常常征引尧舜和孔孟之说作为旁证,虽旨趣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但回儒道德价值观的共通,却是显而易见的[20]。《正教真诠·戒慎章》说:
经云:“尔等近主之至贵者,乃戒慎也。”戒慎者乃事必以正,戒谨恐惧也。盖身体发肤,皆真主所赐,岂得施于违命之赽。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感恩之谓矣。[20] (P205)
“非礼勿视”四句,原出《论语·颜渊》篇,现在成为阐述伊斯兰教戒慎的要点。儒家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对伊斯兰教而言,父母之上尚有一真主,遂有身体发肤“真主所赐”的说法。这类“以儒释回”的例子,在《正教真诠》中甚为普遍。又如《友道章》说:
圣人云:“尔众以己之所悦,施于人;己之不欲,存之于己,始终自一焉。”即此参之,损人利己,家庭亦化仇敌;克己济人,四海可为兄弟。故吾教处昆弟、朋友、亲戚、邻里间,无化外道,唯忠恕而已矣。[20] (P197)
如果拿这段话与孔子《论语·里仁》篇比较,便会发现其中相同的基调: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1] (P42)
两篇的核心观点都是“忠恕而已矣”一句话。“忠”和“恕”是儒家思想的两个重要观点,根据孔子自己下的定义,恕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则是恕的积极一面,用孔子自己的话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1] (P41)。忠是尽己之法,恕是待人之道。儒家认为这两个字是实行仁义的着手处,也是孔子之教的重点,所以《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然而,在《正教真诠》中,王岱舆认为其教处己待人之道也是“忠恕”两个字,显然是借用《论语》以解释伊斯兰价值观中的友道。亦因为如此,《正教真诠》并不给人疏离和陌生的感觉。反之,因为它所用的句子和术语都是耳熟能详的,有些时候使人难以分辨究竟他是在阐述儒家观点还是在宣扬一个外来宗教的教义。
《正教真诠》敘述的价值观,也有类似儒家观点而立场殊异者。如《孟子·离娄》篇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所谓的三不孝,据汉人赵岐的注:“于礼有不孝者三: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22] 伊斯兰教亦非常重视孝道,《正教真诠》衍化《孝经》的观点,提出“忠主者必孝,行孝者必忠,忠孝两全,方为至道”,并进一步认为“不孝有五,绝后为大”。《孟子》中本来也谈到“世俗所谓不孝有五”,问题是《正教真诠》所说的“绝后为大”并非儒家所说的“无后为大”。《至孝章》云:
吾教之道,不孝有五,绝后为大。其一乃不认主;其二乃不体圣;其三乃不亲贤;其四乃不生理;其五乃不学习。所谓绝后者,非绝子嗣之谓也,乃失学也。何者?一人有学,穷则善身,达则善世,流芳千古,四海尊崇,虽死犹生,何绝之有。有子失学,不认主,不孝亲,不体圣,不知法,轻犯宪章,累及宗族,虽生犹死,何后之有。[19] (P194)
虽然伊斯兰教价值观中的五不孝,“不生理”也是不孝之一,但并不是最大的不孝,最不孝是不学习,以致影响其他孝行,与身死绝后无异。这点而言,与儒家的看法便有出入。
回、儒的协调与会通
综观《正教真诠》的论调,对佛道二教采取排斥的立场,但对儒家则强调其同并提出其异,其以“儒”释“回”的手法,可以看出王岱舆有协调和会通“回、儒”的企图。
《正教真诠》本《问答纪言》一篇,王氏以问答方式解释其书中对儒家的立场。他的设问说:“二氏无论矣,儒者之道博大渊微,至于性理尤宋贤精粹之所在,子所引论,特其浮浅糟粕耳。其微,子固未深求也。”王岱舆的回答是:“天下事有不齐,理无二是。予不计人我,但论同异而已。夫国有君、府有牧、州有守、家有长、世界有主,道一也。儒者纷纷,以理气二字尽之,是天下国家可以无君长而治愈异也。若夫孔孟之道,修身、齐家、治国与吾同者,予焉敢妄议其是非哉!”[19] (P9-10)伊斯兰教教义中对真主的信奉,是无可置疑的,这个牵涉到信仰的部分是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差异所在。但就道德价值观而言,回、儒是同多于异的。此所以王岱舆等人以儒家的观点阐释伊斯兰教义,一方面使中国人更容易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中国人对这个外来宗教的抗拒。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代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中国化”或“儒家化”过程。但这种推测是有待商榷的。王岱舆等人的汉译伊斯兰教著作中用了大量儒家的观念和术语,并不一定是有意识地要把伊斯兰教“儒家化”。他们本身的文化背景和对儒学的了解,使他们在诠释伊斯兰教教义的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作为讨论的基础和比较的根据。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主导地位,也使任何外来的思想难以避免与它不产生任何的关系。
儒家思想作为一套生命价值观,也显示出它的普遍性和包容性。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凝聚力、兼容力和亲和力,使中华文化不断吸收外来的养分并壮大本身的传统。Haji Yusuf Lin Baojun在其探讨华籍穆斯林的专著《A Glance at Chinese Muslims-An Introductive Book》中指出,儒家思想的“模糊性”允许了其他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传入,来填补儒家哲学理论框架里宗教信仰的空虚[23]。
文明的接触是否一定会带来矛盾的冲突?从明代回、儒的接触来看,这种论调是否定的。早期穆斯林的汉译著作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之间和谐共存的关键,也为研究儒家思想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有用的参考。
标签:儒家论文; 古兰经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穆斯林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正教真诠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