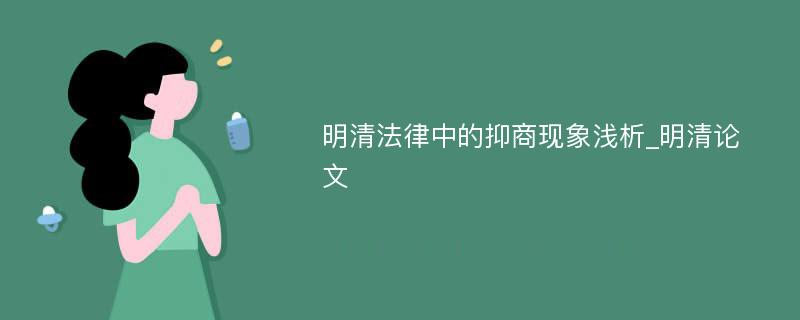
浅析明清法律的抑商色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色彩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05)02-0154-04
自16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产生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迅速成长起来,中国也没有像西方那样由封建社会顺利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封建社会过渡到扭曲的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究其原因,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固然是主要障碍,而封建统治者变本加厉地推行“抑商”的传统政策及其派生的法律制度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一、明清推行抑商政策的社会原因
明清之所以实行严格的抑商政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首先,强化封建统治的需要。中国自秦确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至明清达到了高度完备。中国的皇帝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是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威,普天之下的百姓,必须绝对服从和尊奉皇帝一人。皇帝不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且是一切权力的实际源泉,因此,在中国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对皇帝及其统治地位进行公开挑战的其他权威。西欧则不然,西欧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代表中央集权的王权需要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彻底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而新兴资产阶级则需要加强王权,利用王权保护和发展自己的事业。中国封建专制的中央政府,不但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反而为了强化统治权力,顽固地坚守封建王权的经济根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制度,不允许任何其他经济成分渗透其中。
其次,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根基——传统教化的需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儒学便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体系。为了培养和选拔效忠于君主的各级官吏,明清实行以儒学正统思想为指导的八股取士制度,它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清王朝还屡兴文字狱,摧残文化。而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稍后的启蒙运动都为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为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人生观以及奋发向上、乐观进取的人文精神。虽然明清早期启蒙思想家如李贽、黄宗羲等,敢于批判封建礼教和君主专制,但毕竟只是少数人的呼声,并未形成占社会主流意识的完备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的幼芽既得不到国家政权的扶植,也得不到舆论的声援。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礼教仍然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诚然是光辉灿烂、硕果累累,但就因为过于辉煌,在变革时期一定意义上又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最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制,且生命力很顽强,在这一制度下,土地允许自由买卖,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中国古代社会,商人和手工业者作为一个主要社会阶层,早在奴隶制时代就已出现,但其社会地位往往依据统治阶级的喜怒哀乐而随时发生变化。许多朝代法律都明令商人、手工业者不得为官,他们虽富有但没有尊荣,不能拥有一些政治经济特权。所以,中国古代商人、手工业者一旦积累财富,往往通过购买土地而使自己或子孙尽快转化为地主,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用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扩大再生产,所以在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像西方社会那样真正的资本家集团。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的大量购买土地,缓和了土地权和货币权的矛盾,形成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在经济上的三结合,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三个主要剥削集团,官僚则是它们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从而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的“四位一体”,维护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成为它们共同的根本利益。而这种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又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剥削集团和统治力量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拒绝任何变革因素的产生。再加上明清特殊的政治环境,明代东南沿海一直有倭寇的骚扰,而清初台湾郑氏集团是政权巩固的一大隐患,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的统一和安全,明清统治者极力推行抑商政策。
二、明清法律中的抑商色彩
首先,扩大禁榷范围,通过严刑保护“禁榷制度”。“禁榷制度”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某些重要的商品实行专管的制度。禁榷制度从西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到了明、清时期有进一步的发展。明、清统治者扩大禁榷的范围,不仅继续把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而又一般不能自己生产的盐、铁、茶作为禁榷的主要对象,而且进一步把金、银、铜、锡、硝、硫磺等商品的专营权也网罗在政府手中,使民间可以经营的商业范围极为有限。
封建统治者还以极严酷的刑律保护他们的禁榷制度。汉唐以来,虽然盐禁法网日密,但正式将榷盐列入正律之发端是《大明律》。清律沿袭了大明律的规定,且以条例的形式不断加以补充。据统计,从雍正至道光百余年间,共增加了盐法条例28条,大多异常残忍严苛。如雍正六年定例:“凡拿获私贩,务须逐加究讯,买自何地,卖自何人,严缉窝顿之家,将该犯及窝顿之人,一并照兴贩私盐例治罪;若私盐买自场灶,即将该管场司并沿途失察各官,题参议处,其不行首报之灶丁,均照贩盐例治罪。”[1](《盐律》)明、清封建统治者的暴力所指不限于“私盐”,凡是禁榷的工商产品,违禁制造或贩卖者,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
其次,重征商税,压制私人商业的发展。明清两代推行抑商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广设钞关,重征商税。明宣德年间,开始在长江、运河沿岸各地设立钞关32处;万历年间,关卡大增。清代沿明制,设户部24关、工部5关。钞关的主要任务是征收通过税。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封建国家对钞关的管理也越严密、具体。乾隆二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编制了《钦定户部则例》,其中“关税”5卷、“税则”29卷,占整个法典的1/3还多。它规定:对偷越关卡与漏税等行为,不仅要惩罚客商,地方官也一并议处;还规定“关税短缺令现任官赔缴”。从而促使各钞关官以增课为能事,肆意苛求。客商每临钞关税卡如赴“法场”,胆战心惊。除关税外,明、清两代还征收名目众多的商税,如牙税、落地税、契税、盐税、茶税、酒税等,加上胥吏勒索无度,成了广大工商业者不堪忍受的负担。客商如匿税,“不纳课程”,按律“笞五十,物货一半没入官”。[2](《课程》)
再次,加强对矿冶业的管禁,限制民间自由开矿。矿藏的开采和冶炼是重要的工业部门,也是其他手工业发展的基础。然而,明、清两代都对矿冶业严加管禁,极力限制民间自由开矿。
明王朝的法律规定,金银等贵金属矿藏基本上只能由官府经营,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铁、铜、锡矿也由官府设局采冶;民间一般只许开采除此以外的其他矿藏,并须取得官府的批准,交纳一定的课税。未经官方许可,私人不得开矿,否则“准窃盗罪”论处。《大明律·盗贼》规定:“凡盗掘金银铜锡等矿砂,每金砂一斤折钞二十贯,银砂一斤折钞四贯,铜锡水银一斤,折钞一贯,俱比照盗无人看守物准窃罪论。”
清代对矿冶业的管禁也是严厉的。因为清代是满族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惧怕汉族人民聚集于深山,以采矿为名进行反满活动,因此对矿业开采加以严格管理和限制。如雍正所说:“开矿一事,……人聚众多。从来矿徒,率皆五方匪类,乌合于深山穷谷之中”,因此,决不允许“逐此末利,为闾阎之忧累”。[3](P275)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清王朝制定了矿冶业政策:贵金属的开采、冶炼基本上由官府经营,私采者“正犯处以极刑,家口迁化外”。对于铁矿冶炼,清政府也管制得很严,规定除征收铁税20%以外,凡采铁冶铁地方,要将炉座的数目、产量、工场主以及矿工、铁工的姓名、履历,详细呈报官府,发给执照;贩卖铁斤,某商在某处向某炉买铁若干、运行何处,也要呈报给单,过关验单,严禁无照私自买卖铁,尤其禁止运销海外。特别是清政府对那些既重要而又有利可图的手工业,采取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的掠夺性政策,使厂商非但不能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如云南铜矿的“放本收铜”、江南织造业实行的“领机给贴”、食盐销售的“票引”制等,客观上都给工商业以极大限制和摧残,致使其发展步履艰难。
最后,奉行海禁政策,阻挠对外贸易。中国的对外贸易早在西汉武帝时就开始了。希腊古书中常提到东方有一个国家出产丝绸,叫作“赛里丝(Sorice丝国)”。[4](P315)据考证,这个丝国就是中国。到了隋唐,尤其是宋元时,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可是,正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诞生、成长的时期,明王朝却把“禁海”定为基本国策。三令五申“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5](P372)清初为了镇压抗清力量,颁布禁海令,严令寸板不得下海;接着又颁布迁海令,强制闽广苏浙沿海居民内迁50里,越界者立斩。从而完全断绝了海外贸易。康熙二十三年收复台湾以后,一度有所放宽,旋又严申海禁,迄至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以外各口均奉令关闭。《大明律》、《大清律例》始终都列有“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律文:“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买及下海者,杖一百;受雇挑担驭载之人减一等;货物、船只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给告人充偿。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漏事情者,斩;其该拘束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官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清朝统治者还不断补充其条例,《大清律例》附例规定:“凡沿海地方奸豪势要军民人等,私造海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货卖,……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枭示,全家发近边充军”。[6](P227)乾隆年间该律文类似条例多达36条。由此可见,明、清两代推行海禁政策的顽固性和一贯性。
三、明清法律抑商的恶劣后果
首先,严格的“禁榷制度”,阻碍和破坏了国内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苛重的商税和肆意的掠夺,使广大客商视商业为畏途,许多商人不得不抽出商业资本和利润转而投向购买土地,使得商业资本不易转化为工业资本;严密的法律控制和监督,使得矿冶业的发展十分缓慢;顽固和一贯的海禁政策,打击了刚刚兴起的对外贸易和沿海手工业,堵塞了海内外商品交流的渠道,以致出现“土货滞积,而滨海之民半失作业”[7](P586)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
其次,抑商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挫伤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马克思曾指出:“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手工业时代,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8](P822)历史证明,要从封建的生产关系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须大力发展商业,不仅要有本国市场,而且还必须有广阔的世界市场。16世纪以后,西方各国之所以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发展工商业,开展对外贸易,开辟海外市场,广泛吸收并积极利用外部因素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它是以世界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的,如果不掠夺海外,不掠夺全世界,资本主义是无从发展的。18至19世纪之交英国之所以从一个蕞尔岛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原因之一就在这里。明清严格的抑商政策,堵塞了国内外商品交流的通道,从而挫伤了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的势头。
再次,严格的海禁政策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一方面,海禁促使海外贸易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走私贸易。厉行海禁政策,使得海上贸易集团因“失其生理,转而为寇”,即“海盗商人”;海禁政策还打击了东南沿海各省的农民和渔民,使他们“相率入海为盗”。[9](P982)这样,16世纪为患中国东南沿海的寇,其主体并非来自日本的“倭”,而是违反海禁与倭人勾结的中国人。这些亦商亦盗的海上豪强,通过走私贸易,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往往组建拥有数百乃至上千船只的船队,聚众数万人,在海外设基地,发展成声势浩大的海上武装集团。其中著名的有以日本为基地的“徽王”王直,闽广的林道乾、林冈,以及后来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等,他们往往成为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一股割据势力,影响了中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另一方面,海禁摧残了中国的造船业和海防力量,削弱了中国抵御外敌的能力,窒息了人们的海权观念,使得许多沿海岛屿成为殖民者侵略中国和进行走私贸易的据点。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攻击下,中国的海防显得异常虚弱。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迅速攻占广州、厦门、镇海、定海、宁波、镇江、南京,直抵天津大沽;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定海、上海、天津,占领北京。清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了独立的内政、外交权力,任人宰割,中国大地从此笼罩着“亡国灭种”的阴霾。
最后,抑商妨碍了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和了解,妨碍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清王朝以“天朝大国”自居,沉醉在天朝神圣、无所不有的迷梦之中,拒绝与外国建立平等、正常的外交关系,发展正当、自由的贸易交往,堵塞了正常的交流渠道,闭塞了国民的耳目,丧失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死抱所谓的“国粹”,将外国思想文化视为异端邪说,对西方的民主、民权思想甚为恐惧,认为其最宜使“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统统加以排斥。认为“百工制器,是艺也,非理也”。“一言学人,则骂之耻亡”。[10](P118)一味地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最终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塑造了一部屈辱的近代史。
明清封建统治者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压抑商品经济,摧残资本主义萌芽,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前进起了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以上事实证明,当法律制度为落后的生产关系服务时,它就成为妨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力量;这时改革旧的法律制度乃至整个上层建筑,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