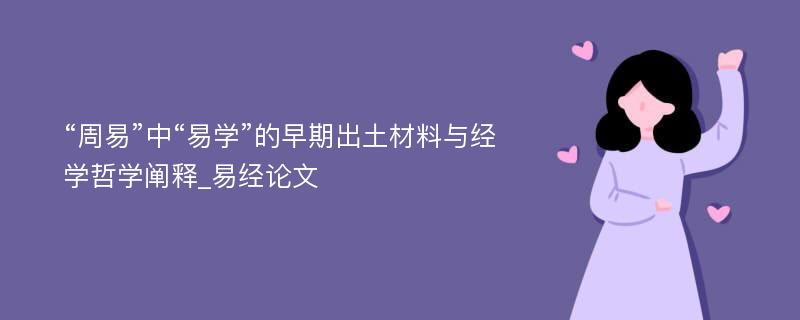
出土早期易学材料与《周易》经学的哲学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经学论文,易学论文,哲学论文,材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12-0001-08
一、出土早期易学材料与《周易》经学的解释观念
现在,《周易》方面的相关出土材料已积累很多,①但这些材料究竟会给今日的研究带来什么作用?对于《周易》义理的当代阐释,又会产生出什么真实的问题以及何种意义?这些问题,是人们十分关心的。
从总体上来看,笔者认为,出土《周易》材料所引起的研究热点,目前还是在文字的释读和文本的校注等方面。②在此方面,学界产生了一些问题,也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楚竹书本所独具的首符和尾符,为他本所无。不过,它们在文本中的含义和作用是什么?但凡研究《周易》或出土《周易》材料的人,对此几乎没有不感兴趣的。对于这一全新的文本现象,许多学者曾下了很大的研究工夫,得出了一些推论,但现在看来,还不太严密,过头的结论占据了书刊版面。③其重要性在于,这是个全新的问题,超出了人们既往的知识,大家都不曾料到。过去,有人曾发高论,认为在先秦《周易》文本没有爻题,爻题是后人加上去的,还认真地论证了一番。④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邻人疑斧式的断想。综合《小象》、《文言》、《系辞》引经之例及楚竹书本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爻题的产生至迟在战国中期之前。而高亨认为爻题为“晚周人所加”的意见,⑤现在看来也受到当时疑经疑古风气的深重影响,明显地将其产生的时间拉后了许多。回过头来看,我的问题是,即使我们依据楚竹书本破除了这一说法,甚至破除了那种“先秦无《易经》”的十分狂谬的“大胆设想”,⑥可是这到底又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呢?它们本来就是一个疑人挠心而抛出来的“莫须有”的东西,然而因为与那样一种带着严重的文化自虐倾向的时代风气相应和,而得以长期在学术界郑重地流传开来!两三代人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积累了这么多有影响力的“或许是”的观点,到头来后人却发现是兜了一个大圈子,好像“噱头”一般,这是时代的可悲、学者的可悲。
通过楚简本、汉帛书本、阜阳汉简本、汉石经本及今本(《周易正义》清嘉庆南昌府学刊本)的对照,《易经》虽然在文字上的变化很大,但其实质性的变化很小。由此可见,《周易》经文很早就已经基本稳定了。作为官学,它的权威性早已不容挑战。而且,从楚简本到汉石经本,《易经》的抄写体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均是以一卦作为独立的文本书写单位,与子书的抄写情况迥异。与此相对,《老子》的文本变化非常巨大,郭店楚竹书《老子》每一章文字的多少,章与章之间的先后关系,乃至于整体文本的字数与今本差异很大。帛书本与今本也有不小的差异。帛本之后,《老子》称“经”,例如《汉书·艺文志》就载有《老子邻氏经说》、《老子傅氏经说》、《老子韩氏经说》三书,从此它的权威性也就不容轻易动摇了。在抄写体例上也开始模仿《易经》,武帝时期的汉简《老子》即以一章为独立的书写单位。⑦总之,《老子》大体代表了子书系统从战国到汉代成书的特性。
《周易》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书?我们首先应当承认它原来是用于占筮、稽疑的。因为不仅传世先秦载籍有大量这方面的直接说法,将筮卜并列为“稽疑”的两种方式,⑧而且出土《周易》及易占材料也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当然,朱熹在其所处的时代,针对当时的学问风气曾特别指明了这一点,所谓“《易》本卜筮之书”也。⑨包山、天星观、新蔡楚简中的卜筮祭祷简包含了易卦,⑩阜阳汉简本通常在卦辞、爻辞之后紧接着书有“卜辞”,而在殷墟、周原出土的一些卜骨上存在一些被张政烺等人认作“数字卦”的契刻符号,(11)这些都说明了占筮之道为《易》本有。孔子并不反对占筮,帛书《要》篇记“孔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而《论语·子路》篇所记孔子云“不占而已矣”一语,可能为战国末季至汉初的编者所加,(12)还不能直接作为夫子不搞卜筮的坚实证据。
既然《易》本为卜筮之书的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在我们的时代就有了另外一个问题。远离史巫时期的今天,占筮所需的氛围在今天的智识阶层已经十分稀薄,即使在民间也未必看得非常认真,而在理性盛行的高等学府里宣扬占筮和卜卦算命之术,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们既要承认“《易》本卜筮之书”的观点,也要实现《易》道在解释和功能上的转化。实际上,这种转变至迟在春秋后期已经开始了,孔子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帛书《要》篇)这是解释的方向问题!今天,如果从思想研究来看,我们如何把对《易经》的解释转变为哲学性的,这是我们需解决的问题。《十翼》的作者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自春秋时期已经储备了相适的观念和开启了这一方向。如对于《诗》,当时贵族们可依据具体场合而作远离本意的解释,这不但不是失礼的表现,反而唯有如此,才具备谈话的资格,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在方法上当时叫做“赋诗断章”(《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也叫做“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对于《书》,孟子有一句话可以管总:“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孟子就是这样以“仁”的原则来做理论,而十分理想地去衡断史事的,“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尽心下》)。至于《春秋》,孔子说它的编修即包含了“知我罪我”的微言大义及不得已的历史情境在里面。(13)总之,这是那时候的学问风气,这种风气提供了人们对经典作义理化、个性化和自由化解释的正当性理由,而彼时士人亦如鱼渐水,置身于其中,浑然不觉。
宋人的《周易》解释,也大体上具备同样的解释氛围,特别是绝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孔子为《易传》的作者,《传》是对《经》最好、最直接的阐释,这为程颐写作《伊川易传》奠定了最基本的解释信念。伊川豪迈,他认为易道自秦以下无传,因而必欲新制《易传》(即《伊川易传》)以接续圣意;而在诠释观念上,他将至微之“理”放在至著之“辞”上来解释,如说“予所传者辞也”,将本来由“变、象、占、辞”(即《系辞》所谓《易》之“四道”)所构成的《周易》文本系统进一步打碎,而又特别排弃“占筮”传统。(14)诚然,从学术观念演进的历程来看,伊川断然排斥“占”、“象”的做法,与彼时的学问风气(即时代呼唤“道学”的兴起)是相应的,这为他赢得了后学的喝彩。朱熹作为程门四传弟子,在学问的格局上远较前辈广博,这突出地表现在一方面包容和涵化北宋诸子的思想,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原始儒家经典“真意”解释的客观性。就文本的解释,朱熹对于程颐多有不满和指斥,在他看来,《伊川易传》的最大问题“只是于本义不相合”、“程先生只说得一理”,甚至认为“程《易》不说《易》文义,只说道理极处”,又说:“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15)无疑,在解释上,伊川的做法是极其恶劣的,“文本”与“诠释”之间严重不相应,二者间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有鉴于此,朱子高扬“本义”的观念,将“占筮”看做《易》之本源,而卦、爻、彖、象之“义”,在他看来都必须落实在占筮之“用”上,否则,“非《易》也”。(16)于《周易本义》,朱子即将《筮仪》一文列之卷首,由此可见他对于“占筮”的高度重视了。虽然如此,朱子并不因此认为“占筮”之“用”即是易道的全部。从究竟的立场来说,一阴一阳之“理”才是“《易》之为书”的终极根据,(17)而《易》虽“本为卜筮而作”,然而毕竟只是在日用的维度上与“卜筮”紧密关联在一起。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个一阴一阳之“理”在《易》上的生现,在朱子看来即展开为五个阶段:画前易、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和程子易五者。(18)同时,从逻辑分类的角度来看,《易》道又表现为理、象、数、图四者的分别和统一。(19)“画前《易》”的说法,来自邵雍;(20而将理、象、数、图看做对《易》道的逻辑展开,这种观念在北宋中期已产生了。朱子的特别之处,在于高举“本义”的大旗,综合伊川与邵雍两家的路数,同时又积极地纠正《程氏易传》之偏失。(21)
《语类》卷六十六云:“若《易》,只则是个空底物事。”这是朱子的又一个著名观点。如果不放在其易学思想的整体脉络中来理解,它就会被单纯看做义理派的一个响亮口号,并作为肆意解释的权威借口。若果真如此,今天看来,这就是一种恶的解释观念,其危险性在清儒的眼中充分暴露出来。清儒常常批评宋明儒“游谈无根”,未必得孔孟之真意、六经之真意,即常以此为借口。其实,人们误解了朱子这一命题。朱子的原意是就《易》与他经相比较而言,《诗》、《书》诸经的特点是因“事”而有“文”,而《易》“只则是个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预先说是理”。而所谓“物事”,在此是具体、实指的,与“明澈空阔”之“理”含义迥然不同。在朱子看来,《易》是为了“说理”的,理在先、事在后,“事”遇“理”而明。“理”与“文本”的关系,综合朱子思想的多个方面来看,特别是对伊川肆意解经的指责来看,他并不认为《周易》“文本”本身也即是一个“空底物事”,《易》“理”仍应当受到《易》“文”的必要制约。今天,人们更有所谓《周易》是“空套子”、“宇宙代数学”的说法,(22)笔者认为,如果对于它们在内涵上不作严格的限定或充实,而单纯作为一种堂皇的口号而流行开来,那么对于今天严谨的《周易》经学的建设来说,只可能是一种看似充满洞见、实则充满误导人们深入思考的戏谑语。
二、经、传解释系统的分立与当代《周易》解释的困境
《易传》对于中国思想的演进来说,无疑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在哲学上,其贡献主要表现在阴阳说、乾坤论和性命说三个方面,而爻位理论系统的建立则为其后历代易学思想的推展提供了基本前提。也可以说,没有《十翼》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后来二千余年的易学的开展和推演。但是,如果仅仅以《十翼》或者马王堆《易传》类帛书为依据,那么我们对于《易经》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学的传统。这里,存在着解释原则上的重大问题。
邵雍之前,学者大体上将《周易》经传二者混同不分,认为经文至简,其义唯赖《传》以显,直接将“传义”看做“经义”本身。自邵子开始,分别出先天、后天之学及“画前易”的概念,正式开启了区别《经》、《传》文本及其思想的学术历程。朱子沿着此一路线,反复阐明“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而“画前易”则是空阔明静之“理”,不挂搭在具体的画、文上面。朱子解经即从“粗处”说,《易》之本意“只是为卜筮尔”,“元未有许多道理在”,纵使道理说得再好,“与《易》元不相干”。他明确反对以《彖》、《象》、《文言》等去解释伏羲之易、文王之易,认为伊川《易》甚于孔子《易》,去《易》之本意更远。应当说,朱子远在宋代已将《周易》经传分别开来,认为不能用《易传》去解释《易经》之本意。不过,综合理解朱子《易》学的逻辑体系,“四易”(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程子《易》)虽然被分别开来了,然而它们仍然只是明个阴阳消息、吉凶消长之“理”。(23)邵、朱的见解,在《周易》解释学上应当说具有普遍意义,值得高度重视,然而宋末至清初,学者贵尚自我,各逞己臆,让《易经》脱离“文本”自身的制约,而成为申述个人主张、意见的单纯工具和“空套子”。
清代,自顾炎武开始重视“文本”自身的研究,“语言”作为“文本”的直接载体受到重视的程度尤为突出。乾嘉学者(比如王引之父子)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将《易经》文本的语言——卦爻辞作了历史性、系统性的还原,将其客观性刻画出来。(24)这一方面衬托出前辈学者(特别是宋明儒)解经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另一方面也为后人解经划出了必要的界线。现在,又经过民国学者的论辩,《经》、《传》分观(但不应该离绝为两橛)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识。这是我们今天重建《周易》经学,或者《周易》哲学解释的第一层学术氛围和背景。这个“前见”,与我们时代的所谓“学术性”共生,还难以随意祛除,如弃土苴。与此同时,几百年来,在《周易》经学方面,从哲学、思想的角度对《周易》作注释,应当说,还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从哲学性或义理性的视角来看,《周易》经学可以说在近现代是大大地萎缩了。20世纪又有高亨、闻一多、李镜池等人的训释,(25)且长期盛行于大陆地区。高、闻、李三人的训解,直抒胸臆,清人的成果都懒得去理睬、利用,而在观念上以与传统注疏相乖异为风尚,任意揉捏、颠覆,无复“经”之为“经”矣。他们的训释虽然包含了一些真知灼见,但从总体上来看,需要商榷的问题很多,用《系辞》的话来评论,他们叫做“力小而任重”。例如,《乾》上九“亢龙”,高亨读“亢”为“沆”,“亢龙”即谓“池泽中之龙也”。(26)闻一多则读卦名“乾”为“斡”,云斡者转也,并说“疑乾即北斗星名之专字”。(27)李氏则完全顺从闻氏意见,还夸奖其“论证精确”。(28)皆为其证。现在,随着古文字学、上古汉语语言学在20世纪的逐步深入和开展,人们对于《周易》经文的认识也是在逐步加深的,无论是在观念、态度还是方法上都变得更为冷静、审慎和客观,这在最近五六年出版的相关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9)这是我们重新哲学地解释《周易》之前已经具备的第二个传统和学术氛围。这个传统和氛围,由清人发端和发展,而近百年的古文字学、上古汉语语言学运动则将其做到了具体而微。
我们有幸处在一个简帛书籍大发现的时代。帛书本、汉简本和楚简本《易经》的相继发现,为我们检验过去三百年的训诂成就和彼此见识的高低提供了基础性的材料,也为我们重新经学化地注解《周易》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认识和消化出土诸本,这是今日之学者肩负的历史任务,“盲人”和“瞎马”是无法登达成功解释之“彼岸”的。三百年来的《周易》训诂成就,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对未来的相关哲学阐释和新的经注传统的形成制造了大麻烦,而且也应当理解为为《周易》文本之“真意”在一个侧面、一定程度上的澄明和勾画提供了基础条件。
今天,可能的《周易》义理性解释或者经注,已经置身于上述两种学术氛围和背景之下,无所逃遁,但是,笔者认为应当超越。如何超越?使用经学的方式对《周易》的含义加以重新的阐发,对于今日的学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突出地表现在甚至连重新作哲学解释、再次进行跃迁的“虫洞”,目前似乎还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虽然如此,就当下的情况来看,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同时具备几种学科的知识和能力,否则的话,我们仍将“力小而任重”,无法将《周易》解释从一种对象化的、分解性的研究方式转变成为一种有机综合的经学训解方式,并接上古人的注疏传统。传统注疏即已包括“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个相统一的方面,但“注疏”本身是“经学”延续的基本方式和载体,也可以说是其命脉所在。就二千余年的经学实践来看,“注疏”既是经义得以延展和新生的基本方式,也是“经学”本身得以存在的基本方式。自乾嘉以来,这一“命脉”即堙塞不畅,胜义难寻。不能不说,这是清儒的罪过。20世纪的经学研究,主流也是一种考古式、博物馆式的工作,不是以经义的创发为目标的,而所谓“校”、“注”、“译”,也多是试图让人理解卦爻辞的字面意思,距离古人在“画—象—辞—占—意”的整体结构上来理解《周易》文本,还十分遥远。当然,20世纪也有一些对于《周易》的哲学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成果,其一数量不多,其二主要是引进另外一套哲学观念来做诠释,很难称得上“经学”的方式,其三避重就轻,舍《经》而以《传》作为解释的依据。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是熊十力先生,此外还有牟宗三先生。熊先生的易学哲学可以概括为两点,一个是“(乾坤)翕辟成变”,一个是“乾元性海”。(30)牟宗三先生先后写了两本关于《周易》的书,一本叫做《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函义》,另一本叫做《周易哲学演讲录》。(31)前一本是牟氏早年作品,用怀德海的过程哲学来理解和研究《周易》注疏,以对注疏的理解来代替《周易》经传本身之义理。当然,这里就存在解释的正当性问题。后一本书是牟氏晚年的讲演录,以《易传》(特别是《系辞》及与乾坤论相关的文本)为哲学解说的材料基础,在该书中,我们同样能随处读到大段引述西洋哲学的文献和观念。另外,两书都是用我们现在的论文方式来写作的,也不是所谓传统的“注疏”形式。因此,牟先生所阐发的《周易》哲学,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很难将其轻而易举地归入“经学”的统系。总之,《周易》解释要重新实现经学化,并将义理性(乃至哲学性)的阐释有机地植入其中,确实存在很大困难:沉舟病树,山重水复。
三、训诂与《周易》本经的重释
笔者还想强调一下,为何训诂对于《周易》经学的新发是如此之重要和必要?这里仍以《伊川易传》为例。朱子曾指出,伊川解《易》与《易》之本义不合,又认为其解说拘碍,三百八十四爻只作三百八十四件事解,(32)切中了程《易》的两大弊病,但是他并没有着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阐明程《易》存在的大问题。程子倡导义理解《易》,所说之理本身虽然很精实,但是他的文字训诂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关键在于,他有一些重要义理的阐发就是建立在这些错误的训诂之上的。即是说,他阐明的道理是有理的、正确的,但是由于他的文字训错了,正确的道理是加在错误的文本理解之上的。总之,他是懂得一个道理,而把它加在一个文本上,将“文”拉来,稀里糊涂地载“道”。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笔者先举一个。《蒙》卦六三爻辞:“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伊川的训解是:“女之从人,当由正礼。乃见人之多金,说而从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33)这就把“金夫”训成今天的所谓“大款”。而在汉魏的故训里面,它是很明确的,虞翻、王弼都解释为“阳刚之男”,(34)与“懦夫”一词大抵相对。伊川利用“多金男”的训释很自然地加进了并凸显了道德性的议论。从今人的眼光来看,将英雄“武松”与商痞“西门大官人”混作一团,这是缺乏基本的分别的。又如,《屯》六二爻辞:“乘马班如。”《伊川易传》云:“班,分布之义。下马为班,与马异处也。”(35)这等训诂近似于糊弄,但也未见程子于此发明出什么高明的道理。实在,伊川不懂训诂,但又喜欢通过训诂以生义理。需要指出的是,这许多“硬伤”、斑斑“劣迹”,很可能也是由当时风气所致。王安石的《字说》谬误不少,甚至是笑料,(36)《宋史》卷327《王安石传》即云:“(王安石)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王氏《字说》受到时人及后人的讥评,究其原因,朱子曾指出:“字本来无许多义理,他要个个如此做出来,又要照顾须前后,要相贯通。”(37)叶适也抨击道:“王氏见字多有义,遂一概以义取之……是以每至于穿凿附会。”(38)固然王氏的解字观念(凡字均依会意为说,又要求得个“义理”)十分偏执,错谬百出,但是程子又未尝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呢?
相对来说,上举二例《伊川易传》的训诂错误还是“小节”,而“元亨利贞”的训解则是今日之“大事”。对于《周易》经注的重构而言,这是今天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元、亨、利、贞四字,遍布整部《易经》,几乎无处不在。《十翼》继承穆姜的四德说(《左传·襄公九年》),而加以普遍化。后人有关《周易》经学的义理阐释,包括《易传》,都是建立在释此四字为四德的基础之上的。不过,程伊川已意识到从辞例的角度来看,“元、亨、利、贞”作四德解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乾》彖辞“元亨利贞”,《程氏易传》云:“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则随事而变焉。”《随》卦辞“元亨利贞”,伊川即读作“元亨,利贞”,“元亨”即训为“大亨”,“利贞”即训为“利在于贞正”。(39)朱熹又前进一步,他认为“元亨利贞”,就孔子《易》(即今本《易传》)而言为四德,就文王《易》(《易经》)而言乃“大亨,利正”之义,并批评伊川将此四字在《经》中分为两种句读来读,缺乏根据。(40)今天看来,朱熹的句读是对的;不过,凡遇“贞”字,朱子与伊川、王弼等人的训解却没有什么不同,皆按“正固”的道德性含义来阐释。现在,由于百余年前甲骨的大量发现和甲文研究的随后展开,“贞”字本意崭露,而传统的训释由此发生断裂和崩解。这对《周易》经文作德义化或道德化的义理阐释,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应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因为我们知道,“贞”字已经不能按照正固、贞洁之义及其在背后定调的道德性方式来理解了。现在早已成为常识:“贞”是占问、贞问的意思。(41)这是20世纪《周易》研究的最大贡献之一。不但如此,语言是有社会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按照《易经》本身的辞例来看,“元亨利贞”当读作“元亨,利贞”,(42)根本不是什么“四德”。可是,由于大多数学人不宗朱子句读,又常将《经》《传》混杂而论,导致此四字误读误断相续二千余年。这不由得不让人感叹、唏嘘三月。总之,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要超越古人,我们要训解《周易》,把它重新变成经学,一种“训故(旨趣)举大谊(义)”(《汉书》卷88),一种充满义理之趣的经学,确实困难大极了。这里,需要旷世大儒的出现。
注释:
①出土《周易》材料,包括楚竹书《周易》(1994年春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海博物馆于同年5月收藏)、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经文及六篇《易传》类帛书(1973年底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汉简《周易》(1977年出土于阜阳双古堆汉墓)、熹平石经。此外,1993年在湖北荆州王家台出土了秦简《易》占材料(学者或称为秦简《归藏》);在汲冢出土了晋武帝时期《易经》及《传》类著作多篇。部分资料,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马衡:《汉石经集存》,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近十年出版的相关专著约有15种之多,相关论文则多达数百篇,仅《周易研究》杂志在近三年即发表了30余篇,例如刘大钧、夏含夷、廖名春、谢向荣及笔者均有论文发表,参见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卦爻辞补释》,《周易研究》2011年第5期;夏含夷:《〈周易〉“元亨利贞”解——兼论周代习贞习惯与〈周易〉卦爻辞的形成》,《周易研究》2010年第5期;廖名春:《〈周易〉比、履、离、泰四卦爻辞零释》,《周易研究》2010年第5期;谢向荣:《论楚竹书〈周易〉“讦”之卦义》,《周易研究》2011年第2期;丁四新:《马王堆帛书〈周易〉卦爻辞校札九则》,《周易研究》2011年第3期。
③对于楚竹书本首符、尾符的研究,始于濮茅左先生,李尚信、陈仁仁等的后续研究比较深入和详细。参见濮茅左:《关于符号的说明》,载《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51-260页;濮茅左:《楚竹书〈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46页;李尚信:《卦序与解卦理路》,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87-102页;陈仁仁:《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4-85页。
④李镜池认为:“‘九’‘六’二字,在原始的《周易》是没有的;它的插入,当在战国末秦汉间,为的是便于应用;创作的人物,当是作《易·象传》、《文言传》等儒生。”李镜池:《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6页。
⑤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页。
⑥参见陈玉森、陈宪猷:《先秦无〈易经〉论》,《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⑦参见韩巍:《北大汉简〈老子〉简介》,《文物》2011年第6期。关于《老子》文本在西汉的演变过程,参见丁四新:《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9-210页。
⑧例如,《尚书·洪范》云:“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左传·僖公五年》云:“(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同书《僖公十五年》云:“(韩简子曰)龟,象也;筮,数也。”《周礼·春官·太卜》曰:“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皆将卜筮联言。
⑨“《易》本卜筮之书”,朱子或说为“《易》本为卜筮而作”、“盖《易》本是卜筮之书”、“《易》只是个卜筮之书”、“《易》为卜筮而作”、“《易》书本原于卜筮”等,意思相近。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6,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20-1633页。
⑩参见濮茅左:《考古易的发现》,载《楚竹书〈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96-510页;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新蔡葛陵楚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张政烺:《易辩》,载唐明邦等编《周易纵横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4-186页。
(11)张政烺:《张政烺论易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76页。
(12)《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段话,与《礼记·缁衣》末章“子曰”相近:“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缁衣》“南人”,孔颖达《正义》解为“殷掌卜之人”,得其意;其实“南”为“宋”字之形讹,郭店、上博楚简《缁衣》均作“宋”,可证。《子路》篇“巫医”,据传本及简本《缁衣》均作“卜筮”,可知此二字当为后人所改。据两种楚简本,《缁衣》自“《兑命》曰”下诸字,皆为后人衍增。而《子路》篇“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十五字,为后人衍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根据大量出土简帛书与传世文本的勘校,可知从先秦至刘向校书定编之前,子书在这段时期内的变化很大,文本多呈现不断衍增、扩充的趋势。《荀子·大略》云:“善为《易》者不占。”《子路》篇文本的变化、衍增,或许受到荀子后学的影响。总之,在目前的学术观念中,我们无法将《论语·子路》“子曰:不占而已矣”一句,毫无保留、怀疑地看作是孔子本人的意思。孔子虽然崇尚“德义”的一面,但由此说他当时有意摒弃占筮而不用,这既非孔子的性格,也与春秋后期的思想背景不合。
(13)《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记·孔子世家》:“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14)参见程颐:《伊川易传·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经部一·易类》第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57页。
(15)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7,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49-1654页。
(16)朱熹:《周易序》,《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朱子语类》卷65:“问:‘易以卜筮设教。卜筮非日用,如何设教?’曰:‘古人未知此理时,事事皆卜筮,故可以设教。后来知此者众,必大事方卜。’”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21页。
(17)《朱子语类》卷67:“问《易》。曰:‘圣人作易之初,盖是仰观俯察,见得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非特《河图》、《洛书》为然。’”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46页。
(18)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7,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22、1629页。
(19)朱子曰:“圣人作《易》之初,盖是仰观俯察,见得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非特《河图》、《洛书》为然。”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7,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46页。
(20)《河南程氏遗书》卷2:“尧夫诗……‘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这个意思,古元未有人道来。”(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5页)《朱子语类》卷62:“伏羲画卦,只就阴阳以下,孔子又就阴阳上发出太极,康节又道:‘须信画前元有《易》。’濂溪《太极图》又有许多详备。”(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504页)“画前《易》”的概念,无疑出自邵雍。关于此概念的含义,朱熹《答袁仲机》书中有明确的说明:“是皆自然而生,瀵涌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势,而天地之文、万事之理莫不毕具。乃不谓之画前之《易》,谓之何哉?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写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晓矣。其曰画前之《易》,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于聪明神武之人以发其秘,非谓画前已有此图,画后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义。若不识此而欲言《易》,何异举无纲之纲、挈无领之裘,直是无着力处!”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8,《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77页。
(21)《朱子语类》卷66:“林择之云:‘伊川易,说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尝说:“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说也好。而今似他解时,依旧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25页。
(22)这两个用词出自冯友兰先生,近30年来成为学界理解《周易》文本的流行观念。参见冯友兰:《〈周易〉学术讨论会代祝词》,载唐明邦等编《周易纵横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页。
(23)以上所述朱子思想,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6,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29-1630页。对于“卜筮”与“理”的关系,朱子以体用来理解,卜筮之中即见理体。当初伏羲画卦,其本意为卜筮之用,然即此可见阴阳消息、吉凶消长之理。文王以下,本意浸失;至于孔子,“尽是说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
(24)乾嘉以来,《周易》研究的著作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字训诂方面,王引之父子的《经义述闻》堪称此方面的代表。此外,惠栋、宋翔凤、李富孙等在恢复古义和辨析异文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参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9年;惠栋:《周易述》,《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宋翔凤:《周易考异》,《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1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李富孙:《易经异文释》,《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1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
(25)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闻一多全集》第10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6)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4页。
(27)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闻一多全集》第10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1页。
(28)李镜池:《周易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29)参见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侯乃峰:《〈周易〉文字汇校集释》,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陈仁仁:《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郑玉姗:《出土与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经文考释》,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张政烺:《张政烺论易从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丁四新:《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0)参见熊十力:《新唯识论》、《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载萧萐父、郭齐勇主编《熊十力全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郭齐勇:《熊十力思想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40-277页。
(31)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3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32)后一点,《语类》卷68云:“祖道举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是君子进德不懈,不敢须臾宁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语亦是拘了。记得有人问程子,胡安定以九四爻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说极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说,则千百年间只有个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一爻才刚而位危,故须著‘乾乾夕惕若厉’,方可无咎。若九二,则以刚居中位,易处了。故凡刚而处危疑之地,皆当‘乾乾夕惕若厉’,则无咎也。”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94页。
(33)参见程颐:《伊川易传》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经部一·易类》第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75页。“金夫”,朱熹的训解与程颐相近。参见朱熹:《周易本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5页。
(34)参见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2,潘雨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10页;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1,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7页。
(35)程颐:《伊川易传》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经部一·易类》第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71页。朱熹训“班”为“分布不进之貌”,虽与程训有所不同,然依旧惑于程《传》训解。参见朱熹:《周易本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1页。
(36)参见曹锦炎:《王安石及其〈字说〉——介绍张宗祥辑本〈熙宁字说集〉》,《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
(3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0,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100页。
(38)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14页。
(39)程颐:《伊川易传》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经部一·易类》第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第157、221页。
(4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6、68,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22、1688页。
(41)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4页;王国维:《史籀篇疏证》,载《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第23页;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94页;丁四新:《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9-190页。
(42)高亨、李镜池等将甲骨学者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易经》“贞”字的理解上,认为亦是“占问”、“卜问”之义。这个意见,逐渐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这也是20世纪《周易》研究的最大贡献之一。高亨:《周易占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4页;李镜池:《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31页。
标签:易经论文; 儒家论文; 经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易经六十四卦论文; 周易研究论文; 国学论文; 老子论文; 读书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孔子论文; 十翼论文; 易传论文; 伊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