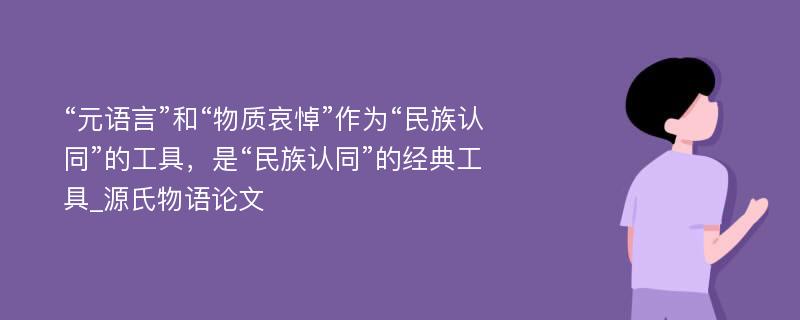
作为“国家认同”工具而被经典化的《源氏物语》与“物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氏物语论文,工具论文,经典论文,国家论文,物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紫式部《源氏物语》(1001-1008)的创作目的,日本历史上有讽喻、物纷、物哀诸说,自1960年代末起,评论界曾一度把《源氏物语》所褒扬的物哀误作贯穿日本古今的“情操性”文艺与审美理念①。尽管“时至今日,应已无人公开认同本居宣长的‘《源氏物语》的目标就是描绘物哀’这一见解”②,“但不知自何时起,我们已将之视为命题化的培育国学的‘风土’,且至今仍立足于此”③,换言之,该错误认识仍深深影响着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对“日本性”的认识。 物哀论经历了曲折多变的历程。本居宣长(1730-1801)以平安(794-1192)贵族深受无常观影响的“哀”为基础,以产生于近世(1603-1867)町人(城市居民)的带有无可奈何的悲哀感与颓废观色彩的“哀”为内核,将原本是歌论术语的物哀扩展为评论物语的术语,并逐步形成了系统的物哀论,用以建构町人的身份认同。④在西方文学批评思想的影响下,近代日本评论者以物哀为关键词,将《源氏物语》解读为写实小说,而在建设“国文学”的热潮中,物哀则被作为日本国民的“特质”而逐渐被经典化。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宣长的国体论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支撑“大东亚共荣圈”殖民理论的话语基础,但其物哀论并未受到同样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宣长的国体论被视为禁区,其物哀论更无人提及。不过,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物哀被逐步用作加强国家认同和心灵救赎的工具,成为了现代日本的象征符号,而自1990年代以来,为克服经济滞涨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人们在进一步强调物哀的同时还开始重新提倡武士道精神。 本文拟从“经典形成”⑤这个角度重新审视《源氏物语》的文化史地位,探讨物哀这一日本文艺与审美代表性理念的特性的变迁,梳理该理念对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并分析它是如何成为日本建设、确立和加强国家认同⑥的重要工具的。 一、近代以前非主流的《源氏物语》与物哀 经历了平安初期的“国风黑暗”后,在平安中期,日本迅速进入假名文学鼎盛期——“国风时代”。尽管物语创作达至巅峰,但由于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直到近世中期,汉字和汉文学在日本一直拥有绝对的公共性、学术性以及宗教性,平假名被视为女性书写符号,物语则仅仅是女性的娱乐读物:“纵览平安时代以降国语文体的发展,稳居潮流中心的是继承古代传统的汉文,而非以平假名或片假名为载体的文章。”⑦在这一语境中诞生的《源氏物语》不是因为其所谓的物哀理念而是因为被视为和歌咏唱指南才显得地位特殊。尽管如此,基于感叹词“哀”发展而来、进入平安时代后才逐渐具有相对稳定内涵的“物哀”,经紫式部《源氏物语》的流布,才“具备了对象性与事件性,发展成为了基准与依据,即具有了典型性”⑧,并最终成为宣长所推崇的“物哀”的基础。 假名的出现表面上是为了满足用新的标记法来体现原本用汉字无法标示的日语固有的发音及语调这一需求,但它实际上是一直受中华这一强势他者压抑的日本本土文化与思想抬头并谋求自立的标志。⑨同时,正如《古今和歌集》的假名序刻意将和歌与力证皇室正统性的《古事记》(712)及《日本书纪》(720)等联系起来这一方式所示,“国风”与后来的日本语言民族主义一脉相承,均与天皇政体密切相关。就《源氏物语》而言,“在平安时代这一口头语言文化时代,文字文化中存在着人们对身份认同的不安。深入到借助文字进行创作的世界中去的作家紫式部,其物哀观念……蕴含着她依靠该创作行为而前瞻性地深刻体验到的这一不安”⑩。 其后,随着律令体制与贵族统治日趋崩溃,国家动荡不安,加上广为传播的佛教末法思想的影响,无常观和厌世思想深入人心,让本来就不占据社会主流的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更加边缘化,处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之中的日本知识分子只能通过“风月诗酒之乐游”来寻求解脱。在此思想背景下,日本国内对紫式部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包括地狱说、观音化身说及相关的寓言说与劝善惩恶说。 地狱说评价的代表为《宝物集》(1177-1181)与《源氏一品经》(1168,亦称《源氏一品经表白》)。这两部著述通过设置好色的作者及痴迷于阅读好色作者撰写的作品的男女堕入地狱这一结局,以传经说法的口吻将《源氏物语》批判为充满淫词秽语的小说,《源氏一品经》即“谓彼制作之亡灵,谓此披阅之诸人,定结轮回之罪根,悉堕奈落之剑林”(11)。《源氏一品经》甚至被认为具有拯救作者及其读者灵魂的功效:自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1192-1333),日本社会流行“源氏供养”及“源氏讲式”,即为拯救坠入地狱的作者和读者的灵魂而为之举行的法会,《源氏一品经》就是此类法会上所咏唱的表白文的文集。该做法被广为继承,如《宝物集》之六云:“歌人相聚,书经供养。”(12) 观音化身说则是对该作品及其作者的正面评价。例如,《今镜》(1170)除认为“纵然杂绮语、秽语,亦未至此深罪[即坠入地狱]”(13)外,还引用了白乐天文殊化身说,称赞紫式部以“女身而行此事,非常之人也。已臻妙音观音,高贵圣女,惟以说法导人哉”(14),将紫式部的行为视为佛家的“方便善行”。该说法为《河海抄》(1362-1368)等所继承,而谣曲《源氏供养》(1384)更将紫式部称为“石山观世音”,将其创作目的解释为旨在拯救众生(15)。与此同时,也有论者基于儒佛思想将《源氏物语》视为寓言,如《孟津抄》(1575)就断言紫式部乃效庄周而创作。“自中世至近世前期的‘寓言说’,似为将《源氏物语》这一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与佛教儒教思想折衷而形成的讽喻之策”(16),其共通点是极力避免提及书中的“诲淫”、“私通”之处。 进入近世,融政治原理和社会道德规范于一体的朱子学被江户幕府确立为思想统治工具。儒学家一方面对《源氏物语》中的诲淫描写深恶痛绝,一方面又重点强调其中的教化之意,认为紫式部借助对书中人物的各种惩罚进行了讽喻。例如,安藤为章认为,该物语“虽其大旨为讽喻妇人,但窃以为诸多事例亦为男子之教训……含劝善惩恶”(「説」:190)。更为重要的是,安藤首先将“物纷”作为关键词引入源学,认为“物纷”乃“全书之大事”,强调“意在讽喻,至关重要的是要对乱伦生子加以劝诫”,还进一步“将紫式部的这种‘讽喻’称作‘大儒之意”’。(17)直至明治(1868-1911)中期仍稳居统治地位的“劝善惩恶”文艺观继承了该观点,而且,“尽管该文艺观为近代文艺自立论所驱逐,但实际上仍然在深处束缚着我们日本人”(「説」:5)。 另一方面,尽管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但由于独特的自然观及传统的熏陶,日本文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没有接受中华文化中诸多与日本传统生活、情感及宗教信仰相悖之处。同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阶层实力日益强大,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始萌发文化与政治上的愿望和要求。这种愿望和要求与“国学”运动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产生了较为强大的影响力。 “国学”始自对江户时代已严重流于形式的中世歌学的批判。中世时期,随着权力从贵族逐渐转入武士阶层手中,知识分子失去了由中古贵族政权所保护的贵族文化这种身份认同,倾向于从数百年来所累积的和歌语言中寻求存在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江户中期部分知识分子基于复古主义立场,批判抹杀人类自然感情的儒教与佛教道德等,试图通过对日本语言与歌学尤其是日本古代文学与神道的研究,重现在受到儒家及佛家思想影响之前的古代日本所独有的文化、思想和精神世界(古道),崇尚真情的自然表露,并据此致力于确立对抗儒学的思想体系。例如宣长虽然宣扬物哀,但却在其著作中坚持“古事记传应排名首位”(18),更注重对日本皇室主导下的为塑造天皇统治正统性而编撰的《古事记》研究。 基于急于摆脱中华影响从而完成思想和文化自立这一对抗意识的“国学”运动的出现,也是中世后期与近世时期日本社会基础发生巨大变化的必然结果。随着武士政权江户幕府所确立的高度集权中央统治体制的日益稳固,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在农村,各村的经济独立性大大降低,村落内部产生阶级分化,建立在以神道为中心的农耕祭祀文化基础之上的农民身份认同受到了侵蚀和削弱;在城市,随着城市发展为经济中枢,各商业团体、商人和手工艺人不再以农村传统的地缘及血缘为主要纽带来获得身份认同,如何构建町人身份成为了现实的社会问题,几乎主导了近世后期的文艺思潮。 就方法论而言,“国学”其实是音声中心主义。“国学者”们认定以假名为载体的和歌与物语才是最具“大和性”的文本,试图将之推升至文艺最高地位以确立新经典,同时又积极将佛教、儒教及中华的诗与史等排除在经典之外,甚至攻击一切他们认为受到了外国影响的事物,希望能借此将日本还原为古代的理想世界。(19)例如,宣长认为只有汉字传入之前的声音语言(古代口语)才是毫不虚伪的世界,所以他追求的是由古语所支撑的世界,所坚持的立场也是“我们[日本人]的世界的根基必须求自我们自己的语言之中……[而这]也是他力图从‘古言’中求得自我确认的一贯追求”(20)。 那么,身为町人的宣长所推崇的物哀究竟为何物?当时,城市支配权为仅占全国人口10%左右的以将军为首的上层武士所掌控,由于被严格固定在严酷的封建专制政治秩序中,町人们产生了深深的闭塞感与悲伤感,不得不转而享受生之快乐:“本应成为深深悲伤的感情,结果却向充溢着颓废气息的‘欢快心情’方向转化。这种内心与外显之间的反转好似梅比乌斯环,借助主体在二者之间的游弋,人们从受压抑的日常生活中巧妙地避身出来。”(『物』:31)故其物哀其实“是大多数人由于被剥夺了政治上的自由,由于受压抑、无法自我表现而弥漫在近世城市中的以悲哀感为内核的感情”(『物』:82)。宣长将町人这种共同感情称为物哀,并溯源至《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所出现的哀,成功地将之塑造为植根于日本文化本质的感情。正如《排芦小船》所言,“和歌之本体,既不为辅政,亦不为修身,不外乎言心中所思”(21),宣长所推崇的物哀实质是主情主义。更重要的是,宣长“视‘物哀’为与天皇密不可分的贯穿日本精神史的基本感情……将自己从小所浸润的町人性的感受性正当化与社会化,将近世幕藩体制所支持和认定的作为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视为外来文化而予以排斥”(『内』:76),形成了所谓的“天皇、和歌、物哀三位一体”(『内』:78)理论。该理论“将古道/惟神推崇为‘大道’,对振兴国民精神发挥了很大作用”(『本』:43),最终发展成为日本国粹主义与皇国史观的理论基础。 不过,在江户时代,作为思想统治工具的儒学才是主流学说,“国学”甚至根本未能进入各藩校(各藩为培养人才而建立的学校)的核心课程;在町人阶层中,浮世草子、净琉璃以及劝善惩恶的“戏作”文学才最受欢迎。而且,该时期对假名文学的负面评价仍据主流,如宣长老师贺茂真渊对古代以及《万叶集》中所体现的“大丈夫气概”赞赏有加,却对平安时代以及该时期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柔弱女性气质”评价颇低,甚至认为该时期由男性的阳刚转向女性的柔弱是历史的倒退。(22)因此,直到明治末年,宣长仍然只在特定研究界中占据一席之地。(23)但是,如今看来,“国学”运动是日本民族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其中心是借助回溯到日本古代这一方式构建与中华相对立的想象中的“大和”,从而形成自我认同话语,最终与中华思想及文化抗衡。同时,这也是以町人为主体的学者们的反抗,反抗的对象则是以朝廷为中心的贵族性质的和学传统,以及由武士阶级知识分子为先导的支配着当时思想界与幕府意识形态的朱子学。 二、近代以降逐步经典化的《源氏物语》与物哀 明治初期是“欧美一边倒”的欧化时代,加上《源氏物语》和物哀的“女性柔弱”气质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格格不入,因而并未受到维新人士的青睐。在急功近利的近代化浪潮中,内村鉴三、斋藤绿雨等人更对《源氏物语》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例如,内村曾质问道:“在鼓舞日本的士气方面,《源氏物语》发挥了什么作用?不但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反而将我们改造为女人般的懦夫。希望从我们中根除这样的文学。”(24)但进入明治中期后,“因其最初数贴(醍醐、宇多朝)对天皇亲政这一理想模式的描述,《源氏物语》适应了明治维新所带来的‘回归天皇统治’’’(25),故短暂受到了重视。与此同时,“国学”尤其是宣长的国体论则受到了高度重视,开始转化为构建国民国家的文化工具。 在文学方面,儒家思想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如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认为《源氏物语》部分内容猥亵,许多评论家也将之视为专述好色的书籍,“至少持续至[二]战后,当基督教系的大学也开始正式讲授《源氏物语》后,将之视为淫书的势力才消失”(「説」:187)。但随着西洋化的迅猛发展和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日本社会对《源氏物语》的评价也很快发生了变化。为与列强比邻,明治政府比照西方积极实施“自我殖民地化”,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与西欧抗衡或者类似的事物,以此来确立国家认同,因此,坪内逍遥将《源氏物语》视为“写实小说”、将宣长所洗练的物哀视为日本传统“写实”理念之立场极大影响了文学评论界。(26) 当然,在探究《源氏物语》在该时期的地位时,我们还须将之置于日本所兴起的建设“国语”与“国文学”热潮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深受西欧音声主义影响、承继“国学家”成果而兴起的日本“国文学”运动仍然是语言国粹主义。日本国文学家们深刻认识到,“在本质上,国语在承担国家诸制度作用的同时,也发挥着作为国民团结之象征这一作用”(27),于是提出了日语与“忠君爱国”思想一道构成了统一近代日本的两大力量这一观点,认为国体体现于国语之中(28)。与此同时,鉴于“国文学贯通于国民一统,赋予同胞一体之感觉,为一国特有之显像;其职能对于外国,可固国民之凝聚力,化其为一元之素”(29),日本国文学家们由此认为“作为‘国民’精神反映的‘国文学’一直在持续发展而无断绝——[日本]具备了作为‘文明国’的条件”(30)。于是,日本掀起了建设国语和国文学的热潮,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日本”、“日本语”、“日本人”及“日本文学”四位一体这一虚像,而日本国文学家们所“创作”与“发明”的日本文学的“特性”也日渐成为日本的身份认同的基础,这可以在明治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国文学家”芳贺矢一、藤冈作太郎和五十岚力对《源氏物语》的评论中找到佐证。 芳贺认为,宣长“在玉之小栉中将之[《源氏物语》]解读为让人知物哀的作品,诚为高论”(31);藤冈也指出,《源氏物语》“是看破人生秘密、详尽描述诸人性情的作品,古今无出其右者”(32);五十岚则将宣长对《源氏物语》的校订视为“精细的科学研究”,认为“唯用语古旧,实乃超越时代之卓见。所谓淫秽之书、教训之书、体现佛理之书之类的愚说,均难望其项背,乃……切中肯綮之名批评”(33)。这些评论站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角度,以西方视角观照日本古代文学,将宣长物哀论置换为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中的写实与抒情等,并将之本质化为超越时空的普遍概念,以实现建构“国文学”这一目标。最终,日本社会形成了一个“常识”,即,“源氏之前无源氏,源氏之后亦无与之比肩者。《源氏物语》非唯平安朝之第一,乃我国横贯古今之第一小说”(『国』:434),并将该文学作品建树为“世界最早的写实小说,对其进行英译以期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34)。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之所以宣传《源氏物语》与物哀,其目的就在于以此证明日本的“写实”历史源远流长,足以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坪内逍遥认为小说应以描写人情为主旨,从而掀起日本小说写实的高潮,而宣长的主情说物哀观正好符合该形势。许多评论家据此提出,“‘满足本能’在古代的平安时期已经实行”(『国』:46),“倘虑及日本文学之特性,深感日本人尤具抒情性”(35),将物哀说成日本人自古就有的特性。该主张与当时的政治言说遥相呼应,例如,从古代到现代一直存在着丝毫不变的日本特质,这正是日本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处等。这与“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皇国史观异曲同工。 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层面,由于适应了建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统治这一形势的需要,继承宣长衣钵的平田笃胤的神道理论成为了日本国家神道理论的一部分,宣长所鼓吹的“天皇、和歌、物哀三位一体”理论,“在政治上有意将家父长制与家族的地位提升至政治高度,即将天皇在象征意义上提升为国家之父,从而完成了将人们自然的家族共同性直接与国家共同性连接在一起的操作”(『物』:35),在近代天皇制最终完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借助“天皇制这一支柱而被普遍化和扩大为日本性,[物哀]转化为涵盖了所有日本人的黑洞”(『物』:15),为形成帝国主义时期日本的国民身份认同提供了方法论。以1883年3月2日明治政府追赠“四大人”——被视为“古道”正统派的荷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正四位”为标志,日本社会树立起了一个神话,即“四大人”的古道论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从而确立了古道论的正统地位和绝对权威,并为确立二战期间宣长的绝对地位奠定了基础。 步入帝国主义时期,日本当局设立了“教学局”、“日本文学报国会”、“日本诸学振兴会”等组织,加强对文化和思想的统治,以“明证国体”,而对当时的“大日本帝国”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是天皇谱系的神圣化。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受欢迎的是宣长的“古道论”,它被用于“为大东亚战争期间的国策服务,煽动国民皇国意识”(『本』:195-196)。佐佐木信纲宣传宣长的《松阪一夜》被改编并收入第三期国定教科书,该著也催生了关于宣长的系列国民神话,宣长在《玉胜间》中所探究的“古代的真之意”,在不同版本的“松阪之夜”中演变为不同的说法:佐佐木信纲沿用了宣长的说法,教科书版阐释为“我国古代精神”,而纸牌版则发展为“日本精神”。其中,“日本精神”这一词语萌芽于1920年代,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流行,并一跃成为“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首的国家组织”的心灵特征,是二战期间最具日本意识形态色彩的用词,在日本侵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详见『本』:195-196)。 宣长理论究竟如何与军国主义产生了关联?首先,宣长的“古言”及“言灵幸国”论适应了日本人的文化习惯:在万叶和“记纪文学”时代,和歌已在上层贵族中具备了政治象征意义,进入中世后,和歌则直接与天皇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成为了充当“政治/文化工具”的宫廷诗,而进入近世社会后,“宣长更进一步从《古事记》所描述的人与神的世界中寻找日本文化的原初形象”(『内』:33-34),“借助‘物哀’,将‘天皇与和歌’联系在一起,参与建构了强有力的近代天皇制意识形态”(『内』:78)。在天皇制这一意识形态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19世纪20年代,宣长的相关理论和所推崇的文献,如其所咏和歌“问道敷岛大和心,山樱香阵熏朝霞”,作为经典获得了特权地位,并在二战期间成为日本皇国思想的支柱。事实上,“敷岛歌”原本与军国主义无关,但由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樱花被视为武士道的象征,该和歌因此被视为颂扬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精神的和歌,其作者宣长则因被视为借助该和歌宣扬武士道精神的思想家而被尊为“军神”。(36) 尽管宣长的“国体论”被改造、利用并提升为经典,其物哀理论则由于《源氏物语》的种种遭遇而没有受到重视,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法西斯体制毫不留情地打压和禁止绝对不利于维护天皇统治的事物,而《源氏物语》即在被打压之列。1933年11月23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了《源氏物语》被日本警视厅保安部禁演一事,认为“真实演出禁中的古代生活、舞台人物中有高贵之人、恋爱故事的连续,均客观存在允许其上演后理所当然会遭到抗议的情况”(37);同日,东京《朝日新闻》则报道称,“当局发布禁止令,并未指出任何具体问题,只是基于整个剧目会损害社会风气这一不疼不痒的理由”(38)。与此同时,将《源氏物语》从学制教育中驱逐出去的呼声也屡现不绝,其顶点就是1938年要求删除介绍该书的短文的运动。《国语解释》主编橘纯一接连发表了《要求删除小学国语读本卷十一〈源氏物语〉》、《不敬之书〈源氏物语〉抄译(之一)》等文章,掀起了要求从学制教育中驱逐《源氏物语》这一运动的高潮。橘纯一视《源氏物语》为“大不敬之书”的理由,与担任谷崎近代语译本《源氏物语》校阅工作的山田孝雄所提出的三点删除意见完全一致,即,作为臣下却与皇后私通、皇后与臣下的私生子即天皇位、作为臣下却登上了相当于太上天皇的宝座(39)。就天皇制这一意识形态而言,这三点意见的出发点则是,在想象力这个层面,《源氏物语》对“万世一系”且神圣不可侵犯的皇统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源氏物语》“与大日本帝国这个巨大的物语之间必然产生倾轧”,而“国定教科书论争,正是《源氏物语》与大日本帝国这两个不共戴天的物语借助义务教育这一舞台所进行的类似于战争的激烈斗争”(40)。在当时,受到推崇的自然是那些力证皇统的卓越与至纯、讴歌“大和魂”与“日本精神”等内容的文学作品,而《源氏物语》一书仅仅在“少女卷”中出现过一次“大和魂”,自然不合时代潮流。因此,当时日本国内的大部分学者要么对该书持批判态度,要么避之不及,而谷崎润一郎则在“翻译源氏之时,将可能招致军部愤怒的部分,或歪曲或省略”(41)。 当时也有学者力图通过扭曲这种形式将《源氏物语》提升至经典地位。例如,部分国文学家援引原有的“劝善惩恶”论,重新将《源氏物语》解读为基于方便法门的劝善惩恶之书,强调该书的颂扬对象是纯正的皇统与国体,只不过自明治以降,在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下,该书被误读为诲淫书,这是日本国语国文学界的耻辱,需要予以纠正等。(42)但是,在“国体运动”占上风的时代,这种主张自然收效甚微。于是,《源氏物语》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物哀在国内被官方排除于“日本精神”主系列之外,受到了打压。 不过,在对外宣传日本形象时,由于“在短时间内就深深陷入八纮一宇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昭和天皇制法西斯必须穷尽一切手段粉饰日本至上主义的幻想,对于能使旭日旗更显荣耀的文化遗产,即便拔除其骨干部分,也须夸示其内容,于是,被去势的《源氏物语》徒具形骸和虚名,被利用于民族政治宣传”(43)。例如,1935年9月8日,《报知新闻》刊发了题为《〈源氏物语〉电影化/拍摄法语版》的报道,宣称在面向海外宣传日本文化艺术以扩大日本影响时,当局对《源氏物语》被拍成电影予以了不遗余力的支持。(44) 三、作为日本表象而被极力宣传的物哀 二战结束至日本经济腾飞之前近三十年间,由于美国占领军主导下的民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宣长理论被改造利用的这段不光彩历史被视为研究禁区,物哀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无人再提及。但是,“天皇、和歌、物哀三位一体理论并未解体,且一直存续至今”(『内』:78):战后的日本一方面保存了作为差别主义与排他主义象征的天皇形象,一方面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救赎,将物哀作为构成日本社会的同质性基础,使物哀在凝聚国民向心力、推进国家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战后社会急剧变化,日本迅速融入了国际社会,借助经济高速增长彻底从战后废墟中站立起来,并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瞩目。如何利用这一形势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建立与加强现代日本的国家认同,成为了日本举国上下的时代课题。在政府层面,日本开始加大力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利用,引发了各种日本论、日本人论及日本语论热潮。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及1970年的大阪万国博览会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举国盛事。东京奥运会期间,尽管之前历届承办国所举办的附属展览仅限于与体育相关的内容,日本却在承办之初就强烈要求将之扩展至日本古今艺术,尝试借助文化符号来象征国家;大阪万国博览会也成功地实现了观念的转换:世博会的重心放在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上,博览会本身被发展成为了“世界文化的盛大节日”(45),其会标图案和日本国家馆的造型设计也源自樱花。 在文化层面,回归传统自然也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68年《本居宣长全集》(筑摩书房)的出版以及川端康成因其“高超的叙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46)而于同年12月10日获诺贝尔文学奖,其创作和演讲将物哀作为日本文化的象征推向世界。不过,川端对《源氏物语》和物哀的痴爱绝不仅仅是对传统美的执着,事实上,在二战期间,以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横光利一为首的部分作家已开始尝试从古典文学作品中寻找心灵寄托和救赎,这种努力在战后更加明显。由于无法直面战争的残酷与战后的颓败,川端康成只能从日本传统美之中寻找救赎,而其作品的主导情调就是物哀美。例如《古都》所描绘的主人公千重子在古丹波壶中饲养铃虫(受中国“壶中别有天地”的启发和影响)这个情节,其目的就在于从古典作品中寻求日本民族“壶有洞天”式的救赎。(47)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身着和服而非燕尾服的川端发表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演讲,提到“在《源氏物语》之后延续几百年,日本的小说都是憧憬或悉心模仿这部名作的。和歌自不消说,甚至从工艺美术到造园艺术,无不深受《源氏物语》的影响,不断从它那里吸取美的精神食粮”(48)。此后,物哀作为日本精神的象征,作为日本代表性的文艺与美学理念,其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大,而川端口中的“美丽”也成为一个关键词,至今仍为日本政治家和民族主义者所继承与积极倡导。(49)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1960年代后,尽管物哀开始被视为国家的象征,但日本学者仍“忌惮借助文字媒体形式完整地公开战时《源氏物语》的境遇以及国文学在战时的真相,而免于战争伤害的战中派则自发地保持缄默”(50)。换言之,研究者们采用切割历史的方法,回避论及战争期间的物哀和《源氏物语》,而仅仅致力于将之建设为日本的国家象征,并以之来投射和观照过去。日本学者坚信,时至今日,物哀“依然是我们国民性的共同感情。天皇制的存续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物哀]保护着我们传统的共同性构造的再生产”(『物』:35-36);换言之,物哀仍然是日本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但它必须被置换为现代因素,才能焕发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极度膨胀导致日本人对自己的文化极度自负,但广场协议(1985)尤其是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经济低迷、政治动荡,国家认同严重受挫。在该背景下,1990年代中期日本新民族主义应运而生,“其主要方式是重新回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价值中,以建设‘强日本’为目标,挖掘民族历史中曾经有过的‘辉煌’和传统文化价值中的日本特性,以重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强日本’的国家目标寻找理论根据”(51)。例如,藤原正彦《国家的品格》(2005)将日本文明认定为世界上唯一的“情绪与形的文明”,认为只有日本国民发展到选择情绪而非逻辑、选择武士道精神而非民主主义时,才能重新恢复这一消失的国家品格。以“美丽”为关键词的论调喧嚣一时,要么着力强调日本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将之认定为可辐射世界的“软实力”,要么强调日本传统文化在构建国家认同方面的强大凝聚力。在《源氏物语》诞生一千年的2008年,日本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掀起重读《源氏物语》和重新认识日本传统文化的新高潮。这些举措中的关键词“美丽”在某种意义上均与川端的“美丽日本”异曲同工,都是在运用传统资源来恢复民众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企图“以此增强软实力,再次为世界人民垂范”(52)。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该民族文化的崛起和复兴为先导。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就必须正确认识历史。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且不容忽视或扭曲的,但实际生活中却存在着极易导致“实用主义”弊端产生的历史认识。20世纪初,克罗齐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受克罗齐影响的柯林伍德则认为“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不是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过去”(53)。他们主张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以当下的问题意识和眼光去观照过去。该认识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不能断章取义地理解上述史观,正确的选择必须以承认史实为前提。然而,当今日本社会仍然存在着缺乏正确历史观指导这一问题。正因如此,出于构建、确立和加强日本的国家认同这一目的,《源氏物语》和物哀才在各个时期被逐步经典化。由于借助“筛选出值得记忆的事件,再统合时间性把这些事件持续不断地讲述给下一代的言语行为”(54),《源氏物语》的经典化与物哀性质嬗变的动态过程被遮蔽,物哀被成功塑造为可涵盖日本、辐射世界的软实力,隐藏了其作为国家认同工具的功用。 ①详见小野村洋子『「あはれ」の構造につぃての試論』,東京:共立女子大学文學藝術研究所,1987年,第3頁。 ②百川敬人『内なる宣辰』,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258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野口武彦『源氏物語を江户から読む』,東京:講談社,1985年,第205頁。 ④自中古至中世,物哀几乎被视为无常观的同义语,而进入近世,物哀中的佛教影响已接近尾声。宣长的物哀论无疑受无常观的影响,但其内涵已主要是在世俗化的城市居民中所产生的基于厌世的悲哀感与相应的以颓废色彩为基调的复杂感情。 ⑤物哀之所以在日本影响深远,原因极其复杂。符合了日本民众的审美情趣和心性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日本人的“从上”、“从众”及“集体”文化心理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拙文仅从“经典形成”角度探讨该问题。 ⑥如本文行文所示,各研究者的用词不同,有同一性、共同性、自我确认、身份认同、国家认同等说法。 ⑦築島裕『日本語の世界5·仮名』,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年,第67頁。 ⑧小野村洋子『「あはれ」の構造につぃての試論』,第4頁。 ⑨详见王宗杰、孟庆枢《日本“女性日记文学”经典化试析》,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5卷第3期,第133页。 ⑩百川敬人『「物語」としての巽界』,東京:砂子屋書房,1990年,第104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1)转引自刘瑞芝《源氏物语与狂言绮语观的关联》,载《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88页。 (12)伊藤正羲『谣曲集』,東京:新潮社,1986年,第54頁。 (13)藤原為経『今鏡』,東京:誠文堂,1932年,第604頁。 (14)藤原為経『今鏡』,第604頁。 (15)伊藤正羲『谣曲集』,第59頁。 (16)小谷野敦「『源氏物語』批判史序說」,载『文学』2003年第4号(1),第190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简称「說」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7)详见王向远《和文汉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18)田中康二『本居宣辰の大東亞戰争』,東京:ぺりかん社,2009年,第43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9)详见王宗杰、孟庆枢《日本“女性日记文学”经典化试析》,第133-134页。 (20)神野志隆光「日本神話」の来歷」,收入ハルオ·ッヲネ、鈴木登美编『創造された古典』,東京:新曜社,1999年,第200頁。 (21)本居宣辰『本居宣辰全集』(第1卷),大野晋、大久保正编集校訂,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第141頁。 (22)详见王宗杰、孟庆枢《日本“女性日记文学”经典化试析》,第133页。 (23)例如,近代以来日本研究宣长的第一本专著村冈典嗣的《本居宣长》(1911)在出版后几乎没有销路,更谈不上有任何影响。在日语中,“宣长”是训读,发音为“NORINAGA”,而书店主人在向村冈询问宣长为何人时,用的却是音读“SENTYOU”(详见「辰谷川如是閑との対談『本居宣辰』」,载『文芸』第10卷第7号,1942年7月)。 (24)内村鑑三『後世への最大の遗物·デンマルク国の話』,東京:岩波書店,1946年,第41頁。 (25)ハルオ·ッヲネ「総說 創造された古典」,收入『創造された古典』,第22頁。 (26)详见山田有策「小說神髓の源氏物語觀」,载『国文学 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69年第1期,第5-55頁。 (27)北川高嗣·西垣通等编『情報学事典』,東京:弘文堂,2002年,“国語”条目。 (28)详见上田万年『国語のために』,東京:冨山房,1897年,第10-11頁。 (29)小森陽一『日本語の近代』,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第139頁。 (30)鈴木登美「ジャンル·ジ工ンター·文学史記述」,收入『創造された古典』,第85頁。 (31)芳賀矢一『国文学史十講』,東京:冨山房,1899年,第109頁。 (32)藤罔作太郎著、秋山虔他校注『国文学全史平安朝篇1』.東京:平凡社.1971年.第4-9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3)五十嵐力『新国文学史』,東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2年,第16頁。 (34)ハルオ·ッヲネ「総説 創造された古典」,第2頁。 (35)土居光知『土居光知著作集第五卷文学序説』,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122-123頁。 (36)由于武士道在当时成为了日本全体国民钦慕的对象,并逐渐成为“大和魂”与“日本精神”的象征,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臭名昭著的神风特工队即据该和歌将下属战斗队分别命名为敷岛、大和、朝日和山樱。这首和歌至今仍题写在靖国神社臭名远扬的“游就馆”第一展室中,而直至今日,仍有某些日本人将“国学”视为武士道之学。 (37)「上演期日を目前に『源氏物語』禁止さる」,载東京『日日新聞』1933年11月23日,朝刊11面。 (38)「『源氏物語』劇に受難上演を眼前に禁止」,载東京『朝日新聞』1933年1月23日,夕刊11面。 (39)详见橘純一「源氏物語は大不敬の書である」,收入秋山虔監修『批評集成·源氏物語』第五巻,東京:たまに書房,1995年,第186頁;谷崎潤一郎「あの頃のこと(山田孝雄追悼)」,收入『批評集成·源氏物語』第五卷,第316頁。 (40)小林正明「喪なわれた物語を求めて」,收入『批評集成·源氏物語』第五卷,第540-541頁。 (41)谷崎潤一郎「藤壺-『賢木』の巻補遗」,『批評集成·源氏物語』第五巻,第305頁。 (42)详见吉澤羲則「大東亞建設と国語国文学の在り方」,收入『批評集成·源氏物語』第五巻,第145-164頁。 (43)小林正明「喪な♂われた物語を求めて」,第537頁。 (44)「『源氏物語』映画化ヮヲンス語版に作製」,载『報知新聞』1935年9月8日,朝刊11面。 (45)大阪世博会总规划师丹下健三语。转引自瞿孜文《世博会如何成为设计产业的助推器》,载《设计》2012年第10期第205页。 (46)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nzes/literature/laureates/1968/index.html (47)详见孟庆枢《诗化的缺失体验》,载《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第81-87页。 (48)川端康成《受奖演说:我在美丽的日本》,收入川端康成《古都·雪国》,叶渭渠、唐月梅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0页。 (49)详见刘金举、孟庆枢《日本右翼重建国民认同的文化策略分析》,载《战略决策研究》2015年第1期,第94-104页。 (50)小林正明「喪なわれた物語を求めて」,第51頁。 (51)李寒梅《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基本形态及其成因》,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第91页。 (52)徐静波《〈国家的品格〉所叙述的日本文化的实象和虚象》,载《日本学刊》2006年第6期,第130页。 (53)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04页。 (54)野家启一语,转引自孟庆枢主编《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31页。标签:源氏物语论文; 日本源氏论文; 源氏论文; 日本和歌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天皇论文; 紫式部论文; 古事记论文; 国文学论文; 日本文学论文; 日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