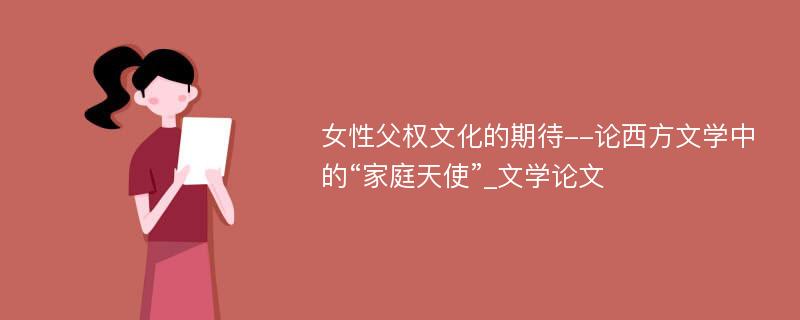
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试论西方文学中的“家庭天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父权论文,试论论文,期待论文,天使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西方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归纳起来具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均产生于欧洲社会进入父权制时代之后。这些女性文学类型,无论是“家庭天使”型、“红颜祸水”型、“悍妇”“女巫”型,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希翼、评价与控制,折射了男性心目中的女性价值尺度。
纵览西方文学史,我们会发现一连串栩栩如生而又异彩纷呈的女性人物形象。尽管她们各有不同的性格、遭际和命运,但基本上可归入三种不同的类型:一类以美貌、忠贞、温驯、富于献身精神等为特征,堪称“高尚淑女”或“家庭天使”;一类以美色加淫荡为主导特征,以至“倾城”、“倾国”,属于一种“红颜祸水”型;第三类则属“悍妇”或“女巫”型,主导性格特征为阴鸷、狂暴与工于心计。在大量文本中,这是一种对现存秩序极具破坏力的性格类型,如希腊悲剧《俄瑞斯忒亚》三部曲中的克吕泰墨斯忒拉王后,《美狄亚》中的美狄亚,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文学类型均是欧洲社会进入父权制时代之后的产物。在这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男性审美估价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体系中,所有的女性类型都表现了男人对女人的希冀或评价,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因此,上述三类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特征,均来自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对女人的控制,是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在文学中的折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红颜祸水”型的女性性别角色,表现了男性在女性性魅力面前一方面不能自己、另一方面又无限疑惧的矛盾心态。一旦好色与维护既定秩序之间发生矛盾,男人就轻易将责任推卸到女人身上,使之成为标准的诱惑者和祸水的形象。古今中外的大量文本均印证了这一事实。在中国传统史书中,夏商两朝的覆灭,不在统治者自身的意志薄弱和缺乏理性,而在于褒姒和妲己的诱惑;中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唐明皇,也正是因为在江山和美人之间作了果断的抉择,赐死杨玉环于马嵬坡,这才有了千古明君的圣名;《圣经》中,人类女性的始祖夏娃首先被解释为理性薄弱者,她在成了撒旦的牺牲品后,反过来又诱惑了人类男性的祖先亚当,终于使人类被逐出了极乐的伊甸园,并世世代代承受着“原罪”的苦难;《荷马史诗》描述了一场长达十年的特洛亚战争,其性质本来是氏族部落之间的劫掠,而史诗本身解释它的起因却是由于一个绝代佳人海伦的过错。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哈钦森出版公司1977年英文版《英文小说》第一卷的引言。其中,对萨克雷《名利场》中的女主人公利蓓加有这样的一段评价:“她不屈服于家庭女教师的奴隶地位,而蒙受耻辱。不择手段,有意识地运用男人为武器,再加上自身的天然财富——性,到处卖弄风情,在男人的世界里掀起狂风恶浪。”这些解释与评价,无不显示了男权对女性这一异己力量的恐惧、贬斥、戒备与疏离。关于“红颜祸水”型及“悍妇”型女性特质的形成及文化意义,笔者拟另文分析。本文主要就西方文学中一种主要的女性类型“家庭天使”的生成及发展,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无论是希腊神话中的珀涅罗珀、安德洛玛刻,莎士比亚笔下的苔丝德梦娜,理查逊笔下的帕美拉,还是莫泊桑笔下的约娜,托尔斯泰笔下的吉提与娜塔莎,这些生活于不同时代、产生于不同国别的女性,均有一些共同的性格内涵,这就是:她们都是西方文学中的“高尚淑女”,是满足了父权文化机制对女性期待的人物形象。她们共有的特质是:美貌、忠贞与温驯,堪称是一种具有圣洁意味的“家庭天使”。
那么,这一女性特质是如何被界定出来的呢?
人类自蒙昧时期进入私有制的历史,也就是母权制被父权制所取代的历史。无论是希腊神话中女神谱系向男神谱系的演变,还是埃斯库罗斯悲剧《俄瑞斯忒亚》三部曲中的人物命运,都无情地证实了这一“女性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恩格斯语)。希腊天神之父宙斯高踞于奥林匹斯山上,为众多妻妾所环绕,构建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庞大神族;俄瑞斯忒斯以克吕泰墨斯忒拉杀夫为由,杀害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却被雅典法庭宣布无罪。从此,父权成了社会的主宰力量,道德伦理的唯一立法者。而女性,由于被逐渐排挤出了社会生产领域,经济上政治上沦为附属的地位,只能以主流文化的异己力量而存在。“嫁人”,几乎成了唯一向女人开放的体面“职业”。而父权文化为了解除这一异己力量的威胁和反抗的潜在可能性,势必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来重塑一套女性观,以使女性磨去棱角,褪去锋芒,永远处于被玩赏、被使用的“第二性”(西蒙·德·波伏娃语)地位。
首先,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男性需要异性来满足其生理需要,需要一个美丽的形体来使他们在感官上感到愉悦,正无异于壁上的油画、架上的古玩、瓶中的鲜花和笼中的小鸟带给他们的快感,父权文化希冀于女人的第一个品质便是美貌。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规定性逐渐成为人类的常规文化心理,哺育和指导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女性自觉将美貌作为估价自身价值的首要标准,真正做到了“为悦己者容”(司马迁语)。然而,美色亦会使好色之徒迷惑心性,导致战争与祸乱。为了解除“红颜祸水”的威胁,父权文化又小心翼翼、同时不由分说地为女性确立了另一种品格:忠贞。只有美貌与忠贞的结合,才是女德完美的标志。而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忠贞日渐成为更加重要的品质。因为在一个从原始蒙昧社会脱胎而来而私有财产无比神圣的社会中,妇女承担着繁衍后代的神圣职责,妇女贞洁事关家产继承人的血统的纯洁性,可谓头等大事。所以,女性的贞洁被视作高于生命的道德体现就不足为怪了。中国封建伦常的卫道者朱熹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十八世纪英国知识界领袖约翰逊博士对贞洁的这一功利作用也直言不讳:“请设想,女人的贞洁对于社会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全世界的财产权都有赖它来保障。”同时,女性作为“第二性”还必须温柔、驯服,这样才能反衬自己的统治者的伟岸和无上权威。莎士比亚的喜剧《驯悍记》中虚构的御妻故事,成了这一父权文化心态的绝好例证。
故而,美貌、忠贞与温驯,是父权文化机制为了解除对自身的威胁而给异己群体强加的规定性。但父权文化又深知:强制的外力只有在转化为女性内心的自觉要求之后,才能确保自身的地位永世无虞。因此,父权文化不遗余力地运用文学这一大众化、形象化的工具来“寓教于乐”(贺拉斯语),为女性树立道德楷模。其实,拔高女德,只不过是将女性更加固定在自己的文化地位上而已。
产生于公元前九到八世纪的《荷马史诗》形象展现了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人由原始的氏族制向私有制脱胎换骨的历史。在这部展示男性对私有财产再分配的战争史诗中,也出现了两位重要的女性:安德洛玛刻和珀涅罗珀。前者是特洛亚王子赫克托耳之妻。在赫克托耳被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用枪挑死,特洛亚城池沦陷之后,安德洛玛刻誓死不为所侮,忠于丈夫和城邦。这一故事成为包括欧里庇得斯和拉辛在内的后代众多作家的悲剧题材,其内容均强调了女主人公的理性与贞节。后者在其夫伊大卡国王奥德修斯飘泊在外的二十年中,抗拒了众多的求婚者,终于保全了丈夫的名誉、家产和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位女性都成了“忠贞”这一抽象品德的符号,她们以自己的枯寂生活和情感折磨为代价,换来了在父权文化中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从此之后,缺乏自我意识、缺乏独立文化传统的女性,只能以父权文化机制中的女性价值观作为标尺,自觉地修整天性中与之不相吻合的部分,来重塑一个自己,以满足主流文化对“高尚淑女”或“家庭天使”的企盼。女性自我的声音潜入了历史地表,作为人的女性的基本生存欲望和权利被抹煞和剥夺了。贤妻良母,成了女性唯一值得梦寐以求的人生终极目标。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渐丰富与扩大化,加之各个时期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变迁,文学作品中“家庭天使”的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显现出父权制文化不同阶段的历史印痕。
安德洛玛刻、珀涅罗珀以及苔丝德梦娜等,属于初级阶段的“家庭天使”。她们身上最突出的品格特征便是美貌和对丈夫的忠诚。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她们的活动范围还局限于家庭内部,还必须操持家务,并从事小规模的农业、手工业或商业活动。进入18世纪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创业的史诗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在迅速改变着。而中产阶级妇女大约应属于生活变化最急骤的人们之列。妇女们突然被资本主义专业化生产所创造出来的空前的财富抛进了无所事事的闲适生活,而随着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迫切需要有相应的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女性规范,成了全社会注目的中心。新兴资产阶级在动用文学创造鲁滨逊式的“高尚英雄”的同时,也在呼唤与之相匹配的“高尚淑女”。事实上,18世纪的小说家们也大量描写了由于缺乏榜样的力量,女人们无所不为的典型个例。笛福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中,女主角有着当过12年娼妓、12年小偷,因罪流放美洲8年,并5次嫁人的奇特经历。哥尔德斯密斯的小说《威克菲牧师传》也涉及了英国社会流风日下的景况,描述了两个女儿如何不听牧师老爹的教诲,在家中大肆熬制美容霜露的故事。摩尔这样的女冒险家自然太不驯良,对建立资产阶级新秩序危害太大。那些涂脂抹粉、对贵族的浮华亦步亦趋的虚荣女人,和资产阶级勤俭致富的清教主义道德也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一时间,鼓吹女子贞洁、指导女性举止言行的“行为指南”汗牛充栋。据说,在英国,有一部《女人义务之探讨》的书连印了十七版,还有本《父亲给女儿的遗产》则不但在英国连续再版,且畅销大洋彼岸的美国。古希腊时代的“高尚淑女”形象被发扬光大,并附加了许多新的特征。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生活的日渐富足,资产阶级妇女的社交面日益扩大,沙龙里优雅的风度与睿智的谈吐成了追求风雅的妇女们一个必备的条件,同时,这也可以炫耀她们的所有者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家庭天使”们渐渐摆脱了繁重的家务活,走出闺阁,成了一个个活跃的“沙龙天使”。娴雅而知书识礼的女才子们,成了暴发户们最大的奢侈品。
进入19乃至到20世纪,文学作品中“家庭天使”的偶像并没有倒塌。尽管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等作品中,发出了争取女性自尊、维护女性人格的呐喊;尽管夏洛蒂·勃朗特以一个女性作家的自觉,真正从女性的体验与感受出发,塑造出一个身躯矮小、其貌不扬,但自重自强、决不仰人鼻息的新女性简·爱的形象,表现了女性视角对传统的“家庭天使”角色的决绝态度;尽管本世纪以来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方兴未艾,法国的西蒙·德·波伏娃、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美国的伊莱恩·肖瓦尔特、吉尔伯特和古芭等女权主义作家和批评家为重建文学史、为发掘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女作家的声音,作了大量筚路蓝缕的工作,然而,人类几千年来所遵循的父权文化机制并未消失,以男权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评估更是根深蒂固地沉积于人们(包括女性在内)的头脑之中。而在这样的前提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更不可能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创造男女各自完美的人格。奥斯丁和勃朗特笔下的人物关系及命运尚体现出男权文化影响的痕迹,这一点自不待言,即便是激进的女权主义批评,本身也存在着相当的偏颇、局限与狭隘之处。既然现实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让人性获得充分自由的程度,既然生活中尚存在改变女性“第二性”生存状态的呼声,文学,作为生活的反映,那些有关圣洁的“家庭天使”的神话还会存在并继续创造下去。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只有在彻底解构了男权社会对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要求和规范之后,才有可能建立比较真实、自然、不受外界强力支配的女性特质。至于这一女性特质将是什么样子,恐怕目前西方最先进的女权主义者也难下结论,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新的女性性别特质,将不再会是作为男权中心文化附庸的“家庭天使”,但也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剥离了女性生理与心理特征的“伪男性”或中性人格,更不会是被卫道者们视若洪水猛兽的红颜祸水。
注释:
〔1〕阿莫尔德、凯特尔《〈英文小说〉第一卷引言》,1977 年英文版,P.153,哈钦森出版公司。
〔2〕转引自黄梅《女人和小说》P.6—P.7 ,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