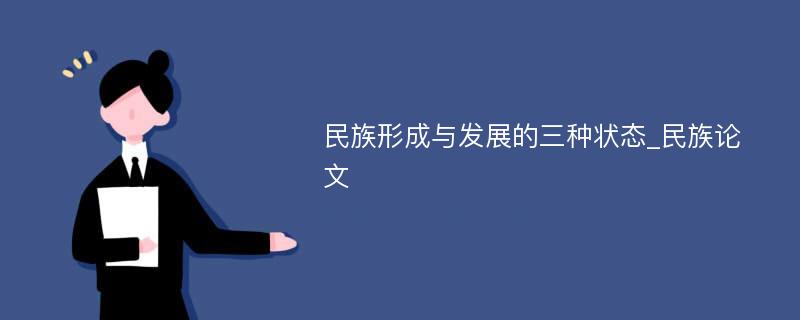
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状态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民族过程中,民族的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可以标示出民族的不同社会性质,由此划分出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或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民族的族体形态过程可以标示出民族的表征演进,从而出现血缘民族和地缘民族、原生民族和次生民族、大民族和小民族。然而,当我们抹去这些性质差别,民族过程所呈现的还有形成和发展状态方面的不同。斯大林就曾把民族的形成分成低、中、高三个阶段。他说:“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不相同,其中如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处于民族形成的高级阶段,彻岑和卡巴尔达处于民族形成的低级阶段,而柯尔克兹则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注:《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20页。)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在民族形成以后,就其内部的凝聚来说,还有一个从初型到定型的发展过程,“从民族的初型到定型也有一个发育过程,即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民族的发育”。(注:徐杰舜:《论民族发育问题》,载《学术论坛》,1991年第4期。)研究证明,作出这些划分是必要的,因为它不但对具体的民族发展有一个可供测度的理论标志,而且对民族过程的宏观进程也将有一个可供测度的客观依据。
根据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不同情况,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潜民族”、“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三种状态。
一、“潜民族”
严格地说,“潜民族”不是民族。但我们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从它开始,正如类人猿不是人,而我们研究人类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从它讲起,甚至要从更早的猿类讲起一样。
什么是“潜民族”?顾名思义,即是潜在的民族。斯大林在谈到资本主义民族形成时说:“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些要素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使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种潜在因素。”(注:《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89页。)这段话并没有直接提出“潜民族”,但它的启示意义是:民族因素是由萌芽状态和潜在状态逐渐形成的,在它们完全凸现、构成完整的民族实体之前,总有一个萌生、孕育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就是“潜民族”。
关于“潜民族”,也有学者以别的提法谈到。杨堃先生在谈到“民族”定义时,在他所说的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之外,还提到“有些正在形成中的过渡民族”。(注:杨堃:《民族学调查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4页。)施正一先生主编的《广义民族学》一书也讲到:“从民族自然属性的角度,也就是民族特征发展成熟的程度,可以把民族划分为形成中的民族或形成初期的民族、发展中的民族。”(注: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58页。)他们所说的“正在形成中的过渡民族”和“形成中的民族”即指“潜民族”。
除“原生民族”之外,新民族的形成不外三种途径:(1)从民族分化而来,如氏族、部落的分化,部分民族成员的迁徙等,都能够形成新民族;(2)由民族聚合而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体或族体的部分成员聚为一体,形成新民族;(3)由其他人们共同体转化而来,如最早的民族即由原始群转化而来,而历史上和当代的宗教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转化为民族的也不乏其例。这三种情况中,第一种和“潜民族”无关。第三种情况中由于原始群和宗教集团等非民族共同体是民族生成的母体,具有形成新族体的潜在可能,因此它们即是“潜民族”。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是相通的,因为形成新民族的族体聚合本身即在一定的地域和社会背景中发生,由聚合形成的民族也是由地域共同体等非民族共同体转化而来的。因此,提出“潜民族”的根据就在于,大多数民族是由非民族共同体转化而来的,它们在形成之前总是寄附于非民族共同体。这些民族共同体虽然还不是民族,但却具有滋生民族因素的土壤,具有向民族转化的趋势。
能够作为“潜民族”的常见的人们共同体有以下几种:
1.地域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可由自然环境所框定,也可由政治行为所裁割。居住于不同地区的人们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以不同的原因共聚一地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必然会使语言和生活方式等趋向一致,从而形成共同的民族特征。
2.血缘共同体。天然携带或能够滋生民族因素的血缘共同体有两种:一种为原生的氏族、部落,这种共同体本身就是原始民族,是一种社会组织和民族共同体的统一,不存在向民族转化的问题;另一种是以一个或一个以上血缘集团(家族、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等)为核心,吸附了周围若干来源不同的族群所组成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核心血缘集团处于支配、统治地位,而其他族群则因各种原因而依附或屈从于这个核心集团,并有与之凝为一体的趋势。这种共同体虽然不是民族,但却有着形成民族的极大内聚性。在我国北方草原民族的发展史上,匈奴、鲜卑、突厥、吐谷浑、党项、回纥等最初都是以一个较强部落为核心的部落集团,只是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部落集团才逐渐凝聚成以核心部落名称为族称的民族共同体。
3.种族共同体。种族共同体是血缘共同体的扩展。同一种族的人们因具有共同的外貌特征而容易发生认同,形成共同体。种族共同体不同于民族,但在特定条件下却很容易生成民族特征,实现和民族共同体的重合。历史和现实世界中有许多民族就是和种族共同体重叠的,如当代美洲的一些国家,其种族界限往往也即民族界限。
4.宗教共同体。宗教不是民族特征,但是原始宗教、民族宗教、世界宗教等各种宗教形式始终都是民族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极易结成以宗教为纽带的共同体;许多民族也都是以宗教为主要联合形式,实现着民族和宗教共同体的同一。于是,这种民族形成时,也明显有一个从宗教共同体的转化问题。
5.政治共同体。由于前国家社会的政治共同体与各类民族共同体重叠,政治单位也即民族单位,所以能够成为“潜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只存在于国家社会中;又由于单一民族国家也与民族共同体重合,所以只有多民族国家才具有“潜民族”的特质。相对于其他共同体,国家具有更强的培植民族因素的潜力,它对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规约的强制性和一体性,使得以国家为范围的民族因素的滋生具有更大的可能。
二、“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
最早对民族作出“自在”和“自觉”划分的是费孝通教授。他在谈到中华民族的形成时讲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注: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费先生在此仅就中华民族的形成谈到了自在和自觉,但实际上这也是民族形成和存在的两种普遍状态。
所谓“自在民族”即作为族体已经存在、但未被自身所认知的民族;而“自觉民族”即作为族体已经存在、它本身也能感悟到自己存在的民族。一般情况下,民族总是先有自身的存在,然后才会被自身的成员所认知。先有存在,后有意识,这个认识论的规律在民族领域也是适用的。在现实世界中,具备民族特征、但未被自身所认知的人们共同体,以及作为一个族体已经形成、也能得到自身认知的人们共同体,都是客观存在的。“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都是“民族”。但奇怪的是人们总是承认后者,而把前者摈除在“民族”之外。英文ethnographical communities的意思就是具有一定的民族特征、但没有自我意识的共同体。在国内通常把它译作“民俗共同体”,因其没有自我意识而不被算作“民族”,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一种存在决不能由是否被自身所认知来决定。我国在进行民族识别以前,很多少数民族和一些汉族成员根本说不清自己的族属,他们的族称十分混乱。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民族认同是不清晰的,但不能说他们所属的不是“民族”。一个具有民族要素的共同体不管是否具有自我意识,都是作为一种民族的实体而客观存在的。
“自在民族”与“自觉民族”的区别在于族体能否被自身所认知,这里的自我认知或自我意识即是民族认同问题。民族认同在“自在民族”那里不一定存在,但却是“自觉民族”的必备特征。因此,民族认同的发生便成为民族自觉的标志。
在研究民族认同的西方学者中,以希尔斯(Shils)和格尔兹(Geertz)为代表的“原生论”(primordialism)者认为,民族认同含有人类最原始、最初生的感情在内,它可以满足个人最基本的感情依托的需求。这无疑是有价值的论点。但他们又认为,一个人的民族认同是先于他的意识而存在的,民族依附的感情是建立在人的生物和基因构造之中的,是根据血统在母体之内就已经开始滋长的。(注:参见A.D.Smith,Theor-ies of Nationalism,New York,1983,前言。)这显然流于荒谬。其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民族认同无论对于一个民族群体,还是对于一个人,都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方可产生的。认同,包括民族认同,属于社会认知的内容。社会认知是认知主体在与客体的交往过程中观察、了解并形成判断的一种心理活动。人们都是在一定的民族群体内生活,始终受到本族体文化的熏染,形成受本族体制约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念。当人们未与外族社会直接或间接接触时,不可能形成关于所在族体与外族不同的判断,也不会有归属哪一族和随之产生的感情依附方面的感受。只有与外族接触,不同于本民族的各种印象才会形成,对本族体的归属感和感情依附也才会产生。因此,民族之间的交往是民族认同发生的前提。民族认同只能发生于民族交往、形成对比之际。这一点,国内外学者也是普遍认可的。如S·科奈尔最近在其《民族过程的内容和环境》一文中认为,和所有的团体认同一样,民族认同的核心是对比。那种“我们的”的感觉总是不同于“他们的”。族体边界(boundary)的建设是对比的勾画。而这种观点早在60年代末就已为著名学者F·巴思所充分论述。(注:参见Stephen Cornell,The Variable Ties That Bind:Content and Circumstance in Ethnic Process,Ethnic and RacialStudies,Volume 19,Number 2,April 1996。)费孝通教授用社会学的术语in-group或we-group说明“人己之别”。他说,民族认同的发生就是“把人己之别用来区别不同的群体,而且用不同的感情和态度来对待这两种群体”。(注: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可见,学者们已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交往和对比在民族认同发生中的决定作用。
民族认同的有无决定了“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的区别。但一般来说,民族认同的发生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不同步。
1.从民族的最初产生来看,一般总是民族的存在先于民族认同的发生。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表明,民族是人类相对隔绝的产物。没有各个不同地域内人群相对隔绝的文化创造,也就没有人类语言、习俗、观念等方面的不同,即没有民族。隔绝是民族产生的土壤,但也是民族认同发生的鸿沟,民族认同不可能在隔绝条件下完成。
2.从民族认同发生的过程来看,总是一部分民族成员最先发生认同,然后推及全族。于是,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总有一部分民族成员因不具有民族认同而使民族形成与民族认同的发生不能同步。根据族体大小与认同扩展速率成反比的规律,族体越大,完成认同的速度越慢,认同滞后于民族形成的现象也就越明显。
3.在大量的次生民族中存在着外加的民族认同先于民族形成的现象。所谓外加型民族认同,即指某一社会群体先被外界视为一族,又被自己认可而发生的认同。其民族的形成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发端的。类似外加型认同的“潜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跨越现象,也是先有认同,后有民族的形成。
因此,不论从民族产生的一般规律来看,还是从民族认同的具体过程来看,民族认同并不是所有民族的必要因素,而只能是“自觉民族”的特征。“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是以有无民族认同来界定的,民族认同是区分两种民族状态的界标。
三、“自觉民族”形成的顺序型及跨越型
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三种状态,既可同时并存于不同的社会之中,又可构成一个整体民族过程中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具体民族而言,一个族体是否进入“自觉”,有时似乎与本身的发展程度并无明显关联。如一个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由于不同的原因而经常与外族交往和接触,它可能已是一个自觉的民族;而一个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因环境闭塞,也可能迟迟未能发生认同,而只是一个自在的民族。此外,由外加型认同发端所形成的民族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自觉的状态,但这并不是它的发展程度的表现。然而,从总的民族过程来看,“自在”和“自觉”的确是民族发展的两个阶段。因为与“自在”对应的总是原生民族早期的隔绝和次生民族的最初形成;而与“自觉”对应的则是原生民族封闭的解除和次生民族较高的发展。此外,个别的、局部的“自觉”民族的存在和世界民族过程普遍“自觉”阶段的到来,这是两个概念,后者须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方可出现。
在整个民族过程中,“自觉民族”是民族发展的成熟阶段。但以民族认同为标志进入自觉阶段则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潜民族”到“自在民族”,经民族认同而进入自觉阶段,这是一般的发展进程,可称之为“自觉民族”形成的顺序型;另一种是“潜民族”未经自在阶段便先行发生民族认同,进入自觉阶段,这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发展过程,可称之为“自觉民族”形成的跨越型。顺序型自觉阶段的进入是容易理解的:“潜民族”共同体经较长时间的磨合、酿就,逐渐滋生出共同的民族特征,达到“自在”。然后经与外族交往产生民族认同,达到“自觉”。然而从“潜民族”直接过渡到“自觉民族”的跨越型,则是一个需多作说明的特殊过程。
从民族的一般形式来看,应是民族的存在先于民族认同的发生。但我们从上述民族认同的发生类型来看,除了自然发生型以外,外加发生型和转化型都存在着民族认同先于民族存在的现象。民族的认同先于民族的存在亦即非民族共同体对“民族”名义的假借,这正是“潜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跨越。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可找到这种假借现象。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始终不渝地强调北美各殖民地的团结,他用以团结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假借“民族”。他强烈要求北美人民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形成自己的民族性格。独立战争一结束,他就指出:“我们现在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们不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就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如果我们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那么,就让我们在有着全体利益的一切问题中,以一个民族特性做后盾的整个民族来行动。”(注:转引自梁守德:《民族解放运动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5页。)众所周知,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民从各自的母国带来的各自的民族痕迹还很清晰。尽管因经济的发展彼此有了一定的联系,但远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特征,还不能说是一个“民族”,而只能说是一个“潜民族”。实际上,近、现代大多数民族解放运动也都是被压迫人民在“民族”的旗帜下团结一致、争取政治独立的运动。这里的“民族”也都是某一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的统称,并非一个民族,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假借的。阮西湖先生曾在对澳大利亚的民族状况作了考察之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著民族开始觉醒,他们称自己为黑色澳大利亚人。有些澳大利亚学者称之为泛土著民族意识。正是由于民族意识的觉醒,土著居民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从政治需要,他们愿意是一个民族,从民族感情来讲,他们也认为所有土著为一个民族,甚至他们还制定了民族旗帜”。(注:阮西湖:《澳大利亚考察报告》,载《民族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而实际上,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讲200-260种不同语言,500-600种方言,还远不能说形成了民族特征上的一致。新加坡学者D·布朗在分析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现象时指出,由于经济发展上的明显差异,使得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周边少数民族加深了与国家的矛盾,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所谓“泛民族意识”逐渐形成。如菲律宾的摩洛人过去分成许多不同的语言集团和地方上的宗教集团,但自60年代以来,“他们的民族共同体观念已经改变,将所有的居民只分成两类:一类是他们自己即穆斯林;另一类则是菲律宾人”。在缅甸
的克伦人当中,“从地方主义向泛民族意识的转变开始得更早些。19世纪初期,不同语言与居住地的克伦人还只是分散反对缅人的压迫。但到本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他们在宪法谈判中被出卖,便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出卖和被歧视的少数民族,从而在泛民族意识的基础上进行反抗”。(注:〔新加〕D·布朗著、马宁摘译:《从周边共同体到民族国家——东南亚的民族分裂主义》,载《民族译丛》,1990年第4期。)显然,出于抗御外部压力的需要,东南亚国家的这些少数民族也对“民族”进行着假借,从而开始了从“潜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跨越。当然,各地情况有所不同,像菲律宾摩洛人的例子无疑是一个宗教共同体对“民族”的假借;而缅甸克伦人的例子,又似乎是一个地域共同体对“民族”的假借。
对“民族”的假借是近代以来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普遍现象。A·D·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为它选择的群体(group)赢得和维持一种“民族资格”。民族主义者在其心理上已经确信他们的群体在道德和观念上是能够自我满足的,这已经在心理上构成了一个“民族”。然而,为获得这种资格,他们还必须向世人提出一些能够令人信服的社会因素,如共同的习俗、语言、宗教,还有天然的边界或独立的历史等。由于民族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为的确存在的民族所主导或为假借的民族所主导的两种现象,所以,A·D·史密斯将前者称作“有民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with nation或ethnic nationalism);而将后者称作“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without nation)。(注:参见A.D.Smith,Theories of Nationalism,New York,1983,pp.215-216。)
“潜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跨越,说明民族认同并不一定从“民族”的实际存在开始,而可能以假借的形式寄附在一种非民族共同体之上。各种“潜民族”在对立的群体和不利的外部环境面前,很容易因利益的一致或其他共同点,在“民族”的名义下自我认同、自我感悟,从而使非民族共同体呈现出“民族”的色彩,最终造成向真正“民族”的凝聚和过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潜民族”的假借认同?根本原因在于,民族比其他人们共同体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它有植根于自然的渊源,人们可以从它身上观照自身的血统、归属、价值和尊严,因而它往往能够超越政治、经济和阶级因素,成为最具凝聚力、最能唤起人们认同的一种共同体。“潜民族”能够向“自觉民族”跨越,完全是由民族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所决定的。
需要说明的是,“潜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跨越毕竟是一种异常现象。所谓跨越,实质上是指民族认同先于民族其他特征的出现。但“自觉民族”的形成仅有这种认同的假借是不够的,它最终还需要“自在民族”阶段的补充。共同的语言、习俗和心理素质等民族要素,最终还要填充因跨越而形成的民族过程的空洞。没有这种填充,没有完备的民族要素,“潜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跨越不能算已完成,“自觉民族”的形成也是没有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