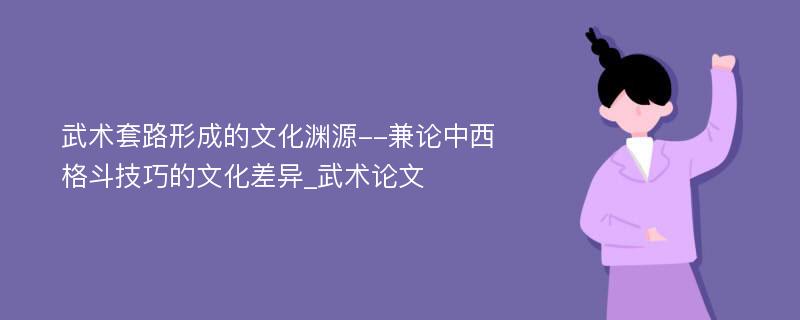
论武术套路形成的文化渊源——兼谈中西方格斗技能的文化学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中西方论文,套路论文,渊源论文,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01)03-0012-04
中国武术在理论上,运动形式和内容、技术、结构等都有别于西方的格斗技术,其显著标志是融技击、艺术表演、健身娱乐为一体,并以套路演练为传袭相承,因而,武术套路中的动静结合、神形兼备、刚柔相济以及强调意、气、形协调一致的运动形式,集中体现了中国武术博大精深的内涵和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和人格修养。假如把中国武术置于各国格斗技能的万花丛中,中国人能很快找到和辩认出这朵“奇葩”。究其原因,套路作为武术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
对武术的研究,单纯从技击的内涵实质去寻究武术发展轨迹很难把握武术的实质。从武术套路形成的文化渊源,探讨中国武术有别于西方格斗技能的机制所在,追究中西方文化意义的差异,我们才能对中国武术有一个较清晰、较全面的认识。
1 “礼乐文化”是原始格斗向武术“嬗变”的契因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几乎所有文化形态的发育初期都是依附或借助已经相对成熟和现成的文化形态。这种被借助的文化形态必定要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它具有全民族性、广泛性(有助于形成社会化)。二是它具有一套系统的规则、仪式和措施(有助于制度化、秩序化)。三是它能够提供衡量和判断标准以及为延续这类活动提供可靠的保证和活动的场所,帮助走向客观化(即所谓内在化的过程)。四是这种文化形态具有极强烈的象征性、意义性、神圣性,它有助于其摆脱原始的实用功能,进入意义世界。五是文化的发展处于多元化向一元化,内在冲突向一体化过渡的时期,多元化为其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一元化为其提供共同的标准。古希腊竞技发展,正是借助于当时相对成熟和多元的宗教文化完善了“奥林匹克竞技”,借机形成全民族性和社会化完成了从军事战争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意义和自身具有价值的文化形态。
而在中国古代奴隶制时期,尽管宗教发育也相对成熟,但与古希腊的宗教比较而言,一神和多神的矛盾并不明显。万能神(一神)开始形成,统治者把天体崇拜和祖先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居住在天上的最高神——帝,统治者被当作上帝的代表,如最后两代商王称为:“帝王”、“帝辛”。殷商甲骨文中有不少类似下列内容的卜辞,如“帝其令风”、“于帝史凤”、“帝其令雷”等。因而,此时期宗教已处于内在的安息,没能提供竞技体育借助的机会。
西周时期,统治者除了继续用宗教迷信的严刑峻法统治之外,还通过制定一套讲究等级名分的“礼制”来实行“德政”和“礼治”。并贯穿于当时政府、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尔后,在孔子思想影响下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的始祖,一般思想史家称之为“礼乐文化”。其内核中的象征性、规则性和仪式性以及“早熟”的文化内涵,具备了上述“被借助的文化形态”的特征,提供了原始格斗技能从军事技艺中的分离,从而走向具有社会意义的武术的契机。
“礼乐文化”是孔子以“仁”为桥梁,一方面把外在的、社会的、对人起着规范作用的政治和道德“礼”化成了人们内在的、现实的心理需求。如“人而不仁,如礼何”;另一方面又给倾诉个体情感欲求为满足感官愉快的“乐”注入了政治、道德的内容,如“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种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个体心理欲求和社会伦理规范的交融统一,是“礼”对“乐”的渗透的制约和“乐”对“礼”的情感性的融化。典型的例证如“射”变成了“以射观德”的“礼射”;“礼、乐”成为教育的首要内容;甚至连休闲娱乐的“投壶”也成为士大夫“礼仪”的活动之一等。从哲学的意义讲,这是中华民族在智慧上表现出的“主客同构”、“天人合一”的传统精神,这种智慧表现在思维模式和智力结构上,就是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把握、领悟和体验。中国武术表现出的虚与实、动与静、阴与阳、形与神等的统一,并在套路演练和传习的过程中获得个人主体心理上的平衡的体验和情与理的和谐的感悟,正是基于这一文化特征。
与之相反,西方《圣经》中上帝造人背叛被逐出乐国而与命运相斗争,一般思想史家称这种文化为“罪感文化”,即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为赎罪而奋勇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以获得神誉,再回到上帝怀抱的精神联系,是以灵与肉的分裂,精神的紧张痛苦从而获得的意念超升、心理洗涤,与上帝同在迷狂的喜悦。“主客体的分离”就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环节和核心,这种思维模式引导希腊人对竞技的狂热,坚定竞技是与神同乐的信念,使希腊人不断追求强壮的身体,发达的肌肉,技艺、技巧的完美,速度和力量的结合。
因此,人类“共性”的原始竞技在两种不同的背景下,即对主客体关系的不同理解和差异,以及不同的文化形态的“借助”,必然走向不同的归宿。
2 民族文化特质的介入,奠定了武术技击理论的思想基础
在奴隶制时期的中国和古希腊的竞技体育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体育,尤其是格斗技击技能,只是军事和战争的一个部分或环节,它自身尚无任何价值而言,它的价值在于战争,战争是其直接动力。但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东西,其发展或获得独立,一方面必须完成从军事战争中独立出来的任务;另一方面必须以文化为内核,武功作为外形,才能走向自身运行的轨迹。
西周时期的“角力”是“讲武之礼”的一项主要内容,在以车战为主的战争形式下,对力量的要求超过对技击技术的要求。无论是广义(制服对方)或者是狭义(角力摔跤)都讲究堂堂正正的“执技论力”的比试。《左传》中记有鲁公子季友与昌驽角力,鲁公子以“奇巧”胜,被时人指责为“弃师之道”。由此可见,与堂堂正正之较力相违背的其它形式还不具备社会基础。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形式由步战(步骑)代表了车战。短兵相接时格斗技巧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军事训练的内容,始有“巧斗力者”,始于阳,常率于阴之“手搏之道”技击术的产生。在求“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的社会条件下,“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魏书·刑法志》)尚武之风的盛行。尤其是从“士”分化出来的以挟武技为生的“武士”阶层。“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庄子·说剑篇》)。更使剑术的发展到了职业化程度,并极惨烈和残酷。
但是,此时期以剑术为代表的技击术,从技术结构上看,还找不到与西方同时期角斗技击术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其形式与后来武术套路的演练尚有较大的差距。其“惨烈残酷”与斯巴达的“角斗士”没有两样。从希腊对竞技英雄的雕像的题词上。如:“尼米亚、德尔菲、奥林匹亚五次给我戴上桂冠。我在四方获得成功,不是靠蛮力,而是靠机灵”。(颜绍泸《体育运动全史》)这里的“机灵”与《汉书·艺文志》云:“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几乎是同一语义。因此,可以说此时期中国和希腊的技击在结构上是一致的,是以取胜为目的,仅仅表现了技击注重个人技能的成熟,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个性特征。这种特征与西方同时期格斗技击技能仍然属于“共性”,反映的是它与军事技艺的分离,完成了浅层次的“升华”。
但从另一个方面,即技击理论上看,中国的技击却明显地打下了民族的烙印。注入了民族文化的特质,逐渐成为其思想基础,仅从先秦时期史籍可见一斑。如《汉书·艺文志剑道三十八篇》中记载的“越女论剑”:“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俱虎,布形候气,与神具往……”。又如《庄子·说剑》“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这种强调先静后动,静中求动,动静结合的道理,是用虚实,阴阳,开合,形神统一等说明击剑的进退攻守的原则和技击策略与方法,这里的“动静”,“虚实”,“阴阳”,“形神”是中国文化的哲学范畴,用中国哲学将技击的生动体现和具体化来源于中国古人对“农业文明”中“天、人、地”的变化关系的认识。中国哲学以乾坤,阴阳,动静,五行等作对应解释,以此来把握宇宙万物生存变化的规律。因而作为人必须与“天、地”(即自然)保持协调,维系生存,“天人合一”便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格斗技能技击的发展,必然纳入民族文化的轨迹,并以此作为理论的基本活动框架和语言工具。武术的技击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具体化和人格化生命化的修炼活动,涵盖了中华民族对宇宙万物的认识。
西方体育总的来说是一种物理体育,来源“海洋文明”以及科技,商品经济的发达,在奥林匹克文化及宗教思想的影响下,表现出自我张扬和与自然的抗争,在形式上表现出以力度,速度为标志的特殊质态,基本理论术语更多地显现物理学特征(生物力学)。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和值得思考的实验。用计算机将武术的剑术和西方的剑术(或其它)“处理”成“棍图”都可以显示整个技术动作的运动环节和人体重心的全部变化轨迹,但是中国武术却无法说明另一方面,即动静、形神、意气、刚柔、节奏等精神内涵实质。
虽然奴隶时期的中国和古希腊的格斗技能都完成了从军事战争中独立出来的任务,在技击结构和运动形式上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但在技击理论上中国民族文化特质的介入,却是中西方格斗技能形成文化学差异的渊源,决定了两者在运动形式上、内容上等分道扬镳。
3 中国武术依附、融摄的发展是武术套路形成的特殊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格斗技能的发展,已表明开始具备了文化学意义的武术,即已初具独立形态,已有武术的主体(侠士和民间习武者)以及武术技击浅层次理论概括。值得注意的是武术中早期体现个性,追求竞争与冒险的精神内涵本应和西方一样沿着自身逻辑道路发展,但是中国历史的变革和特定的社会背景,武术没有继续完成成为独立的文化形态所需的社会化,客观化,内在化进程。这一特定历史背景就是秦汉以后中国政治文化的大一统,以及森严的封建等级观,使初具独立形态的武术被迫走上了一条迂回发展的道路。
与先秦时期借助其它文化形态发展自身不同的是,这一迂回发展是一依附的过程。当时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在“废力尚德”“去武行文”的社会思潮下,衰落下去,如先秦的武士秦汉以后走入绿林贩夫为伍的道路,二是依附统治者认可的文化形态,保留其特质外在形式上却走向审美和伦理的道路。这一依附又是融摄的过程,同时又是一涵化过程,恰好反映了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整合性(笔者已撰文论及此,不再赘述)。
秦汉时期,“角抵百戏”的兴盛,为武术的生存提供了一个寄居处,在互为涵化的过程中,武术的发展在形式上、内容上、结构上寻求到新的契机,最终奠定了以套路演练为核心的发展方向,获得了质的“升华”。
“角抵”源于西周时期单纯的较劲“角力”,战国以后与“戏乐”结合,演变为角抵戏,唐人苏鹗认为:“人通以角胜之戏为角焉,或独以两人竞力为角抵,非也”(苏鹗《苏氏演义》卷下),又《说文》“戏,三军之偏也,一日兵也”,从当时流行的“蚩尤戏”可证实,它是融技击、音乐、舞蹈、娱乐等初步艺术化的综合形式。汉朝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进入了繁荣鼎盛,各种技艺的互相融合,“角抵”的含义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角技为义,兼诸技而有之”,是运用“杂技”(包括武技,舞蹈,音乐等)形式进行比较,即反映社会现实和生活中的一切冲突,与今之戏剧必然反映社会矛盾及斗争是契合的,在内容上增添了“四夷之乐”“其云雨雷电”的场景,“倏忽变化”的幻术等,而作为原始意义的“角抵”,演变为场景中的武术表演并成为主体,从出土文物和史料的相互佐证大致有3种情况。
其一,按规定的情节结构对打,最早的例证为汉代角抵戏《东海黄公》,汉画石中有大表现“对打”“空手夺棍”等场面,这里的技击,已丧失了实用性,而是带有指征性或象征性。
其二,单纯的武术表演。最典型的是南阳汉画像石中的一幅“击刺图”。画幅中一人侧身弓步,挺长挺向前猛刺,左一人侧身扬臂亮掌,作退弓步,欲夺对方长挺,画右端刻一人手持匕首,作刺杀状,画幅空间有云气状的场景布置,证实是在台上表演,从三人攻防击刺动作的身法,手法无一不同于今天武术中的多人对练形式,这种表演,具有强烈的观赏性,是武术走向审美和人格性的雏型。
其三,“象人斗兽”,《汉书·成帝本纪》载成帝时,用此节目招待胡客,“象人斗兽”类似西班牙斗牛,表演者必须具备娴熟的擒拿格斗技击术。在汉画像中就有大量的这种场面的生动形象。
从传播学的角度讲,一种思维和文化形态具有全民族性、广泛性,能为统治者和人民群众认同,才能有助于形成社会化的局面。武术技击依附在“角抵百戏”上,融摄百戏的表演形式和审美特点,迅速被官方和人民群众认同及社会化,从另一意义讲,当武术这种融技击、表演、娱乐为一体的文化现象大量反复地出现,人们就会对此活动及现象进行反思,形成有关这类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这就是内在化的过程。由于百戏表演需要预习编排,演员的动作需要编排;由于观赏性的要求,这就是内在化的过程。由于百红表演需要预习编排,演员的动作需要编排,由于观赏性的要求,指征化了的技击动作有惊无险,需要“美”化;由于需要反复演练和传承,技击动作需用固定的格式加以巩固等。因此,这种“有意识,有组织编排的‘运动形式’用于与人斗,与兽斗的活动,开始具备了可称之武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即武术套路的定型。标志着中国武术沿着自身的文化轨迹发展演变,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理论与技击体系,在运动形式上,内容上,审美情趣上等有别于西方的格斗技能。
可以这样说,“礼乐文化”是中国武术独立发展的母体,而传统哲学和角抵百戏则是其独立出来的助产婆,也是中国武术套路走向独立历程提供社会化、客观化、内在化支持的文化渊源。
4 结束语
中西方格斗技能所存在的文化学差异,决定了两者完全不同的走向,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下和世界性科技时代,中国武术又将进行一次什么样的融摄和涵化?作为一种人体文化和精神表现,以及支撑它的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又将如何走向新的时代?中国武术多元化结构如何适应世界体育竞技一体化,使其更具现代性?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深层次问题。从中西方格斗技能的文化渊源和形成差异的分析,也许使我们能得到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