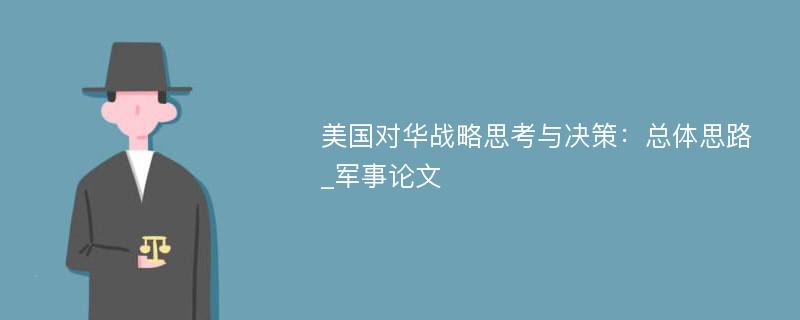
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一般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战略论文,一般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世纪以“大国政治运作”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中,中美两个大国间的“恩恩怨怨”、“若即若离”已经凸显成为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所谓“大国关系”,其核心部分,只能是军事或安全战略关系,中美之间也不能例外。制约与主导中美交往发展的“必要因素”却是两国间的战略态势与定位——无论是长达20余年的公开军事对抗,还是维持了10来年的“大三角”架构;无论是“冷战”结束初期的再度“遏制”,还是20世纪末喧闹一时的“战略伙伴关系”,均无一例外。
对美国而言,中国是敌是友?还是“非敌非友”?华盛顿对北京是“遏制”还是“接触”甚或“又遏制又接触”?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依本人之见,只能通过对美国军事、安全战略决策机制的研究中得出。
从理论框架上,以“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些基本假设,作为本文研究做目标界定、范围预设、“变量”控制。一般说来,借用约翰·路易斯·盖迪斯的关于“战略考虑”的注释,即,美国任何一个“总统决策机制”,对其国防政策、军事“安排”、乃至外交策略制定与实施,都或多或少地按照其内在的一系列“战略密码”所行事(注:参见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遏制的战略(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第viii-ix页。)。而追求“国家安全”目标则是编制这些“战略密码”的最基本框架。
根据对国家安全的传统界定,一国的安全实现,主要指其有效地保卫其国土不受“外部入侵”。据此,国家安全也仅限于“针对外来军事威胁的军事防务”。这种传统的定义显然十分狭隘且过于单一。现代国际安全研究表明,“国家安全”对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环境均存在不同的理解。此外,对国家安全的衡量,除了一些诸如“领土完整”、“主权受到尊重”、“无外来军事挑衅”等相对具体的客观“坐标”外,一国是否“安全”同时也是一种心态,一种“主观评判”。本文接受阿诺德·沃尔弗斯关于“国家安全”的定义,即:“[国家]安全,从客观上看,是指不存在外来为了夺取我核心价值的威胁,而从主观上看,则是指不存在对我核心价值被强夺的担心与惧怕。”(注: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分歧与合作:国际政治论文集)(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150.沃尔弗斯定义的英文原文为:“Security,in objective terms,measures the absence of threat to acquire values,in a subjective terms the absence of fear that such values will be attacked.”)因此,为了实现“国家安全”,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无一例外要作战略考虑与决策,而这一考虑、决策的“理性”顺序,根据约翰·路易斯·盖迪斯的研究,应是:设定“国家战略利益”、认知对这些利益的“外在威胁”、考量应对认知的威胁的可动员的战略资源水平、进而制定军事战略与国防政策(注:参见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遏制的战略》,第ix页。)。
依此类推,可从以下四方面考察美国“冷战”时期对华军事战略行为。
第一,设定针对中国的“核心价值”或称“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美国对其国家安全利益传统的认知,其最核心的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自身“生存”,即美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得以“完整无损”;第二,美国国家的政治制度,即其包括“自由”、“民主”、“公平与公正”等政治理念及价值观得以延伸;第三,美国社会、经济繁荣的机会,即其诸如贸易、航运、海外投资、金融等经济发展不受到限制与打击。在此基础上,美国战略利益的先后排序通常是所谓的“核心利益[Vital Interest]”、“重要利益[Major Interest]”以及“边缘利益[Periphery Interest]”。基于这样一种思维定式,美国在对华的战略考量中是如何界定其“国家安全利益”的?中国在其“战略利益”的排序中又处于那一种地位?
第二,认知所谓“中国威胁论”。任何国家对“外在威胁”的认知主要受“时空”的影响。对“空间”因素的考虑,通常从地缘政治的逻辑出发,一方面从潜在对手的相对于本国距离远近以及要害位置来考察界定“外在威胁”的方位,另一方面从国际各个势力与力量间的“均势”状态及其走向来确定“外在威胁”国的对象。而时间因素则是指对“历史上的外来威胁”出现的条件、方式、发展过程、结果等经验作出的评估,以及基于这一评估所得出的教训,形成所谓“历史意识”(注:关于此点,参见本人拙作,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China and the Korean War,1950-1953(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4),第一章。)。根据这样的时空坐标,战略决策者们进而确认“外在的威胁”是“潜在的”还是“直接的”,是“立即的”、“近期的”,还是“远期的”。根据这种“外在威胁”认识模式,就可以推断美国战略决策界是如何得出所谓“共产党中国威胁美国战略利益”的结论的?
第三,评估自身拥有的“战略资源”。现代战略资源一般包括以下几个内容:首先,战斗员,主要指常备、后备军队的人数以及一旦战争爆发即可动员入伍的人力;其次,战争消耗能源,包括钢铁、燃料、食品等;再次,军事工业生产力,即与国防有关的科技研发[R&D]、工业生产规模与军事装备水平以及在战争状态下可“转型”的民用工业设施与生产力;最后,政府可动用的财政预算与战争状态下的资金征集。二战后的美国,虽在1946-1949年间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萧条”,而其自二战期间形成的战略资源不仅丝毫未受损,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扩张与发展,其总量与质量均超过了“冷战”时期任何一个大国(包括苏联这一所谓“超级大国”)。这种战略资源是如何影响美国对华军事战略考虑与制定的?
第四,推出美国“军事战略”。西方“战略学家”对“军事战略”的理解基本沿用以克劳斯维茨学派关于战略的经典定义,即,战略指“在战争中,为了战争的目的,对战斗或威胁战斗的运用”(注:Willian W.Kaufmann,Planning Conventional Forces:1950-1980(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2),1-26.)。实际上,这种古典的战略定义,已经无法完全界定现代国际安全环境以及经历,充其量只是所谓的战争实施战略,即何时、何地、以何种军事力量实施何种战争方式的考虑、计划与安排。冷战时期“战”与“非战”时期界限的日趋模糊,要求战略考虑与制定能适应新的现实需要。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及国防战略(Defense Strategy)的出现,大大地拓宽了传统的战略观。“大战略”指战略决策者对维护国际安全利益将如何作战略资源配置所作的长期研判,“国防战略”则是根据这些研判而制定的战争政策原则。以上三个层面的相结合及互相作用,演化出战后美国的所谓“战略体系”(注:Daniel J.Kaufman,Jeffrey S.McKitrick,and Thomas J.Leney,U.S.National Security: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exington,Mass.:D.C.Heath,1985),11-14.)。中美对抗的20余年中,美国对华军事战略在上述三个层面上都是如何表现的?
上述美国对华战略运作的四方面以及所涉及的问题,为本文基本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华盛顿决策内在逻辑的“合理”与“非合理”性,仍需就其它因素的作用提出一系列假设以及问题。
假设之一,美国的对华战略决策在“利益”与“威胁”认知与界定的先后程序,往往是更多地以“威胁”确定“利益”,因此,所有影响华盛顿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因素便显得更为重要。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美国相对其“盟友”的所谓“政治信誉”或战略“可信度”成为影响战略决策者们“确认威胁”,进而不断修订利益界定的重要“坐标系”。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二战后“板块政治”的构成而使作为一方“领袖”者的美国将在己方板块内的“可信度”认作是衡量其“领衔”地位是否稳固的标准,另一方面也给“盟友”——特别是那些对中美关系有着切身利益的亚洲盟国——影响甚至“操作”华盛顿的决策,使之朝对其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美国对华的军事战略考虑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合理性”,在夸大中国对美国安全威胁的同时,也夸大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
假设之二,美国的对华战略决策不仅受到外部环境的极大制约,也无法跳出国内政治所设定的圈子。作为一个多元的政治体制,行政决策机构在对外与国防政策的制定上,不可能避开国内政治运作。多元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以及“道德伦理”标准衡量,必定反映在两党政治、舆论炒作之中,而其影响也必定通过国会政治反映在与外交国防有关的“机制设立”、“预算分配”、“法案制定”、及“军事行动允准”等国家行为上(注:Morton H.Halperin,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1974),26-64.)。二战后的“冷战”,在相当意义上是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形态及国际道德规范之争。美国作为所谓“自由民主世界”和“旗帜”,而中国是“共产主义阵营”中人口最多的“红色政权”,美国的国内政治影响到底是如何反映在战略决策层面上的?
假设之三,美国对华战略决策的基本运作是在其战后建立的国家安全系统内进行的,而这一系统中的军政关系是一大决定因素。二战后,美国为了有效地“担负”起其“全球安全责任”,构建了“军政合一”的国防决策体制,其目的是为了取得系统内各个部门间的最佳合作。然而实际运作的结果则仍难免任何“官僚机制”内在的部门利益症结。在其中,军方(主要由1947年设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所代表)竭力维护其传统上对军事战略的咨询、决策、实施、评估“专利权”,并在国家资源配置上争取更大的倾斜。同时,作为“职业军人”对在国家安全系统内就军事战略问题与文官们“共事”,尽力守住自己的“属地”(注:关于军政关系方面的研究,参见:Bobert Murphy,Diplomat among Warriors(New York:Doubleday,1964))。在此机制内的“军政关系”是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决策的行为与结果的?
假设之四,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受到战略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影响甚大。尽管决策首先是在内、外部政治环境以及行政架构的制约下进行的,但是决策者的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特别是是否有从军经历)、政治可信度、行政运作能力与经验等诸因素都直接与间接地决定着其决策行为。二战后美国的行政领导变换几乎是几年一次。随着白宫主子(总统)易人,参与国防、战略安全决策的高级幕僚也会随之变化,“非政治任命”的部门官变动也十分频繁。这个群体的不稳定性,使战略决策的不同层面在各个不同时期都会打上“个人烙印”。因此,也就存在着同一机制内、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决策行为及结果的可能。这些人的个人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白宫的对华决策?
假设之五,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到“战略文化”(注:关于“战略文化”的定义,参见张曙光著《威慑与战略文化》,第一章。)的影响。“战略文化”制约作用是指战略决策者在“理性”思维的约束下,就“外来威胁”以及“是否及如何使用武力”决断时,完全忽略甚至否认敌我双方由于“文化价值观”以及“历史意识”不同而可能作出不同的战略行为。中美文化差异甚大,应对外来威胁的经历也大相径庭,战略决策、使用武力的行为不可能如出一辙。如果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一味地从自己的思维定式、行为习惯出发,并认定中方也如此思考、如此动作,这样的“文化偏执狭隘”观将会如何制约美国对中国所谓的在亚洲的“动机”与“意图”的判断?
对上述假设的论证,本文采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较通行的纵向比较方法。决策行为在某个时间段就某个议题会表现出某种或多种特点,但若依此类推进而得出“普遍的”、“一般的”、甚至“理论性的”结论,则难免以偏盖全。只有将单个的决策行为放在一个较长的时空段内与其它单个的决策行为作比较,方有可能得出接近“普遍意义”的推论。一方面把美国对华战略决策行为置于亚洲冷战的大环境中,另一方面定位于战后中美间长达20余年的全面对抗关系上。
通过对冷战时期华盛顿对华军事、安全战略决策机制运作的研究得出,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考虑基本按照其内在的一系列“战略密码”所行事。在追求美国“全球安全”目标这个大框架下,战略决策者们围绕着中国相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在设定“国家战略利益”、认知对这些利益的“外在威胁”、考量应对认知的威胁的可动员的战略资源水平、进而制定军事战略与国防政策这四方面作战略考虑。
首先,美国对华战略考虑的最初出发点是设定中国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内涵与等级。历届美国政府无一例外都将中国认作与美国的全球或东亚战略“息息相关”。在先后排序上,美国战略家们的认知却经过了从认定为“边缘利益”到“重要利益”以至最后向为“核心利益”位置升级。从二战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杜鲁门政府主要从“地缘安全”观出发,认为中国既非美国的“核心利益”,也非“重要利益”。其参照坐标是:中国的地理位置只是处于美国“核心利益”所在的地中海、近东的外边缘:中国的工业制造水平低下而充其量只对日本的战后重建起到资源供给及市场出路的作用;中国的广阔幅员、漫长海岸、重要港口在大战时可做前进基地或用兵之地。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在美国“冷战”战略利益的考量中上升为“重要利益”,主要因为华盛顿认为已与苏联结盟的中国对美国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影响上升。此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政府除了考虑到“中苏同盟”在该地区造成的新的地缘政治态势之外,还认为中国对其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在不断上升,结果相应提升美国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核心价值”利益位置。随着中苏关系在60年代初破裂,更随着中国在60年代成为“核力量”,华盛顿显出更进一步看重中国对美国全球战略利益重要性的趋势。70年代初,尼克松、基辛格不惜为了构架“大三角”战略关系而将中国的“大国”地位向“超级大国”位置上提升。
其次,美国对华战略利益的定位成为其对所谓“中国威胁”认知的基础。首先依据“地缘政治”的逻辑,杜鲁门政府在考虑了中美的空间因素后,认为中国对美的“安全威胁”是“潜在的”,而不是“直接的”;是“远期的”,而不是“立即的”或“近期的”。40年代后期,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考虑逐渐倾向于维护一条“环型岛屿链”的最低“防御设置”,而这条“链”的主要支撑点为阿留申群岛、日本的冲绳以及菲律宾。由于太平洋与这条防御链将北美大陆与亚洲大陆的隔离,即使中国在未来成为“军事大国”,其对美的威胁充其量也是“远期”;但杜鲁门政府对“中国威胁”的不确定认知,主要受制于对美国主要对手苏联在战时有“潜在可能”利用中国的包括铁路、港口、沿海岛屿等“地缘资源”、将中国变成打击美国“防御链”的前进基地的假设。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国的冷战战略思维发生重大变化,认定莫斯科在指使“地方共产主义势力”对美国及“西方世界”实施有限的军事挑战,继而中国相对于朝鲜与台湾则突然成为对美国地区安全利益的“直接的”、“立即的”威胁,而不再是“远期的”或“潜在的”了。朝鲜战争中美国与中国直接武装冲突并迫使美国放弃“统一全朝鲜”的战略目标,使华盛顿对中国军事威胁出现的条件、方式、发展过程、结果等“记忆性”的评估衍生出“时间”因素。这一因素所产生的“警示”,不断地被所谓“台海危机”、“印度支拉危机”等所强化,进而形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中国贴上“侵略者”、“美国的永久敌人”的标签。随着“冷战”意识形态越来越深入美国的战略思考中,“共产党中国”对华盛顿在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中政治信誉的“挑战”成为评估“中国威胁”的“既定原则”。“中共”对美的战略意图被解读为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创造“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促使一连串国家先后倒向“共产主义阵营”。此外,中国“核技术”与其它“尖端”战略武器的发展,成为美国战略家们考察“中国威胁”的重要坐标系。美国军事情报与“海外”情报系统在整个60年代花大气力对中国“核武器”研发的跟踪、监测与分析,反映了华盛顿对“中国威胁”认知的侧重。
再次,美国对自身拥有的“战略资源”的评估影响其对华的战略考虑。二战后美国作为世界级的战略资源大国,其武装力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的国家战争动员机制不仅在人力动员方面,而且在将科技研发、民用工业设施与生产力尽快转为战争能力上,均显得有效率(注:关于此点,参见Samuel.P.Huntington,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chapter 1.)。然而,美国的战略资源在满足其美国“全球化”国防与战略需求时,仍捉襟见肘,尤其是政府可动用的财政短缺。美国在1946-1949年间出现“经济萧条”,GDP增长缓慢、联邦税收大幅减少(注:参见Alonzo L.Hamby,Beyond the New Deal:Harry S.Truman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41-7.),这些战略资源“紧缺”较大地制约了华盛顿“全球战略”的实施。据此,杜鲁门政府只能“确保”欧洲重点,1948年“援华法案”出台,只是为了求得欧洲项目在国会顺利通过而做出的妥协,并非出自深思熟虑的战略思考。50年代初美国经济转型成功、西欧与日本重建出现转机,特别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使美国可动员的战略资源增大,增强其在朝鲜、台湾海峡武装介入的“资本”。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0年间,美国经济出现了空前扩张与发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保守财政”政策,使联邦可动用财力达到空前规模,以至在资源上保证、支持了美国加大与中国在台海、印支的军事对抗力度与战略遏制态势(如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美与东亚“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防御”框架)。在美国经济“繁荣”、实力膨胀的条件下,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变得越来越“傲慢”,准备对中国处在萌芽之中的核武器实施“预防性打击”,最终从树立南越“国家建设”样板到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由此造成联邦预算的巨额“赤字”。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做整体战略调整,“让亚洲人处理亚洲事务”的“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与中国“缓和”以构造“大三角”关系等,均属这一调整的内容与政策结果。
最后,美国对华“军事战略”正是在上述三方面的考虑基础上形成。美国“冷战”时期的大战略无疑是对“苏联共产主义阵营”或“中苏集团”的“扩张”进行“全面遏制”,而遏制的手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1947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华盛顿的“冷战战略体系”形成。美国对华军事战略正是在这个“大战略”背景下得以出台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罗斯福所策划的将中国纳入美国的亚洲“势力范围”的战略设想破产,但杜鲁门政府为了确保欧洲重点便确定对华的“最低限度防御”战略,其核心是保证美国对西太平洋从琉球群岛经日本到菲律宾的“防御圈”。朝鲜战争的爆发,华盛顿加强对印支、台海、朝鲜的不同程度的“有限军事介入”,以期达到战略上牵制中国的目的。在整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实施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战略。此战略实际上包括了直接针对中国大陆的“核威慑”、为了“阻吓”中国不得挑战美国“政治信誉”的所谓“延伸威慑”、以及“劝阻”中国“武力解放”台湾的“常规威慑”。60年代民主党政府基本延续这一军事威慑战略,仅在具体内容上加以调整:包括对策划“预防性”打击中国以及在越南打“有限战争”以“震慑”北京。60年代末尼克松政府转向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大国均势”战略,中美从战略对抗趋向“缓和”,但美国针对中国在亚太、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并未因此而大幅降低,华盛顿仍将“台湾问题”作为美国对中国战略牵制的“政治筹码”。
倘若美国对华战略的思考与运作完全按上述四方面进行,华盛顿的“中国战略”从现实主义的逻辑看,则起码应属符合美国战略决策的内在逻辑,故而有其“合理”性。然而,用历史的、批判的眼光看,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华战略决策存在着结构上的局限性与主观上的非理性。这种非合理性及其在决策层面上的影响有以下几方面的明显表现。
第一,美国的对华战略决策在“利益”与“威胁”认知与界定上出现严重混淆。假若按照“理性选择”的逻辑,对战略利益以及外部威胁的认定与判断,应该遵照利益在先、威胁在后的程序。然而“冷战”期间的美国决策者们,往往更多地以“威胁”定“利益”。每当华盛顿对“中国威胁”认知在朝“严重”方向延伸时,中国相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地位便显得“重要”起来(注:参见Russell D.Buhite,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1945-1954(Norman:University Press of Oklahoma,1981),conclusion.另可参照:Gordon H.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尽管是“共产党政权”控制了中国大陆,但仍不足以构成对美国亚太安全的威胁,此时中国战略地位“不甚重要”,甚至台湾是否会被“中共”所占对美国也无关大局。但随着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战略判断发生重大转变,中苏同盟关系的确定、北京对北韩、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解放军积极准备渡海解放台湾均突然间成为华盛顿重新确定美国的远东、亚太战略利益的“危害”系数,中国的战略重要性随之升级。朝鲜战争后,美国对北京表现出的抗击美国的决心与能力感到“震惊”与“恼火”,自然将中国当作在“冷战”的亚洲战场的主要对手。此后所谓“中共在亚洲侵略、扩张与渗透”的危险认知,使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乃至约翰逊政府都毫不犹豫地将中国视为仅次于苏联的“冷战”战略目标对待,从充斥于国防战略决策“最高密级”文件的所谓“中苏集团”可见一斑。尼克松、基辛格时期,中国相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又更进一步。实际上,中国的核力量以及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成为尼克松政府将北京与莫斯科等同看待并构建所谓“大三角关系”的重要考虑因素。
第二,美国相对其“盟友”的所谓“政治信誉”或战略“可信度”成为影响战略决策者们“认知威胁”进而不断修订对利益界定的重要“坐标系”,从而造成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中利益与威胁界定出现误区。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政治信誉”与战略“可信度”判断具有明显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不足以作为重要参照变量而纳入战略思考。然而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几乎毫无例外地将美国对所谓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信誉与可信度,作为对华战略的重要—有时甚至是唯一考虑层面。继而将美国在区域内的战略利益无限延伸,同时无限夸大中国对这些利益的危害度。受这种思维影响,在朝鲜半岛,即使无法“解放”北朝鲜也必须恢复南北分裂“现状”;在台湾海峡,即使守住沿海岛屿无军事意义也不得拱手让给“中共”;在印度支那,即使中国只是间接的、非军事的介入,美国也必须予以直接的、军事干涉;中国的核武器即使仍在襁褓之中但也要考虑给予“预防性”摧毁。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受两个因素制约。一是华盛顿决策者对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惧怕。二战前期绥靖政策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战略思考;另一方面,美国的亚洲“盟友”操纵华盛顿决策的程序。他们利用“政治信誉”这张“王牌”迫使美国的战略考虑、国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第三,作为制约对华战略决策的美国式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使得“理性选择”常常成为空谈与幻想。二战后的“冷战”,在相当意义上是“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及“国际道德规范”之争。美国作为所谓“自由民主世界”的“旗帜”,而中国是“共产主义阵营”中人口最多的“红色政权”,美国的对华军事战略是不可能摆脱美国反共意识形态框架。“冷战”时期美国关于“中国政策”的大量研究报告、会议记录乃至决策文件中,“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比比皆是,足以描给撰写者们的思维轨迹。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此类“修辞”很少改变过。甚至在尼克松、基辛格时期,也未能幸免。语言反映了思维但同时又制约着思维(注:关于此点,参见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8(2)(June 1994):384-96;Edward Rhodes,"Constructing Peace and War:An Analysis of the Power of Ideas to Shape American Military Power,"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nal Studies,24(1)(Spring 1995):53-85.),很难使实际政策非意识形态化。此外,尽管美国原则上建立了所谓在对外政策上“两党一致”的原则,但白宫的主人们在对华战略思考时,自觉与不自觉地受制于政党之争。共和党人就“是谁丢失了中国”为题向民主党政府的发难,不仅导致对国务院内所谓“共产党同情者”的“中国专家”的清洗(注:关于杜鲁门时期对国务院内的所谓“中国手”的清洗,参见Gary May,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1979);John Paton Davies,Jr.,Dragon by the Tail (1972),and John S.Service,The Amerasia Papers (1971).当时被从国务院“清洗”的主要“中国手”包括:John Carter Vincent;John Paton Davies,Jr.John S.Service,John King Fairbank,即所谓“四约翰”。),而且形成对美国对台政策的价值取向以及衡量标准。在很长的时间内,决策者中无人会冷静考察美国是否曾经“拥有”过中国,而只担心不要被与“失去中国”相关联。最初挑起这一政治纷争的共和党人,一旦上台以后,也反为其制。在对华政策上如此意识形态化的“两党政治”,又反映在与对外与国防有关的各种国家行为上。美国长驻台湾的“军事顾问团”、“中情局台北站”等机构、美国各个财政年度对东亚、东南亚“自由国家”的经济、军事援助拨款、各个“共同防御”协定与“福摩萨决议”等,均为例证。
第四,军政关系作为美国对华战略决策的一大决定因素,使华盛顿的战略思考错综复杂。二战后,美国为了有效地“担负”起其“全球安全责任”,进行了国防决策体制改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所谓“军政合一”机制。构建该机制的最初动机是为了保证军方对国防政策的决策参与权,从而提升军事指挥官的决策发言地位。这样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便出现军方极力维护其传统上对军事战略的咨询、决策、实施、评估的“专利权”,同时为了在国家资源配置上获得更大的份额,便在“官僚机构”内想方设法地竞争。表现形式之一,“职业军人”们在国家安全系统内尽力守住自己的“属地”:对军事战略的权威发言权。从历次有关中国的“国安会”文件形成过程中看,参谋长联席会议都紧紧抓住“从军事角度考察问题”的“特权”,其对自身的提案、建议是如此加以论证以区别于其它“角度”,对别的机构特别是国务院系统的任何“想法”、“立场”、“计划”更是动辄拿出“军事角度”这一“杀手锏”。如在台湾海峡沿海岛屿的“协防”问题上,军方的意见,使得那些侧重“政治灵活”的文官们屡次受挫、不得不敬而远之。基辛格在调整对华战略时,也迫于军方压力不得不有所妥协。冷战时期美国军方制约对华战略的另一独特现象表现为战区指挥官影响力甚大。无论是朝鲜战争期间“权倾”远东的麦克阿瑟,还是曾在东亚战区担任过指挥官、后进入最高军事系统并担任要职的李奇微、雷德福、泰勒等,几乎无一例外地对美国的“中国战略”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将军们自认对亚洲比较了解,在决策中十分自负僵化。由于这些人多少都在朝鲜战争中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交过手,“感情上”认定中国是美国当然的敌人,任何与北京妥协或“示弱”,对他们都是难以接受的。尼克松时期“战略上”与北京缓和,但美国军方从未放弃过与中国在“军事上”长期对抗的立场。
第五,美国对华战略决策中的“个人烙印”甚大。参与战略各个环节的决策者的包括教育背景、职业背景、政治可信度、行政运作能力与经验以及各自的政治利益诸因素,都会直接与间接地决定着其决策判断与参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杜鲁门政府公开出台了远东地区“环型防御”战略。这项较为保守的战略是在坚持“欧洲第一”的国务卿艾奇逊影响下产生的。朝鲜战争爆发,华盛顿决定武装介入的第一项决定即所谓“保持台海中立”。其中,美国海军退役将领、可能受雇于将介石的库克上下活动、积极游说,起到了重要作用。仁川登陆成功后,“联军”总指挥麦克阿瑟,无视北京警告,力主在朝鲜半岛打过“38线”以至最终导致中美在朝鲜直接军事冲突。韩战结束后,对艾森豪威尔时期在亚太地区通过“军事威慑”、“共同防御”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时任国务卿的杜勒斯是最为积极推动的政府要员。肯尼迪期间,总统特别顾问哈里曼,为了表现对苏联事务的“熟练”,是极力策划并推动美国“联合”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打击”的策划者与推动者;“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因,由于与蒋经国的“特殊关系”,积极促动华盛顿支持蒋军“反攻大陆”;而崇尚“有限战争”、“灵活反应”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则是主张美国选择在越南与北京、莫斯科较量的“领衔智囊”。毋庸置疑,尽管尼克松对缓和中美对抗有自己的倾向,但与此有关的所有策划、酝酿与实施,应该说是“地缘政治”的忠实信徒基辛格的“大手笔”。历史事件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但与事件相关的“个人因素”则使得发展的偶然性加大。同时,不同“个人”的背景、意图等方面的差异,使战略考虑与政策运作的“个人色彩”加重,因此,存在着同一机制、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决策行为及结果的可能。结果造成战略态势不连贯、具体政策相互矛盾,以至给对手传递出“偏差”、“错误”的信息并做出错误判断。
第六,美国式的“战略文化”在“冷战”期间对华战略决策的负面影响。华盛顿的战略咨询与决策者战略决策者,在认知、判断“威胁”的性质与程度以及决定是否动用武力、动武的方式与烈度这两个战略关键层面上,常常“忽略”甚至“否认”中美双方由于“文化价值观”以及“历史意识”不同而可能做出“不同”的战略行为。毋庸置疑,中国、美国文化差异甚大,历史上在应对外来威胁的经历也大相径庭,故而两国的战略决策、使用武力的行为必定不可能“如出一辙”。因此,对一方显得“理性”的,在另一方看来却表现出“非理性”。这是由于“理性”在不同的“文化生态”所蕴涵的“主观性”、“相对性”所决定的(注: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65),27.)。然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一味地从自己的思维定式、行为习惯出发,认定中方也“一定会”如此思考、如此动作,由此形成的“文化偏执狭隘”观不同程度地误导美国对所谓中国在亚洲“战略扩张”、“穷兵黩武”的“动机”与“意图”的判断。杜鲁门政府从西方盟国“国力不对称”逻辑出发认定“中共”实力有限而不得不完全受控于莫斯科。据此,中国大陆被认作为苏联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扩张”、“渗透”的“前进基地”,北京的所有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都被视为是在推行莫斯科的战略目的。在朝鲜战争爆发时,华盛顿便判断苏联在指使北韩发难于朝鲜半岛、而令“中共”在台湾海峡甚至印度支那挑战美国所认为的另外两个“软地带”(注:Zhang,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China and the Korean War,1950-1953(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4),chapter 2.)。更有甚者,崇尚“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的麦克阿瑟,自认能“读懂”东方人“惧怕武力震慑”的“心理”,断定中国军队面对“联军”海空、炮火的“绝对优势”根本不会做在朝鲜“以卵击石”的“非理性”选择。然而,他很快发现,由于自己完全忽视中国战略选择中遵循“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思维的错误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所谓“台湾问题”上,美国冷战期间历届政府都误判了台湾对北京的战略意义。新中国领导人将台湾的“不分割”看作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所崇尚的“祖国统一”这一“核心价值观”(注:传统的战略学家否认“核心价值”作为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而“冷战”的国际冲突经历使国际安全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战略决策者是如何将“核心价值”与“价值观”作为核心国家利益而纳入战略考虑。参见:Kenneth Booth,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79),chapter 1.),因而是中国“核心”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决不会轻易放弃。华盛顿根本无法理解中国领导人考虑“台湾问题”的“历史意识”与“道德价值”,只从传统的“地缘政治”出发,认为中国是企图“攻占台湾”以控制“海上通道”、达到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权”与整体亚太战略利益的“长期战略目标”。
无疑,美国的军事战略与国防政策制定是一个多层次、多方位、多因素的综合系统,而“冷战”时期华盛顿的对华决策正是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系统中运作。对其运作过程、思辨轨迹、行为方式做“历史分析”,起码对了解美国战略决策行为可得出如下几点启示。首先,当代美国国际安全战略的核心部分是其二战后建立的“全球观”,其基础则是“地缘政治”思维。因此,对战略利益的分层次思考,成为指导战略决策的基本框架。忽略这一框架,就无法把握美国战略的实质。其次,美国国际安全战略决策追求的是从美国根本利益出发的所谓“理性选择”,而衡量“理性度”的重要标准则是对战略资源是否作最现实、最有效的动员、配置与利用。尽管制约、阻碍作“理性选择”的“非理性”因素不仅“层出不穷”且“能量极大”,但使美国战略得以长期稳定的关键则是战略决策者对可动员的战略资源的认知与对此资源利用的利弊分析(注:关于此点,参见Gaddis,The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epilogue.)。假如不认识到这一点,便会被某项政策或动态所迷惑。再次,美国的战略思考与对外政策既相关但又相分离,而只有准确地把握其战略思考的逻辑与规律才能判明其对外政策的走向。若仅以华盛顿的某项具体政策去推导其战略态势,难免“以偏盖全”。最后,美国公开的战略设想与国防政策与实际战略策划与政策制定有相当大的“距离”。每当华盛顿公开某项政策甚至于“战略”,其常常是为了特定的政治运作目的,因此政策内容、话语的设计都是针对“锁定听众”:或是对国内某个利益集团、或是对某个盟国、或是对某个敌对国。为了“去伪存真”,就不应过度注意公开的战略或政策说明。
标签:军事论文; 华盛顿论文; 战略决策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