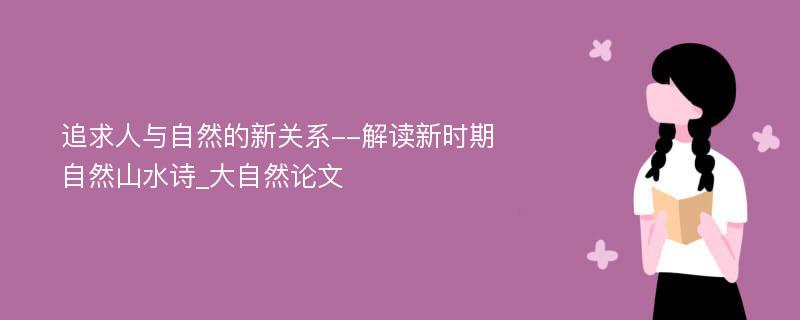
追求人与大自然的新型关系——新时期自然山水诗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论文,新时期论文,大自然论文,自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最初几十年的英国诗人们曾经对表现大自然热衷到一种痴醉状态,以致于勃兰兑斯说它“创造出一种支配着整个文学界的自然主义”[①a]。20世纪初,美国则出现以杰克·伦敦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潮流,发出“野生的呼唤”,呼唤回归大自然和被人类社会扼杀了的自然属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出现了海明威这样的自然主义作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学界也出现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然崇拜,这种崇拜广泛地体现在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等众多的作家笔下,其中以自然山水诗人尤甚。当然,它本质上不同于英美的自然主义。新时期中国自然山水诗人的大自然崇拜,不仅有它形成的特殊原因和特殊内涵,而且是以特有的情感和特定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概而言之,诗人们在加入世界“大自然崇拜”这个主题大联唱的过程中,既不简单地否定先哲又不痴情地迷恋传统——一代成熟的作家已不屑于机械地谈论借鉴与继承、突破与超越了,而是把根基牢牢置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里,试图在恢宏阔大的地理空间内寻找人类与大自然交往的艰难历程,获得若干关于人类生存方式和生命意识的感悟与思考,从而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
大自然孕育了人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然而,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却往往忽视或忘却了它深厚的恩泽。为了实现自己贪婪的欲望,人类曾无休止地征服自然,或者由于昏聩、愚昧,对大自然粗暴地进行践踏和蹂躏,以至使它瘢痕累累,满目创伤。新时期的诗人首先是从这里入手而结识自然的,因而作为人与自然的一种最直接的关系,便是用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揭示人对大自然的种种“不敬”行为,并对这些行为以及所带来的恶果表现出深切的忧思。看看作家笔下的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吧:名胜“滇池”曾以“五百里浩淼的烟波”“将千年兴衰的历史淘尽”,然而眼前的事实却是:“那日夜浸入的污染浊流”,时刻在腐蚀着他的“肌体”(纪鹏《题滇池》)。由于“昨夜一场大火”(文革)的折腾,中外闻名的大明湖变成了“一汪不流动的死水/冷清清,只有几片枯叶在凄风中飘舞”(孙静轩《大明湖》)。傅天琳笔下的长在七层塔顶的黄桷树,由于缺少土壤、同伴(树林)等必要的自然生存环境,只能在“砖与灰浆的夹缝里”求生存,活得十分艰难和“别扭”,但它暂时“并不会死去”,“它在不断延伸的岁月/把孤独者并不狐独的宣言/写在天空”(《七层塔顶的黄桷树》)。这显然是一个象征,一个寄意深远的关于人类现实生存环境的象征。最后的感慨难道不是对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关系发出的长鸣警钟!侯书良的山水诗集之所以命名为《骚动的山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令人悲哀的一面引动得他骚动不宁,在《泰山笋城忧思》中,他不仅为“喊得石笋心颤”的纷乱的现实环境而忧思,而且更为它的前景担忧,“用不了数千年,/笋城将被夷为平地”,因为我们有比刀斧还凶的“灯红酒绿的华宴”。《龙虾的悲剧》更以一种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类无休止地捕杀弱小生灵的行为表示愤懑:“渔者的笑,/在于下网的不空”,人类有时表现得多么荒诞和残忍!
无可否认,人类是在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成长的,改造自然的斗争构成了人类进化的主要特征,改造自然的程度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发达状况。现今,人类已成为主宰地球的最为有力量的生物。但是,人类常常因急功近利而失去应有理智和谦让,对大自然的无休止的索取乃至粗暴地糟蹋、掠夺破坏了生态平衡,这已引起了大自然的报复和惩戒,一系列因此而来的生存困境正或近或远地威胁着人类。诗人们从这里入手来提出问题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上去似乎短浅,但却是一种最积极最现实的人生态度。这将令人醒悟一个熟视无睹的事实:大自然的破坏亦即人类自身的破坏,大自然的死亡亦即人的死亡。在中国古代作家的眼睛中,山水自然几乎全是诗意的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一种单纯的审美关系,很少是一种生存关系。新时期的诗人们弥补了这一缺憾。他们通过自然现象来表现人的生存困境,审视人类自身的行为,是在经历了现实的刺激、尝到了历史的苦果并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之后才获得的。
人虽非大自然的奴隶,但也不是主宰自然的上帝。人在自然面前应当有所节制,有所禁忌,这是新时期不少诗人所获得的共识。因之,他们不仅写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不敬行为以及沉痛的忏悔心情,渴望大自然能够允许人类用悔过的泪水冲洗掉昨天对它所犯的罪恶,而且以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虔诚表述自己回归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重新探讨“天人合一”的内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人与自然基本上是和谐一致的。但二者在何种程度上、何种意义上、采取何种方式取得一致?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将自然山水与人的德性、志向联系起来,视自然为人类可以理解的知己力量,这无疑使山水意识从神的祭坛上解脱出来。然而就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而言,大自然只是文人隐遁和游乐的场所,或者说,当人出于某种精神好尚需要自然时,才想到大自然的用处,才会亲近自然,否则仍可以忘却甚至破坏自然。“果丛药苑,桃蹊橘林。捎云拂日,结暗生阴。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间之芜杂”[①b]。这实际上还是强调对自然的审美的利用,人对自然是一种赤裸裸的有用性的占有。同时,由于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自然山水诗人们大多力主清虚空寂,不主张展现个人主义,因而“从来就不曾把宇宙纯粹作为展现其自我的舞台或背景”,更“见不到生命化的意象”[②b]。新时期的诗人们摒弃了这种狭隘的自然观,在对人自身的生存和人的生命自身的关注的基本视角下,大多从人是自然之子这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体味大自然所提供的甘露琼浆,探讨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意义,以及对人类生存的可能性所提供的某些契机。这对传统的自然山水观念无疑是一种根本性的超越。例如,蓝疆的山水诗集《烟花三月》第一首诗开明宗义地唱道:“一级坚实的石梯,/涌动我一次/美美的情绪。/我便这样,/在一种情绪涌动的波涛里,/一步一步走向你。”(《我登中山陵》)这既是诗人亟盼投身大自然的真诚表白,也是诗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生命律动的真实表现。在诗人看来,自然山水是养育我们民族的摇篮,是供给华夏子孙休憩的眠床,当自己有机会跨出狭小的办公室而接受“月亮的晶莹”、“太阳的热情”、海的“清醇”等“珍贵请柬”的时候,怎能不由衷地感到一种“美美的情绪”在自己的血管里波翻浪涌呢?生命力由此得到一种恣情恣意的舒展。晓雪的舒展是在与大自然相偎相依中获得的:“采了一天的茶,/我睡在苍山的怀抱里/睡着了,睡得那么香;/我梦见/苍山就在我的怀抱里……”(《爱》)。晏明1987年以76岁的高龄冒险登上海拔五千多米的长江源青藏高原时,在大自然的律动中也感到了生命力的生生不息:“我全身沐浴着沱沱雪浪,/各拉丹冬的鲜血涌入我的血管,/心脏在各拉丹冬峰巅跳跃翻滚。/……”于是,自己在接受了“冰雪与风暴的洗礼”之后,获得了生命的“又一次诞生”(《我又一次诞生》)。
这种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大自然的境界,在描写大海的一些作品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例如,曾卓就总是喜欢写自己对于海的向往,写他在海中的飘流,在海滩上写诗唱歌,还写在海泳以后的体验和感受。这并不是他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而是他心目中的海就是生命的对应物,他写种种有关海的诗,也就是写对生命的认识与思考。还在1973年,曾卓就写过一首《海的向往》:“从退潮的沙滩上/我拾回一只海螺/想用它代替丢失的芦笛/吹奏一支海的歌/平静的日子使我烦忧/渴望着风暴和巨浪/我的心里充满了乡愁/——大海呀,我的故乡//我没有能吹响/那有着波涛气息的海螺/它搁浅在我的案头/我们相互默默地诉说/海的向往和海一样深的寂寞”。这首诗倾诉了诗人在特殊的年代被剥夺了创作权力的深沉而寂寞的痛苦,但也同是透递出了诗人把大海作为生命故乡的信息。因而一旦恢复了创作自由,对海的向往情绪便难以自己,大海成为了经常讴歌的主题,他是在“海的梦”[①c]中实现自己的生命理想的。例如,在《瞬间》一诗中,他写了自己海泳后的情景:躺在沙滩上晒着阳光,海浪在脚边跳跃,闭眼沉入迷茫的梦乡,犹如仍在海上飘荡。最后,当他睁眼看到蓝天、白云、阳光和大海时,“一瞬间,我感到自己轻轻地/轻轻地飘升了起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种感受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体验,却充分揭示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生命的神秘感应,表现了个体生命最终“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精神追求。这与勃兰兑斯所描写的“泛神论”境界十分相像:当诗人“凝神眺望时,他的整个生命都从自我狭窄的天地中涌出来。随着溪流流走。他活跃的意识扩展开来,他把无知觉的自然吸入自我之中,自己又消融在景物里,……并同无形的宇宙的生命合而为一”[②c]。
人类文明史已延续了数千年,而由于种种原因所造成的人的精神的异化和扭曲,至今仍在痛苦地折磨着一切追求真善美的人们,特别是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机械化和物欲对于个人主体(包括理性、激情、冲动、本能、体魄、欲望、无意识等生命的全面内容)的压抑,更使人类趋向萎靡困顿。人类的委琐与失重是全面的。卢梭曾十分痛心于人类的这种“所谓进化”,把它看作是“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③c]。这时,回到大自然意味着重温某种古朴、原始的生存方式,这确实有助于抗拒异化的蔓延,正如章德益与大漠相互“设计”与“塑造”、是大漠使自己变得“雄浑、开阔、旷达”(《我与大漠的形象》)一样,也许,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才能体验生命的真正情致。
正是出于这样的追求,新时期诗人们的审美趣味出现了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变化:大多对大自然的秀美与雅致失去了兴趣,尽管描写秀美与雅致的作品仍时有产生。作家们已不再把山水自然理解为一湾湖水、一峰山丘、一堤杨柳、几处楼阁、浅草乱花、浩月繁星,也不再环绕着假山假水作卿卿我我的浅吟低唱——一些成熟的作家已羞于作这一类纤巧、妖媚的编排了。他们收集的自然山水通常是险峻的、粗犷的、阔大的、蛮荒的,洋溢着原始的古朴神秘。大海的汹涌“泛潮”和像“千匹雄狮在旷野里一齐狂吼”的“涛声”(孙静轩《大海泛潮》、《涛声》)、“使万物觳觫”的浩天大漠中的“长嚎”(昌耀《赞美:在新的风景线》)、环绕黄山的茫茫无际升腾奔泻的“云海”(晏明《黄山云海情》)、任何风暴山洪都撼不动的“盘根错节”的“原始森林”(张万舒《原始森林》)、“动得天旋地转”“暴烈如男性”的“大草原”(张万舒《大草原》),……的确都无法使读者作出惬意的、柔情的、甜怡的观赏。作家笔下的这些奔腾着的放荡不羁的强力与野性的激流,原不过是生生不息的自然界所固有的律动,作家不厌其烦地描写他们,描写自己身居其中的情感涌动,无疑是在直接暗示某种强悍奔放的生命力与自由自在的生存方式,或者说,是在呼唤被异化了的具有血性的、充满原始生命力的人性的回归。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缘由,当年的狄德罗的自然观里才注入了一种浓厚的原始主义成分,他鼓励诗人们去接触那些原始的“生糙的自然”,使诗有一种“巨大的粗犷的野蛮的气魄”[①d]。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诗人在中国新时期的诗坛仍觅到了众多的知音,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历史传递,更是一种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血缘联系。
然而,人类最大的痛苦与困惑,也许还不在于自身的不断被扭曲和异化,而是在拥有生命的同时却又明确意识到这生命的必将消失。所以,人们也常常把生命意识归结为死亡意识。古往今来,生与死的主题在文学创作中一直盛行不衰,这并非因为作家有此嗜癖,而是无法回避它,特别是对于心灵特别敏感的诗人来说更是如此。然而,生与死是相辅相成的,生不仅以死为归宿,而且因死而显示其真价值,没有了死,生也就同时丧失存有的意义。所以,不少人不赞同那种专门在“死亡体验”上作文章的倾向。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他却能够而且应当去寻找一种消解痛苦的方式,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使人的生命价值得以实现。写自然山水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消解。但是,采用何种行为和方式消解,诗人们却有不同的抉择。不少作家(如沙白、王鸿、罗继长、李瑛、苗得雨、高平、黄万忠、陈咏华等)曾倾心于对大自然“美”的一面的描写,在自然“美”中偶然意会,物我两忘,一心澄然,万虑尽释,从愉悦中尽情地体验生命的情致。也有些诗人(孔孚、孙国璋等)则积极寻找空灵,追求玄虚,他们在一些孤独幽静的山水物象里如鱼得水,独善其身,并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维持着对世界的哲学渴望,其表面上的同社会现实疏离和超功利,正意味着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拓展着人的精神世界,自由自在地发展着人的品格和情操。在本质上,这确实都是消解痛苦的精神活动。然而就“死亡”而言,这些消解只能是暂时的,甚至是消极回避的,并不脱离古人那种“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窠臼。在这里,引起我们注目的是那些积极进取、充满了强烈的现代意识的山水诗人。
地处茫茫大西北草原上的边塞诗人,如昌耀、章德益、杨牧、周涛等,是通过描写人类在与大自然的争斗中所显示出的伟大精神和不朽的生命价值来消亡因死亡而带来的痛苦意识的。他们笔下的边塞风光也是蛮荒的,骠悍的,代表了大自然的原始力量。在这里,人与大自然后争斗并非单纯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更是一种爱与恨、善与恶、心与力相交织的角逐。边塞草原上的人和动物都是一种强悍勇敢、战取一切的精神,他们从来不怕大自然的袭击,“即便袭来旷世的风暴,/他们也是不肯跪着求生的一群(周涛《野马群》),他们勇往不息地跋涉、驰骋,不仅在“在战胜自然中拥有自然”,而且也“征服孤独,赢得宇宙”(章德益《牧人》),这无疑会使生命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然而,塞北的大自然并非那么容易战取的,它以蛮荒骠悍吸引着征服者,又把征服者弄得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甚至以它“大而无边”的力量将征服者吞噬。但对于那些征服者来说,这样的下场却也是壮丽的,借用诗人王辽生的话说就是:“我原是从那儿来的所以我要回去”(《自然之恋》)——追求的勇敢无畏,毁灭的痛快潇洒。这难道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对痛苦的消解吗?也许,诗人们已经从大自然的惩罚中清醒地意识到,人与大自然的对立和争斗只是暂时的,表象的,人在大自然面前也并非无所不能无所不可为。人与自然应当和平共处,二者关系所谋求的终极目标,应是一种无差别的境界,是同一而不是冲突,是相互依存而不是绝对排斥:“我躺下,我就应该是新绿/我站起,我就应该是新山系”(章德益《我应该是一角大西北的土地》)。这样,就使生命在“凤凰涅盘”般的死亡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获得了价值的永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颇有些相像于把归属自然的死亡作为最终完成对自己的雕塑的海明威。这样的“死”与其说是大自然使然,倒不如说是人类对大自然特殊情感所使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然与生命的全力使然。这样,人就不会再背起因“死亡”而带来的沉重精神负荷。
曾卓是在“大海情结”中寻找他的消解行为和方式的。例如《无题》一诗:
我在沙滩上写一行行字
海浪翻卷着涌来
将那卷去了
我在沙滩上面向大海歌唱
海风飘飘着飞来
将那带走了
于是
我在海涛上读到了我的诗
在海风中听到了我的歌声
近几年人们常由“生命”谈到“精神家园”的话题。人类的“精神家园”何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类的生命是源于大海的,因而人类的“精神家园”也离不开大海。作为一种抽象的人生体验,我以为诗人所追求的“精神家园”和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就全体现在这首诗里了。一个人,不管他的个人遭遇如何,只要能在海涛上读到他的诗,在海风中听到他的歌,即使他的个体生命已经消失,其精神也是不朽的,因为涛声和海风都是永恒地存在着的。当诗人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消解痛苦就肯定不会再是卑微猥琐的求生的拘泥和依恋,而是极力地追求能够称之为永恒的精神建树了。新时期以来诸多山水诗人如孙静轩、舒婷、姜振才、杨牧等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诗笔指向大海,痴情地依恋着“海浪”、“海涛”、“海风”以及海底的“珊瑚树”、“珍珠”、“沙粒”(姜振才《海恋》)等等与大海相关联的一切。甚至连一些经受过海浪袭击并颇知它的“咸”味和“苦”味的人,也同样对大海一脉情深,大多就是因为像曾卓一样从大海中看到一种永恒存在,意识到个体生命是以融入大海为归宿才获得永恒的意义的。曾卓的那首《我遥望》曾写道:“多少人,多少人/为什么,为什么/还有这样多的人/赞美海,向往海,奔向海/在离开海后怀念海?//谁能够,谁能够/回答这难解的谜/你就懂得了,懂得了/人生的奥秘”[①e]。自然山水诗人们正在一步步接近这“谜”团的谜底。
这里蕴藏着一种新的自然观。人类确实需要建立新的自然观了。
人类的祖先来自大自然,人类的最后归宿是大自然,人与大自然必将消除对抗,走向融合,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人本主义”[②e]。然而实际的状况却是:人类正日复一日地疏离自然,有意无意地伤害自然,大自然也在毫不客气地报复着人类。自然在人类心目中的位置与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这个问题确实到了必须严肃对待并作出新的衡定的时候了。所幸的是,大自然和人类都已不再沉默无语,其融合的意愿正在假文学进行宣谕,一批自然山水诗人自觉充当了光荣的信使。这是不是预兆了人与自然关系史的一个新阶段?至少可以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作出肯定的判断。
注释:
①a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英国经验主义》。
①b 《陈书·江总集》。
②b 傅乐生:《潺缓的溪流》第1册,第104页。
①c 《曾卓抒情诗选》有一辑冠以“海的梦”的海洋诗。
②c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册,第175页。
③c 《忏悔录》第2部,第480页。
①d 转引自《西方美学史》上册第273页。
①e 曾卓以及一些诗人笔下的大海往往具有意象的双重性,既指地理意义上的“海洋”,也是“社会”或“生活”的借喻,二者或叠加,或融合,难以分解。
②e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