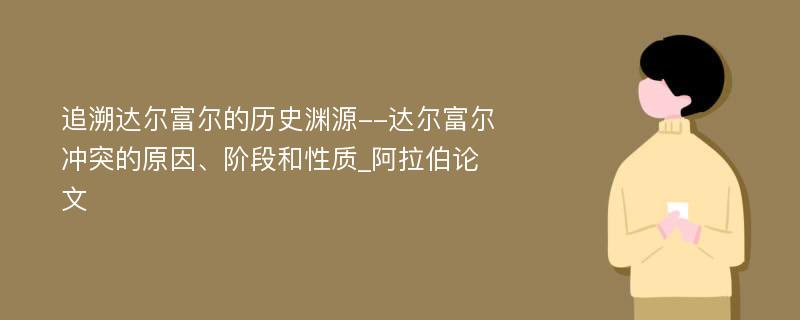
达尔富尔问题的历史溯源——再论达尔富尔冲突的原因、阶段及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尔论文,冲突论文,性质论文,阶段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已持续五年多的达尔富尔危机不仅给苏丹国内造成了深重灾难,而且给邻近国家和地区的稳定,以及当前国际关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冲击。虽然国际社会不断做出各种努力,但达尔富尔地区的紧张局势迄今并未得到彻底缓解。究其原因,除了冲突各方的立场难以协调与统一外,与有关方面对冲突本身的认识失准或不充分不无关系。本文将从历史视角追寻达尔富尔冲突的起因、进程及其性质。
基于土地争夺的早期传统冲突
达尔富尔地区是苏丹西部北、西、南达尔富尔三州的总称,面积约为5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5。可利用水资源的土地是达尔富尔各族赖以为生的农、牧业活动的基础。该地区的耕作业迄今仍主要为自给自足式的传统小农生产,而这种土地使用形式面临与土地的游牧使用形式间的冲突,显然是环境退化、户均土地使用量增大,以及游牧规模扩大的结果。两类土地使用形式之间的冲突反过来又导致了可用土地的相对短缺,农、牧部落内部及相互之间争夺土地的冲突也随之出现。
达尔富尔的土地问题是在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出现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干旱与荒漠化、人口增长及“达尔”(“Dar”,意为“领地”)问题。干旱是引发非洲许多地区冲突的环境因素的共同特征,也是达尔富尔土地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达尔富尔地区的降雨量逐渐减少,北部情况尤甚,年均降雨量下降了1/2,并导致了庄稼歉收和牧场干枯。① 由于降雨量不稳定、害虫横行及农业投入不足,该地区的粮食产量一直很低,且难以预知收成情况。牧场的承载能力也因水草不足而日益下降。② 伴随干旱而来的是土地的退化与沙漠化,而人为因素(诸如砍伐树木、过度耕种、过度放牧等)对沙漠化的加速作用更使土地到了难以维持居住者生计的程度。③
同非洲及苏丹其他地区类似,达尔富尔地区的人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一直在持续增加。2003年与1973年相比,达尔富尔的人口由约135万人增至约648万人,同期人口密度也由每平方公里4人增长到18人。④ 此外,移民也是导致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达尔富尔经历了国内外两股移民潮:十年(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极端干旱引发了北达尔富尔牧民的向南移民,他们在法希尔东南的沙土地区及南达尔富尔寻求避难,使这些地区的人口迅速进入了饱和状态;来自乍得和西非国家的移民不断进入达尔富尔寻找久居地,而扎加瓦等跨境民族的存在又使苏丹政府难以对这些外来“同胞”进行有效监控。⑤ 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对粮食和水草需求的不断扩大,而农作物产量和牧场承载能力却因降雨量减少而下降。为了弥补产量的下降,扩大或争夺耕地和牧场就成了农牧民的唯一选择。
引发土地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部落领地问题。早在富尔王国时期,素丹就只给中部和南部的部落授予了“哈库拉”⑥,而北部的一些游牧部落并未得到属于自己的封地;英-埃共管时期,英国人选择了所谓的“本地管理制度”,即以间接统治和原有的“哈库拉”制度为基础的部落管理制,达尔富尔的土地被分为若干自主管理的部落“达尔”;独立以后,苏丹各届政府从原则上都默认了这种土地管理制度。尽管历史上达尔富尔曾人烟稀少,土地充裕,可是在由生态退化和扩大生产导致的土地资源日渐紧缺的今天,能否拥有或夺得属于自己的“达尔”却成了关乎生存的重大问题。
由于持续干旱(自1967年至今,期间只有几次短期中断)、大面积饥荒、规模空前的人口增长与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达尔富尔地区的两大经济活动即农、牧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所难免,其结果是农、牧民之间的摩擦与冲突。虽然当地的部落,特别是游牧部落之间早就有争夺水草或因偷盗牲畜而发生的械斗,但从出现持续干旱以来,促使冲突加剧的一个更为系统的驱动力便是游牧民对中部农耕地区的破坏和占领。在受干旱威胁的牧民试图通过侵占肥沃的中部地区来维持生计的同时,定居农民也为守护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进行了坚决还击。
除以获取资源为目的外,达尔富尔地区早期冲突(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还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冲突频率呈逐步加快之势。根据优瑟夫·塔卡纳的统计,1968~1998年,当地共发生29次比较严重争夺自然资源的“传统型”冲突(1968~1976年3次,1976~1980年5次,1980~1998年21次)。⑦ (2)基本不具有种族冲突性质。80年代中期之前的冲突大多发生在阿拉伯游牧部落之间,发生在非阿拉伯部落之间及阿拉伯游牧民同定居农民之间的冲突相对较少,而且一些部落并没有向有种族亲缘关系的冲突部落施援。⑧ (3)烈度和规模由初期的低烈度、间歇性和小规模的冲突逐步向高烈度、持续性和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演变,较严重的冲突有阿拉伯雷扎盖特部落与马阿里亚部落的冲突(1968年)、马萨里特人与阿拉伯塔艾沙部落的冲突(1980年)、阿拉伯贝尼-哈勒巴部落与马阿里亚部落的冲突(1980年)、阿拉伯马哈里亚部落和扎加瓦人与富尔人的冲突(1983—1987年)等。
基于对立认同的中期种族冲突
达尔富尔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约有700多万人口,其中约60%是农民。富尔人是最主要的族群,他们和马萨里特人等族群都是定居农民,其余为游牧或半游牧的阿拉伯部落及扎加瓦、迈多卜等非阿拉伯族群。由于历史上土著的非阿拉伯人和外来的阿拉伯人长期杂居通婚,因此,该地区的种族划分并不十分清晰。现在,那些“阿拉伯人”主要通过语言文化属性(即母语是否为阿拉伯语)来区分彼此。虽然90%以上的达尔富尔居民是穆斯林,但40%以上的人口都不是阿拉伯人。⑨
前文已说明,达尔富尔的早期冲突主要是不同族群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争夺,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持续干旱、人口增长及土地沙漠化则加剧了这些冲突。难以维持生计的北方游牧部落不得不南下寻找牧场和水源,这引发了他们同中部农民之间的摩擦。虽说定居农民同游牧部落的冲突在不断增多,但80年代中期以前的冲突只限于争夺资源,并无种族政治色彩。然而,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政府不仅未积极帮助当地民众缓解生存压力,而且出台了一些有损当地管理及种族团结的变革与举措,如废弃用以解决冲突的部落会议、动员并武装阿拉伯部落民兵、重划当地行政区域等。达尔富尔原有的传统管理制度被破坏了,可并没有迎来行之有效的现代管理制度。80年代后期以来,该地区一直处于冲突与混乱状态,这自然会强化当地民众的种族依赖感,因为他们在失去政府保护时只能在种族认同中寻求物质安全与精神慰藉。达尔富尔冲突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令人担忧的变化:种族认同成了冲突的主要动员力量与支持基础。
最早受到种族利益驱动的冲突是阿拉伯部落联盟同富尔人争夺牧场和水资源使用权的冲突。它始于1987年,最初只是北达尔富尔的一些放牧骆驼的阿拉伯部落同迈拉山(Jebel Marra)北部富尔人之间的规模有限的冲突,但很快便因带有政治目的城市精英的介入而恶化。舆论宣传,特别是政府媒体的渲染强化也助长了这一冲突,且最终将所有阿拉伯部落拉向一方,而将所有非阿拉伯族群推向另一方:27个阿拉伯游牧部落结盟共同向富尔人和非阿拉伯部落宣战。正是在此次冲突中,双方首次把各自的认同确定为“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⑩
当时的报道已经把阿拉伯部落民兵称为“坚杰维德”,他们以其对富尔人和其他较小的非阿拉伯部落的袭击而闻名。富尔人也组成了自己的部落民兵,用退伍军人训练了许多民兵,并将他们作为自卫军部署在一些村庄。(11) 这次冲突使双方损失惨重。1989年5月29日至7月7日,冲突双方在苏丹政府的主持下举行了部落和平会议,双方在会议上均发表了种族化的主张。阿拉伯部落联盟代表指责富尔人通过驱逐阿拉伯人并拒绝让他们使用水源和牧场,蓄意扩大迈拉山周围的“非洲人地带”。富尔人代表则认为,阿拉伯人对他们的战争是受到种族主义推动的种族屠杀,其目的是摧毁富尔人的经济基础,并占据他们的土地。(12)
此次冲突还显露了此前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阿拉伯集会”(Arab Gathering)组织,阿拉伯部落联盟就是在“阿拉伯集会”的领导下,按照协调一致的政治和军事方式行动。作为当地种族关系重大转折点的“阿拉伯集会”是1986年出现的,来自27个阿拉伯部落的精英们在集会上宣称阿拉伯人是达尔富尔的多数民族,但是他们却被边缘化了。1987年10月底,该组织在给时任总理萨迪克·马赫迪的一封信中,23个达尔富尔阿拉伯人知识分子、部落首领和高级官员公开代表“阿拉伯集会”,呼吁中央政府解决阿拉伯人的边缘化问题。他们将达尔富尔地区在管理、宗教和语言等方面的文明成就归功于“阿拉伯民族”;他们抱怨阿拉伯人在中央、省和地区政府中的代表太少,要求在三级政府中分别给阿拉伯人50%的代表名额,以承认其人口分量、对创造地区财富和文化作出的贡献,及作为文明承载者的历史作用。(13) 这封信在苏丹引起了很大争议,受到了一些政党领袖和政治家的谴责。他们要求坚决打击这种新兴的种族分裂主义,以免给达尔富尔地区脆弱的社会结构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害。(14) 尽管信件几乎未提及非阿拉伯民族,却有阿拉伯至上主义的味道,因为它只将阿拉伯人当做达尔富尔地区宗教、文化和文明的承载者,且宣称地区财富中的最大份额是由阿拉伯人创造的。
“阿拉伯集会”的出现引起了非阿拉伯人的极大恐慌,他们普遍担心阿拉伯部落制定了一个用武力将他们赶出达尔富尔的详细计划。虽然“阿拉伯集会”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政治而非军事组织,其目的是保护阿拉伯群体的利益,但富尔人、扎加瓦人和马萨里特人等非阿拉伯族群有理由认为,阿拉伯集会的目的是制造种族分裂并破坏非阿拉伯族群的生活。(15) 无疑,在对“阿拉伯集会”的象征性战略意图的恐惧下,非阿拉伯民族自然也会开始其集体动员与结盟,而这些基于种族对抗的结盟被证明具有毁灭达尔富尔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的危险。
苏丹存在动员西部阿拉伯部落支持中部尼罗河河岸阿拉伯人事业的传统,这一点至少可追溯到19世纪的马赫迪革命时期。不过,较近时期对西部阿拉伯部落民兵的动员和武装却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尼迈里政府为阻止“苏丹人民解放军”对努巴山区的不断渗透而动员了名为“穆拉赫林”(Muraheleen)的民兵,这些民兵大多来自南达尔富尔的雷扎盖特部落。阿拉伯部落民兵的暴力活动并不仅限于南方战争地区,还延伸到达尔富尔南部。仅在1986年,“穆拉赫林”民兵便在南达尔富尔达艾因地区(Al- Daein)至少残杀了1000名丁卡人难民,但政府并未深究屠杀者的罪行。(16)
对“苏丹人民解放军”夺取达尔富尔南部地区进攻的成功抵抗表明,达尔富尔的阿拉伯部落民兵有不俗的军事实力。在1991年富尔人达沃德·波拉德(Daud Bolad)率领一支“苏丹人民解放军”部队攻入南达尔富尔后,苏丹政府既未动员军队,也未动员作为苏丹公民的其他达尔富尔人,而是动员主要由贝尼-哈勒巴部落成员组成的“富尔桑”(Fursan)民兵进行抵抗。“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占领图谋被“富尔桑”民兵粉碎了,而达沃德·波拉德帮助其富尔同胞对抗阿拉伯部落联盟的计划也归于失败。(17)
虽挡住了“苏丹人民解放军”的侵入,但政府却因对当地阿拉伯部落的武装和利用而播下了种族冲突扩大化的种子。1994年,苏丹政府重划了达尔富尔行政区域,将该地区由原来的南、北达尔富尔两省划分为南、北、西达尔富尔三州,富尔人及其位于中部的迈拉山区被3个州所分割。新的行政单位主要是在损害“非洲人”利益的情况下建立的,这使他们同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疏远,并激发了他们与“阿拉伯人”的冲突,1995—1998年马萨里特人同阿拉伯人的冲突即是典型之例。(18)
1995年3月13日,西达尔富尔州政府做出决定,将达尔马萨里特(“Dar Masalit”,马萨里特人的领地)划分为13个“阿玛拉特”(“Amalat”,意为封邑),其中5个被分给了阿拉伯部落。这一削弱马萨里特素丹权力的决定引起了马萨里特人的强烈不满,成为马萨里特人与阿拉伯雷扎盖特部落冲突的导火索。1995~1998年,该地区一直处于动荡和严重的种族冲突中。西达尔富尔州在冲突期间一直被苏丹政府宣布为“紧急状态”地区,达尔马萨里特的基层管理更是处于“真空状态”(19)。
显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达尔富尔冲突已超出传统的资源争夺范围,种族对抗成了冲突的主要特征。上述两类冲突的差别是巨大的:第一,早期冲突通常是部落之间的短暂冲突,而80年代中期以后的冲突则基本上是以种族为界的持久对抗,种族属性被用来号召同族的部落加入战斗。第二,冲突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早期的低烈度、间歇性和小规模的零星冲突转变为80年代中期以后的高烈度、持久性和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更多村落及设施毁于战乱,伤亡和难民人数不断攀升。第三,原本保持中立的政府因某些做法而间接卷入了冲突,这给2003年武装叛乱埋下了祸根。
基于权力与财富分享的当前危机
虽然目前的达尔富尔危机出现于2003年初,但是该地区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都持续着有组织的暴乱(如2001年北部阿拉伯部落对扎加瓦人的攻击、2002年图尔地区的富尔人暴动等),只不过专注于南北和平的苏丹政府和国际社会无暇或不愿顾及而已。2002年8月,北达尔富尔州政府曾在尼尔特特(Nyertete)和解会议上向富尔人的传统首领做出过安全承诺,可该承诺并未兑现,这进一步增加了富尔人的愤怒和不满。这类事件不断发生,达尔富尔人对政府逐渐疏远,有的人加入了尚在萌芽阶段的反叛组织。随后,这些原本只有本地要求而无政治主张的地方武装组织,便同流亡海外的有野心的富尔人和扎加瓦人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相互结合起来了。2002年3月,富尔人、扎加瓦人和马萨里特人在迈拉山区的布特科(Butke)召开了一个42人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联合运动,该运动主席一职被分配给了富尔人,军事指挥由扎加瓦人担任,副主席由马萨里特人担任,也就是说,参与目前叛乱的主要族体都在运动中拥有代表。(20)
就武装力量而言,除被称为“坚杰维德”的阿拉伯部落民兵早已被政府动员和利用外,参与反叛运动的富尔人、扎加瓦人和马萨里特人也在目前冲突爆发之前拥有了各自的民兵。而乍得内战和南方战争导致的小型现代武器流入使达尔富尔的这些部落民兵有了不同凡响的战斗力。
政治因素的介入或许是达尔富尔反叛运动出现的直接原因。20世纪末,在同巴希尔总统的权力争夺中落败后,图拉比及其派别被清除出了权力机构。一些因忠于图拉比而被“清洗”的达尔富尔政治精英心怀不满,并迅速变成了达尔富尔的所谓“自由斗士”,试图将达尔富尔变成争夺国家权力的又一个战场。“正义与平等运动”发起人卡利勒·伊卜拉欣(Khalil Ibrahim)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出任过“全国伊斯兰阵线”政府的部长,后因支持图拉比派别而流亡国外。此外,“苏丹人民解放军”对达尔富尔反叛运动的影响也不容置疑。正是在“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协助下,最初只是农民暴动的达尔富尔反叛运动被赋予了政治抱负。事实上,“达尔富尔解放阵线”就是受“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影响才改名为“苏丹解放军”的,它不仅采用了前者的“新苏丹”思想(21),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比前者更为激进。(22) 与此同时,南北内战因2002年7月《马查科斯协定》(Protocole de Machakos)的签署而出现了和平解决的曙光,这给了达尔富尔反叛运动通过武装斗争分得权力与财富的决心与信心。(23) 于是,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叛乱“适时”出现了。
2003年2月,主要由富尔人、扎加瓦人和马萨里特人组成的“苏丹解放军”和稍后出现的主要由扎加瓦人组成的“正义与平等运动”以苏丹政府忽视该地区的发展及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的袭击为由,公开向当地城镇的军事和政府设施及官员发动袭击,要求实行地区自治并分享财富。自此,以“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为一方,苏丹政府军和苏丹政府支持的统称为“坚杰维德”的民兵组织为另一方,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反抗中央政府的“苏丹解放军”迅速取得了早期的军事胜利,其队伍也迅速壮大到近万人。(24) 政府对反叛运动的反应由最初的震惊和犹豫不决迅速转变为武力平叛,政府军及其支持的“坚杰维德”民兵焚烧了数百座村落,使当地1/3的人口流离失所,这也是“苏丹解放军”能够得到当地人拥护的另一原因。然而,政治组织的软弱与政治经验的不足使“苏丹解放军”无法应对自身的迅速扩大,领导层的严重分歧使“苏丹解放军”很快陷入内乱,并蜕变为以种族为界的不同派别,而在经历早期与“苏丹解放军”的协同作战后,军事力量原本较弱的“正义与平等运动”则因内部分裂及与前者的冲突而实力锐减。(25)
当前,冲突双方进行过多次谈判,并达成了不少有名无实的协议或协定(其中包括2006年5月的《达尔富尔和平协定》)(The Darfur Peace Agreement),但当地的紧张局面并未得到彻底缓解,暴力、抢劫及其他非法行为仍然此起彼伏。
虽然目前的危机同样根植于一些长期存在的原因,但也有一些与以往冲突完全不同的特点:(1)冲突规模和范围扩大。以前的冲突都是少数部落或族群之间的局部冲突,而目前的冲突却是政府及阿拉伯民兵与当地最大的几个非阿拉伯族群之间的全面冲突,军事活动遍及北、西、南达尔富尔三州。(2)冲突烈度空前提高,这不仅是因为参与平叛的政府军动用了飞机等现代武器,还缘于“坚杰维德”民兵和反叛武装分别得到苏丹政府与外国势力的军事支持。(3)冲突给当地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迄今已有20多万人因冲突直接或间接死亡,至少200万人流离失所,被毁的村庄、农业资产、基础设施等更是不计其数。(4)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这是目前冲突独有的特点。邻近国家、非盟、联合国、西方国家、中国等有关各方,先后参与或介入了这一冲突的解决,非盟和联合国甚至派出了规模庞大的维和部队。(5)目前的冲突有与以往冲突完全不同的性质,属于政治危机,而这一点与目前冲突的持久性及最终解决直接相关。
结论:对于达尔富尔冲突性质的思考
达尔富尔冲突究竟是种族的,还是政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有些人,特别是西方人倾向于将非洲的政治暴力视为部族冲突的延伸和扩大,认为非洲国家的政治就是部族问题;反叛运动与政党一样反映的是部族关系,国家利益受制于部族利益。这样的看法很难经得住深入推敲,显然也不能应用于达尔富尔的目前危机。事实上,达尔富尔目前发生的是一场政治危机,而且日益从部族层面升至地区甚至国家层面。
虽然反叛组织出自达尔富尔的主要非洲人部落,但是其指导思想在本质上却是政治性的:维护全体达尔富尔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这样的主张很可能会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不管他们属于哪一种族。响应政府平叛号召的只是阿拉伯人部落中的一部分,因此,种族因素只是在“坚杰维德”参与冲突后才显现出来。“坚杰维德”主要由北部的阿拉伯部落民兵组成,其主要目的是获取他们缺少的土地和水,而实现此目的的代价是牺牲非洲人族群的利益,种族政治由此走到前台。西方的分析正是紧扣达尔富尔冲突的这一态势,并进一步提出了种族战争的概念,使原本属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达尔富尔冲突变成了种族问题。但是,达尔富尔危机仍是一场政治危机,其根源也是中心与外围的冲突。就此而论,达尔富尔危机触及了苏丹政治的核心问题,它正在由“达尔富尔问题”演变为苏丹的“普遍问题”及与政府对所有边缘化地区政策有关的“特殊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说达尔富尔冲突无种族方面因素。相反,目前冲突的确存在着种族因素。第一,苏丹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在历史上就存在着种族上的不平等,而独立以来的各届政府都有意无意地在全国推行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政策,有众多非阿拉伯人口的达尔富尔地区也不例外。第二,“坚杰维德”有很强的种族主义思想基础。20世纪末的“阿拉伯集会”组织曾为阿拉伯人获得更大权力设计了详细计划,其中就有建立在从苏丹东部红海沿岸向西一直延伸到达尔富尔中心地带的所谓“阿拉伯地带”组织(26)。第三,许多达尔富尔人已开始在种族背景下认识目前的暴力冲突了。当地的许多非阿拉伯人认为,他们之所以成为“坚杰维德”的袭击对象,是因为他们是“黑人”,而“坚杰维德”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清除出故土。
虽说目前冲突已在某些方面转变为种族冲突,但是将其归结为“阿拉伯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全面对抗却是不恰当的。认识到这一点对达尔富尔的未来至关重要,也是结束目前动荡的希望之一。事实上,加入“坚杰维德”的主要是北部某些阿拉伯部落成员及少数首领,更大、更富裕和更有实力的雷扎盖特、塔艾沙、马阿里亚、哈巴尼亚、巴尼-侯赛因等南部阿拉伯部落却并未参与“坚杰维德”的暴行。与此同时,博尔戈人、贝尔提人、博尔诺人、费拉塔人等多数非洲人部落也一直保持中立的立场。“坚杰维德”并不代表达尔富尔的阿拉伯人,这表明达尔富尔人还有和平共处的希望。从更为积极的意义来说,没有参与暴力冲突的部落可以担当卷入冲突的部落之间的“阿贾维德”(27),帮助争端地区维和部队的部署,甚至领导同反叛组织的政治谈判。
就本质而言,达尔富尔的目前冲突是一场政府及其动员下的阿拉伯民兵同叛乱者之间的战争,是无地部落对有地部落的纷争。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两个彼此密切关联的冲突:一个是政府军与反叛运动之间的冲突,其本质是政治冲突,且与苏丹的其他中心与外围冲突别无二致。这一冲突的解决方式也应是政治的,即眼前的政治和解和日后的法制与良治;另一个则是土地争夺战争,即“坚杰维德”民兵对非洲族群的战争。(28) 目前看来,后一个冲突既是国际维和力量的首要任务,也是令苏丹政府倍感头痛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希望难民返回家园,以便恢复当地的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坚杰维德”却因夺取土地之故而不愿让那些逃难村民返回家园。如此一来,作为盟友的苏丹政府和“坚杰维德”必然会产生矛盾与碰撞。
总之,达尔富尔问题的危险性的确很大。就目前而言,许多人的生命仍处于危险之中。长远看来,该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冲突隐含的资源、种族、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将使冲突久拖不决,并会影响到当地数百万人的生命安全。达尔富尔危机的持续还将伤及整个国家:它会破坏苏丹脆弱的经济,强化政府的强硬立场,并最终危及苏丹的持久和平与统一。可以说,没有达尔富尔的和平,就不会有苏丹的和平。
注释:
① A.De Waal,“Famine Mortality :A Case Study of Darfur,Sudan 1984-1885”,Population Studies,Vol.43,No.1,March,1989,pp.5-24.
② See A.A Fadul,“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for Sustainable Peace in Darfur”,in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as A Cause of Conflict in Darfur (Conference Proceedings),Africa Progress of University for Peace,Addis Ababa,2006,p.38.
③ See Musa Adam Abdul- Jalil,“The Dynamics of Customary Laud Tenure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Darfur”,Report of FAO Project OSRO/SUD/507/CAN,2004,p.12.
④ A.A.Fadul,op.cit.,p.35.
⑤ See Musa Adam Abdul- Jalil,op.cit.
⑥ 哈库拉(Hakura)意为“土地特许权或地产”,是指富尔国素丹为吸引移民、笼络人心或强化王权而将土地赐给某些贵州、宗教人士、商人及部落首领的一种制度。See O' Fahey,R.S.,State and Society in Darfur,London:C.Hurst and Company,1980; R.S.O' Fahey,M.I.Abu Salim and M.J.Tubiana,Land in Darfur:Charters and Related Documents from the Darfur Sultan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 Burr JM,Collins RO,Africa' s Thirty Years War :Libya,Chad,and the Sudan,1963-1993,Westview Press,1999.
⑦ Yousef Takana,“Effects of Tribal Strife in Darfur”,in Adam Al - Zeiu Mohamed and Al- Tayeb Ibrahim Weddai,eds.,Perspectives on Tribal Conflicts in Sudan,Institute of Afro-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Khartoum,1998,pp.195-225.
⑧ Adam Al- Zein Mdnamed and Al- Tayeb lbrahim Weddai,eds.,op.cit.,pp.195- 225.
⑨ 有关达尔富尔的族群及分布情况,请参阅姜恒昆、刘鸿武:《种族认同还是资源争夺: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原因探析》,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5期,第9~10页。
⑩ See Mohamed Suliman,Salah Al Bander,ed.,Sudan Civil Wars:New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1) See ibid.,pp.214-217.
(12) See Adam Al- Zein Mohamed and Al- Tayeb Ibrahim Weddai,eds.,op.cit.,pp.264 -267.
(13) See Hussein Adam al - Haj,“The Arab Gathering and the Attempt to Cancel the Other in Darfur”,December 31,2003,http :// www.sudanile.com/sudanile13.html.
(14) Ibid.
(15) See De Waal A.,“Counter - insurgency on the cheap”,London Review of Book,Vol.26,No.15,August 2004,p.5.
(16) See U.A.Mahmoud,Baldo S.A.,The Ed Daein Massacre:Slavery in the Sudan,Khartoum University Press,1987.
(17) See UNDP,Share the Land or Part the Nation:Roots of Conflict over Natural Resources in Sudan,Khartoum: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2003.
(18) See Nazik Al - Tayeb Rabah Ahmed,“Causes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Tribal Conflicts in Sudan”,in Adam Al - Zein Mohamed and Al -Tayeb Ibrahim Weddai,eds.,op.cit.,pp.139-159.
(19) Abusin Takana,A Socio- Economic Study of Geniena,Kulbus and Habila of Western Darfur State,Khartoum :Oxfam GB,2001.
(20) Se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Unifying Darfur's Rebel,p.2.
(21) “新苏丹”(New Sudan)是由已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主席约翰·加朗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的统称,其核心观点是在苏丹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世俗化的国家,全体苏丹人民不论文化、种族和信仰,一律平等。
(22) Se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op.cit.,p.3.
(23) Se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Sudan :Now or Never in Darfur,May 23,2004,p.1.
(24) 例如,“苏丹解放军”于2003年4~5月先后对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及库图姆(Kutum)和迈利特(Melleit)等城镇发动了袭击。See ICG,Sudan's Other Wars,ICG Africa Briefing,June 25,2003,pp,10-16.
(25) See Crisis Group Africa Briefing N°32,Unifying Darfur' s Rebels :A Prerequisite for Peace,October 6,2005,p.6.
(26) 作为分隔阿拉伯世界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个更大计划的组成部分,这条“阿拉伯地带”还将从达尔富尔向西穿越萨赫勒地带,并最终到达大西洋。See Victor Tanner,“Rule of Lawlessness:Roots and Repercussions of the Darfur Crisis”,Interagency Paper of Sudan Advicacy Coalition,January 2005,p.23.
(27) “阿贾维德”(Agaweed),是“长者”、“调停人”之意,是达尔富尔地区解决部落冲突的一种传统机制。根据惯例,冲突双方都会遵守并履行在“阿贾维德”调停下达成的和解协议,那些不接受“阿贾维德”裁决的部落会被其他部落小视。
(28) “坚杰维德”很少与反叛组织发生直接冲突,这或许是因为一方面“坚杰维德”无意与武装的敌人对峙,他们更喜欢从没有武装的村民手中安全地掠夺土地;另一方面反叛分子不愿同阿拉伯部落结下血海深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