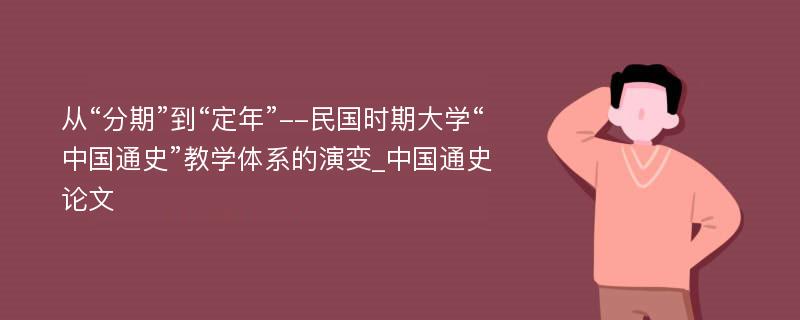
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时期论文,体系论文,中国通史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时期,一个较为完善的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一般由以下几类科目构成:一、通史(包括中国通史与西洋通史,也有设置东洋通史的);二、分期史或断代史;三、国别史;四、专门史;五、辅助科目(如目录学、金石学、考古学等)。其中,“中国通史”一科,是包括史学系在内的文学院各系的共同必修科目,一般由史学系教授讲授。对文学院其他科系来说,只需通过“中国通史”一门课的开设,使学生了解中国数千年文化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即算完成任务。但对史学系而言,既以培养高深史学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就不能像文学院其他科系那样,仅习一门“中国通史”了事,而需要将它再分为若干段落,以进行更详细、深入的学习。分段讲授的通史,实为史学系课程体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不但能满足学生对不同段落历史的学习兴趣,而且为专门史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但“中国通史”该如何分段讲授,不同时期情形不同,各大学史学系之间也很不相同。大略言之,20世纪20年代主要为“分期”讲授通史时期,同时有极少数大学采取“断代”讲授通史之法;进入30年代后,采取“断代”方法讲授通史的大学越来越多,而采取“分期”方法讲授通史的大学逐渐减少,从而形成两种通史讲授法并行的局面;进入40年代后,“断代”讲授通史之法彻底取代“分期”讲授通史之法,成为唯一通行的通史讲授法。
由于相关材料极为零散,且关涉数十所大学史学科系,上述问题自民国以来迄未有人提出并专门研究。笔者经过多年努力,搜集了大批档案等原始材料,愈发认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关系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如何演变的问题,而且关系以往一些作为大学教科书的“中国通史”著作的重新认识、评价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认真探讨一番。本文重点在前一方面,后一方面将另文论述,本文只略加讨论。至于中国历史当如何分期或分段,已超出本文范围,故略而不论。
“分期”讲授的通史体系
所谓“分期”讲授,就是将“中国通史”分为“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古史”和“中国近世史”四个时期讲授,从而形成一个讲授体系。也有不设“中国近古史”而分为三期的。就民国时期各大学史学系“中国通史”开设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系采用四期分法,只是每期名称及起讫时间有所不同。这种以划分西洋历史时期的时间概念来为中国历史分期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进化史观影响下产生的,始作俑者是19世纪末的日本史学家,以桑原騭藏所著教科书《东洋史要》(日文本名《中等东洋史》)最具代表性。①该书根据中国汉民族发展大势,参考旁近各族盛衰,分四期叙述:第一“上古期”,为“汉族增势时代”,“谓自太古至秦统一之间也”;第二“中古期”,为“汉族盛势时代”,“谓自秦统一至唐之亡”;第三“近古期”,为“蒙古族最盛时代”,“谓自五代至清之兴”;第四“近世期”,为“欧人东渐时代”,“自清初至今日”。②此书中译本在1899年由东文学社印行后,很快“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③其分期法也迅速被中国人接受,并为清末民初一些学校讲授历史,或一些学者编撰历史教科书时模仿或采用。如汪荣宝1904年至1906年在京师译学馆讲授清史时,所编《清史讲义》(又名《本朝史讲义》)中就明确承认,系采用桑原騭藏《东洋史要》的分期方法,以“太古至战国之终为上古史”,“秦至唐为中古史”,“五代至明为近古史”,“本朝创业以来为近世史”。④与此同时,一些由欧美人或日本人编撰的外国史教本,如《迈尔通史》、《万国史讲义》(服部宇之吉)、《西洋史要》(小川银次郎)、《万国史纲》(元良勇次郎)等,也开始在学校流行,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模仿西洋史分期法为中国历史分期。
在各大学当中,最早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时间概念来分期讲授“中国通史”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应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史学系。在1917年12月,即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恢复设置之初,⑤就曾召开课程会议,决定将通史分为四期讲授,即“中国古代史”(自上古至秦亡)、“中国中古史”(自汉至隋亡)、“中国近代史”(自唐至明亡)和“清代史”。⑥只是由于当时国史编纂处附设北大,“史学门”课程设置主要为分类编纂国史服务,侧重于专门史,如“经济史”、“法制史”、“学术史”、“地理沿革史”等,因而未能按上述分期法开设通史。⑦1919年夏,国史编纂处划归国务院,北大“史学门”也改为“史学系”,并开始逐步扩充各类课程。同年底,朱希祖主系后,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1920-1921年度起,正式将通史分为“本国上古史”、“本国中古史”和“本国近世史”三期,分别在第一、二、三学年讲授。⑧1921-1922年度也采用了同样的分期讲授法。⑨不过,在同一时间,在朱希祖草拟的《北京大学史学系编辑中国史条例》中,已将中国史分为四期,“拟分编中国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四种,划分时代,以专责任”。⑩1922-1923年度史学系课程因缺乏资料,不得其详。但至迟在1923-1924年度,已增“本国近古史”一期,从而成为四期。(11)此后数年,北大史学系一直采用四期分法讲授通史。(12)
北大史学系之所以采用上述分期法讲授通史,首先是因为主系者认为,史学“宜主进化说”,而非“循环说”,(13)“史学以时代相次,乃能明其原因结果,此乃应用科学方法整理史学者”。(14)另外,将“中国通史”分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与西洋史(或欧洲史、欧美史)各段对应讲授。故当时的北大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明确写道:“历史强分时代与强分国界,皆不适当。惟因教授便利起见,不得不勉强分割。然学习历史时,务期本国与外国同一时代之历史,详细比较。如学本国上古史,同时学外国上古史,得以两相比较其内容,则于史学乃能融会贯通。他皆仿此。故本系课程本国与外国同时代之历史,均排列于同一学年,学习时务宜注意!”(15)
作为最早设立的大学史学系,北大史学系的这个通史分期讲授法,对各大学史学系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此后建立的各大学史学系纷纷采用了这一办法。如中山大学史学系在其前身广东大学史学系时期,仅设一门“中国史”,并未分期。(16)1926年秋改为中山大学史学系后,首先开设“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和“中国近世史”,随后又增设“中国近古史”,从而形成四期。(17)1927年夏,成都大学史学系修订科目,也将中国史分为上述四期,其课程说明书与北大史学系如出一辙。(18)1928年春,第四中山大学史地系重订课程,同样将中国史分为上述四期。同年秋,第四中山大学史地系改为中央大学史学系后,继续实行这一办法。(19)厦门大学史学系在1928-1929年度第二学期首次开设“本国中古史”,1930-1931年度第二学期又开设“中国上古史”及“中国近古史”,虽然尚未形成体系,但可以看出采用的是四期分法。到1935-1936年度时又开设了“中国近世史”。(20)大夏大学史地系(或历史社会学系)约从1929年秋起到1934年前后,也分四期讲授通史,即“中国上古史”(战国以前)、“中国中古史”(自秦汉迄元)、“清史”、“中国近百年史”,其中“明史”一段一直没有设置,后两段名称也与其他大学有所不同。(21)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又有不少大学史学科系采用前述四期分法开设通史。如1931年秋在成都大学史学系基础上建立的四川大学史学系,继续实行原来的办法,至迟到1936-1937年度仍是如此。(22)河南大学文史学系至迟从1933-1934年度起,分四期开设通史,直至1935-1936年度。(23)北平师范大学于1934年秋公布《历史系课程标准》,“中国通史”也分为上述四期,分别在一、二、三、四年级讲授。(24)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则从30代初起至40年代初,一直将通史分为“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古史”及“清史”,(25)其中第四期名称略有不同。浙江大学史地系在1936-1937年度初建时,“中国通史”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世史”三期,1937-1938年度将“中国古代史”改称“中国上古史”,1938-1939年度又增设“中国近古史”,从而成为四期。(26)
也有少数大学分三期讲授“中国通史”,或由四期改为三期。如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1926-1927年度设有“中国古代史”、“中国中代史”,1927-1928年度改为“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1928-1929年度开设“中国近世史”,1931年公布的课程完整划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古中国史”、“近世中国史”三期。其中“秦以前”为“中国古代史”,“秦汉至一五一七欧洲商人东渐”为“中古中国史”,“一五一七至最近期间中国”(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近世中国史”。(27)之江文理学院历史系1930年时的课程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中世史”、“中国近代史”。(28)其中“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古代史”、“中国中世史”起讫不详。东北大学史地系1936-1937年度时尚分为四期,1938-1939年度时已改为“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世史”三期,直至1939-1940年度仍如此。(29)
与上述通史分期讲授法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流行的“中国通史”教本或参考书,也大都是按上述分期法编撰的,最具代表性者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30)、章嵚的《中华通史》、王桐龄的《中国史》、金兆丰的《中国通史》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等。其中章嵚曾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王桐龄曾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等校任教,吕思勉则长期在光华大学任教。
从几种著作的分期来看,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将中国史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31)章嵚的《中华通史》分为四编,甲编“上古史”,从黄帝前后至春秋战国;乙编“中古史”,从秦汉至隋唐;丙编“近古史”,从五代至明;丁编“近世史”,从满洲入主至民国胚胎。(32)王桐龄的《中国史》也分四编,第一编为序论及“上古史”,起于传说时代,止于战国时代;第二编为“中古史”,起于秦汉时代,止于隋唐时代;第三编为“近古史”,起于辽宋金对峙时代,止于明代;第四编为“近世史”,起于清室勃兴,止于清室衰亡,不过只印行了前半部分。(33)金兆丰的《中国通史》将中国社会状态的演进划分为“三世”:“自三五而迄姬周,曰上古;自秦而至隋唐,曰中古;自宋逮清,外交渐繁,事势所趋,莫能相遏,是曰近世。”(34)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正编分为五期:“上古史”(周以前)、“中古史”(从秦的统一至唐朝的全盛)、“近古史”(从唐朝的分裂到元朝的灭亡)、“近世史”(从明朝的对外到清朝的灭亡)、“现代史”(武昌起义以后)。(35)
在前四种通史中,“上古”部分的划分基本是一致的。“中古”部分看似起讫一致,实则不尽相同,章、王二著都叙至唐末,金著虽然分期截止到唐末,实则叙至“五季之乱”,(36)不够严谨。夏著未能完成,只写到了隋代,其“中古”下限也是唐末,但他在“凡例”中却又说:“本章原拟自晋迄五代,今所述自晋讫隋而止。”(37)可知夏著“中古”部分实际上是要写到五代,而非唐末。金、夏二著的“中古史”下限,显然都存在分期和实际叙述的不一致。“近古”开端,章著始于五代,王著实际也从“五代之更迭”(38)讲起,但分期却从“辽宋金对峙时代”开始,同样不够严谨。“近世”部分,章、王二著均从清初讲起,金著则以宋至清为“近世”,未立“近古”时期。至于吕著,除了“上古史”起讫与“中古史”开端,同章、王、金、夏四著一致外,“中古史”下限与“近古史”起讫,均与四著有很大不同。“近世史”下限与章、王、金三著相同,但开端与三著完全不同。“现代史”一期,则是其余四著都没有的。
此处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吕著正编分期,与他在“绪论”中所构想的分期,实际上有很大不同。他在“绪论”中特地写了一章,标题为“本书的分期”,目的是让读者在阅读具体内容之前,先对全书轮廓有一个把握。按“绪论”介绍,全书所分五期为:“上古史”(周以前)、“中古史”(从秦朝统一起到唐朝全盛时代止)、“近古史”(从唐中叶以后藩镇割据起到南宋灭亡止)、“近世史”(从元到清中叶以前止)、“最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39)与正编实际采用的分期相比,除“上古史”、“中古史”的起讫以及“近古史”的开端一致以外,其他各段完全不同。如此严重的漏洞,不是“疏忽”二字可以解释的,它实际上反映出吕思勉在撰写《白话本国史》时,胸中并无一个确定不移的分期标准,而这与他所采用的分期法是有关系的。(40)关于此点,笔者将另文论述。
“断代”讲授的通史体系
大学“中国通史”的另一种设置方法,是“断代”讲授,也就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若干大的段落来讲授,每个段落的起讫,基本上都是以一些王朝的兴衰为标志。“断代”其实也是一种“分期”,只是分期名称不像“上古”、“中古”、“近古”、“近世”那样,能够体现出一种历史演进的阶段来。当然,“断代”也不是简单地以“一姓兴亡”为标准,而是要考虑到一些重大社会变迁,如汉族王朝的统一、分裂,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等。正如梁启超所言:“旧时的断代,以一姓兴亡作标准,殊不合宜。历史含继续性,本不可分。为研究便利起见,挑出几样重大的变迁,作为根据勉强分期,尚还可以。若不根据重大变迁,而根据一姓兴亡,那便毫无意义了。”(41)需要指出的是,在断代讲授的通史体系当中,由于商周以前还有很长的历史时期无法明确断代,不少大学采用了“分期”讲授法当中“中国上古史”或“上古史”这一说法,用来统括秦以前的历史;也有采用其他名称的,如“史前史”、“秦以前史”、“先秦史”;或者干脆从商朝讲起,用“商周史”或“殷周史”等名目。另外,由于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极巨,因此也常常被作为“中国近百年史”、“中国近世史”或“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至于秦以后至鸦片战争前2000余年历史的段落划分,各大学有些差别,较为流行的划分方法为“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及“明清史”六段。
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采用通史断代讲授方法的,当属燕京大学历史系。该系约建于1919年,初由瑞士人王克私(P.de Vargas)主持,从1923年开始,由留美归国的洪业(煨莲)主持。在该系1924-1925年度课程中,已有“中国上古史”、“秦及两汉”、“中国近世史”三种科目。而在1925年5月公布的1925-1926年度课程中,已将通史划分为“先秦史”、“秦及两汉”、“三国及六朝”、“隋唐及五代”、“宋元”、“明”、“清史”七段。(42)此后,燕京大学历史系的通史设置一直是很完善的,只是段落划分时有不同。如1935-1936年度时,分为“中国上古史研究”、“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段。(43)1941年秋时竟多达九段,即“殷周史”、“春秋史”、“战国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辽金元史”、“明清史”。(4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西迁成都,由于师资不足,通史各段不能完整设置。抗战结束后各门课程逐渐恢复,1948-1949年度时又一度分为九段,即“商周史”、“春秋战国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辽金元史”、“明史”、“清史”,(45)但与太平洋战争前的九段有所不同。
继燕大历史系之后,辅仁大学史学系于1929年夏制订了新的课程制度,将“中国史”划分为六段,即“秦以前”、“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46)此后近20年中,辅仁大学的通史讲授一直采用这一六段分法,(47)这一分法也成为30年代以后各大学史学系最通行的通史断代讲授法之一。
清华大学历史系在1929-1930年度时仅设一门“中国通史”和一门“宋辽金元史”。(48)此后几年也没有追求“短期内能包括国史之各方面及各时代”,(49)直到1934-1935年度,方分为“中国上古史”、“秦汉史”、“晋南北朝隋史”、“唐史”、“宋史”、“明史”六段,(50)1936-1937年度又分为“中国上古史”、“秦汉史”、“晋南北朝隋史”、“隋唐史”、“宋史”、“明史”、“清史”七段。(51)北大史学系在1929-1930年度时已不再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分法,不过由于当时刚刚“复校”,师资缺乏,因此只开设了“中国上古史”、“魏晋南北朝史”和“清史”三科。(52)1930-1931年度设置了“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元史”、“中国近百年史”,作为“中国分代史研究”科目。(53)1931-1932年度设有“中国上古史”、“汉魏史”、“宋史”、“满洲开国史”。(54)从1932-1933年度开始分为六段,即“中国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此后一直到抗战前,北大史学系一直采用这个六段划分法。(55)抗战期间,北大史学系和清华历史系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通史仍然采取断代讲授办法,不过没有一个年度能够完整设置六段。抗战胜利后,北大史学系又“恢复了战前的制度”,(56)清华历史系则在1946-1947年度时将通史分为八段讲授,即“殷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或唐史)”、“宋史(或附辽金)”、“辽金元史(或元史)”、“明史”、“清史”。(57)
20世纪30年代以来,其他许多大学也都陆续采用了断代讲授通史之法。如金陵大学历史系1930-1931年度时将通史分为“先秦史”、“秦汉三国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元明史”、“清史”,也是六段,但与辅仁、北大所分六段不同。(58)武汉大学史学系30年代初分四段讲授,即“上古”、“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及清初”。(59)30年代中后期“中国通史”不分段,但另设“专史研究”一课,开设“上古史”、“宋辽金元史”等。(60)40年代初又分段开设,如1940-1941年度开设“商周史”、“汉代史”、“宋辽金元史”,1944-1945年度及1945-1946年度开设“秦汉史”、“宋元史”、“隋唐五代史”,(61)1947-1948年度又增开“上古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从而形成六段。(6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20世纪20-30年代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分期法讲授“中国通史”的大学,从30年代初开始,也逐渐放弃原来的分期法,转而采用断代讲授通史之法。除了上文提及的北大史学系外,齐鲁大学历史政治学系从1932-1933年度起改为断代讲授,不过它未能建立起完整的断代史讲授体系,到1937年夏为止,通史各段中,“明清史”仅开过一次,“先秦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则始终不曾开过。(63)中央大学史学系从1933-1934年度起改为断代讲授,(64)最多的时候分为八段,即“中国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史”、“元明史”、“清史”、“中国现代史”。(65)前四段与30年代的燕大、辅仁及北大完全相同,后四段中,三校均以“宋辽金元史”为一段,“明清史”为一段,中央大学则将“元明史”设为一段,“清史”单列一段,另将“中国现代史”列为一段,意在表明其对于近现代历史的重视。河南大学文史学系也从1936-1937年度起,放弃四期分法,改为断代讲授,当年设有“中国上古史”、“两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元明史”四段,另又设“清史研究”一科。(66)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情况稍稍特殊一些,1932年朱谦之主系后,一方面设置“文化史组”课程,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中世文化史”、“中国近世文化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另一方面又设置“世界史组”课程,将中国史包括在内,设“中国历代研究”一类,分为“殷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元史”、“明史”、“清史”八段。(67)在1938年秋广州陷落、学校内迁之前,文化史是经常开设的课程,此后则主要开设断代史课程。(68)
1939年秋,长期对大学科目设置采取放任政策的教育部颁布了《大学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令各大学实施。其中史学系必修科“中国断代史”划分为“商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或元史分设或元史与明史合授为元明史)及“明清史”六段。(69)此法令的颁布,成为各大学史学系最终放弃“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分期讲授法的转折。此后,更多大学采用了断代讲授法。其中东北大学史地系从1940-1941年度起改为断代讲授,当年设有“两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明史”;(70)1945-1946年度时设有“史前史及商周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辽金元史”、“明清史”及“中国近世史”等。(71)厦门大学也从40年代起改为断代讲授,分为“商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段,基本上与北大、辅仁等校相同。(72)浙江大学史地系1947-1948年度时,设有“商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史”、“元明史”六段,(73)缺“清史”一段。云南大学文史系1947-1948年度时设有“商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史”、“明清史”六段,缺“元史”一段。(74)贵州大学1947-1948年度时完整设有“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段。(75)
还有许多大学也都纷纷采用了断代讲授通史之法,但由于师资不足,中国史课程设置不够充分,因此难以形成体系,只能在不同年度根据师资情况讲授其中一段或数段。如西北大学历史系1939-1940年度开设了“史前史”、“商周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史”,(76)1946-1947年度时,除文学院共同必修科“中国通史”外,仅在历史系必修科中设置了一门“中国断代史”,意在因人设科。(77)福建协和大学历史系在1941-1949年的八个学年内,“明史”一次也未开过,“宋史”和“清史”各仅开过一次,“隋唐五代史”和“辽金元史”也仅开过两次。(78)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系在40年代初时仅设一门“中国通史”,而未能分段讲授。(79)复旦大学史地系1943-1944年度第一学期设有“中国上古史”、“宋史”、“清史”,1944-1945年度第二学期设有“春秋战国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1945-1946年度设有“宋辽金元史”及“中国近世史”,而到1946-1947年度时仅设一门“中国断代史”,其意也在因人设科。(80)暨南大学史地系1946-1947年度时除“中国通史”外,另设“中国断代史”及“中国近世史”,1947-1948年度史地系改为历史系后,开设了“商周史”、“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但到1949年夏为止,其他各段均未能开设。(81)光华大学历史系1945-1946年度时“中国通史”并未分段,1946-1947年度只是在“中国通史”外,开了一门“中国近世史”。(82)南开大学历史系1946-1947年度设有“魏晋南北朝史”、“宋辽金元史”和“中国近世史”,1947-1948年度计划增开“商周秦汉史”(或“隋唐五代史”),也未能形成体系。(83)
总之,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除极个别大学外,“断代”讲授通史之法已完全取代“分期”讲授通史之法,成为各大学史学系通行的通史讲授法。(84)
教本方面,20世纪30-40年代出版了不少很流行的通史著作,如缪风林在东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时编撰的《中国通史纲要》、在中央大学任教时新编的《中国通史要略》;邓之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时编撰的《中华二千年史》;钱穆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编撰的《国史大纲》;陈恭禄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任教时编撰的《中国史》;吕思勉在光华大学任教时编撰的《中国通史》;张荫麟为高中生编撰但在浙江大学任教时使用的《中国史纲》(上古篇);周谷城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任教时编撰的《中国通史》等。
上列通史教本特点各不相同,优点缺点并存,论者已多,无需赘述。其中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吕著《中国通史》在体例上与其早先所撰《白话本国史》完全不同。全书共分二册,上册以各种文化现象为题目,分十八章叙述;下册则“以时代加以联结”,分为三十六章,重点叙述各时代的政治兴衰史。在通史段落划分问题上,吕思勉也完全放弃了早先的分期法,他说:“今之治国史者,其分期多用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等名目,私心颇不谓然。以凡诸称名,意义均贵确实,而此等名目,则其义殊为混淆也。梁任公谓,治国史者,或以不分期为善(见中华书局刻本《国史研究》附录《地理年代篇》),其说亦为必然。然其分期,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当自立名目,而不必强效他人,则审矣。”(85)他生前曾计划撰写一个完整的断代史系列著作,可惜只完成《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四种。
吕思勉对其《白话本国史》分期法的自我否定,(86)一方面是其更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抛弃“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分期方法,在当时已基本成为史学界的共识。事实上,上列通史教本,虽然特点不一,但有一点相同,即在分期问题上,一律不再采用旧的分期法,而更注意按照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特点,来构建各自的通史著作体系。
对两种讲授体系的认识
在1941年出版的《西洋史教学之基本问题》一书中,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齐思和曾写道:“吾尝叩现今大学生以俾士麦究大约与吾国何人同时?有以为约在唐之中叶者,甚且以为盖与汉武帝同时者矣。吾又叩以美国革命之起,约当中国何时?有以为当在五胡乱华之时者矣。吾又叩以西洋中古之末,约当中国何时?有以为盖在秦汉之际者矣。此等中西史事年代不能连贯之弊,乃中国历史教育一般之通病,固非限于一部分学生。”(87)齐思和主要是从西洋史教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从中国史教学的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起由北大史学系率先实行的“中国通史”分期讲授法,实际上可视为一种试图“汇通”以观中西历史的大胆尝试,这是其最大意义之所在。应当承认,将同一时期的中西历史尽可能安排在同一时段讲授,对于比较中西历史发展的异同是有好处的,也能给人以启发。然而,分期讲授“中国通史”的困难和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基本上是王朝兴替的历史,而清末以来的“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时间概念,原本是用来划分西洋历史时期的,由于中西历史发展差异极大,因而当以这些时间概念来划分中国历史时期的时候,就不可避免陷于困难。比如,在西洋史中,“中古”(或“中世纪”)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用来指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所经历的一个约千年左右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教会势力极其强大,“呈现出一个试图在宗教基础上对自身进行政治结构建设的社会”。(88)而在中国,虽然也曾有过佛教较为兴盛的时期,但并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洋“中古”那样的历史时期。因此,在确定中国历史的“中古”时期的时候,就必须寻找新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很难确定,于是对中国历史“中古”时期的划分(尤其是下限)就出现了混乱,“近古”与“近世”的划分也相应地出现混乱。比如,北大史学系以秦汉迄五代为“本国中古史”,宋迄明为“本国近古史”,明中叶迄民国为“本国近世史”;(89)中央大学史学系以秦汉至南北朝为“中古史”,唐至元为“近古史”,明至民国为“近世史”;(90)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以秦统一至唐末为“中国中古史”,五代至明末为“中国近古史”,清初至民国为“中国近世史”;(91)四川大学历史系以秦汉至魏晋六朝为“中国中古史”,宋初至元末为“中国近古史”,明初至民国为“中国近世史”;(92)东北大学史地系以秦统一至五代为“中国中古史”,宋初至民国为“中国近世史”;(93)齐鲁大学历史政治学系以秦汉至一五一七年欧洲商人东渐为“中古中国史”,一五一七年至民国时期为“近世中国史”。(94)可见,除“中古”的起始(或者说“上古”与“中古”的分界)各校划分基本一致外,其下限以及“近古”与“近世”起讫,各校差别很大,可以说划分十分随意。像四川大学史学系,或许出于不该有的疏忽,竟将“隋唐五代”一段排除在“中国通史”之外。如此纷乱的分期,对通史讲授者而言,尚不是问题,他只需要认定一种分期法讲授即可;但对学者而言,耳目所及,既绝非一种观点,势将造成无所适从、难得确切知识的困惑。此种困惑甚且会因大学毕业者执教中学而延展弥散,影响不可谓不大。
其次,从学程安排来看,将“中国通史”按“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分期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将中西历史对照讲授,以便进行比较。因此,各大学一般都将“中国上古史”与“西洋上古史”安排在同一年度学习,其他各期历史也都一一对应,安排在同一时段学习。然而,由于中西历史发展进程事实上差异很大,加之对“中国通史”的分期很混乱,中西历史比较学习的目的实际上很难达到。比如,“西洋上古史”一般划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而“中国上古史”一般划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就已经截止了。到公元476年时(相当于中国南朝“宋”的末年),中国已经历了近700年的所谓“中古”时期,两者根本不在同一学年讲授,何来比较?又比如,“欧洲近世史”的起点,一般有四种说法: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15世纪“文艺复兴”开始、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近世史”的起点则有宋朝、元朝、明初、明中叶、清初、鸦片战争后等多种说法,与“欧洲近世史”相比,要么早500-700年左右,要么晚200-400年左右,又如何比较?还有,西洋史不一定全按四期划分,比如20年代的北大史学系采取的就是三期分法,即“欧洲上古史”(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欧洲中古史”(公元300-1500)、“欧美近世史”(1500-1918后)。(95)如此一来,若要中西比较,“本国中古史”与“本国近古史”近1900年的历史就不得不安排在同一年度,以便与“欧洲中古史”对应,而这在课时分配上是极不合理的。因此,北大史学系在课程安排上,事实上并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中西历史对照讲授。
再次,以划分西洋历史的时间概念来为中国历史分期,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受了“西方中心”史观影响的结果,这在确定“中国近世史”起点问题上体现得最明显。曾在中央政治学校及中央大学讲授“中国近世史”,并且编有《中国近世史》教科书的郑鹤声,在其书“编辑凡例”中说:“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二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以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96)这是典型的将西洋史的分期套用于中国史的表现。虽然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以上所言不无道理,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差异甚大,无视或轻忽这种时空差异,简单地依据西洋历史的发展进程来为其他国家、地区的历史发展分期,难免造成强分时代,乃至割裂历史的弊病。一些大学以明中叶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实际上就是受此种认识影响,从中西交通史的角度出发,特别强调了西洋传教士东来的影响。而在事实上,这种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且非持续性的,远不能和鸦片战争所造成的影响相比。(97)有的大学,如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以1517年欧洲商人东渐作为区分“中古中国史”与“近世中国史”的标志,更是无视中国自身历史的发展。该校为教会大学,历史政治系长期由美国人奚尔恩(J.J.Heerens)主持,如此为中国历史分期也不算奇怪。至于鸦片战争,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开端未尝不可。但如果说道光二十年前为“中国近古史”,此年后便是“中国近世史”,强分时代的痕迹仍不免太过明显。
综上所述,按“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分期法讲授“中国通史”,不但不能切实起到中西历史比照学习的作用,反而导致随意划分历史时期、强分时代乃至割裂历史的弊病,中国历史因此被分割得七零八落。而按照这种分期法编撰的通史教科书,也出现了同样的弊病,以至于像吕思勉这样公认的史学大家,在通史分期上也出现了严重的漏洞。正因为如此,这种分期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渐被断代讲授通史之法所取代,也就是必然的了。其实,对于这种分期法,梁启超很早就表达过不同意见,认为这种分法“不能得正当标准”,(98)“太笼统,粗枝大叶的”。(99)雷海宗后来又有更深刻的批评,认为西洋人将欧洲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的做法本身就有问题,这样的分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其中“上古”一段限于希腊、罗马,但随着19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进展,“地下的发掘增加了惊人的史料与史实,和出乎预料的长期时代”,“上古史”其实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西洋人这种不加深思的行动,到中国也就成了金科玉律”,“西洋人自己既然如此看法,我们也随着附和,还有可说;但摹仿西洋,把中国史也分为三段,就未免自扰了”。他又说:“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国人见西洋史分为三段,于是就把中国史也尔样划分。……以先秦时代为上古,秦汉至五代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代。再完备的就以宋为近古,元、明、清为近代,近百年为现代。此外大同小异的分期法,更不知有多少。……但西洋史的三段分法,若把希腊以前除外,还勉强可通;至于中国史的三段分法或五六段分法,却极难说得圆满。”(100)
以“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为通行分段法的通史讲授体系的最终确立,是在分段问题上充分考虑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特点的结果。不过,从通史讲授角度讲,断代讲授通史之法,也有其不易克服的困难。首先,中国历史悠长,不论将其分为八段、七段,还是最通行的六段,都要求有足够合格的师资,才能开设齐全。而在事实上,多数大学史学系并不具备此一条件,其结果是,断代讲授的通史往往不能形成体系,只能根据师资情况,因人设科,讲授其中一段或数段。而在一年一聘的制度下,教授流动又极频繁,结果是就连通史中的一段或数段,也难以定期讲授。自学生方面言之,所学不免零碎;自学校方面言之,也难以形成特色。
断代讲授通史的另一个问题是,纵使师资充足,但因各人讲授一段,“彼此各不照顾,进行先后既有不齐,又常是讲不完,所以六段都不相衔接”。(101)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北大史学系总结过去20年通史断代讲授经验时得出的结论。其实,早在30年代初钱穆针对数人合开共同必修科“中国通史”的弊病,就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在讲堂上明告学生:“我们的通史一课实大不通。我今天在此讲,不知前一堂何人在此讲些什么,又不知下一堂又来何人在此讲些什么。不论所讲谁是谁非,但彼此实无一条线贯通而下。诸位听此一年课,将感头绪纷繁,摸不到要领。故通史一课,实增诸位之不通,恐无其他可得。”(102)一门通史由数人讲授,尚且如此难以沟通,何况将通史分为若干段落,设为若干课程,由若干人来讲授,彼此的隔膜恐怕就更严重了。还好,以钱穆的能力,可以独自承担“中国通史”一门课的讲授,并编撰出《国史大纲》这样简明扼要很受欢迎的教本来。然而,作为共同必修科的“中国通史”,毕竟不能取代断代讲授的通史。所以,北大史学系仍要另将通史分作六段讲授,并且钱穆本人还一直承担着“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两段。(103)
北大史学系如此,其他大学更是如此。毕竟,在整个民国时期,真正能够以一己之力承担通史几个段落讲授的,只有邓之城、吕思勉、缪风林等少数人而已。因此,断代讲授通史,实为必要且不得不行的办法。也正因如此,如何解决通史各段沟通问题,始终是个难题。1947年夏,北大史学系曾专门开会,讨论“中国通史”分段问题,决定分为四段讲授,请余逊、邓广铭负责拟定具体办法。(104)其目的显然是试图通过减少分段,尽可能将通史各段打通。然而,至迟到1949年夏为止,北大史学系依然采用的是六段分法,直到50年代初才改为四段讲授。根据当时的课表,新划分的四段为:“先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元明清史”。(105)据称,“这一办法曾被许多大学的史学系仿行过,并认为有效”。(106)然而,减少分段,即意味着每段期限延长,也就意味着提高了对讲授者知识背景的要求。这对于少数师资雄厚的大学史学系而言,尚可勉强实施,但对多数条件一般的大学史学系来说,除了能稍稍缓解师资不足的困难外,于讲授效果上究竟有若何之进步,怕是很值得怀疑的。
结语
“历史的性质,是贯一的,是继续不断的,他如一条大河,是首尾连接的,是不能分成段落的”。(107)分期不过是为了讲授上或研究上便利起见。由于认识的差异、标准的不一,因而产生各种不同的分期。但历史又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无论以何种标准分期,都应当以尽可能尊重历史本身为前提。就中国历史而言,以闭锁的眼光看待它,无视它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互动,便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尊重;但若无视历史发展进程的时空差异,脱离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去看待它,同样是对它的不尊重。较为科学的分期,应当是充分考虑这两种因素的结果。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的演变,显然不仅仅是个分期问题,对如何认识与尊重历史,也是一种启发。近年来,有研究者又提出,应当用“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代”等时间概念来划分历史时期,以“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形态特征”,具体说来,“秦朝统一以前,可以称为上古(若仔细划分,还可以把先商文明叫远古);秦汉是中古早期,魏晋隋唐为中古盛期,宋元明清为中古晚期(或称近古时期);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社会进入近代时期”。(108)回顾历史,便可知道,此种分期法至少在时段起讫上,早已有之,并且早就被抛弃了。当然,倘能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确立一种客观的、令人信服的分期标准,则此种分期尝试未尝不可再加进行;倘若不能,则不免如20世纪20-30年代一般,徒增纷扰、歧义而已。
收稿日期:2010-09-20
注释:
①在中国历史文献当中,也曾出现过“上古”、“中古”、“近世”等名词。其中“上古”一般指有文字以前的历史;“中古”或指虞夏时期,或指商周之间,或指秦代;“近世”则无特指,一般用来表示距身所处不远的时代。这几个时间概念的含义,与清末以来它们的含义并不相同。至于“近古”一词,在历史文献中似很少使用。
②[日]桑原騭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上海:东文学社光绪二十五年(1899)版,第5页。
③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三年(1911)第5版,卷末,第1页。
④汪荣宝:《清史讲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94),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页。
⑤北大“中国史学门”于1909年秋开始招生,1910年春开学,学制3年,当时名为京师大学堂“中国史学门”。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1913年春首批本科生毕业后一度停办,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后恢复。
⑥《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第二第三次会议议决案》,《北京大学日刊》第15号,1917年12月2日,第3版。
⑦《文本科现行课程》,《北京大学日刊》第12号,1917年11月29日,第3版。
⑧《国立北京大学文科课程一览》(民国九至十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19029;《注册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702号,1920年9月25日,第3版。
⑨《史学系本年科目》(民国十至十一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869号,1921年10月19日,第2版。
⑩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编辑中国史条例》,《北京大学日刊》第869号,1921年10月19日,第3版。
(11)《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二至十三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302号,1923年9月29日,第3版。
(12)《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三至十四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l919029。《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四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19029。《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五至十六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997号,1926年12月4日,第4版;《国立京师大学校文科教员授课时数预算表》(民国十六至十七年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教育部全宗1057-476。
(13)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编辑中国史条例》,《北京大学日刊》第869号,1921年10月19日,第3版。
(14)《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学之课程并说明书》,《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第3版。
(15)《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三至十四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19029。
(16)《国立广东大学文科各系课程》,广东省档案馆,国立广东大学全宗31-1-10。
(17)《本校课程时间表》,《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2期,1926年10月,第20页;《各科概览》,《国立中山大学一览》,国立中山大学1930年版,第28页。
(18)《历史学系指导书》,《国立成都大学校报》第8期,1927年6月9日,第4-6页。
(19)《史地学系历史门课程规例说明》,《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民国十六至十七年度),国立中央大学1928年,第3-5页;缪风林:《中央大学历史系课程规例说明草案要删》,《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第1-4页;《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规则说明书》,国立中央大学编:《史学》第1期,1930年12月,第293页。
(20)《本学期文科新添学程》,《厦大周刊》第196期,1929年3月9日,第9页;《本学期各教员担任之功课》,《厦大周刊》第256期,1931年4月18日,第14-15页;《各学院教员每周担任学程时数表》(民国二十四年秋季),《厦门大学教职员暨学生名录》(民国二十四年八月至二十五年七月),国立厦门大学注册部1936年版,第4页。
(21)《学程纲要·史学系》,《私立大夏大学一览》(民国十九至二十年度),私立大夏大学1930年版,第20页;《学程纲要·史学系》,《私立大夏大学一览》(民国二十至二十一年度),私立大夏大学1931年版,第19页;《学程概要·历史社会学系》,《私立大夏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度),私立大夏大学1933年版,第43-44页。
(22)《史学系·课程纲要》,《国立四川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国立四川大学1936年版,第47-48页。
(23)《河南大学二十二年度第一学期大考日程表》,《河南大学校刊》第9期,1934年1月11日,第3版;《本校本学期开设学程一览》,《河南大学校刊》第81期,1935年9月9日,第4版。
(24)《历史系课程标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一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4年版,第136-139页。
(25)《文理学院课程纲要》,《私立岭南大学章则课程》(《岭南大学一览》布告第五十一号上编单行本),私立岭南大学1934年版,第128页;《本大学各院系开设科目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广东省档案馆,私立岭南大学全宗38-1-75。
(26)《浙江大学史地学系规程》,国立浙江大学史地学会编:《史地杂志》创刊号,1937年5月,第87-88页;《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史地学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六年度第一、二学期),浙江省档案馆,国立浙江大学全宗L053-001-3885;《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名册》(民国二十七年),浙江省档案馆,国立浙江大学全宗L053-001-3700。
(27)《齐大1924-1931年秋各学期授课时间表》,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J109-02-8;《1932-1937年齐大课程表》,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J109-02-79;《历史政治学系课程内容》,《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文理两学院一览》(民国二十年布告类第81号),私立齐鲁大学印刷所1931年版,第60页。
(28)《学程一览·历史学系》,《私立之江文理学院一览》,私立之江文理学院1930年版,第43-45页。
(29)《史地学系课程说明》,东北大学一览编辑委员会:《东北大学一览》,国立东北大学出版部1936年版,第9页。《史地学系学程号数及说明》,臧启芳编:《国立东北大学一览》,国立东北大学1939年版,第72-73页。《国立东北大学二十八年度课程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5677;《国立东北大学文理学院史地系课程单及说明一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5677。
(30)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初印于清末,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只写到隋末。1933年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之一印行,改名《中国古代史》。
(31)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学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5页。
(32)章嵚:《中华通史》(大学丛书)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目次”,第1-16页;同书,下册,1934年再版,“目次”,第1-12页。
(33)王桐龄:《中国史》第1编,北平:文化学社1930年第3版,“凡例”,第1页。
(34)金兆丰:《中国通史》,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2页。
(35)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4版,“目次”,第1-11页。
(36)金兆丰:《中国通史》,第87-94页。
(37)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学丛书),第2页。按:此处“本章”是指夏著第二篇第二章。夏著第一篇为“上古史”,分两章,第一章“传疑时代(太古三代)”,第二章“化成时代(春秋战国)”;第二篇为“中古史”,也分两章,第一章“极盛时代(秦汉)”,第二章“中衰时代(魏晋南北朝)”,此章原计划写至五代,实际写至隋。
(38)王桐龄:《中国史》第2编,北平:文化学社1928年再版,第1-32页。
(39)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0-11页。
(40)吕思勉还写过一种书,叫《本国史答问》,其中有个问题:“中国史之时期如何划分?”吕思勉的回答是,“可大别为四期”:“上古”(秦以前),“中古”(汉至明),“近代”(清),“现代”(革命起至现在)。(吕思勉:《本国史答问》,收入《吕思勉遗文集》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其中“上古”(秦以前)按一般的理解,是不包括大一统后的秦王朝在内的,可“中古”(汉至明)也没有从秦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统治王朝,竟然没有被纳入分期当中。而且,这个分期,无论是和《白话本国史》绪论的分期相比,还是和正编的分期相比,又都有很大差别。可见,吕思勉在中国史分期问题上,的确陷入了混乱状态当中。
(4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页。
(42)Announcement of Course(1924-1925),北京大学档案馆,私立燕京大学全宗YJ1924006;Announcement of Course(1925-1926),北京大学档案馆,私立燕京大学全宗YJ1924006。
(43)《私立北平燕京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课程一览》,私立燕京大学(第二十届布告第四十三号)1935年,第5-8页。
(44)《历史学系及研究部课程说明》,私立燕京大学(第二十六届布告第四十三号)1941年,第3-5页。
(45)《燕京大学课程》(民国三十七至三十八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私立燕京大学全宗YJ1948045。
(46)《各院系年级课程表》,《辅仁大学》(民国十八年六月订),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私立辅仁大学全宗1-4。
(47)《辅仁大学一览》(1926-1951),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私立辅仁大学全宗1-753。
(48)《文学院各学系学程·历史学系》,《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程一览》(民国十八至十九年度),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第33-34页。
(49)《历史学系近三年概况》(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二年),清华大学档案馆,国立清华大学全宗1-2:1-19。
(50)《文学院历史学系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度),国立清华大学1935年,第2-3页。
(51)《文学院历史学系学程一览》,《清华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页。
(52)《史学系课程》,《北京大学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第3版。
(53)《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九至二十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2470号,1930年10月16日,第2版。
(54)《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二十至二十一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0014。
(55)《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一至二十二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2012;《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3014;《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4009;《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5008;《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6015。
(56)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编:《北大院系介绍》,国立北京大学1948年,第28页。
(57)《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国立清华大学1947年,第22页。
(58)《学程纲要·史学系》,《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至二十年度),私立金陵大学1931年版,第40-43页。
(59)《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二十至二十一年度),国立武汉大学1932年版,第14页。
(60)《文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度),国立武汉大学1935年版,第26页;《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廿六、廿七年度),武汉大学档案馆,国立武汉大学全宗L7-1937-20;《国立武汉大学各院系课目表》(民国二十八至二十九年度),武汉大学档案馆,国立武汉大学全宗L7-1939-57。
(61)《国立武汉大学廿九年度教员名册》,武汉大学档案馆,国立武汉大学全宗L7-1941-21;《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课程指导书》(民国三十三至三十四年度),武汉大学档案馆,国立武汉大学全宗L7-1944-18;《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课程指导书》(民国三十四至三十五年度),武汉大学档案馆,国立武汉大学全宗L7-1945-41。
(62)《文学院概况》(国立武汉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之一),武汉大学档案馆,国立武汉大学全宗L7-1947-68。
(63)《1932-1937年齐大课程表》,山东省档案馆,私立齐鲁大学全宗J109-02-79。
(64)在中央大学史学系1932-1933年度课程中,尚有“中国通史(中古部分)”名目,1933年秋新开“秦汉史”,1934年春时已有“宋辽金史”、“元明史”、“清史”等科目,由此可知,中央大学史学系是从1933-1934年度起改为断代讲授通史之法的。参见《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一年度上学期),《中央大学日刊》第810-811号,1932年10月8日、10日,第24、27-28页;《史学系通告》(一),《中央大学日刊》第1028号,1933年9月9日,第898页;《注册组通告》(第三十一号),《中央大学日刊》第1159号,1934年3月3日,第1421页。
(65)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会:《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表审查意见》(民国二十八年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大学全宗648-2278。
(66)《本学期各院系开设学程一览》,《河南大学校刊》第135期,1936年9月7日,第2版。
(67)《文学院各系分述·史学系·课程》,《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概览》,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3年版,第60-65页;《文学院·课程》,《国立中山大学现状》,国立中山大学1935年,第93-94页。
(68)《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务报告》(民国二十七至二十八年),广东省档案馆,国立中山大学全宗20-1-5。
(69)《大学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教育部1939年8月12日第18892号训令颁发),《高等教育法令汇编》,重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42年,第309-310页。
(70)《国立东北大学送部审查资格教员名册》(民国二十九至三十年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2603。
(71)《国立东北大学三十四年度教员名册》(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2602。
(72)《文学院历史学系课程表》,《厦门大学一览》,长汀国立厦门大学1940年版,第31页。
(73)《国立浙江大学要览》(民国三十七年八月编),浙江省档案馆,国立浙江大学全宗L053-001-3825。
(74)《国立云南大学各院科系目表》(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云南省档案馆,国立云南大学全宗16-2-240。
(75)《国立贵州大学概况》(民国三十六至三十七年度),山东省档案馆,国立山东大学全宗J110-0101283。按:此件存国立山东大学全宗内。
(76)《1939年教职员授课时间表》,陕西省档案馆,国立西北大学全宗667-2-16。
(77)《课程》,《国立西北大学概况》,国立西北大学1947年版,第11页。
(78)《本学期各学科系目一览》,《协大周刊》第14卷第2期,1941年9月15日,第2页;《各科系开设课程》,《协大周刊》第16卷第2期,1942年2月23日,第2页;《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94;《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二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17;《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三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43;《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四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43;《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五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43;《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六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43;《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三十七年度教员名册》,福建省档案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全宗5-1-43。
(79)《私立岭南大学三十年度教员名册》,广东省档案馆,私立岭南大学全宗38-1-78;《私立岭南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广东省档案馆,私立岭南大学全宗38-1-78;《私立岭南大学三十二年度教员名册》,广东省档案馆,私立岭南大学全宗38-1-78。
(80)《国立复旦大学文学院史地学系三十二学年度第一学期科目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5712;《国立复旦大学文学院史地学系三十三学年度第二学期科目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5712;《国立复旦大学三十四年度第二学期教员名册》,复旦大学档案馆,国立复旦大学全宗819;《国立复旦大学文学院史地学系分年课程表》,《复旦大学一览》,国立复旦大学1947年版,第103页。
(81)《国立暨南大学三十五年度教员名册》(第二学期),上海市档案馆,国立暨南大学全宗Q240-1-603;《国立暨南大学三十六年度教员名册》(第一学期),上海市档案馆,国立暨南大学全宗Q240-1-606;《国立暨南大学三十七年度教员名册》,上海市档案馆,国立暨南大学全宗Q240-1-609。
(82)《私立光华大学三十四下学年度教员名册》,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私立光华大学全宗82-2-235;《私立光华大学三十五上学年度教员名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宗5-2688。
(83)《国立南开大学各学院概况》(民国三十六年),王文俊等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
(84)据笔者所见史料,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各主要大学中,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所开“中国通史”,依然坚持采用“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古史”、“中国近世史”的分期法,但到民国三十七至三十八年度时,也最终改成了断代讲授,当年开设的科目有“中国上古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国立师范学院呈报教职员名册及补报人事登记表》(民国二十九至三十六年),湖南省档案馆,国立师范学院全宗61-1-26。)
(85)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3页。
(86)吕思勉晚年谈及《白话本国史》时曾说:“此书在当时有一部分参考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94页。)虽未有具体说明,但对中国通史分期认识的改变,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87)齐思和:《西洋史教学之基本问题》,北京:函雅堂书店1941年版,第13页。
(88)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著:《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89)《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四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19029。
(90)《史地学系历史门课程规例说明》,《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民国十六至十七年度),国立中央大学1928年版,第6-7页。
(91)《历史系课程标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一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4年版,第143-144页。
(92)《史学系·课程纲要》,《国立四川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国立四川大学1936年版,第47-48页。
(93)《史地学系课程说明》,东北大学一览编辑委员会:《东北大学一览》,国立东北大学出版部1936年版,第9页;《史地学系学程号数及说明》,臧启芳编:《国立东北大学一览》,国立东北大学1939年版,第72-73页。
(94)《历史政治学系课程内容》,《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文理两学院一览》(民国二十年布告类第八十一号),私立齐鲁大学印刷所1931年版,第60页。
(95)《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四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19029。
(96)《郑鹤声自述》,转引自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2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97)顾颉刚曾将这一关于“中国近世史”开端的说法,归纳为民国时期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说法之一(另一种说法主张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足见在当时这种说法是很有影响的。(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9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7页。
(9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36页。
(100)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5页。
(101)《北大历史系概况》(1951年),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全宗2011951051。
(10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1页。
(103)《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至二十一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1930014;《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一至二十二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2012;《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二至二十三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3014;《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4009;《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5008;《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国立北京大学全宗BD1936015。
(104)《北大史学系系务会议及史学系五年计划》(民国三十六年),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全宗BD1947447。
(105)《历史系1951-1961教学计划汇集》,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历史系全宗9-13-3。
(106)《北大历史系概况》(1951年),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全宗2011951051。
(107)陈衡哲:《西洋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国难后第8版,第6页。
(108)《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