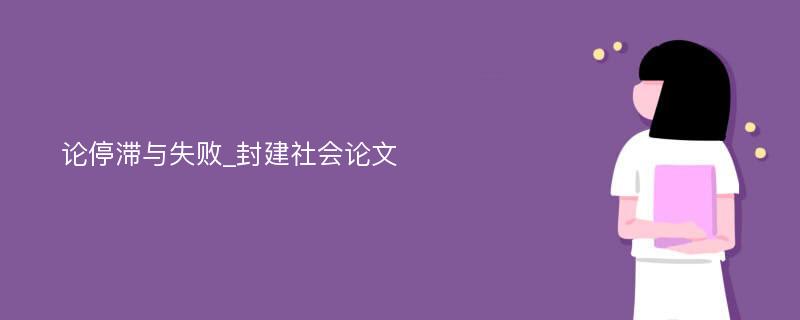
论停滞与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简单的负面看法可以归纳为:中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离,中国文化是从位居顶部的皇帝和朝廷向下贯彻,帝国政府是独裁和专制的,其教育体制建立在对指定的典籍进行死记硬背的基础上,它使得个人服从群体,因而根本上中国文明是没有能力改变自身的。一些人会说,中国直到面临现代西方挑战之际,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入死胡同。事实上,在欧洲海船16世纪抵达中国港口之前很久,中国就已经在现代性面前丧失了脸面。也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停滞,但仍然从积极方面来看待。正面的观点可能会指出:中国发展了一个独特的体制,在没有现代技术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它强调家庭观念,强调个人通过社会关系与他人相连;它发展了一套挑选人才的体系,使最有才能的人从政;它使政府负责教授共同遵循的道德观。它所做的都十分成功,比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成功,原因就是它对社会和谐的重视甚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但是,这种传统的制度却不适合于一个现代的民族。
“一个不变的中国”这种看法是怎么牢固地建立起来的呢?从欧洲来说,一个简要的答案是:这发生在史学理论遇到一个特殊的历史状况之下。在西欧从耶稣会士那里得知中国以前很久,西欧历史学家已经赞同旧基督教所信奉的“定理”:历史是朝着既定的方向行进,有其预先注定的进程。到18世纪和19世纪开始的时候,西欧的发展明显地非同寻常。知识分子在探讨是什么造成他们的时代不同于以往的时代,他们又是在朝哪里行进。人们把历史看作是进步的记录,将会显示理性的质询。黑格尔曾解释,为什么在阐明历史进步的理论时没有必要将中国历史考虑进去,他认为:“中国历史本身并没有发展任何东西,因此,我们不能够研究那个历史的细节。”兰克附和说:“时而有人把东方这个或那个民族(people)从上古时代继承下来的条件看作是一切的基础。但是我们不可能将永恒的停止不前的民族作为一个起点来捕捉和理解历史的内部运动。”相信停滞的中国无力使自己变革,这就是在说中国问题与学术探讨不相干,而这与17世纪甚至18世纪的一些欧洲人的想法正好大相径庭,那些人曾经认为中国的制度(如科举制度)、中国的思想(如新儒学)、中国的产品(如瓷器)值得学习,乃至模仿。
然而,为什么这种观点在中国也可能变得这样普通呢?尤其在今天,各个领域都在奋发图强,中国正在向外寻找其认为是更先进的样板及更先进的技术。我们不论是谈全球化还是谈现代化,都是指要照西方看齐,因为似乎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至少最近两个(有人说三四个)世纪以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欧亚大陆的西端及其延伸的新大陆(或新世界)在决定世界事务的进程。这么少的几个国家如此快速、如此不成比例地获得了财富,并且长时期地持续下来,将他们的势力扩张到其他民族的头上,这在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欧洲人相信他们代表着通向未来的唯一真正道路,这并非没有原因,不过要确信他们自12世纪或者甚至上古时代就已经行进在那条道路上,其理由则不充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可能不愿承认西方的道路是唯一的,也不愿承认西方是真理的唯一掌握者,但是实用主义地说,要争富强,除了向那些更富强的学习之外,别无他择。
怎样能够富强呢?西方社会理论家根据欧洲的历史拟出一定的方式来理解历史的变革,并解释要效仿现代西方需要做什么。例如,马克思论证,一个文明的发展应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的性质产生了阶级斗争,从而推动历史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他也认为中国已经停滞,脱离了轨道。这样一个关于进步的设想使得历史变为了一种竞赛,其中某个国家或姗姗落后或疾行在前,个中原因都可以找到解释。这个设想被传输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者作为指导思想,由于中国未曾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人则断言,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直到公元19世纪都是历史上的“封建社会”阶段。确实也有历史学家拒绝承认这一与中国历史不符的设想架构。有些则力图证实“资本主义萌芽”在16世纪和17世纪曾经存在。还有人论述,在8世纪至11世纪之间有过一个过渡时期。但是他们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使人们接受在11世纪和12世纪开始了“封建社会晚期”的这样一种概念。
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并不是历史从一个阶段进步到另一个阶段分期的唯一道路,也不是应用一个地方的历史经验为其他所有地方的未来创造出了一个处方。但是,认为所有民族的历史都是在同一道路朝着同一目标赛跑,却真成了问题。问题出在它引导我们依据现在(或者说,是依据当今的是非观念)来看待社会的历史以及社会的文化。设想一个国家在跑道上是否向着当代人所认定的终点前进,以此作为对过去进行判断的根据。例如曾经有过争论,探讨儒学是否阻碍了东亚国家转化为西方式的政治和经济,或者说,儒家强调教育或尊重权威这样一种价值观,事实上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传导性。我以为,这要看我们怎么给“儒学”定义了,我反而会说,不是儒学在支持经济,而是儒学受益于经济的增长。问题在于,如果以赢得现代化竞赛作为讨论的主题,那么我们并没有提出重要的历史问题:那些当时努力有所建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所想所为的方式又是怎么变化的呢?
这并不是说不应该比较,而是反对仅仅依据一个历史或者一个当今的社会作为标准来比较其他不同的历史。如社会科学理论的创始人韦伯正是因为想找出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出现的原因,而对中国和印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得出结论,儒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建立的压力制约从来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强烈,因为儒家的世界观是将帝国看作理想;它永远找不到最好的途径来为共同利益服务,因为它坚持的是个人对家庭的服从。而新教徒们却割断了家族关系的纽带,并制定了理性的法律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韦伯之后,又有人将西方优势的萌芽往古代追溯得更遥远,比如,欧洲人对于量化及精确测量的兴趣。有人干脆批评中国人只向内部看,不肯向外国学习。有人从制度方面进行解释:欧洲人发展财产权的概念,而其他人则没有。有人从经济方面进行解释:中国人没能控制人口增长,农业家庭的可耕田地因此而减少,或者说中国的国家机构汲取了过多的盈余。这些议论最终都归结于西方在近期所取得的成就。那我要反问,假使终止是在16世纪,那么我们是否也能以欧洲作衬托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富裕得多、组织得也好得多呢?
这样来进行比较有多重的危险,会假设一方代表的是历史发展的真正道路,另一方则脱离了轨道,代表了失败。一个危险是,若将历史看作是一条单一的跑道,这一设想是行不通的。说这绝不可能,原因很简单,因为世界上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另一个危险是我们开始制造一系列错误的二元论,其中中国被说成是被动的、精神的、偏重家庭的、专制的、被隔离的东方;与之相对的是主动的、物质的、个人主义的、民主的、开放的西方。但是,采用一个比较的框架却是一个好方法,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发现很多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比较框架的出发点,不是先假定存在着基本上的差异,而是询问双方有何相同之处,从而可以做一个有趣的比较。比方说,在一次马拉松比赛中,肯尼亚选手赢得了冠军,而美国选手失利。即使我们承认参赛对手来自不同的文化和地区,而就比赛而言,确实是这些选手之间的共同之点比那些不能跑的人更要多出许多。记住这点,那么我们就应当重点考虑,在那些相同的方面,肯尼亚选手又比波士顿选手有什么递增的优势。很可能,赢者差不多具有输者所有的条件,但也许他训练得努力一点,他的心跳快一点,他的肺活量大一点,他的腿长那么一点点,或是他的体重轻那么几盎司。就民族特征决定结果这方面来说,各个国家之间可能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而是在于机会与差距的递增。
事实上,为什么把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这样有趣,正是因为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我们所指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发达的政府机构、常备军、商业与城镇、税务、法律、宗教以及学界传统等。近来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经济史研究提醒我们,中国在维持世界上最大的统一的政治制度以及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等方面是很成功的。研究表明,直到18世纪,中国那些生产水平高的地区跟其他国家生产水平高的地区极为相似。同时也说明,进行历史的比较,前提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若非唯一的欧洲历史发展式的道路,便是停滞不前。造成这一切差距的原因,也可能是欧洲得到了开拓新大陆这一机会。
以这样的思路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对经济发展进行比较,起码是要设想一个不变的中国会比以往都更难行得通了。这些比较显示,对于西方为何能突飞猛进的解释,其实与发展的长期模式、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可能都没有什么关系。而我们还不应忘记,中国并非与欧洲各国竞争。在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要保持比北方边疆的强大的军事化的部落联盟和国家更先进一步。此外,在参与对外贸易方面,中国商人似乎不存在与国家竞争的问题,在16世纪以前可能都是这种状况。在16世纪,现代世界经济开始形成,大批中国商人居住国外,但是他们不是殖民者,而是移居到人口已经比较多的国家。不论我们是否认为存在一个在欧亚大陆运作的世界经济系统,我们都应当认识到,追溯中国介入更广泛的世界这点很重要。世界史的研究必须要重视东亚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然而,一直到了19世纪,中国政治精英们的意见才趋于一致,认为中国必须与西方(及日本)竞争。
尽管如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历来十分重视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很久以前就承认历史上有胜者败者之分。正如西方史学史近来有一种传统,寻求解释西方为什么在世界上取得了优势,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一种传统,即解释中国为什么(或怎样能够)更优于与之为邻的部落民族,这些人在西方被称作“野蛮人”(barbarians)。8世纪在欧亚大陆的东端,中国史学家杜佑在谈论到相对于中原内地的周边防御时,禁不住从他最熟悉的世界发出感叹:“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至于“夷狄”(周边民族)之中为何“不生圣哲”,他的解释是“其地偏,其气梗”,归结为地理所致。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过去两个世纪,曾经可以居于其中而沾沾自喜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改变。一旦全球化,中国不能只是再把自己与其近邻来对照,也不能继续用自己理想的上古来衡量,上古在过去许多世纪中曾经作为完美国家的典范。现代西方和日本变成了跟中国对比的参照和借鉴。正是在这个语境之下,竞赛中“失利”的意识在中国获得回响,而中国的历史则变为垂死的“封建社会”的记录。这改变了与过去有关的一切。其中一个结果是,宋明理学这样的思想体系不被看作是旨在转变个人与社会的哲学,而是被“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
标签:封建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