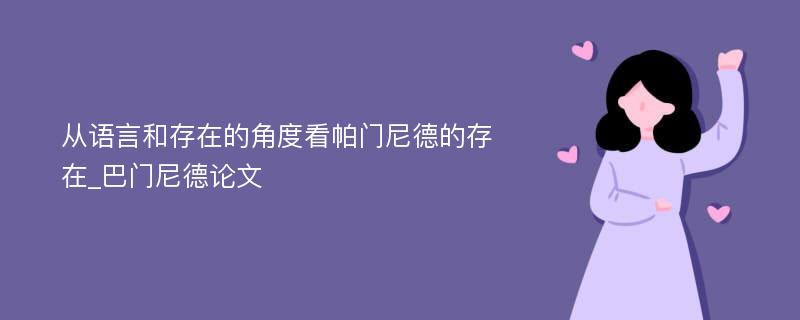
从语言与存在的维度看巴门尼德的Being,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语言论文,看巴门尼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2.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9)03-0049-07
黑格尔认为,只有当巴门尼德提出Being概念时,西方哲学史才真正开始。Being始终是西方存在论(ontology,又译本体论)的核心范畴,实际上也是整个西方认识论的基础。Being的显现涉及认知过程,Being的言说涉及语言结构,所以贯穿西方哲学史的存在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三阶段就在Being之中自然而然就内在地衔接起来了。Being汉译为“存在”或“是”,其实是对Being理解的两种诠释:作为合对象的“存在”和作为合逻辑的系词“是”,“是”的逻辑意蕴已经使Being从一开始就兼有知识论的意味。对Being的词源探索和逻辑分层是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很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怎样把Being放到西方哲学的学理发展语境中去审视,梳理出一条清晰而不简单,深刻而不繁琐的理路,仍然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一、Being作为思维对象
哲学的开端大约有三种方式:第一是从经验开始,经验论、反映论都是这种方式,初看起来这是最为自然的方式,但哲学所追求的是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而经验事实永远只是偶然事实的呈现,用康德的话说:“经验虽然告诉我们某物是如此这般的状况,但并不告诉我们它不能是另外的状况。”[1]胡塞尔在《观念Ⅰ》一书中一开始就探讨本质与事实问题,认为哲学所探讨的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eidos)而不是偶然被给予的经验事实。所以经验除非像在康德哲学中一样受到先验框架的整合和统摄,否则,无法成为真正知识的源头。第二种哲学的开端方式是从自我意识开始,这是最为明晰和顺理成章的方式,这一方式首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胡塞尔的“世界在意识中的消融”和整个现代主体主义哲学皆循着这条思路展开。从有限的外在经验开始推导出无限知识的思路陷入从单称判断到全称判断的归纳逻辑悖论,而自我意识则是无需前提假定的绝对自明呈现者。但自我意识与终极存在的内在关系如果不得到解决,个人自我的有限意识如何能成为绝对知识的起点仍然就是一个危及主体主义哲学的致命难题。因此也就存在着第三种哲学开端的方式:从绝对者开始,这种最为艰难的开端方式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巴门尼德,从Being开始,其次是斯宾诺莎,从神—自然开始,再次是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开始,但这种绝对存在通过何种自明性而进入人的意识过程是一个谜,似乎只有天启和灵感才能解释这种惊世骇俗的哲学起点。
巴门尼德的Being承“始基”之终极追求,但却超脱了水火土气等始基的质料性,与毕达哥拉斯相近,巴门尼德把始基由一种感觉对象转化成为一种理智对象。而且巴门尼德更进一步把毕达哥拉斯之多的并列抽象属性——数发展为一的抽象存在性——Being,但这种抽象性中仍然保留了丰富的内容,当然这些内容也是作为理智对象而不是感性内容,巴门尼德更确信逻辑的推论而不是感觉的呈现,后者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2]18。巴门尼德残篇中所列举的Being的五种特征,也唯有通过这种逻辑语言的方式才得以理解。第一种特征是永恒性,不生不灭,这明显与感觉世界的花开花落,月亏月圆相矛盾。但从理智的角度讲,如果Being是被创生的,那就一定有一个不是Being的Being产生了Being,这个Being要么是Being自身,要么是non-Being,因为Being不可能是别的。如果说non-Being产生了Being,就是说无中生有,这是违背逻辑的(当然后来黑格尔提出“纯有就是纯无”,海德格尔关注东方思想中无的本体论,已是另外一种层面上的东西),因此只可能说Being自身产生了Being,同样是说Being不生不灭。第二是说Being连续不断,不可被分割,经验世界中个物的多样性和可分性是常见的事实,但深入地从纯思维的角度看,犹如后来笛卡尔在《哲学原理》所言,物的广延是有限的经验空间,可以像切割豆腐一样的分离,但真正的空间是作为有限广延物的背景视阈,是一个联续为一的整体,无论如何无法被切割开来[3]。其第三个特征是不动,这更与日常经验中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截然相反。但与前两个特征一起来看,就成为一个可理解的东西了,Being是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一,尽管是后来麦里梭才明确补充说Being是至大无外的“一”,这种思想也可以从巴门尼德那里推论出来,如果至大无外,连续不断,那就肯定没有运动的空间,因此它只能是静止的,而且在古希腊人的心中,运动变化者不完善,完善者不运动变化。第四个特征是Being是球形的,更是体现了Being是一个思维对象而不是一个感觉对象的特征,人们莫名其妙Being怎么会是一个球形的,其实这与古希腊文化信仰密切相关,古希腊人坚信完善者一定是球形的,因为从中心到任何一处边界距离都相等,如果不相等,那就会出现缺陷,所以球形不过是完满性的一个形象代名词而已。很多人由此分析出巴门尼德Being是一个有限物,还是弊于感觉形体而未达到纯思对象。第五个特征乃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即是说“只有它才能被思维和言说,才能拥有真实的名称”。不能被思维和言说者能以何种方式呈现,一直是哲学的亘古难题。我们能言说和思维存在者,我们无法思维和言谈不存在者,反过来说只有能被我们思维和言说者才能成为哲学意义上的存在,那不能被思维言说者在能何种意义上被说成是存在呢?宇宙世界包括科学的对象等观念,究竟是一个感觉对象呢还是一个思维对象?很明显是后者。巴门尼德探讨的虽然是存在,但这个存在从一开始就具有认识论和语言学的维度。
二、Being的语言逻辑特征
Being作为一个哲学术语很晦涩思辨,但它的语言学开端却非常明晰。巴门尼德所使用的系动词eime,其现在直陈式单数第三人称是estin,即英文的it is,所区别的是estin作为系动词,没有主语,也可以说包含主语于自身之中,但语义结构基本可以通过英文it is而表现出来。在it is something句式中,Being就是其联系动词is的名词化形式,当我们不去意指it is a horse,it is soil句式中的宾词horse和soil,也就是说如果当被谓述的宾词处于隐蔽状态的时候,我们意指is本身,它就成了Being。比方我们进入河外星系,看到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它不是星云,它不是恒星,也不是行星,也不是卫星,但它是一个是——it is,其后面的something被悬置了,我们就仅仅在言谈it is,它是一个是,也就是它是一个存在。我们的判断都是把一个个特殊性涵括在一个更为一般的概念之中,例如我们问“苹果是什么?”回答是“苹果是水果”,那么“水果是什么?”“水果是食物”,进一步“食物是什么?”“食物是物质”,“物质是什么?”“物质是不是精神的某种东西”,“东西是什么?”“东西是…?”东西这种包容性最大,特殊性最小,语言尽头的东西,就接近存在了,它就是一个是,而不是是什么,它唯一的对立面就是不是,也就是非存在。
Being是哲学的真正核心主题,其外延要大于物质概念。Being乃是剥离了宾词的具体内容而单单言谈谓词本身的“是”,它不是指“It is something”中的something,而就是指“It is”的“is”,它不是指是什么,而是指“是”本身。它是语言言说的极限之处的最大包容者,而说“世界是精神的、物质的”所涉及的已经是“是”之后的宾词。Being既是“是”又是“在”,具有合逻辑与合对象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它作为系词,所涉及的是合逻辑、合句法、合内容的一贯性,巴门尼德的著名命题“只有‘Being’存在,‘non-Being’不存在”,所意指的是只有合乎逻辑的话语才能被有意义地言说。亚里士多德解释为:同一个东西不可能同时既是又不是,这是最为确定的公理[4]737。例如不可能同时既方又圆,这是对赫拉克利特“我既是又不是”的经验流变的逻辑否定,奠基了矛盾律——即某个命题的反面不可设想的基本思想。柏拉图也认为一旦把巴门尼德曾指明的一种经验物理现象转变成一个逻辑原理,不可能言说非存在就成为真理了[5]。杨适认为:“巴门尼德的最大功绩,在于他抓住了确定性紧紧不放,开创了希腊哲学人的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存在是确定的和静态的。”[6]D.Sedley在《巴门尼德和麦里梭》一文中认为巴门尼德的真理寻求之路有三种方式。[7]第一条道路是真理之路,Necessarily it(Being)is(“存在”存在,“是”是)。巴门尼德认为唯有通过这条路径,才能够把握住真理,而这事实上是在述说逻辑的同一律:A=A,Being一方面作为言说的真理对象,同时又作为真实的存在对象,如果我们把这三条真理寻求之道看成是正反合三一式,那么这第一条路就是正题:“For only Being can be spoken and thought(只有它能够被言说和思考)”。第二条道路是:Necessarily it(Being)is not,non-Being is(非存在存在,不是是),这是一条谬误之路,因为说非存在存在,不是时,违背了逻辑的非矛盾律,A≠non-A,这第二条道路所言说的是思路的反题:你不能认知那不存在的东西,也不能言说它(For you could not know that which is not,nor speak of it)。言说非存在涉及逻辑悖论,就是言说一个不可言说者,比如言说“无”,我们所言说的无,只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对不可被言说的意指,它只是“有”的一种否定和思维极限,并不能作为直呈的意识现象而呈现,本体论上的“无”更是无法进入意识和语言。第三条道路是:It(Being)is and it is not(既是又不是,既存在又不存在)。这是对赫拉克里特我既是又不是,我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经验流变的否定,它事实上是在言说的是排中律:要么A要么非A,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要么是要么不是,而不可能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是又不是,这也是思路的合题:能存在者和能被思维者是同一的(It is the same thing that can be and can be thought)。
Being的逻辑和语言特征对理解西方哲学的存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存在从巴门尼德开始就不是一种纯粹的感觉给与物,它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理性和语法的特征,除非是具有合理性的东西,否则它即使是在感觉中被给与了,也不配被称作存在,如神秘现象和气功,因为得不到后伽利略实证物理学的支持而不能被定义为真实,幻觉、梦境和UFO等也同样地被真实地感觉过,但同样因为得不到理性论证的支持而不能被人们接纳为真实。而科学的世界是一个能够用方程式来描述和计算的标准化的世界,科学地发现也绝不是一种感性的直觉发现,而是对某种感觉现象的理性定位,例如是哥伦布发现美洲而不是土著的印第安人。Being还告诉我们,我们的世界和宇宙概念不是一个感觉的给与物,无穷不尽的时间和无边无际的空间不是一个被感觉到的对象,康德后来严格地区别了经验的广延(空间)和持续(时间)与纯粹先验的时间空间概念,经验的广延和持续是杂多、分离和有限的,而纯粹时间空间本身则是同一、连续和无限。从空间上讲,人们直接感觉所给与的空间只有意识空间的亿万分之一;从时间上讲人的意识活动是一个回忆过去、感知当下、预期未来的连续整体,对过去的回忆,是对感觉材料进行逻辑与内在时间的梳理和有序化,因此逻辑与历史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难题;对未来的期盼中渗透了理想的追求、意义的设定和生存的筹措;即使对当下的感知,也渗透了时空与价值的整合与统摄,如康德的时空观和胡塞尔的“共现”(appresentation)理论所阐释的一样,一个完整的对象是意识填补了直观感性给与的时间空间间隙而建构出来的。因此一个看起来十足的外在对象,其呈现渗透了主体自我的意识成分。
总之Being是一个既合逻辑性又合对象性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外在物。它是被感知被言说了的存在,是进入了人的意识,进入了句法和逻辑结构的世界,被赋予了意义与价值的世界,而不是像黑洞一样的一个存在着的“无”。马克思也说“自然,抽象地就其自身并固定地与人脱离地理解,对人来说什么也不是”[8]。语言的可言传性、可分析性、可持存性、可无限复制和反复呈现性内在地属于这个世界。感性经验世界的模糊性、私人性和当下性,因为进入语言世界而获得了明晰性、公共性和永恒性。只有语言世界才具有陈述式、否定式、和疑问式,事实世界没有否定式和疑问式,也没有应然和虚拟。只有在语言世界里,才有应然、单复数、才有主动式和被动式,也才有虚拟语气。Being作为一种超越事实经验的语言逻辑层面的对象,要求句法形式、逻辑一贯性和内容融通性。首先,进入语言的经验事实必须是合乎句法的,“车撞约翰”或“约翰被车撞”与这个句子被去掉所有句法结构之后的所留下来的纯粹内容:“撞,约翰,车”是完全无法被清晰地理解的。一连串毫不相干的语词拼凑在一起,没法传达一个整体意义。除此之外,还需要有意义的逻辑一贯性,例如,“他走进一座棕色的白房子”,在意义的逻辑一贯性上出现自相矛盾,因此也不能被正确地理解。最后,我们可能成功地提出句法上正确而又逻辑上一致的陈述,但这些陈述还是有可能无效,因为它们的内容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如:“那棵树只会讲一种语言”,树和语言被误置于一种错误的联系之中[9]。没有被言说的存在处于晦暗遮蔽的状态下,海德格尔认为“在没有语言的地方,比如,在石头、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便没有存在者的任何敞开性”[10]57。
因此Being本身就包含着命题结构,尽管它不仅仅是语言命题。命题结构和存在结构从巴门尼德的Being那里开始,就具有内在交融的关系,这也是西方哲学史上存在论与认知论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的具体呈现。存在不是一种杂乱无章的经验给与物,它内在地含藏着合语言与合逻辑的有序性,无论这种有序性是源自一种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的或者黑格尔式的宇宙理性,还是笛卡尔和康德意义上的人的主体理性的建构,抑或是马克思人化世界的实践建构。于是世界内在地具有某种可以传达和理解的结构(form),现代意义上有序结构的信息(information,词根form)传达,作为实存世界的一种根本特征也就获得了一种哲学基础。
正是Being的这种特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西方文化和哲学乃是一种合乎理性的言说,分析理性一直深深地渗透进西方文化的骨髓之中。以希腊语拉丁语为源头的西方语系总体而言呈现为:语法分层细腻,逻辑表达确定,语态上的主动被动,时态上的过去现在将来,名词的单复数,代词的主宾格等都明确分离,这为后来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分析奠定了坚实的思维基础。汉语说“孩子在操场上玩”看不出单复数来,而英文要么说“A boy is playing on the playground”,要么说“Boys are playing on the playground”,开口言说就必须有清晰的单复数意识。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引述了智者论证钓鱼的繁琐但明晰的思维过程,这些繁琐的推论相比于中国文化中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朴实严谨、逻辑清晰、便于操作。这种由逻辑语言奠基的文化显得刻板僵硬,它依托于逻辑的“是是”,“不是不是”,用中国传统的话说是“实则实,虚则虚”“天道无欺”,而进一步涉及人事和特别是兵法,“兵不厌诈”,则“实则虚,虚则实”,也就是逻辑的“是不是,不是是”,而中国人的智慧则是超越这种“是是”,“不是不是”;“是不是,不是是”的逻辑规定性,比方诸葛亮让关羽在华容道点火引曹操,空城计中的城头弹琴退司马,既是“是是”,又是“是不是”,完全超越了逻辑的言说和推理。
三、Being——语言与存在的关系
在中国文化中,“名者,实之谓也”,语言相对于实在,一直是一种次生层面的东西,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巧言令色、纸上谈兵一直是为人所不齿的贬义词。而在西方文化中,语言一开始就具有存在论的优先地位。《圣经·创世记》记载耶和华创始的第一句话是:“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约翰福音》的第一句话是:“太初有道(word,即语词),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希腊哲学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Being、苏格拉底的定义和柏拉图的idea开始,就确立了语言概念的普遍必然性优先于感性经验的偶然性的先验路向。也正是因为语言逻辑的这种优先地位决定了西方文化的法律制度、社会规则的超验神圣性。语言其实有三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其描述性功能,陈述句所作的就是这种描述性功能,比方说“这是一张桌子”,的确是先有桌子的事实而后有陈述句的描述;但语言不仅仅是陈述句,还有疑问句:你是一个大学生吗?大学生不是一种实然的对象而是一种标准,这时的语言在执行其第二种功能:规定性功能;除此之外,语言的第三种功能是其执行性功能,祈使句就是如此:“起立!”“对不起”,它们并没有描述一个什么既有的事实,而是语言本身在执行一种功能。
Being使我们知道哲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赤裸裸的外在物,但同样,哲学也不仅仅是在研究语言和逻辑,否则哲学就成为逻辑学了。尽管语言分析哲学认为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一直试图穿透语言,而达到语言背后的一个非语言的支撑者的观点是一种根本的错误[11],但哲学所一直从事的就是要用语言去触及一个语言背后的终极支撑者——因为语言意识是非自足的。关于语言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大约存在着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客观主义和朴素实在论的观点,它们把语言意识看成是一块透明的玻璃,尽管人们要透过语言意识而达到存在,但存在却是直接穿透语言意识而显现给我们。于是我们并不是在看语言意识,而是透过语言在直接看存在本身,因此语言意识可以被完全悬置掉,它只是罩在存在上面的一块透明玻璃而已。但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语言意识的功能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比方2007年陕西镇平县的虎照事件和1963年美国登月舱的报道,很有可能就不是一块通达实在的透明的玻璃。基于此,就自然会出现与上述第一种观点截然对立的第二种观点,即认为语言意识是一种决然阻隔语言与存在关系的障碍物,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我们根本无法透过语言意识而达到语言背后的存在,或者就像前面所引述过的语言哲学的观点,语言就是语言,语言背后根本不存在非语言的支撑。当洛克说我们所谓的实体,不过是我们无法想象属性会凭空飘浮在空中,而设定某种基质来支撑和维系这诸种属性的时候,当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的时候,当休谟说“我们的经验不能半步跨越我们的经验本身”的时候[2]272,这种语言意识只是在言说语言意识本身的观点,已经不知不觉地主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思潮,并在休谟之后影响到整个科学实证主义。的确我们总是假定在我们的感觉之外有一种非感觉的东西在支撑着我们的感觉,但从认知的角度上讲,何种颜色可以不通过我们的视觉而呈现,何种声音可以不通过我们的听觉而呈现,何种规律可以不通过我们的数学公式而呈现?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第三种观点,语言意识是一种半透明的东西,因为语言意识不是自足的,其非自足性必然会被设定为有一个终极支撑者,尽管这个终极支撑者本身并不显现给我们的意识,但我们的意识却可以意指它。存在通过语言意识而显现,语言意识因为有存在的支撑而厚重坚实。语言意识显现存在,但也可能蒙蔽和歪曲存在,于是语言意识本身的结构和功能成为哲学关注的重点。
四、从Being到substance,从“是”到“是者”
巴门尼德的Being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对于存在本体的探讨。黑格尔认为:“毕达哥拉斯,在哲学史上,人人都知道站在伊奥利亚哲学家和爱利亚哲学家之间,前者,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仍然停留在认为事物的本质为物质的学说里,而后者,特别是巴门尼德斯,则已进展到以存在为形式的纯思阶段”[12]。在巴门尼德之后,智者学派片面地继承和张扬了巴门尼德Being学说中的语言逻辑维度而使哲学完全转向修辞和诡辩的路向,苏格拉底的真理和柏拉图idea的形而上学维度就是又再把哲学拉回到存在维度。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问题再次成为哲学的核心主题,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开宗明义地把第一哲学定义为“一般地研究存在之作为存在”的学问[4]731,这使他把哲学和具体科学区分开来,使哲学的重点再次关注到存在论。那么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存在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将巴门尼德的Being转化为本体(ousia)和实体(substance)概念。ousia是系动词eime的名词形式,拉丁文的实体(essentia,substantia)皆由ousia转译而来。于是实体概念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逐渐成为言说存在的主要名词。实体之取代存在,与亚里士多德把实体(substance)置于和属性(attributes)相关联的主谓结构中来加以言说有很大的关系。在《范畴篇》中他提出,实体是作为主词而被谓词所表述者,而不是作为谓词来表述主词。作为谓词而表述主词性质的有九种属性范畴,而作为被谓词所表述的主词只有实体一个范畴,实体独立自在,而属性只能依附于实体之上。这样,亚里士多德的Being展开为“substance+attributes(实体+属性)”的结构之中,Being也就由一个绝对不涉及任何具体表述内容的纯粹存在转化为一个被具体谓述性质所表述的对象。亚氏把Being本身作为既有的东西,不予追问,一心去建构关于substance的学说。Being由天上逐渐下凡到人间,Being由一个纯粹的存在逐渐转化为一个个存在者(Beings)。巴门尼德的纯Being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一”,不可能有复数形式,而到亚里士多德的substance,复数形式出现了。于是Being也不再是一个纯思的对象,而可以成为具体之思的对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就有了“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之分,而在巴门尼德那里,绝对不会有“第一存在”和“第二存在”之分,于是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一个十分矛盾的东西出现了,就是他把具体物定义为第一实体,而把种属概念的对象表述为第二实体。“实体这个词在最真实、最原初、最确定的意义上是指,既不去谓述一个主体,也不依存于一个主体中的东西,例如,个体的人或马。但是在派生的意义上,像属那样包含着原初实体的东西,以及包含着属的种也被称作实体。”[4]9把具体的个体物称之为实体,这与巴门尼德的Being已经差之千里,风马牛不相及。但亚里士多德又勉强把乃师柏拉图idea的变种概念“种属”也称之为实体,显得矛盾重重。可见亚里士多的所谓的实体,再不是巴门尼意义上的第一的和终极的存在,已经是由终极存在向具体显现物过渡中的不同层级。海德格尔表明,substance之希腊原文ousia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既是哲学术语,又是日常用词,兼有“本质”、“呈现”等义,ousia显现于外谓之呈现,隐处于内谓之本质,而这正是substance的样态。这个实体概念一方面指向显现于当下的“此性(thisness)”,同时又指向一个终极存在本体。亚里士多德取ousia命名他的实体范畴,正是要彰显它所蕴涵的“本质”和“显现”的双重含意。
亚里士多德在《物学》中提出其著名的“四因”说,更进一步显示了其substance乃是居间于Being和particular(个物)之中的某种东西的思路。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的自然个体物都不是终极的存在,任何个体物都可以被分解为质料因和形式因,质料与形式的组合构成个体物,构成“此性”。形式与质料的分离,乃是西方思想从混沌整体向分析理性的一大进步。在此性中,质料缺乏规定性,因此只是潜在的此性,而决定这个此性的,恰恰是形式。形式(morphy),英译form,又有“结构”之意。“形式的意思就是每件事物的本质和它的第一实体。”[4]792质料相对于形式是潜在的、被动的;形式与质料今天被我们用“形式与内容”的话题来谈论,内容成了实质性存在而形式成了外在的附着之物,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恰好相反,质料因相对于形式因而言,只不过是被加工制作的材料、是消极被动的惰性之物。事物的本质是其形式而不是其质料所决定的。每当我们问“这是什么”时,回答“这是茶杯”,而不是回答“这是玻璃”,追问某物是什么其实是在追问其形式。海德格尔也认为:“物是具有形式的质料……人们把形式称为理性而把质料称为非理性……形式指诸质料部分的空间位置分布和排列……形式规定了质料的安排,不止如此,形式甚至还规定了质料的种类和选择:罐要有不渗透性,斧要具有足够的硬度。”[10]11-12形式同时是质料追求的目的和动力,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三者可以合而为一,因为‘是什么’与‘为什么目的’是一回事,而运动的原初根源也与之同类。”[4]248形式是现实的、主动的,形式之于亚里士多德,犹如idea之于柏拉图,至此,亚里士多德自己的第一实体,第二实体之说完全被颠倒过来。亚里士多德在形式的意义上来定义实体,几乎就是柏拉图idea的翻版,正是因为在终极存在之下衍生出来的种、属、类、个体物等存在论级差,也才引发了相对性的本质、本质属性、偶性等概念。终极本体是不显现的存在,因此属性概念无法与之对应,而相对于种属类的存在,不同的属性概念才出现,相对于最为基本的种属,本质属性与之对应,依次个体物则对应于偶性,笛卡尔在《哲学原理》第一部分中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而柏拉图的idea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概念,正是对应于不同级差的种属存在者。
海德格尔提出“基础存在论”,即真正关于“作为Being的Being”的存在论的立场,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纯Being转换成idea和substance的形而上学是对于巴门尼德的“倒退”。海德格尔认为“Being”(das Sein)是最为普遍因此也是最为空洞的概念,它本身就逃避任何对其下定义的企图。Being的普遍性不是种属概念,存在不是最高的种属。存在的普遍性高于一切种属的普遍性。它既不能用定义从最高的概念导出,又不能由较低的概念来描述。Being无法被定义,其唯一的定义是:它是某种不是存在者(Beings,Das Seiende)的东西。[13]海德格尔对于das Sein(Being,存在)和das Seiende(Beings,存在者)进行了严格区分。他批评传统存在论追问存在者,却把存在本身遗忘掉了。这种遗忘存在本身的过程就是从巴门尼德的Being到柏拉图的idea再到亚里士多德的substance和form的历程。然后整个西方哲学史按照亚里士多德能够被谓述的substance之路来追问存在问题,实质上是纠缠于存在者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的最基本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存在存在?而不是什么都不存在?”(why there are essents rather than nothing?)正是因为对“无为什么不存在”的追问才让人回复到对das Sein本身的追问,因为那样的话就不会直接只追问现成的das Seiende,而先要追问das Sein本身。Das Sein可取“在场”(present,呈现)或“无蔽”状态或者“不在场”或“遮蔽”状态之义,“无”正是对应于后一种状态。这样正好回到了巴门尼德追问“存在(bieng)”和“非存在(non-Being)”的基本立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巴门尼德Being追问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及其显著地位。
收稿日期:2008-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