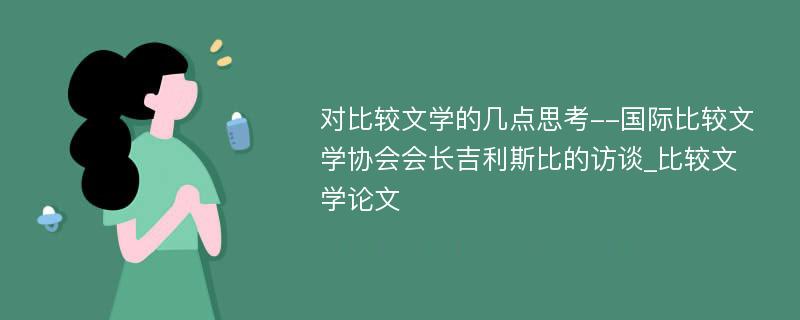
关于比较文学的一些思考——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吉列斯比采访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吉列论文,协会主席论文,采访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作访问学者期间,于1996年年末,在互联网络(Internet)上,以电子通讯(E-mail)的方式对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现任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德语文学教授杰拉尔德·E·P·吉列斯比(Gerald E.P.Gillespie)进行了采访,向他提出了六个问题。对此,吉列斯比教授提交了题为“关于比较文学的一些思考”的书面答复。
一、跟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可以说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请您对比较文学在本世纪的发展和成熟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吉列斯比:我在我的一篇题为“论国际化”的论文中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除非是你相信数字命理学(numerology)的某些奥秘,其实“某某世纪”并无多少神奇可言。比较文学完全可以归入“新近”从具有悠久历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等等生发出来的模式之中。人文主义者创立了现代哲学,这就是比较文学以及现代人类学在世界各地赖以生存的根基,而现代人类学对于我们如何审视文学(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和艺术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欧洲随后的文化时期——尤其是现代主义,为探索带普遍意义的进化式模式,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文化共享,以及为保证在欧洲体系中文化“片断”的连续性,确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方式。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欧洲一些国家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是从在文艺复兴时期得明朗化的文化嬗变中获得了相当的能量。所以,在欧洲海外诸帝国500年时代结束时,比较文学自然就要面对若干类批评的难题。其中一类难题是,对“关于文化领域(cultural realms),比较文学究竟能够告诉我们什么?”重新进行评估。与较为广泛的如欧洲体系之类的“国家”相比,与欧洲体系在欧美诸体系和远东及南亚诸体系中的支流相比,这种文化领域更为复杂、更为广博。第二类难题是对下述问题重新确定:比较文学的一整套基本术语产生于欧洲,那么,比较文学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对欧洲文化区域之外的文学进行有深度而非盲从欧洲中心式的阐释?第三类难题是如何处理各种不同框架之中的普遍现象,如:对人们怎样辨识全球范围内的诗意表达,对某些民族怎样共同拥有一种国际性的综合文化等进行研究,等等。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人们听到的是这样的说法:在比较文学的领域内,从欧洲及其繁衍出的新大陆所产生的术语至今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这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在题为“科学话语与后现代”的论文中论述了一种具有较长的家族渊源,长期存在于西方的倾向和态度。当此历史关头,在比较文学领域,既有诸多迷茫,也有振奋人心的挑战。正如我在论文“独角兽”中指出的,欧洲国家许多持自我批评态度的理论家在批判欧洲文化的属性时,仍然使用欧洲的术语,他们由此感到困惑。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对于深深置根于他种文化体系的术语,保持和深化自己的清醒意识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文化之间的对话。许多欧美学者和欧洲之外的学者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现在他们正积极努力地思考,探索谨慎前行的途径,使自己能够将各种不同的文化并置起来,而又不至于滑入某些粗疏的思想模式(这些思想模式主要产生于欧洲),尽管在世界其他地方,这类模式不过是舶来品,或者是为了迎和当地的倾向面而作了某些修正。为了给未来的比较文学打下基础,世界各地的大学将作出更多的投入,以多种语言和研究领域培养学生,而不要将学生的注意力仅仅局限在业已建立并普及的大范围(如英语文学)之内。
二、在文学研究领域,20世纪被称为“文学理论的世纪”,在此期间,文学批评理论出现了许多完全不同的流派和运动,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派、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等等。这些流派与运动对比较文学产生了哪些推动力与影响?
吉列斯比:历史文献表明,在西方国家,在20世纪之前,“文学理论”已经兴旺了若干世纪。虽然文学理论时常受到哲学思潮和文化关注(其中一些成了今天的文化关注的历史源头)的推动,但通常却是在当地语言和情趣的框架之内,作为一种评论的技艺而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中现存的批评和评论的绝大部分(即有教养的读者今天仍然在阅读的著作)不是出自学术专家之手,而是出自文学艺术家之手。上个世纪末,艺术领域内新宣言和新运动不断产生,进展之快,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20世纪后半叶的变化,是以每种新浪潮不过10来年的速度不断涌现,而浪潮与浪潮之间的覆盖重叠又引发出如何“选择”这类令人困惑的问题。但是,我们还需要把表面上的选择与深层次上的智力创造区分开来。20世纪中,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大学的极大发展可以与学术专家的时代性增长相互媲美。这些学术专家是不带有艺术家或哲学家身份的评论家和“理论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把今天这些专家的人数(有些情况下,简直是一大群)错当成了“文学批评”领域具有意义的增长。这些人只是把若干种液体搅合起来,却不能够产生传世的评论,回首往事,每当质量准则重新提出来时,这样的情况就愈加明显。在像比较文学这样的学术领域内,我们应当怎样评估“创新”,还必须加以认真思考。
我愿用相同的比喻来表达对这个问题的肯定答复:正是如此。问题中提到的各种不同的流派和研究方法,的确深刻地影响着比较文学。当我们进入21世纪之时,我相信,很可能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其中广义的形式主义作出了最富有创新性的贡献,后来从这里面既产生出批评的可操作性,也产生出争议。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心理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两者都置根于浪漫主义的哲学与科学,而且现在经常以交汇融合的形式出现)对于后来的思想运动,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都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影响。就其实质而言,比较文学必然成为开放的主人,所以,从一开始,每一种影响都轻而易举地“入侵”了比较文学,并产生出正面和负面的反响。我在“90年代美国的比较文学”一文中论述了当代美国学术界一直醉心于“创新”所产生的一些后果。在美国,从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教育水平降低,各种标新立异的研究方法竞相涌现,倡导“具象呈现”的策略("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凡此种种,已经严重到了使这一领域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地步。使人担忧的是,我们缺乏具有多种文学知识和理论知识的、涉猎广泛的学者。当今的比较文学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面对为数众多的“单主题”学者们("monothematic" scholars),还能稳得住自己的阵脚。这些学者自称是比较文学工作者,而实际上是一些领域较为狭窄的专门家,他们总是习惯性地努力将比较文学纳入某种特定的世界观,或者某种心理方向的轨道之中。在最近几十年间,涌现出许多跨学科研究机构,每一个这样的机构只致力于比较文学在60年代所预见和包括的某一个特定方面。
三、在西方,近年来在比较文学领域,有哪些主要的成就,存在那些主要问题?
吉列斯比: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其实始于对上面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我在题为“与文学文化重新衔接”的论文中,指出了在比较文学的“现实世界”功效方面,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沟”。西方学者们在比较文学领域内付出了努力,试图对人类和社会的行为作出既具有实际意义又具有普遍意义的阐释。他们的这番努力使下述几点广为人知:
(1)对周围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文明结构所抱有的尊重减弱;(2)置根于这类结构中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实践不再受到重视;(3)伪常规(pseudo-norms)的不合理呈现和对非西方社会所作的错误阐释。
但是,也还存在着正面的迹象,与上述几点形成均势。一些西方的批评家终于意识到需要一种更为开放的、不带倾向性的方法,方可将文学体系作为体系、要素和具体操作(这些都需要审慎而仔细的观察)来加以研究。人们付出了引人瞩目的努力,创造出更为有效的分析工具,来描述现实生活中的人如何在实际文化中“学习”参与文学体系。例如,对认知心理学、接受美学和身份构成等的研究。比较文学在翻译研究中也逐步占有了很大的比重,如研究文学材料共享的实际步骤,在目标文化中产生了“干扰”,等等。在比较文学领域内,就是否可能存在真正的“比较诗学”产生了争论,这种诗学不把单一的文学体系视为规范。正如我在最近发表的题为“心理历史分析的困难”和“文化相对论的意义与局限”的论文中提到的那样,在西方,有人认为,相对主义排斥了研究客观现实(即与文学文化相联系的人类行为)的实用主义途径;但很少有西方学者批判这种思想。在西方国家,许多比较文学工作者认为当代文学能够以某些方式呈现出与科学突破的相似之处,他们对此大感兴趣,我个人也认为这是十分鼓舞人心的。这种兴趣导致产生出一种基本的内审,即对任何时代的视像作更深层次的“模式化”内审。然而,与那些真正的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工作者相比,谁更具备条件去发现既从科学范式(paradigm)又从文学作品中产生的某些特征?
四、东西方比较文学一直是世界比较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东方的比较文学工作都经常会感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某种“失衡”或者“隔阂”。除了1991年日本东京大会之外,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历次大会都是在西方国家召开的,而在西方国家出版的比较文学学术著作,大多数都没有收入东方国家的文学传统和研究成果。您是否认为确实存在着这种“失衡”或“隔阂”?如果确实如此,请问需要作哪些工作才能够消除这种“隔阂”,或者说,调整这种“失衡”状况?
吉列斯比:当已故杨周翰先生来斯坦福大学访问我时,他要我带他去医院探视处于弥留之际的我的同事刘若愚先生。那次探视竟成了我们跟这位在中西比较文学领域享有崇高声誉的先驱者作最后的诀别。刘先生英年早逝,是令人悲伤的一大损失。然而,在世者决不会让他的火炬熄灭。我相信,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会议和出版物方面,关于中西比较文学,确实存在这信息隔阂或者拖延等情况。所以,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鼓励读者们去参阅《国际比较文学协会通讯》第13卷20期(1993年秋季号)所载标题和名单之类的资料。读者们一定可以从中发现,我们的大会议程和文学理论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以及与之相关文字资料等,都包括了东西方以及非欧洲的内容和题材。此外,在亚洲之外出版的比较文学刊物也时常登载关于亚洲文学和东西方比较研究的文章。在美国,这类刊物就有《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与普通文学年鉴》等。
长期以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一直是从事跨文化活动与交流的一个重要基地。在日本研究和东西方比较文学专家厄尔·迈纳(EarlMiner)教授的领导下,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中一个新的研究机构——跨文化研究委员会(CIS,Committee on Intercultural Studies)——成立了,许多同事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无私的奉献。有了这样的机构,类似东西方比较研究的活动一定会更加兴旺。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和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著名专家欧阳桢教授将出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按照该委员会的规定,将由非欧洲国家的语言文学专家组成跨国度的研究班子,再由这样的班子来制订委员会的研究项目。这个委员会将以自我更新的方式从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杰出学者中,从抱有共同研究兴趣的美洲和欧洲学者中吸收新的成员。这个委员会跟不同的工作班子合作,已经启动了三个跨国的研究项目,并将在1997年8月荷兰莱顿召开的第15届大会上有引人注目的表现。
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将协助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众多成员以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即从欧洲和欧美主题的局限中走出来。它还将鼓励那些在欧洲之外地区居住和从事活动的学者们摆脱自身传统的桎梏,创建一套新的批评语汇,并将其用来与比较文学欧洲发源地之外的批评语汇进行比较和对照。此外,这些学者还将对产生于前西方或非西方时期(pre-andnon-Western periods)的实际社会的文学价值作详细阐释。历史文献表明,我们能够预见,不同的批评共生物能够从对实际文化的深刻反思中产生出来。这个委员会还将推进区域内的或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如果比较文学要创建更为牢实的知识基地,我们就迫切需要这种比较。例如,对不同的外来文化影响印度北部那些具有多种文化传统、成分复杂的混合群体的过程进行研究。
将比较文学扩展成为世界范围的学科,其功效之一就是“打破垄断”,牢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跨文化研究委员会创建之前,第一个巨大的扩展就是多种欧美文学被纳入了比较文学的范畴。这一步极大地激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代比较文学工作者的兴趣,同时也耗费了他们不少精力。现在,欧洲语言比较文学史协作委员会的工作得益于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可包容了新大陆文学的强大功能。但是,对欧洲某些被忽略的领域,如对一些斯拉夫民族的研究,比较文学尚未作出任何形式的比较探索,所以,这一直就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而在欧洲之外的地区,一些相关的新的研究项目却已经启动。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可以设想,一支实力很强的学者队伍对东南亚和周边大岛上的马来文化产生了兴趣,他们就此进入了我们的领域。这就意味着,从集体协作的角度看,对比较文学工作者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强烈。在一些重要的教学中心,为了吸引师生的注意,开始讲授与这些地区相关的语言和历史。这就会与早已建立的项目,如中国—朝鲜—日本复合模式形成竞争。
比较文学的环球框架正在形成。我们置身其中,就能够预见,如果将东方与西方这两极作为核心关系定位,这将会使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产生“亚洲中心”的看法。当然,对于亚洲你们所在地区的人们,以及欧洲许多对中国文学、朝鲜文学和日本文学极感兴趣的学者来说,这种关系的确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这种关系只是属于跨区域关系的超级层次(superclassofinterregionalrelationship)。类似的例证之一是北非与“西亚”(欧洲术语称为“近东”或“黎凡特”
至于谈到比较文学的重要国际会议,的确其中大多数是在欧洲或者北美洲召开的。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比较文学开始复兴以来,这一领域的实际历史与操作功能方面的结果。在头几十年间,大会是在进行相关学术活动的高水平学术中心举行。这些中心之所以水平高,实力强,是因为那里的学者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个人的热诚。然而,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大会并不是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唯一的有意义的活动。协会一些主要的研究委员会,如欧洲语言比较文学史委员会、理论委员会和翻译委员会等还跟各主办大学、研究院或学会合作,分别在世界各地举办各自的学术会议。后来成立的若干研究委员会,如关于“文学中的航程”、“争议与方法”和“文化身份”等委员会也都采取了这样的方式,跨文化研究委员会也将照此方式举办学术会议。此外,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至少每年要跟协会的各行政机构以及各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聚会,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还要跟主办机构或学会合作。1995年10月在北京大学,协会跟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合作举办的那次讨论会十分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回顾占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全部历史四分之一的过去10年,我注意到,自1987年以来,协会在以下城市举行过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其中有些是跟国际大会同时):京都、慕尼黑、里斯本、新德里、东京、阿雷格里港、威尼斯、埃德蒙顿、北京、奥登塞,以及莱顿。我们还将在以下地方举行这样的会议:东亚和南亚三次、欧洲四次(包括莱顿)、南美洲一次,北美洲一次。毫无疑问,协会必然要周期性地返回到曾经举办过会议的新老基地去,同时,还要到近年来比较文学开展得蓬勃兴旺的新地方去。当然,如果协会要努力扶持南半球和其他一些地区,那么,自上一次会议以来,在北半球召开这类会议的间隔就会拉长。大型会议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记住下述事实是有所裨益的: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够在某些西方国家飞速发展,主要是由于那里的学者出版了许多种关于比较文学的饶有兴味的著作,展示了如何将比较文学运用于文学分析。其他地区的学者也可以通过出版多种饶有兴味的著作来达到同样的目的。食物可口不可口,只有品尝才能知道。过去时代的学者只能依靠印刷技术和口授讲解的方式来转播他们的思想,而今天的电子通讯网络已经使快速联系和信息交换成为可能,所以当今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学者都能够比过去时代的学者具备更多更好的方便条件。
五、作为一份很有影响的学术刊物,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比较文学》是中国的国家级比较文学刊物。请您通过这家刊物,给中国的比较文学工作者和读者们讲几句话。
吉列斯比:今天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对比较文学的挑战。对其中的主要部分,我想举出罗马神话中人所熟知的雅努斯神(Janus)来加以说明。雅努斯被称为“开端之神”,他是宅院的“门户”,也是时间的“门户”。这就表明,为什么他的名字会用在January(一月)中,而在欧洲,January正是一年的开始。雅努斯的头有两面,既向内外看,也向前后看。我认为,比较文学工作者需要像雅努斯那样,一方面,浸淫在本土文化之中,用自己的语言著述;而另一方面,又应该向其他文化开放,并从它种文化中吸收知识。从群体的角度看,如果比较文学工作者只“向前看”,不“向后看”,他们就不可能承担起多重使命。所谓“向后看”,是指对于多种民族的文化历史应该有透彻的理解,正是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对当今人类的经验与实践奠定了基础。为比较文学作的选择不应当在“本土世界”与“外部世界”两者之间作出,而应该是“两者不可或缺”的选择。所以,《中国比较文学》用中文出版,这样,它就很好地起到了“门户”的作用:既向前后看,也向内外看。
六、您对比较文学在21世纪的发展有什么预见性看法?
吉列斯比:还有几年,就到21世纪了。比起国际比较文学协会1991年的东京大会,现在距离21世纪是近得多了。比较文学的求索必将以种种形式长久存在,因为世界的发展已经注定研究者们必需突破文化之间以及文化层面之间的藩篱。文学与历史的领域将不断获得新生,无休无止,因为它们都是人类自我审视的永恒产物。然而,今后在世界上还会时常出现主张孤立和本土化的反冲现象,其特点是反对开放性,尤其反对对人们喜爱的文化习俗进行“无倾向性”分析。所以,当我们跨越日历上那一条人为的世纪划分线,进入21世纪时,伟大的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tz)早在17世纪末就发出的预言仍将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我们需要交互式的文化意识的汇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