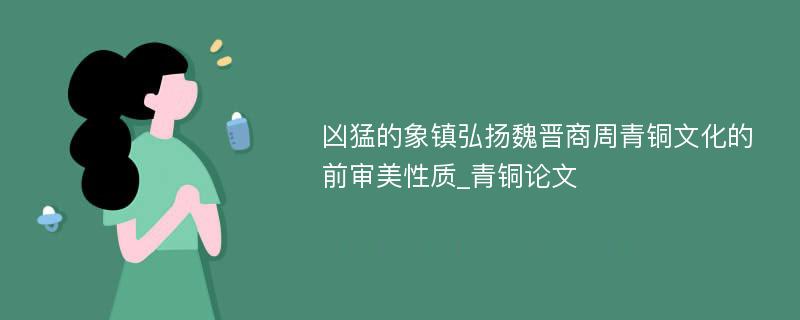
狞厉之象 镇凶扬威——论商周青铜文化的前美学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铜论文,美学论文,之象论文,性质论文,商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如果说,商周以前有石器文化时代、陶器文化时代的话,那么,商周实为青铜器文化的时代。它璀灿的文化光芒集中反映在其青铜铸品上。然而,怎样通过青铜器来认识商周的文化呢?有专家认为:“陶器纹饰的美学风格由活泼愉快走向沉重神秘,确是走向青铜时代的无可置疑的实证”,“中国的青铜饕餮也是这样。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也正只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美——崇高的。……正是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3、34页。)这段专家名言在揭示历史现象方面很精确,但它包含的三个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夏商之际,中国社会的确由石器、陶器文化时代走向青铜时代,而青铜时代是否比石器、陶器时代更沉重、神秘呢?第二,青铜时代的所谓“神秘恐怖”能否构成美学意义上的崇高?第三,青铜文化中是否具有“狞厉的美”?这些问题既涉及到对中国青铜时代社会本质的认识,也触及对商周时期中国人审美意识发展的探索。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是由历史力量推动的,但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看,这种历史力量绝不是神秘的,而是可以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来解释。第一,石器、陶器时代的纹饰多为活泼的写实,而青铜器时代的纹饰多为使人恐惧的动物变形。造成这一变异的动因,在于商朝人的世界观与夏朝人的世界观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样,社会发展到周朝,由于世界观的进一步变化,周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商代青铜器的纹饰又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世界观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礼记》托孔子之口写道:“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礼记·表记》)这段话表明,夏朝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初创期,生产力还很低下,因此统治者尊重政教,勤于民事。奴隶主阶级的生活资料虽然掠夺于奴隶阶级,但他们更多地是以社会管理者而不是掠夺者的面目出现,所以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偏重用俸禄、赏赐的形式来进行。夏朝敬鬼神,因先人对许多世间事物不能把握,故信鬼神而敬之。夏朝又远鬼神,因生产力低下,淫祀并不能多增社会财富,故统治者把多得财富的手段系于勤政。商朝处于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期,由于青铜工具的应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财富有了较多的积余,因此统治者特别敬重鬼神,认为社会财富的充足得之于鬼神的赏赐,而奴隶主阶级能够大肆掠夺奴隶阶级创造的财富则是由于鬼神的安排。所以,统治者的首要社会工作是祭祀鬼神,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对鬼神态度的好坏而赏罚的方式来进行。因此,统治阶级把多得财富的手段系于对神鬼的淫祀。周朝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没落期和封建社会的初创期,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财富余裕更多,因此统治者推重礼法,尚好施与,想用“礼”的条律和“施”的恩惠使被统治者安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听凭统治者占有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周代亦重鬼神,把统治阶级的地位与鬼神先天赋予的“天命”相联系。但仅依鬼神尚不足以把被统治阶级吓得服服贴贴,所以,周代统治者更加推重礼法,以后天的社会秩序规则训戒被统治者,兼以“施与”的怀柔政策,以便在新的生产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占有社会财富。夏、商、周三代由于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便也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夏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造就了陶器时代活泼写实的纹饰形象风格,商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亦造就了青铜时代早、中期恐怖、凶狠的纹饰形象风格。到了周朝,恐怖凶狠的纹饰形象风格虽然尚存(兽面纹至西周中期才逐渐少见于青铜器),但在青铜器上已大量刻制政治性铭文,以代替早先仅凭纹饰所体现的内涵。“西周晚期的纹饰,从整体来看已经没有或甚少有旧的痕迹了。”(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38页)由此可见,夏、商、 周三代纹饰形象的变化皆基于它们的社会生产条件,没有任何神秘可言。
第二,青铜时代的可谓“神秘恐怖”并不能构成美学意义上的崇高。“崇高”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周易·系辞》,曰“崇高莫大乎富贵”,同时的《国语·楚语》亦有曰:“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周缕为善。”“崇高”取义于“高大”、“高贵”、“高尚”。在西方,古罗马的朗吉纳斯著有《崇高论》,但其“崇高”仅指称修辞风格之一种,实为内涵和谐的“大美”。真正美学意义崇高的理论代表是近代德国学者康德。他从主客体的关系上阐述了崇高的实质:有限的主体认识能力与无限的被认识客体之间的矛盾的反映。崇高的这种内涵在中国青铜文化里是否存在呢?回答是否定的。从世界各民族美学思想发展史的实践看,人们形成系统美学观念的第一种形态,都是以主客观和谐的美作为所追求的理想的。这种古典的美的理想把主体与客体、现实与理想、历史与逻辑在经验的层次上统一了起来。它追求自律的封闭性的完善,并以社会义务本位作为“和谐”、“完善”的向心点和评判尺度。因此,它始终与伦理性质的“善”相统一。在高扬社会义务本位的“善”的指导下,这种强调和谐的古典审美理想一直在庄园经济与农业社会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之前,无论在文艺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都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出以崇高作为审美理想的作品。 (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可参考拙作《崇高论》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那么,怎样理解在先秦古典审美理想确立之前青铜文化中所谓的“神秘恐怖”呢?中国青铜器上这种“神秘恐怖”的纹饰实际是前美学时期古人思想观念的写照。如果说,先秦时期人们确立的古典美学理想追求“文质彬彬”、“尽善尽美”,那么,前美学时期则几乎没有系统化的美学理想。尤其是商朝和周初,人们把自己的前途都寄托在鬼神身上,认为生活中的雷霆雨露,皆自神出;相信只要敬奉鬼神就能使自己幸福如愿,而所有的不幸则是敬神不诚造成的。所以,面对统辖世间万事万物的神祇,人们不可能也不敢提出任何的理想追求。 这样的思想反映在社会文化中,便是我们所见到的,几乎全部青铜时代的器皿上,只有带宗教意义的“神秘恐怖”的纹饰,而没有此前与此后都能见到的其它样式的图案了。因此可以说,这种所谓“神秘恐怖”的纹饰绝没有美学上崇高的性质,而只是前美学时期弥漫于古人意识中的宗教观念的体现。
第三,青铜文化中也不存在“狞厉的美”。美,无论怎么说,总是主体与客体、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尽管有时这种统一是暂时的或虚幻的。然而,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皿上,根本不存在这类“统一”。它们狞厉的纹饰,无论从出发点还是从目的看,都游历于宗教范围之内,而与审美绝无关系。
“狞厉”能否作为美的对象呢?回答是肯定的,就象“恐怖”、“丑陋”也能作为审美的对象一样。但至少需有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它或者作为现代崇高的对象之一,或者由于审美的关系,而成为美的对象。在第一种情况下,“狞厉”与恐怖一样,体现着近代以崇高为中心的审美观念。如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油画《柯尔尼卡》就是这样的作品。在这幅画中,画家没有再现小镇柯尔尼卡被德国法西斯飞机炸毁的现实景象,也没有再现与被毁城市有关的人物;他只是用变形的手法画了一些人的残损肢体、一头公牛、一匹剖腹的马和一只电灯,背景上有一座火光冲天的房屋。这幅黑白画的画面十分恐怖,并且不符合客观的真实。然而,它的内涵能够以崇高形态的审美方式强烈地激起欣赏者的审美体验,深切地感受到德国法西斯的残暴和画家对其暴行表达的愤慨。所以,美学史家认为,它“在二十年后并没有失去它的不朽的意义”。(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以此对照,青铜文化中的“狞厉”显然不合标准,因为这种“狞厉”并不产生于以崇高形态作为审美方式的时代。
在第二种情况下,“狞厉”与丑陋一样,由于审美的关系而成为美的对象。如法国艺术家罗丹的雕塑《老妓》就是这样的作品。《老妓》又名《欧米哀尔》,是代表罗丹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作品之一。《老妓》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位年老裸妇的坐像,她低垂着头,双乳干瘪,皮肤皱折;她的姿势表明,她似乎正在忏悔以往淫荡的生活,又似乎正在回忆过去繁华的岁月。毫无疑问,罗丹尽管可能给予这个再现对象些许的同情,但主要是把她作为“丑”的象征而批判的。对丑陋事物的直接再现并不是要欣赏者去直接欣赏丑陋,而是让欣赏者面对丑陋的对象,激起批判的情绪,从而使自己的道德思想得以净化。正是由于经过这样一系列复杂的“批判”、“净化”过程,才能让欣赏者在文艺家再现的丑恶对象上产生属于道德正值的审美感受。这样的创作方式是近代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之一。这样的欣赏方式是近代崇高形态的美学观念的主要审美方式。以此对照,青铜文化中的“狞厉”显然不合标准,因为“狞厉的美”将这种“狞厉”在审美评价上作为“天值”来看待,直接被作为欣赏的对象,而这在当时是不成立的。所以,“狞厉”至少在青铜时代,决不会是美的。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集中体现。商周青铜器上的各种纹饰则是商周时期形象发展的典型代表。然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商周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其形象图案皆属于前美学性质。换句话说,它们都不是为审美而创作的。
二
青铜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青铜文化指青铜时代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文明,狭义的青铜文化仅指青铜器体现的文明。商周的青铜器有工农具、兵器、饪食器、酒器、水器、乐器、杂器等门类,而最能反映当时精神文明的,是以钟鼎为代表的礼器。“礼器这个名词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诸凡可以体现礼的器物,都在它的范围之内。青铜器也称彝器,彝的意思是常,以钟鼎为代表的宗庙常器,也就是青铜礼器。”(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4、15页。)在全部青铜器中,礼器的数量最大,商周时期的形象图案在礼器上的反映也最多、最集中、最典型。除了青铜礼器外,商周时期的形象图案就数陶器上反映的多了,它可被看作是青铜礼器上形象的补充。
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缘故,商代人信鬼神、重祭祀。它反映在商代的形象图案上便是十足的宗教意味。如商代主要的青铜礼器鼎、鬲、尊、盂、爵、壶、觯等,其表面都著有宗教性的纹饰。吕不韦《吕氏春秋》道:“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吕氏春秋·先识览》)自宋《宣和博古图》起,青铜器上著“有首无身”的兽面纹饰即被称为饕餮纹。这种纹饰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最多见,亦见于同时期的陶器制品上。吕不韦称兽面纹为饕餮纹,实际揭示出这种纹饰在商周并非起一般的装饰作用,而是具有宗教的意义。这种看法可在《左传》中得到证实。《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恶,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以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譛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语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祷杌’。……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究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俦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这段话表明,饕餮等本为“四凶”。舜把它们流放到四周边远之地,“以御魑魅”,为的是以凶制凶,以恶制恶。把饕餮之义化为纹饰,著于鼎上,同样也是为了取其避凶制恶之意。
鼎在夏、商、周三代被作为宝物,视作现实权力的象征或宗教祭祀的主要礼器。由于浓厚的君权神授意识,鼎在三代的现实地位和宗教地位往往被看作是统一的。《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民昬德,迁鼎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定也。”这段话中对鼎的论述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夏有天下,故铸鼎。伴着夏至商、商至周的改朝换代,鼎也随之迁移。这里的“鼎”既是实指,又是虚指;实指是那个象征国家权力、放于国都的鼎,虚指是它本身已成国家权力的象征,而并不意味着天下其它的鼎都有这种象征意义。鼎的这种象征意义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如宋国“取郜大鼎于宋”,纳于自己的大庙,就被认为“非礼也。”(《左传·桓公三年》)第二,象征国家权力的鼎服务于国家统治。在三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种服务也不相同。如在夏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文化不发达表情达意的传播媒介——文字——基本还处于图画状态,所以统治者“铸鼎象物”,在鼎上著世间各种事物的图象,使它有认识作用,让民众得知在生活中何去何从。夏鼎的图案——“象物”,显然与它存在的社会条件是相适应的。第三,鼎之所在为国君之所在,国家权力机关之所在。成王定鼎于郏辱即成王定都于郏鄏。这儿的鼎是国家权力机关的代名词了。
随着夏、商、周朝代的变迁,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青铜冶炼技术的发达,越到后来,鼎的产量越多,它的国家权力和权力机关的象征意义也越弱化。但作为彝器,它服务于国家(君权神授之邦)的作用并没有改变,这决定了它表面图文的发展。夏鼎“象物”,旨在起认识作用,“使民知神奸。”商鼎就不同了。商代人信鬼神,鼎又是宗庙里的主要礼器,所以商鼎的图案多有咒符性质,为宗教上趋吉镇凶之用,其中最著名的有饕餮纹、夔龙纹、夔凤纹、人面纹以及其它动物纹饰。它们的“渊源可追溯到荒古的时代,并且不只一种文化保存它的迹象。”(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326页。)然而,它们在商代得到昭著显明的高扬却是基于商人信鬼神、重咒符的缘故。这种图案不仅著在鼎上,也著在其它青铜物器上,甚至在宗庙用的陶器制品上。由于文化的滞后性,“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兽面纹(饕餮纹)最为发达。”(引文出处同上。)所以才有《吕氏春秋》所说的“周鼎著饕餮。”实际上,随着周朝替商,铜鼎的作用又为之一变。周代为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变迁的时期,周人重宗法而远鬼神,因此周中期之后,一方面由于青铜器包括鼎的产量的增多,另一方面由于宗法的要求,青铜器上铭刻现实事功大大超过了著宗教图案。如“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左传·昭公三年》)宋正考父庙中“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左传·昭公七年》)周代享庙内鼎铭的作用诚如《礼记》指出的,“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也”。这儿,鼎和其铭一样,皆旨在宗法的用场,而不是宗教的用场。到了东周后期,鼎又被统治者用作为法制的器具,如昭公六年,郑国子产铸刑鼎。昭公二十九年,晋国范宣子“以铸弄鼎。”(《左传》)把国家的法纪刻在鼎上,使民众行为有所依,违禁有所止。青铜器几乎完全脱离了宗教性质,而与现实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在日常生活中,鼎也只被看作是一般的宝物,如晋侯曾“赐子产莒之二方鼎。”(《左传·昭公七年》)已不再把鼎看作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了。
除了鼎之外,其它青铜器也是如此,在商代和周初,不仅青铜礼器上著着狰狞恐怖的饕餮、夔龙等形象,即使在铖、鏚、刀、斧等兵器上,钟、鏚、錞、鼓等乐器上,也著着这类形象。所以《诗经》有曰:“武王载斾,有虔秉铖,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诗经·商颂·长发(六)》)商王手里拿着这把著有镇凶图象的大斧,有如握火在手,自然所向披靡,没有人敢来阻挡他了。商代统治者把成汤灭夏桀仿佛完全看作是托庇于鬼神的福祉。所以,他们即使在祭祀中,也是称颂天命的多,褒奖事功的少。这种世界观的反映之一,便是注重在青铜器上著各种镇凶趋吉的形象。到了周代,尤其后期列国纷争时,人们的眼中却只有事功而无暇于天命了。如诸侯季武子“作林钟而铭鲁功”(《左传·襄公十九年》)等。这种世界观反映在青铜器上,便造成了饕餮、夔龙等宗教性形象的大量减少。正由于这些变化,至周代,包裹在青铜器上的宗教的、神圣的外衣逐渐衰退、弱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旧的青铜器形制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绝大多数都转化为生活用具而改变了性质。”(《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5页。)
夏、商、周三代青铜文化滥觞、发达、渐至衰落的过程,是中国早期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变动的反映。青铜文化中狰狞恐怖的形象作为以商代和周初奴隶制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上层建筑,随着信鬼神、重淫祀的社会风气转变为“事鬼神而远之”的社会风气,它们也逐渐从中国文化的主要舞台上退了出去,仅在历史的册页中留下其悠长的回声。而青铜时代这种狞厉的形象,就其本身的意义来看,在于宗教性质的显势扬威,镇凶趋吉;而不在于审美。因此,它们属于前美学时期的文化现象,同样不能以后世美学的尺度来衡量。青铜时代的形象主要体现于青铜器上,同时也体现在陶器上,首先,青铜器的造型和外表图案,都首先用陶塑为范本,以陶范浇铸,因此,陶器实为青铜器之母。其次,青铜器上的很多纹饰样式亦见于陶器制品上,如饕餮纹、云雷纹均见于商陶器皿,唯不及青铜器上的精巧细腻。第三,商周时期的有些形象独见于陶器,而不见于青铜器,如出现于青铜时代晚期的陶俑,“当时,奴隶贵族以人及车马殉葬的旧俗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仿人、仿兽的木俑、陶俑等殉葬品。”(见冯先铭主编《中国陶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这类陶俑作品当是青铜时代的独特一类形象,起的亦是宗教上的作用。由此观之,商周时期陶器之灿烂不让于青铜器,只是陶器不易保存完好,遗世精品不及青铜器。而陶器的形象图案多见于青铜器,且亦多用于宗教,故简略述之。
标签:青铜论文; 青铜时代论文; 考古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美学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文物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