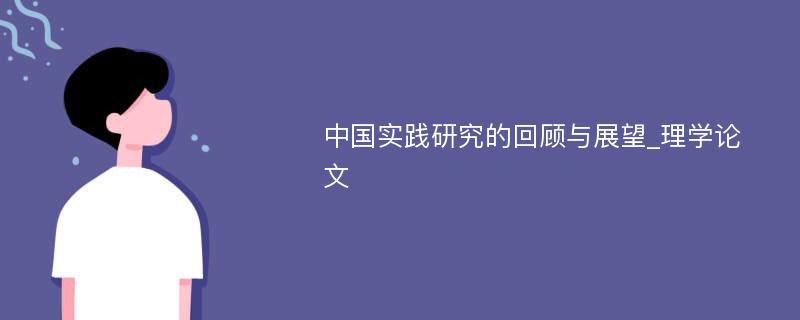
中国实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1940年,我国著名学者稽文甫先生就在河南大学学报《学术丛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陆象山的“实学”》的文章,他从“反空论”、“反矫饰”、“反格套”、“切要处用力”诸方面,系统地论证了陆象山的实学思想,为中国实学研究拉开了序幕。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这只是个别学者的议论,和者甚寡,尚未形成实学研究的社会思潮,实学仍是一块几乎无人问津的荒漠之地。真正把中国实学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研究热潮,是在本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四人帮”被打倒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在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人们不断地呼唤实学,时代也急切地需要实学。于是,在中国学术界,才逐步萌生了研究实学的愿望,并出现了中国实学研究的热潮。这一热潮的出现,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三方面原因所造成:(一)从政治环境上看,许多学者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过程中,认识到中国所以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从哲学上讲,就是因为人们违背与抛弃了中国固有的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内容的实学精神。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再一次说明,凡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实学精神,国家必将富强,社会必将兴旺;凡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实学精神,国家必将贫弱,社会必将衰退。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邓小平先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神武器,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要恢复、继承与发扬中国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就必须从研究与探索中国实学入手,通过古代实学元典去领悟它的精神实质,并根据现代化需要去转换中国古典实学,把现实需要与中国古典实学联系起来,努力寻找二者之间的结合点,并在它们之间架起一座相通的桥梁,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二)从文化学术上看,人们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指导下,在对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反思中,痛切地认识到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某种哲学模式或观念来剪裁中国传统哲学,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把一部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变成毫无生气的僵死的教条,失去中国哲学的固有特点,而成为西方某种哲学观念的附属品。中国学术界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存在,强烈要求摆脱西方某种哲学的理论框架,回到中国哲学元典,按照它的本来面貌,结合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中国实际,去揭示中国哲学固有特点和发展规律。就宋明哲学而言,认为除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外,还必须把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等人为代表的实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来考察。这样一来,中国哲学的发展,除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外,还应在宋明“理学”与近代“新学”之间补上“明清实学”。宋元明清哲学的发展,就不再是理学与心学的两足并行,而是理学、心学与实学的三足鼎立;在理学与心学思想体系中,不仅有“虚学”,也含有“实学”。只有把“实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来考察,才能全面地揭示宋元明清哲学的本来面貌和逻辑结构体系,正确地评价实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三)从国际学术交流上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学术界由封闭走向开放,许多学者走出国门,开始与世界各国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切磋学问,这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中国学者在与各国学者的交流中,特别是与日本、韩国学者的交往中,发现中国虽是东亚实学的发祥地,但在实学研究上中国既落后于韩国,也落后于日本,因为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韩国就已开始实学研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就已开始实学研究。我们认识到在实学研究上,中国虽暂时处于落后地位,但是,中国学者亦理应同日本、韩国及东亚各国学者一道把东方实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建构现代新实学思想体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不可否认,韩国、日本是中国实学研究的先行者,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启示,并学到了许多东西。
正是在这种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呼唤下,中国学术界于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了实学研究的热潮,并且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从八十年代初至今,中国大陆实学研究大体上经过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八十年代,研究重点是放在探讨“明清实学思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承认明清实学思潮的存在以及对它的内涵的界定。经过反复争论,大体上取得了共识,其成果反映在《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中。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实学研究开始由明清实学逐步扩展到整个中国实学,在中国实学的内涵,主流与核心,起点、终点及发展阶段,实学与理学的关系,以及实学现代转换诸问题上,学者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其成果反映在《中国实学思想史》一书中。至今,这一争论并未结束,仍在进行着。但我相信,真理越辩越明,经过学者之间的认真切磋、讨论,是会逐步取得共识的。
从八十年代初至今,中国实学研究走过了将近二十个春秋,经过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如下五项成绩:
(一)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水平较高的实学研讨会。
八十年代,为了编写《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中国大陆先后在北京、成都等地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实学研讨会,就明清实学的内涵、特点、发展阶段及历史作用诸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逐步取得了共识。1987年夏,我们邀请日本著名实学家源了圆先生在北京召开了中日实学座谈会,并决定编写《中日实学史研究》。这是中日两国实学研究者的第一项学术合作。
1992年秋,由于山东大学的全力支持,在济南市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届东亚实学国际会议。在会上,中、日、韩三国学者及台湾、香港地区学者就中国实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实学的本质与核心、实学与理学的关系、中日韩三国实学的异同以及东亚实学的现代转换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今天,在开封大学、河南行政学院和中原宋学研究会的通力合作下,我们又在宋都——开封举办了第五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大家关心的“东亚实学与二十一世纪”这一时代主题进行充分讨论,以便进一步推动东亚实学研究。
同时,从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从事实学研究的学者在中国实学研究会的组织下,先后应邀参加了在汉城、东京举办的第一届、第三届、第四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各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受益非浅,也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二)编辑、出版与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实学论著。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在中国大陆已出版了将近二十部关于实学研究的学术专著,在海内外各主要报刊上发表的实学论文多达200余篇。 在学术专著中,除了《明清实学思潮史》、《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明清实学简史》、《中国实学思想史》、《中韩实学史研究》等专门论述实学的专著外,还有在其他学术专著中设有专章论述实学的,如《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儒学史》、《理学·实学·朴学》等。此外,中国实学研究会还编辑出版了第二届、第五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
(三)初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从事实学研究的学术队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大陆从事实学研究的教授多达200余人, 遍布于全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近年在实学研究领域出现一批有志于实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并且发表了一批学术著作和论文。在某些大学(如中国人民大学)还开设了中国实学研究的硕士、博士课程,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实学研究的研究生,撰写了一批有关实学研究的硕士和博士论文。
(四)成立与健全中国实学研究会。
为了推动中国实学研究和加强对外学术交流,1992年在山东大学成立了中国实学研究会,1994年1月经民政部正式审核批准。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赢利的民间学术研究团体。目前已有100多位教授、学者参加。中国实学研究会的成立, 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实学研究,而且也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五)台湾地区的实学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据台湾交通大学詹海云教授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996年7月, 在台湾地区发表的实学论文共28篇,其中有13篇为台湾学者所写。詹海云教授经多年努力,已撰成《中国大陆实学研究的现况及检讨》一书。台湾成功大学蔡茂松教授撰写的《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1995年),系统地阐述了“朝鲜中后期的实学思想”。同时,为了回应大陆实学研究,还于1992年9月21 日在台湾台北市举办了“明清实学研究的现况及展望”座谈会。在会上,台湾学者就明清实学的名称、特色、分期和乾嘉实学以及明清科技实学等问题,均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这是海峡两岸之间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八十年初以来,中国实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初步的可喜的成果,但是真正的百花烂漫的研究局面还未出现。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知识经济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在广度与深度上把实学研究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推动中国和东亚知识经济的向前发展。近二十年来,中国实学研究的重点是从历史角度去揭示中国实学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对中国历史上的实学家进行个案分析。为了迎接21世纪,我们除了继续探讨中国实学史外,还必须不断地开拓实学研究的新领域,应向专题化、理论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方向进一步发展。
中国实学史研究应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实学专题研究。各省市应当根据自己的学术特点和现有研究水平,集中人力和财力,选择最具有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专题,进行有组织的研究。诸如:“关学与实学”、“宋学与实学”、“湖湘学派与实学”、“浙东学派与实学”、“陆王心学与实学”、“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明清科技与实学”、“乾嘉学派与实学”、“经世实学与近代社会”、“实事求是与实学”、“毛泽东、邓小平与实学”、“中韩实学交流史”、“中日实学交流史”等等。只有在个案分析和专题研究基础上,才能对中国实学作出综合评价,得出规律性的科学结论。
实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哲学派别和社会思潮,也应如中国历史上的“玄学”、“佛学”、“理学”一样,有其固有的理论架构和逻辑范畴体系。对于中国实学的逻辑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完全揭示清楚,亦未能按照实学实际情况将它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思想体系。这是目前中国实学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同时,随着中国实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也需要我们及时作出科学回答,诸如中国实学的内涵和研究对象是什么?中国实学的主流与核心是什么?中国实学的起点、终点和发展阶段如何界定?宋明理学与实学的关系是什么?中国实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什么?如何评价中国实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国实学为何未能完成从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历史使命?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加大研究力度,从理论上加以说明。随着历史层面研究的深入,必然会提出新的理论问题,而新的理论问题的解决又会进一步推动历史层面的研究,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只注意中国实学的个案与专题研究,而忽视其理论层面的探讨,从长远看,必然会阻碍中国实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研究中国古代实学,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如何把中国实学的优秀传统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建构一个富有时代精神的现代“新实学论”呢?如何对中国实学进行现代转换呢?中国实学能够为现代化提供哪些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呢?中国实学的现代社会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只有对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才能赋于中国实学以新的社会生命力,实学才有存在的社会价值。在建构现代“新实学论”方面,近年日本学者提出了“实心实学”即“具有道德性的学问及科学技术”的实学构想,并根据这一构想,小川晴久先生撰写了《两种经济——“经济”与“乾没”》、山崎益吉先生撰写了《现代社会的危机和横井小楠的实学》、《生成论和日本的传统经济思想》等论文。韩国学者李佑成先生撰写的《韩国实学研究的理论与东北亚三国的连带意识》,尹丝淳先生撰写的《新实学论》;中国学者辛冠洁先生撰写的《明清实学思潮及其现实意义》,冯天瑜先生的《中国古典实学的近代转换》等,也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在这一方面,今后必须加大研究力度。
中国实学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封闭性思想体系,而是一门开放的国际性学问。历史证明,它不但善于及时地吸取一切外来文化的思想精华以补充、修正与发展自己,而且又善于将中国实学成果奉献给世界各国,以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中国实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开放品格。近十年来,中、日、韩三国在实学研究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不但在各国分别召开了东亚实学研讨会,而且还通力合作编辑出版了《中日实学史研究》和《中韩实学史研究》等,成绩斐然,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觉得在东亚实学研究与交流方面,还存在一个不足之处,就是由于未能深入地研究别国的实学思想,还是各唱各的调,未能做到真正的交锋与对话。在交流中要想真正进行更为深入的学术交流,除了研究本国实学外,还必须在各国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地加强和组织国际间的学术合作,深入地研究他国的实学思想,把实学变成一门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国际性的哲学流派。中国学者正在编写的《韩国实学思想史》一书,就是实施这一想法的一次尝试。只有在互相研究对方实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东亚社会发展需要,吸取其思想精华,将它转换成一门具有现代生命力的新的哲学思想体系,才能使它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思想动力。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中国实学研究前途似锦,百花烂漫的局面正在形成。二十年来,我们虽在中国实学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离时代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任重而道远”。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术力量,及时地引进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改进与加强实学研究,以期在实学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把实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水平,为建构“现代实学”作出我们应有的历史贡献。
收稿日期 1998—10—30
标签:理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明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