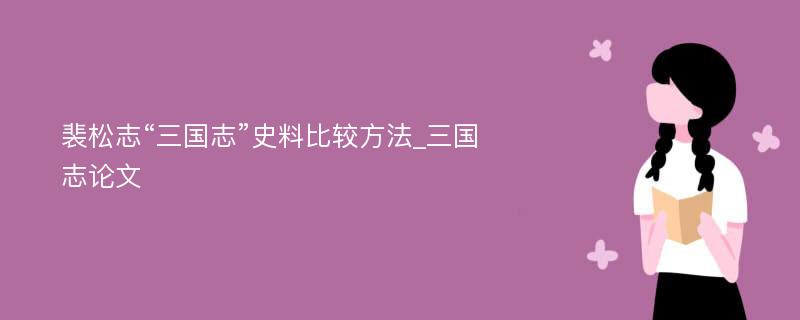
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比较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法论文,史料论文,裴松论文,三国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491(2007)01-0100-04
裴松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注家,其《三国志》注是古代史注名作。清朝学者李慈铭认为,“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中,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1] (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裴松之在史注中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他搜求资料“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2] (上三国志注表)外,与他巧妙使用史料比较法比勘异同,辨别是非,判别正误有关。杨翼骧先生认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开创了史料比较法并发展了史料考证学[3]。本文结合实例就裴注的史料比较法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比较本传前后文
《三国志》完成于三国结束不久,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4],裴松之作注有明确的补漏意图。但这种补漏不是机械地征引他书材料罗列出来,而是建立在对本传深刻研究的基础上。
裴松之注意研究《三国志》的本文,运用本校法以魏、蜀、吴三志的材料相互对证,发现其异同,并进而探察其是非优劣。《吴书·朱然传》记载:“赤乌五年,征柤中。”裴松之以《魏书·少帝纪》和《吴书·孙权传》的材料来论证该处纪年的失误:“按《魏少帝纪》及《孙权传》,是岁并无事,当是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裴松之对陈寿的史学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其著述“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2]。但并不因其成就而盲从其历史记述。他通过对《三国志》前后文的比较中发现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揭示,并且对陈寿提出严厉的批评。如陈寿在叙述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史实,《蜀书·诸葛亮传》强调诸葛亮对促成孙刘联合的作用,“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而在《吴书·鲁肃传》中,却又说鲁肃“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似乎促成合作的关键人物是鲁肃而不是诸葛亮,裴松之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文字处理很不赞同:“臣松之案: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
裴松之对陈寿在《蜀志》和《吴志》中相互歧义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批评本传在处理历史问题时体例不纯,不符合“载述之体”的要求。
比较本传与注文
裴松之征引大量材料补记本传,在使用各种材料时,发现所征引的材料与《三国志》本传有相同之处,也有许多相异甚至相反之处,就通过比较来辨明是非,得出结论。他的结论大体上有三类。
第一,本传是而注文非。裴松之认为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记述“事多审正”,在引用他书作注释,遇到与本传说法不同的材料,不轻易去否定本传,而是以审慎的态度进行比较,并以本传的记载来批评其他著作者的虚妄。《魏志·常林传》说:“晋宣王以林乡邑耆德,每为之拜。或谓林曰:‘司马公贵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马公自欲敦长幼之叙,为后生之法。贵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但是鱼豢《魏略》却说:“太傅每见林,辄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贵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补之”。比较两种说法,裴松之认为根据常林的人品,本传所云更有道理,“案魏略此语,与本传反。臣松之以为林之为人,不畏权贵者也。论其然否,谓本传为是。”
曹魏郎中鱼豢私撰《魏略》,刘知几说:“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6] (《古今正史》)。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用诸书中,以《魏略》的资料为最多。在注释中,裴松之虽然多次使用《魏略》的材料,但是将其与本传相比,认为其可信度上还是要大打折扣的,因此对《魏略》颇多微词,如“《魏略》妄谠”,“《魏略》此语,与本传不同”,“《魏略》此言,未达其心”等等。
关于刘备和诸葛亮最初相识过程,《魏略》和司马彪所著《九州春秋》均记载是诸葛亮主动去求见刘备,而没有“三顾茅庐”和“隆中对”。《魏略》曰:“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后来刘备自顾自编帽子,被诸葛亮直言谏阻,才注意到年少的诸葛亮。对于这个问题,裴松之更相信陈寿“隆中对”的记载,他分析说:“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诸葛亮的《出师表》自明其心志,是值得信赖的。
《三国志·袁绍传》记载,曹军攻破邺城后,“与(审)配战城中,生禽配”,审配拒不投降,“声气壮烈,终无挠辞”,慷慨受死。而乐资《山阳公载记》和袁暐《献帝春秋》却说审配兵败藏匿于井里,被曹军所执。虽然事情不大,但关乎一个人的名节,所以裴松之对此格外留意。他将《三国志·袁绍传》与二书做比较,并且征引《先贤行状》中有关审配“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节”的记述,认为陈寿所记在战斗中被俘更为可靠,而审配临危逃匿井中的说法不足信,并对这种作史态度予以严厉斥责:“臣松之以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岂当数穷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难信,诚为易了。不知资、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通过比较,裴松之不仅发现了征引材料与本传的异同,而且还发现了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在《魏延传》中,裴松之说明了《魏书》中多处不同于《蜀书》、《吴书》本传,是因为其材料多来自敌国传闻,总难免要带一些偏见,因而不可轻信,“臣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不仅敌国传闻不可与本传争审,家传之类的材料使用中也要谨慎。《魏书·刘放传》对刘放、孙资的影响做出了评判,认为“放、资既善承顺主上,又未尝显言得失,抑辛毘而助王思,以是获讥于世。”而《资别传》中却对孙资有言过其实的盛赞,裴松之指出:“案本传及诸书并云放、资称赞曹爽,劝召宣王,魏时之亡,祸基于此。资之别传,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负国之玷,终莫能磨也”。
第二,注文是而本传非。陈寿写《三国志》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阅读《三国志》时,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许多内容尤其是东吴的史料,显得不够充实,因此对许多问题无法做出清晰的阐述,甚至存在许多谬误。这就需要以注释材料指偏纠谬。《三国志·孙策传》注释中论证孙策的卒年,裴松之引用了《汉纪》、《吴历》的记述,分析认为“本传云孙坚以初平三年卒,策死时年二十六,计坚之亡,策应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则为不符。张璠《汉纪》及《吴历》并以坚初平二年死,此为是,而本传误也。”
陈寿写成《三国志》是在西晋初年,作为西晋大臣,陈寿不能也不敢根据实际情况直书事关司马氏罪行的事实,对于司马氏的行为不得不采取回护的办法。如对曹髦起兵向司马氏抗争,兵败身亡的过程却只字不提,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五月乙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这一点历来为史家所指责。刘知几批评陈寿对“发仗云台,取伤成济”的史实“杜口不言”,违背了直书准则[7] (《直书》)。裴松之看出了叙述的漏洞,征引《汉晋春秋》、《世语》、《晋诸公赞》、《晋纪》、《魏氏春秋》、《魏末传》等书达635字来补充陈寿对权臣司马昭指使成济“抽戈犯跸”的记载之缺。在对高贵乡公曹髦之死的记述上,裴松之认为《汉晋春秋》、《晋诸公赞》比陈寿《三国志·三少帝纪》表述得更完善,更符合历史事实。赵翼对裴松之的这段注释给予很高的评价:“使无裴世期引《汉晋春秋》及《世语》以注之,竟似考终寝殿者矣。”[8] (《卷六》)
《袁术传》中讲,“(袁)术以余众奔九江,杀扬州刺史陈温,领其州。”裴松之引用王粲《英雄记》的叙述来分析本传,认为本传记载失实,“臣松之案英雄记:‘陈温字元悌,汝南人。先为扬州刺史,自病死。袁绍遣袁遗领州,败散,奔沛国,为兵所杀。袁术更用陈瑀为扬州。瑀字公玮,下邳人。瑀既领州,而术败于封丘,南向寿春,瑀拒术不纳。术退保阴陵,更合军攻瑀,瑀惧走归下邳。’如此,则温不为术所杀,与本传不同。”裴松之倾向于认同王粲《英雄记》的说法,以王粲的观点来纠正陈寿记述的偏谬。
有些问题,《三国志》与其他书的说法差异非常大。楼玄是东吴刚正大臣,他“正身率众,奉法而行,应对切直,数迕皓意”,被孙皓放逐到交趾,并密令交趾令张奕将他杀掉,《三国志·楼玄传》曰:“玄一身随奕讨贼,持刀步涉,见奕辄拜,奕未忍杀。会奕暴卒,玄殡敛奕,于器中见敕书,还便自杀。”《江表传》的说法与本传不同:“皓遣将张奕追赐玄鸩,奕以玄贤者,不忍即宣诏致药,玄阴知之,谓奕曰:‘当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药死。”裴松之认为,楼玄是清高之士,不会因为个人安危而改变操守,曲意逢迎,因此,《江表传》的记述更符合情理,“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无缘骤拜张奕,以亏其节。且祸机既发,岂百拜所免?《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
第三,本传与注文“未详孰是”。由于资料的缺憾,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比较得出结论。比较正文与注文的目的是决定是非,但在一些地方,裴松之也坦诚地承认“未详孰是”。《三国志·张邈传》说张邈穷途末路,投奔袁术,为其兵所杀,而《献帝春秋》却说张邈进谏袁术上尊号。裴松之找不到确凿的材料来证实哪一种说法更符合事实,不敢妄下结论,所以他以信则传信,疑则存疑的态度说:“按本传,邈诣术,未至而死。而此云僭称尊号,未详孰是。”《高柔传》中记载:“柔从兄干”,而《陈留蓍旧传》等却说高干是高柔的从父,裴松之注释说:“案《陈留蓍旧传》及谢承书,干应为柔从父,非从兄也。未知何者为误。”裴松之将诸说并存,供人们择善而从。
《隋表》不曾提及陈泰为太常一事,而干宝的《晋纪》则曰:“太常陈泰”。裴松之无法搞清楚依据所在,无法确定干宝《晋纪》中相关记载的来源,所以说“案本传,泰不为太常,未详干宝所由知之”。柳诒徵说:“至于征引异同,固多断制,然于考核,亦复不讳言未详”[9] (《三国志裴注义例)》。
注文比较
在注释《三国志》中,裴松之总是对一个事实要征引几种材料予以补证。由于时代局限和作者个人知识结构、撰述旨趣的差异,所征引的材料之间往往又是互相矛盾的。裴松之仔细辨别,提出自己的看法。除了将本传与注文做比较以外,还注意比较注释材料的是非优劣。《孙皓传》注中说:“文多不悉载”;公孙瓒、荀彧传中说:“余语略同者删”,可以看出裴松之对征引的材料还是有去取的。
第一,同作者记述的比较。在为《嵇康传》作注时,裴松之引用了孙盛两部史书中的记述。《魏氏春秋》说嵇康“采药于汲郡共北山中,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逾时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晋阳秋》却说:“康见孙登,登对之长啸,逾时不言。康辞还,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惜哉!’”。裴松之评论说:“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
《三国志·董允传》注引习凿齿《襄阳记》讲董允随费祎出使东吴,机智地回答孙权的提问,“臣松之案:《汉晋春秋》亦载此语,不云董恢所教,辞亦小异,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柳诒徵说“孙、习一人所为之书,互有抵牾,裴氏皆抉发之”[9] (《三国志裴注义例》)
第二,异书材料的比较。《三国志·诸葛恪传》中记载了孙亮与孙浚谋算诸葛恪的过程,“酒数行,亮还内。峻起如厕,解长衣,著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据《吴录》记载:“峻提刀称诏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为!非我所为!’乳母引亮还内。”而《吴历》却说:“峻先引亮入,然后出称诏。”裴松之结合本传对两种材料做审慎的分析比较,认为《吴历》更符合实情,且与本传一致,“臣松之以为峻欲称诏,宜如本传及《吴历》,不得如《吴录》所言。”
《三国志·孙綝传》记载:“亮遂与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议诛玖妃,劲女也,以其谋告沮,夜袭全尚,遣弟恩杀刘承于苍龙门外,遂围宫。”裴松之引用《江表传》的材料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还引用孙盛的一段评论文字分析此事,最后做出判定:“《江表传》说漏泄有由,于事为详矣。”
刘知几注意到了裴松之注释《三国志》的异同比较法,但对这种作法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裴氏“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4] (《补注)》。陈振孙认为,裴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7] (卷四“三国志”条)。这些批评有失公允,清朝学者以“护惜古人”的态度来评断裴注,钱大昭说:“世期引据博洽,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别成畦町”[8]。钱大昕指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8] (《自序)》。正如人们对刘知几“阳毁其书”,一边却“阴用其法”,刘知几在批评裴松之补阙式史注的同时,却在使用裴注所采用的比较法。柳诒徵指出“裴之精心撰注,非漫为捃摭掇拾者比也”[6] (《三国志裴注义例)》,柳诒徵进一步认为刘知几师法裴松之的评断方法:“裴氏之注,不第可谓陈志功臣,且可谓为晋代诸史之南董,刘知几之治史,盖多师其意。”[6] (《三国志裴注义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