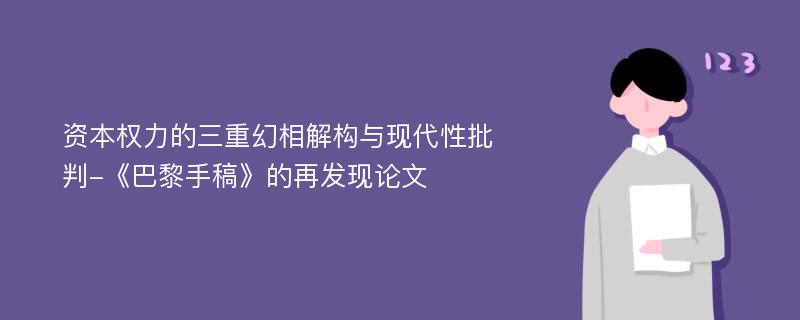
资本权力的三重幻相解构与现代性批判——《巴黎手稿》的再发现
王 雪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长春 130012)
摘 要: 对资本权力的批判成为现代政治和现代政治哲学的重要主题。在《巴黎手稿》中,资本权力问题初现端倪,与现代性批判问题相遇,呈现出一个内在贯通的总体。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权力的三重批判解构了三重幻相,实现了对现代性的两大根基——资本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同时,在对资本权力三重幻相的解构中,沿着“哲学—经济学—哲学”的路径,马克思真正构建了政治哲学的经济学地基,生成了政治哲学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哲学”语境。
关键词: 资本权力; 财产权; 劳动; 自由; 共产主义
海涅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方:“每一个时代都是一头斯芬克斯,人们一旦揭破它的谜,它就跳进深渊。”[1]要想让资本这头斯芬克斯跳进深渊,对资本权力的澄明是必要的条件。资本作为明确主题首次出现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巴黎手稿》)。在《巴黎手稿》中,资本权力问题与现代性问题合二为一,表现为资本权力的三重幻相:资本正当性幻相、劳动幻相和自由幻相。通过对三重幻相的解构,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自由观的批判,从而建构了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框架;同时,通过将政治哲学权力批判内含于经济学之中,马克思构筑了政治哲学的经济学地基。
水库的管理体制建设结合“河长制”统筹考虑,由河长负责全面抓好水源保护各种管护措施落实,遏制人为污染水源现象,及时发现和妥善处置突发水环境事件。出台适应水库管理与保护实际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确保水质安全达标。
一、 资本正当性幻相解构——对资本权力的还原
现代性批判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哲学主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回顾“巴黎时期”①的思想发展历程时提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是马克思批判现代性、寻找人的解放与自由路径的起点。在“巴黎时期”,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诉求具体表现为,通过透视国民经济学以寻找人的解放与自由路径,并将资本首次作为明确主题。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视为“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3]。据此,马克思揭开了资本的神秘面纱,并确定了资本的现实形式——一种权力。资本权力以成文法的形式在物质世界中确立下来,表现为财产权。资本权力合法性的哲学根据在于资本正当性的历史幻相,这一历史幻相由早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奠基,以国民经济学作为理论前设,表现为作为一般权利的财产权以及具有正当性的财产和资本。
财产权理论起源于哈林顿,但财产权作为一般权利并具有正当性这一原则的奠基人则是洛克。在《政府论》中,洛克提出,私有财产就是一种自然权利,“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4]。将劳动作为财产合法性的根据,并将财产权理解为人天生所固有的权利,借此,洛克奠定了财产权理论的基础,将财产权的发展内含于市民社会的发展之中,财产权成为现代社会私有财产正当性的理论根据。
洛克及其后继者斯密将财产权以自然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将这种财产权的应然状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根基。财产权的应然状态以理论的形式破除了中世纪神权与王权对财产的独占和侵害,将财产权设定为一种名义上人人都可以通过劳动占有的权利。政府为先占和私权提供制度保障,以法制支撑权利,财产权合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财产权合法化的过程。资本通过财产权攫取权力,这种权力完全内嵌在法律系统和治理机构中,取得了合法化的地位。
《巴黎手稿》直接面对的正是这种充斥着资本权力的资本正当性幻相,这种幻相以财产权所承诺的应然状态作为理论根基,确立了资本权力的合理化与合法化地位。然而,生活现实所显示的财产权的实然状态与资本正当性幻相的承诺背道而驰。财产权并没有成为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保障,却成为资本权力的保护伞,将人类中的大多数变成了完全没有财产的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成为无法跨越的沟壑。
幼儿园阶段的教育是学生接受教育的开端与基础部分,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影响深远。但由于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乡镇中心幼儿园普遍陷入师资力量匮乏,教师队伍管理问题层出不穷的窘境[1]。许多教师由于自身业务素养低,教学方法守旧,没有站在幼儿未来发展的角度思索自身的教育存在问题。因此,加强乡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队伍的管理势在必行。
且QF41、QF42同QF43不能同时合闸[3]。该系统充分考虑到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主回路系统图见图2。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发现并解构了这种资本正当性幻相。首先,马克思拒绝对私有财产的无条件认同,通过对资本权力的本质还原实现对资本权力的消解以及对资本正当性的解构。对资本权力的本质还原必须通过对表现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镜像还原”完成,因此,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以历史原则介入资本问题,从私有财产构成要素的历史变迁入手实现对资本的“本质还原”。通过这种还原,马克思揭示出资本的历史变迁及其历史限度,破除了表现为财产权的资本权力的正当性。同时,通过将作为“一般权利”的财产权解构为“穷人的权利”,马克思进入了社会问题的批判视域。
拨开层层迷雾,马克思找到了“异化人”生存状况批判与“劳动幻相”批判的关键点——异化劳动批判。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论证了工人的异化是由“自己的劳动产品”成为他的“异己的对象”这一过程造成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活动具有强制性质,导致人同外部世界的创造性的相互影响所固有的统一破裂,僵化的制度割裂了劳动过程与劳动活动,割裂了人的意识和人的存在。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处于萌芽阶段的异化理论,并把它改造成为辩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哲学现象,它存在于阶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雇佣劳动制度把劳动转化为外在于工人的、不受工人控制的、非人的物自体。马克思指出,仅仅通过哲学上的或理论上的理解(虽然这是革命行动所需要的前奏)是不可能消除异化的,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才能消除异化[10]。根据异化劳动这一观念的矛盾运动逻辑,马克思明确指出消除异化的方式:“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81。“劳动幻相”的破除需要在一种新的社会变革中得到解决,马克思描述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这一社会中,异化现象才能被消除,现代性的矛盾才能得到解决。
在“巴黎时期”,马克思的主要论敌是国民经济学家。在研读萨伊、斯密著作的基础上,马克思试图还原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3]44。国民经济学家已经论证了,地产作为“私有财产的根源”,是“它的领主的无机的身体”[3]44-45。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获取财产的方式为“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有所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取地租”[3]35。地租的数量取决于土地富饶的程度和土地的位置。并且,地租随着人口的增长、交通的改善、交通工具的多样化而逐渐增加。土地所有者通过操控地租榨取社会利益[3]39,不仅仅拥有对于所属土地的支配权,还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农奴是土地的附属物[3]44。资本最早从掠夺得来的土地中产生,掠夺者通过“先占权”转变为土地所有者,并通过对地租的操控,使得土地所包含的异化力量——对他人的统治成为现实。这种统治最初仅仅覆盖土地的附属物——农奴,随着私有财产的运动,统治的范围不断增大,最终演变为凌驾于自由人之上的统治权。统治权随着财产权的合法化而合理化,造成了自由人之间的不平等。马克思继续指出,随着私有财产的运动,地产与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存在论基础上的“主奴辩证法”——地产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3]45,由“资本之母”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其政治属性被资本的抽象原则所辗轧,私有财产的原则和资本的原则最终统治一切,形成资本权力。马克思描述了这种变化:“地产的根源,即卑鄙的自私自利,也必然以其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稳定的垄断必然变成动荡的、不稳定的垄断,变成竞争,而对他人血汗成果的坐享其成必然变为以他人血汗成果来进行的忙碌交易。最后,在这种竞争中,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因资本运动的规律而破产或兴起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3]45-46随着地产成为资本的一部分,土地所有者以租地农场主的身份出现,本质上成为普通的资本家,自由人成为雇佣工人,服从资本权力的支配。资本以财产权的名义索取增值价值,使得资本正当性幻相所确立的财产权合法性与一般权利原则所要求的公民平等自由不能兼容,其政治本质在于财产权的压迫性。
自然概念成为探索自由问题的重要启端,由自然生发出的自由问题更具有现实穿透力,马克思以此根本性地颠覆了传统政治哲学的范式。无论是英法政治哲学的“权利-自由”范式还是德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先验-自由”范式,都无法避免“权利变异”的难题。社会契约论传统忽略了对人的无穷需求的限制,德国观念论传统使自由成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传统政治哲学的缺陷决定了“权利”畸变成“权力”,从而限制权利的发展,资本权力的自由幻相正是这种畸变的显现。黑格尔看到了这一难题,所以他才说道:“在对外在事物的关系上,合理的方面乃是我占有财产。但是特殊的方面包含着主观目的、需要、任性、才能、外部情况等等。占有光作为占有来说固然依赖于以上种种,但在这种抽象的人格领域中,这一特殊方面还没有与自由同一化”[16]。面对自由幻相和与之相伴的“权利变异”难题,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活动描述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将自由确立为现实生命的活动原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3]57。同时,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83。马克思将“自然的人”转换为“社会的人”,以价值维度重新确立自由概念。
通过对资本权力正当性幻相的解构,资本的压迫性使得资本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国民经济学语境中的“货币”,而是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对资本的理解使得马克思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分道扬镳,这一理解一以贯之于马克思的整个学术生涯之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6]。这种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支配他人的社会权力,这种畸形的权力不仅表现为其自身通过财产权合法化,也表现为对劳动的控制和扭曲。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权力的现代性本质还原完成了对资本正当性幻相的解构,解构资本正当性幻相的同时,马克思也实现了对劳动幻相的解构。
护理质量控制指标体系设置包括指标配置模块、数据采集模块及自动统计分析模块,通过与信息部门合作,将此质量控制指标体系嵌入护理信息系统。①指标配置模块:此模块旨在建立并持续维护指标库,共收录39项经筛选确定的指标,分别以二级指标形式体现;②数据采集模块:通过信息化数据平台与现场评价相结合方式采集数据;③自动统计分析模块:依托护理信息系统自动进行大数据分类汇总,通过内置品管工具自动分析。
二、 劳动幻相解构——“异化人”生存论状况批判
私有财产正当性的理论前提在于洛克奠定的“劳动财产论”——私有财产的正当性来自劳动。劳动作为财产权的正当性依据,是人们获取自由和幸福的手段,其本身具有合理性。这是早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为构建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而引入的理论预设。然而,在资本权力的统摄下,资本“作为死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6]260。使得早期自由主义的理论预设被扭曲为“劳动幻相”:劳动本应作为人自我实现的方式,却成为资本权力束缚人的手段。
“劳动幻相”的理论预设为国民经济学所发展继承,根据马克思对斯密的重述,“私有财产的主体性质就是劳动”[3]73。那个时期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主流范式是:把财产权视为个人意志对物的支配权,而马克思超越了主流范式,把财产权视为一种反映人际关系的因素。私有财产本身所包含的这一关系可以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财产作为“一定量的积蓄的和储存的劳动”[3]22是资本,作为资本拥有着“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3]21。理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关键节点在于理解劳动的异化,这是马克思破除资本权力“劳动幻相”的关键所在,也是马克思对“异化人”生存论状况批判的枢纽。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理论的费尔巴哈式尝试。为了说明“一般劳动”与本义上的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以及“一般劳动”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的“劳动”概念,以哲学统摄国民经济学术语,建立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勾连。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解读为:“人类此在的一个基本性事件,作为一个连续不断贯穿整个人的存在的事件。”[7]许多诠释者注意到马克思“劳动”概念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马尔库塞说:“在努力为政治经济学建立一个新基础这种语境中,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及其一切本质特征。”而查尔斯·泰勒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作用观念在黑格尔关于劳动概念的“主奴辩证法”中已初现端倪[8]。经过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劳动”概念的继承和重构,劳动已经变成了一种具有解放作用的人的存在的基本性事件。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并不是对于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拷贝,而是一种“综合”的产物。黑格尔的“精神”观念、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都成为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内核[9]。在谈及《精神现象学》的贡献时,马克思说:“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3]101。但马克思同时指出:“他(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3]101那么,黑格尔没有看到的“劳动的消极的方面”是什么?这个消极方面被马克思概括为“异化劳动”。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描绘出这种自由幻相存在的实质:当代伦理世界只有统治,看似已经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统治,但人仍然处于统治与被统治的分裂之中。自由被虚化了,名义上是一种理念,实质上却成为一种宣传性质的教条。人们往往沉浸在这种教条之中,自以为生活信条已然与自己的现实境况等同;自以为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劳动和思想,却无时无刻不在资本权力的压制和胁迫之中。
异化劳动理论解构了资本权力的“劳动幻相”,动摇了传统财产权理论的前提,同时批判了“劳动幻相”之下产生的“异化人”的生存论状况。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将异化问题从哲学理论问题转变为社会政治中的自由问题。马克思和古典自由主义者都把“自由”置于核心地位,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从社会变革而非理性建构的角度重新诠释“自由”概念,这种独特的切入点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意识批判的特色。
“当初,张仪在西边兼并巴蜀的土地,在北面扩大了西河之外的疆域,在南边夺取了上庸,天下人并不因此赞扬张仪,而是认为大王贤能。魏文侯任命乐羊为将,带兵去攻打中山国,打了三年才攻下。乐羊回到魏国论功请赏,魏文侯却把一箱子告发信拿给他看,吓得乐羊行跪拜大礼说:‘攻下中山国不是我的功劳,全靠主上的威力啊。’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预言共产主义到来的确切时间和具体建构,而是承诺了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3]81。历史上的哲学家多多少少愿意充当“预言家”的角色,根据自己把握到的哲学对未来世界进行预测,但《巴黎手稿》中的马克思不在此列。马克思承诺了共产主义的解放意蕴,但关于潜在的人的自由愿景在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中并未得到详细阐明。从这一层面来说,马克思认为他不能预言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的各个方面。相反,他提出人的解放的本质就是自由的人们摆脱了异化和统治而能做出的选择,在自由状态下,人性将创造自身。马克思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提供了足够的留白,并给人的创造性以最大程度的确证。
然而,在以劳动形式表现出的外化活动中,人们的应然存在状态一直受到阶级社会现实的扭曲。马克思在提出这种具有历史特征的劳动和人们生存状况理论时借用了黑格尔意识理论中的概念“异化”。在人们的实然生活状态中,劳动更多体现的是作为谋生手段的工具性的内涵。劳动形成“自觉异化”,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价值理性式微,最直接的后果是,产生了现代性问题视域中的独特群体——“异化人”。“异化人”代表着“异化劳动”制度下现代存在论困境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劳动从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不得不为的活动;人们应该是财富和金钱的主人,却沦为附庸和奴隶;人们的生存不是为了彰显生命本身的价值,而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在现实生活中,“异化人”仅仅被满足最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人与外界物质条件的辩证关系发生了颠倒。人由“主人”变成了“奴隶”,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人们对于这一状况无力改变,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这一状况缺乏自觉性认知。
三、 自由幻相解构——现代性意识批判
哈耶克认为,在洛克、边沁等开创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私有财产权与自由、平等堪称自由主义人权的三位一体[11]。以现代政治哲学为背景,财产权理论与资本权力问题从属于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自由问题。无论是对于洛克来说,还是对于马克思来说,传统财产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对自由的建构。萨拜因认为,洛克的学说尤其是他的财产权理论,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论证政府的起源和根据问题,而是为维护个人自由以及反对政治压迫提供合理性论证[12]。自由问题之于资本权力批判问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权力批判与现代性批判的共同问题。
近代市民社会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摆脱了宗教与宗法束缚的独立个人要求建立一个以现代性为奠基的社会。这种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的信仰,人们不再憧憬彼岸的天堂,而是希求在尘世中建立天堂[13]。带有现代性特征的资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超越了以往所有的时代,以现代资本为奠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是基督教所许诺的“天国”的尘世化。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博爱等信条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所承诺的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由的共同体。但与资产阶级所承诺的自由社会相反,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个体并没有获得自由。这说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所承诺的自由不过是一个幻相。
从现代政治哲学史的思想脉络来看,这种自由幻相源于现代政治哲学中漂浮在半空中的、虚化的自由理念。现代政治哲学中的自由理念源于两个传统,这两个传统均有使自由概念虚化的倾向。一方面,马基雅维利开启了近代政治哲学对于人的权利的初始探讨,霍布斯以“自我保存”深化了整个社会契约论传统中自由理念的基本内涵,洛克把自由理念彰显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在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支配下,整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传统将自由界定为自我保存的欲望与自我利益的追求。这种自由理念看似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实际上仅仅描绘了自由的一种“应然”状态,这种“应然”状态囿于私人利益的囚笼,看似与经验世界相契合,实际上却与真正自由世界的建构脱节。另一方面,在德国古典政治哲学中,自由被先验化为一种至上的原则,康德秉持了与卢梭一致的方向,将自由看作人类的自然禀赋,如黑格尔所言:“卢梭已经把自由提出来当作绝对的东西了。康德提出了同样的原则,不过主要是从理论方面提出来的,法国则从意志方面掌握这个原则。”[14]康德将自由先验化到了形而上学层面,确立了自由至上的原则。讽刺的是,自由理念的先验化使得自由成为了漂浮在天空上的理念,在现实世界,对形而上学的忠诚早就被人抛在了故纸堆中,自由的实现遥不可待。正如阿多诺所说:“即使是实践哲学,当它关系到我们实际行动的时候,就总是与经验材料有关,因而就不能绝对地与经验相分离。”[15]以上两个传统的共同结果是,自由陷入一种自我否定的幻相之中。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劳动概念进行了唯物主义处理,突出其物质性内涵,却没有完全排除黑格尔劳动概念的精神意蕴。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根本特征是把人的个性、意图和目的投射到自然之上的“外化活动”,人的本质正是在作为“外化活动”的劳动中得到彰显。人们通过自己的外化而界定自身,这种外化不受强迫、监督或强制。劳动应该体现出人的尊严和价值,人们在劳动中肯定自己、得到幸福。
在《巴黎手稿》中,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乃至整个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寻得解构自由幻相的枢纽——自由幻相的解构不能诉诸于对自由观念的切割,真正彻底的批判必须立足于现实生活本身。与形而上学的先验化的传统不同,马克思强调,“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3]105。自然性的需求是人存在的基础,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3]105。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离开霍布斯和洛克以自然推导自由的理论路径,但马克思视野中的自然并不是纯粹的无机界,而是与人的生产生活相连、以人的活动为介质的“精神的无机界”。由此,马克思强调自然指向人的属性,将自然需求看作真正人的机能,自然关系也就成为合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
通过对于私有财产起源的追溯和“地产-资本”辩证关系的还原,马克思论证了财产的不合理性和财产权的压迫性。尽管马克思继承了传统财产权理论的某些理论前提,尤其是继承了将财产权与个人自由相联系的观点,但经过对私有财产的“本质还原”,他确证了财产权与自由之间的相互背离。财产权的基础在于私有财产的合理性,而私有财产的起源——地产,本身就是通过不合理的掠夺手段产生的,并造成初始意义上的不平等。随着私有财产的运动,地产沦为商品,资本形态的私有财产统治一切社会关系和自由人,形成资本权力。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和掌控对无产阶级而言“是摧毁而不是培育了人格”[5]。通过揭示私有财产起源上的不合理性和社会生活中的反人格性,马克思成功解构了资本权力的历史幻相,资本作为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丧失了其合法性根基。在这种批判性视域下,财产权问题与现代性批判合而为一。马克思在完成对资本权力正当性幻相解构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资本的批判。
以“社会的人”作为自由理论的立足点,马克思所厘定的自由概念至少包含三个维度:权利话语维度、价值平等维度、超物质维度。这也回答了在资本权力的自由幻相中不能回答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针对人的自然需求,自由的权利话语维度要求认识到劳动产品是劳动能力自身的产品。如马克思所言,“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17]自由的价值平等维度使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推上被告席,并要求人超越自然人的利己局限而进入互利共生的社会共同体。自由的超物质维度指向了人超脱于物而成为人的需要,即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自由概念必须涵盖自我实现的意蕴,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区别了“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162-163。动物与人的真正区别在于属人的创造性,这种本质性的区别必须成为自由概念的核心。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域中,自由问题具有双重视域,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社会实践问题。通过为自由概念厘定三重维度,马克思破除了资本权力的自由幻相,并通过对传统政治哲学核心概念——自由的重新定位完成了对现代性意识的批判,资本权力批判问题与现代性批判问题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合二为一。
四、 结 语
马克思以对资本权力三重幻相的解构揭开了资本权力的神秘面纱。资本权力根植于扭曲的资本逻辑神话之中,以人与物关系的颠倒和异化产生并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奴役。更深层的根源是资本对人的支配,资本以现代性为同谋,将自己的对手——劳动和整个世界席卷于自身之中,并完成自我消化和融合,使现代人和现代世界受资本权力的支配,这是现代性最核心的病症。马克思为超越资本逻辑、消解资本权力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对于资本权力的批判和瓦解也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终极主题。
著名美学家周来祥教授认为:“审美文化是一切体现了人类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趣味,从而具有审美性质,可供人们审美观照、情感体验和审美感悟,并可使人们从中得到一种审美愉快的文化。”[2]在企业审美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和谐企业建设要遵循以下原则: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以对资本权力的还原、对异化人存在论状况的批判和对自由概念的重新厘定解构了资本权力的三重幻相,批判了资本以及资本背后的现代形而上学,形成现代性批判的总体视域。《巴黎手稿》并非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起点,却成为现代性批判范式转折的第一个大纲性文本。在对资本、劳动、自由三者的内在本质和相互关系的揭示中,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指出超越现代政治哲学逻辑的根本路径,构筑了政治哲学的经济地基,开启了研究欧洲社会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哲学”语境。这一语境蕴含着早期政治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内涵,其现实关怀是为彻底改变穷人的境遇,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可能路径。由此,马克思与早期政治哲学家彻底区别开来,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巴黎手稿》是这一宏大叙事的开端,可以视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真正诞生地。
注 释:
在构建微纳测头支撑机构的整体刚度模型时,假设除支撑梁以外的其他部件皆为刚性构件,支撑梁的变形处于弹性变形范围内,支撑梁是薄壁梁,不考虑横截面剪应力的影响,故可采用Euler-Bernoulli梁模型[13]。
①1843年10月至1845年2月,马克思一直居住在巴黎近郊,后人把这一时期称为“巴黎时期”。
为了适应新时期防汛抗旱工作需求,加强防灾抗灾现场监测手段,提高监测能力,江苏省防办组织研发了防汛防旱移动式应急指挥所。
参考文献:
[1] [德]海因里希·海涅.海涅全集:第8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2000.
[4] [英]洛 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 Radin M J.Property and personhood[J].Stanford Law Review ,1982,34(5):957-1015.
[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4.
[7] Marcuse H. Heideggerian Marxism [M].Nebraska: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
[8] 查尔斯·泰勒.黑格尔[M].张国清,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9] Berki R N. On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rx’s concept of labor[J].Political Theory ,1979,7(1):35-56.
[10]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 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1]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2]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M].刘 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3] [美]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M].刘 振,彭 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14]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 麟,王太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5]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M].谢地坤,王 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6]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 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The Deconstruction of Triple Illusions of Capital Power and the Criticism of Modernity —the Rediscovery of the Paris Manuscript
Wang Xu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 powe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heme of modern politics and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Paris Manuscript ,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 power issue and its encounter with criticism of modernity presents as an integrated unity. Marx deconstructed the triple illusions by the triple criticisms of capital power, and realized the criticism of the two foundations of modernity — capital and metaphysic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triple illusions of capital power, along with the path of “philosophy-economics-philosophy”, Marx indeed constructe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generated the “economics-philosophy” context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ssues.
Keywords : capital power; property rights; labor; freedom; communism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339(2019)03-202-06
收稿日期: 2018-11-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72005).
作者简介: 王 雪(1992— ),女,博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王 雪,55246654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