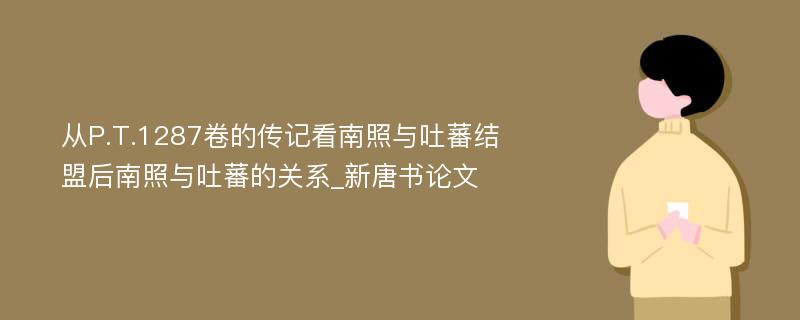
从P.T.1287卷的一篇传记看南诏与吐蕃结盟后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南诏论文,传记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吐蕃史古藏文写卷P.T.1287卷的主要内容为吐蕃赞普传记。在所载的赞普传记中,有3篇传记的内容与南诏(包括洱海地区其他民族部落)有关,即赤都松、赤德祖赞、赤松德赞三位赞普的传记。这三位赞普的在位时间分别是:公元676-704年、704-754年、755-797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正是南诏与吐蕃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赤都松赞普在位时,虽“夺取六诏(Vjang)之疆土,征白蛮(mywa dkar po)之赋税,收乌蛮(mywa nag po)为属民”,①但南诏当时势力弱小,与吐蕃的关系不可能达到与之结盟的阶段,所以此处不作专门探讨。赤德祖赞传记反映了南诏与吐蕃结盟前后的密切往来,笔者将另作研究,这里重点分析赤松德赞传记中的有关记载,以探讨南诏与吐蕃结盟后关系的变化。
赤松德赞于赤德祖赞去世后的次年,即755年继位。据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活了56岁,卒于丁丑年,即797年。②至其去世时,一直在位,是吐蕃时期又一著名赞普,执政近半个世纪。赤松德赞在位时期,是吐蕃王朝发展到全盛而后又逐渐走向衰落的阶段。传记中称:“此赞普时代,疆域之辽阔,为以往历代所不及也。”这与汉文史籍的相关记载是吻合的。就与南诏的关系而言,赤松德赞掌政时期,南诏先是阁罗凤在位,779年阁罗凤去世之后,其孙异牟寻继立,南诏与吐蕃矛盾渐加深。794年南诏背蕃归唐,联合唐王朝对付过去的盟友,南诏与吐蕃的联盟关系完全破裂。分析《新唐书·南诏传》所载《异牟寻帛书》及樊绰《云南志》所收的《赵昌奏状》,可知南诏与吐蕃结盟之初和结盟之后都存在矛盾,但双方结盟期间是否有过武装冲突,关系是否出现过大的反复,汉文史籍里没有任何记载,幸有藏文写卷对这方面做了虽然有限但十分重要的记载。
与赤德祖赞的传记相比,赤松德赞传记中有关南诏的记载占的比例不大,但极有史料价值:
后来,原先收编为属邦的白蛮反叛,赞普命没卢·燃木夏为大将征讨。于岩山之巅交战,斩杀南诏多人,执副都护、微末小吏及平民以上大小官员共一百一十二人。南诏王迷途知返,又前来致礼,遂真正收抚为编民,摊税使役如以往所供。
这段记载中的“白蛮”(mywa dkar po),应即赤德祖赞传记中所记的“白蛮”,即南诏。后面提到了南诏王(vjang rje),更明确是指南诏。这一段材料十分明确地记载了南诏与吐蕃结盟之后发生过武装冲突,但遗憾的是没有具体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记载之前,还有一句话,虽然与南诏没有直接关系,但据此可推测南诏与吐蕃冲突的大致时间:“此赞普之时,没卢·赤努燃木夏进兵兑巧(上方),招抚于阗为属邦,征派赋税。”将这句话与其后有关南诏的记载联系起来分析,可以确定南诏与吐蕃的冲突发生在吐蕃“招抚于阗”之后。不过“招抚于阗”究竟在什么时候,仍需要结合其他记载探讨,下面具体讨论时再谈此问题。
根据赤松德赞传记所记的这段材料,可以肯定:首先,南诏与吐蕃在公开结盟之后曾发生过较为激烈的武装冲突,这一冲突最后以南诏的失败而告终;其次,这一冲突发生在赤松德赞执政期间,而下令派军队攻打南诏的,正是赤松德赞赞普。由于传记所记较为明确,对于这两点学术界没有不同的看法。前已谈到,赤松德赞为赞普时期,南诏先是阁罗凤在位,779年阁罗凤去世后,由异牟寻继位。那么,南诏与吐蕃的武装冲突是发生在阁罗凤时期还是异牟寻时期呢?这虽只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但很重要。结盟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并记入吐蕃赞普传记,说明这一事件有一定影响,当时吐蕃对此也十分重视。因此,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南诏与吐蕃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传记中有关记载不明确,目前对南诏吐蕃间这一冲突究竟发生在南诏何人统治时期分歧较大,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认为发生叛乱的可能就是南诏,或是南诏的部分居民。在其著作中转引日本学者佐藤长《古代西藏历史研究》的看法,即“8世纪70年代中期”南诏的部分居民与吐蕃发生了短暂的破裂,而且这一事件与汉文史籍中“剑南兵合南诏”大破吐蕃的记载可能是相互关联的。③如果这一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南诏与吐蕃的武装冲突就发生在阁罗凤在位晚期。从发表的论著来看,这种观点提出时间较早。马德教授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南诏反叛而吐蕃以武力征服之事发生在唐德宗贞元七年(791)。传记中所记“斩杀南诏多人,执副都护,微末小吏及平民以上大小官员一百一十二人”,即汉文史籍中所记的“执以送吐蕃”的段忠义和吐蕃取为质的南诏大臣之子。不过,据传记所记这一百多人可能是在战场上俘获的。④如按此看法,南诏与吐蕃的武装冲突也就发生在异牟寻即位之后,此时已是赤松德赞掌政的晚期。
以上两种看法都有依据,哪种更有说服力,需要看其所依据的材料。分析以上这两种看法的依据,除了所引的可能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汉文史籍外,相同的是赤松德赞传记相关记载中的一段文字。这段重要的材料译法不同。原文是:“vjang rje gol gyis kyang byag vtsal”。其中关键的是对“gol”的理解。这段文字可以译为“南诏王迷途知返,又前来致礼”或“南诏之王阁罗(凤)亦前来致礼”。⑤两种译法比较,不同之处就在“gol”的翻译上。在赤德祖赞传记中,曾明确提到阁罗凤,原文为“kag la bong”,如将“gol”视为“阁罗(凤)”,与同一写卷中的“kag la bong”差异明显。前一种译法将“gol”译为“迷乱、错误”,没有将其视作人名。比较这两种译法,结合双方的冲突,前一种可能更合原意。但是,南诏与吐蕃结盟后的这场冲突并不能因此断定就发生在异牟寻时期,换言之,即使按此译法,在阁罗凤后期发生这场冲突仍有可能。因此还需结合其他材料作进一步分析。
前已言及,传记在记南诏与吐蕃这场冲突之前,还记载了吐蕃在赤松德赞时期“招抚于阗为属邦,征派赋税”。据此,可知这场冲突发生的时间是在招抚于阗之后。这一点虽然不会有什么争论,但南诏与吐蕃这场冲突的具体时间却仍难以确定。这是因为,首先,于阗在藏文中称作“li yul”,是有广义、狭义之别的,狭义上的li yul指于阗一镇,而广义上的li yul则指今新疆南部或更广的地区。⑥从传记所记,很难判断其中所说的于阗是指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或者于阗的某一地区。其次,唐蕃战争中,狭义的li yul成为唐与吐蕃必争之地,你争我夺,几度易手。尽管国内外学者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材料,考定吐蕃控制于阗全境时间在公元791-792年或790-796年之间,但早在安史之乱后,于阗一些地方应已在吐蕃的控制之下。⑦其三,此传记中“招抚于阗”的记载是否就是指控制于阗全境,也缺乏进一步的材料证明。分析此传记的有限记载,很难确定“招抚于阗”是指吐蕃控制于阗全境。由于这几个原因,此传记中“招抚于阗”的时间显然还不能确定。这个时间难以确定,南诏与吐蕃这场冲突的发生时间也就不能简单地定在8世纪90年代初了。
认为南诏与吐蕃的冲突出现在8世纪70年代中期的学者,其依据除此传记外,汉文史料主要为两条。一是《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不得志,入掠黎、雅,于是剑南兵合南诏与战,破之,擒大笼官论器然。”⑧二是《册府元龟》载:“奏吐蕃寇黎、雅两州,大破之,会南蛮阁罗凤来援,于望汉城生擒吐蕃大笼官论器然。”⑨两书所记为同一事,时间为唐大历十一年,即公元776年。前引佐藤长的看法是,汉文史籍中的这一记载与赤松德赞传记所记“相互关联”,也就是认定南诏之所以与唐军联合打击吐蕃,是因为南诏已反叛,或南诏与唐联合打击吐蕃,就是其反叛的具体行动。如果这两条汉文史料是可靠的,那么此意见是正确的,传记中所记载的南诏与吐蕃的冲突,也就可以认定发生在阁罗凤在位的晚期。但是,这两条史料的可靠性颇值得怀疑。王忠先生在全面分析前后几年汉文史籍相关记载后认为,《新唐书·吐蕃传》“‘剑南兵合南诏’之语当误”。⑩那么,《册府元龟》的记载也“当误”了。分析《新唐书·南诏传》及下文《资治通鉴》中大历十一年的相关记载,这两条记载本身的确存在问题,因为不论从唐、吐蕃、南诏三者的关系看,还是唐、吐蕃大的战略决策来看,8世纪70年代中期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其他汉文史籍也没有相关记载。更重要的是,从汉文史籍记载看,南诏在此年前后常与吐蕃一起攻蜀。这两条史料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显然不能以此为据去判断赤松德赞相关记载的时间。
除了将“招抚于阗”解释为控制于阗全境并以其时间为依据外,认为南诏与吐蕃在结盟期间发生激烈冲突的时间在8世纪90年代的学者,也举出了汉文史籍中的两条材料,并认为与赤松德赞传记中相关记载吻合:
韦皋比年致书招云南王异牟寻,终未获报,然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皋知异牟寻心附于唐,讨击副使段忠义,本阁罗凤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11)
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绐之曰:“唐使,本蛮也,皋听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12)
认为南诏与吐蕃这场冲突发生在此时的学者认为,根据赤松德赞传记所记并结合汉文史籍记载,南诏与吐蕃双方战于岩山之巅,吐蕃斩杀南诏多人并俘获段忠义及大小官员一百多人。尽管也指出汉文史籍与吐蕃史古藏文写卷具体记载有所不同,是“执送”、“取为质”,还是战场上俘获,“孰是孰非尚有待于深入探讨”,但肯定赤松德赞传记中所记俘获的南诏最高官员即是汉文史籍记载的回南诏的段忠义。(13)汉文史籍除《资治通鉴》外,《旧唐书·南诏蛮传》记唐使贞元七年至云南事,但未记段忠义名。(14)另,樊绰《云南志》卷10所录异牟寻誓文中,也提到段忠义回南诏送皇帝敕书并招谕一事,(15)但没有进一步的记载。需要注意的是,段忠义在唐为讨击副使,原为阁罗凤时期南诏派往唐的使者。在赤松德赞传记中,冲突之后俘获的南诏最高官员是spyan chen po,汉文对音即悉编掣逋。《新唐书·吐蕃传》载:“其官有……都护一人,曰悉编掣逋。”(16)据此记载,唐人是将spyan chen po与都护对应。有学者认为,担任这一职务者应是管理被吐蕃征服的周边地区或部族的首领,或吐蕃将周边部族政权军政首领也称作spyan chen po。(17)将此传记中的南诏spyan chen po译作“都护”是按唐人的译法,译作“副都护”也可,但将spyan chen po与“讨击副使”对应,并将传记中的悉编掣逋肯定为段忠义,可能就存在问题了。这是因为:其一,讨击副使是唐的官职,并非南诏官职;其二,段忠义地位并不高,既非管理南诏的首领,也非南诏的军政首领;其三,段忠义赴南诏的任务在异牟寻誓文中讲得非常清楚,《资治通鉴》记异牟寻答复吐蕃时也称其为“唐使”,这表明其不可能率领反叛的南诏军队与吐蕃作战。因此,赤松德赞传记中记载的俘获南诏spyan chen po应另有其人,不应是段忠义。既然这个spyan chen po不应是段忠义,那么南诏与吐蕃结盟之后的这场冲突就不是贞元七年段忠义返南诏之后才出现的了,其时间还需要结合其他材料探讨。
《新唐书·南蛮传》所录异牟寻遗韦皋书中,有两句话值得注意:一是“神川都督论讷舌使浪人利罗式眩惑部姓,发兵无时,今十二年。此一忍也”;二是“又遣讷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罗式私取重赏,部落皆惊。此三忍也”。(18)“又遣讷舌”者是谁?即当时的吐蕃大相尚结赞。这两条材料,实际反映出在异牟寻继位后,南诏与吐蕃之间虽仍有联盟关系,但矛盾已十分尖锐,已出现过某种规模的武装冲突。在记异牟寻继位及与吐蕃合兵攻西川失败后,《旧唐书·南诏蛮传》有“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立城堡,岁征兵以助镇防,牟寻益厌苦之”的记载,(19)《新唐书》亦载“然吐蕃……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异牟寻稍苦之”,(20)可知吐蕃所夺险地主要属于南诏。既然是“夺”,证明南诏与吐蕃之间在异牟寻继位后出现过武装冲突。为何要“夺”?可证明南诏当时的态度可能出现过一些变化,即传记中所说的“反叛”。当然,这种“反叛”可能是专擅朝政的尚结赞以及听其指挥的神川都督论讷舌所言,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已难考证。异牟寻致韦皋帛书是在793年(唐贞元九年),帛书中谈道,“发兵无时,今十二年”,倒推即781年或782年(唐建中二年、三年)。根据异牟寻帛书及新旧《唐书·南诏传》的记载并结合藏文史籍中关于尚结赞任大相后吐蕃统治集团内部变化的记载分析,可以认为,南诏与吐蕃尽管有结盟关系,但在8世纪80年代初或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当出现过一定规模的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这一冲突发生在双方接壤地区,是双方均力图控制的战略要地,因南诏实力远弱于吐蕃,所以冲突的结果是南诏失败,异牟寻前往吐蕃致礼,再次表示臣服。在这场冲突中,南诏除死伤一些人外,可能还有大军将或清平官一类高官被吐蕃俘获,所以古藏文写卷中将其记作spyan chen po。
总的来看,P.T.1287卷中赤松德赞传记关于南诏的记载与赤德祖赞传记有关南诏的记载明显不同,主要反映的是双方的矛盾、冲突以及结盟关系的变化。正是由于矛盾加深甚至出现了冲突,所以,794年(唐贞元十年)南诏才下定决心背蕃归唐,南诏与吐蕃的联盟宣告瓦解。
注释:
①本文所引敦煌吐蕃史古藏文写卷P.T.1287卷译文,均引自黄布凡、马德编著:《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P.T.(Pelliot Tibetain),巴黎国家图书馆藏藏文写卷伯希和编号。引文中藏文转写为笔者加注。
②关于赤松德赞的卒年,有不同说法,但多数记载称其活了56岁。刘立千考证后认为,赤松德赞卒于丁丑年,也就是797年之说“是比较可信的”。(参见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注314)
③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5—96页。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赤松德赞传记,叛乱的是白蛮(mywa dkar po),不是黑蛮(mywa nag po),中译本称“黑蛮发生叛乱”,恐有误。
④马德:《敦煌文书所记南诏与吐蕃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10—11页。
⑤分别见黄布凡、马德编著:《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295页;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67页。
⑥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62、365页。
⑦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研究》之《吐蕃与于阗》,未刊稿。
⑧《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92页。
⑨《册府元龟》卷343《将帅部献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4页。
⑩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95、96页。
(11)《资治通鉴》卷233,德宗贞元七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524页。
(12)《资治通鉴》卷233,德宗贞元七年十二月条,第7525页。
(13)马德:《敦煌文书所记南诏与吐蕃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10—11页。又见黄布凡、马德编著:《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300—301页。
(14)原文为:“七年,又遣间使持书喻之。”(《旧唐书》卷197《南诏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82页)
(15)樊绰:《云南志》卷10,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30页。
(16)《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第6071页。
(17)陈楠:《吐蕃职官制度考论》,《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
(18)《新唐书》卷222上《南诏传上》,第6272—6273页。
(19)《旧唐书》卷197《南诏蛮传》,第5281页。
(20)《新唐书》卷222上《南诏传上》,第62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