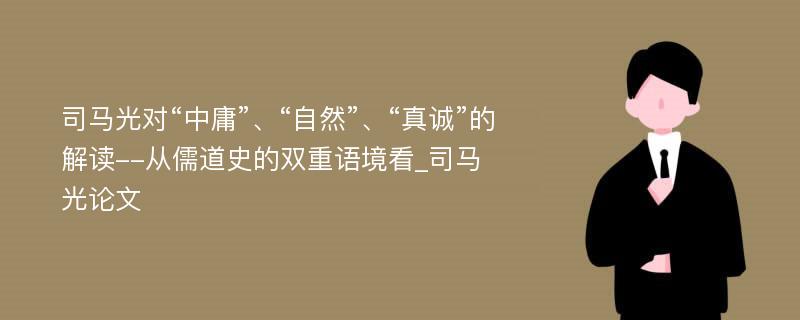
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的诠释: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学论文,经学论文,中庸论文,脉络论文,司马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朱熹的《六先生画像赞》中,司马光(1019-1086)与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五人一起,被视为北宋道学的核心人物,然而,在其作《伊洛渊源录》中却将司马光除去了,“六先生”成了“五子”,司马光也就逐渐淡出了道学的视域。现代以来,虽仍有学者在争辩司马光到底属不属道学家或理学家,然而在笔者看来,其实际意义不是很大。众所周知的是,司马光是道学初兴之际的政治领袖与学术领袖之一,又与当时道学的核心人物二程、张载有着极密切的交往。鉴于此,如果借用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思想世界”一词来说,司马光的学术思想事实上已是张、程等道学家的“思想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北宋道学乃至于两宋道学的研究中,司马光都必须被认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长期以来,学者所关注的司马光,或为一个史学家,或为一个政治家,而较少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进行研究,这样,我们也就很难对司马光有一个完整的把握。而要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来看司马光,司马光对《中庸》的诠释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①
在宋代的《中庸》诠释史上,司马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是北宋最早注释《中庸》的儒者之一,有《中庸广义》一卷行世,②晚年又与范镇、韩维等多次书信往来,讨论《中庸》中的“中和”问题。遗憾的是,《中庸广义》一书未能流传下来,这客观上为研究司马光的《中庸》诠释带来不少困难。然而,相对幸运的是,在宋人的一些著作中,我们仍能辑出某些断简残篇,从中多少可窥见一斑。这里最重要的是南宋卫湜的《礼记集说》,保留有22条司马光注释《中庸》的材料。这些材料与司马光《传家集》中涉及《中庸》诠释的有关文献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研究司马光《中庸》诠释的资料来源。然而,目前所见到的对司马光《中庸》学说的研究,基本上未能注意到《礼记集说》的材料,这使得对司马光《中庸》诠释的认识多少不够周全。
就《中庸》文本而言,“性”与“诚”两字无疑是最具有思想内涵的字眼之一,本文即拟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出发,来考察司马光对《中庸》中这两个关键字眼的阐释,从而来把握司马光的《中庸》诠释的思想特色及其思想史上意义与局限。
一、对“天命之谓性”的诠释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宋代被视为是儒家阐发“性与天道”最重要著作之一的《中庸》,开篇便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对于这句纲领性的文字,司马光注释说:
性者,物之所禀于天以生者也。命者,令也。天不言而无私,岂有命令付与于人哉?正以阴阳相推,八卦相荡,五行周流,四时运行,消息错综,变化无穷,庶物禀之以生,各正性命,其品万殊。人为万物之灵,得五行之秀气,故皆有仁义礼智信与身俱生,木为仁,金为义,火为礼,水为智,土为信,五常之本,既禀之于天,则不得不谓之天命也。水火金木非土无依,仁义礼智非信无成。孟子言四端,苟无诚信,则非仁义礼智矣。夫人禀五行而生,无问贤愚,其五常之性必具。顾其少多厚薄则不同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厚于此而薄于彼,或厚于彼而薄于此,多且厚者为圣贤,少且薄者为庸愚,故曰天命之谓性。③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看到有学者曾经对这段文字展开过较深入的讨论。然而,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在阅读这段文字时,第一印象大概会是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在此隐约可以看到《礼记注疏》中郑玄注与孔颖达疏的影子。因此,我们不妨先看郑玄的注释:
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孝经说》曰:“性者,生之质命,人所禀受度也。”④
郑玄注很简洁,从孔疏那里或许可以对上文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
天本无体,亦无言语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贤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人自然感生,有刚柔好恶,或仁、或义、或礼、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之谓性”。⑤
这样,对郑注孔疏而言,所谓“天命之谓性”,完全是从人之“自然感生”的角度来解读,这样,所谓的“天命之性”即成了人从天那里所自然禀受而来的才质性的东西,故诚如杨儒宾所说的,“郑玄的注解是彻底的‘用气为性’的思想”。⑥
如果把上述司马光的注释与郑注孔疏相比较,不难看出,司马光对“天命之谓性”的理解,基本是沿袭郑注孔疏中这种“用气为性”的思路。故司马光首先指出,“性”本之于天,虽然天“不言而无私”,不可能真正有“命令付与于人”,但天通过“气”的运行,即“阴阳相推,八卦相荡,五行周流,四时运行,消息错综,变化无穷”,使人与万物都各禀之以生而得其性命。
按这一理路,那么我们就可说,既然“性”由所禀受决定,即根据一种完全自然主义的决定论,所禀之“性”就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才质性的“气性”,当然可以认为是无所谓善恶可言,早在孟子的时代就有这样一种看法。⑦不过,从儒家的立场来说,又不能不考虑人所受的这种“天命之性”的道德含义及其存在根据,于是,郑注孔疏便从汉人所尊信的五行说中去寻求“天命之性’’的道德意义及其根据,这就是郑玄所谓的“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因为木、金、火、水、土五行与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儒家的道德属性被认为具有某种关联性,于是,上天所命之性也就获得了道德的含义。⑧然而,人与物俱禀有五行之气,那么人物之别何在呢?郑玄没有讨论这一问题,孔颖达则根据《礼运》中人被称为“五行之秀气”的说法来保证人可能具有的“五常之性”:
案《左传》云天有六气,降而生五行。至于含生之类,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独禀秀气,故《礼运》云:人者五行之秀气,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义、礼、智、信,……但感五行,在人为五常,得其清气备者则为圣人,得其浊气简者则为愚人。降圣以下,愚人以上,所禀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为九等。孔子云:“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论语》云:“性相近,习相远也。”⑨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司马光的论述几乎完全本于孔颖达。在此意义上说,司马光的注释可谓了无新意。根据这一理路,“仁义礼智信之性”完全是由“气”所决定,只是“气性”,它们与种种邪性、恶性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根据这一理论,性既可认为无所谓善恶,亦可认为可善可恶,混有善恶,在司马光的《善恶混辨》一文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夫性者,人之所受于天以生者也。善与恶必兼有之。”⑩
就此而言,杨儒宾先生认为司马光的《中庸》诠释是郑玄、孔颖达这一路下来的“气化论观点下的《中庸》”。(11)当然,站在两宋道学的立场来看,这一“气化论观点”的思路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理论缺陷:如果将道德之依据诉诸于“气”,而这一理路下的“气”则充满了偶然性与任意性,以至于有人禀得清气多则为圣贤,有人禀得浊气多则为下愚,由天所命之“性”事实上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德性基础。或者换成道学的语言来说,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来解读“天命之谓性”,则天道与性命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真正得以打通。
不过,对于上述这样一种“气化论观点”的理路,司马光有时似乎贯彻得不是很彻底。他一方面将“五常之性”的根据建立在“气”的基础上,但另一方面并没有完全接受“气”的任意性与偶然性。在他看来,所谓“五常之性”既禀之于天,那么,人不论其贤愚,所禀之气不论厚薄,都具有这种本之于天的“天命之性”,换言之,司马光还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要努力用“天”这一概念来保证一种普遍性的善。因而,对于司马光而言,那种普遍性的善,即“仁义礼智信之性”,是任何人都具有的,人和人的差别不过是所禀受之量的多少而已。就此而言,他已经表现得与郑玄、孔颖达多少有所不同。按郑玄、孔颖达的看法,人所禀的五行之气是随机而任意的,故人有九等,上智下愚不移,即上智与下愚是与生俱来就已经被决定了的,故不可能有所改变,即便是“中人”,也不过是逐物而移,人根本没有内在的道德决定性。而司马光并没有完全认可这一说法,关于圣人,司马光说:
圣人亦人耳,非生而圣也。虽聪明睿智,过绝于人,未有不好学从谏以求道之极致,由贤以入于圣者也。(12)
也就是说,圣人虽然所禀之气过于常人,但并不因此就必然地成为圣人,即圣人并非必然地被“气”所决定而机械地成为圣人,而是经过“好学从谏”等不断的努力,才得以由贤入圣。至于孔子所说的上智下愚不移,他有着自己的另外一种解释:
是故虽圣人不能无恶,虽愚人不能无善,其所受多少之间则殊矣。善至多而恶至少则为圣人,恶至多而善至少则为愚人,善恶相半则为中人。圣人之恶不能胜其善,愚人之善不能胜其恶,不胜则从而亡矣,故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13)
因此,绝对的“上智下愚不移”对司马光来说是不存在的,只不过对圣人而言,其恶之微不能胜其善,愚人则善之微不能胜其恶,故说上智下愚不移。然而,人虽有上智下愚,其禀之于天的五常之性,却是人所共有。这一观点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是从孟子的理路看,人人都具有的“仁义礼智信之性”,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心性体,故“仁义礼智信之性”是内在于人的东西,此为本体义上立言;而从另一种解读的理路看,虽然人人都具有“仁义礼智信之性”,但这种人人都具有的“仁义礼智信之性”,却是实然层面上说,它背后的根据是五行之“秀气”,从而超越性的性体事实上依然无法建立。
如果按照前面所述的司马光的思路来看,他的理解应该是后者。讨论至此,似乎已经可以下结论了。但是,事实上还不是这么简单。在对《中庸》其他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司马光对“性”的理解似乎又略有不同。在注《中庸》“唯天下至诚”章时,司马光说:
人皆有仁义礼智之性,惟圣人能以至诚充之。如能尽其性,然后修其道以教人,使人人皆尽仁义礼智之性,如此则其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阴阳和,风雨时,鸟兽蕃滋,草木畅茂,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万物莫不遂其性,岂非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功德参于天地哉。(14)
在此司马光直截了当地点出“人皆有仁义礼智之性”这一命题。虽然我们说过,“人皆有仁义礼智之性”的说法可以在一种“气化论观点”下的思路来理解,但是,后文紧接着“惟圣人能以至诚充之”一句,就值得玩味了。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在司马光前面所述的理路里,圣人与普通人在“性”上具有同质性,都是所禀受的“气”决定的;第二,“充”字应该来自于孟子的“扩充”说,其意义无论是从孟子还是从这里所引的上下文看,显然都应该是自内而外的。然而,如果说“性”由所禀受的“气”决定,那么就绝没有自内而外“充之”的可能。因此,能“充之”之“性”,就必然不能从“气化论观点”的层面来理解,故司马光下文又接着说:“如能尽其性,然后修其道以教人,使人人皆尽仁义礼智之性”。即是说,圣人以至诚充之而“尽性”,然后修道教人,使每个人都能够“尽性”。按照这里的上下文来理解,“尽性”云云,恐怕当同样是指通过对人内在之“性”的“充之”之后,使得人人皆本有的“仁义礼智之性”得以实现。因此,这里所谓的“性”,就不能够再从外在于人本身的“气性”角度来理解,而只能着眼于人内在的本心性体。对于这一解读,我们还可以从司马光的另外一些文字中得以进一步的证明。在对《中庸》“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一句进行解释,司马光说:
夫仁义礼智信皆本于天性,其引而伸之,则在人矣。君子知五常之本于天,有之则为贤,无之则为不肖,以此观人,人焉廋哉。(15)
在这里,司马光进一步用天来赋予五常之性以合法性依据。据此,五常之性为天命所赋,人人皆有,而现实中的人有贤有不肖,并不是人有没有五常之性的问题,而在于人能不能将之“引而伸之”。很显然,司马光用了“引而伸之”一语,也大概只能理解成自内而外地引申,亦即前文所说的“充之”。在对《中庸》“合内外之道”的解释中,司马光又说:
内则尽己之性,外则化成天下,皆会于仁义礼智信,故曰合内外之道。(16)
这里就更加明确地指出,是从“内”来“尽己之性”。这样的性,当然不是表现在每个人身上的那种混杂了善恶的、任意的、无规定性的“气性”。如果我们再回到郑注孔疏那里,将司马光的有关注释与郑注孔疏作一个比较的话,可能更加可以说明问题。郑注“合内外之道”曰:
以至诚成己,则仁道立;以至诚成物,则智弥博。此五性所以为德也,外内所须而合也。外内犹上下。(17)
孔疏进而发挥郑注之意曰:
若成能就己身,则仁道兴立,故云“成己,仁也”。若能成就外物,则知力广远,故云“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者,言诚者是人五性之德,则仁、义、礼、知、信皆犹至诚而为德,故云“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者,言至诚之行合于外内之道,无问外内,皆须至诚。于人事言之,有外有内,于万物言之,外内犹上下。上谓天,下谓地。天体高明,故为外;地体博厚闭藏,故为内也。是至诚合天地之道也。(18)
按照这种解法,所谓“合内外之道”,不过是说,无论对己对物,皆需一种至诚的态度,这显然不是要扩充内在之性。再看郑注“唯天下至诚”章:
尽性者,谓顺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赞,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谓圣人受命在王位,致太平。(19)
可以说,对郑玄而言,圣人之“尽性”,只是行教化之事,从而致天下之太平而已,而不是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因为对郑玄来说,不论善恶,人之“性”只是与生俱来的“气性”,对于这样一种“气性”,只能从外在的手段来引导之,使之从善去恶,各安其生而已,这就是所谓的“顺理百姓之性”。(20)这实际上也即是荀子“化性起伪”的思路,它与自内而外的“尽性”之说,显然有比较大的区别,亦即与司马光的上述解读有着根本的差别。
然而,这样一来,司马光对“性”的解读,或许就可以认为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层面的理解:其一是以“气”统“性”,这是郑玄、孔颖达以来的传统;其二则视“性”为内在于人本身,这多少具有孟子“性善论”思路的色彩,其后则为道学家所发扬光大。客观地说,这两种理论各有其针对性。就后者而言,所指向的是人的道德本体,即人的本心性体,它由天保证了人之德性的普遍性与必然性;而前者则要解决人在具体现实生活中的贤愚善恶问题,即由禀得的“气”的不同来说明个体人现实之道德差异性。可以说,司马光一方面继承了汉唐经学的传统理路,从“气性”的角度来理解“天命之性”,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从人的本心性体上,为人的德性寻求普遍性和必然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有道学的理论色彩。但问题是,这两个方面的最后根源,在司马光那里都笼统地被诉诸于“天”,这样,两种不同质的“性”,都不加分析地被说成了“天命之性”。司马光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两种指向在义理上说是相互矛盾,甚至无法调和的。更重要的是,对这两个完全不同层面的“性”的理解笼统地不加分疏,其结果可能是使得其中的一层含义被消融于另外一层含义之中。我们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司马光已经点出了“性”字作为人道德本体的意义,但统观司马光所有的相关文献,这一层含义却相对显得较弱,从司马光的主导观点来说,恐怕还是从气化论的立场来解读“性”字,他的许多表述,诸如“善恶混”,诸如“治性”,诸如“才不才,性也”,诸如对孟子性论的批评(21)等等,都说得相当肯定,可见应该是他自觉认定的观点,或者说是与他的思想之整体性相一致的观点。而反过来,司马光所点出的“性”字作为人之道德本体的意义,只能说是一种弱的表述,或者可能只是随文释义过程中的被文本本身牵带出来的无意识的表述。总之,不管怎么说,我们可认为,司马光对《中庸》之“性”字的理解上,确实存在着含混不清的地方,可见其理论思辨水平不足之处。或许正是如此,在司马光的同时代人的心目中,特别是在二程等道学家的心目中,司马光对“天命之谓性”的诠释在义理上是有偏失的。在《二程外书》中记载了这么一则佚事:
温公作《中庸解》,不晓处阙之。或语明道。明道曰:“阙甚处?”曰:“如‘强哉矫’之类。”明道笑曰:“由自得里,将谓从‘天命之谓性’处便阙却。”(22)
这个故事是谢上蔡所记,当然,在现存《礼记集说》中,司马光对“强哉矫”与“天命之谓性”的注释都被保留了下来。因此,上蔡所记,大概只是一种比喻性的方便说法。在所引的这条材料中,“强哉矫”大概指的是涉及文字训诂层面,而“天命之谓性”则涉及根本义理的层面。由此可以看出,二程对司马光所解的《中庸》,所不满的不是文字之训释,而是根本之义理。在此亦可见明道对司马光“天命之谓性”的诠释显然不甚满意,所以才会有“由自得里,将谓从‘天命之谓性’处便阙却”之说,盖以为司马光对“天命之谓性”没有“自得”的看法。
从道学史的立场来看,二程对司马光“性”说的批评当然可以成立,尽管司马光有隐隐约约的两重“性”说,但事实上最终还是“气性”吞没了道学家心目中的那个本体之“性”,从而司马光不能真正达到道学家心目中应该从《中庸》中开显出来的那种贯通天道性命为一体的理论水准。
二、对“诚”的诠释及其与道学诠释之差异
“诚”是《中庸》中的另一个核心思想,也是宋代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核心思想。(23)宋代道学对《中庸》诠释的贡献,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被认为与“诚”的诠释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就司马光而言,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表现为对“诚”之一字的重视,其曾自称曰:
温公谓安世,平生只是一个“诚”字,更扑不破。(24)
《宋元学案》又记载:
刘安世从温公学,与公休同业,凡三四日一往,以所习所疑质焉。公欣然告之,无倦意。凡五年,得一语曰‘‘诚”。安世问其目,公喜曰:“此问甚善!当自不妄语入。”(25)
由此可见,无论司马光夫子自道,还是门人后学的评价,“诚”之一字,不仅涉及司马光对《中庸》的诠释问题,甚至对于理解司马光之为人为学,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字眼。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司马光的“诚”的学说似乎从来就没有受到重视,历代儒者只有个别人偶有提及,现代学人也很少对司马光的这一思想多做研究。相形之下,与司马光同时期发挥《中庸》之“诚”的学说的周敦颐,以其深远的影响而不断地获得后来儒者的表彰。于是,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同样以“诚”立学,周敦颐获得“道学宗主”的高度评价,而司马光则基本上为后人所忽略?司马光所理解的“诚”之内涵到底是什么?前此司马光教导刘安世问“诚”时答之以“当从不妄语入”,所谓“不妄语”,即是真实无欺之意。对于所谓的真实无欺,司马光则进一步解释说:
凡物自始至终,诚实有之,乃能为物。若其不诚,则皆无之。譬如鸟兽草木之类,若刻画而成,或梦中暂睹,岂其物邪,况于仁义礼智,但以声音笑貌为之,岂得为仁义礼智哉。(26)
这是司马光对《中庸》“不诚无物”一句的注释。在司马光看来,凡物之有,则有赖于诚与实,如鸟兽草木之类,如果是刻画而成的,或者是梦中看到的,都是不实的东西,故不能称为实有之物。同样,对于仁义礼智之类的德目,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声音笑貌之上,而不是诚实其心,就不是真正的仁义礼智。就此而言,司马光所讲的“诚”,基本上讲的是人心之“真实无妄”。
其实,从“真实无妄”的角度来言“诚”,基本上是宋儒的通义,(27)如程伊川说“无妄之谓诚”。但在主流道学家那里,“诚”之作为“真实无妄”,则被开出了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如吕大临说:
诚者,理之实然致一而不易者也。天下万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无二,虽前圣后圣若合符节,是乃所谓诚。诚即天道也。(28)
在吕氏这里,从一般意义上的人伦道德上之“诚”,被进而推到天道之“诚”。这样,“诚”之一字就不再囿于人心之“真实无妄”,而是由人心之“真实无妄”,感通到“天下万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无二,虽前圣后圣若合符节”,从而人由人心之“诚”,进而感受到天地之理,亦即是致一而不易的实理,天地之道,亦即不过是一诚道。因此,对吕大临来讲,“诚”之作为“理之实然”而被赋予了天道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进而追问,在司马光那里,“诚”字有没有天道的意义呢?《宋元学案》记司马光教导刘安世曰:
诚是天道,思诚是人道,天人无两个道理。因举左右手,顾之笑曰:“只为有这躯壳,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29)
按照两宋道学的一般性理解,“诚”是天道之本然,而“思诚”或“诚之”则是人道之当然,(30)那么,在司马光这里,以“诚”为“天道”、以“思诚”为“人道”、“天人无两个道理”之类的说法,几乎与那些正宗的道学家所说的如出一辙。由此而看,司马光对“诚”的理解,似乎也有“天道”的含义在里面,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就可以说,司马光与道学家在对《中庸》之“诚”的诠释上具有同等的贡献。然而,在司马光那里,以“诚”为“天道”,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材料来加以考察。在《答韩秉国第二书》中司马光有如下的一段论述:
《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言聪明睿智天所赋也;“诚之者人之道”,言好学从谏人所为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谓圣德之已成者也。择善而固执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谓贤人之好学者也。(31)
这段文字对于我们理解司马光“诚是天道,思诚是人道”一语应该有极大的帮助。这里清楚地表明,所谓“诚者天之道”的说法,司马光并不是在天道本体的意义上立言,而仅仅是从“天所赋”的角度来说明圣人的“聪明睿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诚是天道”云云,不过是其“性者,物之所禀于天以生者也”一句的转语而已。(32)也就是说,“禀于天以生者”的“性”有善恶贤愚,而圣人之为圣人,亦是“禀于天以生者”。由是而言,“诚是天道”的说法,对于司马光而言,不过只是一句自然事实之描述,而无所谓天道本体之建立。
那么,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圣人之“聪明睿智”,要用“诚”字来予以说明呢?也许下面的言论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率由诚心而智识自明,此天授圣人之性也。由智识之明,求知道者,莫若至诚。故诚心为善,此贤者修圣人之教也。所禀赋于天有殊,然苟能尽其诚心,则智识无不明矣。(33)
圣人有天授之性,这在司马光眼里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在司马光的心目中,圣人之为圣人,又不是完全由自然决定的,虽有天授之性,但仍然需要“以至诚充之”。所以这里司马光说,只有通过“诚心”,圣人天授之“聪明睿智”才可能得以朗现,也就是说,即便是圣人,也仍然需要其“至诚”的工夫,才能全幅朗现其天纵之圣德。司马光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谓圣德之已成者也”,亦不过是那些拥有天授之“聪明睿智”的人通过其“诚”之工夫之后才可能有的效验。与之相对的是常人,通过好学从谏、择善固执之“诚之”之工夫,则亦是“修圣人之教”。就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天命之性各有殊别,但只要是下“诚”之工夫,则“智识无不明矣”,亦即司马光引《中庸》所说的“及其成功一也”,故又说“天人无两个道理”。由此可见,司马光对“诚”字的阐发,全然没有建立天道本体的意味在里面,即便是在讲“天人无两个道理”,也没有道学家所谓的那种天道性命为一体的理论为其背书。对于这一点,朱子倒是看得很清楚:
诚之为言实也。然经传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概论也。如吕氏此说,即周子所谓“诚者,圣人之本”,盖指实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谓“圣,诚而巳矣”,即《中庸》所谓“天下至诚”者,指人之实有此理者而言也。温公所谓“诚”,即《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指人之实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34)
朱子在这段文字中虽然只是表明经传中“诚”字的用法在不同场合各不相同,但其将司马光的用法与周敦颐、吕大临区别开来,无疑是相当正确的。就周敦颐、吕大临来说,“诚”之为本体的意义已相当明确,而司马光那里,“诚”字仍只是在工夫上着眼。当然,司马光之为人,亦以谨守“诚”之工夫而著称,如陈瓘说:“凡温公之学,主之以诚,守之以谦,得之十百而守之一二。”(35)不过,尽管如此,仅着眼道德修养之工夫而不能由工夫上达本体,从道学的眼光看,司马光对《中庸》之“诚”字的阐释,则仍然有所不足,故其地位,亦远不逮周敦颐。事实上,宋代道学对“诚”的新诠释,最重要的特色就在于“诚体”的建立,正是这一点将道学对“诚”的理解与前人区别开来,而周敦颐对道学的最大贡献,也正是通过对《易传》与《中庸》的诠释而建立起这一形上的“诚体”。(36)
三、结语
在宋代的《中庸》注释史上,司马光是最早一批表彰并对《中庸》文本进行全面疏释的儒者之一。鉴于司马光的学术地位与政治地位,我们可以认为,他确实可以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刺激了更多的北宋儒者投入对《中庸》的研究中”。(37)
然而,从后来成为主流之道学的学术范式看,司马光的诸多理论都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不论其论“性”还是论“诚”,如我们前文所述,在道学家的眼中都颇成问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司马光提出的诸多问题,不论其论“性”还是论“诚”,都成为了后来道学的核心语汇。这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司马光与后来的道学诸子,有着相当共同的问题意识。就此来说,对于思想本身而言,问题的提出即可以认为已经指向了其应该有的方向。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司马光又囿于汉唐以来的义理系统,特别是其“用气为性”的根本思路,使得他在面对那些后来成为道学之核心语汇的问题时,终究未能达到后世道学家所具有的理论高度,故道学家对于温公之学多有批评,如朱子称“温公之言多说得偏,谓之不是则不可”,(38)亦可谓知言。这也许可以回答为什么朱子在确认道学的谱系时,面对司马光表现出踌躇不决的态度,并最终决定将其置于伊洛渊源之外。
总之,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司马光正处于庆历“正学”向道学转变的过程中,(39)不论是义理上还是经术上,一方面尚承接着汉唐之旧传统,另一方面虽指向了宋明之新风气,但又尚未达到穷深极微、洞彻心性本体的境界,这一点从其对“性”与“诚”的注释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40)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司马光是宋代学术的承上启下者,亦是宋代《中庸》诠释的承上启下者。
注释:
①漆侠先生指出:“司马光在经学上足以成家,他对宋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就是他对《中庸》的论述和阐释。这个论述和阐释,构成了司马光哲学独具的色彩。”见氏著:《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收入《漆侠全集》第六卷,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9页。
②司马光对《中庸》的注释,在陈振孙的《书录解题》有《中庸广义》一卷,《经义考》亦沿用这一书名。或有与其《大学广义》合称为《大学中庸广义》,另有称之为《中庸解》。三者应为同一书。相对来说,称《中庸广义》更为通行一些。
③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三,《通志堂经解》第32册,台北:台湾大通书局,影印清康熙十九年刻本,1969年,第18215页。
④孔颖达:《礼记注疏》卷五十二,收入《十三经注疏》第5册,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清嘉庆二十年刻本,2001年,第879页上。
⑤《礼记正义》卷五十二,第1662页。
⑥《〈中庸〉是怎样变成圣经的?》,《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6页。
⑦如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
⑧当然,这样一种机械式的论证在理论上不能说是没有问题的。诚如杨儒宾教授所说的:“如果道德意识词目的仁、义、礼、智、信完全可以被化约成自然哲学的金、木、水、火、土之子目,那么,所谓超越的天道性命之事即不好谈。”参见氏著:《〈中庸〉是怎样变成圣经的?》,载《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第496页。
⑨《礼记正义》卷五十二,第1662—1663页。
⑩《善恶混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二,涵芬楼影印宋绍熙刊本,1919年,第3页。
(11)杨儒宾:《〈中庸〉是怎样变成圣经的?》,载《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第502页。
(12)《答秉国第二书》,《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三,第7页。
(13)《善恶混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二,第3页。
(14)(15)(16)《礼记集说》卷一百三十三,《通志堂经解》第32册,第18348—18349、18314、18358页。
(17)(18)(19)《礼记正义》卷五十三,《十三经注疏》第5册,第896页上,896页下,895页上。
(20)杨儒宾:《〈中庸〉是怎样变成圣经的?》,载《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第496页。
(21)参见《疑孟》及《性善恶混》等文献。
(22)《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上册,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第425页。
(23)藤井伦明:《宋代道学中“真实无妄”之“诚”析论》,载《汉学研究集刊》第二期(2006年6月),第166页。藤井同时还指出:“在宋代理学以前,《中庸》所谓的‘诚’,并非思想主流,姑且不论《中庸》,吾人实在很难说:‘诚’本身作为一为学的根本德目,在儒家思想中占有其核心性之地位。”
(24)(25)《元城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收入《黄宗羲全集》第四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5、55页。
(26)《礼记集说》卷一百三十三,《通志堂经解》第32册,第18358页。
(27)如藤井伦明即指出:“‘诚’字于宋代道学中的第一要义,无疑地即在‘真实无妄’。”见氏著:《宋代道学中“真实无妄”之“诚”析论》,载《汉学研究集刊》第二期(2006年6月),第169页。
(28)(33)《礼记集说》卷一百三十二,《通志堂经解》第32册,第18339、18346页。
(29)《元城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收入《黄宗羲全集》第四册,第55页。
(30)如朱子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31)《答秉国第二书》,《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三,第7页。
(32)其实,这种理解亦禀之于郑玄:“言诚者,天性也;诚之者,学而诚之也者。”《礼记正义》卷五十三,第1689页。而由前所述,郑玄所谓“天性”云云,亦即是禀受而已。
(34)《答或人》,《朱子文集》卷六十四,《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37页。
(35)《涑水学案下》,《宋元学案》卷八,收入《黄宗羲全集》第三册,第459页。
(36)如王柏说:“濂溪周子心传子思子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而得于子思子者反深,其著于《通书》曰:‘诚,圣人之本’,此以性言;次章曰:‘圣,诚而已矣’,此以教言;曰‘诚之源’,曰‘诚斯立’,此以天道言;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此以人道言。终其书,推明诚之义不一而止,精悫邃密,皆孟子之所未发。”见《鲁斋集》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本,1986年,第160—161页。
(37)张晶晶:《论司马光对〈中庸〉之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东方人文学志》第六卷第1期,第96页。
(38)《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朱子全书》第18册,第4174页。
(39)关于庆历正学向道学的转变,可以参见吴国武:《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193—253页。
(40)当然,本文的基本倾向是站在道学立场上的论说。我们同时也未尝不可以承认,司马光的《中庸》诠释在汉唐以来旧传统的义理构架下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张晶晶的硕士论文《司马光哲学研究》及其论文《论司马光对〈中庸〉之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就是要努力地证明这一点。杨儒宾《〈中庸〉是怎样变成圣经的?》一文尽管其基本倾向也是站在道学的立场,但同时也仍然承认了这样一种诠释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