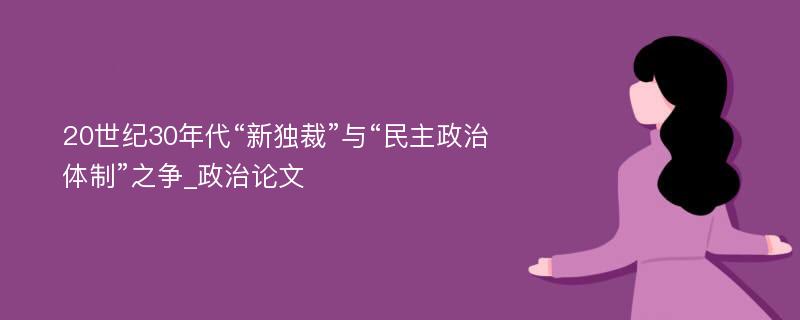
30年代“新式独裁”与“民主政制”的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制论文,论战论文,民主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内乱与外患频仍的30年代中期,一批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笃信英美式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反戈一击”,力主在中国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统治,从而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引起了民主与专制的激烈争论。这次争论对实际的政治虽影响不大,但它所揭示的问题,如民主与专制、国家与个人、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等等,却都是意义深远、至今仍扣人心弦的论题。因此,回顾这一“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当能给人价值不菲的启示。
一
尽管国民党在20年代末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中国的分裂状况并无实质性变化。而且,国民党最高领导层间的明争暗斗一刻未停,严重削弱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和统治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对中国政府软弱无能的痛恨与对一个统一、廉洁、高效、具有高度权威的政府的企盼,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则借机公开宣传实行墨索里尼式的法西斯统治,甚至连形式上的五院制都要取消,而实行元首制。但使人意外的是,一些向以政治“独立”的知识分子,也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能有一个“强力政府”之上。1932年6月,在胡适等知识分子自办的《独立评论》上刊登了傅斯年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提出“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的论点。稍后,丁文江撰文力主强权政治,而翁文灏则明确写道:“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曾留学美国,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蒋廷黻写了《知识阶级与政治》一文,从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这一角度出发,认为“知识阶级的政治活动不可靠‘口头洋’。西洋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当作学术来研究是很有兴趣而且很有价值的,当作实际的政治主张未免太无聊了。”所以“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该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它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实际上,“口头洋”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观察、议论政治的独特视点,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话语的形成。而蒋廷黻此文不仅否认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权利,而且也从根本上否认了全体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的爆发加重了许多人对中国进一步分裂的忧虑。蒋廷黻又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强烈主张专制政治,并从中外历史中寻找立论的根据。他悲观地写道:“自闽变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而“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他强调西欧各国历史上都是经过王权与专制才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中国现在的局面正像英国未经顿头(按:今译都铎)专制,法国未经布彭(按:今译波傍)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按:今译罗曼诺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总之,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家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而且,他认为由于中国国民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不具备民主共和的资格,所以中国“只能有内乱,不能有真正的革命。”在他看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哪种国家的问题。”
国家的统一、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无疑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但把中国与西欧的历史作机械类比,不能不说是牵强附会。
蒋文发表后,虽然遭到胡适等人的激烈反驳,但却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激起了更强烈的共鸣,博得了更多的赞赏,因此也更咄咄逼人。之所以如此,不仅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关,而且深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实行高度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某种程度地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的美英两国,开始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渡过危机。这种世界性的“民主危机”、对民主制度的失望情绪,也深深地渗进了中国的知识阶层。尤有意味的是,他们往往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与斯大林的苏联相提并论,并不认为二者有本质的区别,都属“专制”、“独裁”、“极权”的国家。而这是强国的良策。
如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曾积极宣扬民主政治的钱端升,此时也一反已往地力主独裁统治。“因为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丁文江连续撰文,强调如果独裁政治不能统一中国,那么民主政治就更不可能统一中国。因为民主政治需要较长的民主教育和制度建设,而这两项现在都是“缓不济急的”,因此是“不能实现的”。而且,要使中国免于灭亡,只有让权力高度集中,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蒋廷黻明确说道:“我以为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因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高。”留学美国,此时在北大任教的张佛泉在著文反动专制的同时,又无可奈何地写道:“不过在目前中国状况之下,即使我们要采用民治,在未提高民众政治程度以前,也不能过于信赖民众。所以我们在最近未来的政治,总须要与训政或‘保育政策’相近,甚至都须得含一点寡头政治的意味的。”还有文章认为中国政治走上轨道的唯一途径是“栽培领袖,指导社会。”
无疑,民主程度与效率程度是衡量政治体制优劣的两条重要标准,但问题在于二者的追求目标并不一致。民主的目标是参与最广,效率的目标是决策——执行最快。二者虽不是完全相反,但却时时互有矛盾,其中一个得到张扬时,另一个极易受到损害。因此,一般国家都制定有“紧急状态”一类的法律,以牺牲民主来换取效率,渡过“紧急状态”。此时的专制论者,即明确主张以牺牲民主来换取效率。但是,民主与效率二者虽然很难同高,但却极易同低,因为牺牲民主并不意味必然会有高效。一个高效的集权政府,是需要一系列不可缺少的辅助条件的。如利益的基本一致,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决策程序的科学化,执行机构的合理化,灵敏的反馈机制,对个人擅权、舞弊等非组织行为的监督控制及统治者的自律(此点尤为重要)等等。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实际很容易产生一种既专制独裁又腐败无能的旧式政权。其实,专制论者也意识到此点,因而提出要建立一种与中国传统专制制度不同的“新式独裁”。丁文江认为,“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并提出了“新式独裁”的具体标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材”,“利用目前的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钱端升亦希望这种新式独裁者“能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实际的福利,能对现代经济制度有认识,能克苦耐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从他们对“新式独裁”的种种描绘界定中可以看出那种既希望有一能使国家强盛的强力政府、又惧怕“旧式专制”这种矛盾心态和两难处境。但是,他们虽然提出了新式独裁的具体标准,却未提出如何产生、造就这种新式独裁的具体措施。或许,他们也意识到自身毫无权力这样一个事实,实际根本无力、也不可能造就出一个理想的“新式独裁”。因此只能是种一厢情愿的幻想。而且他们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保证“新式独裁”不向“旧式独裁”转变呢?怎样才能限制、防范独裁者利用公共权力来谋取个人利益呢?
对政治强人的强烈呼唤,深刻反映了他们的软弱性,因此只能幻想、企望一个政治强人来代表自己的利益、观点,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进一步说,这种把国家的强盛、政治的开明系托于个人的观点,其实质仍是对“圣主明君”政治制度的一种变相肯定,乃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折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出发点之一是认为人性本善,坚持性善原则。因此,儒学的政治理想是“德治”,即理想的统治者是用自己的道德示范来“教化”臣民,而不是用法律规条、组织制度来“管理”臣民。这样“天子”便具高度的道德象征意义。从理论上说,儒学的原则是致力于使“最好”的人成为统治者,因此往往寄希望于“圣明天子”。而“圣君”是无需具体的外在的限制的。但历史的经验表明,一种不受任何监督、限制的权力的存在本身,对社会就是一种巨大的威胁,极易演化成“利维坦”。
但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这些对民主制度有着相当了解的自由主义者们在力主“新式独裁”的时候却闭口不谈绝对权力的潜在危害性,值得深思。
二
虽然当时险恶的国内国际环境使许多人丧失了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但以胡适为代表的少数人仍坚持昔日的信念,反驳“新式独裁”论者的种种论点,为民主政治力辩。
针对蒋廷黻的论点,胡适立即连续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两文,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民族国家,“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而且,“我们今日要谈的‘建国’,不单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他反问道:“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大业,我们今日的建国事业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他进一步将专制分为领袖独裁、一党专政和一个阶级的专政三种方式。他坚持反对任何一种方式的独裁,其理由有三:首先是“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作、政治生活极其复杂,而要对所有这些方面都全面管理的高度集权专制是“人世最复杂繁难的事业。”其次,“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最后,“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在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这样,胡适把民智未开难以实行民主政治这一命题颠倒为民智未开最宜实行民主政治这一命题。但这种命题的颠倒过于简单,难成以立。连力主民主政治的张奚若也批评胡适的这一论点“在逻辑上发生问题”。
民主论者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酷事实是,近代中国并未真正实行过民主政治。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而诸如国会等一些西方民主政治的形式,却成为军阀政客的手中玩偶。这就难免使人怀疑、乃至否定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对此,胡适针锋相对地写道:“我们要认清,几十年来割据的局势造成是因为旧日维系统一的种种制度完全崩坏了,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什么可以替代他们的新制度。”但新制度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要经过一段转型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难免要产生某种程度的动荡,或是转入新的机制,或是退回旧的轨道。不过在旧制度已完全崩坏的近代中国,要实行“新式独裁”也并不容易。因为一种长期的专制并不能仅靠暴力维持,还需要一套系统的价值体系、信仰象征来维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即“天子”,作为“天”“人”的中介,维护宇宙和谐,位于世界的中心,具有一种普遍的象征意义,辐射出无上的权威。几千年帝制的突然结束,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使中国传统的宇宙论、人生观产生了根本的动摇、坍塌。某些倾心专制论的人也看到此点,承认“在心理方面,旧日的纲纪早已陵夷,系统早已破坏,譬如神圣已被亵渎了,敬畏的情绪已化作烟云了。”所以要行专制也不容易。尽管此时大敌当前有可能唤起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同仇敌忾,但并没有一种价值系统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使全国真正聚集在“一个党、一个领袖”的麾下。国民党虽居统治地位,拥有全国最庞大的武装力量,但其本身腐败不堪、派系林立、无法统一,更谈不上完全、彻底、有效地统治全国。所以有人忧心忡忡地说:“言及政治制度,既非党治,又非民治,党统法统,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无法实现“新式独裁”。
“新式独裁”的难以实现,不仅在于旧的已经毁坏,还在于“现代的中国,有几件新要素都是从前所没有的。第一是科学,……第二是国际的复杂关系……第三是民治思想。”所以,“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当然,民主论者也认识到民主政治的种种缺欠,但“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不过是残缺的程度问题”,“所以相信民治制度,正因为他比一切其他的制度,缺点较少”。在某种程度可以说,他们对民主制度的选择是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所以胡适呼吁人们警惕“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并坚决地说道:“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可谓语重心长。
三
耐人寻味的是,透过论战双方激烈的辩争之词,却可看到他们的目的大体相同,即如何救国;他们的出发点都不是个体,而是群体。
专制论者认为集权政治是救国的有效措施,因而必须牺牲个人权利。除少数几篇文章外,民主论者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诸如人的价值、公民的政治权利等民主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仅仅把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救国的最佳手段加以论证。实际上,民主政治与集权政治作为制度而言,除有效率、能力的高低强弱这种技术层面的意义外,还有价值层面的意义。民主政治的价值基础是承认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因而其制度便着眼于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专制政治的价值基础是否定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因而其制度便致力于权力的集中。在这次论战中,专制论者不仅从技术层面上,而且也从价值层面上对民主理论展开批判,而民主论者却只有“招架之功”。譬如,胡适论证代议制民主政治、实行分权的国会制也只是“要建立一个象征全国全民族的机关”,国会的根本观念是“让各省的人到中央来参加全国的政治,所以是养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政治的统一必须建设在平时的维系全国各部分的相互关系的政治制度之上。我们所指出的国会制度不过是一个最扼要又最能象征一个全国大连锁的政治统一的制度。”实际上,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出发点是对公共权力实行分割而互相制约,并通过程序化和制度化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当然,也有个别文章提到价值问题。陶孟和在《民治与独裁》一文中论述了民主政治能统一安定、避免革命等益处之后写道:“因为独裁注重特才,所以以一般人为无足轻重,……民治则使每个人都得发展,然后可以得全体,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真的发展。”遗憾的是,以个体发展作为全体发展的前提这一重要思想,根本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更未引起一种更为深刻的探讨。张奚若在几年后写道:“我相信民主政治的最要理由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值得学的东西。别的政治制度,就是容易学,若不值得,也不必学。这是一个价值问题,不应忽略过去。”不少民主论者当时恰恰忽略了“不应忽略过去”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集权论者却没有忽略这一点。钱端升写道:“赞成民主政治者一方提倡个人自由,一方又声言民治为大多数人福利的保障。然独裁既真能为大多数人(几乎是全体人民)增进福利,则又焉能因少数人的自由之被剥夺,而硬要维护谋福不及独裁的民治?”他强调“个人的估价离了社会的估价是无意义的。”明确提出要为全体利益而牺牲个体利益这一与自由主义注重、强调个人权力相对立的原则。尤值得重视的是张佛泉写的《论自由》一文,深入分析了自由与民主、个人与自由的关系。他认为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是弥尔自由论的两个基石。个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而个人功利主义则导致对政府的否定。他写道:“我认为密尔最要紧的一个大前提便是,在他看来,每个个人都是隔绝的,这个个人的中心是不能与另一个个人的中心互相沟通的。”因此个人应有一不容他人侵犯的私人范围。张佛泉明确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人的不可沟通性只是一种“诗人的我”,就更多方面来说,人类彼此具有可沟通性,表现为一种“社会的我”。而“‘诗人的我’是有特殊性的,而这‘社会的我’便是有共同性的。谈社会理论只有由社会的我出发才可;若由隔绝的我出发,……一切社会问题便无从谈起”。他的结论是:“我以为这种的自由概念,在今日的中国是不该存在的。”“我觉得目前在道德哲学上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要使我们把个人与社会打通,而不是要藉荒诞的理论加深已存在多年的个人与社会间的鸿沟。”对密尔等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尖锐批评,表明相当一部分中国自由主义者开始从哲学层次上背弃了自由主义精神。
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首先是民主主义者,然后才是自由主义者。一旦二者矛盾,只能忍痛牺牲后者。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也是把个人的启蒙作为救亡的手段,但相对而言更为注重的是个人的独立、个性的发展。高一涵明确写道:“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扩张一己之权利,搘柱国家牺牲一己之权利,则反损害国家存立之要素,两败俱伤者也。”陈独秀则更加果决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从五四时强调“扩张一己之权利”即是爱国行为到此时要求自觉地牺牲个人权利,表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时段的思想历程。难怪胡适在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但在近代中国残酷的现实面前,信奉“个人主义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者们被迫进行一种丧失“个性”和“独立性”的选择。丁文江无可奈何地说,宁当苏联的地质学家,不当巴黎的白俄:“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在这种情境下,象自由民主、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仅能成为极少数人孤独的个人信念。而且,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集体本位的伦理观相去甚远,不易在传统文化中找到支点,近代中国社会又没有为其提供足够的社会基础,迫在眉睫的亡国之祸更是雪上加霜,使自由主义面临绝境。其命运可想而知。
这场论战之后,蒋廷黻、翁文灏等人踏入仕途,实践其“改旧为新”的理论,但结果毫无作用,并未将南京国民政府改造成为理想的“新式独裁”。其实,在此前十余年的时间内,早有类似的实践。蔡元培、胡适等在20年代宣扬“好政府”主张,企图改造北洋政府,王爱惠、汤尔和、罗文干等组成“好人内阁”;稍后丁文江入孙传芳幕,亦企望“改造军阀”。结果,不是被玩弄于股掌之上就是实际上为虎作伥,根本谈不上“改旧为新”。这一次又一次历史的经验教训,沉重而深刻。
(注释从略、本文参考文献:《国闻周报》、《东方杂志》、《时代公论》、《独立评论》、《新青年》、《甲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