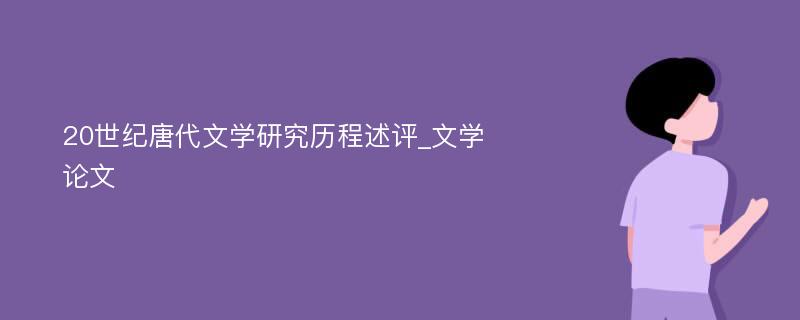
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历程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2)01-0070-08
一、20世纪上半叶
在20世纪前20年里,古典文学研究界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依然是沿袭着宋明以来点评、鉴赏、集说旧的研究方法,重复着一些旧课题。如世纪初出版的王闿运的《湘绮楼论唐诗》就是明清以来古典诗学研究界宗唐派的延续,该书论唐诗重声调、格律,推崇初盛唐诗的声韵和意象,与当时众多的宋诗派有分庭抗礼的意味。而且,作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传统的点评式的审美感悟,而非系统的理论探讨。
唐代文学研究新面貌的出现,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掀起了巨大波澜,而且对当时唐代文学研究的旧思路、旧方法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这首先体现在20年代出版的一些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开始对唐代的重要文体、文学派别和诗人群体关系进行初步的清理,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则着眼于唐代文学阶段性演进的特征和不同流派,尤其注意到影响文学的诸多外部因素,如政局、选举、交通、生活、外来音乐等,均为后来唐代文学“史”的研究开了先河。其次,以郑振铎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明确提出要和传统的文学研究告别。他们除了在理论上引导大家走一条考论结合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而且还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以《文学周报》、《小说月报》、《新月》、《青年界》等新型文学研究刊物为阵地,发表了不少从文学形式、文人心态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之关系等新角度研究唐代文学的成果。这些文章大多汲取了现代西方文学研究的理念,或把作家当作活生生的人来看待,探讨他们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情感世界;或持文学进化论,较为历史地描画出唐代各种文学形式的生长过程,在当时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由于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20年代中期直到40年代末,成为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这30年里,唐代文学研究遍地开花,各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进展。
唐诗研究方面,首先是出现了一大批对唐代诗歌进行综合探讨的“通论”性、“概论”性的著作,如邵祖平的《唐诗通论》、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等。其中邵祖平著作是20世纪较早对唐诗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该书虽然没有能够完全跳出明清以来唐诗研究界“天分”、“学力”之争的旧框框,但对唐诗艺术特质的把握和唐诗优缺点的评述,无疑是深刻而中肯的,而且他对唐诗艺术精彩而新警的剖析,对于扭转当时文坛重宋诗而轻唐诗之风气,引导学界重视研究唐诗,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1]林则在引进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唐诗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她将唐诗繁荣的原因归为“学术思潮之壮阔”、“政治社会背景之绚烂”、“文学格调创造之努力”等三方面,将唐诗的发展历程分为“继承齐梁古典作风之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隆盛之时期”、“写实文学诞生之时期”、“唯美文学发达之时期”、“唐诗衰颓之时期”等五个时期,观点新颖,在当时影响较大。[2](P2-14)
其次,由于受唯物主义文学史观的影响,二三十年代还出现了一些结合当时社会现实,研究唐诗中所反映的战争观、劳动观、妇女观的论文和专著,如胡云翼的《唐代的战争文学》、孙俍工的《唐代的劳动文艺》、石笋的《唐代妇女文学之发展》等。这些成果的出现大多与当时社会现状、新思潮的兴起具有密切的关系,如胡云翼著出版于20年代国内军阀混战之中,具有较强的反战色彩。孙俍工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劳工至上的思想。从石笋文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以后全社会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反映了妇女解放的呼声。
然而,最能体现当时唐诗研究特色和实绩的,还是闻一多从20年代末直到40年代初对唐诗所作的系统、新颖而有效的研究。正如葛晓音先生指出,闻一多充分继承了清代朴学重文献资料的搜集、考证的优良学风,“在诗人生平、交游的考订,全唐诗的校勘、补编,诗人小传、别集校读、文学年表、人名引得等方面,以其多样化的研究手段为20世纪的唐诗研究奠定了广泛的文献基础。而他本人早年留美的经历以及在新格律诗方面的创作成就,又使他能融会西方和中国的意象理论,以现代诗人的敏锐感受和艺术气质挖掘出唐诗更深层的美学意蕴。”[3](P2)从而开创了现代唐诗研究资料考证与审美欣赏相结合的新风尚。
同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唐代小说研究也是从20年代开始的,其中鲁迅和郑振铎的开创之功尤钜。无论是从作品整理方面说,还是从小说史理论探讨方面讲,鲁迅都称得上是20世纪唐代小说研究的奠基人。他首先打破了清儒轻视小说的旧习,从1920年8月起,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于20年代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小说史论著,辑校并出版了《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其中《中国小说史略》于唐代部分发明颇多,为后来学界对唐代小说的系统研究指明了方向;《唐宋传奇集》更是20世纪较早问世的、较为可信的作品选本,对当时和后来唐代小说的理论研究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鲁迅侧重从文人心态研究唐代传奇不同,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等著作中,则着眼于文人创作与民间文学之关系,将唐代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放在“俗文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宽了唐代小说研究的领域。
唐五代词的研究,也在这30年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当时学界对唐五代词讨论的重点是词的起源问题,人们大多抛弃了词为“诗余”、“词起源于诗”的传统观点,将词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艺术等多种因素考察词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其中刘尧民的《词与音乐》更是从词与音乐的关系入手,重点突破,追溯到词的源流演变。三四十年代唐五代词学的新成就则主要体现在词籍的校勘和全面整理、词人生平的考订等方面。20世纪以前,唐五代词作总集未见有人进行全面整理。进入20世纪以后,学者们明确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先后有王国维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林大椿的《唐五代词》、刘毓盘的《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等总集问世,尤其是20世纪初在敦煌石室发现的《云瑶集》和其他唐代民间曲子词作品的整理和校勘工作,也在三四十年代取得了大的进展。在唐五代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订方面,则以夏承焘成果最丰。他从30年代开始,陆续对冯延巳、温庭筠、韦庄、南唐二主的生平行事和创作背景进行深入、细致、系统的考订,为唐五代词学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四十年代,唐代文学理论“史”的建构和研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中郭绍虞、罗根泽用力最勤,创获也最多。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大背景下,对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进行分期,分析隋唐五代时期各个批评家的文学观点,强调隋唐五代文论家和文学家们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这种观点对后来的同类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根泽则从30年代中期就开始对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进行专题研究。他不仅陆续写出了一系列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论文,于40年代结撰为《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更重要的是他还搜罗出不少为人所忽视的文论材料,对晚唐五代众多的“诗格”、“诗句图”等著作进行详细、精审的考订和阐述,填补了学术空白。
尤其值得注意是,当时的两位史学家——陈寅恪和岑仲勉,他们在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为唐代文学的研究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从30年代开始,陈寅恪就在隋唐政治史、文化史研究的同时,对中晚唐诗歌展开了“以诗证史”、“以史笺诗”的“诗史互证”式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不仅继承了乾嘉学派重考据实证的优良传统,而且具有更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更深邃的史学意蕴,所以对人们全面、深刻地认识隋唐五代文学家的社会政治背景,创作倾向、审美风尚与当时社会思想、文化思潮之关系,具有极大之助益。后来,唐代文学研究界愈益注重诗人群体的研究,喜从地域文化、社会阶层等文化史的角度考察诗人的文化心态、创作旨趣、审美习尚,大多是受了陈寅恪的影响。和陈寅恪不同,岑仲勉则颇致力于有唐一代文学资料的清理,他除了对《全唐诗》、《全唐文》、《新、旧唐书》等重要典籍进行较为全面的校勘和疏证,还远搜旁求唐五代墓志、碑刻、石柱题名等相关史料,从中钩稽出当时文士的不少生平资料,并使之初步系统化,为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丰厚的资料基础。
总之,三四十年代虽然社会动荡、战争频仍,但是由于当时学者在学术理路和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新创和日趋科学,就使得古代文学研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境界大开,成为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
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变期。这个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主要是探讨文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在批判并剔除其封建性糟粕,继承和发扬其民主性精华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学界普遍用“人民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几根标尺去衡量、分析唐代的大小作家、作品,给它们划线、定性,学者们多致力于评价作家的世界观、政治倾向和作品的现实性、思想价值,而对作家的艺术成就和作品的审美价值则有所忽视。
然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前辈学者们仍然顶着压力,凭着学术的良心,为唐代文学的研究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将文学和时代的变化联系起来,强调了社会经济、政治、哲学和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其次,明晰地描述了诗文、小说、变文、词等各体文学的发展流变;第三,对重大文学现象初步作了纵贯性的系统研究;第四,大、中、小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基本上得到了恰当的评价。这些成果集中地反映在60年代初出版的游国恩等主编、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主编以及刘大杰所著的三大《中国文学史》里,也散见于从三四十年代过来的学者以及一些后起之秀的个人论著中。在知识的系统性、学术的规范性,以及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的开拓方面,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诗研究方面,以林庚、萧涤非、马茂元、陈贻焮等学者的研究较具特色和影响。林庚是诗人兼学者,对陈子昂、李白等具有浪漫风格的初盛唐诗人及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巅峰——盛唐诗歌情有独钟。他在《诗人李白》和《盛唐气象》中凭着他诗人特有的艺术感悟,用诗一般的语言对盛唐时代的诗歌风貌作了十分精彩的阐述。他认为,盛唐诗体现了一种“开朗的、解放的”、“实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为骨干的“少年精神”,这种精神,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乐观的奔放的旋律”。“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是林庚对盛唐诗歌所作出的两个极为传神的概括,抓住了盛唐诗歌的神髓,是不同凡响的创见,所以不但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就是在今天的学界也具有深远的影响。[4](P26-49)萧涤非则运用马克思文艺理论来研究杜甫。他在《杜甫研究》一书中指出,是贫困的生活使杜甫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但他同时又认为,杜甫仍属封建士大夫,其思想根源是儒家。儒学存在若干可取的优点,主要指入世有为的积极精神,虽主张忠君,也主张节用爱民,杜的思想处于忠君与爱民的矛盾之中,而在特定条件下,又有其统一性。萧涤非将传统的民胞物与的仁者精神提高到人道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将它作为杜甫的基本思想,认为一部杜诗,便是“我能剖心血……一洗苍生忧”之实践。[5](P46-62)他还将杜诗形式的创新(如乐府、律体等)放在生活实践中去考察,认为杜对语言形式的采用,都是为了更有力更逼真地反映生活。这些观点不但立论新颖而且比较辩证,基本符合杜甫创作实际,是当时能够比较妥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的成功范例之一。[5](P122-143)马茂元则能够避开政治风潮、思想论争,对唐诗进行基础资料考证和精到的艺术分析。从1964年开始,他为了撰写《唐诗史》,先行着手编著《唐才子传笺证》,试图以辛氏之书为线索,旁征博引,辨析异同,将有关唐代诗人的传记材料,全面系统地加以考订,从而对唐诗风格流派之形成及其传统继承关系,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尽管他的努力只剩下《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唐诗札丛》和其他一些专门探讨唐代诗歌艺术风格和形式流变的论文,但这种研究思路和治学方法对后来的唐诗研究者影响甚大,八九十年代的唐诗研究正是从这两点上取得突破的。陈贻焮也能逆当时学界贬低王维、孟浩然等山水田园诗人的潮流而动,不仅首次对王、孟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辨,尽可能将王、孟的诗歌作品编年,而且鞭辟入里地分析了王、孟诗歌的艺术精髓,为人们更全面、客观地了解王、孟的生活和行事,正确地评价王、孟的思想和诗歌艺术成就,作了很好的铺垫。80年代王、孟研究得以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陈贻焮在五六十年代的相关研究成果。
另外,王重民在进行敦煌研究的同时,也在唐诗的整理和辑佚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为前此闻一多、岑仲勉等学者对唐诗的整理和校勘,是以存世文献为主要资料依据的。而王重民从30年代就开始就敦煌遗书中不见于《全唐诗》的唐代诗作进行系统的整理,在60年代发表了《补全唐诗》,其另一部分成果则在他逝世后由刘修业整理出来。王重民倡导的从出土文献中搜集唐代佚诗的做法,为唐诗辑佚指出了一个新路。
唐代小说研究方面,当时也出现了新的气象。以孙楷第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不再局限于在唐代文人小说——“传奇”本身作文章,而是沿着郑振铎在二三十年代所开创的“雅俗结合”的研究思路,探讨唐人小说与敦煌讲唱文艺之关系,为唐代小说研究拓展了一个更广阔的研究空间。这一时期,唐代小说的整理也产生了不少成果。单行本中如方诗铭校注的《游仙窟》,唐人小说集如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的《剧谈录》和《三水小牍》,就是在今天看来仍具很高的学术水平和版本价值。同样,汪绍楹校点的《太平广记》的出版,也对唐代小说研究的深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六十年代,唐代文学研究还出现了一个新领域。这就是任半塘开辟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他在50年代中期就计划对唐代结合音乐的词章与伎艺作全面的研究,完成包括敦煌曲研究、唐戏弄研究在内的18部著作。在他超乎常人的努力下,这些理想逐一得到了实现。他在五六十年代,先后出版了《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唐戏弄》、《教坊记笺订》等著作,初步建构了一个唐代音乐文艺的研究体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诸位学者不但在当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以其富有前瞻性的研究思路和切实有效的研究方法启发了一代学人,为80年代以后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后继人材的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文革时期
文革十年,无疑是学术研究的灾难期,唐代文学研究也呈现出荒漠化的倾向。由于当时全国大张旗鼓地扫除“四旧”,作为“封资修”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典文学研究尤其在被禁止之列,所以在1967年之后的四五年间,在各报纸杂志上,论及唐代文学的文章寥寥无几,而且多是大批判性质的。到文革后期,随着“评法批儒”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一大批用“两条路线”来分析、批判古代作家、作品的文章。唐代的诸多作家也被一一划到“儒家”或者“法家”的行列。被划成“儒家”的作家如杜甫、韩愈等,自然就在全国范围内被口诛笔伐。相反,一旦被定性为“法家”,如李白、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则不仅受到异口同声的褒扬和歌赞,而且可以享受到出版大量“大字”作品集的“殊荣”。总的看来,无论是“评法批儒”运动中产生的文章还是出版的作品集,大多没有学术性。
但是,要说文革之中一点“学术积累”也没有,也是不够公允的。因为70年代初问世的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和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虽然有特殊的出版背景,但也都提出了一些学术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当时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过具有学术意味的讨论。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章士钊著系作者数十年研读柳文心得之结晶,几乎未受当时“儒法斗争”的影响。该书不仅在行文和用语等方面与当时的思潮、运动格格不入,而且在柳宗元思想研究方面,赞赏柳“取唯民主义以为政本”[6](P1267-1275),对柳宗元佛学方面的修养亦持褒扬的态度,这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6](P1852-1870)由于该书具有一定的学术性,所以在出版后不久,日本学者笕文先就撰专文向国际学术界进行介绍,给予较高的评价。
相对而言,郭沫若著受当时意识形态影响要大得多,书中始终贯穿着阶级分析标准,但作者所阐述的问题,又不乏一定的学术性。如在“李白研究”部分,作者首次提出李白生于“中亚碎叶”说。当时就得到不少学者的响应,遂成为李白出生地研究中一种较有影响的说法。另外,他还第一个肯定了稗山在60年代初提出的李白“二次入京”说。稗山说虽然是对传统说法的新突破,但在提出之后的十年中一直未有人响应。经过郭沫若的这一肯定,才得到了学界许多人的认同和补证,后来也成为80年代李白研究界讨论的一大热点。此外,作者在李白生平和思想等其他重大问题上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多有论证。同样,作者的杜甫研究,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如杜甫与宗教之关系,一向很少有人论及,20世纪上半叶只有志喻的《杜甫诗中之宗教》一文涉之。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未见有人对之进行探讨。郭沫若在此书中重提这一问题,对开拓人们的研究视野是很有意义的。[7](P121-195)
四、20世纪80年代
文革结束之后,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唐代文学研究经过了一个复苏期。从1978年开始,思想界、文化界展开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逐渐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分析的评价标准,重新以历史的、唯物的观点展开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唐代文学研究也开始恢复生机,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研究领域。
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的复兴,还与学界自身的不懈努力分不开:
首先,学界作了大量、有效的唐代文学的普及工作。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版和新版了一大批唐代文学作品选注本和欣赏著作,其中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的《唐诗选》、刘逸生的《唐诗小札》,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代室选编的《唐诗鉴赏集》和《唐传奇鉴赏集》,霍松林的《唐守诗文鉴赏举隅》等。当时的中央和地方电台、报刊也定期或不定期地播出、刊登一些唐代文学专家撰写的作品赏析文章,而萧涤非主编的《唐诗鉴赏辞典》的问世,则将唐代文学“鉴赏热”推向高潮。所有这些唐代文学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使全国难计其数的一般读者和唐代文学初学者受惠良多。这些著作和文章不仅使人们充分领略到中国古典文学黄金时期作品高度的艺术美,获得了充分的审美享受,而且使得唐代文学研究成为当时全社会所关注的“显学”,极大地激发了大批年青人进一步学习和钻研唐代文学的热情,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唐代文学研究的后继者。
其次,从70年代末开始,全国各大高校的中文系纷纷恢复研究生的招生,唐代文学研究方向又是大多数高校招生和培养的重点。其中成绩较为显著的单位主要有北京大学中文系由林庚、陈贻焮、袁行霈等教授指导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硕士、博士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由吴世昌、邓绍基等研究员指导的唐宋文学硕士、博士点,南京大学中文系由程千帆、周勋初等教授指导的古典文献硕士、博士点,复旦大学中文系朱东润、王运熙等教授指导的唐宋文学、古典文学批评史硕士、博士点,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霍松林教授指导的唐宋文学硕士、博士点,西北大学中文系傅庚生、安旗等教授指导的唐代文学硕士点,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唐圭璋教授指导的唐宋词研究硕士、博士点,南开大学中文系王达津、罗宗强教授指导的唐宋文学、古典文学批评史硕士、博士点,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半塘教授指导的唐宋文学硕士、博士点,等等。这些单位80年代中前期毕业的硕士生或博士生,大多自毕业起就一直活跃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现已成为学界的主要骨干和中坚力量。
再次,从80年代初开始,唐代文学研究界就重视学术交流,并于1982年在西安成立了全国性的唐代文学学会,编辑出版了会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唐代文学论丛》(后改名为《唐代文学研究》),以后每两年举行一次高水平的唐代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二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会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发展最为正常、交流活动最多、学术气氛最好的学术团体之一。
可以说,无论是从外部环境看,还是就内部气氛讲,80年代是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史上最为宽松、自由、活跃的时期。
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中老年学者大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学术激情,在不少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如,程千帆在1980年出版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就是作者几十年来学术心血的结晶。作者在对大量材料的梳理、考订、判别之后,提出“对于唐代文学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这一新警的观点。[8](P2)作者还在这部著作中用三章的篇幅,分别仔细地考察、论证了行卷对唐代诗歌、古文运动和传奇小说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在科举对唐代文学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论述上,还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该书都给当时的唐代文学研究界以很大的启示。另外,程千帆还有80年代中期带领其研究生莫砺锋、张宏生等对杜甫诗歌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作了新的探索,也在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陈贻焮从80年代初就开始倾全力为杜甫撰写评传,前后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三卷本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杜甫评传》。该书在充分掌握清代以来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对杜甫的游踪、交往和杜诗的写作时间、地点等,作了相当多的考订工作,纠补了前人的不少缺失,可谓是20世纪杜甫研究的集成之作。而且该书还将杜甫的生平考订与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时代背景融会贯通,兼顾作家个体和诗人群体之互动关系,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唐代文学活动画卷。[9](P1-104)另外,他对中唐两大诗派的形成原因的探讨和发展轨迹的阐述,也为后来学界对唐代文学艺术流派和诗人群体的深入研究开了先河。袁行霈则注重探讨唐代诗歌所蕴含的独特艺术精神,分析盛唐诗歌得以繁荣的社会文化因素。其对王维诗歌的画意、禅趣的阐述,对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之关系的探讨,对李贺诗歌中独特心理状态、表现艺术的分析,都颇为精彩、独到,启人思维。傅璇琮则在唐代文学史料考据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唐代诗人丛考》是对传统考据学的发展,该书一反前人重视大作家、忽视中小作家的弊病,对唐高宗至唐德宗前期28位史书语焉不详的诗人生平事迹进行审慎、翔实的考证,促进了学界对中小作家的研究。其《唐代科举与文学》则把程千帆的相关研究又往前推进了一步。罗宗强也是一位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学者,他在80年代先后出版了《李杜论略》、《唐诗小史》等立论新警、论述深透的著作。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不仅打破前此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只重视作家文论的局限,首次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放在一起研究,较全面地说明文学思想的发展面貌。而且,他对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趋势的认识和史的分期也与前人大不相同,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些重要环节和不少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敢于打破陈见,提出自己新警的见解,使得本书成为80年代隋唐五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较具学术创意的著作。[10](P447-474)此外,安旗对李白生平及其作品主题的阐述、郁贤皓对唐代刺史的全面考证、陈允吉对唐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的深入探讨、吴汝煜对全唐诗及唐诗作者生平事迹的细致考订、项楚对王梵志诗歌和敦煌文学谨密的研究,也都在学界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同时,80年代初毕业的一批唐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从80年代中前期开始,以其特有的锐气和有素的学术训练,攻克着一个个学术堡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其中,葛晓音、赵昌平、陈尚君、杨海明、董乃斌、李剑国等人尤为突出。从80年代中前期开始,葛晓音就致力于对初盛唐诗歌革新过程的探讨,试图揭开盛唐诗歌艺术繁荣之谜。为此,她远搜旁求,不仅仔细梳理、厘清了隋唐之际直到中唐的诗文革新环节,提出了许多独标胜义的新说,而且针对初盛唐诗人对汉魏六朝文学遗产的辩证态度,发掘出初盛唐作家与汉魏六朝文学之间的种种必然联系,这就打破了学界习惯就唐代而论唐代文学的旧有研究格局。而且,她每每能从人们熟视无睹的大量原始材料中发现问题,并进而升华为理性的认识,积微观而为宏观,又以宏观指导微观,势如破竹,得出某些规律性的结论。另外,因为她在艺术理论和鉴赏方面具有相当的造诣,所以她对唐代诗画表现艺术和诗画审美理论的分析也颇为精彩独到。[11](P85-110、272-296)和葛晓音主要运用传统的治学方法探索唐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环节、重大理论问题不同,赵昌平偏重借鉴西方近现代艺术理论和分析方法,对唐代诗歌艺术的发展演变史进行分阶段、分体裁的深入探讨。和葛晓音一样,赵昌平也同样不轻信现有的结论与依靠现成的研究模式,而是注重自己具体研究后的感悟和新结论。所以,他对“吴中诗派”及中晚唐诗坛的史学考证和理论探索,给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初、盛唐七古、七律诗歌风格、艺术形式演进过程的细腻分析和“史”的梳理,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唐诗发展内在规律发面的独特理论思考。[12](P1-87、131-159)陈尚君则继承并发展了岑仲勉、王重民等前辈学者优良的考据学风,从80年代前期开始,就一直潜心于唐代文学典籍资料全面、系统的清理和辨析。他在80年代先后完成了《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的辑校工作,同时还对唐五代诗人、词人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谨密、审慎的考订和汇辑。由于其考订成果的集成化和系统化,所以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杨海明在唐宋词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他打破了传统的作家小传加作品点评式的词史研究模式,着重对唐宋词各种流派艺术风格的流变进行梳理和描述,撰述了《唐宋词风格论》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接着又在深入研究唐宋主要词人、词派、词风的基础上,开始全面、系统地撰写唐宋词史。在《唐宋词史》中,作者能从社会、文化、心理等角度对词史上的现象进行挖掘,稳实厚重中时见新义。80年代前期,董乃斌主要是用传统的考据和理论分析方法,对中晚唐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到80年代中期,他开始尝试汲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精髓,“洋为中用”,运用各种新方法对唐代文学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他既有运用文化阐释学、符号学分析唐代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如对李商隐心理和艺术创作的分析,又有对中国封建文艺体系进行整体把握、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进行规律性探索的宏观文学史著作,如用叙事学理论分析唐传奇和中国小说文体独立问题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显示了新方法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实绩。李剑国则颇致力于唐传奇基础资料的考证、辑录工作。他除了辑录了唐代以前的志怪小说作品,为深入研究唐传奇本身进行溯源,还对存世的唐传奇作品作了尽可能的叙录和考辨,为开创唐代小说研究的新局面打下了较好的资料基础。
总之,80年代是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复苏和兴盛的时期,这十年中所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是20世纪前面几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五、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最后十年,无疑是唐代文学研究高度繁荣的时期。而且这种“繁荣”又兼具集成、新创和转型诸特点,所以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一些老年学者带领中青年学者进行集体攻关,在90年代完成了一系列集成性质的成果,如安旗带领阎琦、薛天纬等学者编著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陈贻焮主编、陈铁民、彭庆生副主编由全国中青年学者参加的《增订注释全唐诗》,霍松林带领吴言生、邓小军、傅绍良等编著的《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霍松林主持、全国众多中青年学者参加编著的《新编全唐五代文》,任半塘、王小盾合著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郭在贻指导、黄征、张涌泉编著《敦煌变文校注》,詹锳主编、葛景春等中青年学者参与编著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傅璇琮、周勋初带领众多学者编著的《唐才子传校笺》,傅璇琮、陶敏、李一飞、贾晋华、吴在庆合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其次,一些80年代已经取得较大成就的中青年学者,进入90年代以后,能够不断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超越自己,再创学术新高,成为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如葛晓音,到90年代以后,虽然仍以初盛唐诗歌的发展以及盛唐诗歌繁盛原因的探讨为其研究重点,但是已经打破了她自己在80年代多从儒家诗教观点入手的研究格局,而是从女主专政与文学发展、音乐和盛唐乐府诗歌之关系、中西文化交流与诗歌文化特质、教育环境与文人素养、创作范式的定型和普及与诗歌创作繁荣之关系、声律体调与初盛唐诗歌体式特点等更深、更广同时也更切中肯綮的角度,探讨盛唐诗歌之所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高潮的原因。其《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一文,通过追溯初唐到盛唐"How to"之类著作的发展过程,探讨这种树立创作范式的作法与诗歌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为盛唐诗歌的繁荣找出若干被人们忽视了的原因。由于这篇文章“为唐诗繁荣原因问题开辟了新的解释途径,得出结论切实可信。文章所使用的材料,多属当今学界少有论及者。文章层层剥离,内在逻辑性强,视角既新,思路亦清,总体水平颇高”,所以被《文学遗产》编辑部与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古代文学、古戏曲基金联合设置的“《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评委会评为第一届也即1995年度优秀论文奖。[13]赵昌平在90年代对唐诗史的研究也有新的开拓,如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去对盛唐诗人群体和诗风特质,对上官体的研究和评价也为前人所未发。陈尚君90年代以后的成果,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其《唐代诗人占籍考》尤具新意,文中根据现有研究成果,作了唐代诗人地域分布及唐代前后期变化的统计,对探索唐代文化地理和唐诗风貌与地域文化之关系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再次,一些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毕业的唐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已经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新创,如王小盾的《唐人酒令艺术》和《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在其师任半塘开创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领域有新的拓展,张伯伟的《唐五代诗格校考》是对郭绍虞、罗根泽等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系统深化,蒋寅的《大历诗风》和《大历诗人研究》标志着学界开始对唐诗发展中的低谷和过渡期研究有所重视,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在对唐代文学文化精神的探讨中,融入其对传统文化在当前社会中人文价值的深层思考,使古代文学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另外,世纪末的唐代文学研究也初露学术转型的端倪,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21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例如从更深的层次、更直接的环节研究文学高潮形成的原因,以及高潮之间的“创作低谷”在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对于一些20世纪以来约定俗成而又模糊不清的文学现象和概念重新探索;对于唐代文学中蕴含的人文精神现实意义的阐述;对于海外学者研究较多而在大陆唐代文学研究中尚感欠缺的艺术形式问题如声律格调、文体内涵等作纵贯性的考述等。而且研究者的思路已向纵深发展,史实、材料的考证与理论分析的水乳交融将成为下一世纪治学的主导方向。更深细的文学史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可能会取代20世纪的作家作品分析热、文学史写作热、宏观研究热。此外,电脑的使用和因特网的普及为资料的检索和考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但是,研究者自身的学术鉴别能力、艺术审美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收稿日期:2001-07-15
标签:文学论文; 唐诗论文; 诗歌论文; 杜甫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唐诗宋词论文; 隋唐论文; 李白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