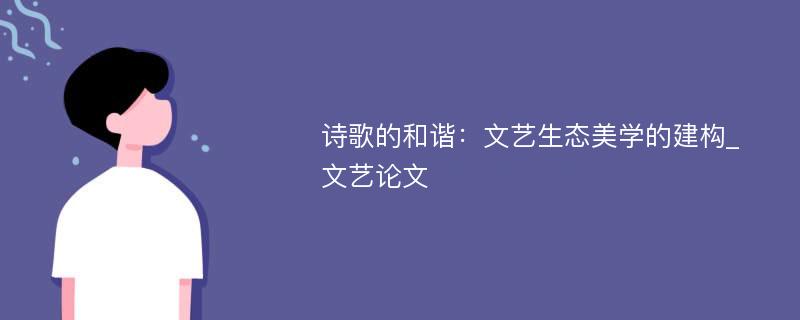
诗意的和谐:文艺生态审美的构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意论文,文艺论文,生态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生态审美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上,以系统整体化的思维品质,在人们追寻和谐自由与灵性化的存在方式中,构建人类朝向未来的审美体验形式。在文艺生态审美境界中,人们始终是和谐与圆融性地游走在与自然存在的审美境遇中,在循环性的,诗意化的历史与逻辑之链中,演奏人类自身由自然而生成的交响曲,并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自然之身,同时又不断地回归与自然共在的审美化的生境中。
一、诗意自然的和谐:文艺生态的构成性
文艺生态所关注的不是自然的物理层面,更不直接介入对自然环境的征服与改造,而是透过人类艺术—精神性生存体验活动,而关注与人类生存发展活动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关系中,人对自然生态的态度、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探悉人类的现实生活、生产实践、精神活动中自然的缺席,并深刻认识这种生存态度、行为观念与自然缺席对生态和谐及人类的生存产生的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文艺生态与自然生态还表现着逻辑演替的趋向,它应该内蕴着起始于自然生态,通过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态的构建,经由社会生态机制运作,而又回归于自然生态。回归朝向的不是本源的、物性的、实体的自然,而是超越性的,是在对生命存在的深层次理解的视域中,更高层次的、精神—审美化的认识、理解和体验自然。
自然生态是生物有机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由人的生存而介入的自然生态就形成了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与环境的关系。文艺生态的“自然”形态,首先是这种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自然生态,它成为文艺活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对于文艺活动来说,体验自然生态并不是目的,因为文艺活动是人的活动,文艺生态活动的目的是生成人的生态性存在,起码是需要构建一种“生态人”的生存路向。“生态人”的生存基础是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但要使这种关系始终处于和谐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结构中,使自身游走在具有生态循环结构性特征的网络中,“生态人”就必须完善自身对于生态系统具有的调适、融通的能力,完善人们那种始终处于自由、平衡的生态状态中的能力。文艺生态要面对实存的,但却不是亘古不变的自然。文艺生态所指向的自然,是对实体自然的超越,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体验被情境化了的“自然”。从结构性状态看,它是本源性自然、情境化自然和心意化自然的结构。这种三位一体结构是双向流动的,一方面由自然生态的实在性、本源性流向主体的心意;另一方面又由心意回归自然的本源,形成生命能量的互动与交换。故刘勰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 从生命的节律特征上看,自然的这种双向流动,不仅印证着生命的实在,更是生命活动中蕴聚的诗性韵律;不仅是有感而发的生命律动,更是在这种生命律动中生态化的能量流动。我们将这种灌注诗性韵律的,既是实存的,能够体现万事万物运动法则的,又具有超越性品质,能够自然而然地融合与流入生命肌体,融入生命的情思、创发生命精神的自然,称为是诗意的自然。人的生命体验与诗意的自然作为两大脉系构筑起了文艺生态的澄明之境,作为文艺生态的本体存在,是在整体化、有机性的生态关联中奠基的艺术审美体验的基石。文艺生态的澄明之境表征着这样的生态情景,在文艺审美体验中昭示着那种无穷无尽的,相互作用的生态关联,世间万物都可以在这种“澄明之境”中寻找到交合点。“这个点是空灵的,但又集中了天地万物的最广博、最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它是最真实的”。[2] 之所以说它是“真实”的,还在于它是消却功利之“有”的“无”,作为文艺生态之源,它是生态化体验情境中生命存在意义的呈现。
文艺生态具有强大的整合性,是一个巨大的、诗意化的整合体。人的生存活动中所表现的一切生态性需求,生命的、绿色的、精神—文化的都可以诗意地整合进文艺生态的怀抱,被文艺生态所蕴聚的生命情感所溶化。文艺生态的整合性首先使文艺成为整体性的活动。它体现为一种由自然感性到精神—审美的生态化的人类活动方式;其次,它又是一种耦合性的功能结构。人类文艺活动的生态化存在方式,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审美化的回归状态,其实就是文艺生态的功能体现;最后,它还是一个过程。它不仅是文艺生态整合性的过程,还是整合体生成的过程,它印记着人类由自然生成的过程,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化体认的过程。
文艺生态也是对象化的存在,并且是人类诗意生存所理解和感悟的对象。由于文艺生态以自然生态为基础,它必然构筑生态审美体验的对象。不论是自然生态,还是人的生态性存在的文艺生态,以及生态人的审美活动,都成为文艺审美活动的对象。它储存着无限的能量与信息,成为文艺审美活动的源泉。
文艺生态还是一种情境预设,文艺生态预设了天地人共生的特殊寓所,是人对天地境界的“觉解”。冯友兰在解释“觉解”一词时说:“解是了解……觉是自觉。”[3]“有觉解是人生的最特出显著底性质。因人生的有觉解,使人在宇宙间,得有特殊底地位”。“从人的观点看,人若对宇宙间底事物,了解愈多,则宇宙间底事物,对人即愈有意义。从宇宙底观点看,人之有觉解对于宇宙有很重大底干系,因为有人底宇宙,与无人底宇宙是有重要底不同底”。[4] 海德格尔所说的“思”与“在”的发生,也使人感悟到自己是在与天地境界同生共荣中,“觉解”到“思”与“在”的本真。文艺生态的这种“觉解”的情境,不同于生物性生命体实体的本能形态,不同理智性、道德规范性的“觉解”,也不同于宗教性神秘体验性的“觉解”,它更多的是在整合性结构与功能的审美化的生命体验中,通过情感体验性的“觉解”,在审美想象的飞跃中,转换实体性的自然及天地人的“可感世界”,而表现人的精神—心灵之境。其实,它是经由感性生命的升华而为精神—心灵的“觉解”,同时又归复于更高层次的自然生态境遇和天地人共生共荣的境界。
二、诗意生存的和谐:生态审美的构成性
生态审美也是以自然生态为基石,以生态自然化的审美为活动的基础,但同时也是生态整体性、系统结构性在和谐自由关系中的审美体验方式。生态审美立足于人的现实存在,解析人的审美实践活动的生成,建构人的精神—心灵境界,消解人类活动中的对立与争斗,审美化地调适人类社会的发展,启悟人类朝向未来的优化生存。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漫长过程,实际也是人的生存斗争的历程。斗争性表现为利益获取中对对象的征服与改造,从斗争的动议和目的性上讲,它内蕴着三个层次:其一,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即人为了自身能够得到“优质化”的生存与发展,对自然进行征服与改造;其二,是在社会存在范围内,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斗争,即个体人,个体与群体、社会,不同社会群体、区域、国家之间,在利益取向的左右下的斗争;其三,是个体生命内在的斗争,这一方面是利益最大化所引发的心灵焦虑,另一方面个体生命活动外化方式所引发心灵矛盾。从斗争的形式上讲,它也可以表现三个层次:其一是肉体的占有和杀戮,包括个体性、群体性、社会性的斗争,肉体的碰撞与战争是其主要表现;其二是经济与交换领域利益之争,争斗的目的显然是利益取向的最大化,斗争的形式可能是和风细雨、温文尔雅式的,也可能是战争性的、狂风暴雨式的,后者就同于人们常说的,“商场如战场”;其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它的动议和目的是利益取向,但形式却往往是权力,是权力话语,或是以人权为表征,或是以获取领导权、统治权、主导权为表征。不可否认,斗争性部分地改变人的生存境遇,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斗争总是不和谐的,非生态化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在生物多样的世界里,斗争也是一种常理,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自然与生物的协同进化,也表现为斗争性的进化。不同的生物体往往是在斗争中或是强化了肌体,成为胜者;或是弱化了肌体,而成为弱者,以至于死亡、灭绝。显然,斗争还可以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人类世界的斗争性与生物多样世界的斗争性何其相似,斗争性伴随着那种权力话语,使人们往往“徜徉”在占有性、征服性、改造性的“神性”境界中,对自然的占有、征服与改造及人类社会自身关系中的占有、征服与改造此起彼伏、共同消长、互为参照。这种权力话语的表征,作为利益的驱动机制,是非和谐性,也是非生态化,它所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一种强势权力,一种非生态化、非审美化、非诗意化的自我认同。在生物多样性的世界中,这种强势权力是自我不断地获取最大生存机遇和时间、空间,那么,就必然挤占了弱小的、生存适应力差的生物体存在的空间。当这些生物体生存的空间和条件越来越小时,就会濒于死亡、灭绝,与此同时,强势生物体的生存伙伴就会减少,所能够获取生存资源的机遇也就越小,这就形成了生存的悖论。
人类的生态化、审美化、诗意化的生存和发展,应该是合理化的演替生物多样世界的节律,符合生命运行的节奏。在人类的生存发展活动中,如要合理地、稳定性地走向未来,并且要优化人类自身的生存结构,就必然需要在生态化的体验中,审美的、诗意的调适多重生存关系的自由与和谐。我们所理解的生态审美,是生态化、诗意性和建设性的统一,是从生存与发展逻辑过程中演绎人的生存魅力。所谓人的生存魅力,不是破坏性、侵犯性的、占有性的,也不是浅层次的指责和批判人类的斗争性和在多重关系中对抗性、不和谐性,而是通过创设一种深层的生态化情节,在生态系统的情境中与多样存在的生物体权利互为认同中,共享生命的快乐,以协同进化的脉络行走着发展的轨迹。
生态审美是消却中心论的审美,即不单是以人为中心的审美,而是人与自然生态在整体性、系统性和一体化状态中的审美,或者说,就是将人与自然生态的系统整体的关系性视为审美对象,其审美关系就建立在这系统整体化的生态关系中。我们还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思考生态化的生态审美。从狭义上看,它是从自然生态的对象性存在,以及人自身的自然性的生存状态把握人的审美化生存,是把本源的自然生态和人的自然存在作为关系性的存在,并且视其为是生命现象与生命的过程。一方面,通过人的活动构建这种关系的和谐与一致;另一方面将生命体的进化与演化的生命过程视为是必然的,并且是与人类生成的生命过程是同体的、协同的发生,其实是人与环境和谐关系的表征。从广义的角度讲,生态审美还需要将人的生命过程放在宇宙的大视域、大系统整体中,在“全宇宙”共在的境界中“觉解”生命现象,从而“觉解”人对生命的审美自由的体认。除了现实的审美化的生存情境外,生态审美还存有审美生存的思维取向,它是以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思维品质,建构人对生命过程的理解与体认,即表现诗意性、建设性和审美化的审美方式。
诗意性的生态审美是沿着生命节律的轨迹,在和谐自由的审美之境中,澄明生命灵境,体味与多样存在的生命体共享生命快乐的美的韵味。诗意的追寻是自由的情境,但它是追寻那种生态化的自由,而不是在人类中心论条件下建立的人类自我的自由。人类自我的自由是建立在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益取向最大化的条件下,体验利益满足时的快感,它最终可以由利益取向的自由而导致整体生命存在的不自由,那么,这就是生态危机状态的不自由。显然,人类自我的自由是“祛魅”的生命的自由。诗意性的生态审美所昭示的自由情境,祈望人类能够浸入心脾的限制利益取向的自由,而呼唤生态系统中多样生命体共生共荣的自由,共享生命的快乐,其实,这就是生命自由的“返魅”。诗意的自由必然需要自然生命体的感发,在充满生态化的情思中“感物”、“浸情”、“形言”,生命的节律只有在诗意的情境中才能够真正彰显自由生命韵律,从而充蕴生态审美的韵味。
建设性的生态审美是在自由魅力的再现中表现了一种强盛的生命力。所谓建设性是超越以对立、斗争为起始点的二元论,以及机械论的还原论,而倡导整体有机论,依照系统整体性思维指向,建构生命自由的逻辑。建设性还是朝向未来的现实化的生命体验形式,也就说,人类在关注以及践行现实的生存活动中,必然需要面对未来的生存,以现实的境遇建构未来的生存园地。一切只重现实,而轻视未来的人类活动,都会是不同程度的有着二元分离的倾向,实际也是轻视自然的主权意识的活动,都是带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性,是解构生命自由魅力的活动。对于生命体的“力”的结构来说,这是生命力的阻隔,是削弱,是“下降”,而不是丰厚,不是强盛,不是“上升”。恩格斯说:“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适合居住状况的相当肯定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有下降的过程。”[5] 其实,自然科学的预言与利益取向的预言是异曲同工的,“上升”与“下降”的合成即给人们以深刻地警示,科学的二元性及利益的最大化所造成的破坏性,有可能使“末日”会过早地向人类招手,因此,这需要人类主动性、建设性地去弥合、阻隔这种“末日”的来临。生态审美是建设性的,需要全面的整合生命“力”的结构,建设多重关系的,全面而自由的生命力,是在系统整体性的关系中,和谐、合理、有效地组合人与一切对象性存在的关系,使之在与自然生态的基础性关系之上,建立全方位的生态系统观,使人们在生态整体性关系中,进行审美体验,能够从中走进悦性怡情,天地人共在审美境界。
审美化的生态审美是人类在生态化、诗意性、建设性的生态审美结构基础上,而呈示深层次的审美活动,是在人—自然—社会—精神—文化的复合性系统构成中,所追寻生命的自由。审美化的生态审美超越了对自然生态的一般性的认同与体验,同时又借助自然生态的魅力,引申、升华人社会生态化存在本性,以精神—心灵体验的魔力去感受生态性生命自由。它对生命灵性境界的探询,而召唤人们对“澄明之境”的“觉解”。
三、诗意的整体和谐:文艺生态审美的结构性
文艺生态审美是文艺生态与生态审美的叠合,组合,是生命化、结构性、整合体的审美存在,是以艺术审美体验的生命情怀,感悟与深层次地体味人的生存魅力,建设性地、诗意化地,以生态性生命存在的韵律,徜徉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行程。
1.“生态”:文艺生态审美的结构中介
文艺生态审美中的“生态”具有叠合性和结构性,它起码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是体现“文艺生态”结构中“生态”的中心意义,表现自然生态的本源性、对象性之义。第二层是体现“生态审美”具有定位意义的,既以本源性的“自然生态”之义为基点,而又从引申、比喻意义上,召唤和谐、平衡、多重自由的,审美状态下的“生态”之义。第三层是叠合性、组合性的“生态”之义,一方面它组合了“文艺生态”和“生态审美”,把两者整合为一体化的审美活动形态;另一方面,它创生了新义,在整体性、系统性及包容的情境中将文艺审美活动放在了人类存在的多重自由关系中,在人—自然—社会—精神—文化的复合性生态系统中构建审美化的生命体验形式,它更突出了艺术—精神性的审美存在形式。
2.演替:文艺生态审美的历史脉络
文艺生态审美还演替着一个进化的、历史性的脉络,它告知人们:人类艺术—精神性的生态审美不仅是时代要求使然,还在于这是一个历史的、生成性的必然。尽管在人类原初的生存活动中,艺术—精神性的生态审美体验还是非自觉的,在我们的“先人”们那非自觉状态的生态审美中,对难以解析的自然现象有着无尽的神往,对生命现象的那种神秘莫测充满了至深的膜拜,对人们确立的无数的图腾、偶像沁浸着无限依恋的情思;“先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倾倒与依赖,不断地转换为他们生存的支撑力、主宰力,他们生存的自由就是这种非主动性的依附在自然生态的家园中。近代以来,主体性的情思,满含我思—我在的激情涌动,如汹涌的波涛,一波一浪地推进着人们不断地归复自我存在的天堂;又如同强力的巨手,将人们从漆黑的地狱中拉出,从灭杀性灵的宗教藩篱中解救出来,在“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面前,人们开始享受着人性自由的灵光。这时的审美是倾注了对“自我”的,主体性的愉悦与畅神,人们又越迁出了自然生态的家园,而游潜于追索欲望与利益需要的深渊。这时的“自然”似乎已经不是那种实存的、本真性的、生态化的自然,而变为宗教性的、观念的自然,对自然的审美似乎已经变成为纯然的人化的审美。当人们深深地感悟到共生的伴侣离去,万物喧嚣的景象不在时,蓝色的天、绿色的地,洁净的心刹那间变成了灰色的、褐色的、浑浊的,鸟语花香、生机勃发的灵性之境也变得沉寂了,“寂静的春天”似乎成了未知的春天,此时,人类似乎在扮演着“终结者”的角色,似乎在行使着“掘墓人”的职责。这其实就含蕴着一个顺向的事实,自然的终结实际就是人类自己的终结;为自然、为万物的生灵掘墓,实际就是为人类自己掘墓。于是乎,人们开始醒悟了,开始接受生态的、绿色的召唤,但这决不是去重演“先人”那莫测而神往的圣洁家园,而是更加现实的,通过重新创制心灵的家园,去廓清浑浊的天与地,这是本真性的生态审美,既为人们创制着、建设着朝向未来的精神—心灵生态家园,又在生态审美化的调适下,使人们驰骋在更加繁复、具体、现实的,富有人类创生力的生态园地。这时的生态审美不仅是精神—心灵化的,更是现实的,实在的,是超越“先人”们的非自觉状态的自然审美,超越近代那种我思—我在的,对立状态的审美,而构建着自觉意义上的生态审美。
自觉意义上的生态审美演替着人类体验生命现象的循环结构。对人类的生存来讲,这种循环不是自然感性生命的重演,而是不断地升华,是超越,是更高境界中的生存,是生态优化形态中人类的生存,其实,这也是深层次地演替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过程。如果说生态审美更是现实的,注重现实生存活动的体验性,那么,文艺生态审美就更是精神化,心灵化的,更是现实的生态审美在精神—心灵结构中的“复制”,或“复生”;它对人们生态化的生命体验更具有警示性,更直接沁入人心腹,洁净着人的灵魂。
3.艺术:生态审美的主要载体
人类的审美活动不是虚设的,而是实实在在地内存于生命活动中,并由不同的、具体的活动方式得到呈现,人类对生态世界的审美体认也必然是在这种方式中体现。
这表现了一个事实:审美活动必然需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通过不同载体的运动节律,而承载着对精神与生命的体验。不论是现实的生活方式,是人的衣食住行,是生产实践活动,还是科学、哲学、道德、宗教等活动中,都在追寻生命的自由,在生存关系的和谐境界中承载着“美”的因子,呈现着审美的魅力。一定审美关系的建立,主体所获取的审美的愉悦,必然是在不同的、外显的、感性的载体所接成的对象性关系中,而不可能直接与内隐的“美”发生关系。只有通过载体,才能与审美主体的感性生命相通联,从而将“美”的精神性品质化为现实的、具体的生命存在形式。因此,当我们谈论审美时,往往都是将这不同的载体冠以“美”的头衔,以至形成不同载体性的审美。
生态审美的基本载体是“自然生态”。生态审美的巨大的包容性就在于:它除了通过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建立审美关系,而凸显以和谐为表征的审美关系之外,还在于,它是以人类的整体化存在,或者是人类生态系统的结构性存在为审美关系的一方,即生态审美主体,因此,作为生态审美主体的人类结构性存在,就必然包容与整合着人的一切活动方式,不论是生活的、实践的、政治的、技术的,以及精神—文化的活动。其实,这是我们研究生态审美不同于人的其他审美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认为,作为载体而存在的人类活动方式中,对于审美,乃至生态审美的承载力最强的人类活动方式莫过于文学艺术,因为艺术是审美的集中体现,它能够最全面、整体化地展示人类本质,展示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活动方式,并且它还是最为直观、形象化地,充满着激情、飞动着现象的生命涌动促发人们对美的感受,就是生命的体验启悟着人们会更加深情地关爱着自身,关爱着自然,关爱着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家园。同时,艺术也是人们之间交流、交往的主要工具,艺术审美感受是无功利的,所以它可以消去交往障碍和心灵的阻隔,在直通人的心灵结构中引发人们对生命精神的直接体验,警醒人的灵魂。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蕾切尔·卡逊创作的《寂静的春天》,不正是利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创造了他们的惊世之作,撼动着世人的灵魂。就如同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所作的序中讲的:“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6] 尽管她曾经遭到巨大的非难,甚至于人身的攻击,但“因为她的著作,人类,至少是数不清的人,保住了性命”。[7]
海明威也曾经以自身所运用的艺术审美体验的方式,承载着他对大自然那特殊的崇尚情结,尽管他可能不是出于自觉意义上生态性地关爱,但他的确是从自然生态的生境中找到了自尊,也找到了人类的自尊,找到了人类与大自然共在的快感。大海是海明威的家,是树立自身英雄品格的载体。他在《老人与海》中所确立的自然生境并非是和谐的,古巴老渔夫桑地亚哥为了生存而与大海中的各种生物进行着殊死的“抗争”,具有悲壮的气势,由此,一个硬汉的神话被诗意地抒写出来。同时他对海的爱,大海对于他的生命的不可或缺,使他深深地融入到大海中。他的失败并不重要,他的生命的搏击其实更是精神的游历。为此,他又是成功的,一方面他在这种生命的历险中,展示了一种品格;另一方面,他又进一步看到了大自然的美丽与崇高,由此而召唤人们更加爱自然。
桑地亚哥老人同大海的精神游历的漫长行程会给予我们些许的生态性启示:其一,在生物多样的世界中权利共存与互为认同是必然的,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错综交织的大网络;其二,生存的斗争与调和也是必然的,它促生了生物体间的能量交换,在这种交换关系中生命体各自确证着自己本质,同时也确证着对象的力量;其三,生存的占有实际是一种悖论,当你在侵犯对象的时候,其实自己也被对象所制约,甚至于侵犯,所以,老人也曾叹息,“是我走得太远啦”,因此,我们可以说,节制欲望是必要的;其四,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是不可取的,只要你向自然索取,就必然会得到反向的回报,最终危机的是人类自身;其五,人要获取最优化的生存环境,就必须回归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在生态家园中共享生存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