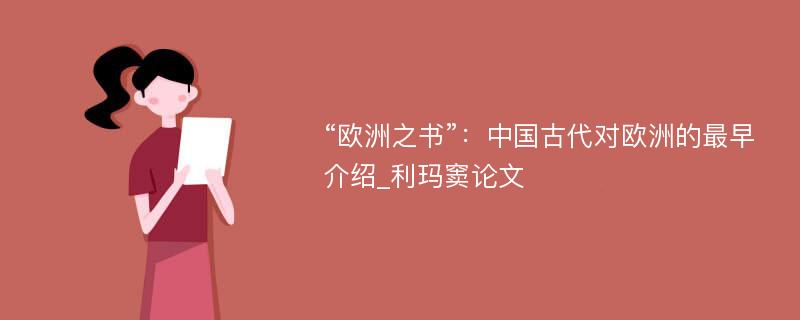
《欧罗巴国记》:古代中国最早介绍欧洲的著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述论文,欧洲论文,中国最早论文,古代论文,欧罗巴国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11-0080-10 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伟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内外学者对利玛窦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①不过,如果翻阅近年出版的一些专著②以及每年近百篇的论文,就可以知道,在目前这个学术高度上,如果没有新史料的发现,就很难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其实,在中国典籍中还有许多史料尚待发掘。例如,不久前,刘明强等人就在《刘氏族谱》中找到了明代广东韶州府同知刘承范所写的《利玛窦传》。③近来,我们在明人徐时进的《鸠兹集》中又发现了一篇题为《欧罗巴国记》的文章。这是一篇关于利玛窦在华早期活动的重要文章,展示了许多前所未知的史实,无疑有助于推动对利玛窦及明代中西关系史的深入研究。 徐时进,字见可,号九瀛,是明代浙江省宁波府鄞县人(鄞县现已改名为宁波市鄞州区,而徐时栋所居住的“柴巷”,④位于宁波府城内,现属宁波市海曙区)。⑤在宁波地方史志以及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所藏《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进士履历便览》、《徐氏宗谱》等文献中,都有关于徐时进的生平介绍。特别是在明代戴澳所著的《杜曲集》中,有作于崇祯十年(1637)的《明正议大夫资治尹大理寺卿九瀛徐公暨沈氏淑人合葬墓志铭》,⑥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徐时进的一生。下面以这篇墓志铭为基础,结合其他资料,对徐时进的生平作一概述。 徐时进出生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十月,万历七年(1579)举人。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进士,被任命为南京工部主事。徐时进自己说,他到南京后“不越月”,就被派到芜湖关去负责收税。⑦此后2年,徐进时都在芜湖工作。梅鼎祚在《赠徐屯田榷满还南司空序》中对此有记载:“万历丙申、丁酉间,而屯曹九瀛徐公来主榷务。”⑧丙申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丁酉为万历二十五年(1597)。接着,徐时进被调到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任员外郎,很快晋升为郎中。沈懋孝在《与徐九瀛职方》一文中曾祝愿道:“愿先生勒勋旗竹,青史亡穷。”⑨万历二十八年(1600),徐时进出任岳州知府。陈邦瞻为此写过《送徐见可太守之岳阳》一诗。⑩不过,岳州的地方志错误地把他的名字写成“徐进达”。(11)万历三十年(1602),徐时进调任荆州知府。(12)万历三十二年(1604)农历二月,(13)徐时进的父亲去世,他只得离职回家守孝。万历三十六年(1608),任广东惠州知府。(14)第二年(1609),升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兼岭东分守道。(15)广东地方志在介绍博罗县的“宁济桥”时写道:“自江东至白沙堆,凡九桥,明万历三十七年岭东道徐时进驾石为之。”(16)徐时进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到北京给神宗皇帝祝寿后,(17)不知什么原因,决意辞官。次年(万历三十九年,1611)获准回家。天启元年(1621),新登基的明朝皇帝熹宗(朱由校)非常器重徐时进,起用他为“南光禄少卿,寻改太仆少卿,皆不就。特加大理卿,致仕”。崇祯五年(1632)六月,徐时进在家去世,享年84虚岁,埋葬于鄞县西三十里孙家湾。(18) 徐时进的主要著作有《鸠兹集》、《啜墨亭集》和《逸我堂余稿》。其中刊刻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啜墨亭集》,(19)在清朝因被政府认为有“诋斥字句”而列为禁毁书。(20)《逸我堂余稿》在清初黄虞稷(1629-1691)所编《千顷堂书目》中有著录,(21)但可能早已失传,所以雍正《宁波府志》将其误作《逸我堂余编》,(22)民国《鄞县通志》也不能肯定哪个书名是正确的。(23) 本文要讨论的《欧罗巴国记》,收录在《鸠兹集》中。徐时进的仕途是从芜湖开始的,芜湖“为古鸠兹地”,(24)故徐时进以“鸠兹”命名自己的文集。在浙江图书馆所藏《鸠兹集》抄本(共8卷)中,《欧罗巴国记》收录在第一卷。在徐时进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改定的《鸠兹集》(共15卷)刻本中,该文收录在第六卷。此外,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所藏《徐氏宗谱》中,也收有此文。由于浙江图书馆所藏《鸠兹集》抄本以及《徐氏宗谱》中的《欧罗巴国记》都有一些脱漏与讹误,因而本文以天津图书馆所藏万历四十五年徐时进补删本为依据。(25) 为了解徐时进《欧罗巴国记》的产生背景,必须先考察利玛窦在中国的行程。 1582年,利玛窦从印度果阿来到澳门。第二年,他随同另一个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1543-1607)移居广东肇庆。1589年,利玛窦被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逐出肇庆,来到韶州生活。(26)1595年4月,利玛窦离开韶州,于5月31日首次来到南京。(27)由于无法获准居住,利玛窦只得离开南京,并于6月28日来到南昌生活。(28)1598年6月25日,(29)利玛窦离开南昌,7月5日或6日第二次来到南京;7月16日,(30)继续北上,于9月7日首次抵达北京,(31)逗留2个月后,启程南下,于1599年2月6日第三次来到南京,(32)并且定居下来。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离开南京北行,1601年1月24日第二次进入北京。(33)此后,利玛窦一直在北京,直到1610年5月11日去世。 万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595年5月1日),(34)神宗皇帝钦定进士名次,徐时进名列第二甲第19名。(35)所以,当利玛窦于1595年5月31日第一次来到南京时,沉浸在及第喜悦中的徐时进还在北京等待分配官职。在此后的2年中,利玛窦居住在南昌,徐时进在芜湖负责收税,两人未曾谋面。从1598年开始,徐时进在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先后任员外郎、郎中。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初,利玛窦第二次来到南京,但行程匆匆,即使与徐时进见过面,也不会有什么深交。利玛窦与徐时进的交往,应当是在1599年2月利玛窦从北京返回南京之后。到了1600年,徐时进出任岳州知府,利玛窦则再次北上,两人各奔前程。从现有文献来看,此后徐时进与利玛窦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保持着通信联系。《欧罗巴国记》后面附有一篇《利玛窦本国刻数不同说》的短文,徐时进注明是“此万历甲辰秋七月从京邸寄来者”。万历甲辰,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此时利玛窦已在北京生活了近4年,但依然写信给远在浙江守孝的徐时进,以说明中国与欧洲在计时方法上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利玛窦本国刻数不同说》是一篇尚未为人所知的利玛窦佚文。 徐时进的《欧罗巴国记》作于“万历庚子四月浴佛日”,即1600年5月20日,正是利玛窦离开南京后的2天。徐时进在文末有过这样的说明:“利生已挟所有往北,期得上贡,而余乡人来,以不及见,征之余,因记之。”由此可见,徐时进撰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一个宁波人到了南京想见利玛窦,正巧利玛窦刚刚离开南京去北京“上贡”,于是徐时进就写下了这篇文章。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将自己的原名译作汉字“利玛窦”。(36)不过,这一名字有多种写法,(37)徐时进将其写成“利马窦”。徐时进这样介绍利玛窦的外貌:“其人目巨而深,色近碧,耳扩而开,浓髭包颔,芃芃而短,鼻中昂而准下垂。中国之貌,远人为之者,肖其三四。”明代一些见过利玛窦的人对他的容貌也有描述,例如刘承范说“其貌则突颡深目,苍颜紫髯”(38),李日华说他“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39)。相比之下,徐时进的描述更为详细。对于利玛窦的才华与学识,徐时进非常钦佩。他写道:“利生自聪警,考验天地坱圠,甚辨”,他本人“独喜生辨博,骇回耳目,好与抵掌”。在明朝末年,还有不少人和徐时进一样为利玛窦的“词辩扣之不竭”而折服。(40) 徐时进的《欧罗巴国记》,是根据他本人与利玛窦在南京时的交谈而写成的。全书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关于利玛窦在南京活动的记载 利玛窦从1599年2月开始在南京居住了15个月。南京是明朝的陪都,权贵密聚,学者蜂附,这为利玛窦拓展在中国高层的活动空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是在南京,利玛窦进入了“中央一级的上层主流社会”,而在此之前,他只是活跃于“省一级”官员圈子之中。(41)利玛窦认为,南京就是此前上帝在梦中告诉他的“归宿”(42)。利玛窦在回忆录中,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叙述了他在南京的活动。(43)但在中文文献中,除了一些诗作(44)以及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的零星记载外,(45)目前所知的史料甚少。现代学者关于利玛窦在南京时期活动的许多著述,实际上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改写利玛窦的信件及回忆录而已。因此,徐时进的《欧罗巴国记》,就为研究利玛窦在南京的活动提供了新的史料。 《欧罗巴国记》不仅保存了关于利玛窦在南京活动的一些资料,而且有的内容还可以在利玛窦自己的著述中找到印证,甚至补充了利玛窦的记载。例如,利玛窦说,他“自进入南京后,所穿的服装都是地地道道的儒服,这种服装穿起来使人显得极其正直”;“登门拜访的南京权贵便络绎不绝,与日俱增”。徐时进则说:“利生入中国,即束发加栉,即习汉音,能汉言,即攻次仲书”;(46)“其在金陵,多访视者,接之卑昂得体,出入肩舆随,童仆冠剑甚都”。浙江图书馆所藏《欧罗巴国记》抄本还有以下文字:“侍儿俱岭粤构得者。客至,具供诸蜜饵,制精美。”在利玛窦带入中国的欧洲器物中,最令中国人感到神奇的是自鸣钟、钢琴、三棱镜、圣母玛利亚画像。利玛窦自己说,当他于1598年初入北京时,在准备献给皇帝的礼物中,就“有钟表和一只中国人从未见过的羽键钢琴及两只三棱镜和一幅来自西班牙的圣母像”;当他于1599年入居南京时,他所携带的“礼物也成了人们的谈资……所有人都想见识一下被中国人称作自鸣钟的钟表,以及美丽的圣像、羽键钢琴、三棱镜和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在中国被传说得神乎其神”(47)。利玛窦自己于1599年8月从南京给欧洲的神父写信,请求多寄一些欧洲器物来,“如一些美丽的油画像、精印的印刷品、威尼斯生产的多彩三棱镜等,这些在意大利不值几文,但在中国可谓价值连城,我们可以当礼品呈献给中国皇帝或要人”(48)。不过,中国文献对于这些欧洲器物的记载并不多。(49)刘承范简略提到过圣母像、自鸣钟(“铜人刻漏”)和三棱镜(“奇石”),但语焉不详。顾起元虽然讲过利玛窦带入南京的圣母像、自鸣钟、三棱镜(“摩尼宝石”),(50)不过此书是利玛窦1601年到达北京后写成的,而且非常简略。这样,徐时进的《欧罗巴国记》是最早全面而清晰地介绍这些欧洲器物的中文著作。 徐时进说,利玛窦带来的钢琴“广尺六、七寸,长倍之,乃方函也。启函,见诸位置彩错,犹不辨为琴。其弦四十五,皆铜质,细如丝。鼓之,不按弦而按其旁之拍。声嘹呖雝喈,万籁相宣出丝间,市人至,皆谓之琴矣”。对于圣母像,徐时进这样描述说:“有像,描于玻璃板,宣色奇艳,如天际虹霓,国人绝贵。草工如写帝以端重,犹计寡韵不得趣。并写帝母,而抱帝于衿带间,气态如生,闪闪烁烁,可爱可畏。图尺许耳,云在国,直亦十金。”欧洲所制三棱镜,更令徐时进感到神奇,他写道:“又有一石,长数寸,似水晶,以横于目,仰视之,地面上物尽倒悬,而色鲜丽绝奇:凭高俯旷,睹逾远,逾奇。” 此外,根据徐时进的记叙,利玛窦带到南京的自鸣钟实际上有大、小两座,他所亲见的小自鸣钟,“钟悬以亭,亭制稍匾,高八寸,广六寸,钟有鸣刻者,有鸣时者。”利玛窦属于耶稣会,耶稣会通过多种经济活动,为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费。(51)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清楚利玛窦的资金来源,误以为利玛窦掌握了某种神秘的炼金术。对利玛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瞿如夔,(52)最初就是因为想学习“这项超人的技术”而找到利玛窦的。(53)利玛窦于1599年来到南京后,人们同样有此疑问。徐时进为此还专门问过利玛窦,利玛窦回答说,他的资金是通过葡萄牙人(“佛郎机”)从广东寄来的。徐时进在《欧罗巴国记》中讲述道:“去国既久,橐应垂,又恭谨无旁,人疑有黄白术取充,而瞰室中无炉鼎。余问之,云其国人多游佛郎机,佛郎机时有往来粤东者,从彼却寄。”这样的记载,在其他著述中尚没出现过。 2.关于欧洲社会的叙述 中国与欧洲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在汉晋时期,中国人就已获悉欧洲。《后汉书·西域传》等文献所说的“大秦”,显然是指罗马帝国本土。(54)隋唐史书中的“拂菻”指的是东罗马帝国、(55)元代文献中的“拂郎”指的是欧洲,(56)这也是学术界的共识。不过,自汉晋到明末欧洲传教士来华之前,除了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介绍过“斯加里野国”(西西里岛)外,(57)在中文文献中尚未找到专门叙述欧洲的文章。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自称“大西洋人”,1601年还以此名向明朝政府提出申请在北京居住。(58)此外,从1584年开始,利玛窦通过绘制中文世界地图,不断向中国人介绍整个世界。他将欧洲译成为“欧逻巴”,并且在地图上写下了近150个字的注文。(59)除此之外,没有发现过利玛窦关于欧洲的中文著述。此后,虽然欧洲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但也没有留下介绍欧洲的中文著作。直到另一个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来到中国后,才撰写了一些专门介绍欧洲的作品,特别是1623年刊行的《职方外纪》,被誉为是“继利玛窦世界地图之后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人文地理的著述”(60)。徐时进的《欧罗巴国记》作于1600年5月,比《职方外纪》早了20多年。刘承范的《利玛窦传》虽然早于徐时进的《欧罗巴国记》,但文中并无关于欧洲的内容。因此,徐时进的《欧罗巴国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篇介绍欧洲的文章,当然,其资料来源是利玛窦的口述。 徐时进采用了利玛窦的译法,把欧洲写作“欧逻巴”,此外还有“欧罗巴”及“殴罗”的异写。不过,徐时进错误地把“欧罗巴”说成是“大西洋所属三十国之一”。当然,明末将“欧罗巴”当作一个国家的并非徐时进一人。与他同时代的顾起元也认为利玛窦是“欧逻巴国人”(61),沈德符则说:“利玛窦自云:其国名欧逻巴。”(62)其实,利玛窦在他的《坤舆万国全图》上清楚地告诉人们,“欧逻巴州有三十余国”。 徐时进在《欧罗巴国记》中,多方面介绍了欧洲。该文一开头,先点明这个“欧罗巴国”的位置:“国在中国西陬,取陆为近,而其国人利马窦取海,从岭粤入中国,途八万里而遥。”文中记述了欧洲的自然环境及物产:“国之陵薮原隰,多产材,而筑室贵石,宇砖楣以垒层台,其最高处乃构木。地饶,梨栗有,桑繁,黍、麦、牟兼种秔,羊、豕、驼、犊、雁、鹜、诸用物,多与中土埒,独无漆、茶。酿以葡桃,桃绝大,聚数斛巨瓮中蹂之,经月成酒,无需曲蘖,味甚浓,酌时和以汤。”文章指出,欧洲在宗教信仰上的特点是“俗无儒、佛教,所崇祀为上帝”。古代中国的官宦富人家庭流行多妻制,因此,欧洲社会的一夫一妻制,使徐时进备感新奇,他这样写道:“国人多不娶,赀数百金以上,度可以给子女三两室,乃娶。即富,而子多亦不尽受室。其俗好游,游不必返首丘。或以此,其诸国君公率有配止一,自富室而上至君公,无二室者。君公之女,必字与君公,其世相为姻者数国。一时君公女多而无可适,则以合中老。”此外,徐时进告诉我们,欧洲人借助于一种可以顺风、侧风航行(“所向兼正傍”)的帆船,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大航海活动,并且将地理新发现记载下来:“国人性好游,以其尝历志里,有质验;其以航浮溟渤来也千余日,航所受千余人,所经国二百许;某国贪剽取货,某国暴噬人,向导者皆前觇得习知,以利帆越度之;某国无虐,则舣航,备糇糗,或为更航,航凡数更抵此;航每七帆,纫以布,所向兼正傍;其通往于光天下,率以海,率有里志,并写所经见。” 中世纪西欧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教权与王权的分立,而且罗马教皇的教权要凌驾于封建君主的王权之上,国王要得到教皇的承认,教皇甚至可以废黜或更换国王。教皇本人则又是选举产生的。这样的权力制度,对于长期生活在君主专制体制之下的中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徐时进的笔下,教皇被描写成类似于中国“天子”的最高统治者,教皇选举制度被理解成类似于中国上古传说中的“禅让”制。他写道:大西洋“三十国有统受令者,如中国天子,名教王国,自有书,能讲解规俗、躬蹈无盭者,得为官。王或倦勤,或殂落,则于官之中举而代,盖世世禅也。王皆无嫡嗣,其始得为宣教之官者,皆不娶者也。”既然教皇是至高无上的“天子”,那么,他对世俗国家的干涉,在徐时进的心目中就成了最高统治者对下属封国首领的直接任免:“国有疵政无道,则王使人让之;不听,则选其宗贤者以更置;无可选,则立他宗。王业有令,则通国人与左右皆不附,如今有司被黜,不可居位,故不必以戈矛去暴。”这样,西欧中世纪教权与王权分立的社会结构,就变成了中国人理想的“仁政”了。由于徐时进的《欧罗巴国记》源自与利玛窦的交谈,因此,很可能首先是利玛窦把西欧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分立比喻成中国式的“天子”与封国之间的关系,以便中国人能够理解。而对西欧社会一无所知的徐时进,则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进一步发挥并强化了这种错误的理解。不过,利玛窦对徐时进所讲述的“国有疵政无道,则王使人让之”,实际上是昔日教皇权力鼎盛时期的情况。在利玛窦时代,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展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教皇已经不再拥有对世俗政权的绝对权力了。而且,当时无论是在利玛窦的故乡意大利,还是整个欧洲,都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根本不是像利玛窦所说的“不必以戈矛去暴”。利玛窦这种美化西欧社会的“选择性”介绍,根本目的是为了使中国能够皈依天主教。如果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欧罗巴”也是动乱不已的话,那么,中国人怎么会接受天主教呢? 在《欧罗巴国记》中,有些内容是《职方外纪》所没有的。例如关于医生的职业制度:“犹贵医,有青囊线缝之术,业此者,试于官,授札子乃得为闾族所延,所全活左验如干人,乃得受饩,隶无且籍。”关于用鹅毛管书写字母文字的方法:“作字以鹅羽管,类吾稚孩所画,千亿相类,而渠读之,各有辨。”关于家庭中的黑奴:“俗甚耻为人厮养,无鬻弟子者。又于黑人国市役之黑人,寓国所产,稍见驯,可任使。”这些叙述,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利玛窦所介绍的欧洲。 3.关于西方天文学理论的介绍 古代中国天文地理学的基本观念是“天圆地方”。利玛窦来华时,中国民间通俗日用类书上表示“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的图画,(63)就形象地反映了这样的观念。相反,从公元前6世纪后期开始,欧洲人就认为人类所居住的世界是个球体。(64)到了中世纪,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同心宇宙学说的基础上,通过结合基督教神学理论,形成了水晶球宇宙体系理念,认为地球静止地居于宇宙的中心,“从里至外,依次分布着层层镶嵌、晶莹剔透的同心多重天球”(65)。利玛窦来到中国后,一直致力于介绍这样的天文学理论。 在《欧罗巴国记》中,徐时进说,利玛窦把天体和地球都比喻成圆瓜:“天地形皆圜如瓜,无所谓四旁上下,地在天中,水介地中”;“天包乎地”,共有九层,每一层“体明而无色,通透如琉璃水晶”;地球和天球都可以分为360度,太阳每昼夜绕地球转一圈,按照中国十二时辰来计算,那么一个时辰间的距离正好差30度(“日轮一日一周,每辰行三十度,两处相违并差一辰”);由于地球南北两极受到阳光照射较少,所以气候非常寒冷(“地之受光各以近远为差,故南北之极皆大寒”)。这些在今天看来是最基本的常识,在明代中国学者看来,却是“中国千古以来未闻之说”(66)。 徐时进在《欧罗巴国记》中写道,根据利玛窦的说法,“地之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奇三十六丈”,地球上每一个经度(或纬度)的距离相当于中国的250里(“每路子二百五十里”)。这是一组很重要的数据。利玛窦于1595-1598年在南昌期间,曾认为地球厚度(直径)为22 908里,每个经度或纬度的长度相当于200里;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绘制世界地图时,已经改变了原先的说法,进而认为地球的厚度为28 600余里,每个经度或纬度的长度相当于250里。(67)徐时进《欧罗巴国记》的发现,证明了我们的这一结论。利玛窦在南京提出的关于地球大小的观点,直到他去世之前没有改变过。此外,在南昌期间,利玛窦估计他从欧洲到中国的路程约为6万里。李日华在赠给利玛窦的诗作中,据此写道:“西来六万里,东泛一孤槎。”(68)1599年来到南京后,利玛窦认为地球厚度比他原先在南昌时期所估计的要大,所以随之增大了关于自己从欧洲到中国的航行距离,认为有8万里。因此,徐时进在《欧罗巴国记》中说,利玛窦“途八万里而遥”,由海路入中国。 利玛窦告诉徐时进,人类所生活的世界其实是个圆形球体,“周遭皆人”。这就意味着,相对于中国而言,地球上许多居民实际上是斜行、横站甚至倒立于地球上的。明末清初的中国学者对此深感困惑,难以认同。徐时进也一样,在《欧罗巴国记》中,就有这样的文字:“余笑谓:地周遭皆人,假令吾当圜处,吾所垫得无忧侧乎?城郭宫室得无忧圯乎?”尽管徐时进记录下了利玛窦对此问题所作的解释,但还是坦承无法理解:“余雅于天文无了,不能准验其说。” 4.徐时进本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 明清之际,利玛窦等欧洲来华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文化知识,被统称为“西学”。“西学”输入后,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反应,“骤闻而骇之者甚众”。(69)除了徐光启、李之藻等少数知识精英接受了西学外,更多的人在根本不了解西方科学的背景下,从正统的儒家理论出发,武断地将其斥为“邪说”,并且认为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诬上诬民,罪可胜诛”(70)。那么,徐时进是如何看待利玛窦所介绍的“西学”的呢? 在《欧罗巴国记》中,徐时进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利玛窦所讲述的内容,“尽信之,似为喜经奇荒唐悠谬;不信,又似蝉不知雪,为远人嗤。而可信为近,人亦愿谨无譥者”。这句话可以说就是徐时进对利玛窦所传“西学”的态度:部分相信,部分不信,但总体上相信。这里,徐时进明确说,他相信利玛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由于自己知识不足,无法否定利玛窦的说法。第二是由于利玛窦“愿谨无警”的人格魅力,使他相信利玛窦不可能说谎骗人。我们知道,在徐时进同时代的中国学者中,徐光启和李之藻是因为真正了解利玛窦所传播的科学知识而信从利玛窦,杨廷筠是因为在精神上认同利玛窦所介绍的天主教而追随利玛窦。(71)徐时进则是另一种类型,他对西方科学并不了解,对天主教也没有多少兴趣。除了利玛窦人格的吸引力外,徐时进是由于深感自己知识之不足而相信利玛窦的。由于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以完全否定利玛窦所介绍的“西学”,所以他相信了利玛窦的一些说法,以免被人视为生命短暂的夏蝉。同样,由于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以完全证实利玛窦所介绍的“西学”,所以他认为应当有所保留,以免被别人看成是一个喜好“经奇荒唐悠谬”的浮夸之徒。因此,徐时进相信与不相信利玛窦的原因,都是由于担心自己知识之缺乏。这反映了徐时进虚心好学、谦虚严谨的求知精神。 利玛窦所介绍的“西学”,与中国正统的儒家学说有很大的差异。明朝末年,许多人就是以儒家学说为武器来抨击“西学”的。有人这样写道:“儒教崇于宇宙也”,“仲尼,日月也”;“吾中国圣贤道脉,志之《经》、《传》。凡一句一字,皆从心性流溢,岂犬羊所可妄议者?”(72)但徐时进在面对利玛窦所介绍的“西学”时,却深深感到儒家经典根本不能反映广博的宇宙。他在《欧罗巴国记》的最后写道,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志宇宙之寥邈,即《书》、《传》不能差数载焉”。在反对“西学”的人中,有人主张:“六合之内,有存而不议、议而不论者,恐其乱人观听也。”(73)而徐时进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六合之外,存而弗论。弗论,可也。论,亦大愉快矣!”只有热爱知识、追求真理的人,才能享受讨论“六合之外”的快乐。而这样的快乐,是那些反对“西学”的人难以体会到的。 在《欧罗巴国记》中,徐时进根据利玛窦的口述,以平和的笔调如实介绍了欧洲社会教权与王权的分立、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度。可是在另一些中国人看来,利玛窦将欧洲社会这种野蛮“夷风”介绍给中国人,其实有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张广湉义愤填膺地写道:欧洲社会教皇(“教化皇帝”)和世俗国王(“治世皇帝”)的分立,实质是“一天而二日,一国而二主”;他斥责说:“何物妖夷,敢以彼国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统治!”对于利玛窦所说的欧洲一夫一妻制,张广湉同样痛斥说:“何物妖夷,敢以彼国一色之夷风,乱我国至尊之大典!”(74)明末一些反对“西学”的人还提出过这样的荒谬逻辑:由于汉代张骞在通西域时没有提到过“大西洋”之类的国家,因此利玛窦所说的那个“大西洋”一定是不存在的,是利玛窦凭空捏造出来的。许大受就说:“汉张骞使西域,或传穷河源抵月宫,况是人间有不到者?”中国古籍“何无一字纪及彼国者”?(75)徐时进也提到了博望侯张骞,但他不是以此来否定利玛窦所介绍的“大西洋”,而是在叙述欧洲人正在开展的大航海时感叹道:“窃又怪博望之槎直抵星河,仅仅以机石归,无他志俟后。”也就是说,在徐时进看来,张骞出使西域虽然远行到了“星河”,甚至带回了织女所用的“支机石”,(76)但其历史意义其实是无法与欧洲人所进行的大航海相比的。可以说,徐时进是第一个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将张骞出使西域与欧洲大航海进行比较的中国人。 徐时进还是第一个试图对欧洲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的中国人。利玛窦告诉徐时进,欧洲位于中国的西面,有海、陆两条道路可以入中国,而且陆路要比海路更近(“国在中国西陬,取陆为近”)。徐时进提出两条理由,推断欧洲位于比西域大宛稍南的地方。第一条理由是,利玛窦说过欧洲盛产葡萄酒,而且还有桑树和秔稻。徐时进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大宛盛产葡萄酒,所以欧洲的地理位置应当与大宛相近;既然欧洲可以种植桑树、秔稻,那就说明其气候是比较温湿的,不会非常干燥,所以应当位于比大宛更南的地方(“《史记》大宛多葡桃,以为酿。利生自谓国在西北边虏,岂与西域之宛近与?而其土可桑可秔,则土风当不甚觱栗皲肤,或西而稍折以南也”)。第二条理由是从中国文献对于“三佛齐”的记载推导出来的。位于现在印度尼西亚的三佛齐国,早在宋元时代就已被中国人熟知了。明朝末年,中国人将扬帆远来的葡萄牙人称为“佛郎机”。徐时进认为,这个已经入踞澳门的“佛郎机”,其实就是中国文献所说的三佛齐。而且,徐时进还误认为,“欧罗巴”与“佛郎机”是两个独立的国家。这样,既然利玛窦说欧罗巴、佛郎机关系密切,那么,欧罗巴应当离现在的东南亚不远。他如此写道:“佛郎机,即《异域志》所谓三佛齐也。国在南海中,为诸番水道绾毂,地产犀玑香药,而利生亦谓殴逻产珠[王母]琭宝精,诸卷握物自来与佛齐诸国市,则其国自西而稍折为南良是。”徐时进根据农作物来推断气候环境,进而推断地理位置,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他所得出的欧洲位于大宛之“西而稍折以南也”的结论也是正确的。不过,他认为“佛郎机”就是三佛齐,这无疑是错误的。但这是由于文献资料的极度匮乏而造成的。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清代的两件事。明朝末年,被称为“佛郎机”的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告诉中国人说他们其实是“大西洋人”。但清朝官方所修的《明史》却把“佛郎机”与“大西洋”当做两个独立的国家,并且认为“大西洋”等国“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77)1842年农历七月,鸦片战争的烈火在中国沿海已经燃烧了两年、清军已被英国侵略军彻底打败之后,靖逆将军奕山等重臣兴冲冲地向道光皇帝报告:经过“细加采访”,终于弄清楚“西洋诸国总名为欧逻巴洲,并无天竺国名目”,“又闻天竺一名印度”。(78)对照一下这两个事例,就可以知道,徐时进在1600年就得出了欧洲位于大宛“西而稍折以南”的结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他的研究方法则更是可取。 以上就是徐时进《欧罗巴国记》的主要内容。虽然艾儒略的《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和张维枢的《大西利西泰子传》等利玛窦传记资料都没有提到过徐时进,(79)现代学者也没有注意到利玛窦曾有过这样一位朋友,(80)不过,利玛窦本人却是知道徐时进的这篇文章的。根据利玛窦手稿而译成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有这样一段话:“在浙江有一位进士,也是一位大官,写了一本精彩的著作,名为《西洋记》,虽然书中对我们的记述要比别的书详尽,但关于我们的事情只是他从神父这里听来的,或是在我们寓所中亲眼得见的,还有的是取材于《坤舆万国全图》,他认为他已将自己在这方面所有要说的东西都写进了书中。”对于《西洋记》一书,译者有这样的注文:“这一书名是德礼贤所译,但该书却无从考证。”(81)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这个浙江进士就是徐时进,所谓的“《西洋记》”其实就是《欧罗巴国记》。翻翻《欧罗巴国记》,可以知道,此书资料来源确实如《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所说的那样,是“从神父这里听来的,或是在我们寓所中亲眼得见的”。利玛窦说徐时进的“记述要比别的书详尽”,这一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罗巴国记》的重要地位。不过,根据新发现的《欧罗巴国记》,此处中译者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译成《坤舆万国全图》,显然不当。因为徐时进的《欧罗巴国记》作于1600年,而《坤舆万国全图》则是1602年完成的。此外,在不久前发现的《利玛窦传》中,刘承范记载说,1589年,在利玛窦建于韶州的房子中,“所藏皆六经正学,子史诸书,求其手自翻译者,独《大瀛全图》耳”(82)。这就意味着,利玛窦在广东期间翻译绘制的世界地图,其中文名称应为《大瀛全图》。但由于《大瀛全图》之名仅见于刘承范的《利玛窦传》,而刘承范的这篇文章又是在1914年所修的家谱中找到的,所以这一孤证难以使学者们确定《大瀛全图》之名是否可靠。由于徐时进在《欧罗巴国记》中明确写道:利玛窦“以所携《大瀛全图》译而视人”,这就证实了刘承范在《利玛窦传》中的记载。现在看来,利玛窦在广东期间所译绘的中文世界地图,其中文名应当是《大瀛全图》。 徐时进的《欧罗巴国记》,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述欧洲的中文文献。此文为深入研究利玛窦在南京时期的活动、深入研究全球化初期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反应,提供了新的资料。 ①张西平:《百年利玛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林金水、代国庆:《利玛窦研究三十年》,《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6期。 ②夏伯嘉:《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向红艳、李春园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菲利浦·米尼尼:《利玛窦——凤凰阁》,王苏娜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汪志文:《当利玛窦遭遇中国》,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之宫》,陈恒、梅义征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耶稣会传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③刘明强:《万历韶州同知刘承范及其〈利玛窦传〉》,《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黎玉琴、刘明强:《利玛窦史海钩沉一则》,《肇庆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④徐兆昺:《四明谈助》卷20,桂心仪等点校,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年,第676—677页。 ⑤全祖望:《甬上望族表》卷下,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下册,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62页。 ⑥戴澳:《明正议大夫资治尹大理寺卿九瀛徐公暨沈氏淑人合葬墓志铭》,载《杜曲集》卷11,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第7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999年,第395-399页。 ⑦徐时进:《鸠兹集》卷7,浙江图书馆藏抄本,第11页b。 ⑧梅鼎祚:《鹿裘石室集》文集卷8,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37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215页。 ⑨沈懋孝:《长水先生文钞》“贲园草”,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第16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999年,第10页。 ⑩陈邦瞻:《陈氏荷华山房诗稿》卷16,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第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999年,第608页。 (11)乾隆《岳州府志》卷19,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乾隆《湖南通志》卷61,载《四库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4-1997年,第217页。 (12)康熙《荆州府志》卷1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第23页a。 (13)《徐氏宗谱》卷5,天一阁博物馆藏,第50页。 (14)万历《惠州府志》卷4,续1页a。 (15)陈梅湖主纂、孙陈端度协纂:《岭东道·惠湖嘉道职官志》,太原:出版社不详,2012年,第54页。 (16)道光《广东通志》卷154,载《续修四库全书》第6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352页。康熙《惠州府志》卷8的知府名单中,有“浙江鄞县人,进士,三十六年任,升岭东副使”,在岭东道官员名单中,有“三十七年任,鄞县人,进士”,但都没有漏印了名字。根据其他资料,这两处漏印了的名字都应是“徐时进”。 (17)张萱:《大观察九瀛徐公入贺序》,载《月湖徐氏宗谱》卷3,天一阁博物馆藏,第648-651页。 (18)雍正《宁波府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卷20第766页、卷34第957页。 (19)《啜墨亭集》“明万历四十九年徐时进刻本”,显然有误,因为万历只有四十七年。参见中国古籍总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集部,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76页;徐时进的《啜墨亭集》“自序”作于“己未三月”,参见徐时进:《啜墨亭集》,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第4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999年,第419页。 (20)佚名:《禁毁书目》,载《续修四库全书》第9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498页。 (21)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37页。 (22)雍正《宁波府志》卷35,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963页。 (23)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戊编上,第1628页。 (24)徐时进:《啜墨亭集》“自序”,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第4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999年,第418页。 (25)徐时进:《欧罗巴国记》,载《鸠兹集》卷6,天津图书馆藏,第18页b-27页b。 (26)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5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耿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43-544页。 (27)利玛窦:《利玛窦全集》上册,罗渔译,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6、155页。 (28)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98页。 (29)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19、221页;夏伯嘉将此日子当作利玛窦抵达南京的日子,显然是错误的,参见夏伯嘉:《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向红艳、李春园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1页。 (30)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自印本,1969年,第1574页。 (31)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27-228页。 (32)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38页。 (33)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71、284页。 (34)《明神宗实录》卷28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5245页。 (35)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575页。 (36)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1页。 (37)中村久次郎:《利玛窦传》,周一良译,载周康燮主编:《利玛窦研究论集》,出版地不详:崇文书店,1971年,第14页。 (38)黎玉琴、刘明强:《利玛窦史海钩沉一则》,《肇庆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39)李日华:《紫桃轩杂著》卷1,载《四库禁毁书丛刊》子第10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999年,第14页。 (40)谢肇淛:《五杂组》,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41)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5页。 (42)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97、239页。 (43)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35-268页。 (44)疏仁华、周晓光:《利玛窦交游与士大夫赠诗》,《历史档案》2012年第1期。 (45)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1-28页。 (46)次仲,即传说中的书法家王次仲,有的说他“变篆籀之体为隶书”,有的说他“以隶草作楷法”。参见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1、1571、1597、3175页。徐时进此处泛指利玛窦研习中国书法。 (47)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32、238页。 (48)利玛窦:《利玛窦全集》下册,罗渔译,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59页。 (49)王庆余:《利玛窦携物考》,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78-116页;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889-890、907-908页。 (50)顾起元:《客座赘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3、194页。 (51)戚印平:《东亚近世耶稣会史论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第127-255页。 (52)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台湾清华大学,2005年,第33-62页。 (53)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61页。 (54)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4-126页。 (5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朱杰勤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81-187页。 (56)金国平:《“The Selden Map of China”中“化人”略析——兼考“佛郎机”与“佛郎机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12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年,第209-223页。 (57)赵汝适:《诸蕃志校释》,杨博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3-134页。 (58)张廷玉等:《明史》第326卷,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59页。 (59)利玛窦1602年所刊的《坤舆万国全图》及1603年所刊的《两仪玄览图》上都有这段文字。参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图版7、图版34。 (60)邹振环:《〈职方外纪〉:世界图像与海外猎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61)顾起元:《客座赘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3、193页。 (6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83-784页。 (63)《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一书汇集了大量的此类图画,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室所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 (64)J.B.Harley and D.Woodward,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Chicago an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136. (65)孙承晟:《明末传华的水晶球宇宙体系及其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66)郭子章:《蠙衣生黔草》卷11,载《四库存目丛书》集第15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4-1997年,第357页。 (67)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1~22页。 (68)李日华:《李太仆恬致堂集》卷5,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第6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999年,第178页。 (6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95页。 (70)徐治昌:《圣朝破邪集》,夏瑰琦整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5年,第285页。 (71)钟鸣旦:《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香港圣神研究中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1页。 (72)徐治昌:《圣朝破邪集》,夏瑰琦整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5年,第154、263页。 (73)徐治昌:《圣朝破邪集》,夏瑰琦整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5年,第303页。 (74)徐治昌:《圣朝破邪集》,夏瑰琦整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5年,第276-277页。 (75)徐治昌:《圣朝破邪集》,夏瑰琦整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5年,第194页。 (76)南北朝的宗檩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张骞寻河源,所得楮机石示东方朔,朔日:此石是织女支机石,何至于此?”参见宗檩:《荆楚岁时记》,姜彦稚辑校,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2页。 (77)张廷玉等:《明史》卷325,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30-8434页。 (78)刘志伟、陈玉环:《叶名琛档案》第1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8页。 (79)钟鸣旦、杜鼎克:《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第189-223页。 (80)林金水:《利玛窦交游人物表》,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117-143页。 (81)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66、369页。 (82)刘明强:《万历韶州同知刘承范及其〈利玛窦传〉》,《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黎玉琴、刘明强:《利玛窦史海钩沉一则》,《肇庆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