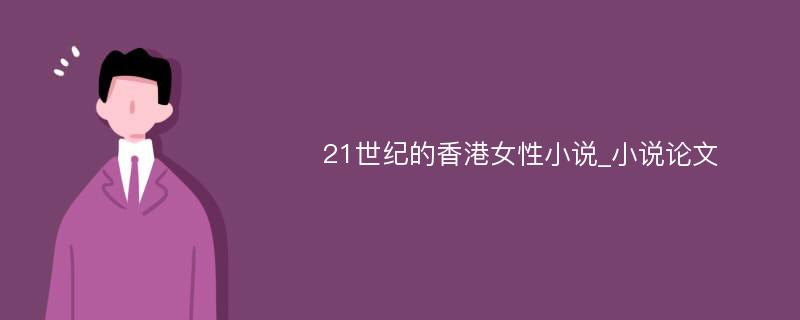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女性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走向论文,女性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九十年代,新世纪的曙光隐约可见,“九七”回归的钟声也即将敲响,对于香港女作者来说,“此时”与“此地”的写作便显得尤其的意味深长;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她们曾经摸索探寻,颠踬向前,不仅超越了“闺怨文学”的题材限制,而且也超越了“女性文学”所能包容的精神内涵,从而入到一种文化范围的理性思考。那么,面对世纪之交这么一个一切都被颠了一个个儿,一切又都刚刚开始,让人充满绝望又充满希望的年代,作为一种边缘话语,她们是如何言说的,能够言说些什么,或者如何与那不可说的相遇?
一、世纪之交的回眸
当一场灾难过后,我们会希望来一次彻底的精神检查和灵魂的荡涤,倘若不这样做,我们怎么能避免下一次的灾难呢?同样的,当一个纷纭繁复的世纪即将过去,许多人都会忍不住回眸,人类并不是只顾往前闯的动物,我们总会在某一些重要时候,以或温情或冷峻的目光检视着所走过的路,历史往往是在现实中起作用的;香港一些女作家在这一层面的领悟力与穿透力令我们惊讶,她们开始摒弃强烈的“个人化”倾向,拒绝了文化的固定角色所给予的单向和平面的形象,把笔触伸向了一个很有说头的城市的历史苍茫中。像施叔青,她中期的小说创作,还凭借着旅居香港的经验,创造出一系列的香港故事,为打造出一个世纪之交的香港作了充分的铺垫。但她并不满足于对现实形态的把握,她的“野心”颇大,追求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价值寻求,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中,对民族性格作全面的反思,所以,她开始以一种尽可能深刻的历史观对香港开埠以来的大裂变作忠实的记录,虽然还离不开女性的言说特征,但她尽量以性别为基础创造了一种共识与身份认同。面向一个更大的社群。《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作为“香港三部曲”的头两部,已在阅读市场上引起瞩目。
以一个风尘女子去见证香港一个世纪之前的历史,曾让人见仁见智。但施叔青终归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的,在她的笔下,历史也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因为,她很明白:有历史的通道,才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了。仅此一点,她便超越了单纯是“女性”的写作。
曾以《我城》、《浮城志异》、《肥土镇的故事》、《飞毯》等饮誉香港文坛的西西,把一座写于1977年的《美丽大厦》结集在1990年也是一件很带隐喻性的事情。《美丽大厦》的写作选择虽然还是“边缘化”的,西西在里面写出的故事都是一些未能进入“大历史”和“大空间”的悲欢,但这些,“小历史与小空间”却在边缘的缝隙之处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庶几也可以代表了香港人身处边缘却创造了另一种历史格局的独特经验?
二、立足现实的拷问
香港女性或许是中国女性中最独立的一群,香港有出女强人的较佳环境,她们的大展风华,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都有着一种前驱性的意义。但女性那种共同的命运,香港女性同样要承担,只要这还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
较为年轻的香港女作家,由自身的成长经验中对女性历经漫长的时光没有得到“质”的改变的命运一掬感同身受的同情之泪后,她们毫不犹豫地去探源,乃至开出药方。
以敏感直觉和浪漫情感在妙龄就踏上文坛的钟晓阳,在她近期作品中,却勇敢地安排了她的女主人公迈出新的一步。在《不是晴天》中,她就让胜慧在等待,象“等待戈多”的结局一样,可能永远等待不到理想的降临,但精神的“空白”总好过被粗鄙的“实在”填充,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传统小说中女性在社会、家庭、情爱等方面的殉道者形象,开始自觉地从心理、情感和性的角度探索女性自身的存在价值。
在一个世纪以前,英国的伍尔芙就以女人应该怎样生活、女人应该怎样认识社会为题写下了《一间自己的屋子》——经济独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赖任何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她设想得那么美妙,但现实却不是梦幻。今天的香港女性,甚至是所有女性依然受难于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悲哀之余,陈宝珍干脆把自己的一本小说集叫做《找房子》。
陈宝珍笔下的女性,大抵都是一群对被指派的身份有反叛意识的“角色”,但她还算一位清醒的女作家,她并没有完全舍弃作品中的性角色,但她会易地而处,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女性本身的生存状态,她明白其中的艰难,却又希望重建被打碎之后的男女关系,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会对男性作出种种指控,甚至有一种同归于尽的危险倾向,不错,我们的文化对女性是太不公平,但这并不是说,毁灭男性就可以达致一个完全公平、完全开放的世界。重建是男人和女人的共同事业,所以,陈宝珍在《找房子》集中以《我和她》压轴,以一个寓言式的故事表达了自己既对父权制的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的漠视和背叛,又对女性的占有欲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似乎是对建立新型的人性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的预测。
三、“乌托邦”式的期待
女性似乎与文学天生有缘,她们往往是用朴素的直感便能捕捉到社会最本质的变动。但可惜,她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却把她们的优越全都放到了爱情的“风花雪月”当中。这些擅于“谈情说爱”的通俗小说作家,总是有意无意地作一种超乎现实的憧憬与怀想,以此去建立一个“爱情的乌托邦”,不由得让人对当今的女性的命运抱有深深的忧虑。
李碧华很想超脱,但是,“在东方,即使是一位手执文学之灯的‘女妖’,面对女人的命运最终也只能陷入一片无奈的茫然。”李碧华于是从现代回归传统,她似乎不想看到当下世界的恩恩怨怨。她着力去塑造“传统女性”,不过,我们细细看了一下,发觉李碧华笔下穿着古代服饰的女人并没有多少这种“传统”的内涵,《胭脂扣》的如花是这样,《秦俑》的冬儿也是这样,在大环境里她们作不了主,但在“小气候”中她们是自己真正的主人。李碧华是不是如陈宝珍那样希望男人变得稍好一些,是世界变好的关键?
有谁说过,文学在理论上根本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不知道周蜜蜜对这一种推断会作怎么样的联系,但我们却知道她是想建造她理想中的“乌托邦”的,用爱心、用童心;用关怀,用热爱,在写过了那么多的童话小说之后,她还能推出那么一个香港儿童文学探索计划,让我们相信,她今后写下的文学,已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女性在社会现实中生存、思考的见证,更是一种提供了新的文化想象、造福下一代的激情表述。
四、对诗情诗意的回避
女性往往被视为是诗化的,但香港女作家中却不乏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诗意与诗化的代表人物。她们凭借着现代小说手法中的荒诞与反讽,展示混乱与肮脏的当下形态,把人们关于女人与爱情的传统建构一一消解。这毋宁是比寻找一间自己的房子更激烈的一种反叛与颠覆。
黄碧云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方便解剖的文本。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其后》中,充斥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图景:呕吐、残杀、虐待等等,在丑恶与荒诞中,她往往选择了死亡,这或许正正体现了东方女性的软弱,因为荒诞论的创始人加谬是拒绝死亡的,他曾说过,荒诞的人拒绝自杀。但黄碧云却禁受不住在绝望变态的梦魇世间还能寻找到诗意,在《其后》之后出版的《温柔与暴烈》里,她的这种决绝显得更加变本加厉。就如同用一把无情刀,剖开世纪之交颓败的人心,血淋淋的显示给人看。
“文学是经验的再现”,黄碧云如此去经营她的小说世界,当然有其原则性在。她是那么坚决地排斥传统女性的角色,那么奋力抗拒男性的一统天下,为此不惜动用多种的艺术手段。乃至遭人诟病也不改初衷。她的笔尖利割人,同样也刺伤了女性自身。就只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废墟中整合与重构?
另一位叫辛其氏的女作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过分私人化的话语方式似乎也已面临着新的陷井。新的局限:女性作家在发现边缘性声音的同时,也往往缺乏升华的对象,很容易便将作品引向作者自身。
辛其氏便尝试着走另一条道路,既然她不想如黄碧云般诅咒人世,她便转为在无奈中表达对女性自身的独特而深刻的自我分析,在她的新作《红格子酒铺》里,给读者以深切印象的并不是男女之爱,而是同性之间的关怀和体恤。说明了这年代的女人已不仅是只有溃败,她们还学会了承担和面对。辛其氏这样认为,好像是对男性的不信任,而转而求助于女性自身。“女人是女人的一面镜子。”男女之间浮泛的肉体关系比起心灵的沟通要容易得多,这种女性之间纯粹的情感却不易维持,这恐怕就是辛其氏在欲海横流中寻找诗意的苦心孤诣了,这会不会又是一个“乌托邦”?
上面列举了香港女性小说家走向二十一世纪所作出的种种姿态,仿若是一扇扇在她们自己的房间中“开向我们的窗户”,有时候令人不辨悲喜,她们动用了她们的生活贮存,她们的情感,她们所能掌握到的一切写作技巧,甚至不惜让生命的激流一次又一次地冲破文本,去建构她们的文字世界,成功与否,她们并不是不执着,但她们更明白,有时候成仁比成功更重要,而我们也正是在她们困惑、选择、追问的过程中,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正在展开,新的生命正在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