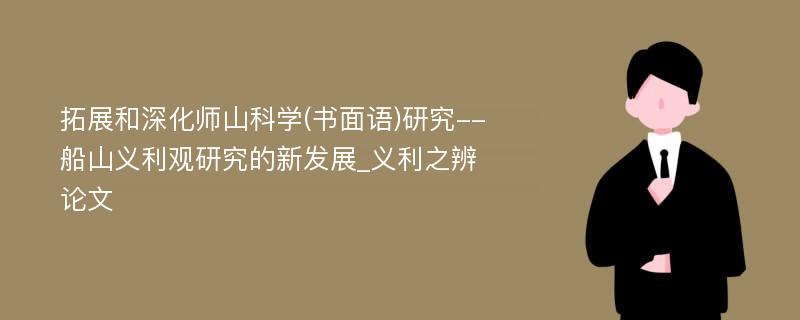
拓展与深化船山学研究(笔谈)——船山义利思想研究的新开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利论文,笔谈论文,思想论文,船山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05)01-0001-11
王船山是王阳明以后儒家伦理学说的集大成者,也是创造性地转换儒家伦理学说,使其实现由中古的权威主义伦理向近代的人本主义伦理过渡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对先秦至宋明时期各家各派的伦理思想作出了全面的批判性的清理与总结,使中国传统伦理哲学取得了完备的形态,而且建立了一个颇有近代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推进了中华伦理文化的发展和向近代的转型。船山的义利思想也是如此,他出入于中国历史上的各家各派的义利学说,对其理论成果予以高度的重视,又能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对其作“暴其恃而见其瑕”的工作,在继承的基础上作批判性的超越,创造性地提出并建构颇具辩证意义的义利统一论。
船山义利思想是与理欲思想密切相关并相辅相成的。伦理的近代化本质上是由圣入凡的过程。关心人的现实需要和正当利益,把道德致思从天上拉回人间,是伦理近代化的基本趋向。船山的义利思想适应了这种趋势,他尖锐地批判了程朱理学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倾向,明确指出天理寓于人欲之中,人欲之中有天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故不可离开人欲而言天理。这种理论比之17、18世纪西方伦理学家们对人的物质利益的辩护与论证丝毫也不逊色。尤为高明的是,船山提出了“理欲合性”的思想,不仅认识到天理与人欲二者之间的相互包含与贯通,而且认识到即便是功能各异的天理与人欲也是健康人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合两者互为体也。”船山的理欲合一论既肯定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见,人欲之中有天理,又未简单地将人欲直接地等同与天理。在他那里,“必寓于人欲以见”的天理所首肯的是“各得”而不是“同我者从之,异我者违之”的人欲,是“大公”而不是“逐物而往,恒不知反”的人欲。对于那种非“各得”和非“至正”的人欲,有必要从道义上予以约束和抑制。由于比较清楚地意识到理欲之间的辩证性,使得船山一方面批判了程朱理学及佛教的禁欲主义学说,另一方面又批判了杨朱学派及魏晋玄学的纵欲主义学说,创立了有别于前人的理欲合一论。船山的理欲合一论既是合理的又是深刻的,他把价值至于事实或存有之中,但又拒绝把所有的事实都归结为价值,既避免了混同事实与价值的“自然主义谬误”,又避免了割裂事实与价值之间关系的“价值无源论”的谬误,不仅透露出试图突破中世纪黑暗的近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而且也昭示出力图避免早期人文主义思想弊端的理性主义光辉。
船山的义利思想从理欲合性出发,肯定义利关系的不可分割性,既主张重义利之别,又主张重义利之合。在中国义利学说的发展史上,船山对义利概念的不同含义与层次作了十分精当的论述与分析,建构起了中国式的义利类型学。他在总结历史、审视现实的基础上,对义范畴作了深入的研究,将义界定为“立人之道”,认为义是人们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作为“立人之道”的义,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即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这三个层次因其适用的范围、时空的限制有轻重的差异、公私的区别,“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权衡之所自定也。”(《读通鉴论》卷十四,《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第535页、536页)在船山看来,义的三个层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是统一的,统一的前提必须是使一人之正义既能反映一时之大义,也能合乎古今之通义。统一是极为理想的状态,也是人们应当努力为之奋斗的。当着三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应当坚持“古今之通义”的价值取向,“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这就是说,无论是一人之正义,还是一时之大义,都必须服从于古今之通义。否则,“执其一义以求伸,其义虽伸,而非万事不易之公理,是非愈严,而义愈病。”王夫之以君臣关系和国家民族关系来对义的这三个层次加以说明,认为“事是君而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难,义之正也。”一时之大义则比一般的事君境界要高,它要求臣子所忠于的君主应该是天下所共奉的君主,“非天下共奉以宜为主者也,则一人之私也;”“君非天下之君,一时之人心不属焉,则义徙矣;此一人之义,不可废天下之公也。”即使所事者是天下所共奉之君,也还有比君臣之义更高的大义所在,这就是夷夏之辨,“而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因此,对于不能保中夏、卫社稷的昏暗之君,决不应当无条件地服从,而应当坚决反对,此所谓“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古今之通义也就是国家民族之大义,它高于并优于君臣之义。船山还把古今之通义与“生民之生死”联系起来,肯定“生民之生死”为“公”,而“一姓之兴亡”为“私”,强调循公废私,故显示出了走向近代的启蒙意义。
船山不仅对义作出了精当而颇富层次性的界说,而且对利也作出了全面系统的界说。从最一般的意义上,他把“利”解释为“生人之用”,认为利是指能够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财富与功利。人如果没有物质利益以满足自己生理的各种需要,他就不能生存下去;离开了物质利益,就要陷入危险或自我灭亡的境地。所以说,“出利入害,人用不生。”(《尚书引义》)卷二,《船山全书》第2册,岳麓书社,第277页)又说:“利者,民之依也。’在船山看来,自然界的一切有生命的事物,无不“各安其本然之性情以自利,”即无不具有趋利避害和自爱自保的功能。人也一样,“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为什么呢?道理很清楚,人也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一样,需要生存,要生存就必须按其“本然之性情以自利。”“各安其本然之性情以自利”虽然是合理的,但在伦理道德上却属于不善不恶的范畴,既说不上什么善,也说不上什么恶。接着,船山从道德上提出了两种利的概念,一种是“益物而和义”意义上的“利”,另一种则是“滞于形质,则攻取相役,而或成于惨害,于是而有不正者焉”意义上的“利”,前者为善,后者则为恶。“益物而和义”意义上的“利”,是一种与人民大众的福祉相一致且能够促进人民大众福祉实现的利,也是国家人民之公利。乾道之利即具有此种性质,船山指出:“乾之始万物者,各以其应得之正,动静生杀,咸恻隐初兴、达情通志之一几所函之条理,随物而益之,使物各安其本然之性情以自利;非待既始之余,求通求利,而惟恐不正,以有所择而后利。此其所以为大也。”(《周易内传》卷一,《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第69页)乾以纯阳至和至刚之德,彻群阴而合之,无往不遂,物皆于此而取益焉。乾利是一种利天下万物,使万物各得其益,人类各得其利的美利,它既是起点意义上的纯正原初之利,又是施与意义上的利天下群类之利,还是不言所利的无往不利。这种利的本质是“义之和”,即它祥和而无害,使天地万物达到一种最均衡适宜的和合。这种利既化生催育万物,又使万物循其自身的特质生长发育,含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品格。“滞于形质”而“攻取相役”意义上的利则是一种惟利是图的个人私利,这种个人私利是一种置天下大义和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的自私自利之利,其本质是损人利己和损公肥私。船山对这种利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和道义的谴责。
落实到义利关系上的对待与处理上,船山总体是辩证的统一论者,主张把“生人之用”的“利”与“立人之道”的“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表面来看,“义之与利,其途相反”,但从实质上来看,义之与利,“则故合也。”这种“合”在于“义者,正以利所行者也。事得其宜,则推之天下而可行,何不利之有哉?”(《四书训义》卷八,《船山全书》第7册,岳麓全书,第382页)船山的义利统一论本质是统一在重视人民群众的正当之利或“生民之生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利是“公”的应有内涵,也是判断义之为义的根本标准。不特如此,船山还从动机与效果等关系上提出了“义之必利”和“离义而不得有利”的命题,认为只有讲求“义”才能带来真正的“利”。背离了“义”就不会有真正的“利”,而只会导向“害”。所以他说:“出乎义而入乎害,而两者之外无有利也。《易》曰:利物和义。义足以用,则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离义而不得有利也。”不讲道义或者说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求取什么个人利益,就不可能得到什么利益,相反只能带来祸害。道义不仅内涵了人们的正当利益,而且还是人们正当利益实现的保证和必要条件,谋求个人利益只能在道义原则的指导下来进行才能真正有所得到和实现。否则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船山的“利物和义论”不是管子学派所谓的“利以生义论”,也不是董仲舒等人的“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而是使利的追求合乎义的要求,使义的讲求落到为人民群众兴利的层面上。这种义利合一论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义利学说的最高成果。
拓展船山义利学说,对于我们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当代社会的义范畴,也可以参照船山的理论,作出层次性的界说。一般地说,所谓义,是指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集体之间关系中的正当、合宜或善,它既包含正当、合宜的心理意识及其观念,也包含着正当、合宜的伦理行为及其实践。义者宜也,宜即是正当、合理、应该,它是一种人们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目标,也是一种人们遵循义的规范和目标所形成的道德品质和所达到的道德境界。义有三层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义,可以谓之曰“道义”。“道义”既是总的价值目标和最根本的道德原则,也是一切道德原则、规范和品质的综合化体现。作为一切道德原则、规范和品质的综合化体现,它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一般所讲的道德具有同等的意义,二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互相通用。作为总的价值目标和最根本的道德原则,它常常代表着至善和最高的道德精神境界,是人们应当努力趋赴的目标和方向。第二种意义上的义,可以谓之曰“仁义”。“仁义”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和重要的道德原则规范,也被认为是基于仁爱之心而产生的较高的富有道德价值的行为,是一种能给他人、集体和国家带来利益或福惠的善举。“仁义”有时也可以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第三种意义上的义,可以谓之曰“正义”。“正义”是一种比较具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也是一种人们应当具有的基本品德。“正义”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既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原则规范的行为,也指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分配的一种原则,即一视同仁和得所当得。一视同仁指按同一原则或标准对待处于相同情况的人和事,得所当得指所得的与所付出的相称或相适应,如贡献与报偿、功过与奖惩之间,相适应的就是正义,不相适应的就是不正义。正义与公正、正当等含义相近,基本上可以互相通用。这三种不同含义的义在境界上也有程度的不同,一般来说,“道义”最高,“仁义”次之,“正义”又次之。我们可以把“大公无私”的行为称之为“道义”,把“公而忘私”和“先公后私”的行为称之为“仁义”,把“公私兼顾”的行为称之为“正义”。“正义”是最基本意义上的“义”,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协调人际关系的最一般的行为准则。“仁义”是较高层次上的“义”,它往往要求人们在利益关系上先想到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并自觉地抑制自己的个人利益以成全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道义”是最高层次上的“义”,它要求人们在利益关系中不仅要先公后私,而且要大公无私,为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当代社会的利范畴,也可以作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区分。利作为祥和、有益的事物或现象兼具个人与社会、心理与行为、事实与价值等多种属性。利既可以作为中立于价值判断的事实存在,也可以被纳入价值判断之中而予以善恶评价。利有应当、正当和失当三种不同的类型及其含义。应当意义上的利是一种理想的和具有正面的道德意义上的利,它的本质是实现了利益的道德化发展,实现了利益关系的和谐,同时是一种与害无关或者说远离了祸害的纯正之利,是一种人们在道德上给予高度肯定性评价并愿意终生为之奋斗的利益。正当意义上的利是一种如同王夫之所说的源于本然之性情的自利,或者说正当的个人利益,它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须,也是建构理想社会和追求高尚人生的基础。失当意义上的利则是一种有悖于伦理道德的私己之利,是一种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并执着地侵犯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以发展自身利益的个人私利,是一种采取了不正当的方式方法所谋取到的个人利益。
船山的义利学说,总体上是既不主张割裂义利关系,又不主张混同义利关系,他主张把义利关系与公私范畴结合起来思考,认为义利之辨本质上有一个公私之辨,而公私之辨又同价值上的轻重、先后的取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价值原则和价值信条是“公者重,私者轻。”最大的“公”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因此这种“公”也是“义”的最高层次,是真正的“道义”。“道义”包含了“生民的生死”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包含了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但并不能由此一味地说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就是真正的“道义”。只有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融合并能促进其发展的个人利益才真正具有“道义”的性质与价值。社会主义的义利观需要而且应当继承船山义利学说的精华,既坚决维护和促进公民个人利益的实现,又主张将其纳入社会主义道义原则的指导与规约之下,在把国家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来谈公民个人利益的保护和实现,进而义利并重基础上的义利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