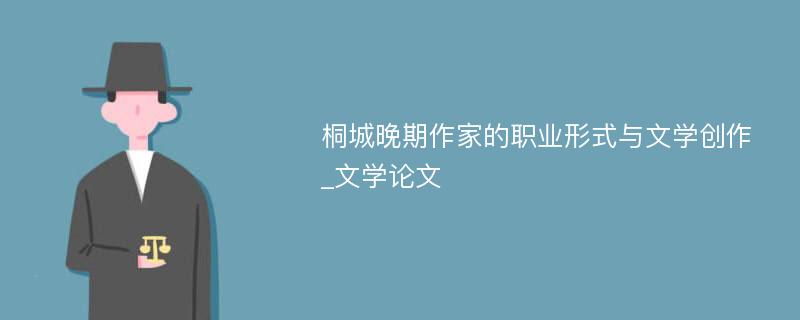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文学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桐城论文,晚期论文,形态论文,作家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05-04
晚期桐城派是指自曾国藩开创的桐城中兴后期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间的桐城派。从作家构成来看,主要为两代人:曾门四弟子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等幕僚群体;桐城嫡传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吴闿生及追随者林纾、严复等人。晚期桐城派作为从主流走向末路的传统文派,作家的生活形态新旧更迭,从职业归属上来说,具有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转换过程。这一职业形态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文学生产与文学理念,也彰显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作家的艰难选择与文学现代性变革的曲折。
一、千年变局带来多元的职业归属
关于桐城派作家的职业身份,有学者认为:早期桐城派大多是由一批既非显宦亦非隐士组成的纯粹文人集合而成的特殊的作家群体。[1](P5)实际上,桐城派鼻祖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均是有功名之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在中国传统士人的两种主要职业,即从政与教育之间交替进行,文学创作是行有余力时所作。中兴时期桐城派依托曾国藩幕府蔚为大观。晚期桐城派作家遭遇社会结构变革与民族危机,大多仕途多蹇,他们在新兴的社会职业中崭露头角,更有人以近代独立文人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晚期桐城派的第一代以曾门四弟子为代表,他们不仅均曾在幕府中任职,还在书院传道授业解惑。不同的是薛福成,他在曾国藩过世后,到福州书局谋职,操持笔耕生涯。这一代桐城派作家中,黎庶昌、薛福成还作为参赞、大使出使国外,吴汝纶晚年赴日本考察,在身份认同与世界视野上都超越了中期作家。晚期桐城派的第二代人,也是桐城派末代作家,既有弃官从商,创办实业的先驱张謇,也有到英国海军留学并创办报纸、传播西方文化的严复。桐城派嫡传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一直坚守古文传统,但也曾与严复、林纾同在京师大学堂这一新式高等教育机构任职。即使是桐城派殿军吴闿生也曾任教育部次长、国务院参议,作家的职业归属出现了新质。
中国传统文人安身立命的两个最重要职业是从政与教育,文学创作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副业”。王水照指出:文学作品与经济利益发生关联始于“润笔”习俗,但此非通过市场渠道的交换行为,其作品是产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商品。[2]多数贫寒之家的文人职业路线是穷困时在私家授徒,考取功名之后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退隐后主讲书院。出身富贵之门的则是少时读书怡情,云游四方,中年入仕、晚年退隐到教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政可以致君尧舜上,实现文道一统;委身书院可以教书育人、传播学术。二者都既是文人乐于安身立命的职业选择,也是士子的主要收入来源,早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归属大体如此。
19世纪中期,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士人的职业路线发生了重大转折。首先是职业的多元化,由传统文人的从政或教育发展为从政、幕僚、教育与其他职业,这与晚清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及总体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有关。其次是传统文人在新兴职业中崭露头角,尤其是驻外使节与现代学堂和自由撰稿人这三个环节值得重视。研究界已经达成共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思潮、传播西方思潮的主导者是传教士与留学生以及新文化运动主力干将。但从桐城派作家担任驻外使节来看,起先导作用的应是传统士人。再次,晚期桐城派士人的传统职业能力在下降,新兴职业能力在急剧提高。晚期桐城派的曾门四弟子中,只有吴汝伦功名至进士,严复只是赐文科进士。其余主要作家均未取得较好的功名,失去在传统社会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本。但是,他们务实学、古文功底深厚,无论做幕僚还是译书撰文都游刃有余。最后,对于桐城派末代作家来说,走商业化写作或者投身实业成了全新选择。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挑战,坚守桐城派写作理念可以获得少量传统士人的青睐,但生活物质来源匮乏;投身现代性创作,意味着放弃已有的文学、文化理想,多数作家都在这两者的调和中艰难摸索。鉴于晚期桐城派作家职业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我们暂且以幕僚、学堂、译书撰稿三个职业,择部分晚期桐城派两代作家进行研究,窥其职业状态及其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从职业归属的角度探讨桐城由中兴走向末路的原因。
二、幕府和传统学堂对桐城派的正向推进作用
曾门四弟子最主要的职业是幕僚与学堂主讲。吴汝伦与张裕钊先后任莲池书院山长,对桐城文风在北方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等人当都是“夷难定倾”之人才。更为有意思的是,桐城能文诸老,率以经术道义相高,而曾国藩在江南平定太平天国时,经常招携宾客,泛舟秦淮,饮酒赋诗,以相娱娭。[3](P97)作为幕僚不仅可以获取生活物质,进入仕进便捷之道,且与曾国藩这样的大家相互切磋还能增进学术与文学造诣,这是晚期桐城派作家乃至其他文士想要加入幕府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吴汝伦虽属专司文事者,也经常参与全局事务处理。唐文治曾专门比较曾国藩幕府和李鸿章幕府的不同,觉得佐曾公幕时日有进益,佐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已然。在曾幕中人争濯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在李幕则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4](P325)参与晚清重大的社会事件以及相对稳定的学术切磋氛围,对于晚期桐城派作家的文学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古文主题与意境的开拓。有研究者认为:晚期桐城派之所以衰亡,它不是强调以当下的“事”作为写作的根本原则,既难以使所写之“物”具有时代个性,又不能从具体的“事”当中开创出新的文体。他们反复讨论“义法”、“声音”,这一现象也说明他们的古文很难具有参与社会实践的功能。[5](P399)事实上,吴汝伦、薛福成等恰恰是因所涉实务于世有裨益,于曾国藩有启发才招入幕。纵观吴汝伦古文,除碑铭、墓表、谱序、寿序等传统主题外,还有大量介绍西学书籍的序、代曾国藩、李鸿章拟的各类奏折,远远超出之前的桐城文范畴。这些如何应对军事、文化、经济危机的古文是传统士人对近代中国走向的前瞻性思考,文章务实,对局势分析到位,同时具有宏观视野,是经世致用的好文。
如果说幕僚生涯推进了桐城派古文风气的革新,那么,主政莲池书院则是晚期桐城派实践文学理想与教育理念的最佳场所,也是传统文人建构现代文学心理积淀的一种努力。莲池书院兴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原希望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惮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吴汝纶的前任山长是张裕钊,日以高文典册磨砺多士,一时材俊之辈奋起朋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继不绝。张裕钊开创了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制度,先后有日本人宫岛助斋和冈千初来门下受业,使莲池书院成为我国此时唯一对外开放的书院,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吴汝纶在1889年接替山长一职后更甚。正是由于眼光远大,而且怀着与欧美“共竞”的志向,吴汝伦在莲池书院先后开办了西文班和东文班,引进外籍教员,选拔优秀学生参加学习,想培养出一批精通外语、熟悉各国政治,能够宏济时变的人才。吴汝纶在戊戌变法期间还主张“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章取士,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材,举而用之,庶不致鱼龙混杂。”[6]可以说,桐城派依托莲池书院不仅奠定了文学流派在北方的地位,乃至形成了分支“莲池派”,还为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文学生产机制的诞生提供了准备。
三、现代学堂与职业作家对桐城派的逆向作用
委身新式学堂与译书撰稿是桐城派末代作家的主要职业归属。晚期桐城派与中国新式学堂有解不开的渊源。吴微指出:文化的天然亲和性促使晚期桐城派青睐以学堂为依托传道授业,实现理想。在京师大学堂初期的15年中,桐城派晚期要员及其盟友云集于京师大学堂,并先后入据要津。[7]晚期桐城派介入的新式学堂不仅京师大学堂一家。1902年,安徽第一所近代大学安徽高等学堂创办,在姚永朴、姚永概(教务长)兄弟的引荐下,严复于1906年担任总务长一职。在此之前,1905年复旦公学成立,严复即被邀请为校董,并于1907年1月底担任复旦校长一职。不幸的是,1907年安徽高等学堂爆发学潮驱逐严复,复旦公学的职工与严复发生冲突,严复退出了两所新式学堂。严复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个案,尽管晚期桐城派与学堂具有文化亲和性,但他主政学堂的时间都不长,且大多数时间纠葛于人事、事务性工作安排,这对桐城文派不仅没有正面促进作用,反而会带来不良影响。
有研究者指出:严复与复旦公学和安徽高等学堂不欢而散,主要是因为任人唯亲和遥控校务。[8](P770)1912年,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从一般思想史的角度论述的话,严复这时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振兴学术、培养学生。当然,这些他也有所涉及,只不过工作岗位的薪水多少也是关心的内容之一。严复接手北京大学不久即遭到反对,况且也缺少运转费用。后来,严复从银行借款,使京师大学堂运转起来,但个中原因究竟是为私还是为公则很难分得清了。主掌新式学堂的桐城文人持有较为“功利”的隐形目的。这种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严复任人唯亲的重要源头,也是其未能长久执掌新式学堂的现实因素。严复在任期间,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乃至林纾均在学堂任教,可以说,其实是桐城派掌控了北京大学的话语权。随着严复的退出,主持校政的胡源等人引荐,章太炎及其弟子进入京师大学堂。民国初年,崇尚魏晋文章的清末的革命党人进入北京大学;1916年蔡元培掌北大后新文化运动的一班人入住北大。后两派人物共同反对桐城派古文家,导致桐城派失去了这一传播古文的重要领地。[9]桐城派失去了最为有利的舆论阵地。仔细梳理桐城派在近代新式学堂的命运,几乎均是共进退的情形,失去了学堂依托对于传统文派来讲就失去了天然的土壤。
桐城派作家在新式教育机构中铩羽而归的另一原因是文学观念与生活状态出现了分裂。新文化运动中,桐城派作为旧派文学的代表,被以“谬种”称之。有研究者撰文指出钱玄同所谓的桐城谬种并非虚指桐城流派。根据此间桐城派作家的性格、修养以及之前与文学革命派发生激烈冲突的实际情况,认定林纾即为桐城妖孽的专指,而桐城嫡传姚永概、姚永朴、马其昶则仍为新文化派和魏晋派所尊重。1935年,桐城弟子王孟复拜见桐城嫡传姚永朴,谈及桐城文与当年的争论。姚永朴仍坚持当年在北京大学任教习时撰写的文学研究教材《文学研究法》并认为:“桐城古文自身具有新变性,有文法可寻,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也是桐城语言。换句话说,桐城语本身就具有普遍的社会性。因此,姚永朴也不赞同林纾贬低白话文为下里巴人语言的说法,而是觉得桐城固白话文学之先驱矣。”嫡派桐城作家认为古文与白话文具有相通性,而号称维护桐城地位的林纾却不如此认为。或许,这才是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姚氏兄弟系桐城嫡传,穷且益坚,观点却更为开放;林纾自归于桐城,卖文为生,观点却更为保守。这种生活状态与文学观念的割裂预示着桐城的末路。
近代文人最为青睐的自由职业是撰文与翻译。这种职业对传统文人来说,既不失士子舞文弄墨匡扶天下的求道之路,又是新式传播媒体产生后较为便捷且自由的谋生方式。科举废除导致仕进途径丧失与现代传媒的兴起是现代文学生产机制形成的重要原因。实则在科举制大兴之时,自由撰稿人已初露端倪。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弟子薛福成在帮助曾国藩的长子料理完丧事后,便雇了两辆马车,载着自己珍爱的书籍和文稿,径向苏州驶去。途经故乡无锡过门不入,匆匆抵达苏州书局任职,操持笔耕生涯。薛福成一生没有取得功名,但进入了权力中心——幕府。在失去这一职业后,他选择的并非传统的授徒讲学,而是依靠撰文过活。确切地说,不是他选择了这一职业,而是历史已经提供了这一职业供他选择。
严复的译书事业中也有诸多现实因素。严复功名无成,委身北洋水师学堂难展鸿鹄之志,且有家庭所累。1898年,严复在给好友汪康年的信中探讨翻译《劝学篇》(即为后来的《群学肄言》)之事:“《劝学篇》不比寻常记论之书,颇为难译;大抵欲达所见,则其人于算学、格致、天文、地理、动植、官骸诸学,非常所从事者不可。今其书求得时故寄去;如一时难得译手,则鄙人愿终其业。《时务报》能月筹鹰洋五十元见寄者,则当按其寄呈,至少一千五百字也。商之。”[8](P507)严复不太情愿把稿子给汪康年当然有现实的考虑,一是担心其他人学力不逮,难以翻译得好。依严复的学识,他是应该有这样自信的。二是版权、收入问题。1899年,张元济邀请严复商讨译书事宜时,严复坦承:“复匏系一官,家无儋石,果费二三年精力,勉成一书之后,能以坐得数千金,于家事岂曰小补!则台端之意,复无不乐从者,固可决也。”[8](P532)严复、林纾等人已经是掌握了近代商业规律且怀有远大理想的传统作家。严复一方面用古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希望能够传递文化理想;一方面在译本选择等方面也考虑现实因素。客观来说,末代桐城派中的严复、林纾等非嫡传者较适应近代文学生产机制,甚至本身就是现代化文学生产机制的推进者。嫡传派虽然坚守古文理想,但是,在全新的生产机制面前不知如何应对,所以,其文学生产的影响反而不如非嫡传派。流派内部的这种分歧不是作家文学理念的不同,而是文学生产机制造就的。
四、职业的过渡昭示文学生产机制变革
王汙森曾在《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中提出:“在学术研究时,需注意生活史对个体思想观念转变的影响。”的确,生活史与创作史是有交集的。我们透过生活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晚期桐城派作家是浸润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潮激荡中的“双语知识分子”(安德森语),他们双脚踏在农业与工业社会过渡的土地上,而这种生活状况对他们的价值取向与文学实践都有巨大影响。阿尔都塞和福柯都认为:任何一个主体和意义都是由他们所不能控制的过程所“建构”的,文学也一样,它的意义并不完全是作家的情感想象和作品的语言意义,而是与整个社会环境、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文学的阅读和评论机制都有联系。所以,文学体制研究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过程研究”和文学的“生态研究”,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文学意义生产的“关系研究”[10]。晚期桐城派的作家恰恰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关系发生巨变的时代,他们的职业圈子由幕府到高等学堂到自由职业(林纾为代表)逐渐自由,人际圈子逐渐扩大,生活资料的获得越来越依靠社会机器和更多的受众,他们的身份也经历了由官(吴汝纶)到半官半自由知识分子(严复)和自由知识分子(林纾)的变迁。这是社会变革导致作家生存机制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文学生产的一个典型案例。
晚期桐城派是中国传统作家适应全新文学生产机制的缩影。两代作家中,吴汝伦一代在传统的教育与幕僚中如鱼得水,他们是站在传统职业遥望新文化、新文学且主动变革的一代;而姚永概一代坚守古文者则不为社会所显,他们是站在新式环境回首传统文学的一代;严复、林纾较为适应近代文学生产体制,期望既能承续古文,又能开启民智,但是却恰恰既不为嫡派桐城所亲,也非为新文学派所崇,更不能充分利用新式教育机构拓展文派影响。尽管“有所变而后能久”的桐城派做出种种努力,但最终失败了。这其中并非简单的新文化冲击的问题,也是整个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及传统文学的适应问题,是作家生活形态与文学生产相互牵制的问题。不管怎样,传统作家流派在近代经历了挣扎与变革,这是文学史的另一面,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另一个路径。换句话说,新式文学生产机制的产生,并非新文学作家的独领风骚,而是传统文学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