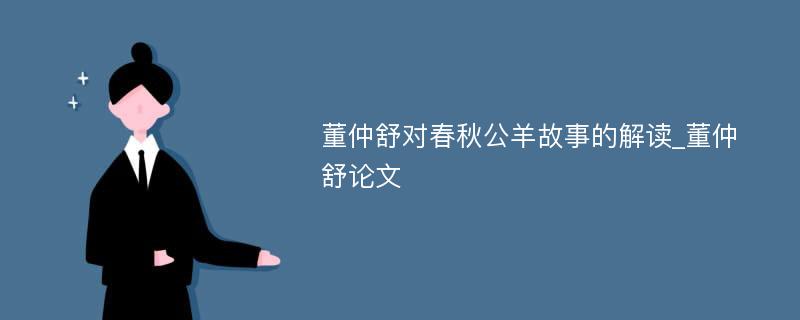
董仲舒解读《春秋公羊传》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公羊传论文,之法论文,春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董仲舒是汉初公羊学大师,其著作《春秋繁露》一书,一部分是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属于春秋学;另一部分是吸取了《春秋公羊传》之外的其它资源,如阴阳五行黄老道家之说,二者都是董仲舒“天的哲学”之组成部分。在属于春秋学的部分可以看到,董仲舒解读《春秋公羊传》有两重入路:一是对文本文面意思的融通;二是古代经学家解经之时往往以“求圣人之初心”为旨归,董仲舒亦不免于此。
一、解读文本表面含义之法
所谓解读文本表面含义,乃是基于《春秋公羊传》之特殊情况,《春秋公羊传》表述十分简单,且对类似事件的表述有貌似矛盾之处,因此融通表面含义是表明其微言大义之必要过程。对此,董仲舒使用了如下方法:
1.对比。
在此“对比”指的是对《春秋公羊传》不同处的表述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说明《公羊传》在处理同类事件之不同态度的理由,并达成统一之理解。董仲舒对此用设问自答之方式来说明,其所用的词是“况”。“况”是对比之意,(注:阮芝生先生论及“况”,主要取其“比喻”之意,就《春秋》而言,是借鲁国以喻天下,即所谓“因其国以容天下”。但此处董仲舒所说“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结合上下文,可知“况”是“对比”。亦因阮先生取比喻之意,所以他不能断定董仲舒是“所述先儒旧说”,还是“取先儒旧传之意而以当时之语作方便诠释”。(参见阮芝生《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台湾大学文学院,民国五十八年,第124页)此处应是董仲舒先儒旧说。)可分为以古况今、以此况彼。董仲舒融通《春秋公羊传》,属于以此况彼,(注:《精华第五》有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知董仲舒春秋学在于借古以况今,有为汉制法之心,但不碍此处“以此况彼”来理解文本。)即在经传所述之各种事端之间作比较,以达成统一之理解。现捃摭两例:
在《楚庄王》第一中,董仲舒自设问:“楚庄王杀陈夏徵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而直称楚子,何也?”仲舒答为:“庄王之行贤,而徵舒之罪重。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晋文不予致王而朝,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则诸侯之得,殆此矣。”
通过对比《春秋》在同类事件上对楚王称谓的不同,说明经文的态度,进而表明一个道理:齐桓、晋文、楚庄皆是贤君,以贤君之行尚有不得(不合于义),其他诸侯之得,便可以知之。所以董仲舒说“《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
又如:在《楚庄王》第一中,董仲舒进一步设问:“不予诸侯之专封,愎见于陈蔡之灭。不予诸侯之专讨,独不复见于庆封之杀,何也?”仲舒答为:“《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诸侯之义不得专封,是已明者。而庆封之罪在《春秋》中却未有所见,所以称楚子讨之,以著其罪。换言之,为著明庆封之罪,“不予诸侯之专讨”可略之,所谓“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与前例同样,乃是董仲舒用“况”,即通过对比之法得出。归纳、对比是一种经验的方法,冯友兰先生总结汉儒性格,认为汉人注意于实际,他们不能作,或不愿作抽象地思想,[1] (P788)也有人以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来概括之。以是观之,董仲舒整理融通《春秋公羊传》文本表面各处距离确有较强的经验色彩。
在一系列的对比当中,董仲舒利用其历史知识,于《公羊传》看似矛盾之说明中,寻出一贯主旨。但此时有一个解释的空间,即在解释之时一定要有所“得”、所“明”之意识,这是因比较而达到融通的关键环节,否则对比只能导致差别。此种所“得”、所“明”之意识,便显然不在语言文字之内了。
2.由因知果、因共明殊。
董仲舒于此方法所用的词是“端”,从“得一端而博达之”所使用之语境,及着眼于对《公羊传》文本的表层理解看,“端”有“原因”、“类别”二义。
作为“原因”者,董仲舒说:“然则《春秋》,义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楚庄王第一》)考其上文,是董仲舒将春秋十二公作三世之划分,并给出理由:“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董仲舒“情”的提出,一方面给出了夫子修《春秋》心理上的依据,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情”正是董仲舒所得之一端,得此一端,三世之划分便不难理解了。“端”指原因,另有多处,如“存在之端,不可不知也”(《灭国上第七》)等。可见在董仲舒那里,欲得对文本统一理解,察孔子“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之《春秋》行事的缘由,此是一法。
除此之外,董仲舒亦以“端”为“类别”。既明一事之义,凡事与此相类者,皆有此义。如董仲舒所言“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精华第五》)其举鲁僖公即位后亲任季子,由于季子之贤,鲁国当时无臣下之乱,亦无外患之忧。二十年后,因季子之卒,僖二十六年鲁便有了邻国之患,而不得不向楚国乞师救难。因此董仲舒得出结论说:“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任贤尚能,是一类,也是一端。有借古鉴今之意,同时也是理解《春秋公羊传》的方法之一。
3.不求通辞。
《竹林第三》中有问“《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董仲舒答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董仲舒将用辞的变化归结为“从其事”,即据具体行事而用同行事相应之辞。邲之战是庄王舍郑之美在先,晋人救郑,所救已解,却仍与楚战,是轻救民之意而重战。基于此事,遂变此前不与(认同、称赞)楚之文,与楚而不与晋,因为君子与夷狄之区别标准在于有无德行(是否文明)。在《春秋繁露》中还有其它表述,《春秋》之法,未逾年之君称“子”,晋里克杀奚齐,奚齐乃未逾年之君,却称“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僖十年),“君之子”之称不是通常所用之辞,为什么呢?董仲舒说“《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仁人”。(《精华第五》,“仁人”从凌本)晋作为鲁同姓,骊姬谋其子即位,导致三君死,乃是为得位之欲望所蒙蔽,而不知有如此灾难。《春秋》疾其所蔽,所以不用称“子”的正辞,只言“君之子”。
如此可见,《春秋》用辞是不固定的。考察《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春秋》常冒改变史实的危险改变某词,这些不固定的用辞算得了什么呢?《春秋》非历史书,孔子借以表达其理想,用辞亦因具体情况而定。《春秋》被一些经典视为“属辞比事”之书,(注:《礼记·经解》有“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之说。)康有为曾因董仲舒发得“无通辞”之例,从而否定属辞比事之说。[2] (P680)这种否定打击面太宽,属辞比事是正常论说文本所遵循之基本规则,否则只能是诗歌了。董仲舒“无通辞”之说,有其特定使用范围,某些事例以常辞不能解者,在其具体情境中,仍有其原因。或者说,如果把握了孔子理想的实质,其用辞若干具体变化都可得到理解。
4.推察史实,明其诡辞。
诡辞在《春秋繁露》中特指通过与史实不符的表达,表明其对某事的态度。如《玉英第四》中有难纪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无去国之义。’又曰:‘君子不避外难。’纪季犯此三者,何以为贤?贤臣故盗地以下敌,弃君以避难乎?”董仲舒对之解释是:“贤者不为是。是故讬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纪季弗为而纪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并举晋文得志,以“狩”讳避“致王”;莒子号谓之人,以避隐公;改庆父之名谓之仲孙;变“盛”谓“成”,来做说明。终而得出“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之法。
因此,传文贤纪季只是诡辞。照此看来,董仲舒所谓诡辞,与《公羊传》中改变事实之“变文”类似,是《春秋》编码同种方法之两种表达。
5.以意见志。
此时“意”的意思是体会,以意见志的意思是通过《春秋公羊传》的表述,体会到其背后的善志。如:《玉英第四》有仲舒自设难:“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传言:‘庄公冯杀之。’不可及于经,何也?”董仲舒认为此“不足以类鉤之”,《春秋》不书庄公冯杀,是避所善。因为宋宣公不将君位给其子而给其弟,而其弟亦不给其子庄公冯与左师勃而反给兄之子与夷,虽不合礼,皆有让高,而“让”乃是《春秋》之所善。如直书庄公冯杀,则宣公缪公为“让”之高义便为残酷的事实所掩盖。董仲舒又自设难说:“为贤者讳,皆言之,为宣缪讳,独弗言,何也?”既然《春秋》善“让”,何以不明言为宣、缪讳?董仲舒认为二君不成于贤,因其“为善不法”,即虽有让,但不合礼,所以董仲舒说:“弃之则弃善志也,取之则害王法,以意见之而之”。
“以意见之”,董仲舒认识到了“善志”与“王法”二者之对立,且皆为其所看重。从下文对“常”和“变”的讨论中,虽言“《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但更重视的是“变”,即“善志”。
如董仲舒在《竹林第三》中,通过楚司马子反与宋国私通一事,讲子反虽“内专政而外擅名”,然因其“为仁”、“推恩(推吾民之爱以及其邻)”,故《春秋》褒奖之,引出难者之问,以加深对经文之理解。在此,难者以古者君臣之义来诘问,就子反虽出于自己仁爱之心,为解二国之难而自作主张,“奈何其夺君名美何?此所惑也”。董仲舒如此设问,提出一个紧张之处,即内在人心与外在沿袭下之“规则”间的矛盾。
董仲舒解决此问题,先分后合。先将“常”与“变”分开,其言:“《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注:阮芝生先生将此处之常与变,与董仲舒论经礼、变礼以及经、权置于“无通义”之主题下,很有意思。(参见《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第135页))君臣之义是常,而子反之行是变。而合者,董仲舒提出两对范畴,质与文、仁与让(礼则)。“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在文与质之对待关系中,(《楚庄王第一》已有分辨,“质”处于逻辑在先的地位)董仲舒言“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支持“当仁不让”者,是董仲舒对心理习惯之说明:“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由此可知,礼是死的对象,而其基本之仁、情则不是对象,而是自然发动者。对于仁与让的地位,董仲舒认为“今让者《春秋》之所贵”,“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竹林第三》)董仲舒此论类似《论语》中所论仁与礼之关系。《论语·八佾》中,孔子因子夏回答“礼后乎”,而称赞说:“起予者商也!”所谓变者,不外是董仲舒对“志”之体认,是对先秦儒家一种呼唤式的承接。
6.由变知常,详而反一。
《玉英第四》有:“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董仲舒认为在不可以然之域者(即只能据经而不能行权者),是“大德”,而在可以然之域者(即可以行之以权者),是“小德”。所谓“权谲也,尚归之以奉钜经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也”。(注:“经权”是公羊学一个重要问题,可参见陈柱“经权说”,《公羊家哲学》,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四月;陈其泰“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经学今诠续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8-257页;李新霖《春秋公羊传要义》,文津出版社,民国七十八年,第188-229页;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2-245页。)
对于“一”,董仲舒举《春秋》公子目夷、祭仲、荀息、曼姑四臣之行为,以说明“事虽相反,所为同,俱为重宗庙、贵先帝之命耳”。可见,“详而反一”之“一”,乃是古来宗法制度之传统。这同前面“变用于变,常用于常”之说似乎有矛盾,因为表面看,变相当于权,常相当于经。然而其间实有细微之不同,前者之变有比常更根本之处,如仁,而后者之权则侧重于为达到经之要求,在操作之时因应时势。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所反的那个“一”,当我们从解释的角度,认为董仲舒的“一”是经过对传统规则改造过的“一”时,表面看来“常”相当于经,实则是转化为“变”相当于经。于是,传统规则变成拖泥带水的东西,一切都要经过重新判断了。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们所据以评判现实的理念都基于个体的判准,这在解释学的求真上,是个相当有趣的问题。
上说六种方法,可分为两类:前四种方法基本上是对《春秋公羊传》借事明义之义旨之融通。而后两种方法则基本在融通文义之外,揭示了内在理念与外在沿习规则之间的冲突,为下面讨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深层融通开启了一个窗口。即便是前一类,前面提到过,也有一个融通文义的关键处,即董仲舒一定是所“得”在先的,这也促使我们着眼于其内在“领受”的一面。
二、把握《春秋公羊传》深层含义之法
即便是以如上方法对文本做这样的初步解释,董仲舒也要有以把握《春秋公羊传》深层蕴涵为前提,不然对“已明者”、“未明者”、“得者”、“不得者”、“常者”、“变者”难有一个基本落实。康有为论及被其视为《春秋》之序言的《俞序第十七》时说:
《俞序》得《春秋》之本有数义焉。以仁为天心,孔子疾时世之不仁,故作《春秋》,明王道,重仁而爱人,思患而豫防,反覆于仁不仁之间。此《春秋》全书之旨也。[2] (P636)
此谓《春秋》之旨在仁,而以“仁”之不确定,正如牟宗三所理解之“明”,不能当对象来解。它既是主旨亦是前提,正因把握了那层底蕴,董仲舒才能做出另一路的融通。
1.志。
“志”相当于心理学中的“动机”,但侧重于道德层面。在儒家强调教化、强调心性的面向中,在先秦就有此传统。董仲舒从《春秋公羊传》中读出“贵志”,亦为此传统之顺承。其言“徐而味之”、“察视其外,可以知其内也”,不外是其心理层面对《春秋》所记事件之回应。
如《玉杯第二》有:“丧之法,不过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娶。娶时无丧,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谓之丧娶?”仲舒答为:“《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今娶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娶也。”此处董仲舒以“志”来概括《春秋》论事,而《公羊传》虽无提出“志”的概念,却有“非虚加”之“人心”。董仲舒又言:“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志,质不居文,文安施志?质文两备,然后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
在“礼”之形式下,含有两个范畴的结合:质(志)与文(物),显然董仲舒是更重视“质”。其对《春秋公羊传》之理解,是在《公羊传》本意基础上,以“志”与“文”两个概念连接礼内外两层意思。董仲舒言:“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疑为‘利’),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孔子是要救周之弊,(注:桓十一年,何休注有“王者起,所以必改质文者,为承衰乱,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亲亲而质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烦。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质而亲亲。及其衰敝,其失也亲亲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亲,故复反之于质也”。)而贵志也。
“志”在董仲舒春秋学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融通《春秋公羊传》时,董仲舒常指向这一层面,同时也有对达成这一层面理解之方法上的说明。董仲舒通过《春秋》中的一个例子申明此意:“《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盾弑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弑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玉杯第二》)
仲舒对此事做了发挥,提出了一个方法:“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察视其外,可以知其内也”。于是就赵盾之事,可知其“终始无弑之志”,所以“盾不宜诛”。然则问者仍有疑,问者曰:“夫谓之弑而有不诛,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故赦止之罪,以传明之,盾不诛,无传,何也?”董仲舒答:“世乱义废,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卢文弨云:‘疑当作大恶之不宜诛’。所言不错),谁言其诛。”问者还有疑,问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弑,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厚薄。《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弑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董仲舒之设问极尽《春秋》之委曲,意思是,何以它国之弑君贼不讨者,有重臣在者不加责,而赵盾不在却使其背弑君之恶名呢?董仲舒之答亦见《春秋》用心之深,其以“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见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回应,此所谓“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这也是前面提及的“《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董仲舒重“志”,并以“矫枉过正”而圆融经传之曲折,其解《春秋》用心深矣!
“志”之层面是董仲舒春秋学的重要面向,其谓:“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其志欲立,故书即位。书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书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隐不言立,桓不言王者,从其志以见其事也。从贤之志以达其义,从不肖之志以著其恶。”(《玉英第四》)《春秋公羊传》屡有“遂公意”之说,应亦为“从贤之志以达其义,从不肖之志以著其恶”也。在董仲舒春秋学中,“志”亦有用“指”来代替。
2.指。
《春秋繁露》中的“指”并不仅是“指称”的意思,“指”在其中有两种用法:一是有明确对象的“义”,(注:陈明恩先生只就此一面言“指”,认为是仅指“微言大义”的“细目”。(“董仲舒《春秋》公羊学解经方法析论”,《经学研究论丛》第八辑,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第239页))一是无明确对象者,指一种心理上的感悟。对于前者,如《十指第十二》中所论“举事变有见重焉,一指也。见事变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别嫌疑,异同类,一指也。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一指也。亲近来远,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此十指皆有一定对象,尽管对象有大小宽窄之别。而后者却无一明确对象可言,如《竹林第三》“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是把握了“指”,就可以抛开辞。犹如玄学之“得意忘言”,所得者是心理层面的东西。此意义上的“指”,亦为心理学上的“动机”,相当于作为道德意向的“志”。
徐复观先生也很注意“指”,其言:
(董仲舒)所说的指,是由文字所表达的意义,以指向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意义;由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大概不出于《公羊传》的范围。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指’,则突破了《公羊传》的范围,而为仲舒所独得,这便形成他的春秋学的特色。[3] (P208)
所说不错,但从徐复观先生论董仲舒整体来看,他所说的突破了《公羊传》的范围,所独得的,就是《公羊传》中不存在的。在我看来,如果品味董仲舒用“指”的环境(context),实乃是借助“指”对《公羊传》的明朗化。
《竹林第三》中有:“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仲舒言道:“会同之事,大者主小,战伐之事,后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例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辞已。”董仲舒此说是取《公羊传》庄二十八年经“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传有“《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故使卫主之也。曷为使卫主之?卫未有罪尔”。不唯如此,董仲舒还以《春秋》之义证之,其言“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见庄二十九年传讥凶年修厩),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此是董仲舒以“考意而观指”之法圆公羊义旨为一系统。故董仲舒认为,战伐乃“《春秋》之所甚疾”。
然而,仍有人对此发难:“《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结言而战,类似于下战书),耻伐丧而荣复仇。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董仲舒回对以“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偏战)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董仲舒自言其法为:“辞不能及,皆在于指”、“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然而,不任其辞,何以见其指?就董仲舒所取《春秋》之事为例来看,其所谓“不任其辞”乃是先有了“任其辞”之阶段。在此阶段,“徐而味之”,涵咏既久,知其经权之变,明了一经之中或有兼正反二义者,于是知不可任其辞,直追其指。从而在文本的部分与全体之对应中,获得统一义旨,此统一义旨是无通义(如任其辞则无通义)之通义也。《春秋》无义战,但不义之中有义,相对偷袭,结言而战就有义,为董仲舒及皮锡瑞等今文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宋襄公泓水之战所表现之仁义,可见其一斑。
还有在《精华第五》中有,仲舒假托难者曰:“《春秋》之法,大夫无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又曰:闻丧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无遂事矣,又曰专之可也。既曰进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谓也?”其答曰:“四者各有所处。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进而,董仲舒又从大夫自专处,明其“指”,其言:“无遂事者,谓平生安宁也。专之可也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率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谓不以亲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谓将得其私,知其指。”
“知其指”亦等于知其“志”。董仲舒始终以“志”为其解《春秋》之根本。“《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因于“志”,故董仲舒言“俱弑君,或诛或不诛。听讼折狱,可无审耶!”又“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子也”。教,是成其志,狱,须原其志。
“志”与“指”是指向并不具体的心理层面的东西,它是一个整体。它表现为一个人因某种文化的熏陶,在处理经验问题时的基本原则。董仲舒在此表达了一种不具体的东西,虽然冯友兰先生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描述为经验的思维性格,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反例。冯先生得此结论与其所取材料有一定的关系,在《新原道》中冯先生论董仲舒几乎没有涉及到春秋学的方面,大多是关于“天”的阴阳五行结构方面,着重阐发了董仲舒具有的“阴阳家的精神”。
“志”是不具体的,并不是可观察的物,因此只能作为自省的东西和教化的目标,或是作为哲学上的探求。但是如果在操作上以其为根据,便是放错了地方。《汉书·五行志上》中述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以其师思想治淮南狱,追索动机,造成诸多冤案。徐复观先生曾对此表达看法,说个人在动机隐微之地,反省自身是好的,但在政治上以此为判罪原则,则不可。[3] (P188)徐先生所言不错,理解董仲舒,必应明其志之义。
因“志”并不是具体对象,《春秋繁露》也有“无端”之说,当与“志”相近。在《二端第十五》中,其言“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无端”处又是何处?“贵微重始、慎终推效”是由无端处而得,董仲舒极力想挣脱对象性认知之所限。“无端”一词表明其认识之所在,是一种与“志”同一层面的觉解。
《春秋公羊传》实际上是孔子个人心理情怀的表达,其虽编排了一套技巧委曲地显现,但那个最深层的东西——因对现实政治之不满而形成的“志”——良好的动机,却是万变中之不变。“志”是心理的面向,在外界没有明确对象可指,但它不空泛的原因除了心理上的感动之外,还有孔子所选取的三代制度——在宗法制度依托下的资源。一旦考虑到这些,“志”便开始丰满而不再单薄,董仲舒在对《春秋公羊传》若干主题发挥之中,皆把握住了这种最基本的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