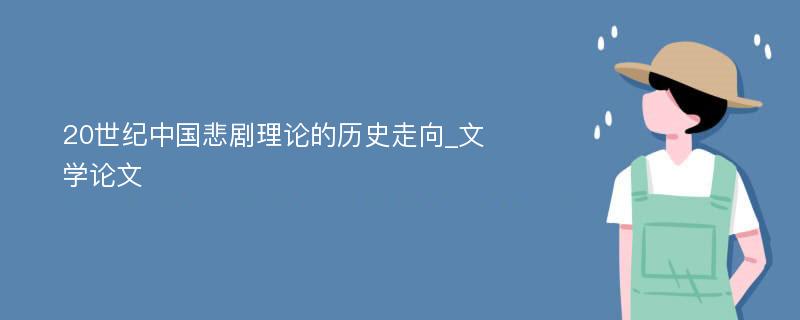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悲剧理论的历史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悲剧论文,走向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8)06-0095-04
20世纪中国现当代悲剧理论的生长深受西方悲剧理论的影响,它是在对异域文化的多次选择过程中走过来的。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继粉墨登场,现实主义悲剧在日渐成熟后逐渐打破了对峙的局面,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主潮地位。然而,现实主义悲剧观的发展过程却充满了曲折,经过伪现实主义,又回归传统现实主义,最终走向开放的现实主义。20世纪中国悲剧走过了一条由多元走向一元,又由一元走向多元的历史轨迹。
一、从现代主义走向现实主义
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在1920年代初步形成,1930年代有了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分别走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条路径,1940年代以后合二为一,选择了现实主义。
20世纪初,随着西方悲剧理论和作品的引介,许多学者追随西方悲剧,以此阐释中国悲剧,对大团圆进行了严厉地抨击,试图唤起人们对悲剧理论和创作的重视。由于学者们是以西方悲剧理论来衡量中国悲剧,更多地看到的是差异,普遍地得出中国没有悲剧的结论。中国的传统戏曲,被称为“旧戏”,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审判。王国维认为中国人“乐天”的精神和文化导致了戏曲的大团圆。胡适说中国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团圆意识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在朱光潜看来,写实主义与悲剧精神是不兼容的,他认为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鲁迅认为艺术上的团圆主义,乃是中国国民性弱点在艺术上的反映,其病根在于我们身上的传统思想因子作祟,人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或社会缺陷所产生的苦难,造就了“瞒和骗”的文学,所以,作家要直面惨淡的现实和人生。王国维、朱光潜与鲁迅虽然都是厚今薄古的,但是,从他们对理想的关注开始,既而转向对现实的直面,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悲剧理论的演绎过程。鲁迅的“几乎无事的悲剧”不仅是自身现实主义悲剧观的艺术演绎,而且开辟了中国现实主义悲剧创作的方向。[1]
如何建设新的中国悲剧,1920年代现代作家们的共同看法是:实现中国戏剧现代化,只有走“西化”的道路。胡适、傅斯年都曾详尽地提出过较系统的主张,呼吁中国人效法西洋人,将自己的戏剧观念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再造。据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集》统计,此时期出版的外国戏剧集有76种,计多幕剧、独幕剧115部,而其间现代主义戏剧竟占一半以上。中国现代大多数剧作家,尤其是那些有成就的戏剧家和评介者,都曾与现代主义戏剧产生过交往,如田汉、洪深、宋春舫、藤若渠、张鸣琦等。在许多人的眼里,现代主义戏剧是现代生活的产物,是人类戏剧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最现代、最先进的。人们发现了现代主义戏剧奇特的审美风采,发现了他们对人类自身,尤其是人的深层内心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表现。熊佛西认为“意志冲突”所引发的“内心的动作”,才能产生“深入人心”的戏剧性。[2] 冰心明确揭示了悲剧的动力源泉,“悲剧必是描写心灵的冲突,必有悲剧的发动力,这个发动力,是悲剧‘主人翁’心理冲突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即是主人翁“自己的意志”[3],中国缺少悲剧,就在于主人翁没有自由意志。这种由外向内、由社会向个人的转变,是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反拨,明显地反映出西方现代主义悲剧美学的影响。但是,这些崇尚现代主义悲剧的作家们,往往又抱着“为人生”的主张,热心“社会问题剧”,积极推动社会变革,同时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因此,早期的中国现代悲剧呈现为多元并立、相互渗透的态势。
1930年代,随着唯物史观的美学思想大规模地兴起,现实主义悲剧观的主潮地位逐渐形成。宗白华所说的“超越生命的价值”[4],与向培良、李安宅的悲剧观都强调的是比生命更为可贵的人生的理想境界,即人性真善美的统一,明显地带有布伦退尔和席勒的痕迹。但是,这一时期的悲剧观大多属于现实主义,着眼于悲剧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强调悲剧的社会价值。欧阳予倩就认为,现代悲剧是由人的“意志和社会环境的斗争而构成”[5];马彦祥也认为悲剧所表现的都是人类在人生奋斗中失败了的事,是人和社会的冲突,和环境的冲突。周扬直接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评价悲剧,认为曹禺的成功“正是现实主义的成功”,明确地意识到悲剧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社会现实之中。在悲剧创作方面,老舍与曹禺更多受到的是西方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老舍将悲剧分为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两种类型,将悲剧实质确定为人生命运的矛盾与冲突,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及其苦难成为其悲剧的主人公和悲剧素材。曹禺从平淡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去探索表现灵魂的隐秘,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使曹禺作品的命运观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描写人性与封建伦理道德和腐朽的社会意识的冲突。然而,老舍与曹禺的现实主义悲剧中又有着鲜明的现代主义印痕,注重展示人物悲剧性内心冲突,我们不难透过老舍作品中平凡的生活悲剧现象察觉到他们的精神悲剧内核,也不难发现曹禺作品中奥尼尔“灵魂悲剧”的影响。但是,这种借鉴更多地体现在艺术手法上,其宗旨仍在挖掘现实悲剧的深刻社会根源。
1940年代,中国历史进入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严峻现实,使越来越多的作家去关注和思考创作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自觉地在文化战场上为正义鼓与呼。随着马克思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入传播,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向国统区的渗透,现实主义悲剧逐渐成为作家在创作上的一种普遍的美学追求。郭沫若自觉地运用马恩悲剧观,其历史悲剧紧扣民族抗战的时代脉搏,他这一时期所写的六部历史剧,无论发生在战国、元朝或者明末清初,都弹奏出抗日战争时期团结抗战的时代强音,立足于揭示形成种种悲剧性格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根源。郭沫若把悲剧精神看作是新生事物向旧社会的积极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精神力量,只有体现了这种精神的历史人物才能成为历史悲剧的主人公,郭沫若更多地是在悲剧作品中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悲剧观。新崛起的美学家蔡仪在理论上直接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悲剧观,蔡仪认为悲剧“是表现社会的必然和必然的冲突的美”,在悲剧中“正的社会的力的必然性,在当前尚小于负的社会的力的必然性,所以它不免于灭亡。但它的前途是必然的,人们对它的必然的前途的期望,随它的灭亡而受挫折,所以是可悲的。”[6] 悲剧体现的既不是偶然因素,也不是个人原因,而是必然的社会因素,它是两种相反的社会力量的冲突。郭沫若与蔡仪的悲剧观,反映出唯物史观已成为中国悲剧观念的主要内核,现实主义已普遍地、自觉地体现在创作与理论中,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现代悲剧的主潮。[7] 但是,单纯地在社会的、客观的方面寻找悲剧的成因,并且限制在狭小的社会力量冲突中,为当代悲剧的沉默埋下了伏笔。
二、从伪现实主义走向开放的现实主义
在20世纪的后50年里,悲剧被误解、被冷落,甚至有过长达十多年的消失期,但是,在与文革历史悲剧告别的同时,现实主义悲剧又回归了。似乎是历史的有意安排,在20世纪末,悲剧艺术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与世纪初的繁盛交相辉映。
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成为一个标志,预示着中国文学新阶段将以解放区革命文艺传统为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确立的现实主义,至此定位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模式。由于年轻的中国相继终止了与西方和前苏联文化的交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取代了传统现实主义,很快却又被“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提法取而代之。当悲剧主张以空想的浪漫精神反对“单纯的现实主义”,由狂热的幻想代替了现实的冷静思考,意味着当代悲剧逐渐远离了传统现实主义悲剧,也远离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悲剧的精神,伪现实主义大行其道。
1950年代的文学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歌颂是文学的基调。即使表现战争的作品,“英雄人物不会轻易死去,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时候,也必须要用更大的胜利场面去冲淡它的悲剧气氛。英雄的死不能引起传统悲剧中的恐惧效果,而是以道德价值的认识来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其结果消解了战争文学的悲剧美学效果。”[8] 面对一片莺歌燕舞的文坛风气,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直谏道:“所谓‘重要题材’又一定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革命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与黑暗”[9]。由于缺少新悲剧,老舍含蓄而又大胆地表达了自己极度的焦灼和困惑,“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了悲剧现实,自然也就无从产生悲剧作品,不必多此一举去讨论了呢?我看也不是。”[10] 老舍的文章发表以后,引发了建国以后第一次关于悲剧问题的讨论。不过这次的讨论规模较小,发表的文章不多,没有形成不同意见间的理论争鸣,时间也比较短暂,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深入,悲剧的讨论中断了。胡风和老舍等人成为反现实主义的代表,现实主义仅仅成为名词被坚守着。
1959年,郭沫若结合历史剧谈悲剧,大胆地指出,悲剧的教育意义比喜剧的更强,充分地肯定了悲剧的作用。但是,他的观点主要针对历史剧,“只有在历史转换期,新旧力量交替的斗争中,才往往产生大悲剧”[11],这很容易导致社会主义没有悲剧的误区,因为社会主义时期,不再存在制度之间的更替问题。这一观点在1960年代初的悲剧问题的讨论中成为定论。马恩悲剧观被引向一条狭窄的小路,这样,顾虑重重的中国当代悲剧,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迅速凋零,1960年代中后期到1970年代末,进入了悲剧的冬季,现实主义悲剧作品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当悲剧在冬眠中再次苏醒时,已是1970年代末期了。“伤痕文学”以真情实感洗涤了伪现实主义的矫情与粉饰,找回了现实主义的真正灵魂,重新打开了尘封多年的悲剧之门,从而引发了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悲剧大讨论。悲剧文学的大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垮了理论禁锢的堤坝,不容置疑地回答了1960年代有无悲剧的困惑,作家与理论家直接切入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向彤以为,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二是人民内部也有矛盾和斗争,此外,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以及一切旧的传统和习惯势利的侵害和影响,都可能造成悲剧。因为向彤只是在社会因素方面寻找悲剧的成因,所以,他极力地说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与旧时代的悲剧有本质的不同:“旧时代的悲剧是当时的社会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残余势力和社会主义的敌人造成的。”[12] 因此,向彤的结论自然是悲剧应该在社会主义文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文学的作用主要靠正剧来实现。这种理解与1940年代蔡仪的悲剧观基本一致,显示出理论的倒退。但是,毕竟悲剧的严冬期已过去,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从外在原因走向内在原因的探讨,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一个新事物,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难免有不恰当之处,也可能造成生活中的悲剧;悲剧要关心人类的命运,认识人自身。这一时期的悲剧论争从1978年末开始,直至1980年代中期,所发表的文章达400余篇。但是讨论的角度还多是政治的,对悲剧的理解更多地是社会学的而非美学的;悲剧虽然开禁了,人们的顾虑尚未完全消解,阶级论的观点随处可见。然而令人欣喜的是,这次讨论重新确立了现实主义悲剧的地位,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成长提供了理论上有力地支持。
1980年代中期以后西风东渐,理论家的视线不约而同地对准了西方文艺思潮的译介,热衷于学习和搬用西方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悲剧理论的讨论再度中断了。但是,“伤痕文学”揭示了悲剧品格,使得各种长期在理论上纠缠不清的问题,从实践上有所突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这一时期的悲剧探索中,文学创作远远地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当理论界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社会主义悲剧的成因时,作家则径直地把思索的触角伸向历史和现实的纵深处;在暴风雨般的悲剧讨论逐渐成为淅沥的小雨时,悲剧文学并未停止探索的步伐。“伤痕文学”之后,相继出现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和新写实主义,从政治悲剧、文化悲剧、人性悲剧的探索一直到日常生活悲剧的反映,现实主义悲剧始终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强音。
随着对外开放和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加强,人们重新接纳和阐释西方各种悲剧理论,在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同时,力求理论与创作的多元化。钱钟书与陈瘦竹在中西悲剧理论的比较中,注重寻找两种文化的共同点,否定了世纪初由于强调差异性而得出的中国没有悲剧的结论。钱钟书用大量材料证明中国和西方都认为最动人的是表现哀伤或痛苦的诗,很多诗人和理论家在说明这一点时不仅看法相近,而且用语也常常巧合。“佩服弗洛伊德的文笔的瑞士博学者墨希格甚至写了一大本《悲剧观的文学史》,证明诗是隐蔽着的苦恼,可惜他没有听到中国古人的议论。”[13] 陈瘦竹以为悲剧的困境是世界文学共同面临的问题,他依据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的“普通人”为主角的悲剧理论否定了悲剧消亡论,认为这指的仅是传统意义的悲剧观念的消解。理论界对西方现当代悲剧理论的“兼收并蓄”,对中国80年代以后的悲剧创作影响很大,涌现出大量的现代主义悲剧文学作品,从“先锋文学”到荒诞派戏剧的大胆探索,都表现出与传统现实主义的不同,现代主义悲剧直面日常生活,解构伪理想,解构伪崇高。许多现实主义悲剧自觉地吸收了现代主义的营养,而使自己获得新的活力,传统现实主义走向了开放的现实主义。
世纪末的悲剧艺术与理论在短暂的绚烂之后,又沉寂了下来。悲剧日渐衰落,难道是在劫难逃的厄运吗?有人认为科学扼杀了悲剧,有人认为平民时代难造英雄,有人认为是经济大潮的冲击。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只会改变悲剧的特点,却不足以成为悲剧衰落的根本原因。中国现当代悲剧的百年历史清楚地昭示:走出封闭、单一的创作方法,张扬“艺术家的勇气”,悲剧的天空才会广阔。
收稿日期:2008-02-12;修回日期:2008-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