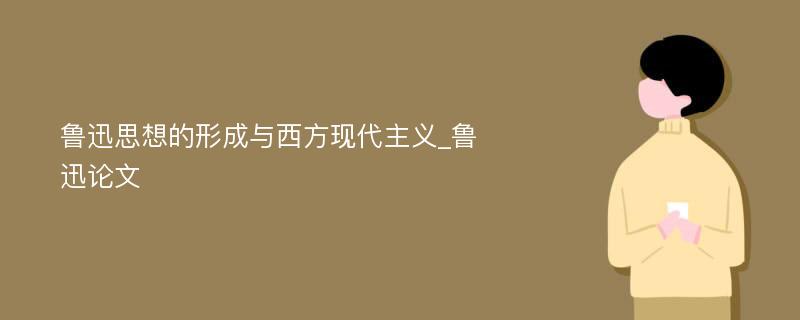
鲁迅思想的形成与西方现代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现代主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鲁迅独立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由于接受主体的知识结构、接受环境和接受目的等原因,使得以反理性为特征的西方现代主义,在鲁迅的思想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了以理性的核心的近代哲学精神。
一
鲁迅是在日本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具体地讲,是通过日本当时的哲学思想氛围,对以克尔凯廓尔、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产生了兴趣。作为西方现代派的一支,人本主义对人的个体、人的意志等问题的关注,引起了鲁迅思想的最初话题。在1907、1908年发表的5篇文章中,鲁迅称赞尼采等人的思想是对19世纪文明史的反省、批判,预言它将是新思想的征兆,新生活的前驱。“五十年来,人智弥进,渐乃反观前此,得其通弊,于是渤焉兴作,会为大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注:《文化偏至论》。)事实上,鲁迅是为了批判的武器而欣赏尼采等人的,他所看中的,并不是尼采等人的哲理,而是他们对当时社会提出的怀疑与否定。此时的鲁迅,通过尼采等人的学说,对十九世纪后叶人类精神的变化已有所察:“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趣,而主观内面之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以萌生,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注:《文化偏至论》。)很显然,鲁迅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关于物质阻碍了精神的观念,把物质的文明与精神的衰微联系了起来。
章太炎曾劝在日留学的鲁迅等人,不能将学问当作生活的手段,学者必须有立身的职业,如医生,思想才能独立。(注:周作人《苦口甘口》。)对鲁迅影响很大的章太炎的这种职业观,并未被鲁迅接受。鲁迅认同的是章太炎关于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政治危机、文化衰退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这种认同,连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使鲁迅并不热衷于科学、实业救国的思想,而是要在精神领域里,张扬个性、倡导启蒙。这种对于独立个性的张扬与追求,又与当时日本学界对尼采的介绍、理解有明显相似的地方。明治时代的“政治青年”,就曾把尼采的个人主义解释成为国家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认为“为了日本国家的独立,个人的独立是第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注: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应该说,留学日本的鲁迅,是在上述的前提下接受尼采等人的。西方现代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条件下,才对鲁迅的思想形成起作用的。
由此出发,鲁迅认为中国摆脱危机的希望“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诚若为今上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帮国亦兴起。”鲁迅这里的“个人”是近代的理性的人,而非它的借出者的非理性的人。
这可以从鲁迅对他所否定的“个人”的对立物的解析中得到证明。
鲁迅批评当时鼓吹工商救国者和立宪众治救国者,称他们为“伪士”,所谓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注:《破恶声论》。)认为“众治”很容易沦为“借众以陵寡”的借口,其结果比暴君更厉害。鲁迅认为欧洲革命时期出现的“众治”,是对往昔独裁政治的反动,但“众治”思想,把“众”的意义过于扩展,结果是压缩了社会成员的意义,形成一种:“偏至”。为此鲁迅倡导“神思宗之至新者”的新理想主义,通过引用叔本华、克尔凯廓尔、易卜生等人的思想,说明个人自由发展的意义。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描述了“神思宗至新者出”的历史背景。“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偏至的表现是“物质也,众数也。”强调物质的结果,是“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而众数则使“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于是在19世纪末叶,才出现了被鲁迅称为希望的“神思宗之至新者”,强调“入于我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的个性。
鲁迅把对个性的强调,与传统的“中国之治”联系起来,更表现出启蒙的色彩。“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樱”,“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这种“中国之治”,进而成为国民性的一个突出特征,要想改变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局面,必先改造社会的主体即人,而庸众是无法改变自己的。所以只得待英哲出,故而鲁迅呼唤“摩罗”之士,“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这时的鲁迅,在极力张扬的个性之中,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绪。鲁迅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东方式的改造,使之成为批判的武器,用充满自信的理性精神,鼓吹启蒙,并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对独特的、主观的个体的尊重与强调,是这一时期鲁迅思想的一个核心主题,有意思的是,它是建立在由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尼采的超人、克尔凯廓尔的孤独个体所构成的理论背景之上的。这些本是对传统理性哲学批判的现代主义,在鲁迅这里变成了确立其启蒙特色的理性主义精神,武器的批判变成了批判的武器。
二
由鲁迅文化偏至的观念表现出的近代理性原则和启蒙精神,所描述的就是把人类和自然界变为对抗着的主客体关系,而所谓历史的进步就是人类征服和掌握自然的过程。在社会历史领域,人类由宗教专制到君主专制再到民主社会,使人不断摆脱自然的束服,最终走向自由。然而事实的发展却与此相反,从个体人的角度看,在人们征服自然,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现实又无条件地牺牲了具体的人,导致人的异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把人变成机器,其主体性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消失殆尽,加之战争等因素,使人类的先觉者开始感觉、研究人的生存危机。所以从主体性出发,探讨人的生存状态,就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任务。鲁迅以其文化偏至的原则,推断出人的“主体”的重要性,是为当时中国的启蒙思潮服务的。所以鲁迅在对西方的“众治”、偏至的物质文明的批判和否定,包含着的是对“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等中国现实政治主张的批判和否定。把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异化思想,转化为对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洋务派、改良派和某些革命派人物的社会主张的批判。因为所有这些改革中国的思想,都忽视了人的重要作用,鲁迅认为只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鲁迅不想创建一个系统的哲学体系,经过以现实为目的的转化,他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概念,作了更切近中国的理解。在他早期的论文中,国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指清朝政府。所谓的“群”,也不是抽象的普遍的群体,而是由于封建专制的原因而丧失了对自我利益的正当要求的人民。鲁迅要求的自由,也不是抽象的人的自由,而是和特定时代的中国人民摆脱封建专制和外族欺压的现实行动密切相关的人的自由。他强调人的“自性”,是对“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常使民无知无欲”为内容的封建伦理体系的无情否定。
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现代派所强调的个人,大体是与群体相对立的。如斯蒂纳尔力证利己主义是人类的一切存在的起点与终点,尼采的“生命意志”和“超人”理论更是把群体作为对立面来看的,把“超人”之外的人群称为庸众。而鲁迅在理性主义作用下,把个体与群体统一了起来。他主张的“尊个性而张精神”乃是立人之道,目的在于“群之大觉”,在于“中国亦以立”。在鲁迅那里,个性自由与社会的解放是统一的,包含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鲁迅意在用个人的个性,唤起民众的“自无退让,自无调和”的战斗精神,并将之注入人道主义的内容,希望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伦理观念。这亦是鲁迅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创造性利用,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实用理性”意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鲁迅看来,中国要从精神萎顿状态下重新振作出来,需要一批具有“摩罗”性格的启蒙者。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赞扬的“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具有摩罗精神及强大个性力量的战士。与尼采式的精神战士是不同的,鲁迅认为两者都想图强,但爱憎却截然不同,“尼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是站在强者的立场上的;而拜伦等摩罗诗人,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的。鲁迅更爱那力抗强者的“摩罗”性格。
鲁迅个体的个性不同于尼采等人的个性,就是对个体本身的理解,也与西方现代派思潮的理解有所不同。
克尔凯廓尔等人在对个体的形而上的思考中,得到了恐怖、忧郁、绝望、死亡等一系列不安定的体验,认为孤独个体在创造自己的过程时,在不可重复的过程中,始终濒于绝望,面临死亡所以悲观,是他们的一种气质,这种悲观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人的异化的认识基础上的。而鲁迅在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个体视角的同时,把对个体的思考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他对个体生命的体验从来没有被化为一种抽象的心理现象,而是把非理性的人生感受,变成一种理性启蒙思想,通过个人的强力,达到中国社会解放。这种精神使鲁迅在接受尼采等人的同时,对浪漫主义也给予了很高的热情,并将浪漫主义的个性主义与现代派的个性,很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极力推崇“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抗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抗俗”者。赞扬“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的诗人,以此对比中国传统文化中“要在不撄人心”的“平和”之音。
个性主义思想在尼采等人那里,是通过对传统的否定进而现实对人类的否定,“超人”是“人类”的一种分离与对立。而鲁迅的个性主义主张通过个性的张扬来解放人类,只有个性觉醒了,才能用反叛的、不满的、探索的心灵去加速对旧的否定。《我之节烈观》是这种思的进一步具体化。鲁迅指出节烈是对人性的摧残,是于人生将来毫无意义的行为,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他要唤起人们“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同个性主义相联系,鲁迅把尼采等人称为“破坏者”。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鲁迅曾这样说到:无破坏即无建设,“卢梭、斯蒂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鲁迅提倡这种破坏精神,想用这种精神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这也和鲁迅对个性主义的理解是一致的。
鲁迅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接受了个体、个性等观念,并将之进行改造,使之成为非利己义的启蒙范畴,并始终赋予一种群体目的的意义。所以他无论怎样地痛恨中国人的国民性,但他的目的是鲜明的。鲁迅文化启蒙的目标显然要达到一种社会目的,而这与他日后思想的发展,形成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
三
鲁迅对现代派文学也较为关注。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其中收录了安特莱夫的两个短篇小说《漫》和《默》。1921年鲁迅又译出了两篇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收入《现代小说译丛》。安特莱夫的小说,从主观感觉和心理体验出发,对人的处境作出一种抽象的思辩。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恐惧、荒诞、绝望的内容恰当与尼采等人的哲学精神相一致。鲁迅是这样介绍安特莱夫的:作为“十九世纪俄人的心理的烦闷与生活的默淡”的反映,“却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世界表现之差,而现出灵与肉一致的境地”。(注:《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185页。)1925年在剧本《往星中》的作者介绍中又说,安特莱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注:《致许钦文》,《鲁迅全集》第11卷第457页。)安特莱夫这种悲观、绝望感,对人的存在的荒诞感,并不与鲁迅早期的那种启蒙者的自信相符,也就是说它无法进入鲁迅的为现实的需要而成的思想体系的主流。但透过对安特莱夫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关于个体生存的思索所达到的深度,这其实是鲁迅《野草》时期现代思想的萌芽。
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鲁迅,将之进行的理性改造和引伸,是他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在这之后,他对现代主义思潮又作了《野草》式的理解与接受,最后,他又接受了西方现代哲学中不同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他自己思想的构建。他这种对西方现代哲学、文化的借鉴、接受过程,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色。
标签:鲁迅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尼采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文化偏至论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