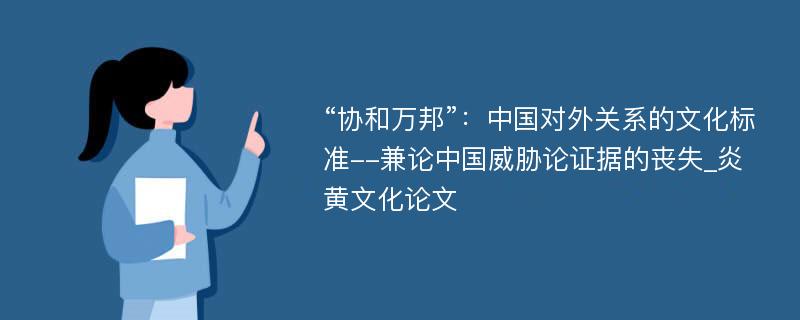
“协和万邦”:中国对外关系的文化准则——兼评中国威胁论的失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威胁论论文,中国对外论文,准则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在其文化性格中,和平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从古代社会直到今天,中国人民都把和平作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并在人们的心灵中孕育成熟了一种向往和平、追求和平、维护和平,甚至为了和平不惜作出巨大牺牲的精神境界。这是中华民族奉献给全世界人民的一分宝贵的精神遗产。中华民族至今仍然以此作为对外关系的准则,世界各民族也应该珍惜这份宝贵的礼物。
一
“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明俊德以柔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北京大学陈来教授认为,这段话中的“俊德”即美德,“钦”指敬,“明”指明察,“恭”指谨慎,“让”即不骄,这些都是“俊德”的具体德目。“明德”的社会功能是亲睦九族、协和万邦,求得世界的普遍和谐。(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291-292页)在这里,“明德”以求得世界的普遍和谐与和平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求得内部的和谐与和平,即“亲睦九族”;二是要求得外部各国的和谐与和平,即“协和万邦”。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对外是对内的延续。一个国家怎样处理内部的各集团、各民族的关系就已在本质上规定着他怎样对待国与国的关系,反之,怎样对待国与国的关系,也就表征着他会怎样对待内部的各集团、各民族的关系。“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处理国内外一切争端的总原则和基本的情感倾向。
坚持“协和万邦”的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合和万国”(《史记·五帝本纪》),或者用《周易》上的话来说:“保合大和”是为了“万国咸宁”、“天下和平”。而且,在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中,儒家认为,坚持“协和万邦”原则,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是建设好国家,强国、富国的重要条件。伊川先生说:“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矣。”(《程氏粹言·论政篇》)这也就是说,如果能维持一种良好的和平的国与国的关系,统治者就有了建设国家、发展经济、调整内部矛盾等各方面的大好时机和条件,只要能正确把握好这些有利因素,慎重地处理好各种问题,那所作所为都有了基础,就自然可以把事情办好。
那么,怎样来实现这种普遍的和谐与和平呢?具体在处理争端时应遵循一些什么原则和方法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有以下几点共识。
第一,“表正万邦”。这句话出自《尚书·仲虺之诰》,是仲虺用来称颂商汤的,“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蔡沈注曰:“表正者,表正于此而影直于彼也。天锡汤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万邦,……率循其典常,以奉顺乎天而已。”意思就是说:商汤自己严格地遵守“典常”,遵守各种公认的规章制度,起到表率作用,那么,各国都效仿他而自觉遵守公认的规章制度。放到我们今天所讲的国际关系中来说的话,那就是要各个国家自觉遵守公认的国际准则,起到表率作用。尤其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如果不能起到这种表率作用的话,那所有的国际准则都会成为一堆废纸。
第二,尊重小国。在国际关系中,如何处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是能否实现普遍和平的关键所在。为了真正实现普遍和平,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小国。老子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第六十一章》)在老子看来,大国应该谦居下位,才能取得小国的信用;小国也应谦居下位,才能取得大国的尊重。如果互相都能谦下的话,就可以实现国与国的平等,实现国际和平。小国本来就不能妄自尊大,夜郎自大,否则就是自欺欺人;但大国凭着实力妄为无度,也必然会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会与天下为敌,这样,其国家强盛也就自然不会长久了。因此,孟子说,交邻国之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认为大国尊重小国是仁爱的表现,小国尊重大国是明智的表现。大国如能乐施仁爱于小国,就能“保天下”,即就可以维护天下太平,维护世界和平;小国能明智地尊重大国,也就可以保持自身内部的政局稳定。无论大国、小国正确地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相反,不能正确处理好国与国的关系,就必然会招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一切灭国亡种的现象的出现,都是先有其内在根源的,是由其内在矛盾引起的。
第三,卫弱禁暴。要维护普遍的和平,仅靠国际间的一些准则是不够的,因为,世界上总难免有侵略成性的国家,难免有些具有兼并野心的政治人物。这些国家,这些政要,往往首先是向弱小国家开刀,强借自己国力、武力,占领、侵略别国。因此,要实现世界和平,就必须要“卫弱禁暴”,保护弱小国家的正当利益。这个任务,在没有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的情况下,当然只能靠大国来承担。在儒家看来,大国保小国是人道的表现,是仁德的要求。“大所以保小,仁也”,“伐小国不仁”(《左传·襄公七年》)。大国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必须要尊重小国,必要时保护小国不受侵犯。这样各国才会尊重他,他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才会越来越大。“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荀子·王制》)反之,以保护之名,行兼并之实,或以保护为名来谋取本国私利,那么,就会失道寡助,落得个众叛亲离,其在国际上的作用就会逐渐削弱,最后可能走向世界普遍和平的反面,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在当今世界上,只要有霸权主义思想存在着,只要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存在着,世界就不会太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未明确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但她的尊重小国、卫弱禁暴主张,是反对霸权主义行径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四,救助邻国。一个国家要受到他国的尊重,在他国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必须要主动地救助邻国,如果不救助邻国,那就是不仁不义,就不可能保持本国的国际地位,甚至可能危害本国的安全。《左传》载:“秦饥,派人乞籴于晋,晋不给。大夫庆郑说: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怜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左传·僖公十四年》)在儒家看来,救助邻国是所有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
“协和万邦”已经确立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文化准则,那么,怎样看待国家的军队建设和对外作战呢?这是一个与“协和万邦”原则有紧密联系的但又似乎矛盾的现象,正确理解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认清对外作战和建设军队的目的,以及用兵作战的原则。
与“协和万邦”相应,中国传统文化中“止戈为武”的理念,代表了中国人的国防观念和对于军事哲学的认识(刘国光:《东方和平主义:源起、流变及走向》,第13页,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止戈为武”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首先明确地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也就是说,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制止暴乱,消弥兵灾,使国家稳定和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多财富。所以,唐朝重臣房玄龄从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出发,也认为:“兵恶不戢,武贵止戈。”(《贞观政要·论征伐》)“止戈为武”的理念充分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用兵作战、建设军队并不必然是与和平、“协和万邦”相对立的。相反,这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用兵作战、建设军队不是目的,而是维护和平,使“协和万邦”原则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得已而用兵
“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这句话的大意在《贞观政要·论征伐》篇、《老子·三十一章》、《六韬·兵道》、《三略·下略》中都有表述,基本思想是“兵”是国家之“凶器”,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擅自用兵的,只有在不得不用兵时,在万不得已时才能动用军队作战来解决问题。因为一旦用兵,就必然会对社会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甚至可能动摇国家的根本。所以,唐太宗说:“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彫;邦境虽安,忘战则民殆。彫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帝苑·武篇》),用兵过度就会导致国家凋敝、人民贫困,这样,就会使国家的安全从根本上动摇。因此,决不可滥用,只有那种不明智的平庸君主,才会“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新书·太宗皇帝》),置国家大利于不顾,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并不否认军队和用兵作战对国家的重要性,而是对“兵”的作用有高度的重视。《孙子兵法·始计》一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程伊川也说:“为国者武备不可废,则农隙而讲肄焉,有时有制,保国守民之道也。”(《程氏粹言·论政篇》)养兵、用兵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国之安危在兵”,国家的强弱,与是否重视军队建设和用兵作战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荀子·议兵》)。可以说:强国无弱兵,国无兵不强。因此,任何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军队建设,重视用兵作战。
但是,重视“兵”,不等于可以滥用“兵”,而是要十分谨慎地用兵,必须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用兵。因为,一旦用兵作战,就会消耗大量的物质财富,就有可能导致国力空虚,“久暴师则国不足”(《孙子兵法·作战篇》)。程子曾根据当时的情况算了一笔账,他说:“今日师行,一兵行,一夫馈,只可供七日,其余日必乏食也。且计之,须三夫而助一兵,仍须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则一日乏食。以此较之,无善术。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后用者,知此耳。”(《程氏遗书》卷二下)据此看来,中国传统社会里,从统治者到贫民百姓,在骨子里都讨厌战争,“兵匈战危,圣人之所慎”(《贞观政要·论征伐》);从兵家到诸子各家都不主张滥用兵。老子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用兵作战过的地方,就像遭受过大的天灾一样,后患无穷。要想恢复兵灾前的景象极不容易。所以,孔子把战争当作非常神圣的事情来看待,不轻易论及之(《论语·迷而》)。老子也说:用兵必须要“恬淡为上”(《老子·三十章》),墨子则明确主张“非攻”,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
2、“兵以正为本”
按照儒家的看法,国家用兵作战,进行战争,必须要以正义为本。战争是用来为正义事业服务的,建设强大的军队是用来维护正义的。伊川先生说:“动众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则民不从而怨敌生,乱亡之道也。”(《程氏粹言·论政篇》)在儒家的观念中,战争不合正义原则,那就是自取灭亡之道,而为正义而战,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孟子也曾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这里的“道”就是道义,就是正义。
正义之师,决不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欺压弱小民族的人是绝无正义可言的,正义之师是用来维护民族独立、领土完整的,是用来伸张正义的。那些主动进攻他国的行为,都是侵略行为,都是不正义的,“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墨子·非攻上》)。这种“不义”表现在:无论对被侵害的国家还是对本国来说,都必然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破坏,杀人如麻,流血漂橹,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墨子说:“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此不可以春秋为者也。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而且国家兴师动众,必然就会“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墨子·非攻中》)因此,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兴师用兵,不但伤害他国,对本国也必然会导致官府不暇治,农夫不稼穑,妇人不纺织,“则是国家失本,而百姓易务也”。“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墨子·非攻下》)
所以,儒家主张战争必以正义为本,“取惟义兵为可”。如果坚持了正义的原则,“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反之,违背了正义的原则,“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孟秋纪·禁塞》)正义是行兵作战、建设军队之本,舍之不如无兵,坚决反对以武力征服他国。一切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行径都是与此不相容的。
3、“不以兵强天下”
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章》)这句话意味着:国家不能恃武力来威胁天下。儒家认为,国力强大或国家强盛,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物质财富富足,二是兵力强大,三是人民对国家、政府信任。这也是一切为政者必须倾注全部精力来料理的。但在这三者中,兵力强大是最轻的、次要的。《论语·颜渊》有一段孔子和子贡的问答,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思想: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从德治主义出发,从仁政主张出发,认为为政不以兵为贵,而要以民为重,以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为根本,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国家就不能巩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说:“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豀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公孙丑下》)儒家的另外一个伟大思想家荀子,虽然在人性论上与孟子相对立,但在战争问题上则与孟子具有相同的立场。他极其精细地分析说:
“用强(指武力)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恶我必甚矣。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则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吾民之恶我甚,则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所以守者损,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诸侯莫不怀交接怨而不忘其敌,伺强大之间,承强大之敝,此强大之殆时也。知强大者不务强也,虑以五命,全其力,凝其德。”(《荀子·王制》)
按照荀子的理解,恃强对他国作战者,必然会激起他国人民的反抗,同样,也会激起本国人民的反抗,在这两股强大的力量的合力打击下,无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强国都会被削弱。所以,他主张“知强大者不务强”,而要以其光明的品德把人民团结起来,取得人们的信任,取得他国的信任,这样,才能永远保持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因此,唐太宗总结历史教训说:“苻坚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而亡。隋主亦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贞观政要·论征伐》)浸润着传统文化的营养的中国人始终认为:无论是从经济上、军事上,还是从道义上来看,滥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国家都必然遭到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反对,越战中的美国是如此,入侵阿富汗的前苏联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也是如此;一切滥用战争、穷兵黩武的国家,都会因人民的反对而由强到弱,直至灭亡;战争和军队只能是“协和万邦”,用以争取和实现世界普遍和平的工具。
三
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对外关系的文化准则,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是一种崇尚和平的文化,中国人民在骨子里是爱好和平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炮制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完全没有文化依据,更没有事实依据的。中国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中国文化中,都没有称霸世界的动机。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对他国乃至世界构成威胁,就必须具有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这个国家以侵略、扩张为主题的帝国主义文化为基础。第二,培养出一个好战的市民社会。第三,在政治、经济政策上,积极扩军备战,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以武装军队和使全国军事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就是如此。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主题已如上所述,始终是坚持以和平为政策导向的文化。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创立了“和平共处”的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并一以贯之的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地向全世界宣布“不称霸”,以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基本指针,确保中国始终是世界上一支维护和平的力量。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明确地制订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调。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道:“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并没有被自己的胜利冲昏头脑,而是以极其健康的心态正确对待国际关系。一方面,要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另一方面,也把“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同上,第9页)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周恩来作为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对我国对外关系的和平政策作了极为精辟深刻的论述。1949年建国前夕,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50年9月30日,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中又重申了上述政策。制约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因素尽管十分复杂,以至于可以说任何研究者都很难梳理清楚。但是,对当代中国来说,尤其是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经济原因是制约对外关系的最强因素。邓小平同志就对这一点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水平……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16-41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邓小平的这一真知灼见是具有时空穿透力的,他强调“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8页,1993年版)前者是争取和平的需要,也是发展中国经济的需要,是我国领导人的非常坦诚的心意,“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但是,要争取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强权政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求得和平,霸权主义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最为严重的威胁,是战争的根源,不反对它,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因为只要有搞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的存在,它们就有可能发动世界大战,而且,它们也有这样的能力来发动世界大战。反对霸权主义表明了“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7页),后者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是中国的责任所在。“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中国自己不打别国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则,它“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7页)邓小平提出在处理港、澳、台问题上要采用“一国两制”方针,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同上)即“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内政问题。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和平共处地解决内政,也是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作贡献。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和平政策,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而且也要求国内各党派、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这样的和平才是普遍的和平,这才从根本上有利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江泽民作为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继承上两代领导人的基本主张,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提出了几项重要的具体措施或政策。“致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坚持睦邻友好”,“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等等。(《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读本》,第305-306页)很清楚,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政策一直是以和平外交作为基本政策的。它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的和平思想的土壤,导源于三代领导人的理性思考,见之于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实践。
当然,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从来都不是为了和平就不要独立性的,因为,真正的和平是以独立的国家来维护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来处理国际关系,同时也坚持独立自主政策,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形式干涉中国内政。周恩来曾明确指出:“我们愿意和一切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2页)他认为,中国处理与任何国家的关系,都“不要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一国的工具”(《周恩来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斐斐的谈话纪要》,1946年7月9日)并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总结历史经验说:“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新中国的外交》,1949年11月8日,第213页)坚决主张各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坚决反对侵略、颠覆、控制、干涉、欺侮弱小国家,中国不做超级大国,不去主宰别国,不干涉人家的内政,不输出自己的政策、社会制度,但也决不能容忍别国向中国输出、控制和干涉。邓小平继承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主张“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95页)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并认为不干涉内政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
不但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的精心培育、指导下,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等的影响下,中国社会还形成了相当良好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国公民都能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所要走的道路,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每个公民所应尽的职责,都极为明确地懂得和平对我们的重要性,和平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把国家有限的资金主要用在现代化建设上;为缓和一段时期内的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1986年,中国单方面在中苏边境裁军一百万,为中苏关系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和前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的良好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我驻南使馆,我国政府和人民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精神,努力把这样的严重事件所可能带来的国际危害降到了最低程度。所以,在中国没有威胁世界的文化基础,也没有威胁世界的社会基础,更没有威胁世界的现行政策和经济条件。
四
那么,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会在国际上叫得十分响亮呢?是什么原因使西方大国乐意炮制中国威胁论呢?简单地回顾一下西方对中国或东方的认识,是有利于对问题的理解的。
在中世纪的马可·波罗来中国前,对他们来讲,东方还是一块陌生的土地。由于马可·波罗的介绍,东方才逐步地对西方具有了巨大的诱惑力,并在一定的意义上,刺激了新航路的开辟。到十六世纪,随着欧洲部分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的前驱已经对海外进行掠夺,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其次是荷兰和英国,把掠夺的魔爪伸向了东方,主要目标就是印度和中国。这个时候他们清楚地看到在东方的巨大利益和巨大潜力。从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满剌加起,西方列强从未放弃过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野心,并且逐步升级、变本加厉,妄想把中国完全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西方列强的阴谋。于是,在不可能把中国完全变成殖民地的情况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谋划用武力来分裂中国的种种计划。中国的蒙古、新疆、西藏、东北、台湾等都是他们的罪恶计划中要分裂的主要地区。在西方列强的思想深处,不能完全变成殖民地的中国,他们就要分裂他,使他永远不能成为可以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弱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大国认识到中国已经永远摆脱了他们的奴役,于是,由过去的武力干涉、武装侵略改变为经济封锁、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对立和舆论上指责等遏制中国的种种措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快速的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加强,这就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的巨大潜力。同时也表明,中国人民只要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就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对世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某些国家对中国的这种发展势头,感到惶恐不安,担心自己的霸主地位、大国地位从此动摇,于是,不遗余力地鼓吹中国强大了就会对世界构成威胁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是想通过中国威胁论的宣传,遏制中国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不得不在一些子虚乌有的问题上分散精力,付出沉重代价,从而使中国不能很快地进入先进国家行列。
可见,宣扬中国威胁论,是与瓜分中国、侵略中国的殖民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它是殖民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和完全没有可能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遏制中国的重要措施。在世界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一方面,曾经备受帝国主义者殖民之苦的落后国家,仍未完全摆脱殖民主义者的控制,很多国家还处在对西方的依附状态之中;另一方面,曾经大肆凌辱过殖民地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其灵魂深处,并未完全放弃其殖民主义思想,还梦想着用其它方式来继续控制这些曾经隶属于他的国家和地区。在中国收回香港前,英国提出主权和治权分离,企图使英国继续保持对香港的实际控制权,就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宣扬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列强难以释怀的殖民主义思想在现代社会里借尸还魂的结果。在他们不能控制、奴役中国的情况下,也要使中国不能迅速发展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民族独立而对他们造成的巨大“损失”。不过,是以牺牲中国正当利益和中国的国际形象为前提的,因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有可能赶上或者超过他们的第三世界国家,只有中国。
具体落实到各个不同的国家,他们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具体目的又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基本的特征都是为了自己的民族私利,是民族利己主义作怪的结果。如:日本在南沙群岛问题上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日本前外相柿泽弘治在1992年《中史公论》12月号上撰文称:“南沙群岛海域是我国油轮通往中东的海上运输线,对我国来说,南沙群岛问题是决不能忽视的问题。中国如何解决南沙群岛的纠纷问题,这对于预测中国在海洋权益(主要是石油资源开发)上的态度及如何对待尖阁群岛问题是重要的。”这已非常清楚地表明,日本之所以要宣扬中国威胁论,目的是为了有利于自己的海上运输和在尖阁群岛问题上争取主动,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心迹表露无遗。
印度也是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国家之一,从五十年代起,印度人就在宣扬中国威胁论了。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入藏,就已经使印度人大为恐慌,在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看来,中国拥有西藏就已经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因为两国间有长达1700多公里的边界线,而且,这一边界线既没有正式划定过,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在尼赫鲁看来,如果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地区,那么,在其北部边界上他就有主动权。而西藏不能被独立出去,那么,印度北边面临的是一个比他还要强大的中国,当然,他在这一边界线上的主动权就化为了泡影,于是,印度人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尤其是1998年,印度在西部拉贾斯坦沙漠进行核试验,使自己成了有核国家。在事发的第二天,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立即向美国等八个工业化国家写信,诡称中巴合作威胁印度,企图用中国威胁论来减轻西方对他的制裁,以中国威胁论作为他谋取不法私利、践踏国际公共准则的借口。
纵使是标榜民主自由、以世界警察形象出现的美国在宣扬中国威胁论时,也是极其自私地从本民族利益出发来丑化中国、美化自身的。以布热津斯基所著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中的观点为例来说,虽然作者没有强烈的排斥中国的心理,但言辞间还是透出了美国本位的特征,还是表现出了民族自私的强烈倾向。他说:“中国通过成功地发展经济,通过出口武器,通过雄辩地宣传平等主义以及利用它在联合国的否决权,可望成为全球民众造反的旗手。”(《大失控与大混乱》,第2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中国可能发展的几个方向中,最危险的一种可能是:中国针对美、日、欧共体三方联盟形成自己的三方联盟,“把中国与波斯湾和中东地区的伊朗及前苏联地区的俄罗斯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反对现行秩序的联盟对不满现状的其他国家具有潜在的吸引力”。(同上)这对世界无疑是一种可能的威胁。就算中国不这样,在他看来,中国也可能走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在远东确立自己的主要大国地位,“对区域性稳定提出严重挑战”。(同上,第212页)布热津斯基的这些设想,最终所要得出的结论不过就是:美国应该在太平洋地区起到宪兵作用,“美国从该地区的任何撤离行动都会加剧这种危险。没有美国的军事存在,局部冲突——主要由经济利益,如海上石油勘探权引起的——就很有可能爆发,中国就会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威力,迫使他国承认自己的权利”。(同上,第213页)正是由于这样的理由,美国人认为世界只有依赖他才能有希望,而他在任何地区都是最公正、最合理的,都是为了全世界的共同利益的。而事实上,美国所宣扬的这一切,无非是想在太平洋地区获得更大的利益,或者使已经获得的利益不被别国所动摇。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有的人主张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说什么台湾人不是中国血统,支持台湾人赶走大陆人,支持台独,甚至建议把台湾变成美国的一个州。
此外,对美国来说,冷战结束后,宣扬中国威胁论,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目的,那就是:用以掩盖“威胁全球的‘美国式’霸权”。(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冷战结束以后,前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他本来就已经是世界的霸主,世界各国人民不希望这样一种独霸一方的世界格局,希望使世界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在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潮流面前,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许多方面的批评和不同程度的抵制,使美国陷入了原来的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各种矛盾之中,如美国与日本、与欧共体的矛盾。为了避免矛盾,转移视线,美国需要塑造一个资本主义阵营以外的共同的敌人,中国当然是最够资格充当这个敌人的国家了。因此,美国也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积极主张遏制中国,并且在行动上第一个准许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问美国,为台独分子提供新的活动场所,导致了两岸本已有所缓和的局势又骤然紧张起来,给中国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中国威胁论的盛行,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也不能改变中国人民自立自强的决心,但是,它对中国周边环境不可避免地会或多或少地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也会产生某些负面效应,会给我国造成一定的国际舆论压力,甚至对我国的边境安全都有某种程度的影响。这就提醒了我们:必须要高度注意国际动态,在国际政治斗争中,要始终坚持有理、有节,不主动招惹麻烦,但也决不能任人宰割、不敢坚持原则。而且,在进行必要的政治斗争时,不能放松国内的经济建设,要始终紧抓发展经济这根弦,排除各种困难,把我国既定的经济建设目标实现。只有我们真正强大了,中国威胁论才会不攻自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