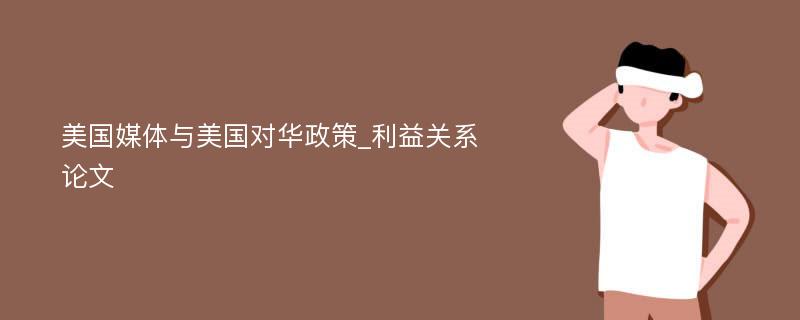
美国传媒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传媒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一段时间,关心和研究中美关系的人都会谈到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特别是美国各种媒介经常刊登批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和歪曲中国状况的文章。为此,一些在美国留过学和工作过的学者和记者专门出版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注:李希光、刘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4年12月。)揭露这些宣传毒化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氛围。在美国生活的许多中国人和美国朋友也都感到一种压抑的气氛。大家对中美关系的走向存在担心。与此同时,由于两国高级人士互访的增多,包括副总统戈尔、美国众议院议长金克里奇访问中国,江泽民主席访美和克林顿总统访华,更由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人们又感到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乐观的。如何看待这种矛盾的现象,特别是如何判断传媒的负面宣传的影响,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许多报刊,特别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大报和《时代》周刊、《标准周刊》这样的新闻杂志等都登载了不少歪曲中国情况和攻击克林顿对华政策的文章。美国电视也播了一些类似的节目。甚至“争取诚实的政府的公民”组织在其社团的刊物中也利用所谓政治捐款事件强烈地抨击政府的对华政策,指责中国收卖美国的外交政策。(注:Citizens' Intelligence
Digest,May 1997。)
从这些负面文章或报道中,可以看到三个特点。第一,除了新闻记者的报道外,其他文章的作者中极少有人专门研究中国问题。这些人对中国的攻击或对克林顿对华政策的不满往往是出于一种冷战的思维。他们总要为美国找到一个敌人,似乎这样才能团结美国人民和动员美国大众。早在冷战结束之前,由于前苏联对美国的威胁减少,有些美国人就把注意力放在日本身上,惊呼日本会再次威胁美国。如今,日本的经济发展遇到麻烦,而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引起世人瞩目,再加上中国是唯一的共产党领导的大国,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中国。当然也有个别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的学者加入这一行列。如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部主任曾在报纸上以模拟一份中国内部文件的形式称,中国要在亚洲推行中国的“门罗主义”政策, 而这方面的唯一障碍是美国。(注:The WashingtonPost,May 19,1996.)
第二,媒介借用各色人等来攻击中国和美国对华政策,主要原因是冷战后美国观众对国际新闻的兴趣日益下降,报导也随之减少。在冷战时期,国际新闻的重点是苏联或共产党的威胁,因为百姓关心自己的安全。冷战过去之后,新闻记者找不到能说明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重大“故事”,也就无法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这在电视报道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低收视率会造成经济效益降低,因此电视网晚间新闻中国际部分不得不大幅度减少。三大电视台中,ABC电视台1989年播了3733分钟, 而1996年只播了1838分钟。NBC电视台1989年播了3351分钟,而1996 年只播了1175分钟。(注:Garrick Utley,"The Shrinking of ForeignNews",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7.)对外政策的介绍也减少了时间。
另外,传统的新闻媒介还面临着其他媒介的竞争,如互联网络,甚至传真机。这种状况迫使报刊电视常常用能打动人心的报道来吸引读者和观众。而最容易吸引人的,一种是各种各样的“威胁”,如某种导弹“可以打到位于海湾的美国舰队”,中国某某想用“核武器打到美国的西海岸”,某公司工人失业是因为大量进口中国的纺织品,贸易逆差和盗版问题使美国每年少收入多少亿美元等等。这些都涉及到美国人的切身利益,而谁也不想看到国家的安全没全保障,谁也不希望自己的饭碗被打破。另一种是有背于美国人价值观的事件。如某某国家的人说话只能有“一种声音”,某某人士因批评政府政策而遭到迫害等。那些经故意渲染出来的事例能轻而易举地捕获读者的同情心。
这些报道在我们看来或者是不真实的,或者是片面的。但若考虑到美国新闻媒介的传统特点,出现这种大量负面报道就不足为奇了。美国的新闻媒介,“在某种程度上,消息差不多都是坏的。一位记者发来的电讯说‘一切顺利’,这种电讯一般是不予刊登的”。(注:梅尔·奥廷杰等编:《传播媒介之职能》,(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出版,1984年)第9页。)如果记者的稿子不能经常上版面, 那他个人就面临着“下岗”的问题。
第三、大批作者为共和党人,包括前布什政府的官员。他们对现政府发难,激烈地攻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其原因正如《旗帜周刊》的一位作者所说:“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注: Weekly Standard,April 7,1997.)近几年来,美国经济发展一帆风顺, 克林顿政府的声誉比较高。共和党为了争取下届总统竞选的胜利,不得不想方设法来贬低民主党的统治。跟踪轰动一时的竞选捐款事件,揭露克林顿私生活的问题,以及抨击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这一切报道都有这样的背景。
二
虽然美国媒介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很多,那么这些报道就能支配美国的对华政策吗?
新闻媒介在美国有着“无冕之王”的地位,对舆论的形成的确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媒介的影响力,每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总要借助媒介来宣传自己。但他们又害怕媒介,所以一些史学家总结说:美国总统要不断地寻找办法把他们的想法原原本本地传达给大众,而不经过媒介中那些“爱唱反调的牢骚鬼”的删节。(注:World &I,July 1997.)但媒介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人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它是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之外的“第四个政府部门”。有的人认为,“新闻媒介虽然是畅言无忌的批评者,但它对于政策制定毕竟只能发出比较小的声音。 ”(注:Howard Bliss ,Beyond the Water'sEdge:American's foreign Policy (J.B.Lippincott,1975)p.216.)因此,想要比较准确地判断媒介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是相当困难的。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一些基本事实来看看媒介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多大的影响。克林顿上台前的对华政策主张与目前媒介的负面看法最相吻合。当时他极力抨击布什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政策。然而,他上台以后又逐步推行同中国的“全面接触”政策。虽然,在他上任后中美之间在台湾、人权和经贸等问题上有过尖锐的斗争,但克林顿先是于1994年宣布把最惠国待遇问题同人权问题脱钩,后又于1996年派副总统戈尔访问中国,继而同意两国首脑进行互访。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2 月的国策报告中指出:“为了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理想,我们必须寻求同中国进行更深入的对话。一个孤立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一个在世界上发挥适当作用的中国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中国保持接触是对付我们共同的挑战的最好的方法,如结束核试验,也是坦诚地处理我们的根本性差异的最好的方法,如人权。”(注:The Washington Post,Feb,5,1997(A19).)美国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也持同样的立场。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批评“遏制”中国的主张。她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说中说:“遏制政策会使我们的亚洲盟友发生分裂,并促使中国退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一个团结而不是分裂的亚洲,一个不威胁他人也不被他人威胁的中国才符合我们的利益。”(注:1997年4月15日, 载美国新闻总署互联网主页)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作为美国军人,在访问中国时也谈到:“在信息时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与你们的安全和繁荣是密不可分的。”(注:1997年5月14日,载美国新闻总署互联网主页)财政部长在人民大学讲演中指出:同中国结成“强劲的关系对全球的繁荣和稳定是绝对必要的。 ”(注: The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6,1997.)
总之,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在对华政策上的态度是积极的。反对党共和党中虽然很多人,包括其领导人,担任众议院议长的金里奇,都批评现行的对华政策,但并非人人都反对同中国发展正常的关系。金里奇就曾应邀访问中国,并且指出:其目的是增进“友好合作关系”,两国需要通过直率的对话来建设“稳定持久的关系”。(注:金里奇在外交学院的讲话。)就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他一直强调要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正因为美国朝野众多政治家的努力,中国江泽民主席1997年11月访美取得成功。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三
媒介并不能支配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是美国经济界不断致力于扩大同中国的往来;二是美国的思想库普遍主张同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美国最大的500 家公司几乎都同中国建立了合作关系。老的如波音公司和福特公司,新的如微软公司。最近,惠普公司甚至在北京购买办公楼,作长期发展的准备。中美贸易不断增长,1996年达到635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是美国的第11位贸易伙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2.21万个,协议投资额356.9亿美元,实际投资额136.8亿美元。美国是在华的最大外国投资者。这些美国公司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努力坚持要求政府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现在又要求取消一年一审议的作法。作为代表美国公司在华利益的美中商会, 其主席凯普经常到国会就两国经贸关系作证。 譬如1996年9月19 日他在众议院贸易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强调:“美中贸易带来的利益如今已延伸到我们国家的各个角落,它表现为成千上万的工作,增强的竞争力和买得起的消费品。”他批评每年审议最惠国待遇的作法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副作用,是方向性错误”。他还呼吁:“支持我们商会的那些在国际上活跃的公司都期待着中国加入WTO。”为此, 他要求:“在争取更加合作的美中关系方面,全面推进的最大希望在于逐件处理不相关的、可分开的问题。”
这两年美国一些研究机构发表了关于对华政策的研究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项目的参加者人数众多,不仅包括著名学者和思想库的领导人,而且包括政府人士,以及国防部、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官员和国会议员助理,商界人士,甚至还有记者,人权组织的成员等等。这些报告普遍建议美国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建议“两国应尽早开始基于现实的议事日程定期举行首脑和内阁级的对话”,“努力地去明确美国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并决定如何加强这些利益,找出美中两国之间的问题和争议, 并决定如何处理或解决它们。 ”(注:Developing
a Peaceful,Stable,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 A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Report)p.24. )1996年11月份,美国国民大会也发表了一份题为《21世纪的中美关系:培育合作,避免冲突》的研究报告,其主旨是“共建未来,发展合作,缩小分歧”。它建议在中国问题上,“最首要任务应该是建立一个新的、全面的和更加相互信任的关系”,甚至具体提出在1997年上半年邀请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进行首脑会谈。(注:China -US Relations in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American Assembly).)1997年7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又发表了另一份报告,题为《塑造美中关系——长期战略》,指出“在未来几年里,对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没有任何关系比同中国的关系更重要。”在“安全、经济关系和发展法制”方面进行合作是首要任务,并进一步寻求最可能取得成果的合作领域: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环境保护、节约能源、改善中国的金融财政体制等。(注:Shaping U.S.-China Relations:A Long-Term Strategy(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这些严谨全面的研究报告, 由于其参与者来自方方面面,加上参与者个人的地位和影响力,势必对决策产生作用。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江主席访美时期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到,这些报告的许多主张都已体现在声明中。
另外,虽然美国媒介作了大量负面报道,但它们不是唯一的报道。如对前述《旗帜周刊》的一篇文章,《华盛顿邮报》曾刊登另一篇文章进行反驳。该文在结尾处引用了胡佛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说:“我们在许多方面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希望她的人民幸福和平,解决环境保护问题, 和处理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带来的危险。” (注: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8,1997.) 又比如美国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思(共和党)在国会讨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的前夕,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所谓最惠国待遇实际上就是“正常的贸易关系”,并举例作出详细的解释,欲使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能搞懂这个问题,即美国并没有给予中国任何特殊的优惠待遇。(注: TheWashing-ton Post,May 21,1997.)
《华盛顿邮报》在1997年1月12 日的一篇“再论中国与人权”社论中,把维护中国少数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利说成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当务之急,甚至建议美国国务卿对中国采取“有效的威胁”。不久,报纸刊登了一位读者来信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主要目标是维持亚洲的战略稳定,没有中国的合作无法实现这个目的。事实上,鉴于美国与中国有大量共同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在如今这个冷战后的时期里,显然没有其他双边关系比这个对华盛顿来说更重要了。”作者在信中还列举了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代表对政策的辩论和乡镇的选举等改革措施。最近另一篇文章批评说,美国一再试图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通过谴责中国人权保护记录的作法是不可取的,其结果“不是北京,而是华盛顿遭到孤立”。它认为,美国本身也存在人权保护方面的问题;应该同中国对话,推动中国法制化。(注:The Washington Post,Jan.27,1997(A18),December 19,1997.)
最近,东南亚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一些外国报纸预言中国的经济也将崩溃。就在这时,《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对中国的经济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它指出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不同于那些国家,人民币不会大幅度贬值,中国不会缺钱还外债。中国通过企业所有制改造、下岗和就业培训等方法会使经济走上正轨。(注:The
WashingtonPost,December 29,1997)
针对台湾在美国用金钱开道的作法,《纽约时报》也曾发表关于“台湾因素”的社论,比较公正地揭露台湾在政治捐款上的种种小动作。(注:New York Times,April 15,1997)
而像《外交》这样的学术刊物,更是注重把不同的观点都摆出来。如它在1997年3—4月号上刊登了两篇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一篇是孟儒(《与中国的未来冲突》的作者)写的,另一篇是陆伯彬(哈佛大学教授)写的。前者强调中国的威胁,认为中国“将会同美国发生冲突”;后者认为根本不存在中国威胁的问题。又譬如在香港回归前夕,美国的媒介普遍怀疑中国政府的承诺,认为香港将出现动荡。而弗兰克·金(《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的高级编辑)的一篇文章则对那里的局势和中国的政策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一方面对法律应用和新闻自由等问题表示担心;另一方面象《外交》双月刊(5—6月号)也明确指出:“香港的变化将是比较小的,不是大范围的。”“总的看,中国会努力信守承诺。”至于像奥克森伯格、鲍大可、李侃如和傅高义等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更是或撰文或在电视台上驳斥关于中国的种种不实之词,比较客观地分析中国情况,对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或者基本支持,或者认为远不够积极。
四
由于媒介报道的倾向性和对决策的影响有限,故不能轻率地就根据那些内容作出判断:美国实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媒介对舆论的影响,应该争取它以客观的态度来报道中国及中美关系,包括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和看法。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改变美国新闻媒介的传统之时,是否有别的途径可以为美国大众提供更多更客观的信息?1997年7月,美国的北加州世界事务委员会组织了一次题为“中国,下一个超级大国?”的报告会,力图客观地介绍中国,为期两天。报告人为持各种见解的人士,如哈丁、田长霖、佩洛西议员和孟儒等。数百名参加者包括学生、教师和工商界人士等。会前和会后,组织者就同样的问题对听众作了问卷调查。其结果值得我们深思。下面是其中部分问题的调查结果。
1、25年后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吗?
是不会没有想法
会前86%5% 9%
会后79%7% 14%
2、无论是否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将对邻国和美国持友好、 敌视或中性的态度?
友好的 敌视的 中性的
会前25%30%45%
会后35%25%40%
3、应该给中国永久性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吗?
是 不是没有想法
会前27%44% 29%
会后48%36% 16%
4、香港将会平稳过渡吗?
会 不会没有想法
会前30% 40% 30%
会后47% 21% 31%
5、如果台湾人民选择不接受“一国两制”政策而要独立, 美国应该表示支持吗?
应该 不应该没有想法
会前
42% 27% 31%
会后
34% 41% 25%
6、如何评价美国新闻媒介对中国的报道?
太多了
足够 不够
会前
10% 17% 73%
会后 0.5% 19% 80.5%
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会前、会后,听众的看法有了显著的不同,而且会后的看法基本上趋于客观、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特别是第6 个问题,听众普遍认为新闻媒介对中国的报道非常不够。尽管现实说明媒介对政策决定的影响有限,但媒介通过影响舆论,进而影响政府的作用还是不可否认的。为了减少媒介对公众的消极影响,有必要为美国大众提供更多客观的信息。如何开展这项活动应成为我们对美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