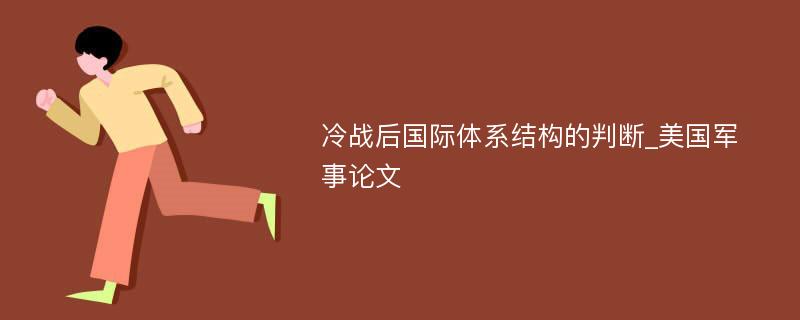
冷战后国际系统结构的判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结构论文,国际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外交政策的分析方面,通常存在文化、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和国际制 度等几种分析范式,其中,权力结构范式最为常见。这是因为国际系统从本质上看仍然是无 政府的,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或动机是自私的理性的国家利益,(注:这样说并没有否定由于国际制度和共同观念存在所决定的一定程度的国际秩序,也没有 否认国家出于最根本的私利而做出的利他或利于集体的行为结果。)国际系统的权力结构是 影响国家利益判定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进行权力结构范式分析的 一个基本前提或根基应该是确定国际系统的结构特征,但是,学术界基本上或者把它当作一 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而忽略了,或者以大而空的语言一掠而过,而没有对它科学、客观地详加 判定。
根据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系统结构是系统的排列原则和能力分配,由于国际系统 无政府的平行秩序和国家功能相同但能力不同状况,大国的数量与能力的差别决定了国际系 统的结构特征,“极”的数目的计算是国际系统结构的基本准则。(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 4—119页。)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二战 以来国际系统公认的清晰的两极结构的瓦解,世界进入了一个结构转换的过渡时期。(注:国内学术界多使用“格局”的概念替代“结构”概念,在真实意指上是相同的,但不如 “结构”概念更具学术准确性和标准性。)这一 点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对于冷战后国际系统的结构特征的判定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围绕 对冷战后国际系统结构的判定,学界在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美国是 不是衰落了?是绝对衰落还是相对衰落?一极还是多极结构?一极还是一极化?多极还是多极化 ?
一、美国“衰落”的争论
美国“衰落”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并迅速波及美国朝野,也成为全世界讨论的热点 问题。关于美国“衰落”的大讨论,最初是由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1987年的 著作《大国的兴衰》引发的。他以历史类比的逻辑得出结论:美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他认为美国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战线拉得太长,军费负担过于沉重。(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纽约1987版,第146页。转引自刘靖华著:《霸权 的兴衰》[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肯尼迪的美国 “衰落”论一经抛出,得到许多人的随声附和。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指出,帝国的 过度扩张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一个崛起的强国必然扩充它的军事力量,逻辑发展的结果就 是,它所付出的成本超过了从它掌握的资源中的获利,从而导致它的衰落。他说:“美国今 天变弱了,欧洲和日本同时强大起来……(美国)如日中天的霸权不复存在了,永远也不会回 来。”(注:Immanuel Wallerstein,“Foes as Friend?”Foreign Policy,Spring 1993.)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美国在世界上“不再占有支配地位”,世界“出现了五个或 六个相差不多的力量中心……美国在军事方面最强大,但是可以使用其军事力量发挥作用的 环 境正在消失。”(注:Henry A.Kissinger,“World Must Turn to Post-Cold War Era,”China Daily,Januar y 18,1993.)而戴维·卡列奥的看法更为彻底,他说:“由于经济紧缩和管理不善,相 对衰落已经变成了绝对衰落。”(注: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M],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关于美国“衰落”的问题,存在着截然对立的观点。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栏作家查尔斯· 克劳特哈默在美国“衰落”论盛行时,提出了“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论。他指出 ,冷战的结束,导致了美国领导的“单极时刻”的到来,而不是什么多极化,在最近的将来 没有其他国家能与美国抗衡。(注: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Vol.70,No.1,(W inter 1990/91).)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认为结构性权力包括 了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大结构,权力就是通过这四种结构对特定的关系产生影响的。 (注:(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M],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51—137页。) 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没有丧失结构性权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对“衰落”论最有力的攻 击还是约瑟夫·奈的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的出版。奈指出历史类比的逻辑是错误 的,美国不同于历史上包括19世纪的英国在内的霸权国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二战后的迅 速下降是正常的,并不能说明美国的衰落。他独辟蹊径地提出了“软权力”(soft power)理 论,认为美国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在软权力方面仍然占有最大的优势,美国根本没有“衰落” , 更不能鼓吹放弃美国的“领导”(lead)责任。1996年,奈进一步断言: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美国通过领先的信息技术发挥软权力的作用,将使21世纪成为比20世纪更辉煌灿烂的“美 国世纪”。(注:Joseph S.Nye,Jr.,and William A.Owens,“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Foreign A ffairs,March/April 1996.)
亨廷顿的观点比较持中,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论证美国是否“衰落”,重要的是应清 楚地看到冷战后国际关系、力量分布和大国关系变化,及时地调整美国的战略以对付更加危 险的世界形势。(注:亨廷顿:“变化中的美国战略利益”[M],译自英国《生存》杂志,1991年1—2月号。)这场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论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随着美国新经 济的到来,欧洲和日本经济却出现相对缓慢的趋势,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所占世界总量 的百分比都在迅速上升,美国一反原来悲观的情绪而空前狂妄起来,美国“衰落”论早已销 声匿迹,取而代之的“美国霸权”、“美国世纪”、“单极领导”的声音此起彼伏。
二、一极结构或多极结构的争论
与美国“衰落”紧密相联的问题就是对国际系统结构的判定,即世界的极数。“极”本是 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它指的是一种磁场中心,国际政治学把它形象地用作强大的世界权力中 心,以界定国际系统的结构特征。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极”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概念的使用已 经过时,(注:资中筠:“‘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会出现吗?”,载袁明主编:《跨世 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M],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但惯性作用,它仍然被广泛使用。
其实,关于世界多极说法自尼克松时代就出现了。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在堪萨斯城发表 讲话,承认美国已失去了战后以来在世界的垄断地位,未来的5—15年间,将出现“五个强 大的力量中心: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这五股力量将决定本世纪最后30年的世界 前途。”(注: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65,No.1674(July 26,1971)p.9511,Kissinger,W hite House Years,p.191.)基辛格看到了军事实力的联系性权力下降和权力分散化的趋势及其对美国的限 制,仍然坚持多极世界的观点。也有人从美国国内政治牵制角度判断,如新孤立主义和新保 守主义的抬头,民众对美国起世界领导作用的冷淡,使政治领导人面对强大的国力徒叹奈何 ,(注:安德鲁·科胡特 罗伯特·托特:“对外事务的断层线”[N],载《华盛顿邮报》1997 年12月28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1月1日。)实力难以转化为行动的权力。
关于美国衰落和世界多极化的观点在美国以外得到了更多的呼应和支持。法国政治观察家 皮埃尔·比亚内斯肯定地说:“21世纪不属于美国。他将是多极的、多文化的,如同过去的 世纪一样。”(注:王辑思:“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初探”[M],载赵宝煦主编:《跨世 纪的中美关系》,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美国虽然是唯一的超 级大国,但它的地位已经相对衰落。”(注:郑必坚、杨春贵主编:《中国面向21世纪的若干战略问题》[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年版,274页。)依据一般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比较美国政治 经济力量的衰退。90年代末,中国对国际系统结构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一方面承认美国唯一 超级大国的优势,“世界多极化进程要比预想的复杂、曲折”,但从长远角度看,“多极化 的趋势是阻挡不住的。”(注:周荣耀主编:《冷战后的东方与西方——学者的对话》[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 97年版,第7页。)
沃尔兹从他的结构理论出发,认为“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世界变成了单极。”(注:Mortimer B.Zuckerman,“A Second American Century,”Foreign Affairs,(May/Jun e 1998).)随着克 林顿政府的上台,美国经济恢复并进入了持续扩张期,美国“衰落”和多极化的声音越来越 微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主编朱克曼认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8个年头,超过 了前几十年的‘德国奇迹’和‘日本奇迹’”,“法国拥有17世纪,英国拥有19世纪,美国 拥有20世纪,21世纪也将继续属于美国。”(注: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 urity,Vol.24(Summer 1999).pp.9-22.)沃尔弗斯在1999年则系统地分析了美国作为 单 极的特征和实质,提出了一套单极体系的理论和战略构想。他认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存 在的超级大国,它的财富、资源、物质力量或权力的集中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霸权国 家,它在经济、军事、技术和地缘方面的优势更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毫无疑问当 今世界是美国的单极世界。(注:Aaron L.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 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Winter 1993/94)pp.5.)
也有不少人持中间立场,“从战略来看,两极并未让位于单极,也还未让位于多极,而是 让 位于一系列的地区次体系,一系列毗邻的国家在其中交互作用。”(注:Richard K.Betts,“Wealth,Power,and Instability: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 tes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Winter 1993/94).)“今天全球的单 极化与地区的多极化同时发生。”约瑟夫·奈认为,冷战后世界现实情况是“多层相互依存 体制”,世界政治中的力量分配犹如一个多层蛋糕,顶层是美国军事层,是单极的;中层是 经济层,美日欧三极平分秋色;底层是跨国相互依存,力量更为分散。(注:Joseph S.Nye,Jr.,“What New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Spring 1992).)亨廷顿的观点是 “单极——多极”结构,即一个超级大国和一些地区大国。美国在经济、外交、军事、文化 各方面具有超强的实力,但一些关键的国际问题需要美国与其他大国的联合行动,其他大国 也可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联合对美国进行否决。(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Vol.78(Much/ April 1999),No.2.Pp.36.)
三、判定冷战后国际系统结构
学界对国际系统结构的判定上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分歧,原因在于学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对力量来源的认识不同,也在于学者对“霸权”和“极”的定义不同,所以结构判定的原则 就难以统一,结论也就大相径庭。
第一,系统结构判定的原则
沃尔兹认为,“在一个无序的领域里,结构是由结构之中的主要单位来限定的。国际结构 随着列强的数目的重大变化而变化,把列强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依据是列强所拥有的综合 能力(或实力)。”(注:(美)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思想与新现实主义理论”,载袁明主编:《跨世纪 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M],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既然能力的分配是界定结构的标准,那么对于能力的界定就成为结构 概念的关键。沃尔兹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军事和其他的力量不能被割裂开来,而必须使用 国家的综合力量来衡量。具体说,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里的位置应该取决于在下述因素上的 得分:“人口的多少和领土的大小,资源的储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政治的稳定性和能 力。”(注:(美)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思想与新现实主义理论”,载袁明主编:《跨世纪 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M],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而我们在他的著作或文章中体会到的是,他所谓的能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军事 力量。这样的界定自然比较简约明了,容易衡量和计算,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遭到了理论 界最广泛的质疑和批判。
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吉尔平对经济力量更加重视。他认为,权力不仅来源于实力(军事力量) ,还来源于经济和技术因素,国家行为体正在从寻求权力转向寻求福利。他在权力(政治权 力)分析中加入了财富(经济权力)变量,结构形成的动力不仅是沃尔兹意义上的实力即主要 是军事和政治力量,更有经济力量(财富后盾),它以霸主国为核心,向整个国际体系辐射其 政治、经济影响。(注: 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新自由制度主义对结构现实主义在国际结构定义的简洁性上也持批评 态度。基欧汉认为,产生权力的来源已变得更加复杂了。他主张“把各种不对称相互依赖看 作行为体的权力来源。”(注: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M],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20页。)约瑟夫·奈将权力区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他认为, 国家权力不仅来源于它的军事、经济和科技等力量,也来源于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等 ,他特别强调了美国文化的同化力和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制度对美国霸权 的 意义。
对结构的界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议,原因在于:(1)从根本上说,构成国家能力或实力的 因素很多,而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甚至不同的领域,这些因素的作用又具有不同的地 位和影响;(2)这些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又不具有准确的可比性,不同的学 者和流派从自己本身的理论出发,对不同的因素的关注或研究的程度不同,对权力的来源的 结论也就不同;(3)时代和国际系统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全球化时代,争取在国际 制 度和国际机制制定上的参与权和决定权的意义也愈发显得突出,而且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信息也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力量来源。
从科学哲学方法论上来说,理论的简约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则。理论的根本目的和 功能在于解释,纯粹为了简约之美的理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约翰·伯顿(John Burton)认 为:“国际关系的动态性质是现实的一个显著特征。任何总体理论,如果不思考这种迅速变 化的技术、社会和政治环境,它就不是一种适合时宜的理论。”(注: 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7页。)因此,判定冷战后国际 系统结构特征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根据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特征,参考借鉴各派学者的意 见,既沿袭沃尔兹的模糊性原则和综合国力原则,也吸收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制度主义 的思想,对沃尔兹的结构概念给予丰富和扩展。这样,国际系统的结构就被定义为国际系统 中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注:权力的概念与沃尔兹所谓的能力、实力不同,权力指使别的行为体按照自己意愿行事 的力量,而能力或实力往往强调国家客观的物质力量,接近于奈所谓的“硬权力”,包括经 济、军事、外交、资源、技术等,一方面实力成为权力必须经过主观意志的转化,另一方面 没有涵盖文化、制度甚至信息等“软权力”。)而国家权力的来源主要包括: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 科技力量、文化力量、国际制度因素(注:国际制度至少应该有两种角色:一是作为国际进程的核心变量;二是作为界定结构的 国家能力的因素之一。在这里,它是后者。)以及包括领土(面积和位置)、资源和人口(数量与 质量)在内的自然物质因素。虽然很难精确地计算,但是根据这个标准,国际系统的结构还 是可以大致地确定。
第二,系统主要力量权力对比的考察
国际系统结构特征决定于系统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也就是大国之间权力的对比,单纯一 个大国的绝对权力指标既不能说明它自己在系统中的地位,更不能判定结构,权力对比的考 察才是合适的方法。根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综合国力(注:这里的综合国力指标与我们界定的国家权力来源比较接近,它包含了经济、军事、科 教、资源、政治、社会、国际影响等七个领域,既包含有形的物质力量指标,也覆盖无形的 文化、意识、制度等方面。)评估课题组的研究结果, 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1998年世界各大国的综合国力,美国的分值是8371,日本是4966,法 国是4254,英国是4039,德国是3715,俄罗斯是3325,中国是2629。从分领域的对比来看, 在经济和科教领域日本已经比较接近美国的得分(比分分别是8921/6670,9492/8641),英国 、法国和德国都大大超过了美国的一半;在资源领域,中国和俄罗斯的分值都超过了美国( 两国与美国的分比分别是4621/3330,5210/3330);在军事领域美国几乎与其他六个大国的 实力相当(美、日、中、俄、德、法、英分别是9503、1338、1068、3172、1222、2085 、2183)。(注:参见“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评估”,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全球战略大格 局》,时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从综合指标上衡量,日本、法国、英国和德国都接近或超过了美国的二分之 一,俄罗斯和中国也接近或超过了美国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实力显然达不到单极结构的要求 ,除军事之外的其他分领域指标更是证明这个结论;美国在军事领域具有绝对优势。毫无疑 问,军事力量仍然是权力结构中至关重要的因素,美国军事力量与其他大国的如此严重不均 衡,难以支撑多极结构的判断。从这个测评的结果看,“一超多强”的结构特征判定相对比 较客观。
王辑思教授为了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估,在纵向尺度、横向尺度和 多重视角的原则上提出了七项重要衡量指标: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军事能力、教育水平 和人才流向、社会凝聚力、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力以及美国的形象、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 的支配力以及自我调节的能力。他根据这些指标并结合了全球化进程的国际背景及其与美国 国内变化的互动关系,对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演变趋势进行了详细的审查和研究。他的结 论是,“美国不会失去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不会拥有传统意义上(如19世纪的大英帝国)那 种称霸世界的能力。”它也“无力领导世界”。(注:参见王辑思:“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初探”[M],载赵宝煦主编:《 跨世纪的中美关系》,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6页。
)这个结论,实际上否定了“单极”或“ 霸权”的结构判定,支持了“一超多强”的结构特征观点。
第三,概念的界定
系统结构判定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来定义“单极”、“多极”、“霸权”概念。亨廷 顿认为,单极结构应该存在一个超级大国和许多小的国家,而不应该存在一些主要的大国, 超级大国能够独自有效处理重要的国际问题,其他国家或国家联合不能阻止它的行为。而多 极结构应该存在一些力量大致相当的主要国家,它们在不断变换的组合或类型中进行合作或 竞争,重要国际问题的解决要靠主要国家的协调与合作,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 大致与此接近。(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Vol.78(Much/A pril 1999),No.2,pp36-35.)根据这个定义,冷战后国际系统显然既不是单极结构也不是多极结构。 沃尔弗斯认为,单极在结构中,某个国家的能力是如此巨大,以致于无法被抵消,与此同时 ,实力又没有集中到一个全球帝国的程度。根据这个标准,现在是美国的单极世界。(注: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 urity,Vol.24(Summer 1999).)显 然是由于定义和标准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结构判断。
在“霸权”(hegemony)的定义上更为混乱和含糊。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重复了他和 奈在1977年对霸权的定义:霸权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国家有能力并有意愿保持统治国家 之间关系的主要规则。(注: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34-35.
)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从创造、加强自由经 济秩序和规则方面来定义霸权,认为英国(从181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1945年至197 3年)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两个成功的霸权。实际上,他们二人都只是强调了经济和经济规则 方面,定义并不十分全面。沃勒斯坦认为,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就是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在经 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把它的意愿强加于他国。霸权的取得,必须同时在农——工生产 、商业和财政三个领域获得优势。中国学者秦亚青认为,霸权国定义霸权结构,霸权结构定 义霸权系统,霸权系统就是一个权力超强的国家,在系统中占据统治或主导地位,这种状况 近似于一个由单一国家领导国际事务的单极体系。他将冷战时期的国际结构称为“两极霸权 ”,冷战后的国际系统则趋向于“多极多元霸权”或“多极霸权”。(注: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他认为,一极 的消失,而另一极仍然存在,而且没有一个次级大国接近一极的实力,也没有一个大国比其 他大国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霸权”结构没有改变,但考虑到权力在各问题领域的分散 化,这个霸权又不是全面的甚至完全意义上的霸权。
总体看来,“霸权”与“单极”的含义是比较接近的,都是指一个国家的实力明显超过其 他国家很多;而且这个国家应该具有基本不受其他国家限制的行动自由。冷战后美国的实力 可以满足第一个条件,但难以达到后一个条件;而“一极——多极”与“一超多强”或“多 极多元霸权”的含义比较接近,只是表述或者程度细微的区别,它们既强调了美国的超群优 势,又看到了它的权力与行动的局限。因此,与冷战后的现实最为符合的判断应该是“一超 多强”、“一极——多极”或者“多极多元霸权”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