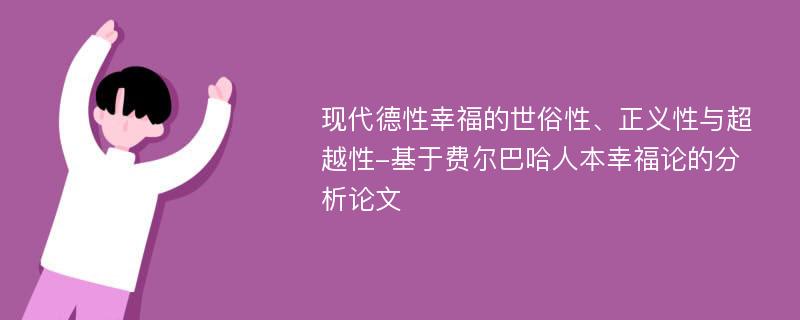
现代德性幸福的世俗性、正义性与超越性
——基于费尔巴哈人本幸福论的分析
张方玉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曲阜 273165)
[摘要] 对宗教幸福的猛烈批判是费尔巴哈人本幸福论的重要使命,同时费尔巴哈也深刻批判了古典德性幸福,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现代德性幸福的进程。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和幸福论在表面上很容易造成快乐主义、自然主义、利己主义的粗鄙印象,然而其理论上“幸福——道德”“人——上帝”的内在逻辑表明,人本幸福论中德性幸福、理性主义、人本宗教的旨趣并不逊色。费尔巴哈幸福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把人的幸福从虚幻的天堂重新拉回现实的世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典德性幸福的复兴,并对现代德性幸福的世俗性、正义性和超越性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
[关 键 词] 德性幸福;费尔巴哈;人本幸福;世俗性;正义性;超越性
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以来,对于幸福范畴做出自觉反思和深入论述的西方哲人群星璀璨,然而哲学史上直接以“幸福论”为题名的专门著作却不多。仅此而言,费尔巴哈的《幸福论》自当引起幸福伦理学的特殊关注。进一步而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幸福论既在宏观层面论及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又在具体的层面考察了幸福与利己主义、幸福与义务、幸福与良心的关系,探讨了包括宗教幸福、德性幸福、儒家思想和康德伦理在内的诸多问题。因此,在现代幸福观建构的视阈中,深入考察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是一项颇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讲析:(1)“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前一句说的是古人出门时不像今天科技发达,可以通过手机网络或电视收看天气预报,而是只能出门观看天象,判断是否会下雨,进而决定是否出行。后一句说明客人进主人家时,要看主人的脸色或态度决定去留。(2)“穿不穷吃不穷,人无打算一世穷”,说明为人居家过日子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会谋划,想办法,精打细算,日子就会越过越红火,否则“坐吃山空”变成“叫化子”。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要做到主观符合客观,一切从实际出发;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意识推动事物的发展,错误意识阻碍事物的发展;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客观规律,谋划、打算好自己的事情。
一、何谓人本幸福
“人”是费尔巴哈伦理学的基本范畴,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学。当人本学与宗教神学相遭遇,费尔巴哈指出神学的秘密在于人本学、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当人本学应用于阐述社会伦理思想,人本幸福论应运而生。幸福总是人的幸福,称之为人本幸福似乎有些同义反复之嫌。然而,“谁之幸福”“何种幸福”并非可以忽略的问题,天上的、天使的幸福正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所要批判的对象,因此在概念上厘清何谓人本幸福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目前学界对费尔巴哈人本幸福的概括往往直接采用《幸福论》中的原句,比如“生命本身就是幸福”“生活的东西都属于幸福”“健康是一切幸福的前提条件”“道德的原则是幸福”……这样的概括当然是忠实于原著的思想,但显然也未能对人本幸福进行深入分析与挖掘。在内在和深刻的层面上,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首先是人的幸福,而这里的“人”又是以自然为基础的人,因而可以称之为生命幸福;其次,人本幸福是针对宗教神学的幸福而言的,并非虚幻的、病态的幸福,因而是现实人间的生活幸福;最后,人本幸福是关涉义务与良心的幸福,并非自私的、物欲的幸福,因而是贯穿着爱、伦理与意志力的德性幸福。
生命幸福的层面上,人本幸福立足于人的动物性和自然性。“从有生命、有感觉、有愿望的生物观点看来,只有幸福的存在才是存在,只有这种存在才是被渴望的和可爱的存在。”[1]535为充分论证生命幸福的命题,费尔巴哈列举了幼虫的艰苦流浪只为寻觅适宜的植物,列举了浣熊需要足够的水维持特有的洁癖,列举了蝴蝶在性交时或性交后即死亡,等等。生命幸福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幸福,正因为费尔巴哈的生物学论证,其人本幸福容易造成粗鄙和低俗的感觉,并常常被视为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老调重弹;但同时,生命幸福无疑也是反对禁欲主义的有力武器。
生活幸福的层面上,人本幸福充满着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猛烈地冲击着宗教神学虚幻的幸福观念,阐明幸福不在天堂或彼岸,而应当返回地上和人间。费尔巴哈称颂古希腊人所追求的世间的、实在的幸福:“即使当他们凭着哲学而将他们的神灵精致化与精神化了的时候,他们的愿望也仍然留在实际的基地上,留在人性的基地上。”[2]73生活幸福就是用现实世界中的材料,建设幸福生活的内容,包括精美的食物、优美的音乐、思想的魅力等尘世的幸福满足。
在此意义上,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思想达成了物质基础上的德福一致,人的幸福构成了道德的基础。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具有道德工具论的色彩,即把德性、德行看成是达到幸福的手段,但费尔巴哈的幸福也并非狭隘的个人主义的幸福。“自己的幸福自然不是道德的目的和终结,但它是道德的基础及其前提条件。”[1]577在道德与幸福的关系的重新审视中,费尔巴哈强调的是幸福对于道德的基础性作用,而且更加重视幸福的地位与意义,其著作《幸福论》直接以“幸福”为题名,内在的逻辑不言而喻。
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在猛烈抨击宗教幸福观的过程中,以其鲜明丰富的启蒙思想,在实质上也推动了德性幸福的现代化进程,而世俗化则在这一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无论是在生命幸福、生活幸福的意义上,还是在德性幸福的意义上,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一方面把人的幸福从虚幻的天堂拉回到现实的人世间,另一方面又使人的幸福显得更加真实和亲切。
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是生命幸福、生活幸福与德性幸福的统一,凸显了幸福的自然性、现实性和超越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动物性、人性与神性的统一。幸福概念的如此界定,为人本幸福进行有力的批判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生命幸福、生活幸福的层面上,人本幸福对于宗教幸福、禁欲主义展开深刻的批判,这是众所周知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本幸福在德性幸福的层面对古希腊德性幸福观加以继承、对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展开批判,对古典幸福的扬弃也是人本幸福观的重要使命。费尔巴哈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学说充斥着诅咒、祈福、堕落、福乐的内容,这些学说并不是诉诸于理性,而是诉诸恐惧与希望的感情。基督徒摒弃自然物欲的满足,认为幸福是上帝的赐予,其愿望是那无限美好的天堂,而只有信仰上帝才能摆脱人间的黑暗生活,费尔巴哈对此予以辛辣的讽刺。费尔巴哈还认为佛教追求幸福的思想不是健康的、自然的,而是那充满了恐怖的、病态的幻想与涅槃。
恩格斯清楚地看到了费尔巴哈幸福论的这一特质,准确地指出,“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原则”[7]30。恩格斯认为,在费尔巴哈的道德理论中,追求幸福的欲望一方面受到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另一方面又受到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的头痛,放荡行为后的疾病便是自然后果的矫正,所处理的正是人与自我的关系;不尊重他人的幸福追求后引发的纷争与反抗,便是社会后果的矫正,所处理的则是人与他人的关系。但恩格斯同时也认为费尔巴哈的一切道德理论准则均是从对己节制、对人以爱中引申出来的,因而其道德理论是贫乏的、空泛的。实际上,就费尔巴哈幸福论本身而言,人本幸福探讨了幸福与正义的内在关联,涉及利己主义、义务、良心、爱等诸多道德范畴,思想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值得称道。《幸福论》共十一章内容,后五章的标题分别为“道德的幸福追求”“幸福与利己主义的本质区别”“追求幸福和对于他人的义务”“良心与追求幸福的一致性”“德行和对于幸福的追求”。这些标题在幸福论的专门研究者那里,无疑是令人兴奋的主题,便是恩格斯本人也承认费尔巴哈对此的议论可谓妙趣横生。
二、德性幸福的世俗性向度
(2) 改变再生粗骨料取代率,对高温后试件滞回曲线变化的影响不大;与试件S-5相对,试件S-4的滞回曲线饱满,因为套箍指标提高,核心混凝土受钢管约束能力增强,使得强度和刚度的退化缓慢。
建立健全的能源管理制度也是关键一环。医院陆续编制出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节能降耗考核制度等,从管理文件、技术文件、记录文件、节能制度、岗位职责等多个维度建立全面的制度体系。
古典式的德性幸福,无论是先秦儒家的“孔颜之乐”还是古希腊哲人的“思辨幸福”,总是充满着一种高贵的人性光辉与迷人的思想魅力。毫无疑问,这样的德性幸福是一种榜样和典范,从而成为道德精英或者知识精英孜孜以求的方向。然而对于多数普通大众而言,古典德性幸福往往显得“高高在上”或者“可望而不可及”,圣贤哲人的幸福状态恐怕是世俗百姓所难以企及的理想。尽管人们能够普遍认识到幸福与快乐的实质性差异,许多人甚至清楚地认识到幸福本身包含着德性的要求:“幸福是以德性为先决条件的,而且德性还是幸福的保障、工具和内容,”[4]269但要求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降低感性欲望需求,并追求更加纯粹的精神需求——比如孔颜的境界、思辨的乐趣,恐怕也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科技的进步、生产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资本、商品、信息、市场共同打造的高楼大厦、餐厅酒吧、香车时装、休闲娱乐形成了消费主义的超强漩涡。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德性幸福如何完成现代转型成为关乎自身前途和命运的课题。
正如一千个读者的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个体的幸福总是千差万别的。《尚书·洪范》有“五福”的表述: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这可以视为古老而通俗的幸福理解;而在儒家思想中,“乐”可以被视为幸福的雅文化表述,比如“孔颜之乐”“君子之乐”;在古希腊哲学中,幸福又常常被理解为中等的财富、健康的身体、灵魂的无纷扰。而在现代社会,幸福通常被解读为人生的重大快乐、是人生重大需要、目的、欲望得到满足、是生存和发展的达到某种完善的心理体验。[6]22费尔巴哈的解读与诸多幸福观念存在共通之处,而其鲜明的特色在于将幸福与公正内在关联。健康、安乐的生活状态首先是每个人与自己的关系问题,合理地处理这一关系必然关涉公正的原理,公正或正义在这里是作为一种善待自我的德性存在的。后者,饮食、衣服、阳光、空气和住居作为幸福的内容和条件,必然涉及利益分配的公正。物质生活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人取得较多的利益,那么其他人将可能因此而失去一些利益,合理的幸福还必须公正地处理人与他人的关系。公正地处理他人与自我的关系,既是善待自我、追求个体幸福,也是尊重他人、实现群体幸福。
传统的德性幸福往往限制物质需求的满足,要求尽可能降低感性欲望,“孔颜之乐”所描述的“箪食”“瓢饮”“陋巷”为儒家所称道,就是典型的表现。西方伦理也有类似的表达,比如对于欲望满足的讽刺:“牛吃草料的时候是幸福的”。然而,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却宣称“没有幸福就没有德行”,提出幸福就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安乐的生活状态,饮食、衣服、阳光、空气和住居就是追求幸福的对象。“生命本身就是幸福”,或者“一切属于生活的东西都属于幸福”,当人的幸福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被论证,当幼虫的艰苦流浪与人的幸福追求相提并论,人本幸福不可避免地陷入粗鄙的自然主义。这与古典德性幸福的道路似乎渐行渐远。人们不禁心存疑惑:如此粗俗的人本幸福是否还能具有古典德性幸福的高贵与崇高?
德性幸福的层面上,人本幸福主张追求幸福的道德,赞同“没有德行就没有幸福”,同时又坚定地提出“没有幸福就没有德行”。人本幸福“会带着微笑承认义务的囚衣是根据我自己追求幸福的命令,穿在我身上的”[1]561,实现幸福的条件也正是维持德行的条件。德性幸福的层面上,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不仅批判旧的神学,而且也为新的哲学留下地盘。幸福的存在者,是具有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的主体,费尔巴哈将此视为真正的和崇高的存在。这就使得人本幸福在剥离宗教虚幻性之后继续展现着一种德性幸福的超越性和崇高感。
重新审视“德福关系”只是《幸福论》所要完成的一项工作,另一项同样富有启蒙意义的工作就是对于德性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费尔巴哈通过自然主义的论证和生物学论证,赋予德性幸福更加面向现实生活的内容。传统的德性幸福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排斥自然物质需求、感性欲望满足,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则始终宣称食物、健康、生活、安乐和幸福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幸福不是别的,只是某一生活的健康的正常的状态,它的十分强健的或安乐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下,生物能够无阻碍地满足和实际上满足为它本身所特别具有的、并关系到它的本质和生存的特殊需要和追求。”[1]536这样,人本幸福就被解读为健康的、正常的、强健的、安乐的生活状态,费尔巴哈认为这种状态正是纯朴的、诚实的道德要求,而不是那些伪善的、道貌岸然的道德要求。
费尔巴哈甚至认为意志就是对于幸福的追求,人对幸福的追求是被自然界所创造和决定的。这样,人本幸福一方面使德性幸福具有了更多现实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使德性幸福的门槛不断被降低。费尔巴哈甚至直接宣称:“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1]591如此,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径直走向了感性主义、自然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批判费尔巴哈“把人追求幸福的欲望与动物本能等同起来,片面强调生命在生理意义上对享受幸福的重要性,忽视了生命在社会意义上对享受幸福的重要性”[5]399,并不难理解。 但是,费尔巴哈的意图也并非有意混淆人与动物的区别,或者轻视幸福的道德性与社会性,而是要猛烈攻击宗教虚无主义幸福观,使人的幸福重新归于现实生活。
在早已告别物质匮乏的现代社会,古典式德性幸福中压抑自然物欲、甚至禁欲的思想已经失去原有的意义。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重新审视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重新界定德性幸福的概念,实质上意味着对于古典德性幸福的改造与升级。在一定意义上说,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试图促成“没有德行就没有幸福”与“没有幸福就没有德行”的统一,以及促成“我思故我在”与“我欲故我在”的统一,从而为古典德性幸福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可能的致思路径,为现代德性幸福的世俗化和大众化开辟了可能的道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费尔巴哈批驳康德的伦理学不是为普通百姓而是为哲学教授们进行著述,而人本幸福所面对的则是零工、樵夫、农民和手工业者。
三、德性幸福的正义性向度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伦理实践中的重要现实课题。伦理思想的历史长河中,主流的思想家总是趋向于高尚的德性论或者幸福主义。从苏格拉底“正确的生活”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再到亚里士多德的“至善”与“幸福”;从原始儒家的“孔颜之乐”“君子之乐”到现代新儒家的“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德性幸福总是闪耀高贵人性的光芒。历史上的哲人不断地论证着、实践着“德福一致”的思想,或者不断地探讨如何化“德福冲突”为“德福一致”。以德祈福、以德为福,德福内在一致、德福外在相关,幸福是德性的酬报、道德是幸福的标准,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幸福的思想精彩纷呈、令人炫目。
费尔巴哈关于幸福的正义理论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也在内在的逻辑上拉近了幸福与正义的距离,幸福与正义显得如此地密不可分。“幸福吗?不,正义!正义是绝对相互的、或两方面共同的幸福;它反对旧世界的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或不公平的幸福。”[1]593正义与幸福几乎成为了同义词。只有社会中的成员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这个社会才能被称为是公正的。费尔巴哈认为那些平常的、在完成工作以后享受的与物质福利有关的幸福才是真正必要的幸福,这样的社会才是公正的社会,才能防止人陷入恶德和犯罪行为。真正的幸福,则必然是相互的、共同的幸福,而不是单面的、少数人的、利己主义的幸福。
宝清县在20世纪50—60年代,地下水资源组成为降水入渗补给量和地下水侧向径流补给量。地下水基本没有开采,地下水排泄以蒸发为主,侧向流出为辅;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开采地下水用于灌溉,但开采规模并不大;地下水资源量组成中,增加了井灌回渗补给量,但由于开采量小,所以灌溉回渗补给量所占的比例也相对较小。20世纪90年代年到现在,局部地段地下水开采增大,导致地下水水位逐年下降,地下水资源量中灌溉回渗补给量所占比例也逐渐增大,此外由于地下水水位下降,河流泄流补给量所占比例也不断增加。
比之于对宗教幸福的猛烈攻击,费尔巴哈对古希腊的德性幸福充满敬意。古希腊的伦理学充满着人性的光辉、进取的道德热情,对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取幸福拥有充分的乐观,这在无形中为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提供了丰沛的思想资源。“至善”的理想追求、精神幸福的强调、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思辨是最大的幸福,这些思想也构成了费尔巴哈幸福论的重要内容。“道德上的完善或完美,总是以存在本身的完善为题中之义,后者同时又构成了幸福的内容。”[3]273而对于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则较多地持批判的态度:“康德不注意幸福,而向人提出自为的义务作为目的;这或许有合理的教育的和道德的目的,但这并不表现任何形而上学的观点,即不表现人的相应的本质。”[1]592不难理解,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更加重视物质、健康、生命等现实生活的价值,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平民大众而非少数知识精英或者道德精英,实际上已经为现代德性幸福的世俗化和大众化做了富有启蒙意义的论证。费尔巴哈所要完成的,正是使德性幸福由纯粹、抽象而变得更加现实可及。
利己主义在伦理思想史上向来不被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被贬斥的情形比比皆是。费尔巴哈的《幸福论》要为利己主义“正名”,要为人本幸福开辟合理的空间和地盘。费尔巴哈的语言是风趣且犀利的,利己主义被形象地区分为“臭的利己主义”和“香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获得了深刻的论证。伪善的道德学家把利己主义看成是“对圣洁处女的玷辱、侮辱和耻辱”,正如费尔巴哈所指出的,这样就在道德中抹消了幸福的存在,而幸福的缺失也就意味着道德的虚无。因此,存在着一种健康的、人生所必需的、不可避免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是一种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诚实的道德,是内在于人的生命与生活的道德,然而这恰恰是被伪善的、道貌岸然的道德所指责的。
生存论的意义上,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存在者,自我肯定、自我维护本身也就意味着存在的完善性和正义性。“一个不幸的人甚至对不起自己,谁又能指望他去对得起别人?在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幸福的人更容易使别人也幸福,而一个不幸的人将更倾向于坑害别人。”[8]161不仅如此,费尔巴哈的利己主义幸福走得更远,人本幸福深刻指出个体幸福并非道德的目的和终结,只有与人共处的社会幸福才是幸福的正义论。费尔巴哈以家庭中父亲与家人分享生活资料为例,并援引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论证了利己主义道德也要求积极关心他人的幸福和不幸、也要求同甘共苦。“事实上,被思考为自身独立存在的个人的道德是毫无内容的虚构。在我之外没有任何你,亦即没有其他人的地方,是谈不上什么道德的;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因为只有你存在和与你共处,我才是我。”[1]571这样,在费尔巴哈那里,摒弃恶的、残忍的、冷酷无情的、任性的利己主义,实践善的、合乎人情的、具有同情心的、宽厚的、自我克制的、关爱他人的利己主义,构成了幸福公正性的主要内容。
人本幸福的正义性还体现在关于义务、良心的论述中。在费尔巴哈看来,那些对自己的义务与幸福的追求是很容易协调的,因为所谓的各种义务就是一些行为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正是为了维系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强健、安乐的状态,正是为了追求幸福而产生的。费尔巴哈批评康德强调义务忽视幸福,认为康德或许有道德教育的意图,但脱离幸福的义务并不能表现人的本质。现代德性幸福的理论中,一个公正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即是一个德行有用的社会,“德行不再仅仅是修身养性、令人赞叹敬畏的深谷幽兰,也不再是在外在强暴与欺骗下的麻木不仁,而是人们谋取现实利益的有效途径与方式”[9]152。人本幸福关于义务的论述可以被视为现代德性幸福中这些思想的先导。费尔巴哈还进一步论证了良心与追求幸福的一致性,提出良心既是自我幸福的代理者也是他人幸福的代理者,良心既立足于自己追求幸福的基础之上,也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需要;良心与同情心紧密相连,是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规则的确信与实践。
(3)提倡女性参加政治。秋瑾有较强的政治意识,提出妇女应当关心时政,拥有爱国思想。因为如果国亡,权利亦亡。保国,就是保权利。应把权利与义务联系起来,把女子尽义务,参与革命,作为争取女性权益的条件之一。岸田俊子首次以国家观念为媒介而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在这种国家观念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强烈的“爱国之情”。不仅如此,岸田还将矛头指向男性民权家,期待将女性解放伸张纳入到男性民权家的话语中去,以图谋求女权。
现在过敏体质的孩子越来越多,所以容易致敏的食物(比如水产海鲜)幼儿园很少会吃到。幼儿园很少安排吃水产品,即使吃,可能只是吃带鱼、虾这样好处理刺或没有刺的。而水产品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和帮助宝宝大脑发育的DHA,还有促进宝宝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锌元素。
四、德性幸福的超越性向度
在这其中,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却具有独树一帜的“另类”精神。人本幸福一方面毫不迟疑地承认道德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即“没有德行就没有幸福”;另一方面,费尔巴哈振臂一呼,喊出了伦理思想史上难得听闻的声音,这就是“没有幸福就没有德行”。这是德性幸福潜台词,耀眼的伦理学光辉下,德性的地位崇高,幸福的地位难免逊色。然而在实质的意义上,疏离或者淡化幸福的德性,往往流于空虚和抽象。“没有德行就没有幸福,这个话你说得很对,你是道德学家,我衷心地同意你,我已经这样承认你!但是,你须注意:没有幸福就没有德行,因此,道德就归属到私人经济和国民经济的领域中来了。如果没有条件取得幸福,那就缺乏条件维持德行。德行和身体一样,需要饮食、衣服、阳光、空气和住居。”[1]569 幸福化身为更加具体的衣食住行, 费尔巴哈提出生活上的必需品也就意味着道德上的必要性,于是生活的基础、幸福的基础也就构成了道德的基础。
所谓“超越”,就是不局限于当下现实的一种理想主义,要求超凡入圣,确立更加崇高的意义追求或者形而上价值。形而上的超越,要求“此时此地的东西和彼时彼地的东西、今天的现实和过往的历史以至未来的期待融为‘共时的’一体,从而形成一种境域或境界”,从而“人也就有可能超出个人的有限性,达到无限,达到自我超越”[10]230。费尔巴哈的《幸福论》批判佛教的幸福是病态的疯人和幻想的追求,批判基督教徒所追求的幸福像驴一样愚蠢、像猪一样在粪中辗转,批判康德由于忽视幸福而无法把握人的现实本质。这不仅更让人疑惑:人本幸福对于宗教来世幸福如此深恶痛绝并深刻批判,那么人本幸福自身是否还能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超越性?
费尔巴哈的答案是肯定的。在《基督教的本质》《宗教的本质》等著作中,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宣布人是第一性的,真正的宗教是人本学的宗教。基督教徒所谓的无穷的、无限的天堂幸福固然妙不可言,然而在现实的人世间,饮食的丰盛、爱情的美好、优美音乐的欣赏、道德自由的满足、思想的魅力,等等,本身也具有人性的高贵与崇高。人性是有限的,但人的意识对象却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人可以将现实人间的幸福无限性地外化,从而变成无限的、具有超越性的幸福。
在费尔巴哈看来,基督教的幸福观打乱思想演进的自然逻辑,认为人是第二性的东西,使本来平凡的东西具有了不平凡的意义,从而使原本一般的生活获得了宗教神学的意义。一方面,人本幸福则要把基督教所颠倒的东西重新扶正,使虚幻的天堂幸福回归人间,使神圣的幸福重新回归到人自身。这是人本幸福所要实现的一个方面,即“从无限者回归到有限者”。另一方面,人本幸福还要推动生命幸福、生活幸福不断上升,为了主要的幸福而放弃次要的幸福,为了高级的幸福而牺牲低级的幸福,按照无限的本质规定自身的幸福,完善自身的幸福。这就是人本幸福“从有限者上升到无限者”。
费尔巴哈引用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提出认识自己不是要自我抑制,而是要使人们认识到缺点和渺小,从而提高自我、改善自我,鼓励人们实现完善的、神圣的本质——上帝。“费尔巴哈通过人的幸福—道德—上帝的逻辑过程,通过将上帝理解为道德的完善存在,就逻辑地将人的幸福作为他心目中的上帝的目的,即,人的幸福生活是道德的最高价值依据与最高价值目的。”[11]238,239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看,“从无限者回归到有限者”是“神学下降为人本学”“从有限者上升到无限者”是“人本学上升为神学”;从超越性与世俗性的关系上看,人本幸福在一定意义上化解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冲突,促进了“超越性下的世俗化”与“世俗化中的超越性”的内在结合。
毛泽东心中的“中国梦”,既是强国梦,也是富民梦,梦想有一天把国家建设成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人民改造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人。虽然有时急于求成,忽视了客观规律,但是这中间透出了的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干事业就是要得“一股子劲”!抚今追昔,毛泽东为梦的奋斗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激励和一种希望。如今的中国日益强大,人民生活和民族素质不断提高,毛泽东当年的梦想有的已经变为现实,但人类追梦的过程永无止境,我们现在正聚气凝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只要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砾岩成分及结构成熟度低,大套砾石层夹多层薄层细砂岩,较多砂砾混层沉积。砾石粒径最大可达100mm,一般10~40mm,磨圆为次棱角—次圆状,砾石无定向排列。砾石成分为灰岩、白云岩,泥质、灰质胶结。砂岩单层厚度小于3m,其间多含炭屑,且多呈层状沿层面分布。薄片鉴定多为含灰质岩屑长石细砂岩及含泥质长石粗粉砂岩。砂岩成分主要为石英、长石及灰质和硅质岩块,以薄层细砂岩及粉砂岩充填在砾岩层之间,与泥质岩呈纹层状分布。
“超越性下的世俗化”与“世俗化中的超越性”构成费尔巴哈人本幸福的鲜明特质。此种幸福比之于宗教幸福显得更加现实可及,比之于快乐主义又显得更为高尚。在中西哲学会通的视阈中,人本幸福的这一特质似与儒家幸福观的内在超越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备受推崇的“孔颜之乐”中,儒者安贫乐道,通过德性主体的“学之乐”进而达到形而上的“道之乐”;在孟子“天人合一”的幸福观中,作为主体的人因为“尽其心”而“知其性”、因为“知其性”而达到“知天”的超越性境界。费尔巴哈与儒家的幸福均立足于现实人间,并不企盼彼岸世界的福乐,遥远的天堂幸福与极乐世界被视为虚幻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也是“内在的”,即为“内在于人世间”的生命幸福、生活幸福。同时,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也“内在于人自身”,就是使人的本质具有了无限上升的可能性。
“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就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12]31这样,思维着、爱着、希望着的存在者上升为完善的、属神的存在,神圣的本质就是人自己的本质。在费尔巴哈那里,一切真善美的意识,和一切幸福的意识,都是与人的本质的意识、存在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道德、幸福与人的本质存在内在关联,而人的本质又无限外化为神圣的价值,人本幸福由此而实现了内在的超越。值得一提的是,在理性、意志和爱的三位一体中,费尔巴哈最推崇爱,爱几乎成为随时随地都能创造奇迹的特殊存在。“爱,是完善的东西跟非完善的东西、无罪者跟有罪者、一般的东西跟个体的东西、法律跟心、属神的东西跟属人的东西之间的纽带、媒介原则。”[12]85因此,在费尔巴哈那里,爱是实现人本幸福超越性的重要纽带与媒介,爱连接着世俗的快乐与超越的幸福。人本幸福的超越性提升了世俗幸福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也促成了理想主义幸福观的高贵与崇高。
费尔巴哈的人本幸福论可以被视为现代德性幸福观的前奏,它在总体上逻辑地呈现了世俗性、正义性和超越性向度。对宗教幸福的猛烈批判是人本幸福论的重要使命,而人本幸福重新审视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重新界定德性幸福的概念,实质上也意味着对于古典德性幸福的改造与升级。费尔巴哈关于幸福的正义理论充满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内在地拉近了幸福与公正的距离,幸福与公正显得如此地密不可分。在世俗性与超越性的关系上,费尔巴哈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冲突,促进了德性幸福的世俗性与超越性的内在统一,“超越性下的世俗化”与“世俗化中的超越性”构成人本幸福的鲜明特质。因此,人本幸福论的意义不仅在于把人的幸福从虚幻的天堂重新拉回现实的世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典德性幸福的复兴,并对现代德性幸福的世俗性、正义性和超越性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
参考文献:
[1][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M].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德]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杨国荣.伦理与存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江畅.德性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冯俊科.西方幸福论:从梭伦到费尔巴哈[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孙英.幸福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高兆明.幸福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10]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1]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2][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Secularity, Justice and Transcendence of Modern Virtue Happiness:An Analysis Based on Feuerbach's Theory of Humanistic Happiness
ZHANG Fangyu
(School of Marx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Abstract: The fierce criticism to religious happiness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Feuerbach's theory of humanistic happiness. Feuerbach also profoundly criticized the classical virtue happiness. On this basis, he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modern virtue happiness. Feuerbach's view on humanism and happiness are likely to make a vulgar impression of hedonism, naturalism and egoism, but the logic of "Happiness-Moral", "Human-God" of his theory indicates that the purport of virtue happiness, rationalism and humanistic religion in his theory is not inferior. The significance of Feuerbach’s view of happiness lies not only in that it has brought people’s happiness from the illusory heaven back to the real world, but also in that it has promoted 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virtue happiness in a certain sense. And it has profound enlightenment value on the secularity, justice and transcendence of modern virtue happiness.
Keywords: Virtue Happiness; Feuerbach; Humanistic Happiness; Secularity; Justice; Transcendence
[中图分类号] B82;B516.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478(2019)05-0079-07
[DOI] 10.19649/j.cnki.cn22-1009/d.2019.05.011
[收稿日期] 2019-06-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家德性幸福的现代转型研究”(17BZX063)。
[作者简介] 张方玉(1977-),男,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杏坛学者”。
责任编辑:禚丽华
标签:德性幸福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人本幸福论文; 世俗性论文; 正义性论文; 超越性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