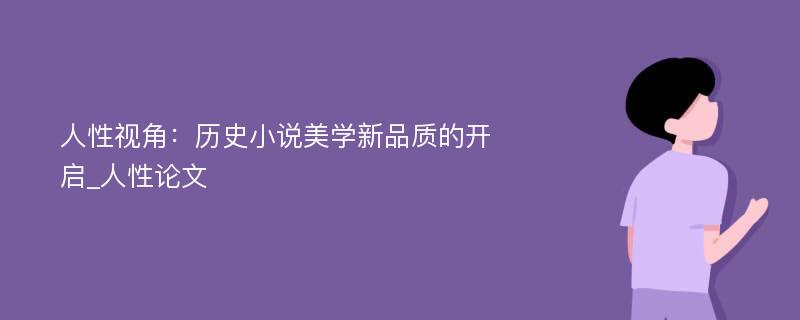
人性视域:历史小说美学新质的开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美学论文,历史小说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1)05-0125-04
一
不论从何种角度来考察新时期小说的整体发展态势,批评界早已确认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商业社会的逐步形成和进一步发展,小说创作所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文化消费的多元化和人们价值追求的物质化倾向使得文学人口以日胜一日的速度大量流失。但这一令人忧虑的境况在小说家族中的历史小说那里却是个例外:且不说80年代文坛繁荣兴盛时期,历史小说以其别具一格的审美特质倍受读者欢迎,就是进入社会经济、文化大转型、商业气氛日见浓厚而文苑渐趋凋零的90年代,历史小说依旧葆有对读者的吸引力,以文坛幸运儿的身姿受到广泛的青睐。
历史小说的走俏,既与大众读者对于历史故事的偏爱密切相关,也与身处变革时代的人们在潜意识中对于从历史演革中寻求可资当下文化建构参照的历史经验的渴求相关联,但更为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历史小说除了提供历史故事和历史经验外,作为以人为表现中心的文学作品,它还提供了种种文学化了的异彩纷呈的历史图景和众多个性化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那些置身于特定历史图景中的历史人物所显现出的与现代人相同或相异的人性形态,无疑是最令现代读者感兴趣的。虽然曲折离奇、波澜起伏的历史故事具有莫大的美学魅力,但这种魅力的形成,显然离不开故事中活生生的人物行为。事实上,正是人的丰富复杂的心理、情感活动所支配的人的行为的集合,才构成了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因而历史小说美学魁力的核心,还在于人性,在于特定政治体制、历史环境、文化环境乃至生活环境下的人性表现。这种被置放在某一历史情景中的人性表现,虽然在许多方面与今人有相通之处,如人的妒嫉、宿命、性爱、友谊、亲情、仇恨、理解、爱、尊重等人性因素在任何时代的人身上都存在,但由于生存背景的迥然相异,这些因素的表现形态就不可能与今人一致,而具有区别于现代人的独特形态。正是这种独特的人性形态的展示,才构成了历史小说的特殊魅力。
新时期之初,在人们尚未摆脱泛政治意识巨大阴影的时候,历史小说的创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当时意识形态下历史观念的束缚——历史的主体是由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与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的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构成的,这样的历史主体构成不仅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而且带有明显的群体性运动的性质。体现在历史小说文本中,便表现出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本身的关注,由历史事件铺衍而成的故事情节便成为小说文本的核心,而人物则仅仅起着贯穿情节、勾连事件的一种道具作用。仅存的一点有限的人性表现不仅被事件所遮蔽,而且受既有观念的影响,难免有概念化的痕迹。如《金瓯缺》和凌力早期作品《星星草》等。这些作品所形成的着重于写历史事件的创作模式到80年代仍被继续延用,虽然一些作品已逐渐将重心移向对人物的描写,但尚未完全摆脱在写历史中附带写人物的模式。如李晴的《天京之变》、顾汶光、顾朴光的《天国恨》、鲍昌的《庚子风云》、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等,作家历史书写的落脚点依然是放在历史事件和故事上。这不仅仅是作家历史观使然,同时也是作家人性意识觉醒程度的反映。真正实现从写历史中的人物到写人物的历史的创作取向大转变的,则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历史小说创作。
90年代商品经济的汹涌大潮,在带来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物质繁荣的同时,对于80年代已经松动的传统理性框范又一次构成新的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的力度之大,使传统的道德理性、观念理性和价值理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社会现实存在必然会诞生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观念意识,人们道德感的淡化和趋利意识的强化,形成了这个时期人的价值理念演变的总体趋向。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中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共存格局的形成,导致人们道德准则、价值准则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现实特征存在。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和精神氛围里,不仅人性的表现有了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形态,而且人们对于现实人性乃至整个历史、文化所持的观照视角也有了新的变化,变得更开阔、更具有人性意识和人性深度。这一切必然要对作家的审美观念、审美取向产生深刻的影响,反映到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中,便表现出审美着眼点的移变上。作家不但将目光投向在既往的历史视野和观念中被视为体现着人性负面因素的反面人物,而且对这些人物身上存在的人性的正面因素也给予充分的表现,同时对身处复杂历史情状中的历史人物之人性形态的表现亦有新的突破,从而使历史小说在人性描写上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更为恒久的审美价值。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寒波的《龚自珍》、《刘鹗》、《石达开》、陈斌的《李鸿章》、李全安的《左宗棠》、巴根的《僧格林沁亲王》等历史小说;凌力的《倾国倾城》、《少年天子》、《暮鼓晨钟》、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颜廷瑞的《庄妃》、吴因易的《明皇系列》(四部)和《则天皇帝系列》(四部)等帝后系列小说,均对风云际会、波诡云谲的历史烟尘中的人物进行深入的人性描画和开掘,为新时期小说的人性绘写提供了一幅色彩斑澜、摇曳多姿的艺术画卷。
二
为了便于对历史小说的人性描写有一个更清晰、更突出的认识,我们将主要就90年代出现的部分有影响的历史小说作品进行考察分析。在文学作品中,人性描写事实上就是对特定环境中具有个性特征的人的欲望、心理和灵魂的逼近和把握。就历史小说这一特殊的小说门类而言,其人性描写通常要求作家首先进入所叙写时代的历史情景(这是就一般的、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言的,新历史小说即先锋小说不在其列),然后再进入这一历史情景中人物的心灵世界,实现这两个层次的进入是历史小说能否具有成功的人性描写的重要条件。除此之外,当然还需要作家拥有不囿历史成见和艺术传统的独到的观照人物、洞悉心灵的角度。惟其如此,历史小说才能产生具有深厚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
唐浩明的《曾国藩》由于摒弃了泛政治意识时代对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的既成看法,而依凭诸多史料绘写出曾国藩的真实的历史面貌,这其中虽然也有因对史实史料的拘泥而未能更充分地发掘这一人物的人性内涵,但曾国藩所处的晚清社会风云际会、矛盾重重的历史时代和文化氛围,必然形成他极为复杂微妙、深邃难测的心灵世界,这就为人性描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任何一个文学形象,其人性蕴涵的丰富与否,通常与人物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如能力、气质、性格)的突出程度以及个性意识倾向(如需要、理想、信念、价值观等)的强烈与执著程度有着直接的关联。人的诸多心理和行为表现事实上是个性心理和个性意识倾向的外在现实表现,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越鲜明突出,个性意识倾向越强烈,在其面对现实世界时,尤其是在面对错综复杂、矛盾交织的现实境况时,越是可能演绎出莫测难辨、繁复多姿的人性形态来,从而表现出丰富的人性内容。
在《曾国藩》中,唐浩明抓住了曾国藩这一历史人物的最主要的特征作为其人性表现的切入点,通过他着力绘写出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特征,从而提供了一个有着丰富人性内涵的人物范型。要展呈体现于曾国藩身上的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并且进而揭示出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个人性特点,显然离不开对这一人物独特的极富个人性特点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价值理念、精神世界的深入细致的摹写。个性心理特性和意识倾向是形成区别于他人的人性形态的关键的、基本的因素。唐浩明正是从对曾国藩独特的个性心理和意识倾向的悉心着墨与精心铺写的基础上,绘状出体现于人物身上的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人性形态。
出身于地位卑微的农民家庭的曾国藩,其童年生活环境的贫寒使他对自身地位的低下有明确的意识,天姿聪颖的他自然不会甘于这样的现实,出人头地的欲望自幼就埋藏于胸。随着他学识才能的增长,随着他政治视野和人生视野的扩展,其在仕途上向上攀援的欲望日趋强烈,逐渐成为其人生追求的一种内在动力。同时,由于曾国藩自幼便受到儒家学说的侵染,儒家的入世思想正好强化了他改变现状、建功立业的人生欲望。他博学多才,广为吸纳各家学说,曾拜一代名师唐鉴攻理学,对法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亦不生疏。这使他不但成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成为传统文化的实践者、承传者和捍卫者。于是,曾国藩早年所萌生的单纯的人生欲望与其后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意识便实现了一种内在的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可能是密契无间的——自我的人生愿望不可能与传统儒家文化在所有的价值取向上相一致,即便是儒家文化本身也充满着内在的矛盾性。在此我们已能看出曾国藩在人格结构和人性形态上的基本轮廓,而这一人物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丰富的人性内容,都是源于这一基本的人性形态的,其人性表现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是由于基本的人性形态在面对变纪莫测的人生遇际和冷酷险恶的官场权变时的一种心态调整与灵魂搏斗的表现。
在作家笔下,曾国藩的人性构成中,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奋斗意志所构成的价值理想与对谦恭和蔼、仁爱诚信的人格境界的自觉追求所构成的道德理想是同时共存的。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我们不难看到,在曾国藩身上价值理想是高于道德理想的。当道德理想与价值理想相一致时,他可以把道德表现得非常完美;而当道德理想与价值理想发生冲突,妨碍了价值理想的实现时,他便会毅然舍弃道德理想,以确保价值理想不受损害。这种反映了曾国藩深层个性心理特征的信念,往往会导致道德理想与价值理想的冲突与矛盾,从而表现出他外在人格行为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太平天国的无情剿杀和冷酷凶狠上。在他眼里太平天国被视为违儒家正统思想的草寇流民,他们的作乱起义行为是大逆不道的。因而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一改他平日的儒雅风度和仁义情怀,不仅使尽刻毒奸险的心机诡计,而且手段凶残酷毒,毫无怜悯之心,与他儒雅的一面形成极大的反差和强烈的对照,几乎判若两人。这两种有着极大反差的性格表现,事实上仍是曾国藩内在道德理性与价值理性激烈冲突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冲突才构成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三
历史题材小说中,绘写天子皇帝是一个特殊的领域。皇帝作为一国之君,不仅体现着封建时代至高无上的赫赫权势与威仪,同时还象征着一种超尘脱俗的荣华富贵。但这一切可为人们体会和想象得到的关于皇帝的概念,其实只显示着皇帝外在的、人们观念中的形象内容。而事实上由于具体的历史情状的复杂性和具体的某一个皇帝所具有的特异天性,皇帝并非都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而是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在人们一般观念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然而就某一个具体的皇帝而言就不尽然:种种政治的、经济的因素常常会困扰着皇帝,使他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活动受到来自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当然作为帝王在许多方面又可以不受约束),这就使得皇帝在面对这个世界时,他所持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就往往显得与众不同。这种不同虽然有天性所使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面对复杂的现实情境时不得不对自身进行调节的结果。凌力的《少年天子》可以说较好地把握了历史描写与人物描写的关系,透过顺治皇帝福临这个少年天子形象,揭示出深刻的人性内涵。
就《少年天子》中顺治皇帝所处的历史时代而言,同为帝王,福临所面临的政治难题、宫闱权变、社会民族矛盾显然要比太平盛世时期的王朝复杂得多。于是,在福临身上,作为帝王的社会角色和责任与作为一个人的情感和愿望之间的矛盾冲突便显得格外激烈、突出。凌力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不遗余力、浓墨重彩地加以表现。这位少年天子所处的历史情境,事实上是一个只能产生悲剧的时代环境,偏偏这位少年天子又有那么多宏大的理想、那么炽热的情感,却唯独没有承受人生挫折的坚强意志。他想推行“满汉一体”这—在当时有利于巩固清王朝统治的政策,却遭致满族大臣的竭力抵制;他想变后宫祖制,亦招来种种不满和怨恨,导致一系列后宫事件;接踵而至的挫折,带给福临的是深重的心理阴影和精神负累。由此人们不难想象出这位年轻皇帝在其短暂的24年生涯中,当他从多的理想抱负竟然无一能圆满实现时,内心深处该会有怎样的浩叹,尤其是在抗拒这些失败的过程中,其身上的种种人性因素该会有怎样的纠葛、撕缠和搏斗。
作为同是描写帝王的小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以更为宏大的规模、更加多彩的笔墨展示了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性形态。当然,由于作家创作观念、审美追求不同,同样涉笔帝王描写,甚至写了同一个皇帝(凌力《暮鼓晨钟》写少年康熙),其表现的人性形态及人性内涵也就不尽相同。凌力的历史小说,虽然体现着以写人为中心的特点,力图以各种艺术手段描绘出有着完整的人性构成和丰富的人性蕴涵的人物形象,但她事实上在对历史材料的运用方面,还是持传统的较为严肃、严谨的态度,在创作风格上,也体现出高雅文学的品位。而二月河关于历史小说的创作观念则与凌力不尽相同。对于史实与虚构的关系,二月河抱持这样的观点:“我既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性,又忠实于艺术的真实性。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我在总体上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历史细节的描绘让位于艺术的真实性;当读者与专家发生矛盾时,我尽量的去迎合读者,历史小说允许虚构。”[1]很显然,对于艺术真实性的偏爱和读者审美趣味的注重,成为二月河创作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取向。但面对历史素材,作家以怎样的方式来把握历史、进入历史,怎样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美学内涵与人性内涵。二月河认为:“历史小说创作者既不能抱取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和不介入的态度,也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与现实社会毫不相干的东西,要把自己投入进去。找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脉息,让历史真正活起来,既让读者感到真切、地道,又让读者有所鉴戒和教益。”如果说凌力是循着历史的印迹去全面再现作为完整的真实的人而不是观念的人的人生道路的话,那么二月河则是打通了现实与历史的联系,接上了现实的人与历史的人之间的人性脉息,既考虑到历史情境中的人受当时客观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制约与影响,又将今人的某些情感、观念渗透于历史人物的塑造,使历史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形态,不仅具有那个时代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规定性,而且蕴含着现实人在情感、意识方面所具有的某些特征。这是作家迎合读者口味的结果——当代大众读者不单是想从历史小说中看到不同于现实的社会人文风貌,而且渴望在历史人物身上寻觅某种精神和情感的共鸣点。基于这样一种审美追求,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在人性表现上便显示出其独特的内涵。
《乾隆皇帝》(六卷)虽以其浩繁宏大的篇幅着重表现了一心开创清王朝盛世的乾隆,如何壮怀激烈、励精图治、宵旰勤政、执着坚韧,精心绘写出一个睿智聪颖、机敏能干、气度不凡的帝王形象:不论是审时度势、竭力推行“以宽为政”的方针,以期通过实行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殚精竭虑为平定边疆而进军大小金川、为肃清叛乱而调兵遣将追捕白莲教女首领“一枝花”;也不论是任人唯贤、破格起用年轻有为的官员,还是为整肃朝政,惩治贪官腐败毫不心慈手软,都充分显示了乾隆作为一代明君所具有的雄才大略、胆识魄力与人格品性。这无疑是乾隆身上最主要的人性光采——他在一国之君这个角色位置上淋漓尽致地施展了他的政治才干和智慧。但乾隆作为一个帝王并非时时刻刻都埋头政务、思考治国兴邦之策,政事之外,皇帝的生活有着多方面的内容,读书、吟诗、听戏、书法、骑射、闲游、私访、寻花探柳等等,不论与治国有无关系,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呈现出人物的人性光采来。事实上在《乾隆皇帝》中,作家确也花费了相当的笔墨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乾隆。这方面的描写,虽然既有与政事相联系的,也有纯属一己私情的,但都对乾隆形象的表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之更为血肉丰满,更具有耀人眼目的人性光采。
《乾隆皇帝》在对帝王的描写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彻底摆脱了人们对于帝王的既成观念的束缚,摒弃了写帝王之性情必处处体现帝王之尊贵威仪的模式,而将帝王视同普通人,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只是帝王所处的环境、地位与常人不同而已。在这样一种创作观念的支配下,我们看到的乾隆皇帝就不仅有威镇四海的皇权尊严,也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充分显现出作为真实历史情境之中而不是观念形态中的皇帝形象,使人物拥有更为丰富的人性内涵。乾隆一朝曾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围剿殄灭与朝廷对抗的女教主“一枝花”,然而正是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江湖女杰,不但与追剿她的乾隆有过奇特的相遇,而且有一番曼幻迷离、推心置腹的交谈。对于胸怀壮志、励精图治的有为君王乾隆来说,对“一枝花”这样的逆匪本不会心慈手软,但当他结识并知晓了对方的身世后,便产生了特殊的情感态度。一方面是国法之理,另一方面是异样之情,在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中,乾隆选择了情(当然这种选择是以“一枝花”隐居不再危害朝廷为前提的,只是不治罪对方而已)。这种选择尚不能从徇私枉法的角度去理解,乾隆显然不会以牺牲王朝的安宁作为满足一己情感需要的代价。“一枝花”的身世之所以能唤起他深切的悲悯之心,表明这位君王不仅有着刚毅果决的王者品格,而且有着体恤弱者的深厚的同情心。“一枝花”非同寻常的经历铸就出的特殊气质固然是引起乾隆注意的重要因素——这种气质带给乾隆的是一种迷离莫测的神秘感,从而勾起这位探知欲望强烈、情感丰富的君王的莫大兴趣;但真正使乾隆心生怜悯之心的,是“一枝花”独特而悲凄的身世。这种怜悯之心透露出的是作为帝王的乾隆精神情感世界的独特一面:这位性情中人的君王,对于情谊情意的倚重有时会超越世俗理性的层面,进入一种超拔于一般社会准则的精神境地,体现出乾隆非同一般的个人情怀与心灵世界。由此所显露的人物之人性内质便显而易见了。
综观唐浩明、凌力、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我们不仅看到了作家如何在历史的特定情境中去把握人物的人性形态,同时也看到具有不同创作观念和人性认知的作家,在人性表现上所体现出的不同角度和特点,从而拓展了人性描写的空间,丰富了作品的人性内涵。相对而言,唐浩明、凌力的作品在对史料的运用上较为严谨,注重于历史感的体现,基于这种观点而创作的作品,就人性表现而言,就带有明显的属于那个时代社会条件的种种印痕,是人的一般本性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的具体显现。曾国藩、顺治皇帝福临各自身上所体现出的复杂、矛盾的人性内质,除了他们与生俱来、异于他人的个性心理特质外,还与客观外在条件,即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二月河的小说,虽然也忠于历史的真实,但由于他奉行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发生矛盾时,“尽量去迎合读者”的创作准则,这就使他的虚构在一定程度上稍有偏离历史的真实,但这种偏离在损害历史感的同时,又有其扩展想象的自由度、充分发掘人性内涵的艺术作用。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因此也就区别于既往的同类作品,在全面地、多角度地展示帝王形象所包孕的人性内容方面,显现出其独特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6-11
标签:人性论文; 二月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乾隆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少年天子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曾国藩论文; 凌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