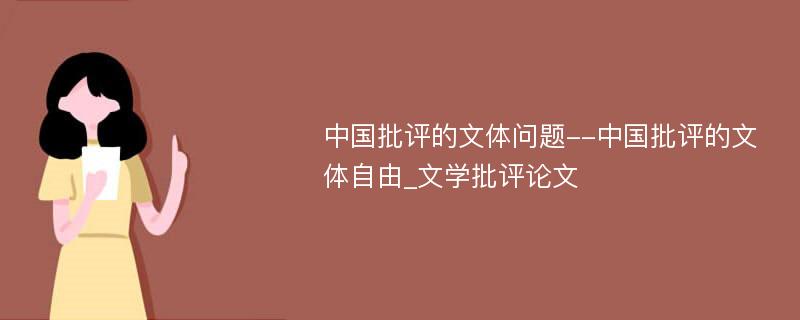
汉语批评的文体问题——汉语批评的文体自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文体论文,批评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体自由”即批评家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文体来书写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古代批评家的文体自由是如何获得的?文体自由对于文学批评的意义何在?文体自由在现当代文学批评中遭遇到何种命运?这种命运给予我们何种启示?这些,正是本文要探讨的。
一、 “文体自由”的获得
朱光潜在评价维柯《新科学》的“历史方法”时指出:“事物的本质应从事物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来研究。”①在某种意义上说,事物的起源影响甚至决定事物的本质及其特征,“文体自由”作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本质性特征,她的产生或获取,是由批评文体在其滥觞期的“寄生”和“外借”形态所决定的。
先秦文论没有自己的批评文体,其文学批评只能以只言片语的方式寄生于经、史、子、集之中。“诗言志”是中国文论开山的纲领,它寄生于《尚书》之《尧典》;“季札观乐”是对“诗言志”的极好说明或展开,它记载于《左传》之襄公二十九年;原始儒、道的文艺思想,则分别散见于《论语》、《孟子》、《荀子》与《老子》、《庄子》等;《诗经》的一些篇什中亦有文学思想,而且采取的是被后人称之为“以诗论诗”的方式。我们知道,《尚书》是五经之一,《左传》是史书之首,语孟老庄是子书,《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可见先秦经、史、子、集中皆有对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的言说;或者反过来说,先秦文学批评皆寄生于“它者”(经、史、子、集这些非批评文体)之中。经史子集是传统的分类方法,若依照现代的分类方法,则先秦文论言说所寄生的文体可谓多多:诗歌体、对话体、语录体、寓言体、史传体、议论体等等。
汉代文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诗经》和《楚辞》,故汉代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是《毛诗序》、郑玄《诗谱序》、班固《离骚序》、王逸《楚辞章句序》等。就文本的外观和内质而论,这些“序”均可独立成体,而且是专门讨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问题,已经不属于先秦式的寄生性言说。但是,“序”这个文体在汉代是经学和史学的附庸②:诗之序是《诗经》的传注,骚之序则是依经立论;而与文学批评相关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史记》、《汉书》中志、传之类的短序,则是汉代史籍的组成部分。因此,从文体分类的角度来考察,“序”这种文体是汉代文学批评从“经部”和“史部”那里所借来,或者说是汉代文学批评的“外借”式言说。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在“序”这种外借文体中,亦有“寄生”成份,如前述《太史公自序》并非独立完整而是片断式的文学批评言说,其它如扬雄《法言序》、王充《论衡·自纪篇》等子书的序亦属此类。由此可见,“寄生”和“外借”成为先秦两汉文论之批评文体的主要形态或方式。
中国古代文论,在其滥觞期“文体寄生”和“文体外借”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了汉语批评的文体自由;或者这样说,因为滥觞期的文学批评书写所寄生的母体所外借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一种文体,故此特征从源头和根基上赋予古代批评家以文体自由。从事诗文评写作的批评家,一旦获得这种“文体自由”便爱不释手,即便是到了文体意识日趋成熟、文体分类日趋精细的时代,批评家们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文体自由。
汉魏之际,曹丕作《典论·论文》,既从体制(体裁)层面区分“诗赋”与“书论”,又从体貌(风格)层面区分文学性之“丽”与论辩性之“理”。西晋陆机作《文赋》,因“体有万殊”、“为体也屡迁”而将文体一分为十,并指明各体“殊”在何处,“迁”往何方,比如“诗缘情而绮靡”,“论精微而朗畅”,他自己就有“缘情”的《赴洛道中行》和“精微”的《辨亡论》。稍后,挚虞《文章流变》和李充《翰林论》的文体分类均有十多种。到了刘勰《文心雕龙》,用后来《四库总目提要》的话说,干脆就是“穷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刘勰的文体分类依次有三个层面:首先将所有的文体划为“文”与“笔”两大类,然后在文类与笔类之下再分为总共33种文体,最后在每一种文体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比如“论”体,向上,它属于无韵之笔;向下,它依据其功能的不同又可分为陈政、释经、辨史、诠文四条流,其中“诠文”之“论”大体上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
深谙文体理论的魏晋南北朝文论家,本应按照他们所制定的分类原则来使用不同的文体,诗赋归诗赋,书论归书论:有韵之诗赋用之于创作,无韵之书论用之于批评。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如果说曹丕的《典论·论文》用的是无韵之“论”体,而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用的则是有韵之“赋”体和“骈”体。较之曹丕,陆机和刘勰有着更自觉的文体意识和更细密的文体分类,可是陆、刘二人在文体的使用及实践之中并不贯彻他们自己制定的文体规则和理论。为何如此?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受早期文论“寄生”和“借用”的影响,批评家不愿意放弃自己已经获得的“文体自由”。
依照《四库全书》的分类,集部中的诗文评是严格意义上的批评文体,而《四库总目提要》诗文评部分所标举的范例所辑录的文本大部份是诗话③。尽管诗话体成为六朝之后批评文体的大宗或主流,但历朝历代的批评家仍然拥有自己的文体自由,诗体、赋体、骈体、书信体、史传体、史志体、序跋体、选注体、评点体……批评家仍然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文体来书写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直到清末,直到民初。
二、“文体自由”的价值
古代批评家为什么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文体自由”?因为文体自由对于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批评家的理论构建、学术创新和风格形成等诸多方面。
前面谈到,刘勰的那个时代,文体理论已经成熟,包括刘勰在内的批评家已经具备自觉的文体分类意识,《文心雕龙》已经将文学性的乐府诗赋与理论性的诸子论说区分得清清楚楚。可是刘勰却偏偏选择用文学性的骈体来撰写他的理论性著作。为什么?刘勰看出他那个时代批评家的“各照隅隙”、“密而不周”之病,看出那个时代文学理论的“碎乱”、“疏略”之弊。年青的刘勰立志遍照衢路,弥纶群言。要实现这一目标,骈体应该是最好的选择。《说文》曰“骈,驾二马也”,段注“骈之引伸,凡二物并曰骈”④。一位文论家,要想建构宏大的体系就不能“东面而望,不见西墙”,要想实施精深的理论分析就必须笼圈条贯、擘肌分理——骈体正好能做到这一点。以“辨”为中心、以“对句”为语言形式的骈体成全了刘勰,帮助刘勰“骈”出范畴术语的对立统一,“骈”出文学思想的体大虑精,“骈”出《文心雕龙》辩证而慎密的文论体系。
如果说,刘勰选择骈体是为了他“体大虑深”的理论建构;那么,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选择诗话体则是为了立异标新。钟嵘与刘勰大不一样:刘勰是正统的是建构的,钟嵘是反叛的是解构的;刘勰要惟务折衷,钟嵘要标新立异。钟嵘的心里装满各种各样的怪念头:沈约的声律说伤了诗歌的真美;有滋有味的诗都是不用典故的;比兴用得太多读起来就不顺畅;曹操的诗歌只能列为下品……钟嵘又是有才藻有个性有真义有深情的,“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以他要选择能诗能歌能散能骈能笑能哭能褒能贬的诗话体。诗话体不仅安放了钟嵘的怪念头,驰骋了钟嵘的新思想,而且铸成了钟嵘独特的批评风格。诗话“体兼说部”⑤,其源头在笔记小说,与子部的“小说家”同类。用庄子的话说,“小说”者,其于“大道”远矣,故无须明道载道,亦无须美刺教化,这样的文体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因而也更容易出新。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书信体,尤其是写给至亲好友的书信,不用小心翼翼地走中庸路线,更不用端着架子讲大道理。亲友之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不敢说?胆子一大,真话就出来了;真话一出口,新意也就跟着出来了。比如,曹丕《与吴质书》的“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曹植《与杨德祖书》的“南威之容”、“龙渊之利”,韩愈《答李翊书》的“气盛言宜”,以及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新乐府理论等等,都是颇有新意的。
汉语批评的文体自由,说到底是批评家思想表达和人格诉求的自由。因此,从批评主体的角度论,文体自由的获取和拥有,有利于批评风格的形成。18世纪法国文论家布封那句著名的“风格即人”,其实也可以翻译为“文体即人”。《四库总目提要》则将文体称之为“体貌”⑥。论诗诗典雅而清丽,论文赋精巧而细密,诗话词活鲜活而闲适,小说评点灵动而犀利,史传序跋事信而理切,书信日录情深而语长。比如,同为唐代的文论经典,陈子昂《修竹篇序》扬其清刚,杜甫《戏为六绝句》含其雅润,皎然《诗式》体约而不芜,白居易《与元九书》情深而不诡。又比如,同为小说评点,李贽评《水浒》愤怒而真率,金圣叹评《水浒》诙谐而细密,毛宗岗评《三国演义》雄辩而尖锐,张竹坡评《金瓶梅》通俗而流畅……这些评点文字的独特风格和魅力,借用李贽的话说:“若令天地间无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⑦刘永济说:“《文心》一书,即彦和之文学作品矣。”⑧古代批评家文体各异的文论著述,也是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后人在阅读中可以同时获得理论之熏浸与审美之愉悦,这正是今天的批评文本所匮乏的。
三、“文体自由”的丢弃与守望
20世纪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理论和批评)大势,虽然有“西方化”与“中国化”之争,但基本趋向是前者而非后者。就汉语批评而言,不仅“说什么”(言说思想)层面的命题、概念和范畴以西学为准的,而且“怎么说”(言说方式)层面的体制、语体和体貌同样是以西学为矩臬。文学文体的分类,基本上是西方文论“四分法”(诗歌、小说、散文和戏曲文学)的天下;而批评文体的分类,因其类别单一根本就用不着分类。在西学东渐的百年进程中,汉语批评逐渐丢弃了自己的文体自由。
我们知道,无论是“文学理论”(或曰“文艺学”)还是“中国古代文论”(或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化和科(课)程化,都是“现代性事件”,都是20世纪西方学术制度东渐的产物。西学百年,汉语批评对强势话语的顺应和对自身传统的中断,在形成学术制作和传播之现代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文学批评书写的格式化。现代批评家尽管在研究对象、学术兴趣、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气质类型、语言特性等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他们大体上都会选择相同的文体——论文(著)体——来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写作。就文体样式(体制)而言,古典批评是“文备众体”,现代批评是“一体独尊”;就汉语修辞(语体)而言,古典批评是“文学性”弥漫,现代批评是“哲学化”统驭;就批评风格(体貌)而言,古典批评是“其异如面”,现代批评是“众体同貌”。虽然论文(著)体有它的长处(如层次清楚、格式规范、便于发表、便于评奖等等),但如果所有的批评家(专业或业余,年长或年轻,女性或男性,理性或诗性)都在往相同的文体格式里填充思想时,思想就可能被格式化,理论创造就可能沦为为理论制造。
20世纪以来,当大多数批评家自觉不自觉地放弃“文体自由”时,仍然有对“文体自由”的守望者。如果说,对“文体自由”的放弃导致了批评文体的格式化;那么,对“文体自由”的守望,则成就了批评文体的现代经典。以钱钟书的文学批评为例,他既用当时通行的论文体(如《七缀集》以及《人生边上的边上》的部分论文),也用古代流行的选注体和序跋体(如《宋诗选注》及序),而堪称现代批评经典的则是集诗话体、评点体、笔记体于一身的《谈艺录》和《管锥编》。钱钟书自称《七缀集》所选录的是“几篇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⑨,虽说是谦词,却也道出作者在选择批评文体时的那种不拘中西、不屑古今的自由心态。
现代批评家对文体自由的守望,依次表现在体制、语体和体貌三个层面。就体制论,有王国维的词话体批评、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钱钟书的谈艺管锥体批评等;就语体论,有周作人的学术美文、朱光潜说理而深于取象、李健吾的鉴赏式感悟式批评等;就体貌论,有鲁迅的建安风骨和卓吾体貌、宗白华的诗画一体和散步风格、沈从文的抽象抒情和印象复述等。站在21世纪的低谷,仰望上一个世纪的文学批评巅峰,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但凡能够称之为20世纪文学批评大师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守护着自己的“文体自由”。由此亦可见出,汉语批评的文体自由有着何等顽强的生命力和何等巨大的影响力。
钱钟书将古代批评家的文体自由喻为“侵入扩充”,《谈艺录》论及“文体递变”时引宋人林光朝(字谦之)《艾轩集》辨韩柳文体之别:“林谦之光朝《艾轩集》卷五《读韩柳苏黄集》一篇,比喻尤确。其言曰:‘韩柳之别犹作室。子厚则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即余前所谓侵入扩充之说。”⑩韩愈敢于“侵略别人田地”,打破不同文体之间的区囿或界域,“惟意之所指”,在诗与文这两类文体之间自由出入。韩愈的诗歌创作是“以文为诗”,而他的批评文体书写(如论诗诗)则是“以诗为文”,是别一种意义上的“侵入扩充”。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古代批评家如果没有“侵入扩充”的才胆识力,汉语批评也就不会形成“文体自由”的传统。而20世纪以来真正创造出现代批评经典的文论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没有放弃汉语批评的文体自由,均有不同程度的“侵入扩充”。同处21世纪学术大跃进之中的文学批评的作者和读者们不知有没有想过:那些发表于权威或核心刊物的文体规范的论文,那些出版于国家级或省部级出版社的文体规范的论著,有几篇(部)能逃脱覆瓿的命运?当成千上万的批评家都按照统一的模式生产批评文章时,还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吗?
注释:
①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2页。
②褚斌杰先生认为,“序的正式出现大约由汉代开始”,见《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390页。
③⑤⑥参见《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779、1779、1781页。
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65页。
⑦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0页。
⑧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前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页。
⑨钱钟书:《七缀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⑩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页。
标签:文学批评论文; 文学论文; 文体论文; 四库总目提要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谈艺录论文; 刘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