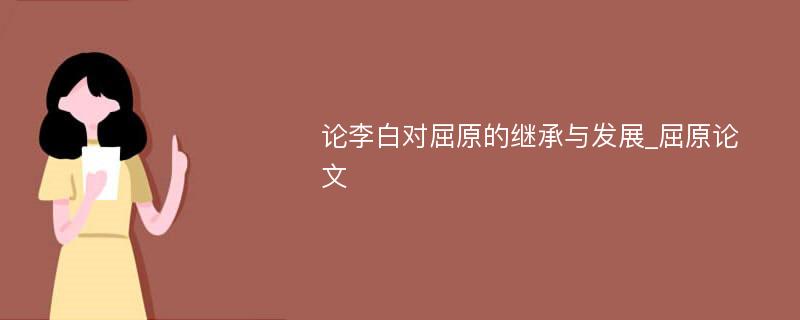
论李白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李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屈原和哥白尼、拉布雷等四人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几年以后,李白也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尽管这只是某个国家或地区性的推举,但不可否认其合理的成份,屈原和李白都是具有世界意义、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屈、李齐名”说,但屈、李早就被公认为两大浪漫主义诗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当然,由于时代、心理、性情不同,他们的创作又存在着多重差别。本文拟对屈、李异同及其传承关系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理解与认同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代,他的谪仙之才和自由放达的性格使他在政治上获得了优厚的礼遇,名响东亚,虽没有成为治国之器,但唱出了地道的大唐帝国的盛唐之音。李白力排齐梁以来的艳丽诗风,他在《古风》中喊道:“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对六朝轻柔香艳的审美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历代文坛武库的开掘,而是对前代的创作进行了科学的审视与合理的借鉴。他从那里吸取有价值的成份,丰富启发深化拓展自己的创作。李白对大诗人屈原就采取了理解与认同的态度,从而形成带有骚体基因、具有盛唐风范的浪漫主义创作特色。
李白《将进酒》诗说:“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饮酒的作品,往往是他最辉煌的诗篇,他对古来圣贤积极进取,不愿醉世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屈原是自称世人皆醉我独醒,李白却要长醉不醒,虽情在酒之二极,但却有着相通的意韵。关于古代圣贤,李白在《行路难》中有进一步的表述:“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即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这道诗表现了路的情结。他要追求永恒的生命之路,而成与败是历史的选择,非圣贤个人所能为也。故他求醉,以避“明时”。说明诗人深谙人生之路的真缔。他笔下的圣贤不是三皇五帝,而是弃江的子胥、投水的屈原,体现了他对屈原的高度认同与理解。对屈原的创作成就,李白给予很高的评价:
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篇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这首题为《江上吟》的作品一般认为是早期游江夏时的作品。屈原晚年常在江夏流浪,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和美丽的诗篇,李白睹物思人,情接千载,给屈原以很高的评价。诗句用屈原《涉江》中“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争光”句意回认,体现了他对屈原作品的钦佩。“楚王台榭空山丘”,则对屈原不幸表示深切的理解,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与奚落。李白还对楚国的历史进行了纵览。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说:“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犹来贱璞。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此与屈原“荃不察余之衷情”用意很象。表现出他知音难觅、尽忠遭嫉的处境和超然出世的主张。不仅对屈原,对整个骚人集团,李白都给予中肯的评价与认同。他在《古风》中还说:“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认为,由于朝廷的腐败,没有正声,所以文士哀怨,便有了骚人,对骚音的缘起进行了分析,指出时代与文学的关系,表达了与屈原、司马迁一样的看法,符合历史实际。
尽管诗人大力从前代创作中获得营养和诗兴,但不是随意取舍,而是有选择的。李白不喜欢死读“四书”“五经”,他的《朝鲁儒》云: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向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到,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未先达,归耕汶水滨。
李白漫游山川古迹,思接千载,往往从中获得诗兴。《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就说:“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其诗对鲁儒的迂腐无用进行了讽刺,肯定地表示与他们不是同类。李白从孔丘故里和屈原旧踪中皆获得诗兴,但取舍态度截然相反,表现了他对屈原的热爱与敬重。这种感情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表现得更加明确:“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把自己看作超脱凡尘的楚狂,不仅是对屈原的敬爱与吸收,他甚至作了根的认同。他表示“五岳寻仙不辞远”,情“愿接卢敖游太清”,把自己打扮成孤傲不群的楚仙。无论是史实的判别,还是文学的评价,人生的观念,李白对屈原都表现了高度的认同和理解,达到了心灵的沟通。所以李白的浪漫主义的根就在屈原和楚辞的历史沉淀之中。
二、自我形象及感情趋向
古代浪漫主义的诗人在万物归怀以后,审美心理往往膨胀为极度感伤的狂放忧愤之情进行激烈的发泄,甚至出现变态的迷狂的心理反应。而现实主义的诗人往往收敛转向沉郁、绪密和衰飒。相对来说,自我形象以浪漫主义诗人更具鲜明特色,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同是浪漫主义又具有不同的自我。
屈原生活在动乱的年代里,武断的楚怀王和无知的顷襄王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逼他自沉汨罗浊水之中。他在《离骚》、《九章》、《九歌》等著述中塑造了个有别于世俗的高洁的自我,是那么地忠贞、修能、循礼、痴情,心甘情愿地在官场上济世,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多地剖心表白,恳求希望能够得到理解重用。他的情感表现为崇高、善良、怨怒和失望,其核心就是美政的建设和参与美政的建设。李白处在包容古今万物的盛唐时代,强烈的时代趋动力和进取精神,使他有“逸兴壮思飞”和“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洒脱的心理结构,他在极度悲痛以后不是象屈原那样更加失望,更加愤怒,一步步走向绝望,而是外化为放达孤狂,情感的渲泄方式也更加广泛。他时而沉醉,时而怕醉,时而振奋,时而狂歌。他以醉自慰:“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古风》)倾吐苦闷:“寸心增烦纡”(《古风》)。鸣泄不平:“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江夏赠韦南陵冰》)……。他无论怎样表现丰富的情感,自我总是那么自信充满高世的力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种超越时代、生命的酒神精神是多么自傲旷达,李白就是这样超世、高世、旷世和济世,这就是他的浪漫。而屈原则不然,他认为极谏断头的贤臣才是真正的贤才,他梦游、神游,与天地相通,他驱马五岳,飞驰四海都是为了表达他贞忠不二,贤能的自我。所以李白出世入世皆未能牢笼,而屈原则只入不出,两个自我自然有别。这反映了李白对屈原“余不忍为此态也”,“惜壅君其不识”,“指九天以为正兮”等心物的扬弃与发展。
在抒情的表达方式上,李白屈原也有同中见避的特点。屈原的抒情方式因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从《离骚》到《九章》步步强化,通过托物、想象、夸张表现出一种日渐其浓的系统的忧伤悲绝的悲剧气氛,是心灵的全部投入,更加真诚。凄凉的秋景,不息的流水;僻野的幽清,孤雁的悲鸣,浓烈的悲情融为一体,格调幽暗、苍凉、悲壮,情深笔长。李白的抒情方式继承了屈原的浪漫特色和幽深笔长的特点,更增加了自己壮脱的特点,壮在力度上,自信雷霆万钧,直挂云帆济沧海,千金散尽又重来,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力量,带有盛唐之音的强劲,挟风带雷,显示出积极浪漫的雄壮之美;笔致飘逸,悠然九天四海,不受人力、物力、心力、自然力的束缚,给人一种五彩缤纷、目眩神摇的境界。表现了他对富贵功名的蔑视和对生命永恒的深刻感悟。所以,李白对屈原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作品数量、视角、方法上李白皆优于屈原,但宏篇巨制和专注系统上李白逊于屈原。
三、审美心理与表现手法
在楚辞中,屈原已注意到用物理世界来表现心理世界,达到心灵的物化,物我合一。如《桔颂》以桔自喻,通过桔的对外界自然受命不迁的特征来表达自己高洁、忠贞的品格,把物象与生命互相感应、体验,体现了审美能力的高超。屈原能够注意心灵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同构对应,如“洞庭波兮木叶下”的秋风萧瑟和凄凉的心境达到了有机统一,将内心情绪的移动用联觉的方式通过审美客体表达出来。他要从彭咸又忧楚国伤心难舍,他要投水自尽又怕壅君不识……他在审美过程中唤醒激活对象,使之联类不穷,加强了审美表现力。他通过鸡、犬、凤、鸾等色调动差的自然世界和江界、南夷的麻木情形的描述,为五岳九天的众仙、众女的形象行为配置出无限广阔的空间,表现自己无穷的哀怨。屈原更注意意识世界的直接发露:“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指九天以为正兮”,“虽九死犹未悔”,“忠不见察兮。”直接发露是感情激愤、不能自控的心理反映,但更显示其抒情与愿望的强烈。在直觉意识的表现上,屈原能物以心役,通过物候的变异表现心理的沉重反差,增强了诗的感染力和审美价值。
在审美感受的二极形态上,屈原把理性的辩证思维融入审美心理,构成新的审美心理机制。一首《天问》,一部《离骚》无不处于矛盾、对立、常觉与错觉的表现之中。“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远去与恋国表现了他强行压抑的精神折磨,“欲擅徊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离尤”(《惜诵》)“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这种种心灵的煎熬,终于使诗人形容枯搞,投江而死。审美的行为和理想都必须经过审美主体的加工和反射,当心理的沉淀和思维定势与外界的矛盾居高不下、长久僵持时就必然会引起心理的崩溃。屈原之死正是心理崩溃的结果。
屈原在审美的艺术表现上大量地运用了象征手法。如善鸟花草以配忠贞,飘风云霓以喻小人等。完全根据诗章的需要配置。
李白在对屈原美学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创设出多极的审美心理,把心灵的感受——诗提高到惊风雨泣鬼神的艺术高度,呈现豪放洒脱、进取飘逸的积极浪漫主义风格。例如他的《将进酒》写他借酒消愁的状态,指点黄河,天上人间,挟水击浪,从黄河奔海的时空落差与自然节奏中感受到的生命短促,一饮三百杯,尽情尽心,这种狂放的发泄方式是李白消愁的特殊行为,体现了他浪漫的气质与旷脱的变态心理。人生与时空的同步及其反差同样在折磨着诗人的心灵,但他不象屈原那样有着沉重的心理压力和单一的美政追求,李白更想到自己,把审美体验从屈原时代的以真善为中心转移到以美为中心,进而转移到审美主体的心灵上来。唐代诗人也注意用象征的手法,以物理世界表现心理世界。如骆宾王的蝉,刘禹锡的鹤……但李白则不同,他既不用屈原的美人、骐骥,也不愿去做那知了知了的蝉。在他看来,燕雀之志已无法追赶时代的风云,美人飞龙不过是故作姿态的驯服,他要用屈原提到的、庄子详尽表现的直上九万里的鲲鹏来代表自己,乘海运而图南,飞九天而扬气,在无穷无尽的时空尽情地享受和运行。李白赋的首篇就是《大鹏赋》,据说他年轻时候就写过《大鹏赋》,这篇是上篇的继续。在李白的笔下大鹏非常巨大,气格豪迈,充满了英雄气概,显然大鹏寄托了李白的审美理想,是他的精神形象。在李白的《古风》中也提到了大鹏,横吞百川,仰喷三山,飞翔九天,邈视万物,分明是他济天下的理想化身;但在《上李邕》诗中,大鹏失去了风候,只好歇下来,可“犹能簸却沧溟水”,期待“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充满了希望与顽强的进取精神。就是在他的《临终歌》中,也念念不忘大鹏:“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但他终于用骚体写出了他被折断翅膀的痛苦,回归到屈原之心上,可是他又比屈原多了豪迈之气和深沉的历史意蕴。
四、文本和现实
李白和屈原都是浪漫主义诗人,不是幻想主义者,所以他们的作品只是用雄奇浪漫的手法来折射曲说他和那个时代,是托物言志,构景抒情式的现实主义和文化娱悦符号。历代大文学家对他们的作品都有正确评价,只是到了现代,才出现一些异常的现象,如把屈原诗作中的一些文化意象随意曲解等。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屈诗曾说:“较之《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鲁迅所言,大致符合屈原作品的实际,屈原的作品是具有相当力度的深邃的“现实主义”作品。至于“不遵矩度”,汉儒已有批评,指其不经之说,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已有驳正:“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不遵矩度”正是屈原独特的表现风格,应当充分肯定。
李白对屈原的“风格”进行了消化包容的吸收,显示出盛唐气度。屈原做过梦,他在《惜诵》中说:“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杭。”到了晚年,更是恶梦有加。李白也做梦,梦中不但登上了天,而且“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你看他飘然凌云,受到了神仙的礼遇,天又怎么样?屈原的《远游》、《离骚》等诗一再说到他的远游,李白有《远别离》与此十分相似,诉说远别离之苦,“皇穹窃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在他看来皇不察忠心,就会于无声处响惊雷。他还干脆写出了《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样全篇梦别之作。在屈原的笔下,往往是对天道不公的愤怒和呵责,李白也写天道,但在他眼中,上天比走蜀道还要好走一些,“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所守才是可怕的人生路上的敌人。李白把所守比喻成豺狼、猛虎、长蛇,比起屈原的小人、众女来要形象深刻得多,屈原的失败很大程度上败在他过于自信,对党人估计不足上,所以李白的见解要比屈原深刻一些。从全局看,李白对屈原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又加以全面的发展。其中千头万绪,非一时可以理清。但可以肯定,他们号称浪漫主义的作品皆是作者和社会的深刻的反映。这是完全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