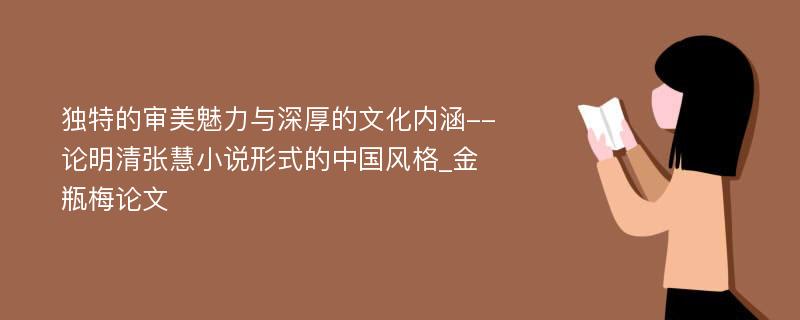
独特的审美魅力 深厚的文化内涵——试论明清章回小说形式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章回小说论文,明清论文,气派论文,深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03)05-0094-10
英国的艾伦·梅西在评论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对传统英国小说冲击时提出:“尽管人们崇尚时髦,愚昧无知,还有学术评论家的抨击,传统小说仍然保持它的活力。”明清章回小说作为中国的“传统小说(注: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和近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现代和当代仍有小说家采用此种形式创作小说,如张恨水的小说,唐人的《金陵春梦》,姚雪垠的《李自成》,等等。),虽然并不是当代小说家采用的主要文学样式,但“仍然保持它的活力”,其叙事模式和艺术表现是西方现代主义所无法取代的,对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仍然有着借鉴作用。
明清章回小说可谓中国之国粹,是中国小说家的一大发明创造,在世界小说之林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明清两代的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今天的广大读者也仍然把它视为珍宝。
明清章回小说在内容方面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容易理解和把握的,因为它艺术地反映了中国人的历史、生活、心理、情感和理想。至于明清章回小说形式方面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看法,很值得深入探究。本文仅就这方面的问题,略述管见,抛砖引玉,以就正于海内外的专家和同好。
一
1.章回体式
明清章回小说在形式方面最突出的特点,乃是采用章回体式来叙说故事、展开情节和塑造人物。每部小说分若干回,每回均有醒目的回目,结尾常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话,承上启下,吸引读者续看下回。综观明清章回小说,一部作品少则几回(如《太虚幻境》四回,《水月灯》四回,《天足引》八回),十几回(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大多在十六回到二十回之间);多则几十回,一百多回(常见的是一百二十回),也有二三百回的(如《于公案奇闻》二百九十二回,《闽都别纪双峰梦,三百三十五回);个别作品多至一千余回,如无名氏的《济公传续集》一千二百回。
明清章回小说的章回体式,有一个逐步成熟的演变过程,大致到明中叶已基本趋于定型。但是,在明末清初和晚清,章回体式又有了新的变化。从分卷、分节、分则到分回;回目则从单句到双句,再到工整的对句,这是明清章回小说章回体式发展的总趋势,但也有不少例外。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单句回目。明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十卷,一百回,回目基本上是七字对句,也有一些九字对句。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二十卷,一百回,回目基本上是七字对句和八字对句,也有六字对句。清初康熙年间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一百回,不分卷,回目均为二字对句(不讲究工整)。作者曹去晶序于雍正八年的《姑妄言》,二十四卷,二十四回。每回篇幅长达三四万字,这是明清章回小说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此其一。其二,《姑妄言》各回既有一般章回小说的以一对句为回目,作为正题;又有另一对句为回目,作为副题。其三,各回的正题回目和副题回目,尚有正目简略,附目复杂;正目复杂,附目简略;正目和附目均较复杂,以及正目和附目比较匀称四种情况。窃以为《姑妄言》的回目新创是其每回的篇幅较长和故事内容复杂所造成的,当是受了《照世杯》等小说的影响。康熙年间酌亭主人的《照世杯》,全书四卷,每卷一回,有单句回目;每回又分为若干段,每段皆有联语的回目。例如,卷一《七松园弄假成真》,共有七段,其第一段回目为:《真才子酷慕死西施 蠢佳人羞辱生潘岳》;第二段回目为:《返吴门座中逢恶友 赴扬州园内遇名姝》……
晚清,章回小说受西方小说技法的影响,为适应新的内容,在章回体式上的新变也很明显。有分章的,如宣统二年单镇的《苏空头》,“专述苏州各界之怪现状”(《例言》),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眼目司堂之香伙》;第二章《玄妙观之犯人》;第三章《城隍庙之热闹》;第四章《学生之忙碌》;第五章《妓女之出风头》。也有分卷分段的,如同光年间怜香惜玉生华卿吴氏的《两缘合记》,两卷十六段,全书按“奇遇良缘”和“诡遇恶缘”两个中心,各成八段,一段叙一故事。也有分章分节的,如宣统年间彭春俞的《闺中剑》,共六章,每章有标目;每章又各分五节,每节亦有标目。如第一章《教育为振兴主义》,五节分别标目为:溯源,遭侮,劝学,课女,改题。
明清两代的长篇小说,为何采用章回体式,这很值得研究。窃以为这既与宋元“说话”伎艺有渊源关系,也受了南曲戏文和北曲杂剧的影响。南戏分段演唱,首段前有“题目”,北杂剧则分折演唱,末折尾有“题目正名”,它们对章回小说的分回叙说和每回皆有回目显然是有影响的。另外,明清章回小说的回目,与唐代以来律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讲究对仗亦不无关系。还有研究者认为,明清章回小说的标目之法,虽与“说话”艺术有关,但也从传统的类书编纂体例中借鉴于经验。[1]
结构艺术:明清章回小说的结构,形式多样,且都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管哪种结构样式,都十分讲究有头有尾,脉络清楚,上下连接,前后呼应,组成统一的艺术整体。众所周知,明代“四大奇书”在明清章回小说发展史上,既是高峰,又是楷模,在章回小说艺术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结构而言,明代“四大奇书”各有特点和妙处。
历史演义的杰作《三国演义》,以历史为结构的形式,陈寿的《三国志》已为它奠定了基本框架。作者叙说三国故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国故事总与其它两国有内在的联系。诚如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所说的:“《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自首至尾,无一处可断”。这种结构形式在西方的历史小说中是罕见的,研究者称之为绳辫式结构。
英雄传奇的典范《水浒传》,其结构形式,用金圣叹的术语,叫做“鸾胶续弦法”,即描写一个人物的经历时,与互不相识的另一个人物在特定的场合相遇,从而引出另一个人物的故事。例如,鲁智深倒拔杨柳树引出林冲,宋江于柴荣家中一绊引出武松。此种结构的关键,在于精心构思一个特定的场合,使一个人物故事过渡到另一个人物故事,必须自然而巧妙。用今人的概括,《水浒传》乃是扣环式结构:一个或二三个好汉的故事叙说完毕,自然地引出另一个或二三个好汉的故事,环环相扣,最后一百零八个好汉聚义梁山。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总结得好:“《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自成文字。”
神魔鬼怪小说的翘楚《西游记》,其故事情节由三个部分组成:孙悟空的出世、学艺和造反;取经缘由和唐僧来历;唐僧师徒四人的西天取经历程。由于受原来唐僧西天取经故事题材的限制,《西游记》采用了单线发展的纵式结构。但作者凭其高超的艺术手腕,把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内容有机地组织在一个统一、完整的巨大结构中,人们称之为珠链式结构。
人情世态小说的首创者《金瓶梅》,其结构特点是透过家庭看社会、人生和时代。诚如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所指出的:“《金瓶梅》因西门庆一份人家,写好几份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全县。”百回巨著的情节主线,则是西门庆家的兴衰史和罪恶史,以及一群女子的悲剧命运。
再看清初的三部奇书,西周生辑著的《醒世姻缘传》,其结构由“前世姻缘”(1~22回作为引子)和“后世姻缘”(23~100回是正文)组成,叙写了“悍妻恶妾”闹得一个家庭“家反宅乱”的故事。它走的是《金瓶梅》的路子,但亦有其创新之处。随缘下士编辑的《林兰香》,在结构上同样借鉴了《金瓶梅》,而又有所创新。全书六十四回,虽有不少触及时政的情节和人物,但以耿府两代(耿朗、耿顺)的兴衰际遇为背景和线索,其主要笔墨放在记述闺友闺情上,着重刻画了耿朗及其六妻妾的性格和命运,突出地描绘了燕梦卿的悲剧。与《金瓶梅》一样,《林兰香》亦因耿朗一份人家,写了好几份人家,并概括了社会、人生和时代。至于曹去晶的《姑妄言》,作为世情讽刺小说,在结构上,既不同于《金瓶梅》,又与《醒世姻缘传》和《林兰香》大异其趣;与后来的《红楼梦》亦各有巧妙,在明清章回小说史上可谓别具一格。《姑妄言》有三条线索贯穿全书:一是竹思宽这个篾片、赌棍兼龟子的浪史,以及由他引出的市井风俗的丑史;二是正人君子钟情与瞽妓钱贵的悲剧性情史;三是宦(萼)、贾(文物)、童(自大)三人从依仗财势胡作匪为,到弃恶从善、大做好事的转变史。这三条色彩迥异的线索,涉及到五个形态各不相同的家庭。由于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三条情节线索和五个家庭,互相联系和作用,组成了一张上联朝廷重臣、京官大老,中接地方官吏、土豪劣绅,下结地痞流氓、平民百姓的巨大网络,把特定社会(晚明和清初)的方方面面都涵盖其中。
乾隆年间问世的《儒林外史》《红楼梦》和《歧路灯》,在结构上也各有千秋。对《儒林外史》结构的评价,虽至今尚有分歧(注:三部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史》对《儒林外史》结构的评价就大相径庭。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不严密,不完整;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说有独创性,但也有松散的缺点;中科院《中国文学史》则赞扬备至。溯其源,三书的观点皆有前贤的评论为依据;卧闲草堂本评者,誉之为“是国手布于,步步照应”;“其布局之妙,莫与言矣”;“文章交互回环,极尽罗络钩连之妙”。胡适则贬之为“没有—个鸟瞰式的布局”,“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别士(夏曾祐)在胡适之前早已指出《儒林外史》“有枝而无干”,“布局松懈”。鲁迅则主要揭示了《儒林外史》结构上的特点。近二十多年来,海内外的研究者,对《儒林外史》结构的评论,似有一味美化的倾向。美国学者林顺夫在《〈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事结构》(载《文献》第十二辑)一文中,批驳胡适的看法,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其“条理性和完整性,决不比非常出色的西方小说作者逊色”,就是—例。),但对其结构特点的认识则并无二致。在这方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概括最为全面:“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行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如集诸碎锦,合为贴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歧路灯》的结构可说是李绿园的一大独创,朱自清先生对此曾赞扬备至:“单就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还较逊一筹,我们可以说,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2](P.447~450)《歧路灯》全书一百零八回,始终围绕着主人公谭绍闻的失足堕落——倾家荡产——败子回头——家道复初来叙说。它以主人公的命运为线索贯穿全书,写出了他的性格发展的历史。如此一人一事,大起大落,针线细密,首尾相应的长篇结构,在明清章回小说中确实罕见。至于《红楼梦》的结构,既有对明代“四大奇书”和清代前期诸章回佳作,尤其是世情小说结构艺术的借鉴和吸收,更有与其丰富、奇特的内容相适应的创新,研究者誉之为“《红楼梦》式”的圆形网状结构。它有一人一事(宝玉的故事)贯穿全书,又叙“群钗”的悲剧;它写四大家族,但突出的是贾家荣宁二府的兴衰际遇;它情节复杂,包括了现实故事和神话故事;它运用倒叙的手法,以神话方式从结局写起,以虚带实地倒叙了“石头”在红尘中的经历。
再看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在结构上它们无不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但又各有特色。《官场现形记》,“其体裁仿《儒林外史》,每一个人演述完竣,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它“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二十年中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缀成一书”,其结构方式又与《西游记》的珠链式又有相似之处。《老残游记》,通过老残的游历,主要把两个封建酷吏的暴政贯穿起来,故有人目之为“串字式”结构。虽然只写了三十五回,未完成原定计划,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结构工巧,文采蜚然”。至于《孽海花》,则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反映了十年间的社会生活。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自谓:“《孽海花》和《儒林外史》虽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然组织法彼此截然不同。比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链;我是蟠曲廻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朵珠花。”
明清章回小说的丰富多彩的结构形式,大而言之,不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以历史为结构,如《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二是连环短篇结构,最典型的作品是《儒林外史》,《水浒传》和《西游记》为此种结构形式开了先河。茅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评得好:“《水浒传》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自独立的短篇,而无割裂之感。”三是《金瓶梅》式的结构,它以一个家庭的兴衰反映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醒世姻缘传》《林兰香》均属此类,《歧路灯》则是其变体。四是《红楼梦》式的结构,《姑妄言》开了此种结构形式的先河。
2.故事情节
在故事情节方面,明清章回小说具有丰富性、生动性和完整性的特点。明清传奇具有“无奇不传,无传不奇”[4]的美学追求,明清小说同样十分重视故事的传奇性,所谓“稗家小说,非奇不传”[5]。“拍案惊奇”,可说是明清章回小说承继宋元“说话”伎艺的优良传统。如何把故事讲好,娓娓乎有令人听之忘倦的魅力,乃是明清章回小说家积极探索的小说美学课题,这既有题材和结构问题,更有情节问题。
明清章回小说故事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与“非奇不传”、“拍案惊奇”的意识大有关系。但是,优秀的作品,并不因追求“非奇不传”、“拍寄惊奇”,而不顾人情物理。它们并不“狠求奇怪”,而是尽力在日常生活和凡人琐事中发掘奇人和奇事,能够用“极近之笔”,写出“极骇之事”,力求做到“无奇之奇”。同时,优秀的作品,既十分讲究情节之奇,又非常重视故事之真和全。这就是说,明清章回小说的故事情节,必须合乎人情物理,必须有头有尾,一切人与事的来龙去脉必须交待清楚,给读者一个相当完整、十分有趣又令人相信的故事。金圣叹在批语中认为《水浒传》“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起承转合之法”,他强调的就是故事情节的完整性。
明清章回小说的情节发展,其特点在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换言之,下一回的情节,一般地说,一定是衔接着上一回的结尾继续发展的。所以西方意识流技法(老百姓谓之跳来跳去。实质是倒叙和插叙过多),与明清章回小说的情节组织法,显然大异其趣。而现今有些小说和影视作品,有意识地“淡化故事”,窃以为亦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中国人从宋元“说话”和杂剧开始,就已习惯于听讲、阅读和观看小说、戏曲中的离奇曲折、有头有尾、扣人心弦的故事了。今天,故事不精彩和不吸引入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仍然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是耐人寻味的。
3.人物塑造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明清章回小说的显著特点是,人物与故事一起出来:故事一开始,人物就出来了;人物一出场,作者就在行动和冲突中刻画其性格。人物性格总是在动态中加以刻划的;同时,人物性格的最突出之点(性格核心,个性特点),总是随着情节的发展,冲突的深化,不断地予以强化和渲染。明清章回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的这种特点,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对后来为数众多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影响深远。《金瓶梅》以后的世情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除了保持传统技法之外,更重视如实描写,所谓“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特犯不犯”(注:明叶昼评《水浒传》最早指出:“同而不同处有辨”,强调在同类人物对比描写中突出各个形象的不同个性,写出其同中之异。后金圣叹评《水浒传》提出“犯之而后避之”,即故意在同类人物的描写中突出其个性差异。张竹坡《金瓶梅读法》则指出:“《金瓶梅》妙在善用犯笔而不犯也”。脂砚斋评《红楼梦》始总结出“特犯不犯”之法。)之法运用自如。(如《金瓶梅》和《姑妄言》中的众多淫荡妇女,《红楼梦》中众多贵族小姐,等等。)故而人物形象更真实,更典型,更富个性色彩,也更有艺术深度和魅力。
明清章回小说既重视人物的外貌描写,更讲究人物神情意态的刻画,强调“绘形”(指身体、面目、妍媸、声音笑貌、表情举止等可以外视的形象)与“传神”(指风韵意态、精神气质等内在特点)的结合,要求“形神毕肖”。在人物的肖像和心理描写方面,明清章回小说也有区别于西方小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动态描写多于静态描写,写意笔法多于工笔刻画。
抓住特征,用言简意赅的白描手法为人物造型,使人物一亮相就给人以深刻印象,这是明清章回小说肖像描写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比如,《水浒传)写李逵的出场:“不多时,(戴宗)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宋江看见,吃了一惊。”李卓吾对“黑凛凛大汉”作眉批曰:“只三字,神形俱现。”金圣叹则评曰:“画李逵只五字,已画得出相。”“‘黑凛凛’三字,不惟画出李逵形状,兼面出李逵顾盼、李逵性格、李逵心地来。”《水浒传》对九纹龙史进和青面兽杨志的肖像描写,也是颊上添毛,令人神往:
……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
只见那汉于……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腮边微露些少赤须,把毡笠子掀在脊梁上,坦开胸脯,带着抓角儿头巾,挺手中朴刀……
《水浒传》的人物肖像描写,常采用静态和动态相结构的描写手法。比如,吴用是在刘唐和雷横撕杀中亮相的:
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銮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人乃是智多星吴用。
妙在如此描写之外,作者又补了一笔:“只见侧首篱门开处,一个人掣两手铜练,叫道:‘你们两个好汉且不要斗……’,便把铜练就中一隔。”秀才打扮,又能手提铜练隔开两把格斗正酣的朴刀,这才是吴用的英雄本色。
《红楼梦》擅长从一个人物的眼中描写另一个(或几个)人物的肖像。比如,第三回从“黛玉眼中写三人”:
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妈并五六个丫环拥着三位姑娘来了:第一个肌肤微丰,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儿,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束。
虽然三言两语,但诚如陈其泰桐花凤阁评本所批,确实“各肖其人”。又如,从甄家丫环眼中白描贾雨村的肖像:
即甄家丫环……见窗内有人,敞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这丫环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楼,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是什么贾雨村了……”
明清章回小说对于首次亮相的人物,不止有独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肖像描写,也十分讲究人物出场的方式方法。常用的先声夺人写法和于无人处写法,就颇有艺术魅力。《水浒传》写大闹野猪林的鲁智深就采用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写法。金圣叹第八回回评曰:
今观其叙述之法,又何其诡谲变幻,一至于是乎!第一段先飞出禅仗,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详其皂布直裰与禅仗戒刀,第四段始知其为智深。……先言胖大而后言直裰者,惊心骇目之中,但见其为胖大,未及详其脚色也。先写装束而后出姓名者,公人惊骇稍定,见其如此打扮,却不认为何人,而又不敢问也。盖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
金氏在这里所总结的借情节叙述变化的手法,是以情节取胜的明清章回小说刻画人物常用的技法。《红楼梦》写王熙凤的出场亦用此法,同样极有艺术魅力,令人难忘。
至于于无人处写法,是指本该正面描写某一人物,但作者故意作侧面描写,使此人物处于呼之欲出的情势。典型的例子是《三国演义》写刘关张的三顾茅庐,先写元直和水镜先生的介绍孔明之才,接着刘关张见崔州平、石广元和孟公威,以为是孔明,见诸葛均和黄承彦又以为是孔明,如此烘云托月,孔明虽尚未出场,但其才、其奇凸现无遗,已呼之欲出,读者的兴趣也由此而倍增。毛宗岗在第三十七回回批中总结这种写法说:“此卷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如(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
明清章回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其角度重点和手法,也与西方小说大异其趣,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十分明显,这是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识的不同所造成的。西方小说家习惯于从宗教角度描写人物的心理(比如,忏悔意识、赎罪意识),明清章回小说则多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角度描写人物的心理(比如,忠义观念、正统观念);西方小说家又喜欢从生物学角度描写人物的心理,明清章回小说则绝少这方面的解剖,性心理描写也较简单;西方小说家更擅长于长篇大论式的“纯心理描写”,明清章回小说则善于融人物心理于举止言行和音容笑貌之中,言简意赅,含蓄委婉,更多地要求读者去体验和领悟特定情境中的人物内心世界。
明清章回小说的人物心理描写,明代著名小说评点家叶昼称之为“画心上”,他在《水浒传》第二十一回的一则批语中指出:
摩写宋江、阎婆惜并阎婆处,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
比如,《水浒传》第五十一回,写宋江带领人马攻打高廉,林冲跃马出阵,对高廉喝道:“你这个害民的强盗,我早晚杀到京师,把你那欺君贼臣高俅碎尸万段,方是愿足。”林冲被高俅迫害得被逼上梁山,故一见高俅的堂兄高廉,怒上心头,大骂高俅,以发泄内心之怨恨和愤怒。而当时林冲的心理活动,则留给了读者去体会和领悟。这种极富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人物心理描写,金圣叹大为欣赏,他有批道:
对高廉骂高俅,各人心中自有怨毒,妙极此等意思又确是林武师,宋江不尔,武松不尔,鲁达不尔,李逵不尔,石秀近之矣,而犹不尔。
当然,如此用动态、写意的笔法描写人物的心理,与中国山水画一样;“简淡中包具无穷境界”,“无画处皆成妙境”,[6](P.231)自有其长处,但也有它的不足。因此,《金瓶梅》以后的世情小说,随着人物性格的日趋复杂化,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除了动态、写意的传统笔法之外,也开始采用静态、工笔的刻画;到晚清,章回小说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小说的技法。《姑妄言》在人物性心理的描写方面,就已经比《金瓶梅》前进了一步;而《红搂梦》在人物心理的静态描写和分析方面,更比明代“四大奇书”有了长足的发展。《红楼梦》的人物心理描写,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这里仅举数例,以窥一斑。
《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写宝玉挨打后,在怡红院养病,黛玉去探望后回到潇湘馆,晴雯奉宝玉之命送来两条“半新不旧的绢子”,小说写道:
这黛玉体贴出绢子的意思来,不觉神痴心醉,想到“宝玉能领会我这一番苦意,又令我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可能如意不能,又令我悲。要不是这个意思,忽然好好的送两块帕子来,竟又令我笑了。再想到私相传递,又觉可惧。他既如此,我却每每烦恼伤心,反觉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由不得余意缠绵,便命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研墨蘸笔,便向那两块旧帕上写道:……
收到宝玉所赠绢帕,黛玉是又喜,又悲,又笑,又惧,又愧,这是典型的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心理描写。又如,第三十二回,宝玉在史湘云面前,称赞黛玉从来不说“混账话”,恰巧被黛玉听到。于是作者便对此时黛玉的心理作了细致的描写;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的知己,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宝钗呢?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我虽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间,不禁泪又下来。待要进去相见,自觉无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
这里的所喜、所惊和所叹,所悲,皆是黛玉此时此刻之所“想”的内容,亦即是她复杂的心理活动。作者的描写应该说是细致、深刻的,但仍然是简洁、含蓄的,这正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与明清章回小说同步发展的明清传奇,相当重视心理描写,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因对杜丽娘的心理作了精细、生动、准确的刻画,被研究者誉之为心理剧。明清文言小说,比之章回小说也更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这也是个值得研究的有趣问题。)
尚须提及的是,喜欢给人物提绰号(突出的作品如《水浒传》《姑妄言》,等等),也是明清章回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振。为小说人物提绰号,也是源于生活之法,因为实际生活存在着人物有绰号的现象。明清章回小说中的人物绰号,有雅俗之分,恰到好处,自有其妙处;用得太滥太俗,也令人厌烦。
4.环境描写
明清章回小说是很重视环境描写的。张竹坡《杂录小引》中,有专论房屋环境描写与整篇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性格发展的关系,他说:
写其房屋,是其间架处,犹欲耍狮子,先立一场;而唱戏,先设一台。恐看官混混看过,故为之明白开出,使看官如身入其中,然后好看书内有名人数进进出出,穿穿走走,做这些故事也。
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回评指出:
书中如扬州,如西湖,如南京,皆名胜之最,定当用特笔提出描写。作者用意已囊括《荆楚岁时》、《东京梦华》诸笔法,故令阅者读之飘然神往,不知其何以移我情也。
在第二十九回回评中,评者又点到了特定的环境描写与刻画人物的关系。
写雨花台正是写杜慎卿,尔许风光必不从腐头巾胸流出。
明清章回小说在环境描写方面,也有浓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西方的长篇小说大多通过人际关系描写社会环境,喜欢描写物化的环境,并擅长于将环境象征化和神秘化。明清章回小说中罕有将环境象征化和神秘化的环境描写。至于通过人际关系描写社会环境,亦是明清章回小说描写环境的基本方法,但它与西方的技法也有明显的不同;而描写物化的环境在个别作品(如《姑妄言》)中也有,但也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人物在画图中,环境靠人物来表现,这是明清章回小说在环境描写方面的一大特色。《红楼梦》第十七回,作者对大观园的介绍,不用静态的客观的描写,却巧妙地用人物的“游园题对额”代替了“演说”(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演说”,即叙说、介绍也。)此回脂本回目为:《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怡红院迷路探深幽》,前半部分写贾政携宝玉,在贾珍导引和众清客簇拥下,一路游览了新落成的大观园。通过题写“对额”,既细致、生动地介绍了大观园的各个风景点,测试了宝玉之才,又艺术地反映了贾政、宝玉父子在人生观和审美观等方面的严重分歧。作者如此介绍大观园,不止在描写大观园的环境,更是在写人物,尤其是宝玉。故脂批认为,如此写法,“却是宝玉正传”。
《红楼梦》大观园内众多小姐的住所景物和房间摆设,皆因人而异,各具风采,起到了衬托人物性格和气质,渲染氛围的作用。为人所称道的宝黛的蘅芜院和潇湘馆,以及探春的秋爽斋,就是突出的例子。其实,贾母的院落、房间和摆设,亦很能表现出这位老祖宗的崇高地位和不凡气派。请看第四十回中刘姥姥眼中的贾母住房及其房摆设:
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昨儿见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柜子比我们那一间房子还大还高。怪道后院里有个梯子。我想并不上房晒东西,预备个梯子作什么?后来我想起来,定是为开顶柜收放东西,若离了那梯子,怎么得上去呢?
问世于《红楼梦》之前的《姑妄言》,有不少静态的环境描写,也有些近乎西方小说中写物化的环境。比如,第三回为写火民与竹思宽在书房内幽会,作者先对铁化家的房屋作了不厌其烦的描写。又如,第九回,小说通过邬合之眼,对童自大家从大门外到大厅上的细致描写,就有力地衬托出了这位财主、监生以“效官样”的人物的个性特色,耐人寻味,引入发笑。
5.语言艺术
在语言艺术方面,明清章回小说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自不待言。
一是以通俗的白话为主,历史演义小说常用浅显文言(所谓“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少数作品用骈文,弹词体小说则用韵文。
二是散韵结合,以散文为主,诗词曲歌等韵文常被巧妙地穿插在散文中间,用以描写环境,烘托气氛;人物亦常以诗言志,以词抒情,以曲表意。
三是在通用白话语言中,喜夹杂方言俗语,不少作品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比如,《水浒传》中多用陕西方言,《西游记》中常有淮安方言,《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中颇多鲁南方言,《歧路灯》中又多豫东方言。即使文学语言最为纯净的作品,亦复如此。如《姑妄言》中夹杂有下江官话和吴侬软语,《红楼梦》中颇多北京话和吴语,《儒林外史》中亦多下江官话。这些情况都与作者的籍贯和生活经历有关。晚清的《海上花列传》,其人物对话全用苏白(苏州方言),则是别开生面之创造。
6.插图、评点
小说中附有插图和评点,这也是明清章回小说在形式方面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西方小说也有插图,但明清章回小说的插图数量多,甚至半图半文。插图或在正文之前,或插入各回之间,或半页图半页文。至于评点则是西方小说所没有的中国特色,它们已成为明清章回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注:许多明清章回小说,从题目已能看出其附有插图和评点。比如:《新镌出像批评金瓶梅》《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增评补图石头记》等等。)
托名李贽的《忠义水浒全书发凡》曰:
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
明清小说(还有戏曲)采用评点对作品进行批评和赏析,源于诗文的评注。从汉代开始,历代学者常以评注方式诠释典籍,比如,《诗经》的郑玄笺,《史记》的三家评,《楚辞》的王逸注,《四书》的朱熹注等等,皆影响深远。宋元以前,这种方式尚未被用之于小说,南宋刘辰翁的评点《世说新语》,实是绝无仅有之例。明代的批评家将小说和戏曲与儒家的“六经”相提并论,于是借鉴评注方式评点小说、戏曲作品便蔚然成风。
明清章回小说的“评点”,“评”是指批评、评论;“点”,则指圈点,精彩之处加圈加点。一部作品的评点,通常有回前评(或称批,下同),回末评,回中评(又有眉评、侧评、夹评),卷首还有凡例,总评,读法、序跋等。明清章回小说(还有戏曲)的评点,是极富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理论批评形式,为明清两代各阶层的读者所喜闻乐见。评点的特点,一是灵活机动,长短不拘;二是紧密结合具体情节和人物;三是寓鉴赏于批评。好的评点本,诚如《忠义水浒传,发凡》所指出的:“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
二
明清章回小说在形式方面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上述七个方面能否概括,当然尚可研讨。至于明清章回小说在形式方面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民族特色,则更须作深入的研讨。这是明清小说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笔者也只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现在不揣浅陋,提出来聊供同好作深入研究的参考。
1.“说话”伎艺的影响
明清章回小说与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一样,皆起源于宋元的“说话”伎艺,尤其是“讲史”和“小说”家数,它们与“说话”有着血缘关系,其形式上的许多特点皆与此有关。明清小说有个独特的名称——“说部”,即由此而来。明清章回小说中常见的“看官听说”,则是“说话”遗留的痕迹。
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指出:
此书与《五代平话》、《京本小说》及《宣和遗事》体例略同。三卷之书,共分个七节,亦后世小说章回之祖。……
《取经诗话》目录和正文有:《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入大梵天王宫第三》《入香山诗第四》,等等,王氏认为章回体式源于“话本”之分节,此说良是。“话本”之分节,又源于“说话”,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诚如前文已指出的,分章回的体式溯其源,当与古代经书、子书有关(注:如《孝经》,有《开宗明义章第一》《天子章第二》《诸侯章第三》,等等;《墨子》有《亲士第一》《修身第二》等等;《晏子春秋》,有《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景公饮酒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等等。)。与宋元诸宫调和体式亦有关(注:金代流传的残本《刘知远诸宫调》,存有《知远走慕家庄沙陀村入舍第一》《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第二》《知远从军三娘剪发生少主第三》《知远探三娘与洪义厮打第十一》《君臣兄弟夫妇团圆第十二》。)。
除章回体式外,明清章回小说在情节、结构、人物和环境描写等方面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皆与“说话”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不少前辈学者,对于明清彦回小说与说话的血缘关系,皆有精辟之论。比如,郑振铎撰于20世纪30年代的《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和《西游记的演化》;[7]赵景深有关元刊全相平话与明代历史演义关系的诸论文。[8]笔者以为,要探究明清章回小说与宋元“说话”伎艺的关系,首先必须注意以下两个事实。其一,明清章回小说中有一类作品,是在“话本”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如康熙年间钱彩、金丰合作整理加工的《说岳全传》(其全称为《新镌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此类章回小说在形式上当然更多受到“说话”的影响。其二,在“说话”(短篇的“小说”,长篇的“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同样在形式上更明显地受到“说话”的多方面影响。《三国》《水浒》和《西游》皆有个复杂的成书过程,故研究者把它们归入“说话”型章回体小说,以区别于主要由文人独创的章回体小说(注:近年来徐朔方先生力主《金瓶梅》亦属世代累积型章回小说,可参考其《小说考信编·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历史与历史著作的影响
艺术形式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审美心理密切相关。明清章回小说形式上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审美心理密切相关。中华民族的历史观念根深蒂固,大于文学观念。其审美心理可说源于历史,而不是源于文学。明清章回小说形式上的诸多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溯其源,与此亦大有关系;比如,明清章回小说喜用“传记体”的结构和叙事法,故事情节求真求全,等等。
在小说理论批评的萌芽时期,学者探讨小说与历史关系,无不认为:(1)小说乃史家所作。小说家采用《史记》所开创的传记体结构方式,创作“鬼物奇怪之事”,“染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原,盖亦史官之末事也”。[9](2)小说乃正史所遗。从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列“小说家”,记载小说篇目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已可看出小说包含了“史”的因素。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论十类小说则认为,“史氏流别,殊途并鹜”,小说内容属正史所缺漏、遗逸、或不采用的人事,前史所遗,后人所记,便有了小说这一家。(3)小说与正史可参订。南朝梁朝的萧绮早在《拾遗记序》中指出,小说“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故与经史有互补作用。刘知几《史通,杂述》则确认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明清章回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与历史难解难分,小说家的创作无不深受《史记》等著作的影响,与上述小说理论显然有着直接的关系。
《史记》中的列传,有一人之传,二人合传和三人合传等形式,这对明清章回小说的结构是有影响的(注:比如,《范睢蔡泽列传》,前半部分主要写范睢逃难秦国以报杀父之仇,后半部分则重点写蔡泽之事,虽仍有范睢其人的存在,但他已作为蔡泽的陪衬。《魏其武安侯列传》,是窦婴、田蚡和灌夫的合传,先写灌夫之事,再重点写田蚡之事,最后写窦婴之事,而此三人之事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史记》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诚如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所指出的:“举世诸史之列传,多藉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唯藉人以明史。”关于历史人物的塑造,司马迁提出了不少富有创见的看法,这对明清章回小说的作者也是极有启示的。比如,史传的任务在于“述故事,整齐其世传”。要求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做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对人物的全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10]《史记》本纪、列传中的史传文学作品,可以看作为明清章回小说中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以及侠义小说,讽刺小说的源头。比如,《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写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和垓下之围,对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李将军列传》《陈涉世家》等作品,对明清英雄传奇的创作影响亦不可忽视;至于《游侠列传》和《滑稽列传》对明清侠义小说和讽刺小说也不能说没有影响。
关于历史著作,尤其是《史记》对明清章回小说的影响,金圣叹和王无生均曾有过很好的论述。金圣叹《水浒传》第三十三回回评曰:
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一篇之中,凡有数事;然但有一人,必为立传,史氏之例也。
近代王无生(无僇生)在《中国历史小说史论》中,则指出明清章回小说,“其源于太史公诸传”。
3.读者的影响
明清章回小说在形式方面极富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与它的接受者——读者也大有关系。明清章回小说的读者,除士大夫和中下层人士之外,主要是粗通文墨的市民和农民。宋元时代的“说话人”和明清两代的小说家,无不牢记着这样一句格言式的俗话:“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11]他们可谓目中有人,在“通俗”二字上下了不少功夫。明清章回小说在形式上的不少特点,显然与“通俗”颇有关系。
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肯定《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诵读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则谓:
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颐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
陈继儒《唐书志传序》亦曰:
演义,以通俗为义者也。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
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赞赏《水浒传》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人“捧玩不能释手”。
甄伟《西汉通俗演》自序,主张小说要“言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浅而不乖于理”。
冯梦龙编撰《古今小说》,之所以分别以《喻世名言》、《警世通俗》和《醒世恒言》命名,诚如《古今小说序》所指出的,其原因就在于:“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由此可见,与正史和诗文词赋相比较,“通俗”(并不止是语言易懂),乃是明清章回小说的突出特点,其形式上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皆与此息息相关。
4.佛教的影响
佛教(包括佛学思想、佛教仪式、佛教文学等)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并逐步中国化之后,对中国文学有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小说,自魏晋的志人志怪,经唐宋传奇和宋元话本,以迄明清的章回小说和其它小说(拟话本、文言小说等),同样深受佛教的影响。仅就明清章回小说而言,佛教不仅与某些作品的故事情节、思想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西游记》等;佛教徒的“俗讲”,对明清章回小说的情节、结构和语言也有一定的影响。至于因果报应、色空观念等佛教思想,不止影响章回小说的内容,也影响到明清章回小说的布局结构和人物塑造。比如,《红楼梦》,第一回关于石头的来历,甄士隐的《好了歌》解;终局宝玉的“悬崖撒手”;贯穿始终的一僧一道,虚幻的“太虚幻境”与现实的荣宁二府;神话故事与现实故事的有机结合;色空观念的笼罩全书等等,无不与佛教的影响有关。
5.传统诗文的影响
中国是个诗国,诗歌对中国文学的各种形式均有深远的影响。小说和戏曲都与诗歌关系密切,皆有诗化的倾向;讲究诗情画意,追求神韵和意境。明清章回小说中的韵文部分比重不小,作用巨大,且形式多样(诗、词、曲、民歌等)。因此,深入研究明清章回小说形式方面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能忽视诗歌的影响。同样,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艺术精湛,富有优良的民族传统。明清章回小说是叙事文学,其主体是用通俗的散文写作的,它的语言(无论是白话和方言,还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文言),无不深受散文的影响。
6.戏曲艺术的影响
明末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评元杂剧《老生儿》曰:“盖曲体似诗似词,而白则与小说演义同观。”清初的李渔则认为,小说与戏曲是“同源而异派”[12]。他把自己的拟话本集称之为《无声戏》,并在《窥词管见》中指出,小说是“纸上之忧乐笑啼”,戏曲则是“场上之悲欢离合”,有其共同的特点。近代黄人《中国文学史》同样认为,小说是“工细白描之院本”,而戏曲乃是“设色押韵之小说”。
明清两代,小说和戏曲同步发展,它们互相影响和渗透,故戏曲对章回小说形式的某些特点的形成,不能不起作用。这在李渔的戏曲和小说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戏曲小说化和小说戏曲化,乃是李渔的戏曲和小说作品的一大特色。仅就明清章回小说而言,其戏曲化既反映在故事情节方面(如题材的相互移植,讲究“无奇不传”等),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如戏曲的脸谱运用,分行当,虚拟化和程式化的表演)。明清章回小说人物一出场的亮相,忠奸人物性格对比强烈,等等,更是戏曲化的突出表现。
《红楼梦》有些情节的处理,就深受戏曲艺术的影响。比如,第二十一回,写贾琏追逐平儿求欢,一个在屋外,一个在屋内,两人隔窗调笑。庚辰本有条脂批指出:“此等章法是在戏场上得来。”第四十三回,宝玉在水仙庵祭莫金钏儿,茗烟代宝玉祝词。庚辰本亦有脂批道:“此一祝,亦如《西厢记》中双文降香第三炷,则不语,红娘则待(代)祝数语,直将双文心事道破。”《红楼梦》作者酷爱昆曲艺术,《红楼梦,从“戏场上得来”的章法很多,且运用自如,很有艺术性,可作专题研究。
[收稿日期]2003-03-01
标签:金瓶梅论文; 水浒传论文; 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明清论文; 醒世姻缘传论文; 读书论文; 儒林外史论文; 林兰香论文; 姑妄言论文; 歧路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