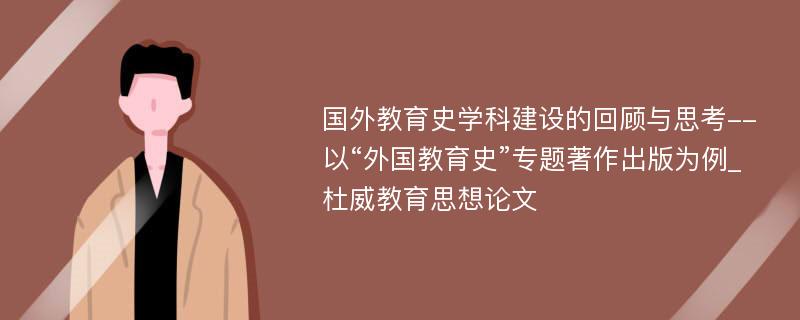
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基于外国教育史学科著作类出版物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史论文,外国论文,学科建设论文,出版物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而敏感的时期。一方面,正如4年前张斌贤教授所分析的那样,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在研究人员的数量、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课题的申报、经费的获取、研究成果的发表以及研究工作的外围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或困难,正处于“全面危机”之中,且这种危机是“基本的”、“全面的”和“令人震惊的”。不仅如此,在当今实用主义盛行、师范院校在职能和结构方面都面临改革和调整的背景下,教育史学科作为师范院校一门基础学科的生存空间已被大大压缩。但另一方面,“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朴素道理也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想象空间:教育史学科也可能在对“生存”问题的关切和对自身建设的反思中寻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有关教育史的学科反思,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首部学科史研究著作已于1998年问世。相比较而言,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工作略显滞后。本文试图对外国教育史著作类出版物的回顾分析,展示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发展轨迹、所获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为更为深入和系统的学科反思抛砖引玉。
一、20世纪80年代前的外国教育史著述回溯
从世界范围看,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19世纪中叶欧美各国师范教育系统的大发展之际。普及义务教育带来了对师资培训的巨大需求,欧美各国纷纷开设师范院校以解决教师培养问题,而有关教育历史的知识被认为是教师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遂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纳入到师范院校的课程之中。可以说,教育史的学科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师范生的培养方面。
在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系统研究开始于清末。1893年李家珍编写的《泰西教育史》(上海昌明公司版)是笔者见到的我国最早的关于外国教育史通史类著作;1899年由美国学者卫理口译、我国学者范熙庸笔述的《日本学校源流》(上海江南制造局版)一书可算是最早的专题史类著述;另一本较早的通史类著作是1901年叶瀚翻译自日本学者的《太西教育史》(能势荣著,金粟斋译)。同年,我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问世,并刊载了不少包括外国教育史在内的研究成果,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从此气候渐成。20世纪前20年,目前已知出版的通史类著述包括《东西洋教育史》(译者不详,1904年)、《西洋教育史》(张怀编译,1912年)、《西洋教育史讲义》(蔡振,油印本,1912年)、《中外教育史》(中岛半次郎著,周焕文等译,1914年)等。
与欧美国家一样,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获得长足发展得益于制度化的师资培训机构的建立,我国教育史学科的出现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教育改革而带来的师范学堂的兴起有关。自1904年《癸卯学制》要求“大学堂、进士馆、师范学堂课程中必需设教育史科”以来,教育史便开始成为我国师范教育系统内的一门重要课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也在师范教育的框架下快速发展起来,并在二三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入了被教育史学界称作为“第一个学术高潮”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教育史专著问世,其中有些至今仍不乏生命力。
在通史方面,姜琦的《西洋教育史大纲》(1921年)是这一阶段较早出版的一本,并一度被视为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最早的一部通史类著作。此后,仅以《西洋教育史》命名的著作至少就有杨廉(1926年)、冯品兰(1933年)、林汉达(1933年)、王克仁(1939年)和马宗荣(大夏大学部出版,出版年代不详)五个版本;此外,还有范寿康的《教育史》(含中外,1923年),雷通群的《西洋教育通史》(1934年)、王凤喈的《西洋教育史纲要》(1922年)、詹文浒翻译的《世界教育史纲》(E.P.Cubberly著,1935年)等。
在断代史方面,主要以编译著为主,如吴康译的《中世纪教育史》(格雷夫斯著,1922年)、《近代教育史》(Graves著,1925年)、《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E.H.Riesner著,陈明志等译,1934年)、姜琦的《现代西洋教育史》(1935年)等。在人物与思想史方面,主要著作有《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1924年)、《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1925年)、《教育理想发展史》(1929年)、《西洋十九世纪之教育家》(1931年)、《近代欧洲教育家及其事业》(1939年)、《西洋教育思想史》(1931年/1934年)、《西洋教育思潮发达史》(1935年)等。
在专题史方面,这一阶段较为注重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和学校制度发展史的研究,《法德英美教育与建国》(1930年)、《欧美学校教育发达史》(1934年)、《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1938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德国职业教育史、欧美初等教育史、欧美女子教育史和日本教育史等都有著作问世。
译著方面,可谓硕果累累,许多重要教育家的著作在二三十年代都被翻译了出来,如卢梭的《爱弥儿》、康德的《论教育》、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凯兴斯泰纳的《工作学校要义》、拉伊的《实验教育学》、克伯屈的《教育方法原论》、华虚朋的《文纳特卡教学法》、桑代克的《教育之基本原理》、柏克赫斯特的《道尔顿教育》、爱伦·凯的《儿童的教育》(又称《儿童的世纪》)等等。对杜威教育著作的翻译更是达到了顶峰,至40年代,有关杜威教育思想相继出版的译作就达13部之多。
从二三十年代外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看,这一时期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不仅包括了通史、断代史和国别史,也涵括了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教育译作;从研究所涉及的地域看,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欧美、日本等国;在研究的内容和体系上,也深受上述国家的影响。同时,由于教育史是师范学校的一门课程,相当一部分著作是为开设课程而编制的,如姜琦撰写的《西洋教育史大纲》就是作者根据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的自编教材修订而成的。这就使得我国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在其早期阶段就打上了师范类教材的印记。
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教育史研究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教育史的研究随即进入了低潮时期,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宣布和实施为止。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史研究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出现了可怕的历史断层,第一高潮期间丰硕的研究成果和长期的史学积累被轻易地一笔抹杀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俄为师”的全盘苏化。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开始在抛弃历史遗产的状态下重起了炉灶。
50年代是我国学者在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集体“失语”的时代,在笔者收集的资料中,除一窝蜂地批判杜威和引进前苏联的著述外,竟然没有发现一本由我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教育史著作(非正式出版的自编教材除外)!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外国教育史的著作都译自苏联。
60年代,我国学者试图摆脱50年代以来的只“译”不“著”的局面,开始着手编写自己的外国教育史著作。我国建国以来最早公开出版的外国教育史通史类著作分别为曹孚和罗炳之所编,都发行于1962年。但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氛围和学术语境,曹孚主编的《外国教育史》基本上套用前苏联教育史的体系和内容,罗炳之的《外国教育史》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尽管如此,自编的教材毕竟经过了我国学者自己的消化和处理,体现了我国学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建构我国自己的外国教育史体系的不懈努力,为我国外教史的学科建设作出初始而积极的贡献。
值得指出的是,自50年代以来,不少师范院校如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都相继开发了自编教材,这些教材许多虽未正式出版,但都体现了学者们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成果。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史著述概览
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复兴肇始于1978年对“左倾”路线的拨乱反正。1979年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的成立以及次年“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研讨会的举办,标志着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全面复苏,从此进入了一个恢复和重建时期。有关8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史著述情况可分述如下:
1、外国教育通史研究
据笔者的初略统计,从80年代至今,公开出版的外国教育史通史类著作超过30余种。除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再版的曹孚和罗炳之的《外国教育史》外,以《外国教育史》为名的著作还有王天一(1984)、戴本博(1989—1994年)、袁桂林(1995年)、袁锐锷(2003年)等不同版本;其他还有“史纲”、“新编”、“教程”一类的著作近10本;通史类的译作较少,只有3本。最为系统的通史类著作当推滕大春主编出版的《外国教育通史》(1989—1994年),这套6卷本著作将通史类外国教育史著述推向了高峰。
在通史类著作走向系统和深化的同时,8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史著述的编写也出现了压缩内容篇幅的趋势,表现为“简编”、“简明”、“史略”等一类著述的大量出版。仅《简明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话》就各出现了3个不同版本;《外国教育简史》、《外国教育史简编》和《外国教育史略》各出现了2个版本;《西方教育简史》和缩编的《外国教育史教程》各1个版本。
可见,在80年代以来的30余本的通史类著作中,约有近一半是以简史、简编、史话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绝大多数的通史类著作主要是为师范院校开设的教育史课程编写的,这与我国外教史最早的教材编写定向相一致,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虽经近百年的发展仍未摆脱这一定向。随着教育史学科在师范院校的被压缩,教育史课程在部分师范院校不再分成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门课,而是被并成一门课,课时也被大大缩短,外国教育史著述也由此开始出现中外合编的局面,2000年以来出版的《中外教育史》一类著作至少有5部。
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教材化取向虽然有能够满足教学需要的长处,是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过程,但长期满足于这种研究定向,也会阻碍教育史研究的深化,没有对这种现象的自觉反思和改变,教育史研究是不可能自动走向具有深度的研究的。
90年代在中西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曾出现过2本力作,一是许美德等著的《中外比较教育史》(1990年),二是张瑞藩等主编的3卷本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1997年),这两本著作不是为授课而准备的教材,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教材体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代表了我国大陆在中外教育比较史方面的成就。除了通史的比较外,有些学者还就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教育或某一历史阶段的具体教育现象进行了比较,如具滋亿的《中韩近代教育思想比较研究》(1998年)、李鲠平的《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1995年)、卫道治的《中外教育交流史》(1998年)。
对国别教育通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美、英、德、日和前苏联教育史的研究,已出版了相关论著,其中英国教育史还有两个版本。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高明士)打破欧美中心的研究取向,标志着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著作层面上进一步拓宽。
2、断代史研究
80年代以来,有关外国教育断代史研究的著述大约有20部左右,较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陆续出齐的一个系列:曹孚、滕大春等的《外国古代教育史》(1981年)、滕大春主编《外国近代教育史》(1989年)以及吴式颖主编《外国现代教育史》(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于1987年版了赵祥麟主编的《外国现代教育史》单行本。断代史的研究以当代史的研究为最多,如季萍的《西方现代教育史论》(1995年)、张耀源的《世界当代文化教育史》(1996年)、陆有铨的《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1997年);在译作方面,有张人杰等译的《世界教育史(1945年至今)》(米亚拉雷等著,1991年)、樊慧英,张斌贤等译的《当代教育史》(安多旺·莱昂著,1989年)。澳大利亚学者康内尔著的《20世纪世界教育史》还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翻译版本。
对近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古代教育史的专门研究较为匮缺,褚宏启的《走出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情怀》(2000年)是笔者所见到唯一的一本。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在90年代中期着手进行了一项世界文化教育史著述的系统编撰工作,于1996年出版了世界教育文化史系列。各册内容和体系相对独立,对文化教育史的时代的划分也很细,将古代和近代分别分为三个阶段,现代分为两个阶段,另加当代部分,由此编出《世界古代前期文化教育史》、《世界古代中期文化教育史》、《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直至《当代世界文化教育史》共10卷本。
3、专题史研究
早在90年代初,布鲁柏克著《教育问题史》就被译为中文,这标志着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界对教育问题史或专题史初步关注。随后的研究出现了不断分化的趋势,形成了不同的专题史研究领域。研究最为密集的是高等教育史领域,相关著作不下十余本,既有专题史内的通史,如《外国高等教育史》就有贺国庆(2003年)、黄福涛(2003年)撰写的两个版本,也有将中外高等教育史一并加以研究的《中外高等教育史研究》(张慧明,1998年);更多的则是对欧美各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历史的研究,如陈学飞的《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1989年)、王英杰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1993年)、许明的《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98年)、张泰金的《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1995年)、贺国庆的《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1998年)。随着高等教育史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不断细化,出现了注重研究某一种类型的大学或某一所大学发展史的趋势,如沈红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1999年)、续润华的《美国社区学院发展研究》(2000年)、郭健的《哈佛大学发展史研究》(2000年)。
在著述数量上位于第2位的专题史研究是外国教育管理史,数量不下6本;其次是学前或幼儿教育史,不下4本。数量位居第4的分别为外国职业教育史和外国美育发展史,专著都在3本以上。此外,对国外德育思想史、女子教育史、美国的进步教育等专题史的研究都出版了专著。反映了教育专题史研究领域正在走向深化,出现了初步的繁荣局面。
4、人物与思想史
人物和思想史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多个人物或历史上的多种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另一类是只对某个人物或某种教育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在对历史上著名教育家的研究上,至少有10本以上的著述。其中,赵祥麟先生主编的《外国教育家评传》(1—4卷)(1992和2002年)是这类著作中最为系统、也是最具学术水准的一部。有些人物评传的著述为适合读者一般了解的需要,在内容上进行了精选压缩,并注重内容的可读性和生动性。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研究已出版的著作也不下8部,仅以《西方教育思想史》为名的就有3本。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研究最为系统的成果当推吴式颖主编的10卷本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这部卷佚浩繁的著述,集全国外教史研究者之智慧共同编撰而成,是外国教育思想史方面的标志性著作。此外,还有一些著作注重从微观的角度研究教育家对某一论域的研究,如《当代外国著名教育家的教学论思想》、《外国教育家论德育》。
对历史上某一教育家的思想(当代之前,即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包括:洛克(译作)、卢梭、裴斯泰洛齐、乌申斯基、蒙台梭利、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等。其中,研究杜威的论著最多,数量不少于6本。新近出版的《德国教育思想概论》(范捷平,2003年)还从国别的角度对近现代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
5、译著
80年代以来,大量的外国著名教育家的著作被国内翻译出版,翻译自西方国家的主要有: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与葛笃德》、福禄培尔的《人的教育》、第斯多惠的《德国教师培养指南》、乌申斯基的《人是教育的对象》、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斯宾塞的《教育论》、赫胥黎的《科学与教育》、拉伊的《实验教育学》、沛·西能的《教育原理》、罗素的《教育论》、克伯屈的《教学方法原理——教育漫谈》、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克雷明的《学校的变革》、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博尔诺夫的《教育人类学》、巴格莱的《教育与新人》、皮亚杰的《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等。西方教育家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依然是杜威,杜威的教育类翻译作品至少有3部;翻译自前苏联的主要著作有阿莫纳什维利7部,苏霍姆林斯基6部,赞科夫4部,巴班斯基3部,马卡连柯1部。
除上述完整的原著的翻译外,80年代以来,还出版了大量的历史上教育家的教育论著选,数量在20部以上,包括昆体良、夸美纽斯、赫尔巴特、裴斯泰洛齐、乌申斯基、斯宾塞、凯兴斯泰纳、杜威、蒙台梭利等。在这类著作中,古代人物偏少,只有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主要以近现代为主;在人物国别上,以西方国家为主,其次是前苏联(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克鲁普斯卡雅等)和日本(小原国芳、福泽谕吉)。2000年以来新译的著作主要有:夸美纽斯的《图画中见到的世界》(杨晓芬译,2001年)、杜威的《道德教育原理》(王承绪等译,2003年)、杜威的《天才儿童的思维训练》(张万新译,2001年)等。
对国外教育家的思想进行选辑汇编的著述至少在12本以上,除西方古代、近代、现代教育论者选外,还有名著提要和名著评价一类的著作出现。内容最为丰富的名著选读单行本当属任钟印主编的《世界教育名著通览》(1994年),有89个国外教育家和120余种教育著作入选,全书1700多页,共390余万字。
从已出版译著的数量看,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热点人物除杜威以及苏霍姆林斯基等几个前苏联教育家外,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受到了国人的极大的关注。2002年以来已经有5家出版社出版了相关译作或编著,有关蒙台梭利的著作和译作已达11部以上。
6、史料建设和学科反思著述
外国教育史的史料建设工作总的来说发展缓慢。70年代中后期,华东师大曾出版过《外国教育发展史资料》(1976年)和《外国教育资料选译》(1979年)。80年代史料方面的著述只有3部,《外国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华东师大教育系,1985年)、《外国教育史简明教程:教学资料》(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等,1987年)、《中世纪教育文选》(吴元训主编,1989年),只比70年代多一部。90年代仍只有4部:《外国教育史料》(E·P·Cubberley著,任宝祥等译,1990年)、《外国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赵荣昌等,1991年)、《外国教育史资料》(徐汝玲,1995年)、《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夏之莲,1999年),而且,90年代的史料挖掘、拓新不够,相当程度上是对80年代的重复或重组。对外国教育史学科本身进行反思的论著目前还未问世,只是安徽省教育史研究会在1984年出版过一本《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讨论会论文集》,方晓东等在2001出版了译著《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卡特林虹,2001年)一书。
三、分析与展望
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若从第一本著作——1893年的《泰西教育史》算起,距今已有111年的历史,比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还要早十多年,通过对百余年我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在著述方面的成果和发展过程的回顾,我们看到:
1、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出现了初步的繁荣局面。百余年来,我国外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应当说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通史、断代史、人物与思想史、国别史、专题史、译著等等方面都有不少的成果问世,总计达数百部之多。尤其是在拨乱反正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外国教育史著作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前十年多于后十年的趋势,而且研究领域进一步走向综合和分化;各种不同方向和题材的专题史的研究著作的出现,反映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初步繁荣局面;通史、断代史、人物和思想史、比较史等领域的研究都构成了系列,出现了代表目前各自领域最高研究水准的标志性扛鼎之作,且这类著作大都是在国内教育史学界德高望重的学者的主持下众多研究人员集体合作的产物,形成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界集体合作、联合攻关的良好学风;对国外教育名著的出版也形成了系列,越来越多的历史上重要教育家的著述不断问世;在研究区域上,欧美虽然还是中心,但不再是唯一的研究领域。值得高兴的是,近年出版的部分著作是著者在读博士期间的研究论题,是在博士生论文的基础上扩充修改而来的,研究范围不大、立意较新,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对提高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走向更高的水准发挥较好的作用。
2、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我国的外国教育学科总的来说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现今的研究成果与50至70年代相比至少是大大增多了,部分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过了20至30年代,如对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就是如此。但不可否认,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严重的曲折和断层,尤其是50至70年代对前几十年的研究成果的简单化处理方式:或束之高阁,或进行不公正的政治化的批判,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失去了与以往学术史的联系,加之对苏联教育史研究模式的盲目照搬,给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外国教育史不仅在当时大大落后于50年代之前的研究水平,而且有些研究领域到了拨乱反正20余年后的今天仍未超过二三十年代。80年代之后,我们做的不少工作实际上是在补课,是对五十年代之前研究工作的重复。这在80年代以后出版的译著中表现最为明显,不少译作50年代前就有了,现在不过是重印或重译。有些研究还比不上50年代前的研究,如80年代以来对杜威教育著作的翻译还不如20至40年代来得齐全。在初等教育史研究、女子教育史研究、职业教育史研究等等方面,也很难说我们超过了二三十年代,至少在著述的数量上是如此。此外,在史料的拓新和学科建设的反思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3、外国教育史的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深化。8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史通史类著作主要是为师范教育课程中开设的外国教育史课程而编写的,主要用作教材,注重体系,研究深度有限。当学者们为满足教学的需要,都将精力放在教材的编写上后,研究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就难以避免了。外国教育史“简编”一类的著述占了通史类著述近一半的比例,虽然这种状况是外国教育史学科在师范院校压缩基础学科教学课时背景下为“求生存”而出现的,但长时间地满足于教材取向的著作编写,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长远发展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近年来出现的教育史中外合编的趋势,表明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正在被进一步压缩。应当说,外国教育史作为基础学科,它在今后教师教育机构中的地位不可能再恢复到我国80年代初那种状态。作为一门授课课程,它不仅面临着与中国教育史的合并,而且还可能与其他教育基础学科(如教育基本原理、教育哲学)进行整合。因此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不能再拘泥于被动地应付教材体系,而是要寻找自己新的研究定位。
4、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应更加关注与现实的联系。从已经出版的著作看,外国教育史学科除有过于注重“教材”编写的研究取向外,另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对当今教育改革现实缺少必要的关注。历史研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远离现实,但历史研究不具有当代视角,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是难以让历史研究为讲求务实的当代社会所接纳的(至少在当前的我国是如此),历史研究也因此会丧失自己的生命力。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不少的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需要教育史研究者为之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借鉴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如果能与人们所关心的教育改革问题联系起来,让沉浸当前教育改革的人们听听历史发出的声音,这对改革的健全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我国当前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与杜威和进步教育主义思想之间是否具有某种联系?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怎样的经验或告示?再如教师专业化成长是我国师范教育改革的重要理念之一,如何从教师职业发展史出发认识和理解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并为我国教师教育结构和职能改革提供历史的分析?这些都是关涉教育改革现实问题的重大历史题材,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总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注重自身体系建构的同时,还必须关注当前国内外的教育改革和现实,进行与改革和现实问题相关的历史研究,为之提供历史的借鉴,这也许是外国教育史研究在“后师范”时代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标签:杜威教育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