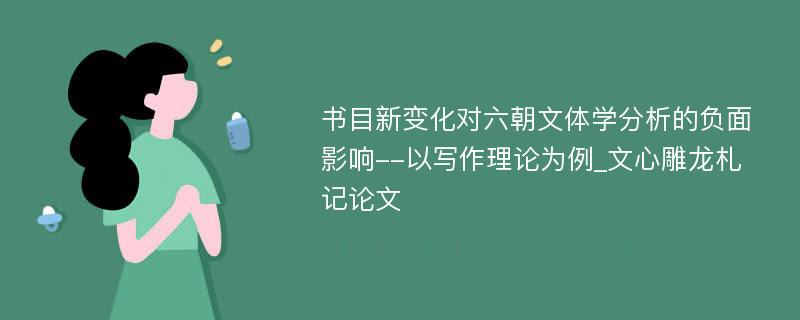
六朝目录学新变对文体辨析的消极影响——以“文笔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为例论文,文笔论文,文体论文,消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0)01-0115-07
施畸在上世纪30年代即已提出:“考旧日汇类文体者,约有两派,一曰校雠学之汇类,二曰文学之汇类。校雠学上汇类之得失今略而不论,兹专论文学上之分类。”①施畸所谓校雠学,实即目录学,所谓汇类,实即文体辨析。他认为文体辨析当区分为目录学、文学两种意义,所见极是,但认为可将前者悬置而专论后者,则恐未必然。历史上的文体辨析,多以目录学为其背景,尽管我们现在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其文学意义,但其目录学背景亦同样不容忽视。
自西晋至隋,在目录学史上是四部分类法逐步取代《七略》分类法的历史②,而这也同时是文学批评大发展的时代。关于此一时代目录学对于文学批评尤其是文体辨析的影响,前人已多有论述,但所论多着重于《七略》旧传统作为学术渊源的影响,而对于其时四部之新变,则似乎重视不够。这或许是因为四部分类在今日看来已属常识,对它的影响已习焉不察。但常识在成为常识之前,必经过一相当长的时段,而它在此一时段中的影响,却往往决定了它在成为常识之后所起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今日太过熟悉而忽视它在当日的影响。
前人对于四部分类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多以为此种分类将经、史、子排除在集部之外,是文学独立性的表现。但实际上此种分类,恰不能导致较为纯粹的文学观念的产生,这是四部分类对于文体辨析影响的消极方面。本文拟就文笔说证明此点。
选择文笔说为讨论对象,是由文笔说的特殊性决定的。郭绍虞对文笔说的地位有很好的总结:“文笔之分,实在是认识文学之独立性的必要条件。就当时的文学作风而言,假使看不到文笔之分的作用,就不可能使文学独立成为一种学科。”③笔者同意郭先生的看法,文笔说可说是当时追求文学独立性的最突出表现。如能证明文笔说尚且受到四部分类的限制,则整个文体辨析在追求文学独立性方面所受的限制,自可不言而喻。这是笔者撷取文笔说作为讨论对象的原因所在。
一
逯钦立认为文笔之说有前期(东晋)、后期(南朝)之分,而后期又有传统、革新之别。④笔者大体上接受逯先生的意见。至迟在东晋初年,文笔已分指两类著作,文指诗赋颂诔,笔指书论表奏,而对此两类著作的特征,则尚处于日用而不知的阶段。其后随着文学批评的深入,不能不对二者的内涵有所探讨,而诗赋颂诔有韵,书论表奏无韵,乃是二者最明显之特征,《文心雕龙·总术》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别目两名,自近代耳。”刘勰所说的近代,是指刘宋而言⑤,则最迟在刘宋时期,明确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已成为常言。刘宋属于逯钦立所说的后期,但不代表前期的文笔说便不具有此种内涵,毋宁说此种内涵至南朝时方被明白地揭櫫出来而已。有韵无韵,可说是文笔说成为一种理论的比较稳定的基本内涵,而其外延,则局限在集部,“经、子、史等专门著述,不入单篇的文、笔范围。”⑥这两点在文笔说的前期是完全成立的,逯钦立举出了很多证据,此处不赘述。但随着使用者的逐渐自觉,他们不再满足于旧说而试图本于自身的文学观念对文笔说重新加以界定,如逯钦立所说“加上一点自己的斟酌和修改,所以与晋人的文笔义界,多少显示些异彩”⑦。逯钦立主要着眼于论者对文笔说内涵的修正,并据此认为南朝文笔论者有传统与革新之别。笔者注意的是,论者在修正文笔说内涵的同时,对外延也开始有所改变,不再局限于集部,从而对四部分类的前提有所突破,但最终没有完全摆脱四部分类的影响;逯钦立传统、革新之别,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得到说明。下面对南朝文笔说的代表人物逐一加以分析。
1.颜延之、刘勰
将两人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关于颜延之文笔理论的一段重要材料仅见于《文心雕龙》转引,并且这两人的文笔之说颇有相关之处。
《宋书·颜竣传》载颜延之语:“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这是今日所见明确以文、笔分指两类文体的最早史料。颜延之关于文笔说的更重要的一段材料,见于《文心雕龙·总术》篇:“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
此处如范文澜所言,是将文分为三类,“‘言’字与‘笔’字对举,意谓直言事理,不加彩饰者为‘言’,如《尚书》之类是;言之有文饰者为‘笔’,如《左传》、《礼记》之类是;其有文饰而又有韵者为‘文’。”⑧刘勰对此反应激烈:“《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果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⑨他要证明的是经典亦属笔类,但实则“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范注:“强弱犹言质文。”⑩弱到什么程度算无文采之质言,强到什么程度又算有文采之饰笔呢?他实际上是在模糊言、笔之间的界限,也等于间接地承认了颜延之“经典则言而非笔”的合理性。他欲证明的是经典全属笔类,但能证明的只是经中有笔,即有所谓“言之文”者。所以刘勰最后结以“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如果六经皆是笔类,则这个判断是无意义的。别立“典奥”为标准,适见刘勰并无自信在“经典则言而非笔”这个论题上驳倒颜延之。
而何以刘勰又必须反对颜延之此说呢?这和刘勰的宗经观有关。刘勰认为文须是“美文”,须有文采,作为“群言之祖”(《宗经》)的经典自然需要“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宗经》),为“衔华而佩实者”(《征圣》)。如果按照颜延之“经典则言而非笔”的说法,则经典即非“言之文”,全无文采,此与刘勰基本的文学观念相左,故刘勰不得不极力反对之。
虽然我们不知道颜延之这段议论的具体背景,但笔者认为很可能是针对当时文笔说的前提——四部分类而发。理由是,颜延之此处实际上是将传记纳入笔,而将经典排除于笔。但文笔之分本在集部内部进行,经典非笔,理所当然,何必费言?故刘勰虽极力抨击“经典则言而非笔”,而颜延之所重实不在此句,而在后一句“传记则笔而非言”,前一句不过连带述及而已。他实际上是要把传记纳入到笔的范围。“传记”依范文澜说是指与经典相对的儒家传记,逯钦立则以为“传记亦或指史传,但与经典而言,似以指《左传》、《礼记》两种为得”(11)。无论何指,颜延之此处确是将笔的范围扩大,“晋人所谓文笔,不包括子史等专门著作,到了颜延之,才把子史类加入笔体”(12)。按照传统的文笔说,这些著作本不当属笔,故颜延之欲将之纳入笔类,必得郑重提出。那么颜延之何以要将传记纳入笔呢?因为他对笔有一个定义,“笔之为体,言之文也”,而“言之文”又何限于集部,所以颜延之实是因为自身的文学观念而欲突破集部的限制,突破四部分类这一前提来讨论文笔说。
我们再来看刘勰。刘勰关于文笔的直接论述已见上引,此外刘师培且以《文心雕龙》篇次为刘勰“隐区文笔二体之验”(13),此说确有所见,黄侃亦同,但他又说:“彦和他篇,虽言文笔,而此篇则明斥其分篇之谬。故曰:‘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师法彦和者,断从此篇之论可也。”(14)正因为认为文笔之分无必要,但又为当时之常言,所以刘勰为叙述方便,乃用文笔之说,但内心是无可无不可的。所以“彦和之分文笔,实以押韵脚与否为断”(15),在内涵上只是承袭晋以来旧说而已。
但刘勰文笔说同旧说却有一绝大之不同,即是将文笔的外延扩大到经、史、子三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刘勰反对“经典则言而非笔”,而对“传记则笔而非言”则无所论辩,实际上是同意颜延之将传记纳入笔的做法,同时更要将经典也纳入笔类。这里须注意的是经典并不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文体论部分,而属于“文之枢纽”(《宗经》)。施畸说:“夫六经亦文也。……刘氏尊之,以为文章之本,不当以体言。”(16)所见甚是,经典的确不属“论文叙笔”(《序志》),但此篇明言“经传之体,出言入笔”,则经典亦可以体论。这大概是由经典的双重性质决定的。经为文之本,故不可以体论,但经本身即又是文,故又可以体论,刘勰论文叙笔,何曾排斥六经。所以刘勰的文笔,是涵盖经部的。而笔类的前两篇,即是《史传》、《诸子》。(17)文体论的其他诸篇,正可看作当时集部的范围。故刘勰实是将四部均纳入文笔的范围,这与旧的文笔说,是大不相同了。
刘勰将经、史、子三部皆纳入文笔范围,实与其文学观有关。李士彪称刘勰“将《史传》和《诸子》列入笔类,只是他的权宜之计,绝非当时人普遍观点的反映”。(18)将史、子纳入笔,确非当时普遍观点,但也绝非权宜之计,毋宁说是刘勰的文学观决定了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而导致对传统文笔说的修正,立场和颜延之相类,但两人文学观毕竟有别,所以对于旧有的文笔说的修正也并不相同。罗宗强认为“他虽说论文叙笔,而其实他接受的是不分文笔的固有观念……从文学观念的角度考察,他似乎并无区分出一种纯文学来的意向”(19),所见极是。将经、史、子纳入文笔的范围,正可看作刘勰此种意向的一种表现。
2.萧统
萧统关于文笔说的意见,主要见于《文选》序。此序并未明确提及文笔说,故黄侃言其“未尝有文笔之别”。(20)但序中自述选文范围,将“姬公之籍,孔父之书”(经部),“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子部),“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史部)一一剔出,逯钦立认为“这与东晋不把经史等专门著作,列文笔范围,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昭明的选文凡例,大体承袭晋宋人旧的文笔说”。(21)逯说甚有理,但似仍有未尽之义。
萧统此序,表面上承袭旧的文笔说,但在操作上却不尽相合。萧统的破例有两点,一是将某些子部著作收入文笔的范围,章学诚认为《文选》所收《过秦》、《典论·论文》本属子书,而《文选》“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22)章太炎发挥此说:“总集不摭九流之篇,格于科律,固不应为之辞。……未知贾生《过秦》、魏文《典论》,同在诸子,何以独堪入录?”(23)二人均指出文笔之分本在集部,不录诸子,理所固然,是所谓“格于科律”,又何必牵合“立意”“能文”为说?且既明言不录诸子,又何以录子部之《过秦》、《典论·论文》?王运熙、杨明承认“《文选》之不录经、史、子,首先是由于沿袭总集编纂体例的关系,萧统的解释,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制约下而作出的”。又说:“此二论久已别出单行,传在人口,被视为单篇论文,故亦入选。”(24)二位先生是从两论别出单行的角度上作出解释,但仍不能不认为萧统此处实属破例。且二论以“别出单行”入选,而此一标准,实源自四部。盖集部所收,本为不能纳入经、史、子之单篇著作,故以“别出单行”为文笔,不是文笔说自身之要求,而正可看作四部分类影响文笔说之一例。
萧统的另一破例之处,是其将史传中的赞论、序述也收入《文选》,理由是它们“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两句话,诚然不能作为《文选》总的选录标准,却无疑是其选录标准的一个方面,至少部分的代表了他的“文”的观念。王运熙、杨明证明时人颇重视赞论、序述这两类文字的审美价值,所以萧统才会加以收录。(25)但这正说明了萧统是以自己的审美标准挣脱了文笔说原有的四部分类的束缚。逯钦立对此赞叹有加,称之为“昭明的卓越见地”(26)。着眼点恐怕也是在此。
但总的来讲,萧统还是遵守四部分类这一前提的,因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经、史、子之中,何限于史传之赞论、序述。仅以此不完全的选录标准而言,萧统已未能一以贯之了。
萧统《文选》对于后世总集的编纂影响极巨,大部分总集的编纂都是在集部内部进行,这可以从对相反者的评价中看出,《四库提要》称真德秀《文章正宗》“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27)。又如施畸评论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文体汇类由总集扩张至经史子集四部矣。此实曾氏之特识,大有造于文体论者也。”(28)凡此,适可以看出后世总集多遵从《文选》限于集部的规定。刘师培称《文选》此种做法为“后世选文家之准的”(29),诚非虚言。
3.萧绎
萧绎关于文笔之分的意见,主要见于《金楼子·立言篇》,分今之学者为四:儒、学、文、笔。他的文笔之分,黄侃认为其标准是“情、采、韵”三者,(30)逯钦立将之归于革新派,“把文的范围缩小了,把笔渐渐推到‘文’囿之外,违背了历代的传统说法”(31)。郭绍虞阐述更为直接,“文相当于纯文学,笔相当于杂文学”(32)。笔者赞同黄、逯、郭等诸先生的意见,认为萧绎的文笔之分着眼于文学自身之特质,而不仅在于形式上的有韵无韵。但同时想指出的是,萧绎的此种区分,仍是在四部分类这一前提下作出的,而且并未能贯彻到底。
王运熙、杨明认为萧绎所说今人四学可与刘宋国学四科儒、玄(子)、史、文相对(33),所见极是,而落实到著作上,则是与经、史、子、集四部相对。儒对经部,学对子、史部,文、笔对集部。
郭绍虞对四学之分的辨析颇为明晰,述之如下:“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便,质于心用”,“以上四句指今之学者的第一种,即仅能解释五经字句而不能贯通其理的儒生”;“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辨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之流,亦足可贵”,此为第二种,即“博穷子史而不能通经者”。(34)第三为文,第四为笔。笔者感兴趣的是,第一种“守其章句”,“仅能解释五经字句而不能贯通其理的儒生”,入于经部;第二种“博穷子史”,则可以入于子史两部,则就当时的知识领域而言,便只余集部。所以萧绎文笔之别,实是集部的内部划分。
但萧绎对于四部分类亦非完全遵循。他的破例之处在后文“任彦升甲部阙如,才长笔翰,善缉流略”句。此处“甲部”指经部言,“甲部阙如”,是指任昉没有经学著作。(35)“才长笔翰,善缉流略”,郭绍虞下的断语是“史即是笔”(36)。验之任昉著作,除文集外均入史部,郭先生此说可信。萧绎此处认为任昉虽没有经学著作,但其笔才表现在史书写作中。质言之,萧绎虽将经部与笔相区分,却将史部纳入笔类,或因为他认为史书写作更贴近于他对笔“神其巧慧”的规定。但此种做法,实已背离了四部分类的前提。
更就萧绎“文”的观念而言,亦相应的存在一个问题,即是经、史、子里面符合萧绎所说的“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荡摇”标准的文章,算不算是“文”呢?如算,则四部分类的前提不能成立,如不算,则萧绎自身文笔之分不能成立,这两个划分标准间是存在着矛盾的。这虽只是逻辑上的推断,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但从萧绎因其对笔的认识而突破四部分类而言,他因文的认识而突破四部分类的拘束,非不可能。
二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四部分类这一前提贯穿于文笔说的前期后期,文笔之分始终在集部内部进行,这从正面证明了四部对于文笔说的限制。后期文笔说对此一前提已经开始有所突破,而突破恰从反面证明了限制的存在。四部分类对文笔说之影响,于此可见。下面试对此种影响何以存在,以及此种影响何以是消极的原因作一初步分析。
文笔说的产生与发展,与四部取代《七略》约略同时,大致相当于六朝时期,此点并非偶然。二者有着共同的渊源,即是文集创作的繁盛。文集之兴始于两汉,至魏晋时造成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文集以附庸而为大国,旧有的《七略》分类已不能涵盖,这成为四部代替《七略》之一因。章学诚认为“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有五,其三即为“文集炽盛”(37)。二是促进了文体辨析的发展,如刘师培所言:“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38)而文笔说作为文体辨析的结果,也随之逐渐显豁。郭绍虞谓“文体分类的开始,是由于结集的需要”。“文笔之分有两个来源”,其中一个,即是“由于编选总集的需要”(39)。因之四部分类与文笔说二者的逐步确立,便几乎同时了。
二者之间的关联表现在主体上,则是从事文体辨析的人,同时对目录学也颇有研究。王瑶指出:“注重文体辨析的人,很多都是从选家和目录家的态度出发的。这就是这个时代大家都注意文体辨析的原因,也就是辨析文体对于文学批评不能有太大的理论建树的道理。”(40)王先生的判断有两点,一是从事文体辨析的人多从选家和目录学的态度出发,二是因为这种态度所作的文体辨析对于文学批评不能有太大的理论建树。关于第一点,王先生所举的例子是任昉,任昉而外,还可举出多人。如最早确定四部次序的李充,同时亦曾为《翰林论》,中颇多辨析文体之语。再如刘勰与目录学的关系,学者已有详论。(41)而关于萧绎,《梁书·臧严传》载臧严为湘东王侍读,“王(萧绎)尝自执四部书目以试之”,足见萧绎为湘东王时对于四部已很熟悉。《北齐书·颜之推传》载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记萧绎即位后曾敕周弘正等校书,其时已分经史子集四部,经史子集四部之名,最早亦见于萧绎敕周弘正等校书事。(42)文体辨析与目录学研究主体的高度一致性,是四部分类制约文笔说的直接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瑶判断的第二点,他所点出的正是目录学对文体辨析的消极影响,但何以从目录学角度出发便不能有太大成就,王瑶并未明言。笔者拟就本文所论述的对象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解释。
如前所论,两汉以来文集创作繁盛,论者将众多文体归结为文笔两大类,这形成了文笔说的两个要素,内涵上区分有韵无韵,外延上限制在集部,这两个要素完全是实用性的,并无更深学理可言,很难对文学观念的演进产生积极影响,这使得前期的文笔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实用性的公共话语而存在,具有强烈的目录学意义,逯钦立对前期文笔说的论述,主要本之于史传在总结传主作品时所列目录,足可说明此点。作为一种习惯性的规定,并不会对其逻辑有周密性之要求,所以不会有类似“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何以必须限制在集部”的问题,因为文笔之分本为分析集部作品而产生。但到了文笔说的后期,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南朝时期文笔说已成为“常言”,论者即使不赞成此说也不得不用,刘勰即是一著例。但此时的文笔论者已不满足仅从目录学意义上讨论文笔说,而试图把它改造为符合自己文学观念的理论,成为自己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则对于文笔说不能不作更严密之要求。但论者在改造文笔说内涵的同时,却保留了四部分类的前提,二者之间却存在矛盾。颜延之以笔为“言之文”,是要将“文采”这一新要素纳入文笔说,然而欲使“笔之为体,言之文也”这一判断的主项得以周延,就不得不把传记纳入笔类,但这样一来,就突破了四部分类的前提。刘勰在内涵上沿袭了文笔旧说,但他自身以“美文”为文的观念,却使得他把文笔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四部。同样地,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观念,也使得他讨论文笔不能不逸出集部之外。此三人虽对文笔说的内涵有所修正,但并无根本改变,萧绎则不再遵从旧有的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的做法,但他的区分仍然是在四部的大框架下进行,其文笔新说,同四部分类也仍然存在矛盾。
而南朝文笔说何以会与其前提四部分类产生矛盾?根本上讲是由于文学与目录学性质的不同。文笔说既以四部分类为前提,则文笔之分相应地具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文笔作为一个整体与经、史、子相区别的独立性,二是对文笔之间差异的强调而导致的对于纯文学独立性的追求,如郭绍虞所言,“文相当于纯文学,笔相当于杂文学。”(43)尽管此种以“纯文学”“杂文学”标举文、笔的提法在一开始就受到质疑,但对文学自身内在规定性,对纯文学理念的追求,确属正当,并且是文学批评深化的表现,这第二层次实更为可贵。在实际的理论探讨中,第二层次的讨论始终是在第一层次的限制下进行的,即是说,对文学内在规定性的追求,必须在集部内部进行。而四部分类,如余嘉锡所论,多出于实用目的。四部分类,于六朝时尚属草创,其实用色彩尤浓。(44)因其实用,则学理上不能无缺憾。姚名达曾总结四部分类之缺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曰经史子集四部之界画并不谨严也。”“二曰各篇小类之内容并不单纯也。”(45)这恰巧对应着我们所说的文笔说的两个层次。前期文笔说作为一种实用性的习惯用语,它同四部分类实用性的一致使得二者间的矛盾并不突出。但后期论者逐渐自觉,对文笔的界定日益注重从性质上加以区分,更富文学与审美意义,但与此同时,文笔说的前提四部分类,并未被舍弃,其实用性质,也未改变。这样,文笔说与四部分类这一前提的矛盾日益加深,文笔开始不限于集部而旁及经、史、子各部,文笔之别,也不再局限于集部。我们可以看到,颜延之、刘勰、萧统主要是第一层次,他们是把文笔作为一个整体而有所界说;萧绎则是第二层次,他已不再满足文笔说的旧有内涵,而试图通过凸显文学的内在规定性来区分文笔。相较而言,萧绎走得更远一些,所以逯钦立将颜延之等三人归结为后期的传统派,而将萧绎归入革新派,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说明。但由于四部分类的实用性质,决定了他们的努力都是在实用目的前提下的审美划分,这两方面不能不产生矛盾,从而不能将他们的划分一以贯之,以产生更为纯粹的文学观念。这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种在四部分类下对文学独立性的追求,从逻辑上看是不能成立的,从南朝的文笔说的历史来看,也是不成功的。
在集部内部进行文体辨析的做法在六朝时为首创,而在后世影响甚广,我们随文已有举例。在四部分类定型之后,在集部中进行文体辨析的做法已被视作理所当然,作为常识而存在了。全面讨论四部分类对后世文体辨析的影响,非本文所能涵盖,需作更广阔之研究。但推测地讲,中国历史上纯文学观念的难以产生,固然有很多更深层的原因,以四部分类为前提在集部中进行文体辨析,或许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技术性原因。
收稿日期:2008-12-26
注释:
①施畸:《中国文体论》,北京: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版,第10页。
②汪辟疆称六朝为“《七略》与四部互竞时期”(《唐以前之目录》),见《目录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又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八节《目录学源流考中·晋至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0-120页。
③郭绍虞:《文笔说考辨》,原发表于《文艺论丛》1978年第三辑,后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页。
④逯钦立:《说文笔》,《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⑤刘勰“近代”指刘宋的辨析,见逯钦立:《说文笔》,第173页。
⑥逯钦立:《说文笔》,第189页。
⑦逯钦立:《说文笔》,第206页。
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8页。
⑨“果”原作“不”,依王利器说校改,见《文心雕龙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8页。
⑩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658页。
(11)逯钦立:《说文笔》,第201页。
(12)逯钦立:《说文笔》,第203页。
(13)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页。
(14)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2页。罗宗强以为刘勰称“别立两名,自近代耳”,“看似与对待文、笔的态度无关,而其实却是一种委婉的态度。如果我们考虑到他论述各种文体时都索其原始,并且在论文之枢纽时主宗经的话,那么这‘别立两名,自近代耳’,其中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含有微辞”。正可为黄侃说做注脚。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65页。
(1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262页。
(16)施畸:《中国文体论》,第33页。
(17)有趣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纪昀对此两篇的评却可看出四部分类法直至清代仍然对文体辨析有影响。纪昀对此两篇评价极低,并于《诸子》篇评曰:“盖子书之文,又各自一家,在此书原为谰入,故不能有所发挥。”纪昀发此议论,正是胸中先横一四部分类之成见。必先将经史子一一别出,方可言文。文体辨析,须在集部内部进行。见黄霖编《〈文心雕龙〉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18)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19)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377页。
(20)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260页。
(21)逯钦立:《说文笔》,第205页。按,《文选》不选经、史、子,阮元早已指出,刘师培更进一步指出萧统此种做法“所以明文学别为一部,乃后世选文家之准的也”。但至逯钦立始明确将之与文笔说相联系。阮说见《与友人论文书》,《研经室三集》卷二,四部丛刊本;刘说见《中国中古文学史》,第103页。
(2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页。
(23)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24)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页。
(25)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第278-279页。
(26)逯钦立:《说文笔》,第205页。
(27)总集类二,卷一百八十七。
(28)施畸:《中国文体论》,第86页。
(29)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103页。
(30)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261页。
(31)逯钦立:《说文笔》,第208页。
(32)郭绍虞:《文笔说考辨》,《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册,第335页。
(33)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第277-278页。
(3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40-341页。
(35)钟仕伦将此句释为:“勿需通经入仕,同样可以诗、赋、铭、诔一类作品的写作所表现出的才华而成为文坛豪杰。”见《金楼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2页。此说恐未确。《新唐书·李守素传》载虞世南语“昔任彦升通经,时称‘五经笥’。可见自其生时至于唐代,任昉通经之名不衰。此处称任昉“甲部阙如”,或是指其并无经学著作。《梁书》本传载其“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卷,文章三十三卷”,《隋书·经籍志》将《杂传》、《地记》皆归入史部,又有《地理书抄》,亦入史部,文章自入集部,则任昉虽称“五经笥”,却无经学著作。此当是萧绎称其“甲部阙如”之意。
(36)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册,第332页。
(3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956页。
(38)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23页。
(39)郭绍虞:《文笔说考辨》,分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第294、292页。总集之作,本为囊括别集,采厥精英而作,它是文集创作繁盛的结果,同时又是文体辨析的一个直接动因,在文集炽盛与文体辨析之间,居于联结点的位置。关于文体辨析和总集编纂两者之间关系的详尽论述,请参看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7-106页;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100页。
(40)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第103页。
(41)可参看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294-298页,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56-63页。
(42)此条材料为余嘉锡所指出,证明萧绎时已有经史子集之名。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158页。
(43)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册,第335页。
(44)六朝时期四部分类的实用色彩之表现,举其大者,如四部在六朝时多称甲乙丙丁,至隋唐犹然。姚名达引毛春翔之说:“甲乙丙丁犹之ABCD,一二三四,乃分类之号码,非分类之标题。”见《中国目录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6页。余嘉锡谓:“其日甲乙丙丁者,甲乙丙丁非名也,因其中所收之书不纯,无可指名,而姑以是名之也。”再如六朝官撰目录,均为四部,而官修目录,自不得不更多的考虑储藏入架等实际操作条件。是则当时四部分类,为官修目录,多出于实用目的,而乏学术意义,故多仅以甲乙丙丁标目。”余说分见《目录学发微》第153、169页。
(45)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95-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