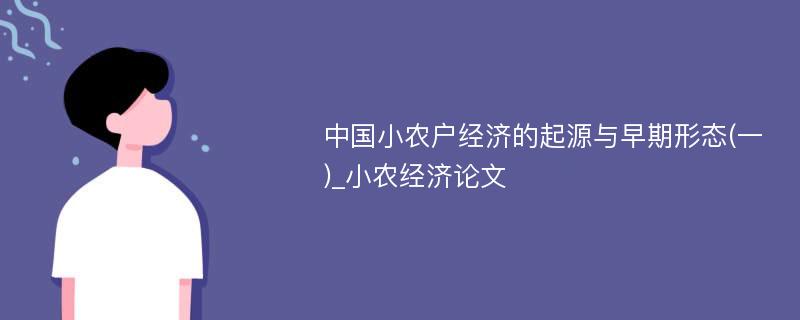
中国小农经济的起源及其早期形态(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农经济论文,中国论文,起源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史学界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小农经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的出现是封建制或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标志。按照这种观点,春秋战国以前固然无所谓小农经济;而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领主制社会中是否存在小农经济,实际上也是被否定的。这个问题,不但牵涉到如何正确认识小农经济,而且牵涉到如何正确把握夏商西周的社会经济形态,很值得认真讨论。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的同仁。本文的讨论,打算从什么是小农经济谈起,然后分析我国小农经济的起源,夏商西周小农经济的存在及其特点,并对小农经济早期形态的某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一、什么是小农经济
目前学术界对“小农经济”的理解存在很多的分歧,人们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比较混乱。有的学者所说的“小农经济”只是指自耕农,而不包括依附农和佃农(注:如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有的学者则把经营地主也包括到“小农经济”中去(注: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译本,中华书局1986年。);又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类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并对“小农经济”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注:赵冈:《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小农经济”的含义不能光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实际上是有其确定的科学内涵的。我们现在使用的“小农经济”的概念来自马克思。马克思把小农经济视为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方式,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是内涵基本一致的同一系列的概念,只是涵盖范围大小有所差别而已。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因为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中,只要这种状态允许独立的单个小生产者存在,农民阶级必然是这种小生产者的大多数。”(注:《资本论》第三卷第672页。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这种小生产大体有以下的一些特征:
1、它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或者说, 它把生产和消费统一于个体家庭之中。马克思说:“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注:《资本论》第三卷第909 页)他甚至把小农经济称之为“小家庭农业”(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476页。 )或“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注:《资本论》第三卷第1207页。)。小生产又称“个体小生产”(注:《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41页。),所谓“个体”, 就是指个体家庭而言,并非只是指单个的农民。我们习惯上所说的“个体农民”,实际上也是指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2、与此相联系的是生产的孤立、分散和自给自足的性质。 这种小生产是“在劳动孤立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注:《资本论》第三卷第715页。)。“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 而是孤立劳动”(注:《资本论》第三卷第916页。)。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注:《资本论》第一卷第830 页。)与劳动生产的这种孤立性和分散性相适应,小农经济是一种小而全的经济。“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注:《资本论》第一卷第555 —556页。)因此,小农不但要独立地完成农业生产的全过程, 而且总是“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注:《资本论》第三卷第890—891页。)。这是一种“维持生计的农业”(注:《资本论》第三卷第674页。);因此, 也必然是一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经济。
3、它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一种经济。 马克思说:“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注:《资本论》第一卷第830页。)这是一种不同于剥削者私有制的劳动者的私有制, “靠自己劳动挣取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注:《资本论》第一卷第830—831页。)。马克思把小农经济称为“生产者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或占有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个体小生产”(注:《资本论》第三卷第674页。), 而把小农称为“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注:《资本论》第三卷第672页。 )。可见, “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注:《资本论》第三卷第198页。),或者说,“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是它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所有者”(注:《资本论》第三卷第672—673页。),是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的内涵比较宽泛,它既包括“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这种“典型形式”(注:马克思有时称之为“小块土地所有制”、“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自耕农的这种自由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等等。),也包括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形式的从属关系中存在的,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或劳动条件实际上的所有或占有。马克思提醒我们,“决不要忘记,甚至农奴,不仅是他们宅旁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虽然是负有纳租义务的所有者),而且是公有地的共有者”(注:《资本论》第一卷第785 页注191。)。这种小私有制根源于生产资料、主要是生产工具的细小、 简陋和原始。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注:《马恩选集》第三卷第308—309页。恩格斯也说过:“中世纪社会:个体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见《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41页。 )马克思又说:“在小工业和到目前为止的各处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注:《马恩全集》第三卷第74页。)
根据马克思上述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把小农经济界定为:农业领域内与简陋的手工工具相联系的、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以劳动的孤立性为特征的小生产。或者说,小农经济是农业中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小生产和小私有的统一。
以上是就共性而言。若就个性而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小农经济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同一国家、同一地区、同一历史时期的小农经济因其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的差别,也会形成不同的阶层和类型。这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的。
二、中国小农经济的起源和夏商时期的小农
如前所述,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因此,小农经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个体家庭的形成。个体家庭即一夫一妻制家庭不同于它所由脱胎的对偶家庭的主要之点是,它不但是一个共同生活和消费的单位,而且是一个从事生产和有独立经济的单位。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在野蛮时期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注:《马恩选集》第四卷第57页。)。个体家庭的形成是以分散的个体劳动的出现为其生产力前提的。马克思在谈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时说:“最重要的还是私人占有的源泉——小土地劳动,它是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和农奴等动产积累的基础。”(注:《马恩选集》第十九卷450页。 )据此,个体家庭的分散劳动和独立经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恩格斯也谈到交换如何使公社分化为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而“家长仍旧是劳动农民:他们靠自己家庭的帮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注:《资本论》第三卷第1015页。)。这应该视为最早的小农经济。
从我国的具体历史事实看,具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确实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我国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开始普遍发现小型的住房遗址,不少房子遗址除了有生活工具外,还有生产工具、粮食、窖穴等伴随出土;这种情况到了龙山文化时期更为普遍,并出现在小房子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双室或套间等较大的房子。这些住房的主人显然是具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它不但具有消费的职能,而且具有生产的职能。这表明个体家庭不但已经出现,而且其独立经济已有所发展。这一时期的住房遗址中,有些属于个体工匠的住房;但大多数个体家庭则是从事农业生产。(注:详见李根蟠、黄崇岳、卢勋:《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第430—4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这种情况,在古史传说中也可以找到踪影。如《韩非子·难一》载: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而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暮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注:《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淮南子·冥览训》说黄帝治理天下,做到了“农者不侵畔,渔者不侵隈”。《说文》:“畔,田界也。”这里所说的田界不是指公社间的地界,而是指个体农民所占有和使用的耕地的标界。“畔”的出现及其受到保护表明,当时的农民已在从事“小土地劳动”,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这种情形延至后世,如《史记·周本玘》载虞芮之人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左传》襄公十五年郑子产说:“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西周春秋时“农之有畔”,与黄帝尧舜时代一脉相承;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应该从黄帝尧舜时代算起。
夏商时代小农经济的史迹延绵不断、灼然可辨;当时的“众”和“小人”等,基本上属于小农的范畴。
夏商,尤其是商代,主要的农业劳动者被称为“众”。夏商的“众”,一些学者视为奴隶,看来是不恰当的。“众”在甲骨文中,作日下三人形,原意为太阳普照下的一群人;即“人三为众”(《国语·周语》)。进入阶级社会,“众”发生了分化,少部分成为统治者,大多数则处于被统治地位,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因此,“众”虽然仍然保持有“人三(指多人)为众”的意义,但更经常地用以称呼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如《左传》哀公元年载夏少康奔有虞氏,“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众”既是井田制下(“成”和“田”都是井田制下的编制单位)的农业劳动者,又是少康的战士。在商朝建立以前,汤曾征调“亳众”(亳地之众)的牛羊和劳力,供相邻的葛伯祭祀之用,并为之耕种(《孟子·梁惠王下》);说明这些“亳众”是拥有自己财产的农业劳动者。后来汤伐夏桀,对军队发表训词曰:
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亟之。今汝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征)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征)。(《尚书·汤誓》)这些被称为“众”的战士是具有个体经济的农民,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对抛下农活(即所谓“穑事”)远征服役发出怨言;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汤因而不能不向他们作出解释。因此,从卜辞看,“众”虽有沉重的兵役和力役的负担,但并不能抹杀他们是具有独立经济的小农的事实。(注:对于商代的“众”,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有奴隶说、奴隶主说、自由民说、族众说等。予取族众说,但认为这里的“族”,并非单纯的血缘组织。关于“众”的性质和演变,可参阅胡庆钧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众”相对于被称为“君子”的上层贵族来说,地位比较低下,故有“小人”之称。如《尚书·盘庚》,中篇是迁都前盘庚对民众的训话,上篇和下篇则是迁都后对臣僚贵族的训话,而要求他们向民众传达,“无敢或伏小人之攸箴”;这里的“小人”即中篇之“众”,或者是“众”的主体。从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看,夏商的“小人”之为小农更是无可置疑的。《逸周书·文传》引《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所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所有也。”《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这些“小人”从事农作以养家糊口,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的单位,当然是属于小农的范畴。
被称为“众”或“小人”的夏商小农,基本上是与贵族奴隶主同一部族或同盟部族之人,这是夏商小农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夏商尤其是商代存在“族”的组织,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不过我们不应把商代族的组织视为纯粹的血缘亲属组织,由于各部族之间的长期斗争,商人的族中已融合了众多的不同成分。商人的族的组织,延续到商朝灭亡以后。《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分封时,鲁公分得“殷民六族”,康叔分得“殷民七族”,族之下有“宗氏”(宗族),宗氏之下有“分族”(大家族),分族中有“类丑”。先秦古籍中多“族类”连称或并称之例,“类”当指同“族”之人。(注:“族类”连称例,如《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卫成公欲祭夏后相,宰武子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族类”并称例,如《左传》僖公十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杜注:“类,族也。”)“丑”则是指来源于俘虏的奴隶。(注:《诗·大雅·常武》:“仍执丑虏。”《笺》云:“丑,众也……执其众之降服者也。”大致这种奴隶主要来源于俘虏。)这里的“类”,其主体就是卜辞中的“众”,《尚书》中的“小人”。同一族体的人在原始社会里本是平等的,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君子”和“小人”这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阶级。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见《国语·鲁语下》)。小人虽然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备受压迫和剥削,有时甚至到了嫁妻鬻子的地步,但他们毕竟不是奴隶。他们保持了比奴隶高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国语·周语上》引《夏书》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以守邦!”虽然是奴隶主贵族调和阶级矛盾的一种说教,毕竟说明“众”与奴隶主贵族属同一族体,有相互依存、利害与共的一面。上引《汤誓》,汤以最高领袖之尊亲自向颇多牢骚的“众”说明伐桀的理由,“众”有此面子,决非毫无权利的奴隶。商汤十传至盘庚,因受洪水威胁而迁于殷,引起相当一部分臣民、包括一些安土重迁的小农的怨尤;迁都前盘庚召集民众训话,申述了“视民利用(以)迁”的衷曲,一方面对不服从命令的民众进行恫吓威胁,另一方面又套近乎,声称“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善也)民”,并许诺“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尚书·盘庚中》)。这些“民”显然与商朝统治者属同一族体的人,有一定政治地位,并有自己的独立家庭与生计。
夏商小农既从属于族的组织中,又生活在农村公社之中,这是夏商小农经济的又一显著特点。
古书中记载的我国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及其变体。它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汉武梁祠黄帝象有“造兵井田”的榜文。黄帝时代是我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私有制已经产生,部落与部族之间的战争相当频繁,故有“造兵”之说。但当时大规模开发黄河流域的低平地区,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修建农田沟洫系统,为了维护这种公共经济职能,不能不限制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从而导致了土地公有私耕的农村公社的建立,这就是原始的井田制。史称黄帝“明民共财”(《国语·晋语四》),以致“农者不侵畔”,应该理解为建立了农村公社的份地制。我国最早的小农经济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看来不是偶然的。以后,虞舜解决了“历山之农侵畔”的问题,使之“畎亩正”(《韩非子·难一》);传说大属治水,“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而夏王朝建立后,“以设制度,以立田里”(《礼记·礼运》):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以份地制和沟洫制相结合为特点的井田制的继续和发展。甲骨文中的田字为区划整齐的方块田的形象,说明我国方块田制已有久远的历史。为什么中国上古时代会形成方块田的形制?这是和修建沟洫系统的需要有关的。因为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中,以方块田的周边最短(圆形者除外,但一般土地没有规划成圆形的);在中国古代井田制中,土地经界和沟洫系统是结合在一起的,采用方块田制修建沟洫系统的工程量最少。(注:关于井田制中方块田的形制与沟洫系统配置的关系的论述,吸收了美籍华裔学者赵冈的观点。参见赵冈与陈钟毅合著《中国土地制度史》第一章第一节。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从周代的材料看,井田制下的田是有一定的亩积的,步百为亩,亩百为夫,作为农民份地单位的一“夫”即一“田”正是一个正方形的地块;这种方块田的份地大概由来已久。甲骨文中田字的形象所反映的就是沟洫制与份地制相结合的井田制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看到有垄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了的农村公社的地产。(注:《马恩全集》第19卷第453页。关于井田制和农村公社的问题, 拙著《井田制及相关诸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有所论述, 可参阅。)
在商代,田和邑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注:卜辞中有田邑相连之例,如:
沚戛告曰:土方征我东鄙捷二邑,邛方亦侵我西鄙田。(合6057正)
长友角告曰:土方侵我示至田七十人五(同上)。)这些邑许多就是农村公社。邑的本义是人们集中居住的聚落,商代的邑有多种类型和含义,其中最基本、最大量的形态是村落。商代的这种村落考古工作者已有发现。例如在山东平阴县朱家桥的殷代遗址中,发掘20平方米,出土小型房屋基址21座,其面积7—12平方米不等,房屋内都有灶坑、 一套陶制生活器皿和劳动工具,包括农具和猎具。这显然是一个邑即村落的遗址,而邑中的居民是以家庭为单位独立从事生产和生活的;这些居民理应是具有独立经济的小农。(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山东平阴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2期。 转见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7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关于商代聚邑的农村公社性质,杨升南曾根据河北蒿城台西等商代墓葬的葬式和人骨的“种”“型”等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这些墓葬中的人,其民族成份是很复杂的,埋葬在同一墓地中的,并非具有相同血缘的一群人。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商代的邑是农村公社而非家族公社。(注:见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二章第三、四节。)甲骨文中有“邑人”之称,邑人就是村社的社员。 这些“邑人”有自己的财产, 卜辞中有“呼邑人出牛羊”(合9741反)的贞问,《周易》中亦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得之,邑人之灾”(《易·无妄》六二爻辞)的记载。另外,邑人可以当兵,参加献俘典礼。邑人的这种经济与政治地位,和上述关于“众”和“小人”的记载是一致的。(注:杨升南认为“邑人”有别于“众人”,前者是村社社员,后者是奴隶。彭邦炯认为“邑人”就是“众人”(见胡庆钧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第四章)。予取彭说。但这里有一个矛盾:按流行的观点,“众”为“族众”,但邑落墓葬中却包含了不同种族的成分,应如何解释?我觉得不应该把商代的“族”理解为单纯的血缘亲属组织,它可能是以原来的殷族人为主体吸收了多种不同种族成分而形成的群体。这个问题还须作进一步研究。)
三、西周时代农民成分的变化
上文谈到,夏商小农多为本“族”之人,周族在灭商之前的情况与此相似。当时周族已进入阶级社会,本族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形成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劳动大众的阶级对立。这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所反映。但对该诗的时代性和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学术界理解很不一致,因此需要作一些讨论。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这首诗的时代性。毛序云:“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徐中舒《豳风说》斥为无据之谈,认为《七月》为春秋后期之鲁诗。李亚农已驳正之。(注:《李亚农史论集》下册第858—8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今补充论证如下:
1、李氏以卜辞(《殷墟书契后编下》三七·四:“贞, 隹[唯]火。五月。”)证明大火星在商代确实是以五月昏中的:其后逐岁渐差,殷周之际,乃以六月昏中,七月西流矣。与陈奂《毛诗传疏》说一致,甚是。《七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毛传》:“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二月也,民无不举趾以耕矣。”孔疏:“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月令》季冬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则修耒耜当在季冬之月,举足而耕,当以孟春之月者,今言豳人以正月修耒耜,二月始耕,故云豳土晚寒。”不但《月令》夏历正月春耕,《国语·周语》也是夏历正月春耕。毛、孔看到了这种差别,企图以“豳土晚寒”解释之。但在黄河流域,“豳”地(在今陕西省旬县西南)的纬度并不高,不应比黄河流域其它地区寒冷;故此解释是站不住脚的。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据竺可祯的研究,在古代气候的变化中,周初有一个短暂的寒冷时期。(注:竺可祯:《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变迁》,《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七月》诗中季节的晚寒, 正是周初气候寒冷期的一种反映。因此,无论从星象看或从气候看,《诗·七月》都应该是西周初的诗,而它的内容则是对周朝建立前情况的追述。
2、《七月》写农夫的生产和生活诚然是极其艰苦的, 但他们仍有自己的工具、住房,吃自己的饭;从这些情况看,他们应有自己的私田,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这和西周其他史料所反映的情况大体一致。但诗中还描写农夫在每年收获后杀羊设酒,到主人的公馆中去拜年,一派和乐融融的气氛:“朋酒斯嚮,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种情况说明农夫与主人是同族之人。虽然阶级分化已很明显,但仍有宗族或部族的纽带相联系。这应是周灭商以前的情形。因为周灭商后,周族各支被分封到各地,一个个成了卿大夫士,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夫一般是属于异族的,“野处而不暱”,不大可能出现《七月》所描写的场面。(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公子重耳流亡,向野人乞食,“野人与之块”,可为一对照。)但在周灭殷以前则是可能的。毛传的说法应有根据。
3、 沈长云在《由〈诗·七月〉论及西周庶人的社会地位》(注:载《人文杂志》1989年第6期。)一文中, 对诗中“殆及公子同归”一语作了很好的解释,指出“公子”是女公子,“归”是出嫁;这位农家女担心充当女公子的陪嫁。文中以凉山彝族的材料说明这种陪嫁女是从同族的下层民众中抽取的。《七月》诗中所反映的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领主制封建社会形态。我认为这正符合周灭商前的社会状况。
农业劳动主要由本族下层民众担任的这种情况,在周人灭殷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周的主要农业劳动者已不是本族的下层民众,而是属于异族的土著的或迁入的居民。
周族是以一个偏居西陲、地方百里的蕞尔小国而战胜“大邦殷”的。为了有效地控制其征服的广大地区,采取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语)的措施;据说光是姬姓国就分封了五十几个。周族灭殷时的人口,有人估计为六七万,有人估计为十五万人;(注:《李亚农史论集》上册第581页,667 —672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朱凤翰:《商周家族形志研究》第25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年。)当然不可能很准确,但人口不多是毫无疑问的。以这样少的人口分封到广袤地区内的众多国家里,与被封诸侯一同到封国去的周族人都是被武装起来的,“比户而封”,基本上都成了大小贵族,被称为“士”、“王人”。他们和为他们服务的工商居住在设防的城市——“国”中,而对居住在鄙野的,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土著居民实行统治。这就是西周的国野分治制度,《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治齐,实行国野分治:士与为其服务的工商居住在国中,士脱离生产,充当甲士;农居野,一年到头“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没有当甲士的权利,传称其“野处而不暱”,暱者亲也,农和士无论从阶级地位或民族成份看,都是判然有别的两种人。这据说就是取法于西周以来的旧制。要把握西周小农经济的特点,就不能不看到西周国野分治这一基本事实。
西周小农成分的这种变化,在其称呼中也反映了出来。从《诗经》看,西周的农民也有称为“众”的。如《周颂·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鎛,奄观铚艾。”这些使用各种农具从事耕作的“众人”,自然是农民了。在《诗经》中,农民更多地被称为“农夫”或“农人”。(注:西周农民称“农”的,如《周颂·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是农夫,播厥百谷。”《大雅·甫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农”在甲骨文中从林(或草),从辰,是手执石质工具清理场地,从事农作的形象,其本义当系指农业生产劳动。“农”用以表示从事农业的人,从文献记载看始于《尚书·盘庚》:“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劳作,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而《诗经》中则在“农”后加上“夫”或“人”。但农民作为一个阶层主要被称为“庶人”。“农”或“农夫”取代“庶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称呼,从目前的资料看,始自春秋,《国语·齐语》载管仲提出“四民”说:在那里,“农”与士、工、商同列为“四民”。到了战国时代,“农”或“农夫”作为一个阶层的称呼就相当普遍了。)不过不管“农夫”或“农人”,都是指具体的从事农业的人,本身似不含身份或阶层的意义。在西周以至春秋时代,农民作为身份与职业统一的一个阶层,其称呼是“庶人”。“庶人”在当时的社会等级阶梯中处于士之下,工商和奴隶之上。如《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隶食职,官宰食加。”所谓“庶人食力”,亦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其庶人力于农穑”。《国语·鲁语上》载:“……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庶人既与工商并列,其“业”显然是农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被称为“庶人”,这种情形延续至春秋战国,如《管子·君臣上》:“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时令者,庶人也。”
为什么商代的农业劳动者多称“众”和“小人”,而西周的农业劳动者则多称“庶人”呢?这不光是语言习惯的不同。“庶”虽然亦有“众”义,有时可以通众,但其基本含义是卑贱、渺小、旁出(与正出的“嫡”相对)。(注:周谷城:《庶为奴说》,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庶人”一词不见于甲骨文和《尚书·商书》中,(注:《尚书·洪范》中提到“庶人”,但该篇出于战国,未可为据。)但在金文和西周文献中却屡屡出现,看来,“庶人”作为一个等级的称呼形成于西周初年。这既与周人形成了嫡庶之制有关,也和当时的军事征服有关。“庶”往往用以指称被征服的外族人。如把周公东征胜利后迁于成周殷民称为“殷庶”,把一般被征服的部族或国称为“庶邦”(《尚书·召诰》)。《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三后(虞夏商)之姓,于今为庶。”盖周灭殷后,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把殷人都变为奴隶,而是让他们“各安其宅,各田其田”(《尚书大传·大战》),但殷人整个从统治族变为被征服的族,地位降了一等,被称为“殷庶”。(注:斯维至先生曾指出,甲骨文中有“众人”而无“庶人”,金文和西周文献中却习见“庶人”,众人和庶人是商周对农民的不同称呼。他又指出“小人”是同族之人,“庶人”是异族之人。(《论“庶人”》,《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二期)颇有见地。但他把西周的庶人等同于商代的众人,则可商榷。)周初分封,封国中被统治的劳动者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土著居民,二是外来迁民,他们都属于被征服者。例如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鲁公受封时,分得“殷民六族”,还有“土田陪敦”。所谓“陪敦”,即《诗·鲁颂·閟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的“附庸”,是指附着在土地上的土著居民。这种“附庸”或“庸”,屡见于诗和彝铭。上引《左传》文还谈到分封时让鲁公“因(统治、役用)商奄之民”。商民即“殷民六族”,奄民即这些“土田附庸”;除了殷民六族的上层外,他们都被称之为“庶人”。大约康王时的《宜侯矢簋》载周王把虎侯矢改封于宜,除赐其川邑外,还赐其“在宜王人”、“宜庶人”和“奠伯”辖下的“卢”人等,“在宜王人”是原属周王的周人族属,他们隨原宜侯被封于此,构成为统治集团。(注:裘锡圭:《关于商代宗族组织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 《文史》十七辑; 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268—269页。)“宜庶人”是原宜侯受封时的宜地土著和外来迁民,“王人”来到以后,他们全都变为“庶人”。“卢”人则是新的迁民,也加入“宜庶人”的队伍。这些“庶人”都是异族,处于被统治地位,比属于统治族的周人即所谓“王人”低了一等。他们主要居住在鄙野,被授予土地从事耕作,即所谓“鄙以权庶”(《逸周书·五权解》)。夏商的众和小人主要是同族人,西周的庶人主要是异族人;三代农民名称的这种区别反映了农民成分的重大变化。
庶人居野,故亦称野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公子重耳出亡于五鹿之郊,“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论衡·纪妖》引述此事时径称“耕者”。孟子向毕战陈述为滕恢复井田制的构想时说:“将为(有)君子焉,将为(有)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在西周,“野人”是以殷遗民为主体的跟泥巴打交道的农业劳动者,但他们原来的文化却比处于统治地位的周人先进。所以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野人亦称“氓”。“氓”之称,西周可能已经有了,《诗》中有以“氓”名篇者,其使用延至战国。如《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许行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为氓”。注:“氓,野人也。”“氓”,《周礼》称作“甿”,(注:“甿”,古本或作“氓”,如宋本《经典释文》作“氓”,宋本《白氏六帖事类集》卷23“给授田第26”引作“氓”。或作“萌,如”《说文》耒部耡字引《周礼》为“以兴耡利萌”,郑注亦作“萌”,清代学者认为古本作萌。)作为“六遂”(相当于野)农民的专称,以区别于乡遂居民的泛称——“民”。在有的场合下也称之为“野民”。《周礼》中的甿是农业生产的主要负担者,比起六乡的居民,负担重而地位低,在一定程度上仍反映了西周国野异制事实,虽则在《周礼》中国野之间的界线已经比较模糊。
总之,西周时代,特别是周初,构成农民阶级的主要成分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异族民众,而不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本族民众。
那么,西周是否存在本族的自由农民呢?有的学者认为西周的士就是当时的自由农民。这种观点尽管很流行,但恐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士作为周初实行宗法分封制所形成的等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是脱离生产的吃剥削饭的武士集团,属于贵族阶级的下层,不可能是自由农民。关于这个问题,将另文予以讨论。但这并不否认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西周春秋时代也出现了身份比较自由的自耕农。虽然西周初年周族人一般都成了卿大夫和士,但他们这种贵族地位的保持是以有充足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保证宗法分封制的持续实行为前提的。在西周初年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条件是大体存在的。但随着贵族的支庶繁衍以及他们之间斗争的日益激烈,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势必有一部分贵族或其后裔趋向衰落,其中有些人变成了自耕农。上文说过,自夏商以来,君子和小人是同族中阶级分化的产物。但商代“小人”与被称为“众人”的农民基本上是同一意义,而周代“小人”与被称为“庶人”的农民的含义则有相当的差别。《诗经》中也有君子、小人之别。如《小雅·采薇》:“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矛盾已经存在,但在西周早中期还不是很尖锐;也看不出这些小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豳风·东山》大约写于西周初年,诗中描写一位当兵的自由民想家,想象中的家变得很荒凉,但还是在想,“不可畏也,伊可怀也”;又回想起新婚时的排场,有不尽的思恋。论者多以此作为周代自由农民之例证,可商。这首诗反映了频繁的战争和沉重的兵役造成部分“士”的困顿和怨烦,但并不能证明其主人是一位农民,且离家三年,若无庶民代耕,其家计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更可能是一个“职业”武士。《王风·黍离》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这是战士的妻子思夫之作。诗人称其夫为“君子”,应属“士”阶层。但从诗中对鸡儿进窝、牛羊下坡的描写看,是一派的田园风光;则这个“士”有可能已经务农了。《诗经》中反映自耕农情况最为清楚和确定的诗篇,是《唐风·鸨羽》,但时代已相对晚后。这首诗写一个战士由于没完没了的服役,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以赡养父母,而发出的怨恨之声。“王事靡監,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这应是有一定政治地位的由士转化而来的自耕农。诗序说:“刺时也。[晋]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而作是诗也。”三家无异词。晋“五世之乱”见《左传》桓公二、三、七、八诸年。是时许多公族子弟沦为自耕农,但仍要负担军赋。大体说来,到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以后,包括士阶层在内并贵族分化越来越剧烈,不少变成了自耕农,作为重要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小人”问题才逐步凸显出了。
四、西周小农独立经济的存在
我们在上文已论证了中国小农经济起源于黄帝尧舜时代,夏商小农经济的史迹灼然可见:那么,西周时代存在小农经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学术界不少同仁否认西周的农民是独立的小生产者,因此,对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进行讨论。
关于西周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诗经》的农事诗有较多的反映。一些学者根据其中“十千维耦”(《周颂·噫嘻》)和“千耦其耘”(《周颂·载芟》)的记载,认为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奴隶劳动,说明农民并非独立的生产者。
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诗经》中的农事诗主要描写农民在贵族领主“公田”上服役的情况,其描写的劳动场面较大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所谓“十千维耦”、“千耦其耘”,并非象有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一次出动两万农夫的大兵团作战式的集体劳动;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徐中舒先生曾经指出,《噫嘻》中的“十千”并非指一万个农夫,而是指面积为十个“千亩”的公田(西周公田以千亩为单位,周王室的公田有十个千亩之大),而《载芟》中的“千耦”则是指一千个农夫在耦耕。按“什一而藉”的比例,十个千亩正好需要一千农户来助耕。(注:《先秦史论稿》第98—101页, 巴蜀书社,1992年。)这个解释是相当合理的。为了便于监督,农民在公田的服役无论时间和人员确是相对集中的,于是有《诗经》中描写的那种场面。但我们不能机械地认为“千耦其耘”刚好是一千个农夫同上一块地,因为这是诗的语言,实际上可能是“千夫”轮流股役:即使在相对集中服役时,也不是“大呼隆”地干活,而是分开配对儿协作的,即所谓“耦耕”。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耦耕”。
耦耕本身并不要求大规模的集体劳动,不能把耦耕等同于大规模的集体劳动。从技术上讲,耦耕是以两人为一组的简单劳动协作,其原始形式是两人各执一耜并排挖沟起垄。《考工记·匠人》云:“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甽。”郑注:“古者耜一金,两人并发之。其垄中曰甽,甽土曰伐,伐之言发也。”后来耦耕这种劳动协作方式扩展到各种农活中去,但仍然以两个人为一组。如《论语·微子》记载“长沮桀溺耦而耕”,“协而耰”,只有两个人。如往上推,象尧舜禹时代的“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馥”(《世说新语》),也是“协而耰”,亦应为二人,而不是大规模的集体劳动。
从生产关系方面讲,耦耕是独立生产者之间在对等基础上的换工协作。《说苑·正谏》云:
楚庄王筑台,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御诸己者,违楚王百里而耕,谓其耦曰:‘吾将入见王。’其耦曰:‘以身乎?吾闻之,说人主者,皆闲暇之人也;然则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诸御己曰:‘若与予同耕,则比力也;至于说人主,不与予(按,予原作子,今按前后文义改为予)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见庄王。这里谈到了耦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比力”,即耦耕伙伴体力要相当。所以耦耕的编组又叫“比耦”(《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我先君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或“合耦”(《周礼·地官·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趋其耕耨。”)。正如程瑶田在《沟洫疆理小记·耦耕义述》中所说的:“合耦者,察其体裁,齐其年力,比而选之,使能彼此相佐助而耦耕也。”为什么要“比力”呢?因为这是具有独立经济的小生产者之间的换工协作,是要讲求对等的。而“庸次比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逸周书·大聚》)中的所谓“庸”,就是换工的意思。(注:“比力”不能从技术上的原因来解释,有些农活,如并耜挖沟,合作者体力大体相当,但也不是很严格的;另外一些农活,如一人耕一人耰的“耦耕”,从劳动本身看,完全用不着“比力”;所以,“耦耕”之所以要求“比力”,只能从生产关系方面寻找原因。关于耦耕的解释,详见拙作《耦耕纵横谈》,载《农史研究》1983年第1 期,农业出版社。)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耦耕而否认当时有独立小农经济的存在。
另一些学者认为西周农民是以家族公社为生产和生活的单位的,因而也否认西周存在独立的小农经济。其主要论据是《周颂·载芟》: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租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疆侯以。
毛传说:“主,家长也;伯,长子也;亚,仲叔也;旅,子弟也;疆,强力也;以,用也。”这些学者据此认为,当时整个家族公社的成员都出动参加劳动,表明农业生产是以大家族为单位的。
我们知道,《载芟》是“春藉田而祈社稷”(诗序)的乐歌,它描写的是藉田劳动的场面。参加藉田的人,不可能出于同一家族,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无论如何是完成不了公田的耕作任务,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即使是参加藉田的农民中存在着若干家族组织,也不可能每个家族都是整个家族的成员全部出动。因此,如果毛传的解释是可靠的话,它也只是表明参加藉田劳动的有各式人等,并不表明这些人都出自同一家族。据赵光贤的考证,诗中的“主”指周王,“伯”、“亚”、“旅”都是官名,是卿大夫之类,他们来参加籍田礼只是一种形式;只有“疆”和“以”才是“终于千亩”的庶人。其中“疆”是指农夫中的强劳力,“以”是辅助劳力。这个解释是颇有道理的。(注: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80—8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无论如何,不能根据《载芟》的上述记载得出西周以一个家族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结论。
《周颂·良耜》:“获之挃挃……以开百室。”郑玄笺:“百室,一族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间而耕,人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欢。”这也被认为是西周存在家族公社的证据。其实,《良耜》中的耕者是“野”中的居民,“百室”只是亟言其多,不应作机械的理解;(注:《诗经》中屡见“百谷”、“百卉”、“百川”、“百礼”、“百禄”、“百尔君子”等,均为泛指,不能着实为一百;如果那样理解,肯定要脱离实际。)其中并没有家族公社存在的痕迹。郑玄无条件地相信后出而真伪杂揉的《周礼》,本来就有问题,《周礼》中乡遂异制。“六乡”编制中有族党之称,“六遂”田制中有“百夫共洫”之说,但无族党组织。郑玄把两者牵合在一起,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即使就《周礼》所载“六乡”之制来看,虽存族党之称和同族共葬之类的风俗,但其反映的只是家族制的孑遗,“六乡”居民都是一些五口至七口之家,以家为单位“均土地”,实行小家庭的独立经营,并不能构成“公有共耕”的家族公社。因此,郑玄的上述解释是不足为据的。
西周实行宗法制,在先秦古籍中,关于西周春秋时期“族”的记载俯拾即是,而宗法制是由父家长家族演变而来的:这种现象最容易使人迷惑,认为当时必定存在家庭公社。其实这些记载所反映的大多是社会上层的情况,而不是社会底层的情况。我国西周时代的确有大家族,但只存在于士阶层以上的贵族阶级之中,而不存在于庶人之中。周代的大家族以宗法制的形式出现,贵族行宗法,庶人无宗法,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生活的单位,称为匹夫匹妇。《左传》桓公十年:“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疏:“士大夫以上则有妾媵,庶人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虽单亦通,故书传通称之匹夫匹妇也。”《白虎通·爵》:“庶人称匹夫者,匹,偶也:与其妻为偶。……一夫一妇成一室。”从现有的资料看,西周农民家庭的规模是不大的。例如《尚书·大诰》中有“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的记载,表明这些农夫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而这些家庭大概是由父子两代组成的小型核心家庭。《诗经·豳风·七月》是描写农家生产和生活的,“嗟我妇子,入此室处”,同样是一个核心小家庭。《周礼》是比较晚出的书,也有些可供参证的材料。《地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代农民家庭的规模。《地官·遂人》讲对居野之“甿”的治理,更多地保存了西周农民的史影。其中谈到了“以下剂致甿”。所谓“下剂”,即上引《小司徒》“下地家五人,其可任也者家二人”,以此作为授田和征役的依据。虽然这是表示对“甿”的“优惠”,但也反映了居野之“甿”中五口之家的普遍存在。有的学者根据考古发掘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指出西周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为39岁,以二十岁为一代,儿子20岁时,父亲约40岁,正当平均死亡年龄节。所以大多数家庭只能是二世同堂的核心家庭。又以张家坡遗址为例,指出农村公社成员长期占有的住宅实际上已为私有,房址旁一般有家庭独用的水井,房址及房址附近的灰坑中出土较多的农业工具,表明以居室为代表的个体家庭已成为农业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注:李朝远:《西周土地关系论》第261—263、 191—1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由此看来, 《周礼·地官·遂人》的“以下剂致甿”是颇有根据的。
总之,认为西周农民以大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即使是在《诗经》描述农民在贵族公田上服役的诗篇中,也可以看出这些农民是有自己的独立经济的小生产者。例如他们有自己的农具。《周颂·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鎛,奄观铚艾。”这首诗是写贵族领主在麦收前检查生产,这句的意思是命令我的农奴们(众人),收藏好你们的钱鎛(中耕农具),准备开镰收割了。《小雅·大田》:“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这首诗是以农民的口气写他们在大田上的农业生产,所以备耕工作称“乃事”,耕具则是农民自备,故称“我耜”。总之,这些钱鎛铚艾和耒耜,是属于农夫的。他们吃自家的饭。如《周颂·良耜》记载农妇到田间送饭的情形:“或来瞻女,载筐及莒,其饟伊黍。”《周颂·载芟》则把农夫农妇在田头吃饭时的情态描绘得活灵活现:“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显然,这些农夫是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和生活的。
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农夫有其实际使用和占有的土地——“私田”。从描写农夫在公田服役的诗篇中,我们仍可窥见农夫私田存在的事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田》:“有渰淒淒,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里的“私”指“私田”,即农民的份地,历代注家无异辞。说明农民除了要耕种公田外,还有自己的私田,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战国时孟子引述这句诗后说:“唯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他把这里的公田私田与助法联系起来,“私”为农夫的私田已在不言中。但反对者说,《大田》不是农夫的诗,也不是为农夫写的诗,诗的作者对“王事”忠心耿耿,诗中的公私关系决不是阶级对抗的关系;故诗中的“我私”不是指农夫的私田。那么它指的是什么呢?论者引述《吕氏春秋·务本》“诗云:‘有晻淒淒,兴云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认为“私”是指“三王之佐”之类的贵族。(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少。如周自强《论西周主要农业生产者的阶级地位》(载《华夏文明》第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其实,《吕氏春秋·务本》只是取诗中“由公及私”之义,这就是所谓“断章取义”,丝毫没有把“私”看作“三王之佐”的私田的意思。所以高诱作注时把“私”理解为农民的私田,这无疑是对的。《大田》诚然不是农夫写的诗,但确确实实是以农夫口吻写的诗,故诗中的“我”只能是农夫。如诗中“以我覃耜,俶载南亩”,这个拿着耜耕地的“我”,难道不是农夫,而是什么“三王之佐”吗?诗的作者确实没有脱离贵族的立场,表现了对王事的忠心,但也多少表达了一点农民的愿望。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虽含有“先公后私”的说教,但也反映了农夫在公田上服役时仍然不能忘怀于他们的私田。
有关的证据还见于《周颂·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是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诗中前四句是成王命令田畯率领农夫播种:后四句是田畯秉承成王旨意让农夫在公田和私田上进行耕作。这里的“私”,也是指“私田”,与《大田》同例。毛传:“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让于下,欲民大发其私田耳。终三十里,言各极其望也。”当时一般来说,是先要完成公田的耕作任务,然后才能从事私田的耕作;“骏发尔私”是成王为兼顾公私而施惠于民,故诗人大书而特书。郭沫若谓“私”为“耜”之借字,误。赵光贤指出,“发”的对象只能是田土,不能是耜:因此,“私”只能解释为私田,因四字一句,故省田字。(注: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按汉代仍有称耕田为“发”者,见《九章算术》;赵说是。如果把“终三十里”都视为公田,把“十千维耦”理解为二万人在方圆三十里的田场上耕作,那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终三十里”必然包含助耕公田的农夫的私田在内。徐中舒先生指出:“私”是私田,“十千”是公田。十个千亩的公田由千夫耕种,每夫又各耕私田百亩,千夫共耕私田十万亩,公私田共十一万亩,都分布在三十里的范围内,所以说“终三十里”。“三十里恰好是一天可以来回的路程,因此籍田和份地的最好安排,是千夫围绕着十个千亩而居。”(注:《先秦史论稿》第98—101页,巴蜀书社,1992 年。或把“十千”理解为万夫,徐氏指出,以五口之家计,万夫起码有五万人:三十里地容纳五万人,先秦时代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口密度。我们还可以换一种估算方法。如果按每天耕田百亩(不算休闲田)计,“十千”夫需要耕地百万亩。但方三十里即使全部是耕地,也只有八十万亩左右,按方里而井计,顶多能安排八千夫。还没有把道路、河流、房屋、荒山等非耕地计算进去。所以,这些解释的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解释最为合理。
私田的存在还可以从《诗经》的其他篇章中找到证据。例如《大雅·韩奕》:
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为伯,实庸实壑,实亩实藉。这是讲周王封韩侯于北国,以追、貊为其属民,韩侯在其封地中建筑城池、区划土地。在区划土地中,既要划分农民的私田(份地)——“亩”,又要从中划出公田——“籍”来。怎么知道这里的“亩”是指农民的“私田”呢?《左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这个“藉”就是“藉田以力”(《国语·鲁语》)的“藉”,即公田:“亩”是“藉”以外的耕地,显然是农民的“私田”。两条记载正好相互印证。又,《尚书·大诰》:“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穑夫”即农夫,这说明农民使用的耕地确实是称为“亩”的。亩字的古文或从“亩”从“厶”,见《字汇·田部》。“厶”即古“私”字。《韩非子·五蠹》:“仓颉之初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近人柳诒徽曰:“自环者,人私其居,筑为垣墙,以自围匝也。?(注:《中国文化史》上册第31页,正中书局1947年。)证之以民族学的材料,它实际上是指农村公社时期作为“第一块私有土地”的园宅。古亩字或从“厶”,正是“亩”为私田之称在古文字中留下的痕迹。
在反映西周农业劳动者状况的其它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小农经济的存在。例如,《国语·鲁语》载孔子追述西周的制度,说当时是“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这说明西周的农民是围绕着公田分散居住的,他们的住所距离公田远近不一;他们不是奴隶,而是拥有自己的独立经济的个体农民。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产生按其住处距离公田的远近平衡其力役负担的需要。(注:详见拙作:《春秋赋税制度及其演变初探》,《中国史研究》,1979第3期。 )《国语·周语上》载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极力反对。他认为举行籍田礼不但是为了在籍田中生产供祭祀祖先神祗用的粮食,而且也是为了劝导“庶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使“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时,财用不匮,民用和同”。如果不行籍礼,就等于放弃了先王重农、劝农的传统,就会“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于民?”从这一记载看,被称为“庶民”或“民”的农民是有其独立经济的。他们除了耕种籍田以外,还有自己的私田,所以要“修其疆畔”(这里的疆畔即上文多次引到的“畔”,乃是农民份地的田界);他们有自己的农具,所以能“日服其鎛”;他们在私田中生产的产品是他们自己可以支配的财富。《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之言,也主张对“民”要“懋正其德而厚其性(当从王念孙读作生),阜其财求(当从汪远孙读作赇)而利其器用”。也说明“民”(其主体是“农”)是有其自己的工具、财产和生计的。
有关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它们无不表明西周时的农民是有其“私田”和独立经济的。西周时代小农经济的存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标签:小农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论论文; 七月论文; 农民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家庭论文; 井田制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