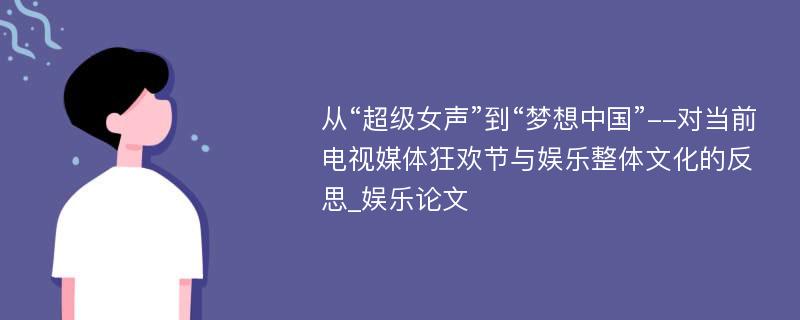
从“超女”到“梦想中国”——对当下电视媒体狂欢娱乐的整体文化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超女论文,梦想中国论文,媒体论文,电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刚刚才偃旗息鼓的“超级女声”似一股突然袭来的飓风,在各种媒体炒作和成千上万的所谓“粉丝”(FANS)的鼓动下,声势浩大地影响着当下商业化了的大众文化的定位和走向。这场由湖南卫视和天娱公司主办的长达半年之久的真人秀节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狂欢娱乐浪潮,900万的短信投票,4亿人次的观看,至少15万人参赛,超过《新闻联播》黄金时段的天价广告费用……就连《时代》杂志亚洲版也来凑热闹,竟让李宇春登上了《时代》的封面亮相,而致使千百万“粉丝”们欢欣雀跃,百感欣慰,终于迎来了平民狂欢的胜利和国际娱乐界的承认。其实2005年的媒体狂欢娱乐不止“超女”,在“超女”运动掀起不久,中央台随即推出了一档同样是高收视率的轰动一时的所谓“梦想中国”,而上海电视媒体也不甘落后地搞了一次来自全国各地少男少女们一齐参与的“我型我秀”。只是由于“超女”的风头实在太大,使得“梦想中国”和“我型我秀”等相形见绌。随之而来的关于“超女”这一文化现象的评论也同样是铺天盖地,网上的帖子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说好的,认为“超女”的海选与评分机制与西方竞选模式相似,是民主政治在中国的一次预演,是草根阶层登上文化舞台的典型代表。说坏的,认为这是一种伪民主,是一种集体性癫狂,“文革”和“传销”都带有这种特质。不是全民娱乐,而是全民“愚”乐。暂且不说“超女”所引发的争议和有关评论的孰是孰非,从“超女”到“梦想中国”,这一中国当下的媒体狂欢娱乐文化,绝不会因“超女”的稍稍停歇而被人们所遗忘,很难保证来年不会有第二次“超女”或类似“梦想中国”、“我型我秀”的节目出现,为此,当这些风靡全国的狂欢节目暂告一段落,稍稍冷下来时,倒恰恰值得我们去认真作一番反思:即从“超女”到“梦想中国”究竟怎么会出现的,它们的兴起反映着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一种什么样的情结?中国的大众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而这正是我们对由电视媒体操纵的娱乐版全民狂欢作整体反思的主要原因。
一、当文化真正成为商品,“市场”的意义就被放大了
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说文化产业,但文化如何产业化却是一个不易说清楚的东西,文化产业化的一个重要保证就是必须有真正意义的文化市场。从“超女”到“梦想中国”,你说它们是媒体事件也好,社会事件也罢,总之,当文化、大众艺术一旦成为商品,策划者、组织者自己就会从市场和消费的角度去思考它们的出路。诚如杰姆逊所言:“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理论家用自己的理论来发财,而是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产品。”①
不可否认,湖南卫视和天娱公司是本次选秀活动的最大受益者。从前期庞大的短信投票数额、广告商上亿的投入、广告时段天价的招标,到后期各种形式的演唱会和歌迷会,相关衍生产品的开发等等,“超级女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节目形式,而是已经产业化了,出现了所谓“超女经济”、“梦想产业”。或许“梦想中国”、“我型我秀”等娱乐狂欢节目的收益,因涉及到太多的商家机密,难以准确地统计出来,但从“超女”活动与信息的互联,可以看出这类所谓“事件”的背后,是文化市场史无前例的被拓宽、被占领了。策划者和组织者从美国一档普通的“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得到启发,中国化地引进后,使之成为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品牌,为了能取得最大的商品效益,电视工作者们费尽心思,从海选的原生态展现和全程记录,到评委的极尽挖苦之能事,再到网络游戏中引入的PK大赛,短信投票率来决定选手的淘汰等等,这些手段和花招的背后都直接和收视率挂钩,都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而追求高额的商品利润,强化商业动机本身恰恰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典型的内驱动力。据统计,“超女”事件中不完全的手机短信收入就是3000万,光碟销量突破百万。首张《超级女声终极PK》首批已发行了60万张,总销售量肯定将突破百万。而走红或胜出的“超女”们,如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何洁、纪敏佳、叶一茜等人接下来的巡演、包装后的签约唱片公司和参拍影视剧,又将为组织者、唱片公司、影视公司等打开新的生财之道,更不用说“超女”的广告收入上亿元,“梦想中国”、“我型我秀”的广告也都令人瞠目结舌。蒙牛公司因冠名“超女”,其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主办方湖南卫视所属的上市公司电广传媒的股价也迅速攀升,市值已增长1.24亿元。湖南卫视也再次对央视提出最具威慑力的挑战,一下子将几亿观众的眼球从被美国、日本、韩国流行文化长期霸占的市场上抢了回来。而且,“超女”在华人群体里掀起的热潮,又吸引了海外媒体,大量身处世界各不同地区的“粉丝”,在号称海外华人第一门户的“未名空间”网络上掀起了追捧中国女孩唱中文歌的热力竞赛,如,弃明星而投“超女”,投“梦想中国”中所谓的“翻版刘德华”吴文璟一票,在美国暑期大片的档期追看中文电视的娱乐节目,在BLOG中记述他们的观后感,各种“帖子”的热门话题都远隔着太平洋在追逐着中国流行节目的兴奋点,不仅国内文化市场,世界文化市场也被冲开了,中国的大众文化终于以成人版的“欢乐蹦蹦跳”形式杀出了一条血路,使全球化中的年轻一代将目光都投向了中国的“流行偶像”。于是乎,全球化梦工厂里的“中国特色”不再是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李连杰的拳脚功夫,而是一夜成名、梦想成真的活生生的少男少女。
当文化真正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被注册、被冠名后,电视与流行的紧密结合就必然会产生出巨大的商业利润,“市场”被放大,“市场”已不是一个空洞的标签,而成了实实在在的捞钱、发财之所的代名。大规模的文化消费也终于有了真实而具体的落实,它再次证明了阿多诺所说过的大众文化产品的背后,是“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流行文化,一旦真正流行起来,它就是货真价实的商品,不管是“海选”、是“竞赛”,电视提供的恰恰就是一个吸引市场的传播平台。正如费瑟斯通曾说过的“使用‘文化消费’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垄断市场等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② 而且,当文化成为一种商品,一种正在流行的消费品后,则不仅电视广告收入剧增(其实广告收入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它的后续连锁产业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如手机、网络、影视公司、图书、服装、拍卖等等一起参与,风潮一浪胜过一浪,市场的意义被突显出来。电视台与传媒公司迎合青少年的流行欲,共同推出了一种大众狂欢式的电视品牌→然后获取巨额利润→再轻而易举地操纵青少年的流行文化市场获取新的商业利润(发行唱片、图书、推出新人参与的影视剧等等),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没有商家的背后推动,即使是“超女”这样的时尚节目,也难以形成如此规模的流行文化,可以说,电视媒体与各种商业公司的合作,推出品牌节目,产生轰动效应,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拓宽市场的一个必然结果。从“超女”到“梦想中国”此类节目的产生,可以证明中国当下的电视策划人,传媒公司的组织者已经变得非常聪明,也变得极具实用性,他们认识到了文化商品的价值,不管评论家如何说三道四,任凭风浪如何拍打,反正他们要的是抢争市场,占领市场,这就是游戏规则,就是以文化“嘉年华”的形式通过集体狂欢来赢得他们自己的“嘉年华”。
二、在“造星”运动的背后——“明星梦”与“狂欢”:青少年的一种内心理需要
从“超女”到“梦想中国”实际上走的就是商业操作的“造星”运动路子。尽管《梦想中国》的总导演周怒则曾说:“‘超级女声’为了争夺观众的眼球,有时不惜以‘丑’来吸引观众。……这是一种纯粹的‘商业化’炒作,利用的是人们喜欢窥视别人丑恶的阴暗心理,缺少对真正艺术的尊重”③。但其实《梦想中国》在整个组织和录制中同样也不乏以出“丑”来招徕观众的视线,或借普通百姓毫无自知之明的心态,以他们的丑态来逗乐观众的画面,特别是总决赛后的“精彩”过程回放,其中那位“五音不全”的革命歌曲演唱者的认认真真的“走调”表演,更是缺少对艺术的尊重,二者都是“商业化”炒作,都想利用人们各种明视或窥视的心态来达到赚钱的目的,何须厚此薄彼、遮遮掩掩呢?而这种与所谓“真正艺术”的大相径庭,不恰恰正是对所谓“庶民的胜利”的另一种注解吗?
“超级女声”和“梦想中国”都存在着令成群的青年学子不惜逃课奔赴充满酸涩,甚至痛苦的“海选”赛场的情景,这种不同版本的“想唱就唱”和“受挫就是好”,似哄抬物价似的人为包装,是当下电视媒体狂欢娱乐秀的共同特征,这就是人为“造星”运动背后的商业动机,只要有人来唱、来跳,我们一概允许登台表演。所谓“零门槛”,只不过是一种当下商业策划的手段而已。当然,真正胜利的除了商家、电视台外,还有最后成功的超女们,但是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以及“梦想中国”的最后赢家吴文璟都是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他们本来就是专业艺术团体或亚专业艺术团体的后备人选,而绝大多数的各种所谓“真人秀”无非是陪太子读书。在“海选”过程中,那些五音不全、相貌不佳,又敢于大胆亮相,穿着奇装异服,脸上涂得花里胡哨,声音尖锐难听,毫无乐理知识,却又试图用搞笑的手段来吸引评委的选手,当她们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时,自身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只是为了寻开心,满足一种可以在公众面前发泄的欲望罢了,因为这场选秀比赛没有传统节目中的框框条条和各种规则的制约。
问题在于,为何能推出“造星”运动?不正是因为它迎合着青少年群体的内心理需要嘛?所谓“流行歌曲”就是一拨拨地将旧的流行送走,又迎来新的流行,当如今四十多岁的人还时不时地哼着邓丽君的情歌时,三十多岁的人已认为这实在太老,这只是怀旧;而当三十多岁的人还在留恋着崔健的红色摇滚时,二十多岁的人则认为那不过是上世纪的故事。如今十几岁的青少年嘴里唱的究竟是什么,或许永远只有他们这个年龄段才知道。这说明“明星梦”始终是青少年时期的一种心理情结,青少年一代代长大,长江后浪推前浪,几年前的小不点如今又成了新的青少年,于是,追星族永远存在,不同的只是谁成了新的追星族。一个新歌手只要上台后伴有无数尖叫和荧光棒的追逐,一夜间就成了明星。周杰伦的《蜗牛》入选教育曲目时,不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吗?追捧明星的潜在心理意识是,“我”也想,或我也可能成为“明星”,而且,一次唱红就能立即成名,又何须去读书、升学、排名次、挤来挤去地参加什么就业竞争呢?寻找成功的捷径,像明星那样被人抬举,有钱有名,光彩照人,何乐而不为?“超女”、“我型我秀”、“梦想中国”给青少年的启示是,我们完全可以摆脱父母、学校为我们制定的人生轨迹,去造就自己的“超级”和“梦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文化市场的公平竞争来实现自我的价值,于是,在应试教育的传统成长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新的快捷而又轻松晋升的途径——走上荧屏,成为“超女”或者“我型我秀”去吧。尽管明知道,几十万人中,最后的冠军只有一个,入围者也只有几人或几十人,绝大多数参与者都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不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吗?失去了这一次,还有下一次,下下一次。于是“造星”运动应运而生,“造星”就是给没有机会的人造出机会,“造星”就是抹平明星与常人的界线,而且“造星”运动这种媒体亮相的比拼比之主流教育模式中接受的价值观更为现实、坦诚,也更为公平。
支撑“造星”运动的另一个群体心理需要是合法化的狂欢娱乐。过去我们总认为狂欢是西方人的普遍需要,西方才有“狂欢节”,其实在世界各国的民族节日、民间舞蹈和民俗中都有狂欢,狂欢是一种欲望的释放,尤其是当人们又唱又跳,伴随着身体扭动、尖叫和人潮的涌动时,狂欢就成了释放欲念、轻松一下,甚至返朴归真的最佳手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狂欢的民俗和群体释放也不少,比如集体打腰鼓、舞龙、舞狮、赛马、扭秧歌,“最能体现大众狂欢的是各种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如‘三月三赶集’、‘火把节’、‘泼水节’等都是独具民族特色的东方式狂欢节”。④ 在“火把节”、“泼水节”中,不分民族、国别、男女、老少,一起狂欢,周恩来总理当年在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时照样与人们互相泼水、嬉闹,被淋得浑身是水,人们都笑逐颜开,他本人也毫无怨言。这时,一切“尊尊、亲亲、长长”的地位、界限、等级、秩序都被抹平了,“所有在场的人都被狂欢而揭去了平日的身份面具,在瞬间还原为一个所谓‘本真’的自我状态”⑤,就此而言,集体狂欢肯定会被大众娱乐、消费文化所欣然接受,正如巴赫金曾指出的“狂欢不是供人们驻足观赏的……它的参与者们置身其中”,它“将宗教与世俗、位尊权重者与卑微贫贱者、伟人与无名之辈、智者与愚夫结合在一起”,并使得“人性中隐性的一面被揭示并体现出来”。⑥
青少年的内心深处和潜意识中易被狂欢所煽动的倾向性肯定更加明显,他们好动、善变、求新求异的期望也更强烈,加之主流教育方式的千篇一律,整一而又呆板,教育方式是“个体服从群体”、“胜不骄,败不馁”、“懂礼貌,要规矩”等等,青少年天性中的本真,他们的欲望、躁动、感情、追求都被有意无意地抑制了,因此,当“超女”,“梦想中国”一类的电视狂欢娱乐一旦出现,就必然迎合着他们想释放的心理需求,他们奔走相告、共同参与、有欢笑、有泪水、有呐喊、有感动,在狂欢中他们实现着集体解放,同时也是对现存教育体制和父母望子成龙的另一种反叛。于是就出现了学生宿舍的所谓“暴动”场面,出现了不亚于看“世界杯”时的废寝忘食,出现了一个高中女生为了给自己的“偶像”手机投票,花了家里两个月的生活费,而更多的追星族则是选择集体逃课,上街拉票等现象。
毫无疑问,“封杀”狂欢式娱乐是不可能,也无必要的,但“超女”等因此而产生的另一种效应,乃至青年学生逃课去亲身体验等等,难道就一点不值得媒体和电视工作者们去深思和反省吗?更应反思的是,我们应当如何利用这类电视媒体所提供的狂欢娱乐,在满足青少年需要狂欢释放的过程中,注入更多的审美性、知识性和一定的理性思考,同时对“明星梦”本身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让娱乐与读书、狂欢与冷静、感性与理性能更恰当,同时也更带责任感地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才能在展示民主、才华、成功中添加进更多的深度追问,也才能使我们的电视娱乐节目既能有商业性回报,又能给青少年一些正面引导,而不至因太过媚俗竟完全背离了社会的普遍价值观。
三、悖论中折射出的争议与启示
从“超女”到“梦想中国”,所有此类媒体策动的集体狂欢都必然会伴之以相互矛盾的悖论。例如所谓“零门槛”,只要你填个报名表即可参加“海选”,但没有了门槛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集体狂欢、集体逗乐,许多人认为只要能在电视上亮相,即使在一开始就被淘汰也行,只要自己觉得开心,管它唱成什么样,一切都无所谓,其中还有不少“超龄女声”也在起哄、凑热闹。这是娱乐选秀,还是一场持久的开放的群众游戏?如果说“超女”、“我型我秀”在名称上还比较模糊的话,则“梦想中国”的名称,其实更离谱,“梦想中国”,顾名思义是拿整个中国在作梦想的载体,人们立即可联想到难道中国的梦想就是一帮年青男女在唱唱跳跳中最后成为明星吗?是梦想中国还是梦想成为明星?这是两个完全不能划等号的不同概念。
又如,有人提出精英文化使人感到沉重、疲惫,草根文化具有巨大的亲和力和平民性,那么是否所有的理性都应被消灭,系统的规范的知识体系都必须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大众的狂欢,是感性的发烧,是对知识的不屑一顾?如果说如今的教育体制只能培养“高分低能”学生的话,有了“超女”就一定会转而成为“低分高能”或“高分高能”呢?那么设计和制造中国的原子弹、长征号系列火箭、“神舟六号”的工程师、科学家都是外国人或都是海归派吗?众所周知,不管是梦想中国,还是中国梦想,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一切都是空想,别说中国实现不了自己的强国梦,即使是“秀”得再好的“女声”也绝不可能因自己国家的文化荒芜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批青年学生的逃课和对“超女”现场的心向往之,使得“娱乐”与“教育”发生了正面冲撞,当然,你可以说这是“轻松对抗沉重,娱乐对抗说教”,沉重与说教的确令人讨厌,但教育就一定都是沉重和说教吗?更何况全世界又有哪一种教育体制能少得了应有的沉重和说教呢?至于说到在展现自我,实现自我,是否所有人的自我价值都只能体现在唱歌上,除了唱歌外,就再没有展现自我、实现自我的途径了?这显然又说不通。在媒体娱乐中,不仅可以看到所谓“薰衣草般笑容的李宇春”、“天使在唱歌的张靓颖”,还能见到“一跪惊人”的“红衣教主”,徐娘半老的木子美、流氓燕。据说芙蓉姐姐又出名了,她的自谱人生传奇,究竟是让青少年们反对走以升学为目标的人生阶梯,别视清华、北大为圣殿呢?还是对将青春肉身祭上网页的直接歌颂?电视上天天见到的都是各种流行歌手的演唱会,都是劲舞、狂欢,网上不断出现自作多情的丑陋的裸女在卖弄风骚,难道就不会产生审美疲劳?多元的社会当然不能干涉别人的自由和私生活,但自由是有限度的。既然是私生活,又何必要找一个公共亮相的平台呢?
至于说到影响了民主政治,不也是某些精英分子一厢情愿的夸张想象?当然,当《今日美国》报道中国人以参加选举的热情给“超级女声”投出所谓“神圣”的一票时,当娱乐论坛以惊人的刷贴速度表明此地已成为公平和道义的首选场所时,似乎“超女”运动真的带有影响民选的意味?果真如此的话,“春春”、“笔笔”们就不该只是成为流行歌手、影视新星,而是去当部长、省长或谋求更高的政治权力,事实是能唱《超级女声奔小康》的,不一定就能带领人们奔小康,会哼《农民兄弟逛巴黎》的,也绝不可能带着近十亿农民去法国。换言之,这样的梦想不属于中国,中国的梦想绝无可能在成人版的“欢乐蹦蹦跳”中得以实现,硬把这些放大为中国梦,而且还引领众人去实现,这才是最大的“愚”乐,可怕的“愚”乐。
从“超女”到“梦想中国”,给人最大的启示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可怜了,中国人的娱乐太少了。当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处于相对贫困的生活状态中时,中国人是玩不起高尔夫、网球、台球这类高档娱乐的,甚至连进几次低档次的舞场都会感到囊中羞涩。而中国人又太压抑,太需要娱乐,太需要放松了,正因为如此,“超女”才会有如此的市场和声势,“梦想中国”也才会如此煽情地拴住各种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的心。在中国还没有真正进入工业化,中国人的文化素质还谈不上普遍上了档次,而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老百姓买房仍困难重重之际,西方的后工业化、后现代观念和技术已经全面渗透至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复制技术、数字技术的迅速扩张,不仅便利了消费,也进一步将“虚拟现实”、“幻觉效果”混同于真实,模糊了现实与非现实,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不可否认,众多参加“超级女声”的选手都是冲着“一夜成名”而去的,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光鲜亮丽的明星生活和用以吸引提高收视率的噱头,成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信仰和奋斗目标,于是才出现成都上万女生逃课到现场报名参赛的奇特现象。“超级女声”背后一道蔚为壮观的景象便是众多粉丝团(FANS)有组织的活动,一时之间,网络上、生活中到处充斥着“玉米”、“盒饭”、“凉粉”等等这样的称号。许多青少年已经模糊了真实与虚拟的界限,把游戏化的过程渗入真实生活,她们整天热衷于为自己心目中的“超女”拉到更多的选票,热衷于与别的粉丝团的竞争而奔波,精力的分散势必影响她们的学习和工作,有报道称,有一在英留学的女生为了将其经手的粉丝团的“组织工作”完好地转交给继任者,竟推迟回去读书达半年之久。
影像符号下的“虚拟现实”、“超现实”替代了真正的现实生活,这也正是后现代社会中一个显著的特征——仿像和现实之间既混淆又断裂。大众媒体通过对符号的“复制”、“模拟”与“仿像”,使得现代社会所确立的种种现实的边界逐渐消失,而人们对于世界的了解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电视所构建的“影像世界”所决定的,如是,电视一类的媒体就负有更大的责任。大众文化强调以形象、视觉冲击来吸引观众的视线,一旦这种影像造成的是某种“真实”的假象,抛出的是某种虚幻的美好前景,结果就必定加剧年轻一代的精神分裂和虚妄症,那么,媒体的责任何在,媒体的良心何在?其实,当下媒体的大众文化消费,抑或由电视台推出的种种反精英化的集体狂欢,草根性娱乐等,恰恰正是由掌握媒体、把持媒体的精英们自己策划,自己炒作出来的。老百姓从来不考虑什么“零门槛”存在与否,大众也不明白这是不是草根的胜利,是媒体说出来的,精英们制造的,目的仍很简单:商业利润和他们自己的声名鹊起。
无可否认,从“超女”到“梦想中国”,不管是地方台还是央视台,此类选秀节目的确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鲜的观念和想法,并使观众第一次成了遥控器的主宰。难怪有媒体在“超级女声”落下帷幕后,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超级女声”结束后,我们还要再看电视吗?但不可忽视的是,“超级女声”只是一个案例,它是在中国夹杂着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即使没有“超级女声”也会有相类似的形式出现。“超级女声”是典型的后现代现象在中国文化市场上的集中爆发和体现,而今,我们不得不承认,后现代已经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进入了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过,后现代主义的渗透毕竟是良莠不齐,正负效应互显的,在中国当下的文化转型期,如何正确看待后现代主义及其给大众文化带来的深远影响,又如何在大众文化泛滥之际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寻找相应的对策,这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有良心的媒体策划者、精英知识分子和文化市场工作者深思的重大现实问题。不是不要钱,不是不图名,只不过仍是那两句中国老话说得对,不管何时何地总应“生财有道”,尽量“名副其实”。
注释:
①[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58页,北京大学1997年版。
②[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译本,第123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③引文见《文萃》2005年第11期载《“超级女声”:别样狂欢与别样冷思考》。
④⑤金丹元:《国际后影像文本及其在中国的生存》,《戏剧艺术》2002年第六期。
⑥米哈伊尔·巴赫金:《陀思妥也夫斯基讨论中的问题》,第122-123页,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