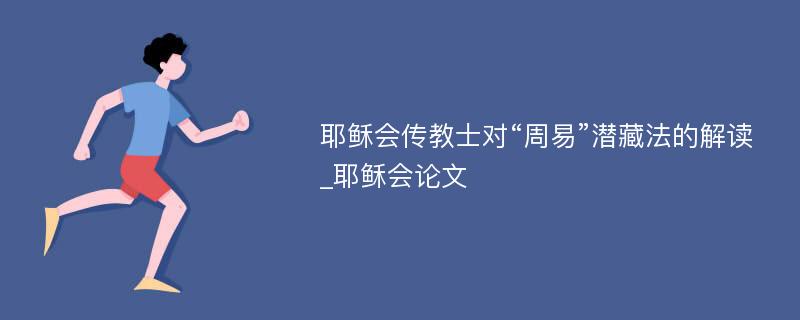
耶稣会传教士《易经》的索隐法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经论文,耶稣论文,传教士论文,索隐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3)04-0039-08
“索隐法”或“索隐主义”(Figurism)有时也被汉译为“符象论、形象派、尊经派、易经派”等,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一个奇特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异邦文化中包含了基督教的启示信息。它本来是一种关于作品中的形象的思想,后来意味着在中国的文学作品或经典著作中找到可以证实基督教是真理的符码结构。“索隐法”最初是基督教响应犹太教和其他宗教及哲学的责难,而试图将基督教与他者联系起来的一种努力,特别是为证明《旧约》是对《新约》的预表,而努力在两约之间寻找对应的类型文字,因此可被称为《圣经》类型学(Biblical Typology)。索隐法诠释《圣经》有三种途径:(1)类型学解读(Typological exegesis),目的是在《旧约》中寻找揭秘《新约》的隐含意义和诸种神迹。(2)古代神学(Ancient Theology),即设想在犹太-基督教文本之外的“教外圣贤”身上可以发现神圣的上帝启示。(3)犹太-基督教的神秘教义(Kabbala),它作为对犹太理性教派和塔木德宗(Talmudism)的一种反叛,其目的在于揭示《圣经》的隐含意蕴①。
索隐法西方早已有之,但将此法用于解释中国文献和传统,则主要得力于耶稣会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及其追随者,其基本倾向在于从中国古籍尤其是《易经》中寻找基督教及《圣经》的遗迹。用这种方法探讨犹太-基督教与汉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汉语索隐法,而试图从《易经》中找到基督教人物、事迹和教义的方法就是《易经》索隐法。有关明清传教士的《易经》研究以及耶稣会传教士针对中国古籍的索隐法研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些探讨②。白晋等耶稣会士对中国经典尤其是《易经》进行了开创性的索隐法研究,本文将耶稣会士在康熙年间从事的专门针对《易经》的索隐法解读称为“《易经》的索隐法诠释”。
一、索隐派对《易经》的索隐法研究
所谓“索隐派”(Figurists),是指在华耶稣会士中以白晋为首的力图从中国经典中发现《旧约》事迹与人物的一小派,成员以法国人为主。索隐主义是一种对中国古书的解释体系,其基本立场是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和人类历史观,即世界上所有现存人类都是大洪水以后诞生的诺亚(Noah)的子孙,以此为标准,索隐派把中国历史上的“洪水”与圣经中描述的洪水联系起来,认为中国人是诺亚之长子闪(Shem)的后代,中国人长期以来保存着族长们的古老传统,并且更进一步将中国历史上古代皇帝和英雄们同耶稣基督救赎人类的“形象”和寓言相对应,甚至相信中国人的神话中可以找到撒旦(Satan)和亚当(Adam)的模型③。
索隐法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利氏在《天主实义》中就多次指出天主教与中国经典所含法则之间的联系,其焦点在诸如上帝的存在、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保全者、灵魂的不朽和上帝对人类善恶行为的赏罚这类题目上。后来的耶稣会士大多遵循此道,力求从中国古籍中寻找能与天主教义相印证之神迹。利玛窦认为宋代理学家误解了中国的经典著作,因此未来理解儒学必须追本溯源,也就是说要依据原始经典。白晋、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1665-1741)、郭中传(Jean-Alexis de Gollet,1664-1741)等传教士作为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特使被差遣到康熙王朝,将汉语索隐神学发挥到极致。白晋等耶稣会士学者的索隐神学认为,中国历史、经典、文字不但与基督教相通,而且它们都是犹太-基督教上帝的启示。
索隐派的理论可以看作是耶稣会士在华调和策略的新发展。调和策略的理论基础在于确立基督教和儒家传统的一致之处。利玛窦从儒家传统文本中引经据典,意在说明古代中国人崇拜的“天”和“上帝”正是基督教信奉的独一无二的真神,基督教不仅与儒家思想没有抵触,而且是上古纯正的儒教传统的完美体现,因此可以起到“补儒”的积极作用。索隐派首先通过解析汉字笔画而宣称其中蕴涵着基督教的奥义,一些简单的字形和笔画被赋予特定的神学含义:如“、”指上帝,“一、二、三”指三位一体,“人”表示耶稣基督,“十”表示十字架,“口”指宇宙,“丄”指天堂、天等。他们进而又认为《易经》的卦象是基督教真理的数字化表现,最后发展到从中国各种文献中搜集有关“道”的描述,以论证“道”就是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
白晋于1688年来到北京的皇宫并成为康熙皇帝(1662-1722在位)的老师,教授数学、物理、天文等学科知识。他很快对《易经》产生兴趣和崇拜,并与康熙“日讲《易经》”④。尽管有很多传教士觉得《易经》只是迷信之作,白晋却对此书评价很高,认为它“蕴含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⑤。康熙想用《易经》来证明“西学中源”说,委托白晋来研究其内在的含义。白晋的索隐神学著作主要有:1699年之前,他写了《天学本义》(拉丁文名为Observata de vocibus Sinicis Tien et Chang-ti,直译为《关于华人的“天”和“上帝”两个字的观察》),1707年他写了《中国古籍中出现的三位一体的奥迹》(Essai sur le mystere de la Trinite tire des plus anciens livres chinois)、《古今敬天鉴》(De Cultu Celesti Sinarum Veterum et Modernorum,1707年自序,仅有抄本)和《象形文字之智慧》(Specimen Sapientiae Hieroglyphicae)⑥。1712年他用拉丁文写了《易经释义》(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ye kim)(该抄本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阐述了世界的三种状态:完满、堕落和拯救,并在此前提下发现了隐藏在《易经》里的“自然神学”。有关他《易经》研究的一些著作可从梵蒂冈图书馆找到。白晋提出了三个命题:中国人信奉的哲学中没有任何内容与基督宗教律法相违背;“太极”即上帝,为万物之源;《易经》是中国人最上乘的道德与自然哲学教旨之浓缩⑦。白晋认为,《易经》所有的概念代表的是一种象形和象征寓意的哲学思想。有两种象形符号,一种是自然的,反映造物主荣耀的,在《易经》里被称为是“万象”;另一种是科学的、数学的,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数字化表现。白晋据此把《易经》的教义分成内在意义和外在意义两个部分:内在意义是导向上帝的真理,外在意义是掩盖这些真理的象数。⑧
傅圣泽于1711年被上谕召至北京帮助白晋研究《易经》,时间长达六年之久。他承袭白晋的索隐手法,试图证明《易经》是真神传给中国人的玄秘经典。现存关于傅圣泽索隐神学的最早著作,是一封他于1709年写给马若瑟的长信以及论文《论尧至秦所谓统治中国的三代》(Memoire sur le systeme des 3 dynasties que I'on pretend avoir gouverne la Chine depuis Yao jusqu' aux Tcin)。另外有关手稿有九十篇,书信六百三十一封,他所刊布的西文数据、传记、专著、论文及中文和日文资料,魏若望(John W.Witek)在其传记书中有详细列举。经过多年的哲学思索之后,傅圣泽总结出三条索隐主义原则:第一,中国古代文献源于天启,也就是说它们来自“天”,来自“上帝”,因此它们的来源就是神性的。第二,这些奥义书中的“道”这个字表明着永恒的智慧,即天主教崇拜的上帝。第三,“太极”一词代表了相当于“上帝”和“天”的一般意义上的“道”。⑨傅圣泽还说,伏羲是第一位圣人故而是所有圣人之首。《易经》是五经之源,则与五经相类的诸家学说亦可因此而得到正确的解释。⑩
马若瑟坦言,对中国典籍的疏证和撰述,目的是要使世人皆知:基督教与世界同样古老,中国创造象形文字和编辑经书之人,必已早知有天主。《诗经》之譬喻,《易经》之卦爻,咸加利用,以备传教之引证。(11)马若瑟的索隐派立场:一是以《易》为诸学之本原,“圣人之心在经,经之大本在《易》”。二是认为先秦儒学之“真道”随着孔子之死而衰微,汉代经学大盛,异端之说乘隙蜂起,佛道二教是坏乱儒家真道的根源。三是祈求“黄天上帝”眷佑中国,以“天学”来补足先儒真道之“缺废”。(12)1725年马若瑟发给法国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关于中国书籍和文字的一篇论文——选自梅尔希奥·达拉·布列加译自易西斯女神腰带的一封信》(Dissertation sur les letters et les livres de Chine,tiree d'une lettre au R.P.de Briga,Interprete de la bande d'lsis),其中附有随船教士鲁约(Rouillot)对该文的质疑及马若瑟的辩护文字和一篇辩护文。《象形字典文稿》(Draft of a hieroglyphic dictionary)则从汉字来讨论索隐神学(13)。《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Selectae quaedam vestigua praecipuorum religionis christianae dogmatum ex antiquis Sinarum libris eruta,也称《中国经书古说遗迹选录》,拉丁文本)现藏于巴索邮政图书馆。《易经理解》(Notices critiques pour enter dans l'intelligence de l'Y King,也称《经书理解绪论》,二开手写本,共98页),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编号12209号,书有三篇。此手稿仅有一篇。它详细分析了六十四卦的前两卦。《六书实义》则是写给博学华人的中文著作,重在分析象形文字的表意功能,流露索隐本质,内容更集其汉字托喻之大成。另有《怎样应用五经及解决其中的问题》、《天学总论》和《经传众说》等。(14)
二、索隐派对《易经》的索隐法诠释
《周易·系辞上》云:“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疏:“索谓求索,隐谓隐藏。”由此可见,中文“索隐”一词不仅说明其解经路数,而且也表明《易经》为其研究首要之文本。索隐派认为,只有用索隐方式解读古经,才能返回正道,理解神启。汉字本身是一套符号,蕴含独特的宇宙观。而《易经》卦象也在符码中运作,为索隐派研究的核心。
索隐派对《易经》的宗教诠释是基于如下几个基本观念:《易经》本身就是一部上帝的启示书;夏、商、周并非真正的历史朝代,而是救世主耶稣的神迹显灵的表现;三皇五帝也并非真正的历史人物,而是基督上帝的化身;从《易经》可以推算出世界的未来走向:从创世纪到道成肉身,从道成肉身到世界末日;(15)《易经》中的许多宗教和哲学概念,如天和上帝、太极、无极、太乙、道、理、阴阳等都与《圣经》中的上帝和圣灵联系在一起。
索隐派们试图在《圣经》和《易经》中寻找契合的方式和方法很多。第一种方法是汉字字形分析法,也就是拆解中国汉字,利用汉字的象形和会意法来对汉字进行寓意和象征性的解读,以此来揭示中国古书中包含的基督教奥义和关于《圣经》中古老事件的记载。根据六书的传统汉字造字法,耶稣会士较早用拉丁文Hieroglyphy来翻译汉字的“象形文字”,把表述中国文字字形特点的方法理解为“神圣形象的描述”,认为其中隐藏着上帝的神圣启示。白晋认为,伏羲是仿照天上的日月星辰创造了这些“神圣的符号”,它们反映的是上主和救世主对过去和将来规划的奥秘,伏羲之所以选择象形文字,为的是借助占星术真实而又神秘的本质使人类形成对上主的爱和认识。(16)白晋在1701年11月4日致莱布尼茨的信中写道:“太一”(大同一)这种表达方式和“上帝”这个称呼是相一致的,这两个词都表示的是天主教中的上主;“大”表示“伟大”,“、”表示“统治者”,“一”表示“独一”或“同一”,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独一无二的伟大的统治者”。同样,由“大”和“一”组成的“天”字代表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的天,也是“上帝”的意思。(17)白晋等人还把“天”分解成“二人”,就预示着第二个亚当即耶稣基督的显灵,也代表上主圣三中的第二位即圣言与圣人的完美灵魂的结合。(18)他们又把“船”分解为左边的“舟”和右边的“八”、“口”,就表明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诺亚方舟,船上刚好搭载了诺亚的八名家庭成员(诺亚夫妇、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及其配偶),所以上帝把诺亚方舟之事启示在这个汉字之中,中国人就是诺亚之子闪的后代。(19)同样,“义”(義)被理解为“羔羊”(耶稣基督)披戴在“我”之上,使人“称义”而圣洁。而“婪”则表明“女子”(夏娃)在两个树木(林)前的贪婪和被诱惑犯罪之事,暗指夏娃的原罪。
第二种方法是把《易经》等典籍中涉及的传奇人物与《圣经》中的宗教人物进行类比。于是,中国之古帝即是《圣经》中之族长,“彭祖”相当于人类的始祖亚当,伏羲就成了《圣经·创世纪》中与上帝同行的先祖以诺(Enoch),《易经》也就是《圣经·新约》末卷《启示录》中的一个片段。白晋将中国古代统治者和英雄们看做是《圣经》中的先祖们,认为尧和诺亚应该是同一个人,因为这两个人在先祖列表上都排在第十位。(20)傅圣泽认为,伏羲之“伏”等于“犬”和“人”,也就等于犬头人身的埃及古神阿努比(Anubis)以及奥尔菲斯、琐罗亚斯特等上古圣贤。至于传说中的远古圣明君主尧(Yao),应该是来自希伯来语汇中与它发音相似的“耶和华”(Yahweh)。(21)17世纪德国神学家乔治·霍尔恩(Georg Horn,1620-1670)试图将中国皇帝比附与《圣经》人物而将中国的古老历史纳入《圣经》。他认为伏羲有可能是《摩西五经》中的亚当(Adam),神农就是该隐(Cain),二人事迹相似且名字有亲密关系;该隐的儿子以诺与伏羲的继承人黄帝的名字十分近似;从对尧帝的系列描写来看则明显就是诺亚。所以他的最后结论是中国古代史与《圣经》原本为一体。(22)索隐派耶稣会士们还从中国神话传说中寻找与《圣经》的相通性,如女娲补天、黄土造人、大禹治水,以及姜源履巨人足印而生周人祖先后稷与圣母玛利亚因圣灵感孕而生耶稣基督的相似等(23)。
第三种方法是将《易经》卦象与上帝神圣启示结合起来,认为《易经》的卦象是基督教真理的数字化表现。白晋强调《易经》中伏羲八卦图暗示着“阴阳”、“善恶”与“有无”等二元观念。他认为卦图阳爻“—”等同于“完善”,而阴爻“--”则等同于“不完善”,所以八卦图的变幻莫测与《创世纪》中关于创世后人类存在善以致福、恶以致祸的多变命运相符合,伏羲以这种方式来宣扬上帝的原初律法,也是适应当时人类认识能力之举。(24)白晋借助乾坤二卦来解释“王”字,认为“王”字就是由坤卦或乾卦通过一竖连接起来的,象征的是救世主及其至高无上的权力。(25)傅圣泽指出,《四书》、《五经》都是隐喻,“易”字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神秘的符号;《易经》中“卦”的短线可能各自表示一个数,每一个数都喻救世主的某种品德或奥秘,或者某一重要事件。(26)索隐派人士还把《易经》中的“既济”卦和“家人”卦演绎成天道→地道→天道的基督教神学史观,即:“既济”卦被认为隐含了伊甸园时代没有原罪的人类状况(天道),“家人”卦被诠释为天使的背叛以及被造者的要做主人(地道),然后又回到“既济”卦,这次它所暗含的密旨是人子耶稣所承负的天道。(27)马若瑟在《中国古籍之基督教主要教义痕迹》一文中讲到,始祖从上帝那里得知元圣(基督)救赎世人的道理,将之作为“家训”代代相传,后“恐口传有失,故造书契以指之焉,画八卦以象之焉,系辞以断其吉凶。”(28)索隐派人士还指出,“乾”卦中的三条实线就代表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圣灵合成一体)论,而且乾卦本身就正是指上帝创造天地之神灵。卦五“需”,《象》曰:云上于天,就只能是指耶稣基督救世主的荣耀升天。卦十二“否”和十一“泰”在他们眼里就分别指被“罪恶所玷污的世界”和“通过基督道成肉身而拯救的世界”。(29)白晋等人还认为,《易经》卦象中包含着世界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最初上帝造人时的完美,后来人类和天使背叛上帝时的堕落,以及最后救世主的救赎,这与《圣经·旧约》里创世纪的观念不谋而合。(30)
第四种方法是把《易经》编年史归于《圣经》的编年史之下。早期传教士的《周易》研究之中,也有从历史角度对《周易》卦爻辞、历史年代进行考证的学者,如马若瑟通过《易经》卦爻辞史料考证,断定中国纪年体古史比其他各国历史的可信度高。但是传教士们的考证与结论大多服务于其附会天主教或基督教教义之目的,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31)诺亚洪水的时代早于中国文明是索隐派的基本立场之一。该问题不仅通过编年时代确定中西文化起源孰先孰后,而且还要回答这两种文明的同源奥秘。索隐派认为,洪水过后,诺亚的儿子闪迁徙到远东。闪将神启奥秘带到了中国,因此在中国上古典籍里面充满了隐藏着启示奥秘的征象与符码,如先知的寓言、原罪的故事、天使的堕落,等等。白晋指出,伏羲(即以诺)仰观天象,发现了许多未来重大事件的启示,从而形成了《易经》文本。伏羲用的是比喻和象征的手法来记录这些神启,所以该书被误用来占卜,只有通过神启的算术才能解读其奥秘并且建立新的编年史。为此,白晋借助于《易经》的“河图”和“洛书”重修编年史,计算的是从《创世纪》到救世主再次降临人间来救赎世界的七千年历史。(32)
第五种方法是确立中国的经学与基督教的关系。白晋认为,在《易经》里蕴涵着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根基,该书是一个完满的形而上学的体系,伏羲的卦以一种简单和自然的方式体现了所有科学的原理。但是孔子出现以前,中国人看起来已经丢失了这些知识,必须重新发现这些古代中国人的真正的哲学原理,并且把中国人带回到对真正的上主的正确认知那里。(33)在白晋等耶稣会士看来,中国先古的圣人们就像《圣经》中的先知一样早就拥有了对上主的认识,《易经》是促使中国人回归上主的一条格外重要的途径。索隐派们从《易经》和《春秋》所论述的“圣人”观点,认为中国所有经典所指向的都是“那个人”(弥赛亚基督)。他们认为,像《圣经》乃欧洲人的文化根源(甚至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也都被看成是关于“救赎”的预示)一样,《易经》乃中国文化的根本,一切的经典都是对其的注释、说明和发挥。传统儒家的诗、书、礼、春秋、四书,道家的老、庄、列,法家和杂家的韩非、鬼谷子、吕氏春秋、山海经等,都被视为《易经》之发展。甚至连《楚辞》里提到的昆仑山也与基督教的“乐园”联系起来。(34)所以在索隐派耶稣会士们的眼里,中国所有的经学也都是《圣经》和基督教的诠释和发挥。
三、索隐法的理据及其意义
不难理解的是,汉语索隐神学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首先,这种方法是以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为前见(presupposition)来诠释中国文化和历史,这种生硬的比附难免牵强。其次,索隐派是选择性和诠释性翻译(selective and interpretative translation)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未考虑反证。第三,索隐派逻辑是演绎而非归纳,从犹太教和基督教前提所推出的结论,使很多人无法接受。但是,正如芬兰籍华人学者黄保罗所言,白晋等提倡汉语索隐神学,并非异想天开或者标新立异,其背后有悠久的传统与合理性根据。以汉字字形的六书分析为例,为什么索隐神学的“六书”被理解为荒诞不经的“拆字法”,而中国文字学家的分析就被认为是学术性的真理探讨?这牵涉双重证据和三重证据问题。现代诠释学表明,所有论证都离不开论证者的“前见”。这种“前见”可能是错误的“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文化人类学之想象力。因此,索隐神学有其合理性。(35)
索隐派发展这种诠释体系的目的是使中国人主动彻底地皈依基督教。因为如果中国人认识到他们视为神圣的经典原来就是《圣经》的隐喻式表现,经典中原本就包含着基督教教义,那么他们信奉基督就不会违背中国古训。基于这种逻辑,索隐派宣称中国人丢失了理解古书的钥匙,而他们的使命是为中国人找回那把丢失的钥匙。(36)以白晋和傅圣泽为代表的索隐派人士相信中国最古老的典籍(《易经》和《尚书》)里包含基督教义的象征印迹,《易经》文本已经取代孔子教义而成为神圣智慧的来源。所以,他们强调,正如17世纪后期中国考证学者所指出的一样,只有通过《易经》才能真正地重构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和真谛。(37)索隐法的体系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上。首先,中国文字在最根本的本质上是象形的或神性的书写,而基本的宗教真理就掩藏于其下。即使最有学问的中国人也不能彻底弄明白这些隐藏的真理,因为他们没有揭示它们所需的钥匙。其次,在中国经典中发现的事实并非如注经者所称只限于中国历史,而是评述了世界之历史与起源的更具普遍性的材料。(38)这些书籍来自“天”并拥有一种隐藏在书写它们的中国文字之下的了不起的教义,“天”和“上帝”完美地表达了基督宗教之神的名称。索隐派们的目标是为中国人找回这把他们丢失了的,但理解这种了不起的、神秘的教义所必需的钥匙。
德国学者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认为,以白晋为首的索隐派在《易经》的研究中采取了神学对比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典籍诠释的一条崭新途径。尽管索隐的途径对卦象的解读显得有些荒诞不经,但是对如何理解中国和中国人开辟了一个新的视域,也对神学的走向提供了新的参考。通过比较东西神话,索隐派们开启了一种欧洲文化以外的思考方式,也重新审视人类对超验的理解的方法。(39)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指出,白晋等耶稣会士试图把《易经》确证为早期基督教经典的思考似乎是毫无根据的,但是索隐主义的思想体系导致了欧洲对中国编年史的研究,激发了一大批欧洲作家的想象力,促使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带来了“早期汉学”的发展,并为18世纪晚期的第一批态度认真的、严谨治学的汉学家们奠定了基础(40)。所以,耶稣会传教士对《易经》的索隐法诠释有其积极的意义,不仅对《易经》等中国经典的对外传播指出了一条新的途径,而且对跨文化交际和东西文明对话提供了一定的指南。
索隐派在把中国典籍推向欧洲这一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介绍中国经典的耶稣会士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尽管他们对中国经典的诠释和研究方法并不是为了深化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是要证明基督教的普遍性和正确性;尽管其理论和方法显得牵强附会和充满偏见,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但索隐派理论指出的基督教信仰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相似之处,可以部分说明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和人类文化的某些共性因素。追求不同文化的契合是完全正当的和至关重要的,归根结底,作为传教士,他们只是中国文化的利用者,而非真正的研究者(41)。只是,我们很难把各种各样的对文化的研究与对文化的利用完全区分开来,而且利用一种文化来为另一种文化服务也是客观存在的和很有必要的。
耶稣会传教士《易经》的“索隐法”诠释对于《易经》在西方的传播以及中西跨文化交流有着重要和积极的影响。虽然其解读策略受到其他天主教会甚至耶稣会本身的批评与指责,最后还遭到罗马教廷的制止,而且也不受中国学者的青睐,最终受到康熙皇帝的冷落,但是这种解经途径是《易经》诠释学以至文化传播学的一种富有创意和成效的方法,古今中外的易学家们和典籍传播者们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利用类似的方法来诠释和传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经典作品。为了使中国的经典作品更好地走向世界,中外汉学家、翻译家和研究者们有必要改进和创新翻译和诠释的方式方法,使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更好地为海内外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①Claudia von Collani,in Standaert,ed.,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one:635-1800(Leiden,Boston,Koln:Brill,2001),668-679.
②参见杨宏声《明清在华耶稣会士之〈易〉说》,载《周易研究》2003年第6期;张西平《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张西平《〈易经〉在西方早期的传播》,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冬之卷;黄保罗《汉语索隐神学——对法国耶稣会士续讲利玛窦之后文明对话的研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德)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其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刘耘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Claudia von Collani,"The First Encounter of the West with the Yijing",Monumenta Serica 55(2007); David E.Mungello,"Seventeenth Century Miss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ism",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8(1978); Knud Lundbaek,Joseph de Premare,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Denmark: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1); Richard J.Smith,"Jesui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 (Classics of Chang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uticle based on the conference "Matteo Ricci and After:Four Centuries of 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sponsored by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Beijing University,October 13-16,2001; Richard J.Smith,"The Yijing (Classic of Changes) in Global Perspective:The Value of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2(2004).
③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2页。
④John W.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cquet S.J.(1665-1741)(Roma:Institutum Historicum S.I.,1982),171.
⑤转引自林金水《易经传入西方考略》,载《文史》第29期,北京:中华书局,第367页。
⑥黄保罗《汉语索隐神学——对法国耶稣会士续讲利玛窦之后文明对话的研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5-11页。
⑦[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⑧Claudia von Collani,"The First Encounter of the West with the Yijing",Monumenta Serica 55(2007):285-286.
⑨傅圣泽1719年10月26日于北京致吉贝书,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日本中国卷182号,第199页。
⑩[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90页。
(11)[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其书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27页。
(12)刘耘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
(13)Knud Lundbaek,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Denmark: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1),120.
(14)黄保罗《汉语索隐神学——对法国耶稣会士续讲利玛窦之后文明对话的研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5-11页。
(15)Claudia von Collani,"The First Encounter of the West with the Yijing",Monumenta Serica 55(2007):247.
(16)[德]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42-143页。
(17)[德]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18)法国国家图书馆新收藏之拉丁文手稿1173,37.
(19)Claudia von Collani,Joachim Bouvet S.J.Sein Leben und sein Werk(MSMS XVII)(Sankt Augustin-Nettal,1985),117.
(20)法国国家图书馆新收藏之法文手稿1173,f.20.
(21)Paul A.Rule,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Sydney,Boston:Allen & Unwin,1986),174-175.
(22)[法]毕诺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5-237页。
(23)黄保罗《汉语索隐神学——对法国耶稣会士续讲利玛窦之后文明对话的研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5-11页。
(24)卓新平《基督宗教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0页。
(25)[德]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
(26)许明龙《中西文化交流先驱——利玛窦到郎世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25-226页。
(27)刘耘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
(28)徐宗泽《明清耶稣会士著作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6页。
(29)Richard J.Smith,"Jesui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 (Classics of Chang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rticle based on the conference "Matteo Ricci and After:Four centuries of 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sponsored by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Beijing University,October 13-16,2001.
(30)[德]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55-172页。
(31)赵娟《问题与视角:西方易学的三种研究路径》,载《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第71-77页。
(32)Claudia von Collani,"The First Encounter of the West with the Yijing".Monumenta Serica 55(2007):254.
(33)David E.Mungello,Leibniz and Confucianism.The Search for Accord(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7),42.
(34)黄保罗《汉语索隐神学——对法国耶稣会士续讲利玛窦之后文明对话的研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5-11页。
(35)黄保罗《汉语索隐神学——对法国耶稣会士续讲利玛窦之后文明对话的研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5-11页。
(36)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2页。
(37)Lionel Jensen,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Chinese Traditions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117.
(38)[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66-167页。
(39)Claudia von Collani,"The First Encounter of the West with the Yijing",Monumenta Serica 55(2007):257-258.
(40)史景迁著,廖世奇、彭小樵译《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2-34页。
(41)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标签:耶稣会论文; 基督教论文; 圣经论文; 易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传教士论文; 伏羲八卦论文; 国学论文; 旧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