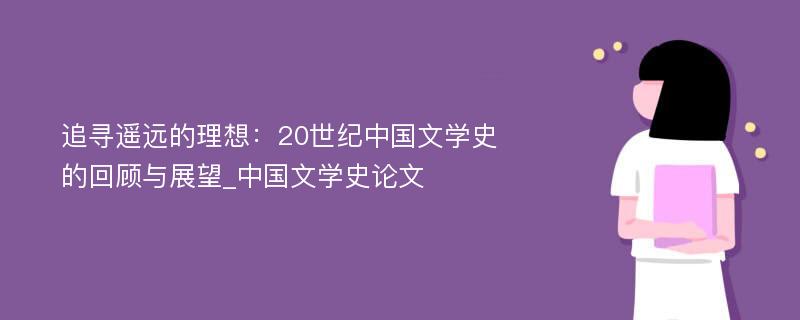
追寻遥远的理想——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回顾与瞻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遥远论文,理想论文,世纪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2年,美国文艺理论家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慨叹:“编写一部总的文学艺术史仍然是十分遥远的理想。”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学人们依然在执著地追寻这遥远的理想。1904年,林传甲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它借鉴日本和欧洲学者的方法,试图重新描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此后,将近一百年来,诞生了王国维、鲁迅、闻一多等著名文学史家,出版有1100多种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著作。[①]在世纪之交,为了推进文学史研究的进程,面对逝去的近一百个风雨春秋,面对一本本层累起来的一千多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发生、发展的脉络与成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事实上这一工作已经和正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本文拟就近百年来中国文学通史教科书(不包括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分体断代文学史及其它各类文学史论著)的编撰、研究谈点个人粗浅的看法。
本文认为近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可以分为三大时期:本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一阶段;建国初期至“文革”结束为第二阶段;新时期以来为第三阶段。为了深入体认各个时期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大体走向,本文在此三大时期中分别选择了一部文学史名著作为析论的重点。这三部著作分别是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上卷)(以下简称为胡著文学史),[②]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二、三、四)(以下简称为游编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下)(以下简称为章编文学史)。为了便于横向比较,本文论述的范围约束于先秦文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之间。
一、反传统的号角:胡适《白话文学史》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了一批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巨人。他们的学说一度震撼了中国学术史,他们思想的光环一度笼罩了中国文化的一切领域,贯通地看,在中国历史上也许只有先秦诸子才可以与其匹敌。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在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开拓性的贡献,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③]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
我在这十几年的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上,如果有一点点贡献,我的贡献只在:
(1)我指出了“用白话作新文学”的一条路子。
(2)我供给了一种根据于历史事实的中国文学演变论,使人明了国语是古文的进化,使人明了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什么地位。
(3)我发起了白话新诗的尝试。
从胡适的自我介绍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极为重视,“整理国故”、研究古代文学史是胡适新文学运动和启蒙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胡适的古代文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明清章回小说的考证,一是撰写了《白话文学史》(上卷)。《白话文学史》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反传统的精神而饮誉学术界,成为我国当代学术名著之一。诞生于胡著文学史之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都受到了胡适学术观点的影响,建国前的文学史著作尤为明显。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运动中,有学者指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不但有许多接受了胡适的观点和方法,扩大了胡适的影响,甚至有一部分发展了胡适的论点。”该文列举的受到胡适“思想毒素”影响的著作有: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出版),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1931年出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年发行),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1930年出版),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1935年出版),张世禄的《中国文学变迁论》(1933年版),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出版),蒋祖怡的《中国人民文学史》(1949年出版)。[④]这差不多包括了当时最出名的所有文学史。在建国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版)不仅在大陆地区有很高的知名度,而且在台湾地区多次印行,据台湾学者说,该书“是目前流行最广、而影响最大的文学史书。初学者往往以此书为基础,建立起文学历史的概念和知识。”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刘氏的主要理论基础及脉络,是进化论、历史有机循环的命定论和反传统精神”[⑤]。而这一理论基础及脉络与胡适思想及文学史观一脉相承。
胡适反传统的文学史观在他《白话文学史》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该书的主要观点有:
(一)白话文学有一个漫长的传统,它是中国文学史的核心。胡适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明确说:“这书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在该书的《引子》中他还说:“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古文传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我们讲的白话文学史乃是创造的文学史,乃是活文学的历史。因此,我说:国语文学的进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是最重要的中心部分。换句话说,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史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史的发达史。”胡适的这一观点与五四文学革命紧密相关,既然一部中国文学史乃是创造的活的白话文学与模仿的死的古文文学的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历史,而且在这一斗争中白话文学始终占据着主动,最终必然能够战胜古文文学,如此,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便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二)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派的宗。第一,“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胡适认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那一样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⑥]“这无数的民歌在几百年的时期内竟规定了中古诗歌的新式、体裁。”[⑦]第二,民间文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庙堂的文学终压不住田野的文学,贵族的文学终打不死平民的文学。”[⑧]在他看来,一个时代的诗歌是否能够兴盛主要取决于民歌的发展程度以及文人对待民歌的态度,魏晋诗歌的兴盛是这样的,唐代诗歌的兴盛也是这样的。“到了东汉中叶以后,民间文学的影响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文人出来公然仿效乐府歌辞,造作歌诗。文学史上遂开一个新局面。”[⑨]“唐代的文学的真价值,真生命,不在苦心学阴铿何逊,也不在什么师法苏李,力追建安,而在它能继续这五六百年的白话文学的趋势,充分承认乐府民歌的文学真价值,极力效法这五六百年的平民歌唱和这些平民歌唱所直接间接产生的活文学。”[⑩]相对于古人重视“载道文学”、“庙堂文学”的旧观念,胡适的观点具有“革命”的意义,从此以后的文学史家和文学史著作无不重视到民间文学对文人文学的启迪与渗透。
(三)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进化论在19世纪末叶经严复等人的介绍而传入我国,在20世纪,特别是在五四至建国之前的历史时期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胡明先生云:“每一个学术上成熟的史家都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史观,胡适的这部《白话文学史》更是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进化的文学史观。”[(11)]在《水浒传考证》中胡适自己说,他要“贡献”给大家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具体而言即是“种种不同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时代之公例也。”在《白话文学史·引子》中他把文学的进化分为两类:“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显然,这部《白话文学史》是其文学进化史观的具体化的结晶,而胡适整理、总结古代文学史的最终目的乃在于为了促使新文学出现一次“革命”式的进化。
胡著文学史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在此仅指出有关文字形式的两点:
一曰模糊了文白界限。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云:“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众所周知,与“白话”相对的概念,不是“古文”,而是“文言”,胡适摒弃“文言”而选择了“古文”决不是无意的,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以文言为主,白话的作品所占比例很小,胡适的“白话”范围内事实上包括了许多非白话的作品,例如陶渊明、王绩、杜甫等人的诗歌。不如此,他便难于自圆其说,难于证明文学史以白话文学为中心的“公例”。胡适固然用心良苦,但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太大,以至于溢出了“白话”的领地,侵占了“文言”的家园,毕竟不大妥当。
二曰偏袒白话、贬斥文言。胡适首先看重的不是作品的内容而是作品的形式,他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逼上梁山》)如此,在他那里不难得出凡白话文学必然优于文言文学的结论。于是,在《白话文学史》中便出现了这样的咄咄怪事:王褒的《僮约》、王梵志的打油诗之类作品被大肆颂扬,许多文人的文言作品却受到了冷遇。他把汉代以前的包括《诗三百》和楚辞在内的文学一笔勾销,略而不提;对于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律诗,则认为它们“全无文学的价值”,他在列举了杜甫诗歌的“毛病”后说:“律诗是条死路,天才如老杜尚且失败,何况别人?”[(12)]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胡适明确说中国两千年没有真正有价值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而文学史的事实却昭示我们: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并不取决于它的文字形式,至少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文字形式。古文文学固然有僵死之作、晦涩之作,白话文学未尝没有失败之作、浅陋之作。
总而言之,胡著文学史是一部在进化论文学史观指导下的具有反传统色彩的著作,本世纪以来,出版于胡适文学史之后的同类著作无不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胡适文学思想的浸润或侵蚀,即使是在50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和八九十年代新方法新观念接踵而来的季节里亦不例外。
二、社会政治的摹本:游编文学史
建国后至“文革”结束是本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以1966年“文革”开始为界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许多优秀的成果皆产生于“文革”动乱之前,十年“文革”中古典文学界虽然出现了刘大杰先生的新修改本《中国文学发展史》(1973年、1976年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二两册)和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但整个学术界呈万马齐喑、百花凋零之状。“文革”前出现的比较著名的文学史著作有: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1954年初版),詹安泰、容庚、吴重翰等先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57年出版),杨公骥先生的《中国文学》(第一分册)(1957年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一、二、三、四)(1958年9月出版),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下)(上册1958年12月出版,中册1959年4月出版,下册1959年12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一、二、三)(1962年出版),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63年新一版),游国恩等先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一、二、三、四)(1964年出版)……。在上述文学史著作中,游编文学史发行量最大(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仅次其后),迄今仍然是高等院校文科专业普遍使用的教科书,故本文以之为例来探讨本期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态势。
建国后,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无不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来探索说明文学史上发生的重要现象,给古典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因而,从整体上提高了古典文学的研究水平。但也无庸讳言,建国以来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导致了学术研究上的偏失,主要表现为对马列主义理论理解和应用中的简单化与片面化,甚至形成了庸俗社会学的学术观。被誉为“红色文学史”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序言”云:“希望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领域里,为插红旗拔白旗贡献一分力量。”该书部分作者云:“我们认为文学艺术是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反映。因此,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我国文学史上就贯串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我们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力求作具体的、客观的、历史的分析,并力求掌握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肯定或否定,尽量避免简单化。”[(13)]应当指出,认为文学史的根本任务在于阐明文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及其发展规律,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观点,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学者的共同观点。相较之下,游编文学史和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是当时条件下最好的成绩”,“它们是两次极左思潮间隔期的产物,且对50年代后期的极左思潮有所抵制。”[(14)]虽然如此,却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像当时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作一样,游编文学史亦特别强调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文学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它把纷纭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一分为二,在第一方阵内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民生疾苦的文学家,在相反方阵内的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和消极厌世的文人。第一方阵的作家的作品多是现实主义的或积极浪漫主义的,第二方阵内的作家的作品则是反现实主义的、是形式主义的、是唯美主义的。使用这种简单逻辑归队的结果,就使一部文学史变成一部社会政治的反映史,变成为一部阶级斗争消长史。这是游编文学史的最大的最根本的缺失。
游编文学史的另一个缺失是框架结构的单调与呆板。整部文学史的框架是:(1)时代背景;(2)作家生平;(3)思想内容;(4)艺术特色。这种结构不是游编文学史独有的现象,它是诸多文学史著作(既包括古代文学亦包括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既包括中国文学亦包括外国文学,既包括出版于“文革”以前的亦包括出版于新时期之后的)的共同特征。与此单调、呆板的结构相联系,四大块的内涵亦有雷同之弊,凡时代背景必着重叙述本期政治、经济的一般状况,从而使时代背景的论述过于狭窄,忽略了本期哲学、美学、心理学以及书法绘画等其它艺术门类的发展状况。即使是政治经济状况的描述亦较为笼统,看不出与本期文学之间的直接关系;凡作家生平多强调其阶级出身,讨论其对待人民的态度;凡思想内容必涉及现实主义、人民性、爱国主义精神;艺术特色的分析亦较为单调,如果是叙述性作品,多不出生动的情节、细致的心理刻画、典型的人物性格等等。
这样说并非是要完全否定游编文学史,恰恰相反,笔者认为:游编文学史(包括社科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失误,但迄今为止尚没有别的文学史著作可以取而代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会在大学文科讲坛上占据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其一,如前所述,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极左思潮有所抵制,是一部相对而言较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其二,同时,它的撰写集中了当时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院校的知名教授,他们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精深的学术造诣,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故由他们合力撰写的著作自然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其三,游编文学史的论述具体而清晰,章节内容的份量比较均匀,结构完整,与高校教学的需要极为吻合;其四,6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培养起来的一批又一批大学生、文学硕士、文学博士无不受到游编文学史和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沾溉与滋润。
三、人性的证明:章编文学史
进入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的大背景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学术研究突破了极左思潮的樊篱,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二是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学术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表现出一些商品经济环境下的新动向。
新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影响较大的有:褚斌杰、袁行霈、李修生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一、二、三、四)1990年出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编的《中国文学通史》(此套书正在陆续出版之中,已经出版的有《南北朝文学史》和《元代文学史》两部),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修订本全本1995年出版,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这些文学史著作各有所长,构成了新时期学术园囿中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其中,林先生《中国文学简史》的修订历时半个世纪,被学界誉为“带有个人风格的写活了的文学史”。至于引起媒体不间断曝光,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则首推章编文学史。
对人性的强调与张扬是章编文学史区别于以往文学史著作的最大特征。此处的“人性”并不等同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性”这一概念,而是指“人类本性”或“人的一般本性”,“所谓‘人类本性’或‘人的一般本性’也就是要求自己——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章编文学史《导论》)章、骆两位先生认为:
文学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人性的发展,并反映着人性的状况。……文学中的喜怒哀乐,归根结底表现着人性的欲求;而优秀的作品总是能够深刻地揭示人性的困境、人性欲求与僵化的社会规制的矛盾,伸张个人的权利,要求给人自由发展以更大的空间。
在我们看来,一部比较理想的文学史,首先应该抓住上述中心环节,深入地揭示出文学所反映的人性发展的过程和文学在人性发展中所显示的积极作用。
文学形式的发展在根柢上也离不开人性的发展。[(15)]
无疑,相对于以往文学史对社会政治、对阶级斗争的强调,章编文学史对人性的重视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它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文学研究打破了旧的思维定势,完全走出了政治因素干扰的时代,使文学研究进入了自由的新天地。它向人们宣告:文学不是政治的传声筒,文学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是人的情感、人的本性的载体。文字的演进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人性不断争取和扩大自由的过程。
章编文学史的另一特征是吸收、渗入了许多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例如,在谈到文艺的起源时,流行的观点是认为文艺起源于劳动,章编文学史则认为从文艺产生的具体过程来看情况非常复杂,并非只与具体的生产劳动相联系。王充的《论衡》作为唯物主义的杰作,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受到了极大的礼遇,章编文学史在肯定其历史意义的同时,正确指出:“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以前在民间文学主流论的影响下,在狭隘的阶级斗争学说支配下,学人们普遍认为:愈接近下层民众的作家愈有进步性,愈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的作品愈具有文学价值,章编文学史对比作出了全新的评价,认为贵族文化自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对于长期以来受人诟病的宫体诗,章编文学史的评价是:“尽管宫体诗存在一些缺陷,它毕竟扩大了中国诗歌的审美表现的范围;尽管它在理论上遭到严厉指斥,仍旧在事实上广泛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概之,章编文学史的看法或别开生面、自成一说,或吸纳它说、熔铸百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的文学史框架,是近年来出现的文学史著作的翘楚之左,将其置之于近百年来的文学史著作中亦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佳作。
但章编文学史并非尽善尽美,甚至可以说它距离人们的期望尚有一定的距离,其理由是:
第一,人性不是唯一的视角。虽然说较之于阶级论文学史观、人本主义文学史观是一种解放,但人本主义文学史观并非绝对正确的唯一的文学解读模式。葛红兵先生在评价现代文学领域内的人本主义文学史观时指出:“它只能使文学史研究由一个窠臼跳入另一个窠臼,使文学史异化为非文学史,……‘人的发现’应该是哲学的目标,准确地说是人本主义哲学的目标,它不应该是文学史的目标”,“因此将‘人的发现’定义为文学史研究的目的,显然是以外在于文学的目标规范文学史研究。文学史就是文学史,它不是阶级斗争的现象化历史,同样也不是‘人的发现’历史。”[(16)]本文认为上吮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亦有偏颇之处,文学一如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复杂,文学不是阶级斗争史,文学不是人性展现史,这是无庸置疑的,但也没有脱离了阶级斗争、脱离了社会政治、脱离了人性、脱离了意识形态的“纯粹”的处于真空地带的文学史,文学史在任何时代在任何条件下总是与阶级斗争、社会政治、人性、意识形态紧密绾结,是故,从人性的视角来描述文学的历史是一种独特的全新的视角,它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应该不应该采用这一视角,而是如何深化如何光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人性不是唯一的视角,人性的剪刀不能剪裁文学的全部材料(例如用人性无法准确说明文学的艺术特质),观察研究文学的视角应该是多角度的。
第二,如上所述,从局部看该文学史已经有了许多突破,但从整体上审视似未能尽如人意。韦勒克·沃伦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17)]遗憾的是,像过去的文学史著作一样,章编文学史分期的标准依然是取决于王朝的更替,而不是依据文学自身的嬗变规律。此外,从全书看,似乎偏重于对思想内容的论述,相对而言,对艺术特色的分析略为欠缺;在主编的意图完整准确的贯彻到全书之中这一点上,似乎还需加强,部分章节中似乎不能清晰地看到主编在看不出《导论》中提出的以人性的发展为核心来描述文学史的理路。我们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也许与我们的期望值太高有关,也许与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相关。文学史教科书的撰写在一定程度上了取决于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分体断代文学史的研究水平,水涨船高,而现在我们不能脱离水面而孤立地要求船的高度。
章、骆两位先生说:“以人性的发展核心来描述中国文学史,应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牵涉的范围极广,有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尽管本书还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但我们相信这种重新描述中国文学发展流程的尝试和一系列的问题的提出,是必要和适时的。”[(18)]这也是本文作者的看法。
四、多元与个性: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思考
1988年第4期《上海文论》出现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这一口号很快汇聚成一股学术思潮。在这一思潮下,已经和正在形成各种新的文学史著作,其中有中国文学通史、有中华民族大文学史、有分体文学史、有断代文学史、有分体断代文学史,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各种新的理论和方法,种种迹象标明“重写文学史”已上升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在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方法论热潮中,更多的是拿来主义者的天下,西方学术理论中的精神分析法、心理结构分析法、神话原型批评法、接受美学、热力学第二定律,耗散结构法、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语义学、符号学……一时接踵而来,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然而,这些方法并没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新贴了许多标签而已。到了90年代,部分学者不再满足于援引、套用西方的学术方法,他们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去建构新的文学史科学体系,从新的视角去审视中国文学史,从而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方法,例如:董乃斌先生认为文学史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文学文本,二是作家心灵,三是文学氛围。以往的文学史往往停留于第一层次,触及第二层次而不深,第三层次基本未碰。[(19)]王钟陵先生在完成了具有方法论新意的《中国中古诗歌史》之后,又撰写了《文学史新方法论》,他尖锐地指出:“我妹至今还甚少那种具有理论形态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人们迄今所做的大多往往还只是对文学发展外在表象的孤立的、断续的描述,……截至目前为止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还仅仅处于前科学的状态之中。”[(20)]为此他提出了更新文学史研究的四项原则:一、史的研究就是理论的创造;二、整体性的三个层次;三、建立一个科学的逻辑结构;四、从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建构伤把握文学史的进程。赵明、赵敏俐先生提出了重构文学史的“系统·综合·比较”的三维动态结构原则,[(21)]他们的这一构想贯彻于由赵明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之中。钱志熙先生提出了“审美·历史·逻辑”的三种基本方法,[(22)]这一方法亦体现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之中。上述新方法新著作的出现标明新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突破,古典文学研究正在走向新的恍煌。
本文作者对待“重写文学史”的基本看法是:第一,“重写文学史”是历史的必然,新的材料在不断发掘,“文本”的意义与范围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研究者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是变动不居的,研究者自身的价值体系、兴趣焦点、认识取向、理解能力亦处于动态之中,是故,文学史著作不会一成不变,相反,它不仅需要重写,而且需要不断的重写。第二,“重写文学史”必须放弃建立一元论的解读模式的幻想,树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撰写出具有个性化的文学史著作。后者是“重写文学史”的关键之所在。
文学史学科的特殊性注定了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文学史学科具有不同的层次,涉及不同的学科领域。面对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和文本,首要的工作是古籍整理,对史料的勾稽、考校、辨伪,对文本本义的注释、翻译,构成了文学研究的第一个层次;其次,需要对作家作品、流派集团、文学思潮、题材体裁、形象的塑造、意向的组合、意境的开拓、艺术的创新等加以剖析、描述、概括和评论。此为文学史研究的第二个层面;最后,在前两个层面的基础之上,探究文学史学科的内在规律,展开文学史哲学研究,此为文学史研究的第三个层面。这就要求研究者应该具备和善于应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目录学、美学、文艺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种知识及方法,需要具备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学识。而任何一元化的文学史观及方法皆无法探明包罗万象的文学史现象,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任何一种单一的范式都不能准确地描述一个事物。”[(23)]从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本身看,任何一种具体的文学史观及操作方法皆有利有弊,没有一种具体的文学史观可以取代所有文学史观,没有任何一种操作方法可以取代所有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观是一种基本的文学史观,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一种基本的方法,是指导具体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所有的文学史观和具体的研究方法皆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指导。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不能取代具体的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凡是从史料出发的研究方法,凡是实事求是的文学史观,皆有其存在的价值。在此前提下,一切旧的方法既不会完全过时,一切新的方法也不是洪水猛兽。目标只有一个,方法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文学史观皆可以从不同的渠道接近文学史的本质。俗语曰:“条条道路通罗马”,释家云:“门门见佛”,此之谓也。
学术个性的形成是研究者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由于研究者的出身阅历、学术环境、性格性情和理想兴趣的差异,自然会选择出适合自己的方法,章学诚云:“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以撰述以自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如果高明者选择了考索之法,沉潜者走上了独断之路,则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方法固然有难易之分,却没有高下之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自己掌握的方法有必要自信,却没有必要迷信。研究水平的提高,不能依靠一个人、一种方法、一种文学史观,它有赖于诸多学者、不同方法、不同文学史观的合力。对个人来说,即使是博古通今的天才人物,亦应该在广泛涉猎、熔铸多种方法之后,形成独特的学术个性。是故,司马迁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追求,马克思有“只有用我的方法”的表白。[(24)]换句话说,只有形成了独特学术个性的研究者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史家,而文学史学科整体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富有学术个性的文学史家群体的诞生。
21世纪的驿站已经在望,理想的文学史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停滞观望、裹足不前,让我们鼓起学术的风穻,以前辈学者的终点为新的起点,继续去追求那遥远的理想!
注释:
①此数据引自张炯《走向完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②胡适《白话文学史》是一部未完成的文学史,本文之所以选择它作为本期文学史著作的代表,不仅因为胡适是按照通史的体例、构想来撰写上册的,更重要的是着眼于胡适及其著作的巨大影响力。
③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胡颂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1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④余冠英:《胡适对中国文学史“公例”的歪曲捏造及其影响》,载《胡适思想批判》,三联书店1959年版。
⑤龚鹏程:《试论文学史之研究——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例》,载《古典文学》第五集,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⑥ ⑦ ⑧ ⑨ ⑩ (12)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9、55、15、56、156、356页,新月书店出版1928年版。
(11)胡明:《胡适整理文学遗产的成绩与偏失》,《文学遗产》1991年3期。
(13)见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室编《中国文学史讨论集》第5页、第6页,中华书局1959年10月版。
(14)董国炎:《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取向与学科态势——兼论〈文学遗产〉的历史使命》,《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15) (18)章培恒、骆玉明:《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复旦学报》1996年第3期。
(16)葛红兵:《人本主义文学史观质疑——与朱德发先生商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17)韦勒克、沃伦:《文艺理论》第303页,第306页。
(19)董乃斌:《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第24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王钟陵:《文学史新方法论》第2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1)赵明、赵敏俐:《关于文学史重构的理论思考》,《吉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22)钱志熙:《审美·历史·逻辑——论文学史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缀玉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3)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24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96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标签: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论文; 胡适论文; 人性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白话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