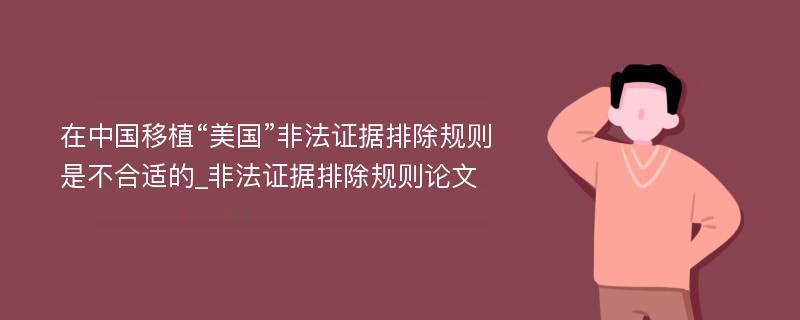
我国不宜移植“美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据论文,规则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33(2002)02-0035-04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与核心,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据制度中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我国现行立法明确禁止非法取证,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定案效力,但是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以及言词证据衍生的其他证据的证据能力,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和解决司法实践中因立法空缺带来的诸多难题,我们需要在总结本国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他国的有益做法,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移植美国的做法,以此作为设计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蓝本。那么这种主张是否可行呢?笔者认为此种主张不够妥当。
法律的移植是将其他国家的法律规范或制度移植到本国,作为本国法的一部分。法律的移植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与武装侵略和文化扩张相伴随,如殖民地被动实行殖民者国家的法律,这种是法律的被动移植;另一种则是主动的法律移植,即移植国认为他国的法律具有先进性和可采性,主动接受和采用他国的具体法律规范和制度。本文所指的是后者,它与我国清末大量的法律移植的主要不同点在于主体的主动性和移植对象的任择性。这种移植既是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又是主体要求进步的自我完善的途径。而法律的本土化则主张法律必须注重利用本国资源,注重本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这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移植,笔者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们所要移植的法律规则本身是否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与生命力。第二,假若移植过来,是否与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相吻合。如果二者不相吻合,现行的体系有缺陷,需要如何完善并使之与“移植物”相衔接。第三,与我国传统的法文化、民族传统是否相互排斥。笔者认为在引进国外,特别是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要求移植“美式”排除规则的呼声最高)时,这三个问题是可行性分析的必要组成部分。
一、美国对违法取得的证据排除规则的自我反省
美国的自白排除法则经历了三进三退的起伏过程。违法取得的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过程虽不像自白排除法则那么复杂,但学界和司法界对此规则的争论却尤为激烈[1]。在排除规则的发展过程中,最高法院提出了实行这项规则的三点主要理由:第一,威慑作用。排除使用非法证据是对那些进行非法搜查和没收,或者在其他方面侵犯宪法规定的被告人权利的警察官员的惩罚,从而使警官们不敢再有同样的违法行为。第二,私生活秘密权利。从威克斯案(1949年)到马普案(1961年),最高法院认为排除规则维护了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所保证的个人私生活秘密权利不受非法搜查和没收的侵犯。第三,法院的公正无私。最高法院采用非法收集的证据使法院制度声誉扫地。但这三条主要理由逐渐遭到质疑和抛弃,几种例外的确立就是伴随着此过程而产生的。对于“威慑作用”,首席法官伯格声称“……没有以实际经验为基础的材料能够支持这种说法,即这项规则实际上制止了违法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因为从逻辑上看,“除外规则对于制止检察官的违法行为是十分适宜的。但是,在一次非法逮捕、搜查或没收事件中,检察官不是违法的当事人,而且他对那些应负责任的警官们很少能采取任何监督措施。”对于第二种“私生活秘密权利”的理由,1961年马普案以后,最高法院不再强调这种保护私生活秘密权利不受侵犯的理论。其原因是此理由有明显缺陷:这项规则似乎对宪法修正案第4条所规定的权利受侵犯的无辜的受害者的补偿无能为力,以及对于那些非法手持火器、麻醉毒品和以彩票打赌的罪犯们(经常是进行搜查和没收的对象)究竟应该享有什么样的私生活秘密权利感到令人痛心的怀疑。至于第三点“法院的公正无私”,现在对这种说法不再强调。正如布兰代斯法官在审理麦克道尔一案时提出的不同意见:“在执行法律中采取一般公民关于正直与公平的观念受到震动的手段,不会促使人们尊重法律。”人们对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基础进行理性的反思是因为它没有取得理想的期望值,反而让社会、许多无辜善良的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美国一法官所言:“当前,美国正着手坦率地正视和切实地检查过去四十年中怀着满腔希望制定的各项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和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在文明世界中,唯有美国社会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这是我们在刑事案件中实行独特的证据排除规则所造成的结果。”(注:马尔科姆·R·威尔基:《除外规则:为什么禁止采用确凿的证据》[J].(美)《司法》1978年第11期。)的确,结合世界其他国家如英、日、德、法等国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坚定地实行“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情况下,只是否定了非法自白的效力,而物证或交法官自由载量,或明文规定排除极少数情况下取得的非法证据,或在司法实践中认可其证据能力。
二、“美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之间存在相斥性
当前诉讼理论界对程序的内在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些学者甚至主张“程序高于实体”,在非法证据问题上表现为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设立具有美国法内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称“美”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种“美式”排除规则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价值观、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结构是否相吻合,即与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体系是否相融,是我们在法律移植之前必须思考的问题。是改造移植法还是改造我国某一部门法的体系,或是将二者加以调和,在此之间我们必须进行选择。正如上述,比较彻底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有在以正当程序为法律灵魂的美国确立,这是与其实行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其它诸多因素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有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未必有“美式”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有“美”式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必有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排除规则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体,它不仅仅是存在于体系之中,还必须与体系相融合,成为其有机的构成要素。
如果在我国确立“美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会使我国刑事诉讼目的——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相统一转向“重保护、轻惩罚”,而且会驱使我国的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走向“当事人主义”。与此同时,一些具体的诉讼制度必须有大的变革。例如我国现行的认证制度就与排除规则不相符。我国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控方提出支持公诉的一系列证据中包含有非法证据,按照排除规则,这些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组成合议庭的法官要了解哪些证据为合法的,哪些证据为非法的,就必须进行必要的审证。在审证过程中,法官不可避免地要受证据内容的影响,导致先入为主,进而左右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心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是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性;证据之间、证据与已证实的事实之间、证据与情理之间的不矛盾性;证据锁链的闭合性;证明结论的唯一性[2]。但证明标准是否符合这四个要求仍要由法官去判断,没有一个客观的尺度(同一案件,由于不同的法官自身的素质不同,经历、情感各异,有可能形成不同的认识)。如果把所有证据,包括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交由审判案件的法官审查,与只把合法证据交给法官审查相比较,很明显,二者的结果有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对如果排除非法证据就会形成“疑案”的案件而言。因此,在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必须先行设立证据审查制度,审查证据的法官要回避案件的审理,以防止先入为主。而在美国,非法证据在庭审前就由被告方提出“动议”予以排除;而且上诉审法院可以以证据违法作为推翻被告人有罪的法定理由。总之,一些基本的证据规则在我国尚未建立,奢谈一律排除非法证据是不现实的。
三、我国民族的心理、法文化传统与“美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相适应
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在其本土受到指责,一旦移植到我国,也不易为绝大多数公民所接受。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儒家思想的熏陶,使人们养成了“温、良、恭、俭、让”的民族性格特征,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的观念,普遍对政府的权力抱有很高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寄托了较高的期望值,而对犯罪行为表现出极大的憎恶和恐惧。守法的公民遵循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信条,对被害人给予极大的同情,并宁愿牺牲很大一部分自由来换取政府的有力保护,这正如德国很多学者坚信职权主义优于当事人主义一样。试想:当被告被指控犯有故意杀人罪时,警察从其家里搜查出来的凶器由于取证方法有瑕疵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而使凶手逃脱;或者当被告被控犯有贩卖毒品罪时,警察搜查出来的毒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使毒贩逍遥法外时,绝大多数公民是否能理解和接受?在改造外国法,还是改造我们的文化这一问题上,有些人主张改造我们的文化,这无异于削足适履,本末倒置。文化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这是因为文化的载体——民族亦无优劣之分——当然这并不否认人类和文化是可以进化的。
时下,国内一些学者一谈到诉讼模式、司法改革、法治等,无不将美国的司法制度奉为圭臬。不可否认,普通法确有诸多优点和长处,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一谈到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便一味以美国为楷模,言必称美国,就显得极其不正常了。姑且不论我国法律秉承的是欧陆法系的传统,与普通法传统相去甚远,即使在西方国家,美国法律制度在许多方面也相当特异,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制度更具代表性和普遍性。在美国法律发展史上曾经兴起过一场法典化运动,试图把整个普通法制定成各种不同的法典,但终因失败而告终,那只是“一个那个时代的法律所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注: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这也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半个世纪以前,美国法学家庞德在考察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与法学教育后指出,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法律传统,不宜改弦易辙,另起炉灶。庞氏还指出,改习美国制度将要遇到的种种困难,很可能导致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结果。我们之所以对此充耳不闻,既与美国的强势文化的影响有关(它使我们深信美国的成功经验也必然切合于我国),也与我们视野的狭隘有关,因为现在我们接触最多的外国文献是英文,我们有较多机会访问的国家是美国,这足以使我们深受美国的影响,但这并不能证明美国的经验就最适合于中国。
四、结语
当然,笔者并非反对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是反对建立脱离我国实际、全盘“美”化的证据排除规则。依法治国,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必须提升程序化的地位,改变人们“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使人们认识到依程序法办事不仅必要,而且也符合诉讼客观规律。但我们切不可矫枉过正,导致“轻实体,重程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实体和程序并重,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在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我们不能闭门造车,而要实行“拿来主义”。我们要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以及各种立法模式的借鉴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在具体的模式选择上,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多借鉴欧陆国家的经验,这既同我国的法律传统相适应,又可以减少因制度重建带来的震荡并降低改革成本,也与我国整个司法制度、诉讼模式相协调。
[收稿日期]2001-12-20
标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 法律论文; 法官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