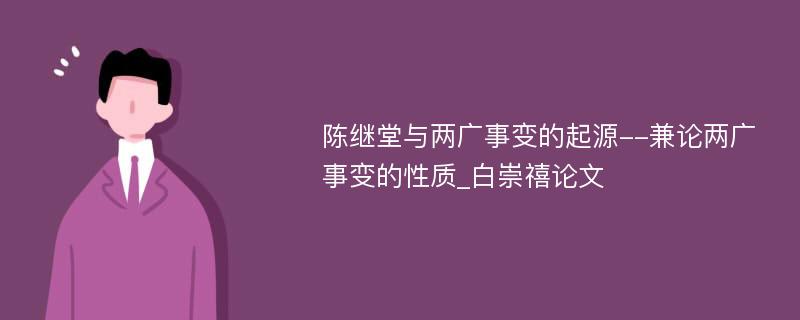
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兼论两广事变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广论文,事变论文,性质论文,陈济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8-0114-05
在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中,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各起了什么作用,即谁是事变的策划者和发起者,事变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说法。后来的研究者一般都采纳李宗仁一面之词,认为陈济棠是事变的发起者,而且他发动事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迷信思想作怪。(注:如张同新称:“两广联合行动的酝酿说明,陈济棠的主观动机政治投机占主导地位。”见张同新:《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3页;《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亦称陈发动事变的原因之一为“迷信天命”,见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5页。)笔者认为,陈济棠是两广事变的发动者之一,但事变的发起者实为李宗仁、白崇禧,是他们的策动才使得陈最后下定反蒋的决心。弄清这个问题,事关恢复和认清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并涉及对陈、李、白等人的历史评价和两广事变的性质判定等问题。为此,笔者就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问题进行考证论述,并由此顺便论及事变的性质。(注:论述两广事变性质的文章有:李静之:《“两广事变”性质初探》,《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谭庆:《如何正确评价“两广事变”》,《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沙东迅:《论两广事变的性质》,见《粤海近代史谭》,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夏潮:《试论“两广事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有的说是“抗日反蒋”,有的说是“联日反蒋”,有的说是派系之争。均欠确切。)
一
在两广事变之前,两广地区的基本政治格局是:两广地方实力派以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以西南两机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招牌,与蒋介石中央政权相抗衡,保持一种独立和半独立的状态;陈济棠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两广地方实力派中起着主导作用,桂系要仰仗陈济棠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才能与蒋介石对抗,但陈济棠并不干预桂系内政,桂系却一直在推动陈济棠反蒋。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因脑溢血突然在广州逝世。蒋介石乘机要拔除西南两机关,统一西南。两广地方实力派心有不甘,便发动了两广事变。由于陈济棠的作用和影响,他当时的态度实际上是事变能否发动的关键因素。但究竟是他的态度影响了桂系,还是桂系影响了他的态度,当事人的说法却大相径庭。
在策划两广事变的过程中,白崇禧和陈济棠联系最为密切,活动最为频繁,影响也最为深刻。但白崇禧的回忆录对事变只字未提,陈济棠则语焉未详。他在其自传稿中对事变的记述相当简略:“廿五年六月,余以抗日准备工作已将完成,抗日时机亦已成熟,及决心派兵十师北上抗日。同时发表抗日主张通电,并由党部募捐款项逾数十万元,分别援助之抗日军,及韩国革命志士,以增进抗日声势。而中央认为时机不到,制止余之行动,国人亦间有误解余之主张,诸多揣测。余以耿耿忠心,既不为中央及国人所谅,为表明心迹及避免分裂计,即发表通电,自动下野赴港。”(注:《陈济棠自传稿》,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年,第43页。)显然,白崇禧和陈济棠都在淡化两广事变的严重性,而且陈济棠把发动事变的原因归结于“北上抗日”,这是不完全真实的。
李宗仁是两广事变的另一主角,他在回忆录中也是尽量淡化事变的严重性。在关于两广事变的章节中,李宗仁对于“活龙口”(陈葬生母于洪秀全祖坟风水穴上)、“机不可失”(迷信相士之言,以为反蒋“大运已到”)、“陈维周为蒋介石算命”(称蒋“骨相”不如陈济棠,难过1936年这一关)等故事,大肆渲染,可是对于桂系如何暗中策划事变及事变的真正预期目标却毫未提及。仿佛事变的责任完全在于陈济棠,他与白崇禧早就料定事变必败无疑,参与事变无非是碍于情面为陈抬轿子而已,而陈一走事变就告结束。(注: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5年,第433-437页。)桂系的重要成员、李宗仁的幕僚程思远也持相同说法。他称胡汉民去世后,陈济棠和其兄陈维周得知蒋介石将对桂用兵,“兄弟密商竟日,以为粤桂相依为命,蒋如得了广西,广东安能幸免。与其坐以待毙,何如铤而走险,先发制人,以北上抗日为名,举兵反蒋。计议已定,遂以此一决策与广西方面商讨。”此后,李、白、陈曾多次讨论,“李、白主张慎重,邹鲁也反对用兵,但陈济棠却要求采取积极行动。至是,李、白认为,粤桂不能各行其是,于是与陈济棠共同行动”。(注: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86页。)李宗仁和程思远都把两广事变发动的责任推到陈济棠身上,桂系似乎是迫不得已的追随者。
与上述说法相反,广东军事将领将发动两广事变的责任归结于桂系。两广事变爆发后通电投蒋导致陈济棠下野的余汉谋称:“二十五年(1936年)上半年,他(陈济棠)受不了李、白的怂恿,再加上韩复榘、刘湘等派人来广东游说,遂又称兵反抗中央。陈济棠太自信,又相信他的那位老哥陈维周。陈维周脑筋不清楚,李、白利用他,把他捧上了天,他就嗾使陈伯南反判中央。”(注:《余汉谋先生访问记录》,《军系与民国政局》,台湾近代史所“口述历史”之七,第226页。)两广事变爆发后“封金挂印”的李汉魂称,白崇禧早在5月17日即已悄然来穗活动,并约李汉魂、邓龙光夜谈二三小时,对此次事变起了重要策划推动作用。(注:《李汉魂将军日记》,香港1975年版,转引自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3页。)陈济棠的另一将领李洁之称:胡汉民去世后,白崇禧以吊丧为名来穗与陈济棠会晤。“白对陈治粤成绩备及推崇,然后谈论形势,竭力怂恿陈济棠反蒋抗日。白大说蒋如何不得人心,内部如何互相猜疑,财政如何困难等等,以加强陈的反蒋信心和决心”,接着白又大谈两广的有利条件,称反蒋机会千载难逢,不应错过。“陈济棠听了白的形势分析以后,认为十分精确”,加之“陈一向相信乃兄的星相之术,故亦认为此时反蒋正合时机,一经白崇禧提出粤桂联合反蒋的建议,他便欣然接受,决心大干一场”。(注:李洁之:《陈济棠主粤始末》,《南天岁月:陈济堂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24页。)余汉谋、李汉魂和李洁之都把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说成是受桂系怂恿推动的结果。
粤桂将领均把责任推给对方,自然不可全信。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李宗仁和程思远都称胡汉民去世后的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就致电陈济堂,请陈派亲信人员赴京,共商善后。陈济棠乃派其兄陈维周入京谒蒋。陈维周得知蒋将对桂用兵后回广州与陈济棠商议对策,最后决定联桂反蒋。按当时条件,陈维周去宁返穗,到最后作出决策,不会早于5月15日。而白崇禧已于15日来穗活动,劝陈反蒋。这些说明桂系作出发动事变的决策早于陈济棠。相比之下,桂系重要将领、湖南籍的刘斐的说法更值得注意:“当蒋提出彻底统一两广的要求后,陈济棠当然不愿意,桂系则极力主张趁此时机反蒋。这时,陈济棠若不共同反蒋,就会陷于孤立地位。他感到与其坐以待亡,不如和桂系一起反蒋,以便进可以争取全国舆论的同情,扩大西南声势,进一步瓜分蒋介石的政权;退也可以使蒋投鼠忌器,多少向西南让点步,以便维持西南现状。”(注:刘斐:《两广“六一”事变》,《南天岁月》,第463页。)刘斐曾和李宗仁长期驻留广州,推动陈济棠反蒋。胡汉民去世后,刘斐和白崇禧同飞广州,后又作为两广代表到湖南劝说何键共同行动,他应该知道相关内情。他属于桂系,但又是湖南人,他的话应该说更可靠一些。
二
如果说,仅仅是少数当事人的回忆尚不足为凭。那么,考察一下陈济棠和桂系的政治志向及双方与蒋介石的关系,可更加清楚地认识双方在发起两广事变中的作用。首先,桂系的“政治兴趣和怀抱是面向全国的”,而陈济棠“所愿意承担的义务只在广东本省,他表示自己毫无超出省界向外扩大权力的欲望。”(注:[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第136页。)桂系在北伐以后即想把势力扩展到全国,并曾一度控制中央。后来虽退回广西,但始终不忘入主中央。广东胡汉民等元老派一直想以争正统来重回权力中枢,但陈济棠实际上只满足于“南天王”地位,他不愿因反蒋而引起南京对广东过多的仇视和注意。1932年桂系即想以入赣、闽“剿共”为名把势力扩展到广西以外,后因广东方面认为桂军有准备入粤之嫌,李宗仁不得不停止桂军行动。1933年福建事变发生时,胡汉民想利用形势,在西南建立有别于南京、福州的“第三政府”。陈济棠对此持异议,李宗仁却予以支持。胡汉民便决定以桂系为武力中心,在广州组织政府,如能乘势逼蒋、汪下野,则将此政府全盘移往南京。陈反对在广州开府,胡、李便准备在梧州建立政府,因陈反对而未果。(注: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二一1028。)余汉谋云:“西南人士像刘文辉、龙云、李宗仁、白崇禧,都是自命不凡的人物,决不以静处一隅为满足,他们对中央总是怀有二心;陈济棠有广东土皇帝思想,与中央总是格格不入。”(注:《余汉谋先生访问记录》,《军系与民国政局》,台湾近代史所“口述历史”之七,第226页。)充分说明了桂系和陈济棠抱负的差异。
其次,桂系和蒋介石的矛盾比蒋、陈矛盾要尖锐深刻得多。1929年武汉事变后,蒋桂矛盾已打下“死结”,(注:参见拙文:《论武汉事变对桂系的影响》,《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98年第6期转载。)蒋介石为消灭桂系,“确已用尽一切手段。”(注:《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台湾近代史所,1988年编印,第940页。)桂系亦不愿善罢甘休。1930年12月桂系最为困难时白崇禧即说:“广西人是不会投降蒋介石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环境再坏一些,也是不会投降的。我们为要争取生存,必须奋斗到底,一息尚存,此志不渝。”(注: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44页。)西南两机关成立后,李宗仁即常驻广州,专事推动反蒋的政治活动,并和元老派共同劝说推动陈济棠反蒋。(注:刘斐:《两广“六一”事变》,《南天岁月》,第462页。)1935年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蒋介石的势力进入贵州,广西处于蒋介石直接威胁之下。尤其是,当时对由滇黔经桂运到粤湘的烟土收税是桂系收入的主要来源,烟税占桂系财政收入的1/3以上。(注:黄绍竑:《新桂系与鸦片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蒋介石控制贵州以后,令滇、黔两省烟土都改道武汉。于是,桂系烟税大减,与1934年同期相比,1935年的收入不到1/2,1936年不到1/3。(注:陈雄:《新桂系统治下我所主办的广西禁烟》,《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广西财政陷入严重困境,于是加紧推动陈济棠反蒋。1936年初胡汉民回国被南京任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后,李宗仁看到南京方面的人事部署,更深以蒋存心拆两广的台为虑。白崇禧提出留胡在粤三点做法以对抗南京,即政治上尊重、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顾。(注: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84-85页。)胡汉民去世后,陈维周在南京“探悉了中央彻底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注: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5年,第433页。)在蒋介石首先要解决桂系的条件下,桂系决不会只是被动地给陈济棠抬抬轿子而已。相比之下,蒋、陈矛盾要缓和得多。1931年“非常会议”前,蒋利用陈反桂,双方关系密切。“非常会议”后,蒋顾忌胡汉民和西南两机关,始终未对广东压迫过甚。而陈济棠也主张有条件地与蒋介石合作。“事实上,在每次西南实力派发出联合通电批评南京统治时,陈便秘密拍一个私人电报,要蒋放心,表白他只是迫不得已在公开电报上署署名而已。”(注:[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第140页。)桂系首领之一、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称:“广东的领袖反蒋是很不坚决的,湖南的实力派领袖(何键)是不堪信任的,广西被挤在广东和湖南之间,它是虚弱的,它不能鲁莽轻率地采取冒险的举动。”(注:[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第140页。)为了反蒋图存,桂系必然要推动陈济棠共同行动。
再次,陈济棠敷衍各方,互相利用,患得患失的性格特征和为政之道也决定了他不可能率先坚决反蒋。陈济棠有“福将”之称,程思远称他是“因人成事,夤缘时会,没有什么特殊贡献”。(注: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80页。)福建事变时,陈济棠不仅不同意组织“第三政府”,而且,蒋介石以1500万元即换得了他不支持十九路军,而十九路军和广东还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注: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74页。)现蒋介石要进攻桂系而要广东维持现状,李宗仁谓陈济棠即认为“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故要“抢先一步,采取主动”,(注: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5年,第434页。)似不符合陈济棠的处世之道。关于这一点,刘斐讲得非常清楚:“尽管他(陈济棠)每次都是开出反蒋的支票,但总没见他兑现。他既想扩大地盘,又怕丢了老本,患得患失的心情老在折磨他,各方策动他反蒋的人,对于他这种迟疑不决的态度非常不满,有时候我也气得跑回广西去了,白崇禧便常常带着挖苦的口吻说:‘我们跪在猪栏门口喂猪,唯一目的是要猪肥嘛!只要猪肥就好了,急也急不来的呀!’这说明当时推动陈济棠反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只有后来蒋介石逼得他无路可走了,他才被迫走上反蒋的道路。”(注:刘斐:《两广“六一”事变》,《南天岁月》,第462页。)佐之以事变后陈济棠因部下反叛即告下野,而桂系在蒋介石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苦力周旋,拒不接受蒋介石任命,最后迫使蒋让李、白留在广西的事实,可以看出桂系是两广事变的真正发起者和策动者。
三
当然,陈济棠在发动两广事变时,也不是完全被动而受李宗仁、白崇禧怂恿操纵的。陈有“土皇帝”思想,与蒋介石的“安内”政策相矛盾。而且,由于陈济棠在以两广为首的西南地方实力派中居主导地位,蒋介石往往把广东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面对蒋介石对广东咄咄逼人的攻势,陈济棠不可能无动于衷。1931年“非常会议”期间,蒋介石于7月23日发布《告全国同胞一致要安内攘外电》,首次提出了“攘外应先安内”的口号,而“粤逆”是安内的主要对象。(注:《先总统蒋介石全集》第3册,台湾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125页。)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主力“围剿”工农红军。但蒋介石的“安内”不仅是要消灭共产党,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要消灭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包括利用他们与红军互相残杀。这一点陈济棠可谓洞若观火,因此,他与红军“外打内通”,对付蒋介石。在追剿红军长征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西南贵州、四川等省。红军到达陕北已元气大伤,蒋介石“安内”的当务之急便是地方实力派。中央苏区本是广东与中央军之间的天然屏障,红军长征后,广东便直接处于蒋介石的军事威胁之下。陈济棠之所以能偏安广东,很重要一个原因便是有胡汉民和西南两机关作护身符和挡箭牌。有了胡汉民的存在,不仅使西南反蒋的号召力倍增,蒋介石也不敢作过分的逼迫与威胁,而且西南各派的团结也较易维系。因此,胡汉民的去世给蒋介石提供了拔除“两机关”统一西南的极好机会,而对于陈济棠在广东的统治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胡汉民死后,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对陈济棠展开了强大的攻势。中央军在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积极进行军事布置,表现出以武力统一西南的迹象。(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6页。)南京中央所属各级及与中央关系密切的各报都以悼念胡汉民为名,大肆宣扬全国统一于南京中央的主张,向西南发出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上海《大公报》称:“且以中国现状言之,国际环境困难至此,非有统一之政府,巩固之中央,欲求保持残喘,且不可得。”“吾人以为凡爱胡先生者,当知因胡先生之死而促进团结,则益增死者之光荣。”(注:1936年5月6日上海《大公报》。)这些都给陈济棠以极大的压力。
如果说,在蒋介石决定首先对桂系用兵的情况下,陈济棠对反蒋还有所犹豫的话,那么,在蒋介石改变策略,决定把两广一起解决时,陈济棠便不可能坐以待毙。胡汉民死后,蒋介石派王宠惠、居正等来吊胡丧,乘机向陈提出五条件:一、西南执行部和政委会取消;二、改组广东省政府,省主席林云陔调京任职;三、在西南执行部和政委会工作的负责人,愿意到南京工作者,中央将妥为安排,愿意出国者,将给旅费;四、陈济棠的第一集团总司令改为第四路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五、统一币制。(注:程思远:《我的回忆》,第86页。刘斐称“外传蒋曾提出五项要求,有无其事我记不起了。”(《南天岁月》,第463页)但据1936年7月9日《红色中华报》的报导称:居正赴粤,带来四条件:1.取消西南军政委员会;2.两广军队改编;3.统一财政;4.未详。当时中共有不少地下工作者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包括情报系统),这一消息自非空穴来风。可见蒋介石确有五项要求。)在这些条件中,取消西南两机关为关键。因为这是保持两广半独立状态的重要屏障。陈济棠不甘束手就擒,加之桂系的怂恿和策划已到一定火候,于是便和桂系以“抗日救国”为名,起兵反蒋了。
陈济棠可以说是在桂系怂恿和蒋介石逼迫双重原因下决定发动两广事变的。他在下反蒋决心的过程中,也是顾虑重重,反反复复的。根据已有材料,可以看出他决策的过程:5月15日,陈济棠与白崇禧会晤,白向陈分析时局,劝陈反蒋;16日,陈即同在穗的高级将领商议,但许多人对反蒋不置可否,意见无法取得一致;19日,陈再次召集高级将领近20人进行会商,并请白崇禧出席和讲话。余汉谋认为蒋介石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反蒋没有绝对的把握,这实际上是持反对意见;20日,莫希德、李洁之等各位将领,准备联合制止陈济棠的反蒋行动,并拟请余汉谋出面领导反陈。正因为如此,26日,陈济棠取消反蒋的决定,并通知各高级将领;但到29日,陈济棠、李宗仁派赴湖南的密使陈维周、刘斐归来,得到何键口头答应支持两广的信息;当晚,李、白与陈续谈反蒋事(详情不得而知,但对陈下最后决心无疑起了重要作用);30日,陈济棠问“计”于陈维周、翁半玄,得谶语“机不可失”;当晚,陈又通知广东将领反蒋。陈济棠作出反蒋决定的过程,表明他主要受桂系影响,自己的决心并不大,内部渐趋不稳,这些实在已是失败的征兆。
四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两广事变的性质既不是“抗日反蒋”,也不是“联日反蒋”,或是单纯的派系之争,而是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斗争,即“安内”与反“安内”的矛盾和斗争。事变主要是蒋介石要解决西南问题而起,是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和两广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一方要扫除异己力量,实现对全国的统一;一方要巩固地盘,进而争夺全国的统治权。争夺的中心是地方,依靠的是实力。蒋要利用胡汉民去世之机取消西南两机关这个地方主义的大本营,粤桂均不能接受。蒋要先对桂系用兵,有着“反蒋情结”的桂系不愿坐以待毙,便联合广东对抗。陈济棠不愿彻底统一两广,要保持两广的半独立地位,便和桂系一起行动。尽管他们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招牌,但很显然他们只是利用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作掩护,而不是在这一潮流推动下去抗日反蒋。就广东方面而言,陈维周后来承认事变原意不是抗日反蒋,不过想虚张声势,挡住蒋指向广东的锋芒而已。(注:黄启汉:《两广的“六一”运动》,《学术论坛》1987年第1期。)就桂系而言,李宗仁、白崇禧决心反蒋后,“想来想去,只有用出师抗日这块招牌,才能取得各方的同情与支持。”(注:程思远:《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学术论坛》1987年第2期。)于是,打出了“抗日救国”的旗号,宣布“反蒋抗日”。白崇禧劝陈反蒋时尚称:“至于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系。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代表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练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陈维周鼓动广东将领时介绍了自己与日本领事接洽的情况,“并说我们的策略是‘明修见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注:李洁之:《陈济棠主粤始末》,《南天岁月:陈济堂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5页。)因此,两广事变只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权利之争,派系斗争只是其表现形式而已。
两广地方实力派反蒋并没有“联日”。尽管1931年后两广为增强反蒋声势,与日本多有接洽,也购买了一些日本武器,聘请了日本顾问,但他们出于民族大义,并未与日本签订什么协议,最多是一些心照不宣的幻想和默契。广东地方实力派中甚至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且有翟歧卿到蒋统区暗杀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只是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注:刘斐:《两广“六一”事变》,《南天岁月》,第468页。)两广事变发动时白崇禧、陈维周所言,至多只能视为虚张声势的打气之词。陈济棠下野后曾说:“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注:胡铭藻:《李汉魂封金挂印与余汉谋回粤倒陈》,《南天岁月》,第506页。)两广只是利用了少数日本人而已,并没有到“联日”的程度。(注:详见拙文:《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1931-1936)》,《学术研究》2000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0年第11期转载。)
综上所述,两广事变是一次由桂系策划的、由两广地方实力派共同发动的、以“北上抗日”为招牌的地方实力派反对中央统一的斗争。其结果,陈济棠下野,广东半独立地位取消,桂系也与蒋介石中央实现了部分和解,这对国民党团结对外无疑是有利的。
标签:白崇禧论文; 胡汉民论文; 两广事变论文; 陈济棠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李宗仁回忆录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程思远论文; 我的回忆论文; 李宗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