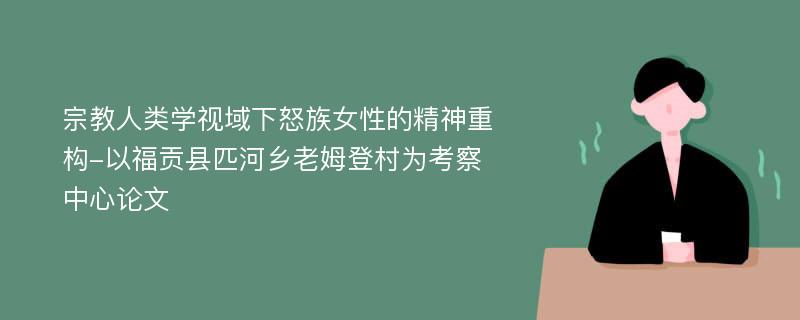
·金沙江文化研究·
宗教人类学视域下怒族女性的精神重构
——以福贡县匹河乡老姆登村为考察中心
何城禁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怒族女性形象经过不断发展变迁,逐步引起了民族学和人类学学者的注意。中国怒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通过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乡老姆登村为中心的考察,从宗教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可以透视出怒族女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对自我精神的重构。
[关键词] 宗教人类学;怒族;女性;精神重构;民族学;祭祀;基督教;母系社会;父权制
怒族起源于氐羌民族,历史上生活在中国的西北,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至隋朝前后入滇,生活在怒江、澜沧江两岸,如今的怒族主要分布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县和西藏自治区的察隅县有少量分布,主要聚居在碧罗雪山、高黎贡山之中[1]。怒族由“阿龙”、“阿怒”、“怒苏”、“若柔”四个支系组成,总人口三万多人[2],属于人口特少民族。怒族在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中,形成了多元复杂的宗教信仰文化。怒族妇女是怒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的参与和主导作用。2018年11月,笔者一行进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乡老姆登村进行田野调查,在怒族妇女的精神建构中发现宗教学与人类学的意义。
一、母系社会中的怒族女性:积极主动
怒族在母系社会中存在“女婚男嫁”的习俗,在今天少数怒族地区仍有女子娶夫、男子出嫁以及公房的文化习俗遗存,这些都是怒族母权制曾存在的证据。在当代怒族社会中保存的大量关于怒族女性的故事和歌谣中,体现出在约1500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怒族女性在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以积极主动的精神面貌参与发声,并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流传于匹河乡知子罗村的怒族民间故事《男人生小孩》中,叙述在人类远古时期,由男人生小孩,女人照顾男人坐月子,女人看到男人生小孩后呻吟不止、不吃不喝,女人对男人充满了同情和怜爱,决定不让男人生小孩,而由自身承担生育功能,从此妇女生育儿女、织布、做家务,男人种地[3]。在匹河乡等怒族地区都集体流传着《始祖的传说》,怒族人将民族的始祖追溯到茂充英,而茂充英时是从天而降或者是动物交配的后代,女始祖茂充英又和虎、蜂、麂子、鹿等动物交配繁衍,逐步形成了虎氏族、蛇氏族、麂子氏族、蜂氏族、马鹿氏族,而茂充英是这些氏族的始祖,统治和管理一切事物。茂充英还要娶很多男人,而生下的女孩都很聪明机灵,而男孩则笨拙。女子娶夫时都用炭火灼烫男子,直到男子有痛感直觉后才娶回家去,男子嫁人时也不舍家中财产十分痛苦,女性见状,便改男嫁女婚为女婚男嫁[3]。这些流传至今的怒族民间故事是怒族社会早期生存经验的当代遗存,是属于民族的集体性历史记忆。
式(10)中,解释变量为cuit,表示2001~2016年各地产能利用率,被解释变量有cycit(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代表各地区历年经济波动程度,goiit(government investment)表示各地区历年政府投资,demit(demand)表示各地区历年的需求,scait(scale)表示各地区历年炼化企业的规模大小,μi表示不可预测的固定效应,εi为随机误差项,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如表3所示。
在怒族氏族社会早期,女性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女性形象也多被塑造为始祖形象、猎神形象、山神形象、圣母仙姑形象和龙女形象[4]。怒族女性聪慧机敏,吃苦耐劳,极富担当精神,与同时期的男性相比则形成了女强男弱的性别结构。女性在社会中主动承担社会和家庭的责任,男性则龟缩在女性的保护中,缺少独立的性别声音和担当意识。在《三妹与蛇郎》的故事中,作为男性形象化身的蛇郎娶三妹为妻,大姐心生嫉妒谋害了三妹并代替三妹和蛇郎生活在一起,和大姐生活多年后蛇郎一直没有发现自己的妻子三妹已经被谋害和调换,死去的三妹的化身与大姐斗智斗勇终于战胜了大姐回到了丈夫[3]。这则民间故事中,男性主人公看似一直在场,实则发挥的功能并不多,女性主人公三妹承担了主要的情节叙事功能,她和加害者大姐之间几个回合的斗争十分吸引眼球,显示了女性主人公的机智善良。在怒族地区还有大量的龙女故事,如《腊塞与龙女》、《猎人的妻子》、《雪峰洞》、《孤儿的奇遇》、《金花和银花》和《变小狗的姑娘》都塑造了个性鲜明、重情重义、善良果敢的龙女形象[5]。这些女性形象身上都凝聚着怒族女性不屈不饶地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和不怕困难、不畏强权艰险的果敢坚毅,以及善良博爱奉献等美好品德,这些氏族社会早期的民族精神品质在当今社会怒族女性中仍然受到认可,并得以代代相传。
紫花鹤顶兰属鹤顶兰属(Phaius Lour.),该属植物在我国有8种,在贵州有记录且分布广泛的是仙笔鹤顶兰(Phaius columnaris C. Z. Tang et S. J.Cheng)和黄花鹤顶兰(Phaius flavus (Bl.) Lindl.)。紫花鹤顶兰区别于其他种的特征是:假鳞茎细长,粗2 cm左右;花葶侧生于茎中部以上的叶腋,长38 cm左右,超出叶面之上;花苞片早落(封三,图Ⅵ)。模式标本采自印度,在我国台湾、云南、广东、广西、云南亦有分布。
“仙女节”又称“鲜花节”“山母节”,是怒族重要的民族节日,至今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丙中洛乡怒族聚居的民间盛行,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怒族仙女节的起源故事讲述了名叫阿茸的美丽姑娘用聪明智慧发明了溜索,为怒族人民带来了便利,受到怒民的爱戴,却遭到了土司的陷害。阿茸姑娘躲进高黎贡山的山洞中,在农历三月十五日这一天土司放火将阿茸姑娘烧死在了山洞中。于是在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这天,怒族人民都会纪念这位聪明能干的姑娘,这一天便被定为仙女节,成为怒族的民族传统节日。仙女节的故事实则为一则始祖故事的变型,在阿茸作为民族女始祖的故事基础上附会了奴隶制社会的产物——土司。女始祖阿茸姑娘在改善民族生活后又承担了反抗土司压迫的功能,实则为一种箭垛式的形象塑造[7],让阿茸姑娘成为所有美好精神品格的化身和符号,是怒族人民赢得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
原始宗教信仰的精神建构对怒族女性的排挤和打击在如密期祭词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3月6日怒族如密清节日这一天,祭师便会在节日上举行祭祀仪式、念诵祭词以清洁村寨,为村民祈福。由怒族学者曲路、叶世富搜集整理,由老姆登村祭师拉吉口述的《怒族如密清祭词》表达了怒族人民对血鬼和瘟疫鬼的憎恨,赞扬了怒族百姓不屈不饶地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英勇精神以及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同时如密清祭词也将怒族村寨的不幸遭遇归咎于怒族女性的不贞不洁,“在天神创天时,在地神造地时;天上一片净空,地上一片净土;怒寨一片净空,怒村一片净土;怒寨没有血鬼,怒村没有瘟疫;后来女子舂米,久舂舂不出米;男子到碓房帮舂米,男人舂碓女人筛米;男女久处生出情,双双伤风败俗;男女生情出邪气,邪气变成恶血鬼;血鬼败坏了净空,瘟疫沾染了净土;血鬼败坏了怒寨,瘟疫沾染了怒村;血鬼夺走了怒家的性命,瘟疫威胁着怒人的生存……”如密清祭词中将瘟疫和血鬼的出现归因于怒族男女两性关系,而男女生情的原因则认为是女性劳动的拖沓和对男性的有意引诱。
1913年,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并在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中产生极大影响。从1913年至1949年,经过外国传教士麦克卡西、杨思惠等人的传教活动,怒江地区建起了207座基督教堂,拥有21062名教徒[7]。1949年怒江地区实现和平解放时,在原碧江、福贡两县的基督教怒族教众达5000余人,约占两县怒族人口的总数的61%,教徒人数超过非教徒人数[8]。老姆登村毗邻原碧江县城,在1986年碧江县撤销县制后,纳入福贡县的管辖范围。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老姆登村一直都在基督教的文化辐射范围中,民族解放后实行的宗教信仰政策也给怒族人民自由地进行宗教选择留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在怒族村寨老姆登村进行田野考察过程中,发现女性教众明显超于男性教众。结合老姆登教堂每周三、每周六、每周日开展宗教礼拜活动的情况,调查数据显示老姆登村信教女性达83%,男性信教比例为60%,女性信教比例超男性23%。调查数据表明怒族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接纳基督教文化作为精神信仰。
在流传至今的众多怒族民间文学中可以看到大量氏族社会母权制的残余,女性多以一种光辉正面、坚强美好的形象留在民族记忆中,她们在民族的发展和传承过程中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积极主动地参与发声。无论是民族的女性始祖、神灵还是机敏的普通人,怒族的女性都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融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过程中,并掌握着较多的话语权。
二、父权制与原始宗教信仰中的怒族女性:压抑和缄默
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乡老姆登村主要盛行原始宗教信仰和外来宗教基督教。原始宗教信仰是老姆登村的本土宗教信仰,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至今在怒族社会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怒族属于直过民族,解放前仍然保留着原始公有制和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庭公社残余。而怒族女性从享有崇高地位的母权制社会过度到漫长的父权制社会,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被剥夺了,成为父权制社会的附庸。为了打击怒族女性的权威,彻底地惩罚和规训女性,父权制在民族的精神建构中将女性驱逐出去,在精神上给女性套上了低贱和歧视。如此一来怒族女性的生存境遇就处于一种边缘的境地,在精神建构上相对于当权的支配话语而言,她们是一个压抑而缄默的群体。
k-means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nkt)。其中,k指聚类簇数,t指迭代次数,n指对象数,所以对于处理大数据集时,具有高效性,而且实现方式简单、快速。通过实验表明,k-means对于处理簇接近高斯分布时,效果更好。因为k-means需要事先指定k作为初始质心,对k的选取会导致不同的分析结果,所以对于一些事先需要分类的数据分析效果不好,影响最终分析结果。对“噪声”和孤立点数据较为敏感,容易对均值产生较大影响,且分析只能保证局部最优,不能保证全局最优。
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传入之前,怒族地区主要盛行的是与其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始宗教,信仰万物有灵。怒族原始宗教有其固定的祭祀仪式,仪式主要由祭师来完成。祭师是怒族的民间仪式专家,掌管怒族的民间宗教事务,是人与鬼魂沟通交流的中介,是鬼魂在民间的代言人。匹河乡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怒族乡,老姆登村也是当地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整的村寨,通过对老姆登村的两位当代怒族祭师的访谈,进一步探知怒族原始宗教信仰祭祀仪式,以及女性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呈现的角色。
每个铸模浇到银阳极板重量所需深度,此时倾转机构稍稍回位等待;圆盘回转使下一个铸模进入浇铸区,倾转机构继续倾转对该铸模进行浇铸;以此类推,直至浇完。
杨大林是老祭师拉吉的徒弟,近年来的如密期开春节祭祀都是由杨大林来担任祭师。在对杨大林的访谈中,他也指出女性在传统祭祀活动中是被排斥的,最初不能参加、不能触碰到祭品,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女性开始可以到场参观。祭师杨大林介绍在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六大样中,牲祭中鸡和猪一定只能是公鸡和公猪,可见在传统民间宗教信仰中仍然保持着对带有女性性别表征的事物的深刻排斥和疏离。
在原始宗教信仰中的怒族女性是被父权制社会打击和排挤的,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话语空间,被塑造成民族精神苦难的原罪,被推到民族的边缘乃至缄默失声。女性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受到歧视,她们的形象被刻意扭曲,精神状态受到传统民间宗教的压抑而不得舒展。
95岁的祭师拉吉在当地怒族村寨中属于年龄最长者,享有较高的社会威望,曾担任老姆登村传统节日如密期开春节祭师。据拉吉描述,在远古时期怒族就是一个相对弱小的民族,在历史上曾受到傈僳族等周边民族的侵略,怒族女性常被作为族群之间抢夺的对象。被抢走的怒族女性往往成为他族的妻子,或者被卖往别处。在怒族人去世的祭祀仪式中,金竹这一具有民族迁徙意义的象征物是不会为逝去的女性吹响的,只有民族的男性去世才具备吹响怒族龙竹的资格。
对于单层工业建筑来说其结构时钢组成的所以其防震体系较高;并且建筑所使用的钢结构是一种可以循环使用的材料;钢结构厂房组件标准化加工,工厂生产,装配式施工;钢可以合理地用于高强度钢;高强度钢筋可用于混凝土基础中的钢筋;预拌混凝土用于基础现浇混凝土,预拌砂浆用于建筑砂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它符合绿色工业建筑物资源利用评价指标。
在怒族的祭祀歌词中还有许多反映女性在原始宗教信仰中的处境的,如《同八动》、《指路经》等。同八动,怒语音译词汇,意为出松林,为怒族人民过新年的一种祭祀活动,妇女不得参加,凡参加祭祀活动的男子每人拿一只公鸡、酒、米、粑粑到松林里祭后杀吃。《指路经》运用于人去世之后,怒族原始宗教认为人死之后还有魂,魂魄不能留在故去之地,于是死者家属会请求年长而有权威的男性手执公鸡,为死者送魂指路。在怒族的祭祀歌词中对民族女性的态度饱含着排斥和歧视,怒族女性是不被父权制社会结构所接纳和宽待的。
三、国家的在场与基督信仰中的新女性:自信舒展
在日益严峻的生存压力之下,个体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 当升学、就业等一场场非此即彼的角逐来临之时,昔日同窗将会成为强劲对手。 面对这样的情景,大学生群体极易产生不当竞争心理和行为,不但会影响个体的健康发展,还会对大学生群体的人际关系产生威胁,继而破坏集体凝聚力,集体和集体主义原则就这样“被消解在竞争的酸浴中。”[10]38
结合对老姆登村基督教上层教职人员牧师桑鲁斯和长老以利亚的访谈,证实女性较于男性而言更容易接受并且坚守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桑鲁斯更是指出夏娃和亚当是人类的祖先,并且夏娃是第一个认识上帝的人。通过对老姆登村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访谈,表明基督教这一宗教文化空间是一个被怒族女性广泛接受的精神场域。成年的怒族女性在基督教堂中可以担任基督教徒领袖和传道员等职务,她们在这里自由的开展文体活动,享受平等和救赎。国家在场前提下的中国基督教让怒族女性在民族解放后的基督信仰中找到了更加舒展的宗教文化空间,让女性从原始宗教信仰的压抑和缄默状态中得救。
基督教主张自由、平等、原罪、救赎、博爱,这些思想主张都应和了怒族女性对父权制文化下受打击和受歧视的境遇的反抗。在成熟而系统的基督教信仰文化中,怒族女性得到了新生,她们开始重构女性的精神世界,同时基督信仰也渗透到怒族女性的精神重构中。在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怒族女性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积极转换自身角色,从家庭、经济、信仰、教育等方面参与到民族的精神建构和社会发展潮流中。
从家庭角色上来看,老姆登村怒族女性开始从父权制下昂贵的聘礼交易以及一夫多妻制变成国家主张的自由恋爱和一夫一妻制婚姻。信教者的婚姻在基督教堂举行仪式,并在基督教的特定场所举办宴席,非基督教徒不得参加。绝大多数信教女性都能坚守不酗酒吸烟、不淫乱偷盗等基督教教规戒律,饭前坚持祷告。怒族女性在家庭中担任妻子、母亲、女儿的角色,她将自己和整个家庭的繁荣融为一体,撑起家庭的半边天,她们或是开客栈或是在茶厂务工或是务农致富,没有让自己成为家庭的附庸。怒族女性在家庭角色中开始掌握话语权,实现了在家庭中形象和角色的变革。
在经济角色中,怒族女性能够敏锐地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给怒族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旅游文化的日益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扶持让老姆登村成为著名的怒族文化旅游特色村寨,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为怒江峡谷的怒族百姓带来了机遇。老姆登村姐妹花客栈就是当地开办的第一家民宿,老板是怒族普通女性。即使是信教的妇女,在如密期这样的民间信仰节日中也会到场做点生意,将自己的商品带去节日现场为往来的游客提供便利。怒族女性看准商机,将民族服装、手工艺品、特色美食等推到旅游市场中,为闭塞的村寨旅游注入了活力,推动了老姆登旅游文化的发展。
在怒族民间文学中还有一部分将怒族女性和山神、猎神等神灵联系起来,成为怒族人民崇拜的偶像。流传于匹河乡老姆登村的民歌《祭猎神》讲述古时候有两姐弟,姐姐被山神抓走,弟弟经过千辛万苦找到姐姐,姐姐正在山顶织布,她告诉弟弟不要再找她,她已经嫁给山神为妻,以后打猎时带些酒肉给山神,山神自然不会让他两手空空地回家[6]。怒族民间故事《山神娶妻》同样讲述怒族村寨女子义梅变成山神之妻,庇护亲族百姓,成为怒族人民心中敬畏的神灵偶像[3]。
从教育角色上看,怒族女性获得了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传教士结合拉丁字母及其变形创制了傈僳族文字并在怒江地区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中得以推广,至今傈僳文书写印刷的《圣经》、《赞美诗》等宗教文学书籍仍广为使用。在老姆登村考察过程中发现,怒族女性对傈僳文的掌握极为普遍,基督教传教语言和《赞美诗》的歌唱也均使用傈僳语。1986年和1992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名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6年国家颁布《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女童教育的十条意见》,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也为推动怒族女性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突破性的作用[9]。老姆登村怒族女性中有毕业于南开大学的,也有在省内高校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医疗卫生事业的,她们是最早一批获得高等学位的怒族女性,引领了怒族女性教育角色的勃发。
在信仰角色中,怒族女性积极参与到基督教活动中,在每周三、每周六和周日的礼拜活动中做到了自觉自愿地参与,在每月的圣餐中她们感到幸福和得救。在对老姆登村的信教妇女访谈中,村民阿玉祥认为只要有了基督信仰,生命和永生就被无偿地赐予了,而并非任何其他的缘故,并坦言在几十年的信教生活中有了强烈的生命得救之感。
一位已嫁入怒族村寨二十年的傈僳族妇女表示:“信基督教很好,没有什么坏处。我从小时候开始一直信的,后来我这家开办了农家乐,一般信教的人礼拜天不能杀生,我做着生意,礼拜天有客人,所以我暂时不信。”她介绍说她的父母和公婆都是信仰基督教的,而她也表示在将来不做农家乐生意后也会重新皈依基督教。即使因为某种原因暂时不进教堂礼拜,怒族女性也是对基督教充满着无限向往之情,她们在基督教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属,基督教堂也成为怒族女性重塑精神自由的文化表征。
怒族女性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基督信仰内化到民族心理中,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基底。她们相信自己生来是有罪的,而基督信仰让她们得救,让她们洗清了内心的罪孽感。这种渗透到民族心理的原罪感与民间原始宗教信仰对女性的排斥和歧视是否存在密切联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无疑深入到怒族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中,让她们在潜移默化中更能接受基督信仰的宗教精神。
4.师生互动教学设计。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开发与使用,利用网络技术优势,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任务,在课程讲授方式的设计中应当创设一定的虚拟情境,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情境尽量靠近生活,尽量真实,以激发学生学习、探究、体验的动力。设计师生互动的几个模块和环节,甚至根据学生的即时提问,系统生成学生所需的课件网页。这种“人—机”交互或者“人—人”交互式平台,可以实现师生双方的实时沟通、交流。课后讨论的设计应当引入小组模式,实现分组合作的“学生—学生”的真实交流[6],充分肯定学生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合作精神,从而激发学员学习的积极性,调动其探索知识的欲望,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国家在场的背景下,老姆登村怒族妇女的基督信仰打破了女性在宗教空间的缄默状态。“世界”宗教基督教以其成文的经典《圣经》、《赞美诗》为基础,带着救世学的理念包含或者取代了“原初”宗教在怒族社会中的作用,并且形成了独立的活动场所,即教堂[10]。老姆登基督教堂是教会活动的固定场所,而教会是信仰与仪式活动结合而成的一个独立的道德共同体,教会中怒族女性成员在这里执著共同的信仰和仪式活动[11]。西方基督教在怒族地区的传播让怒族女性获得了精神的舒展和自信,扩大了民族女性的生存空间和心理空间,实现了怒族女性的自我精神重构。怒族女性对基督教的吸纳也有利于实现“外来宗教中国化”,成为基督教在中国边疆地区实现本土化的强大推动力,并成为与原始宗教信仰对峙的一大文化阵地。
四、结语
怒族女性经历了母系社会的精神主导,过度到原始宗教信仰中的父权制文化时,女性的自我精神经过男性的过滤和解释,被湮没在漫长的男权话语历史中。20世纪初传入怒江地区的基督教在与怒族文化的不断接触中,不断重新解释,从而迎合了怒族女性追求平等自由、独立自尊的心理需求,也让怒族女性有了精神上的归属感,得到了怒族女性的广泛认可。在国家在场下的经济新潮流中,怒族女性进一步走出狭隘的小圈子,她们在精神上走向了自由和独立,实现了怒族女性的精神重构。
参考文献
[1]杨宏峰.中国怒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1-3.
[2]张跃,李绍恩.峡谷中的怒族社会[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24.
[3]李昆.怒族独龙族民间故事选[M].昆明:云南省测绘局印刷厂,1989:7-8,13-17,20-22.
[4]刘薇.怒族民间传说中女性形象解读[J].红河学院学报,2017,15(4):49-51.
[5]叶世富,郭鸿才.怒族民间故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36-77.
[6]杨元吉.怒江少数民族民歌集[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4:232.
[7]陶天麟.怒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2):183-189,232.
[8]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方志编写委员会.怒江州志[M].泸水:云南省怒江州民族印刷厂,1998:253.
[9]蒋美华.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89.
[10]菲奥伊·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M].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8.
[11]杜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A].史宗.二十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68.
The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of Nu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Anthropology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Laomudeng Village, Pihe Township of Fugong County
HE Chengjin
(School of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Abstract : In the long course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image of Nu women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thnologist and anthropologist. The Nu ethnic group in China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Lujiang Lisu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Yunnan province. In this paper, Laomdeng village, Pihe township of Fugong county, Nujiang Lisu Autonomous Prefecture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center to study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u women’s self-spirit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anthropology.
Keywords :religious anthropology; Nu ethnic group; women;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ethnology; sacrifice; Christianity
中图分类号: C912. 4; K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63( 2019) 06-0007-05
DOI: 10. 13773/ j. cnki. 51-1637/ z. 2019. 06. 002
收稿日期: 2019-03-27
作者简介: 何城禁(1994—),女,重庆綦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李仲先]
标签:宗教人类学论文; 怒族论文; 女性论文; 精神重构论文; 民族学论文; 祭祀论文; 基督教论文; 母系社会论文; 父权制论文;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