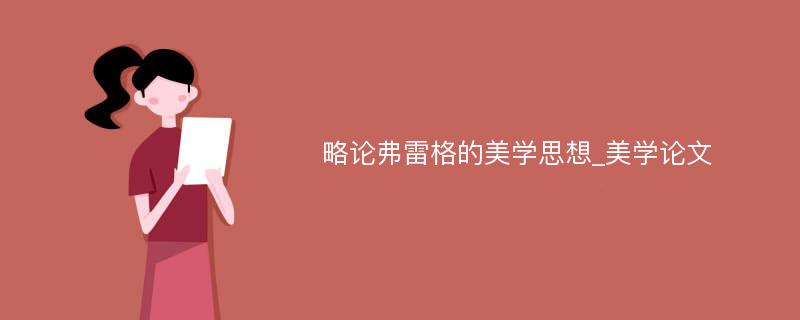
弗雷格美学思想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思想论文,弗雷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83-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6-0065-05
赖特在《分析哲学:一个批判性的历史概述》中指出:“我们世纪的哲学主流之一,被称之为‘分析的’,它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风潮。”① 毋庸置疑,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在此“精神风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哲学观念、理论范畴、思维方式等不仅深刻影响了分析哲学与分析美学的进程,而且对二十世纪以来的哲学、美学、文学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深入而系统,但对其美学思想的研究则比较薄弱,这主要由以下两方面的因素所致:第一,弗雷格未能像康德、黑格尔等那样,留下专门、系统且具有体系性的美学理论著作,其有关美学思想的论述比较零散,散见于相关哲学论著中;第二,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弗雷格有关美学的论述未能如其哲学论述那样富有创新性与深刻性,未能对分析美学的发展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当然,他们并不完全否认弗雷格对分析美学的影响,只是认为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维特根斯坦等人这种间接的方式来体现。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弗雷格对分析美学乃至20世纪西方美学的意义和影响?我们认为,这一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弗雷格有关美学的论述作出清晰的勾勒与恰切的评价,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从其哲学理论、思维方式等方面来探究其对美学理论建设尤其是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设的意义。鉴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具体展开:第一,对与弗雷格美学思想相关的主要哲学观点作扼要论述;第二,对弗雷格相关美学思想作简要概括与评价。
一
客观而言,西方学界对弗雷格哲学的认知并未完全取得共识,主要有如下两种观点:② 第一种观点以达米特(M.Dummett)等为代表,认为弗雷格的哲学是语言哲学,它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哲学时代;第二种观点以克里(G.Currie)等为代表,反对将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化,认为其哲学关注的首要问题是认识的确实性和客观性问题,因此他的哲学是认识论的而非语言论的。如果从弗雷格美学思想这一视角来反观这一问题,其美学思想就很难说是语言论的,恰恰相反,认识论色彩更为浓厚。因此,尽管第一种观点获得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我们不应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看待上述两种观点,这主要是由于弗雷格哲学自身具有异质性、复杂性,它是语言论与认识论的“交织”。不言而喻,弗雷格的思想不仅对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哲学的主要理论问题与方法诸如逻辑形式问题、意义问题和指称问题等来自于弗雷格。因论题所限,我们无意在此就这一问题以及其哲学的主要问题作全面论述,而把阐释的重心放在与其美学思想密切相关的主要哲学理论问题上。在语言哲学看来,一切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同理,作为哲学部门之一的美学问题自然也是语言问题。语言哲学对哲学问题进行语言分析有“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两种主要方式,前者以弗雷格为代表,后者以摩尔为代表。在我们看来,弗雷格的“形式语言”和“意义”理论对分析美学以及20世纪其他美学理论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深刻影响。
弗雷格在1879年的《概念文字——一种摹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形式的语言》中提出了“形式语言”理论,开创了对语言、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先河。弗雷格认为,所谓的形式语言即“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而“形式语言”的提出则源于“日常语言”某些难以避免的不足和缺陷:“最重要的是必须使推理串完美无缺。当我致力于满足这种最严格的要求时,我发现语言的不完善是一种障碍,在现有各种最笨拙的表达中都能出现这种不完善性,关系越是复杂,就越不能达到我的目的所要求的精确性。概念文字的思想就是由这种需要产生出来的。”③ 在弗雷格看来,传统语言的缺陷主要是由于其在逻辑上是不完善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它不能满足正确思维所要求的“一义性”;语言中恰恰没有严格确定的推理形式的范围,以致无法将语言形式方面完美无误的进展与省略了中间步骤区别开来。④ 换言之,传统逻辑无法达到认识的精确性,其中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即“逻辑总是过分紧密地同日常语言和语法结合在一起”,⑤“人们一再感到缺少一种既可以避免别人的曲解又可以避免自己思想中错误的工具。这两个问题的原因都在于语言的不完善。”⑥ 基于此,弗雷格针对在逻辑、哲学等领域中盛行的心理主义等方法论倾向,强调应对逻辑与心理学、逻辑与语法作严格区分,反对把逻辑心理学化,“对逻辑进行心理学的处理起因于一种错误,认为思想(判断,正象人们通常所说,)和表象一样是心理学的东西。这样必然导致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对逻辑进行任何心理学的处理都是有害的。”⑦“为了排除各种误解,为了使人们不混淆心理学和逻辑学之间的界线,我规定逻辑的任务是发现实真的规律,而不是把某物看作真的规律或思维规律。”⑧ 这一主张与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提出的三项基本哲学原则一脉相承:“要把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意谓,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意谓;要时刻看到概念和对象的区别。”⑨
正如研究者所论,弗雷格的形式语言理论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弗雷格在句子表达的内容和对句子表达内容的判断之间作出了区分,从而使逻辑学和心理学区别开来;第二,弗雷格打破了由概念、判断、推理等构成的传统逻辑体系,以函数和自变元构成其谓词演算系统,初步建立了现代逻辑的体系结构。⑩ 概言之,形式语言理论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方法,其“任务在于澄清问题和论断,而不在于提出特殊的‘哲学的’论断,这种澄清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区别开来了。”(11)
对意义的哲学分析是弗雷格对语言哲学的主要理论贡献之一,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1892年的《论意义和意谓》一文中。在意义和所指(意谓)关系这一问题上,分析哲学阵营内部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以弗雷格为代表,认为意义和所指两者完全不同,不可混淆;另一种以罗素为代表,认为意义和所指完全同一,意义即所指。弗雷格关于意义和意谓的理论论述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对后来的语言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在此主要围绕意义和意谓、意义和表象以及意义、意谓、表象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作简要论述。
首先,弗雷格非常明确地把符号的意义与符号所指称的对象即意谓(所指)区别开来:符号(sign)—意义(sense)—意谓(reference)。意义和意谓两者之间呈现为如下关系:“对于一个符号(名称,词组,文字符号),除要考虑被表达物,即可称为符号的意谓的东西以外,还要考虑我称之为符号的意义的那种其间包含着给定方式的联系。因此,尽管在我们的例子中,‘a和b的交叉点’和‘b和c的交叉点’这两个表达的意谓是相同的,它们的意义却不同。‘昏星’和‘晨星’的意谓相同,但意义却不同。”(12) 弗雷格以“昏星”和“晨星”为例强调指出,不能把符号的意义与符号的意谓混淆甚至等同,“昏星”和“晨星”两者虽然指向同一个“意谓”,但各自的“意义”完全不同。此外,弗雷格认为,对于某些符号只有意义而没有意谓,比如独角兽、方的圆等,对于另外一些符号不仅有意义而且有意谓,比如金山、红海等。相比,前者具有意义,但没有意谓,后者有意义而且也有意谓。
其次,弗雷格强调指出,应把符号的意义、意谓和表象进行严格区分。在此之前,十分有必要对弗雷格的表象概念及基本特征作出较为准确的界定与梳理。那么,何谓表象?一般而言,表象是心理学概念。但是,弗雷格是在探讨逻辑真值时提出这个表象概念的,因此与传统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而言,一般所说的表象是在直观的同时形成的,是未经概念整理的心理图像,而弗雷格所说的表象则是非直观时意识中所出现的回忆性的图像,“表象指一种幻象,它与直觉不同,不是通过眼前的知觉而形成的,而是通过过去的知觉或活动的再现而形成的”,(13) 它是“一个与外部世界不同的内在世界,即一个感官印象、想象力创造物、感觉、感情和情绪的世界,一个愿望、倾向和决断的世界。为了简明的表达,除决断以外,我用‘表象’这个词来概括这些。”(14) 在弗雷格看来,由内在性与主观性构成的表象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表象不能被看见或摸到,也不能被闻见、被品尝,也不能被听见,如一个人看见一片绿色草坪,同时有了绿色的视觉印象但看不见它;第二,表象可被拥有,人们有感觉、感情、情绪、倾向、愿望,一个人具有的表象属于他意识的内容;第三,表象需要一个承载者,相比之下,外界事物是独立存在的,你我同时看见一块草坪,但各自拥有一个绿色的视觉印象;第四,每个表象只有一个承载者,两人没有同一个表象,我自己是表象的承载者,但本身不是表象。(15)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意谓意义和表象三者之间究竟有何本质性区别?弗雷格认为,“如果一个符号的意谓是一个感官可以感觉的对象,那么我对它的表象就是一幅根据我所曾有过的感觉印象和我所做过的内在和外在活动的记忆而形成的内在的图像。这幅图像常常浸透着感情,其各个部分的清晰性均不相同,也不确定。同一个意义即使在同一个人那里也并非总是与同一个表象结合在一起。表象是主观的;一个人的表象不是另一个人的表象。因此与同一种意义联系在一起的表象自然就有各种各样的区别。……以此,表象与符号的意义就有了根本的区别,符号的意义可以为许多人共有,因而不是个别心灵的部分或形式。人们大概不能否认,人类有共同的思想财富,它代代相传。”(16)
再次,弗雷格对符号的意义、意谓和表象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十分清晰的论述:“一个专名的意谓是我们以它所表示的对象本身;而我们同时所有的表象则是主观的。在二者之间是意义。它尽管不再象表象那样是主观的,但也不是对象本身。”(17) 为了说明问题,弗雷格给出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有人用望远镜观察月亮。我把月亮本身比做意谓。月亮是观察的对象,而观察是通过望远镜内的物镜所显出的真实图像和观察者视网膜上的图像为中介的。我把前者比做意义,我把后者比做表象或直观。望远镜中的图像只是片面的,它取决于观察方位,但是尽管如此,它却是客观的,因为它可供许多观察者使用。必要时可以安排得使许多人同时使用它。但是,视网膜里图像却是各人有各人自己的。”(18)
总之,正如西方学者所论,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对原有的语义结构进行了创造性置换,即把传统的sign—referent语义模式转化为现代的sign—sense—referent模式,强调意义自身的客观性与独立性。(19)
二
在对弗雷格的形式语言和意义理论作扼要论述后,我们再来看弗雷格本人有关美学问题的基本理论观点。需要指出的是,弗雷格并未将其形式语言理论具体运用到他本人关于美学问题的相关论述中,这一理论只是在此后的分析美学中才得以实践。我们在此主要论述弗雷格意义理论在美学问题上的具体实践。概言之,弗雷格把美学所研究的问题归于表象层,认为美不是“意谓”也不是“意义”,而是一种“表象”,也就是说,美是一种个人性、主观性的东西。
众所周知,肇端于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根本特点在于,它不以思辨的而以语言分析的方法探究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它不把概念而是把句子作为思考相关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不是“语词”理论而是“句子”理论。具体而言,句子的思想即意义,句子的真值即意谓;所谓真值,就是对句子的意义所做的或真或假的判断,逻辑学就是关于真值的理论。与逻辑的“求真”不同,美学和艺术是“求美”,即对“真值”的探究是逻辑而非美学的理论使命。弗雷格以“奥德赛在沉睡中被放到伊萨卡的岸上”为例指出,“情况并非总是这样。比如,聆听一首史诗,除了语言本身的优美声调外,句子的意义和由此唤起的想象和感情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若是寻问真这一问题,我们就会离开艺术享受,而转向科学的思考。这里只要我们把这首诗当作艺术作品而加以接受,‘奥德赛’这个名字是否有一个意谓,对我们来说就是不重要的。因此对我们来说,追求真就是努力从意义推进到意谓。”(20) 换言之,弗雷格认为,对句子而言,不仅有意谓即真值,而且还有意义、想象、情感等,比如,美学、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断定只是一种“虚假断定”即虚构:“文学旨在假象,譬如绘画也是这样。在虚构中断定不会得到认真对待,这里仅是虚假断定;甚至思想也不会象在科学中那样得到认真对待:这里只有虚假思想。如果应该把席勒的《唐·卡洛斯》理解为历史,那么这个剧的很大部分都是假的。但是一个文学作品绝不会得到这样的认真对待;它是戏剧。这里的专名也是虚假专名,尽管它与历史人物的名字一致;它们在这里不应得到认真对待。一幅历史画也有类似情况。它作为艺术品绝不要求使我们看到真实过程。一幅图画若是像摄影一样准确地表现出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就不是较高意义的艺术品,而最好比作一件科学作品的复制解剖品。”(21) 弗雷格进一步指出,“戏剧里的雷声只是虚假的雷声,只是虚假的战斗一样,戏剧里的断定也只是虚假的断定,这只是表演,只是文学创作。处于自己所扮演角色的演员没有断定,也没有撒谎,即使他说了一些他相信是假的东西。在文学创作中有这样的情况,一些思想被表达出来,虽然它们采用断定句的形式,却没有被认为是真的,尽管甚至可能会导致听众作出一个赞同的判断。因此,对于形式上表现为断定句的东西也应该总是问它是否确实含有一个断定。……一个断定句除含有一个思想和断定之外,还常常会有与断定无关的第三种成分。这种成分常常能够影响听者的感情、情绪或激发听者的想象力。”(22) 弗雷格认为,区别逻辑、科学与美学、艺术的标准即是否有“意谓”:“对于科学来说,一个句子仅有一种意义,这是不够的;它必须带有一个真值,我们称这种真值为句子的意谓。如果一个句子只有一种意义,而没有意谓,它就属于虚构,而不属于科学。”(23) 这是因为,美与真分属美学与逻辑这些不同的领域,“诗歌中可以称之为情调、魅力、闪光的东西,通过音调和韵律所表现的东西,不属于思想……逻辑学家认为无关重要的东西,对于语言中为了美而追求的意义来说,可能恰恰表现为重要的东西”,(24)“句子不仅限于一个思想和断定它的真。在许多情况下,句子还应该影响听者的表象和感情;而越是接近诗一般的语言,这种作用就越大。……对于诗人来说,有不同的语词可供选择使用是很有价值的,这些语词能够相互代表,而不改变思想,却能以不同方式影响听者的表象和感情。”(25)
概言之,在弗雷格看来,思想的判断之真与美学的表象之美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第一,思想和表象根本不同,前者是真的领域,后者则是美的领域:“思想不是表象并且不是由表象这样的东西构成的。思想和表象是根本不同的。通过表象的结合绝对形不成可以是真的东西。思想的实际表达工具是句子。这种工具不适于描述表象。而绘画和音乐不适于表达思想”,(26)“正象‘美’这个词为美学、‘善’这个词为伦理学指引方向一样,‘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27) 此外,弗雷格认为,表象是表象者专有的,思想与此不同,它不是思想者专有的,思想是无个性的东西;思考不产生思想,而是把握思想,思想不是有空间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思想就其本质而言是非时间性非空间性的东西。第二,真没有程度之别,而美则有程度之别:“比较‘真’这一谓词与‘美’。后者有程度,前者没有程度……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对象是美的,但是其中一个更美。相反,如果两个思想是真的,那么一个不会比另一个更真。”(28) 第三,真的存在是自足的,而美的存在则需要人的在场:“美的东西仅对那些感到它美的人才是美。对于审美力不必争论。真的东西凭自身是真的;没有东西凭自身是美的”,(29)“真的东西不依赖于我们的承认而是真的,而美的东西仅对于觉得它美的人才是美的。……涉及真的地方可能会有错,但涉及美的地方却不会有错。正因为我认为某物是美的,它对我来说就是美的。……任何东西都不依自身是美的,而总是对于感觉到它的人才是美的,并且在关于美的判断中必须始终把这一点考虑进去。”(30)
我们认为,在研究弗雷格美学思想的过程中,应严格区分弗雷格对有关美学问题的具体论述和他的哲学理论、哲学方法对分析美学的影响,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从上述论述中不难发现,弗雷格本人在阐释有关美学问题时,要么没有要么未能“正确”地将其哲学理论、哲学方法运用到具体美学问题。比如,弗雷格的形式语言理论其实可以对美学问题从语言角度进行逻辑分析,以此来颠覆传统美学的问题及相关论断,为美学研究开拓一种新的研究方向。令人遗憾的是,弗雷格本人没有在美学领域进行这样的具体实践。再比如,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其实可以从意义角度对美学问题进行哲学分析,从而为美学研究开拓出另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公允地讲,弗雷格确实将其意义理论非常自觉地具体运用在对美、真等问题的论述中。但是,更令人遗憾的是,弗雷格是对其理论存在严重的“误用”,他用一个十分现代的理论方法论证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美学命题即没事主观的、审美趣味无争辩。我们认为,这一“误用”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理论失误,它直接影响了此后分析美学的发展方向。毫无疑问,美确实需要“意谓”的感性激发,但美不是意谓;美也确实需要表象的“介入”,但美不是表象;意谓和表象属于审美活动中的客体与主体,它们只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前提和条件,美既不是客体也不是主体,但美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即美是某种意义。如果以弗雷格的意义理论来审视,美不属于意谓层也不属于表象层,美属于意义层,弗雷格的“误用”之处就在于把应属于意义层的美归属在表象层。此外,弗雷格在论述逻辑之“真”、伦理之“善”和美学之“美”的过程中,对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还不够辩证,有将三者截然对立、刻意割裂的理论嫌疑。在我们看来,弗雷格对分析美学乃至美学的发展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不在于其关于美学问题的具体论述,而在于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范畴,进而将美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过,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限制,更由于对弗雷格哲学理论的了解不够,客观上影响了我们对弗雷格美学思想的相关研究,本文对弗雷格美学思想的理解只是初步性的,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还有很多疏漏之处,这是在以后的相关研究中需要努力克服的。
注释:
① [芬兰]乔治·亨里克·冯·赖特:《分析哲学:一个批判性的历史概述》,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② 详见王路:《世纪转折处的哲学巨匠:弗雷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页。此外,参见Chripin Wright,ed.Frege:Tradition and Influence(New York,1986),p185-243.
③⑤ 《概念文字》,《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4页。
④ 具体见《论概念文字的科学根据》,《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8-39页。
⑥ 《论概念文字的科学根据》,《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7页。
⑦ 《逻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0-206页。
⑧ 《思想》,《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4页。
⑨ [德]G·弗雷格:《算术基础》,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9页。
⑩ 《译者序》,《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8页。
(11) [奥地利、美国]汉斯·汉恩、奥拓·纽特拉、鲁道夫·卡尔纳普:《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01-202页。
(12)(16)(17) 《论意义和意谓》,《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1、93、94页。
(13) 《逻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85页。
(14) 《思想》,《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3页。
(15) 以上具体见《思想》,《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3-134页。
(18)(20) 《论意义和意谓》,《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6-97页。
(19) 详见Maurita J.Harrey:Intentionality,Sense and The Mind(the Hague:1984),p.40-46。此外,胡塞尔也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出发也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即以act-noema-object取代act-object模式,体现了它们作为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在思维方式层面的整体超越。
(21) 《逻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85页。
(22) 《思想》,《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8-119页。
(23) 《数学中的逻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78页。
(24)(27) 《思想》,《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主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9-120、113页。
(25)(26)(28)(29)(30) 《逻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5-196、179、179-186、179-180、186页。
